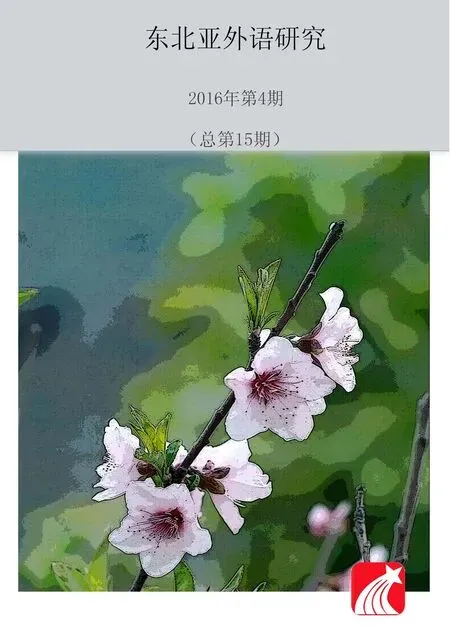学术主持人语
学术主持人语
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论提供了这样一个悲观的结局,人的本我以快乐为原则,人本身就是非理性的动物,由这种非理性动物组成的社会在自我和超我的监控下,实际上汇聚着众多戴着人格面具的精神上有问题的人。据此推论,社会发展必然是非理性的,结局注定是悲剧性的。如果把社会发展比作一列疯狂行驶的列车,而人类是其中的乘客,那么列车之所以能够停下来的唯一原因是乘客控制了列车。但实际上乘客因为自身人性的缺陷,所以不想或者也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
生态文学所描述的正是来自不同地域的乘客对自然戕害后的诗意反思。还好,人除了要求当下满足的本我,还有追求自我完善的理性和具有强制性的法律及道德意义上的超我。在面对满目疮痍的自然,文学以深邃的目光凝视自己的所作所为。《夜猎》中的安东之所以从高速行驶的火车上纵身跃下,看似自戕的行为,实则是他希望用自己的理性来制动国家机器这列疯狂的列车,遗憾的是,安东体内残存的理性不足以扼杀他心中翻卷的动物本能,最终使得他所居住的空间变成难以立足的人间地狱,诚如《自然不存,人之安在?——论生态伦理观照下〈夜猎〉中的反乌托邦图景》的作者所言,在人可以猎杀同类的世界里,真正的上帝并不是存在于“神圣文本”之中,上帝就是安装了红外瞄准镜的狙击枪。可以设想,如果人类不能有效遏制自身的欲望,噩梦般的未来或许真的存在。诗意的反思说明,人类或许还有希望,尽管希望渺茫。
当然,生态并不仅仅是自然生态,文化的异化也可以导致人文生态的扭曲,社会看似波澜不惊,人人似乎平安无事,日子好像歌舞升平,谁知道在安静祥和之下又深藏着怎样的罪恶?《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下的〈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给读者提供了在女性生态主义观照下的世界图景。依论文作者之见,在拉斯普京的作品《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中隐藏着与“道法自然”契合的话语,具体而言,人类所有活动都应当在“道”这种形而上最高实体的关照下遵循万物本身的规律。作者通过俄罗斯文化中对女性的形而上意义的想象,发现了在拉斯普京这部小说中女性和自然的神秘关联,从而得出伤害女性就意味着伤害自然的结论。
如果说上述两篇文章侧重点在当下,那么《俄罗斯白银时代生态创作思想探析》一文则强调“生态意识”存在于俄罗斯民族的精神结构之中,而白银时代的文学使得“人与自然”这一传统主题通过文学创作得以延展。不过,借助这篇论文我们看到,20世纪初尽管人们心存危机感,但总体来说,俄罗斯的大自然充满了生机,其存在的价值之一就是勾起布宁们的思乡忧伤,片片白桦林让叶赛宁得以成为“大自然的器官”。尽管如此,科技的进步已经让人们意识到一股“暗黑力量”正在袭来,布尔加科夫笔下的“生命之光”让莫斯科狂蟒成灾也不是没有可能。
也许,我们的邻国日本对自然有着不同于俄罗斯的思考方式,论文《处所意识的重新建构——有吉佐和子〈复合污染〉之生态批评解读》以“本处”(place)为突破口,通过对该词意义的去蔽以及对《复合污染》与美国作家的《寂静的春天》互文性的深度解读,来阐释日本和平年代的“战争”、民众的生态苦难和全球生态系统的生态危机所能产生的反乌托邦图景。日本作为身处东方的“西方国家”,早已经在许多方面影响了全球的生态,论文作者敏锐地意识到该小说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即对生态伦理的坚守,绝不是个别国家所能完成的任务。在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蝴蝶效应无处不在。
——郑永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