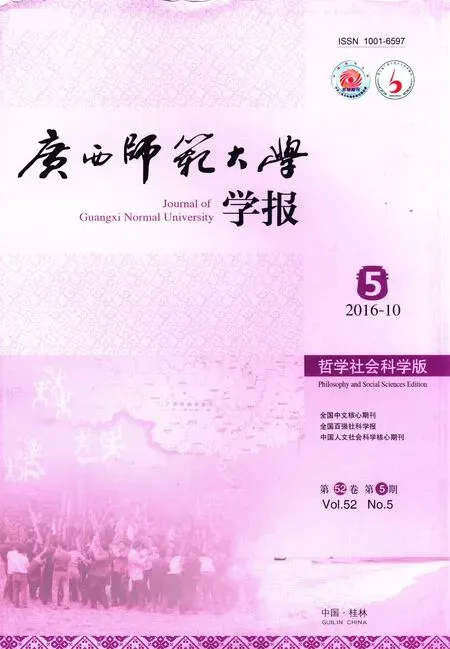儒者化的庄子
——王安石的庄学思想
张 娜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儒者化的庄子
——王安石的庄学思想
张 娜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王安石“以儒解庄”的解读思路开拓了宋代庄学的视野。在其专论《庄周》中,庄子以儒者的面目出现,文中指出庄子之用心是为了矫时之弊,庄子是圣人之徒,《庄子》之书“特有所寓而言耳”。不过庄子的形象在王安石那里并不是统一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从无为到有为的过程,这与王安石个人的思想发展及为政治改革寻求理论根据有关。王安石谈性命道德的风气影响了其解庄思想,称“庄生之书,其通性命之分”,其子王雱对庄学的性命解读也可视为继承王安石思想的表现。从庄学诠释史来看,“以儒解庄”的理念自魏晋时向、郭已有发展,王安石起到了过渡作用,既开启了宋代庄学普遍儒学化的倾向,又为明末清初的“庄子儒门说”作了铺垫。
王安石;庄子;以儒解庄;庄周;性命道德
王安石是宋代庄学史上一个绕不开的人物。就宋代的理学家来说,他们大都有出入老释的经历,或明或暗汲取佛道思想,对《庄子》多有关注,王安石尤为突出。王安石习染道家学说,喜嗜《老子》《庄子》,且不拘一格,以儒解庄,肯定庄子之用心是为了矫俗之弊,庄子亦有为,庄子的性命之学与圣人相通,开启了宋代解庄“儒学化”的风潮。
一、《庄周》中的庄子
注《庄子》由来已久,自魏晋至隋唐,注《庄子》论《庄子》者纷纷涌现。叶梦得称:“自熙宁以来,学者争言老庄”[1]。宋代庄学的繁盛与王安石注《老子》解《庄子》密不可分。郎擎霄也指出:“庄学得王、苏之提倡,故当时治《庄子》者已次第臻于极盛,而《庄子》之学遂如日之中天矣。”[2]337
王安石对《庄子》一书颇为重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五载王安石著有《庄子解》四卷,可惜已佚。目前能够探知王安石庄学思想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王安石的庄学专论《庄周》上下篇,现存的《王文公文集》、《临川先生文集》中有一些直接或间接论述庄子思想的文章,如《九变而赏罚可言》、《答陈柅书》、《答王深甫书》、《季子》等以及诗歌《杂咏八首》、《无营》、《绝句》之五、《绝句》之八、《陶缜菜示德逢》等;二是王安石多次引《庄子》注《老子》,这也为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三是其子王雱继承了王安石的庄学思想,也可以视为了解王安石庄学理论的一个途径。
在《庄周》中,王安石首先列出世人论庄的不同观点,指出无论是好庄者还是学儒者都没能真正理解庄子的真意。
世之论庄子者不一……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尝求庄子之意也。好庄子之言者固知读庄子之书也,然亦未尝求庄子之意也。[3]311
通过学儒者与好庄者之间的激烈争论可以看出儒家思想与庄子思想之间似乎存在水火不相容的对立。学儒者认为“庄子之书,务诋孔子以信其邪说”[3]311,这一观点可以追溯到司马迁在《老子韩非列传》中谈庄子:“庄子……作渔夫、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4]394好庄者则百般护着庄子,认为庄子“以为仁义礼乐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耳”。[3]311王安石指出这两种传统的论庄观点都偏执一言,未能把握庄子的真意。那么庄子的真正精神到底何在?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王安石提出了两个解读庄子的方法:一是知人论世,二是以意逆志。
昔先王之泽,至庄子之时竭矣,天下之俗,谲诈大作,质朴并散,虽世之学士大夫,未有知贵己贱物之道者也。于是弃绝乎礼义之绪,夺攘乎利害之际,趋利而不以为辱,殒身而不以为怨,渐渍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庄子病之,思其说以矫天下之弊而归之于正也。其心过虑,以为仁义礼乐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齐彼我,一利害,则以足乎心为得,此其所以矫天下之弊者也。……然而庄子之言不得不为邪说比者,盖其矫之过矣。夫矫枉者,欲其直也,矫之过,则归于枉矣。[3]311-312
王安石将庄子还原到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中来考量其学说的时代精神指向。这是运用孟子“知人论世”*出自《孟子·万章章句下》,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土,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的方法揭示了庄子所处的特殊时代环境。随着世风日降、礼崩乐坏,世人只知尔虞我诈、趋利避害,全然不知贵己贱物的道理,抛弃了圣人之法。庄子深恶痛绝这种现象,因此才“思其说以矫天下之弊而归之于正也”。从时代背景来分析,王安石认为庄子并不是人们口中所谓的消极避世者,相反庄子清楚地意识到时弊,试图以其说改变礼崩乐坏的现实,使社会归于“正”,即儒家话语体系下以仁义礼乐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在王安石的论述中,与以往的隐士形象不同,庄子呈现出一个积极入世、殚精竭虑的儒者形象。但是单凭此不足以解释《庄子》中所存在的弃绝礼义、剽剥儒墨的言论,王安石给出的辩护理由是“其心过虑,以为仁义礼乐皆不足以正之”,即庄子时代的积弊甚多,儒家的仁义道德并不能真正起到矫正的作用,所以庄子不得不提出要泯是非、齐万物,专注于内心的精神,这并不是专门以弃绝仁义来对抗儒家。不过王安石承认这样做的副作用也是明显的,庄子之说矫枉过正则偏向邪说,但必须肯定的是庄子本质上仍出于治世的考虑。
接着,王安石给出了一个“骇人之论”,庄子用心是圣人之徒:
既以其说矫弊矣,又惧来世之遂实吾说而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也,于是又伤其心于卒篇以自解。其篇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观之,庄子岂不知圣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用,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皆有所长,时有所用”。用是以明圣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书于宋钘、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为不该不徧一曲之士,盖欲明吾之言有为而作,非大道之全云耳。然则庄子岂非有意于天下之弊而存圣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矫于天下者也。庄子用其心,亦二圣人之徒矣。[3]312
从这段话中,可以归纳出王安石论证这一点的理由:其一,庄子“知圣人”,主要表现在精通儒家典籍。在《天运》篇中庄子首倡“六经”之名,且对其宗旨把握相当到位,所谓“《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足以说明庄子对儒家思想的深刻理解。其二,庄子维护儒家的崇高地位,主要体现在知“圣人之道全在彼而不在己”,承认自己是“百家众技之流”、“不该不徧一曲之士”,尊儒家为道术之大观,把自己和其他各家都放置在儒家之下。由此顺理成章推出庄子“有意于天下之弊而存圣人之道乎”。王安石甚至以伯夷、柳下惠比况庄子,认为庄子的用意与此二子相同。这就近于将庄子归入儒门之下。另外,王安石强调不应该局限于表面上的文字或行为,而要“善其为书之心,非其为书之说”,即以善意推测庄意,而不要以强调儒道之异为贵。依王安石,从庄子为书之心来看,庄子的目的在于矫正时弊,庄子的真精神与要传承圣人之道的儒家相通。
另一方法是“以意逆志”。王安石认为要以孟子“以意逆志”的方法重新诠释庄子,世人之所以非庄的一个原因是“不以意原之”。如果能运用这种方法观庄子,就会发现庄子并非恶意诋毁儒家圣人,而是“有所寓而言”:
学者诋周非尧、舜、孔子,余观其书,特有所寓而言耳。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读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为周者之所以诋也。周曰:“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而为天下用。”又自以为处昏上乱相之间,故穷而无所见其材。孰谓周之言皆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间,而遭世遇主,终不可使有为也?及其引太庙牺以辞楚之聘使,彼盖危言以惧衰世之常人耳。夫以周之才,岂迷出处之方而专畏牺者哉?盖孔子所谓隐居放言者,周殆其人也。[3]312-313
庄子《天道》中有“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而为天下用”,主张君主无为而臣有为,说明庄子并非不知君臣父子之义,然而因生逢乱世,其才无法施展,反其道而行之,隐居自保,成为孔子所谓的“隐居放言者”。这种做法事实上应和了孔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思想,如此看来,庄子之行与圣人之道相符。善读庄之人能得意忘言,读懂字面背后的真实意图,这是庄子希望读者能做到的。但庄子忽略了一点,孔子有言“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庄子不区分言说对象,一概“不详而略”,终使天下陷于困惑之中,由此得罪了圣人之徒。王安石在此表面上指出庄子所犯的错误,实则为庄子辩护,阐清庄子为人所误解的原因,证明庄子其实用心与圣人无异。
可见,在王安石的解读中,庄子的传统形象被颠覆,从超然离世的隐士变成了心系天下、因郁郁不得志而“无道则隐”的儒者。其言行虽与儒者异,但其本意与圣人同,可归为伯夷、柳下惠之流。概而言之,如果能通过“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方法去重新审视庄子,以得意忘言的方式去理解,就能发现庄子的真精神与儒家的大道是一致的。
二、无为有为之间的庄子
王安石在《庄周论》中构建出一个儒者式的庄子。这种构建是从方法和内容两个方面着手,上文已详细分析了王安石运用孟子“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方法去把握庄子本意的过程。从内容上来说,王安石的意图在于通过此分析框架达到世人对庄子形象的转观,即儒者式的庄子。儒、道核心区别之一在有为与无为。我们看到王安石竭力调和儒道,拉近道家与儒家的距离,指出庄子讥讽孔子的话多为寓言,实则尊孔子,庄子毁弃仁义并非本意,而是为了矫时之弊。这一切最终都指向一点:庄子其实是有为的,《庄子》本质上是圣人之用心,只不过矫枉过正了而已。所以王安石在内容上是通过建构有为的庄子来达到诠释儒者式庄子的目的。
众所周知,王安石的庄学思想并不局限于《庄周》,其他材料中也存有王安石论庄的言论。那么,王安石的庄学思想中,庄子的形象是否为统一的儒者式形象?如果不是,为何会有变化?只有仔细考虑这些问题,才能真正理解王安石“以儒解庄”的目的所在。
王安石对庄子的态度在其早期诗歌中多有反映,如:
圣贤何常施,所遇有伸屈。曲士守一隅,欲以齐万物。丧非不欲富,言为南宫出。世无子有子,谁敢救其失。[3]456
赐也能言未识真,误将心许汉阴人。桔棒俯仰何妨事,抱瓮区区老此身。[3]806
第一首诗否定了庄子齐物论的观点。第二首则批评《庄子·天地》中汉阴老人舍机械不用而保真思想的寓言故事,王安石认为他抱瓮灌圃、用力甚多而见功寡,终身碌碌无为。《季子》有评价庄子的部分:“昔庄周丧其妻,鼓盆而歌;东门吴丧其子,比于未有。此弃人齐物之道,吾儒之罪人也。观季子之说,盖亦周吴之徒也。”[5]王安石指出庄子鼓盆而歌的做法是弃人齐物之道,是把人当成物来看,表示出一个儒者对道家死亡观的愤慨指责。而在《答王深甫书三》有语:
期于正己而不期于正物,而使万物自正焉,是无治人之道也。无治人之道者,是老、庄之为也。所谓大人者,岂老、庄之为哉?正己不期于正物者,非也;正己而期于正物者,亦非也。正己而不期于正物,是无义也;正己而期于正物,是无命也。是谓大人者,乞顾无义命哉?扬子曰:“先自治而后治人之谓大器。”扬子所谓大器者,盖孟子之谓大人也。物正焉者,使物取正乎我而后能正,非使之自正也。[3]83
王安石在此明确批判老庄的无为而治,“期于正己而不期于正物”是老庄的做法。无论是“正己而不期于正物”还是“正己而期于正物”,都是弃“义”或“命”的表现,儒家兼顾义和命,所以孟子所说的“大人”则不为。至于如何正物,王安石认为儒者的做法是“使物取正乎我而后能正,非使之自正也”,此即以儒家的有为标准去衡量道家的无为之治,对老庄之道表现出严厉的批评态度。
由此可知,在王安石眼中庄子仍然是超然无为的道家形象,批判庄子的无为之治是王安石此时的主流思想。要注意的一点是这些言论作于王安石为相之初,他积极主张变法,强调有为作风以及强劲的入世精神,庄子的无为思想与此格格不入,需要大加批判。但是熙宁变法遭受挫折之后,王安石开始重新审视老庄的无为思想,对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比如他解读《老子》时常采用老庄互证:
惟善摄生者则能无我,无我则不害于物,而物亦不能害之矣。庄子曰:“人能虚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6]44
侯王守道,则无为也。万物将自化于道,故无不为也。庄子:“无为而万物化”。[6]37
且圣人之于百姓,以仁义及天下,如其仁爱及乎人事,有终始之序,有死生之变,此物理之常也。此亦物理之常,非圣人之所固为也。此非前爱而后忍,盖理之适焉耳。故曰不仁乃仁之至。庄子曰:“至仁无亲”,“大仁不仁”,与此合矣。[6]10
庄子曰:“怪人以必不必,故无兵。众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勇于敢,以不必必之,故多兵而杀。勇于不敢,以必不必,故无兵而活。[6]57
上述引《庄子》之语注《老子》为我们理解王安石的庄学思想提供了一个侧面。文中他指出老庄都是讲虚己无为的,所谓养生之无我、存身之游世、为政之不仁皆是无为的表现,但只有无为才能达到无不为的目的。换言之,无为只是有为的一种方式。从这一层面来看,庄子实质上是讲有为的。可见庄子的形象开始出现从无为到有为的转变。在《庄周》中庄子则完全是有为的,所谓“周曰:‘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而为天下用’。又自以为处昏上乱相之间,故穷而无所见其材。孰谓周之言皆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间,而遭世遇主,终不可使有为也?”[3]313庄子实则精于进退之道。
至此,王安石通过对无为的庄子进行有为的阐释,完成了儒道之间的调和。这中间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说明庄子的形象在王安石那里并不是固定的。一般来说王安石关于庄子的看法前后不一致,对庄子的态度早期否定多于肯定,后期则肯定多于否定。至于当中的原因固然与王安石个人对庄子认识的深入程度有关,但结合具体社会背景来看,其中的转变与政治改革有密切联系。
北宋实行士大夫政治,凸显出士大夫的话语权,经由范仲淹等砥砺士风,学者们大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士大夫们企求“回到三代”,建立一个贯通内圣外王的人间秩序,反映到宋学中即体现出鲜明的经世主义倾向,这对宋代的庄学产生了影响。王安石作为熙宁变法的领袖人物,是一位大政治家,自然会考虑前人学说的现实意义。他一方面反对无为而治、因循守旧、沿袭祖宗之法的思想,另一方面又积极地为变法寻求学理上的根据。所以,我们看到王安石早期否定庄子,撇清儒道界限,倡导积极有为的政治。对于北宋来说,道、佛思想盛行,道家思想成了唾手可得的可借鉴资源之一。在赵宋王朝推行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文化政策下,王安石力求将《庄子》变成有益于治世的著作,对庄子儒学化的解读也就顺理成章了。
《庄子·天道》有云:“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此段话旨在表达主上无为,臣下有为,以无为为尊,以有为为卑,治国之道要次第有序,要以无为为本的意思。但王安石的解释如下:
尧者,圣人之盛也,孔子称之曰:“惟天为大,惟尧则之”。此之谓明天;“聪明文思安安”,此之谓明道德;“允恭克让”,此之谓明仁义;次九族,列百姓,序万邦,此之谓明分守;修五礼,同律度量衡,以一天下,此之谓明形名;弃后稷,契司徒,皋陶士,垂共工,此之谓明因任。三载考绩,五载一巡符,此之谓明原省。命舜曰“乃言底可绩”,谓禹曰“万世永赖,时乃功”,“条兹有苗,昏迷不恭”,此之谓明是非。“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谁明”,此之谓明赏罚。[3]325
这就是完全无视《庄子》的本意,将道家的思想内容儒家化。对于《天道》中建立的“天—道德—仁义—分守—形名—因任—原省—是非—赏罚”的序列,王安石表示赞同,同时认为“古之人孰不然”,并强调“古之言道德所自出而不属于天者,未之有也”。[3]325在此基础上,他根据自己的需要从儒家的角度诠释,引用儒家经典《论语》、《尚书》,对这个体系的每个部分做出了相应注解,论述了儒家的政治诉求和社会人伦秩序,传达出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儒者理想。王安石由此吸收并改造了庄子后学的政治思想,使其成为变法的理论支撑。
王安石也对《庄子·天道》中“五变而形名可举,九变而赏罚可言”的观点作了儒学化的阐释和发挥:
弃道德,离仁义,略分守,慢形名,忽因任,而忘原省,直信吾之是非,而加人以其赏罚。于是天下始大乱,而寡弱者号无告。圣人不作,诸子者伺其间而出,于是言道德者至于窈冥而不可考,以至世之有为者皆不足以为,言形名者守物诵数,罢苦以至于老而疑道德,彼皆忘其智力之不蟾,魁然自以为圣人者此矣,悲夫!庄周曰:“五变而形名可举,九变而赏罚可言”、“语道而非其序,安取道?”善乎,其言之也。庄周,古之荒唐人也,其于道也荡而不尽善,圣人者与之遇,必有以约之,约之而不能听,殆将摈四海之外而不使之疑中国。虽然,其言之若此者,圣人亦不能废。[3]325
在这里,王安石指出天下大乱的原因在于没有按照从天道到人道的次序,又“弃道德,离仁义,略分守,慢形名,忽因任,而忘原省,直信吾之是非,而加人以其赏罚”。在《致一论》中他对“语道之序”作了说明:“语道之序,则先精义而后崇德,及喻人以修之之道,则先崇德而后精义,盖道之序则自精而至粗,学之之道则自粗而至精,此不易之理也”[3]341。治理天下的枢机在于根据庄子所谓的“语道之序”来施行仁义、分守以及形名赏罚。
三、性命道德之间的庄子
宋学向来以义理之学著称,义理阐经在内容上表现为重点阐发性命道德之学。《宋史·艺文志》云:“宋有天下,先后三百余年。考其治化之污隆,风气之离合,虽不足以拟伦三代,然其时君汲汲于道艺,辅治之臣莫不以经术为先务,学士绪绅先生,谈道德性命之学,不绝于口,岂不彬彬乎进于周之文哉?”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道德性命之学已成为宋代学术的标签,也是宋代三百年学术精髓之所在。清代蔡上翔也说:“自诸儒讲学,专于道德性命,而学术为之一变。”[7]王安石的新学在北宋影响深远,开启了谈性命道德学说之风气。早在二程理学形成之前,王安石就以性命学说阐释经典。王安石主持编撰的《三经新义》以及他的《字说》等著作,都是言性命之理的。他在《虔州学记》中指出:
先王之道德,出于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于人心。《诗》、《书》能循而达之,非能夺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无也。经虽亡,出于人心者犹在,则亦安能使人舍己之昭昭,而从我于聋昏哉?[3]402
简而言之,依王安石,“性命之理,出于人心”,儒家经典在通达性命之理时只能起桥梁作用,并非能夺性命之理。经书虽然佚失,但凭借着共同的人心,儒生通过经典注疏依然能挖掘出精义。王安石对性命道德的关注反映在他对庄子的解读上。他在《答陈柅书》中说:
庄生之书,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祸福累其心,此其近圣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智矣,读圣人之说,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于周之说,则其为乱大矣。墨翟非亢然诋圣人而立其说于世,盖学圣人之道而失之耳。虽周亦然。韩氏作《读墨》,而又谓子夏之后,流而为庄周,则庄、墨皆学圣人而失其源者也。[3]93
在这里,王安石把《庄子》看作通性命之分的书。庄子强调“不以死生祸福累其心”,这与儒家的乐天知命相似,是近似圣人的行为,表明王安石充分肯定了庄子的通达性命之学。但将死生祸福放置身外需要足够明智,否则沉溺于庄周之说会造成大乱。同时,王安石将庄子与墨子相比,认为二者学圣人之道却“失其源”,并非刻意诋毁圣人,再次肯定庄子。
王安石的《庄子解》已佚不存,我们今天无法得知具体内容,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借《庄子》来阐释道德性命之理。王安石学派门人作品仍多有保留,如吕惠卿、陈详道等人在解《庄子》时,都引入性命道德之理,并成为宋代以道德性命解《庄子》的典型。王安石之子王雱注《庄子》颇有见解,著有《南华真经新传》和《南华真经拾遗》。如王雱说:
庄周之书,究性命之幽,合道德之散,将以去其昏昏而易之以昭昭,此归根复命之说、剖斗折衡之言所以由是起矣。虽然,道于心而会于意,则道问而无应,又奚侯于言者欲?盖无言者虽足以尽道之妙,而不言者无以明,故不得已而后起,感而后动,迫而后应,则驾其所说而载之于后,而使夫学者得意则忘象,得象则忘言,此亦庄子之意有冀于世也。[8]
又云:
庄子之书,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祸福动其心,其近圣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知失。读圣人之说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于周之说,则其为乱大矣。[8]
这两段论述在王安石文集中都有出现,尤其是“庄子之书,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祸福动其心,其近圣人也”与王安石《答陈柅书》几乎一致。可见,王雱强调《庄子》一书讲的是性命道德之说,只有“得意忘言”,才能真正了解和把握这种思想。他无疑继承并借鉴了王安石的庄学思想。由此,我们可以认定王安石的思想在王雱的庄学论著中有所体现,王雱的论述是认识王安石庄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
王安石父子都以道德性命注解《庄子》,并引领了宋代以儒解《庄子》的风潮。赵秉文说:“自王氏之学兴,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谈。”[9]在王安石学派的倡导下,学者们大多在解《庄子》时加入对性命道德的探讨,乃至许多学者指出《庄子》是讲性命道德的。所以,在以王安石为首的宋代学者眼中,庄子也是探究性命道德的。
四、余论
王安石“以儒解庄”的思路无疑开拓了宋代庄学的视野。南宋楼钥在《跋张正字〈庄子讲义〉》中对王安石解庄给予高度评价,称王安石解《庄子》能“超乎先儒之表,得庄子之本心”、“前此未有发此秘者”[10],但这种说法的可靠性却值得怀疑。
前文已经分析过王安石以儒解庄的动机主要在于为变法提供理论支持,发掘出《庄子》一书的治世道理。王安石在阐释庄子思想时,选取了《庄子》中的外、杂篇,尤其是像《天道》、《天下》等本身就存在争议的篇章。一般来说,这些篇章更可能是庄子后学的作品,其中已经吸取了很多其他学派的思想内容,并不能完全真正代表庄子本人的思想。作为一名熟知老庄的学者,王安石不可能不明白这点,但他却依旧根据这些资料推测庄子本意,将庄子推向儒家,得出“庄子用其心亦二圣人之徒矣”的结论,所以,能否得庄子本心自然值得怀疑。不过抛开这些不论,以儒解庄是否“前此未有发此秘者”?
杨儒宾提出“庄子儒门”的说法,简言之,即把明末清初一股将庄子迎向儒家阵营的思潮称为“庄子儒门说”[11]112-144。他认为这股思潮的源头要追溯到魏晋时期,向、郭的《庄子注》可视为“庄子儒门说”的前驱,他们将庄子定位为已知“大本”,但尚不能充分体现此大本的哲人,强调儒道同风,道述玄理,儒证斯境。老庄可视为“述者之谓明”的哲学家,孔子才是智及仁守的圣人,庄子与儒门价值相融说在此一时期首度取得显赫的解释权。我们看到,庄学发展至宋代,以王安石、苏轼为代表的理学家们认为庄子实质上本为儒者,庄子用心与圣人同,庄子是助孔子者。宋代理学家对异道异教的判教意识非常强烈,宋代儒学复兴是在批判佛老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但矛头大多指向佛教,对道家道教的批判程度相对较轻,对庄子的批评更少。宋儒对庄子的批评处基本都在其人放纵、不守规矩等小罪名上,但对庄子的一些思想表示赞同,如连一向护教意识强烈的二程也指出“庄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此言却最是”[12]93。二程亦说过“庄子,叛圣人者”,这其中隐含的意思在于庄子原本学于孔子,只是后来背叛了儒家之道,实际上庄子与儒家存在血脉联系。
因此,从这条线索来看,以儒解庄的理念在魏晋时期早已存在,王安石在其中起到了过渡作用,既承接了向、郭以来的思路,使庄学“儒学化”的倾向更为深化,带动了宋代普遍以儒解庄的风气,又为后来明末清初“庄子儒门说”做好铺垫。“庄子儒门说”是将庄子推向儒家最彻底的一种主张,道盛、方以智师徒提出有名的“托孤说”,虽看似令人惊诧,但考量自王安石以来理学家对道家的亲近态度,以及纵深的理学背景,就不难发现庄学从宋代发展至明清越来越儒学化是必然的趋势,这也算得上是后人对“以儒解庄”的呼应。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也能对王安石的庄学思想有一个更为准确的定位。关于庄子与儒家的关系,自古以来议论纷纷,无论是以儒者面目出现的庄子,还是企图解构儒家价值体系与儒家相对抗的庄子,都是诠释史中的庄子,因后人价值取向的不同而产生多种形象的变化。
[1] 叶梦得. 避暑录话[O]. 四部全书影印本.
[2] 郎擎霄. 庄子学案[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
[3] 王安石. 王文公文集[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4]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5] 郭预衡,郭英德.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第5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
[6] 容肇祖. 王安石老子注辑本[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7] 蔡上翔. 王荆公年谱考略:第11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8] 王雱. 南华真经新传·拾遗[O].四库全书影印本.
[9] 赵秉文. 滏水文集:第1卷[O]. 四库全书影印本.
[10] 楼钥. 攻媿集:第75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 杨儒宾. 中国哲学与文化:第4辑[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2] 程颢,程颐撰. 二程遗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 李长成]
Zhuangzi as a Confucian: Wang An-shi’s Study on Zhuangzi
ZHANG Na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Wang An-shi’s study on Zhuangzi opens a new path for the study of Zhuangzi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book Zhuang Zhou by Wang An-shi, where Zhuangzi appeared as a Confucian, pointed out that Zhuangzi was one of the followers of Confucians and that he intended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his times and that the book Zhuang Zi had its own special meaning. But for Wang An-shi, Zhuangzi’s image changed over time, that is, Zhuangzi’s attitude towards the world changed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And this phenomenon seems to correlat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Wang An-shi’s thought and his intention to seek th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political reform. Also, Wang An-shi paid much attention to discussing the concept of morality, humanity and destiny and he said that “Zhuangzi’s book knows a lot about humanity and destiny”. This focus of Wang had affected his explanation of Zhuangzi, too. Additionally, Wang’s son named Wang Pang had a good grasp of Zhuangzi, whose theory could also be regarded as manifestation of inheriting his father’s thoughts. From the history of explanation of Zhuangzi, the thought of Confucianism of Zhuangzi had been developing since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and its representatives were Xiang Xiu and Guo Xiang. Wang An-shi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transitional role in this process, which not only opened up the tendency of the Song dynasty’s Confucianism of Zhuangzi, but also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idea of “Zhuangzi as a Confucian” in the Qing dynasty.
Wang An-shi; Zhuang Zi; the way of Confucianism of Zhuangzi; Zhuang Zhou
10.16088/j.issn.1001-6597.2016.05.012
2016-03-25
张娜(1991-),女,安徽阜阳人,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古代文论。
B244
A
1001-6597(2016)05-007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