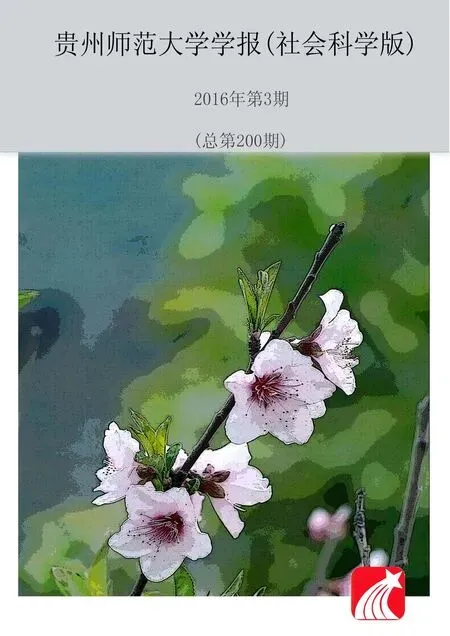《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抽象”概念
唐正东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抽象”概念
唐正东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210023)
摘要: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转化成物与物的社会关系的角度对个人受“抽象”统治的论述,只是他这一时期对“抽象”问题的首次阐述,这并不代表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核心观点。经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思想过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从商品关系的内在矛盾性而不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抽象性的角度,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论维度上的“抽象”范畴进行了崭新的解读,并以此深化了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丰富内容。
关键词:资本论;抽象;具体;内在矛盾
顾名思义,“抽象”就是从具象中抽离出来。因此,什么是具象以及如何从中抽离出来,便会影响到“抽象”概念的内涵。如果你把具象理解为经验性的某物,那么,从中抽离出来的便一定是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而且还往往带有观念论的色彩。如果你把具象理解为经验性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那么,从中抽离出来的“抽象”也许会带有关系主义的特征,但不变的是其形而上学的特性。当然,如果你把具象理解为社会历史发展到某一具体阶段时的产物,那么,由于你所关注的不仅仅是这一“物”的经验性存在,而且还有把这一物“产”出来的社会历史进程,因此,从中抽离出来的便一定是社会历史过程中的某种共同的东西。我们在汉语语境中会从“物”、“事物”、“产物”等不同的角度来言说某种作为具象的物,由此凸显的实际上是不同的抽象之方法论及内容。因此,当我们把对抽象的解读与社会批判理论联系起来的时候,理应对抽象的不同方法论做出清晰的解读。就马克思而言,他在对德国唯心史观、英国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等不同批判对象的解读中,展现出了对“抽象”的不同理解。即使是在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这一特定对象的解读中,马克思在不同时期也表现出了不同的“抽象”观。在这里,我主要聚焦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层面,通过解读抽象概念在这些文本中的真实内涵,来凸显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资本批判理论的真实内容。
一
一想到《资本论》及其手稿层面的“抽象”,我们一般都会谈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货币章”中的那段著名论述。“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1]107在此章的另一处,马克思还说:“这种与人的依赖关系相对立的物的依赖关系也表现出这样的情形(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互相间的生产关系):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1]114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化成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便很自然地成了马克思基于对抽象的批判而展开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核心内涵。事实上,这种观点在国外学界是很有市场的。德国学者索恩-雷特尔(Alfred Sohn-Rethel)发明了“现实抽象”的概念来诠释这种抽象过程。“自然知识的概念是思维抽象,而经济学的价值概念是现实抽象(Realabstraktion)。后者虽然不过是存在于人的思维之中的,但是它却并不是源自思维的。它直接地是一种社会本性,其起源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时空领域之中。不是人,而是人的行为、人们之间的相互行为产生了这一抽象。”[2]日本著名学者广松涉也用物象化概念来指称上述现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对‘物象化’进行过定义式的论述,也未必频繁地使用过这个概念。尽管如此,在‘晚期’著作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用法,即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事物的契机也中介性地、被中介性地介入)是以‘物与物的关系’,或者是以‘物所具备的性质’、‘自立的物象’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事态。不难看出,这样的事态被物象化一词所称呼着。”[3]由于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关系到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不同理解,因此,我们应该对它加以细致的辨析。
从文本上来看,上述两段论述都出现在“货币章”中。我们知道,《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从第二章即“货币章”开始的。在谈论货币关系的这一章中,马克思当然应该通过阐述人的社会关系向物的社会关系的转化过程,来阐明货币关系或者说交换价值的本质。这其实并不是什么新观点,早在1844年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在摘录到交换的中介问题时就已经提出了与此相类似的观点,“其实,进行交换活动的人的中介运动,不是社会的、人的运动,不是人的关系,它是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的抽象的关系,而这种抽象的关系是价值。货币才是作为价值的价值的现实存在。”[4]但必须指出的是,如果说在1844年时期马克思的上述抽象观代表了其资本批判的主导思路的话,那么,我们要证明这种基于物化的抽象观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仍然是马克思的主导性批判思路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货币章”所谈论的其实只是产品与产品之间的交换关系,而不是商品与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后者是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最基础的关系,从它那里所引出的是解读资本过程的矛盾性批判线索,而不是从应有性的社会关系所引出的物化或物象化批判思路。而前者只是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依赖关系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个人全面发展相比较的视域中,资本主义社会形式所呈现出来的具体特征。它只涉及不同的社会形式在历史学意义上的前后不同,而不涉及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最基础性内容的挖掘, 更不涉及从这种最基础性内容出发通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而对资本关系的历史特殊性进行深刻诠释。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直接从阐述货币关系入手的,即从商品的交换价值入手的,“同各种商品本身相脱离并且自身作为一种商品又同这些商品并存的交换价值,就是货币。商品作为交换价值的一切属性,在货币上表现为和商品不同的对象,表现为和商品的自然存在形式相脱离的社会存在形式。”[1]94即使是在最后补加进去的“价值”篇中,马克思虽然谈到了商品范畴是表现资本主义财富关系的第一个范畴,并且也指认了商品本身包含着两种规定的统一,但需要看到的是,马克思此时说的只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统一。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虽然在商品中直接结合在一起,同样它们又是直接分开的。交换价值不仅表现为不是由使用价值决定,而且正好相反,商品只有当它的所有者不把它当作使用价值来对待时,才成为商品,才实现为交换价值。只有通过商品的转让,通过商品同别的商品相交换,商品的所有者才能占有各使用价值。通过转让而进行占有,这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制度的基本形式,这种社会生产制度的最简单、最抽象的表现就是交换价值[5]293-294。
此时的马克思事实上只是把使用价值当作交换关系的前提来看待的,而没把它融进商品的内在要素之中。这样一来,仅从交换价值入手的马克思自然就无法从一种更为辩证的角度来阐释商品关系的本质。事实上,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马克思由于是从“资本一般”的角度,而不是从货币关系本身来阐释商品和货币的,因此,他在商品的内在要素问题上的理解水平显然要向前推进了一些。尽管他仍然只是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角度来理解商品,“最初一看,资产阶级的财富表现为一个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则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原素存在。但是,每个商品表现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方面。”[5]419也就是说,他还没有把商品理解为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但是,马克思已经不再只是把使用价值当作某种前提来看待,而是清楚地把握住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相互矛盾关系。“一个商品作为交换价值发生作用,倒是在于它作为等价物去任意替换一定量的任何别的商品,而不问自己对别的商品所有者是不是使用价值。但是,对于别的商品所有者来说,它只有对他是使用价值的时候才成为商品,而对它自己的所有者来说,它只有对别的商品所有者是商品的时候才成为交换价值。……所以,这里不仅因为一个问题的解决以另一个问题的解决为前提而出现一个恶性循环,而且因为一个条件的实现同另一个与它对立的条件的实现直接结合而出现一个相互矛盾的要求的总体。”[5]436-437应该说,正是这种内在矛盾性的解读视域,使马克思在商品关系的解读上一步步地越出单纯的交换价值视域,进入到真正的商品关系视域之中。或者说,使马克思一步步地越出单纯的经济学视域,进入到社会历史性的哲学视域之中。因为只有在商品关系层面具备了这种内在矛盾的观点,才可能在劳资交换关系层面把握住由劳动力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而产生的剩余价值,并进而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进行真正深刻的批判。
二
到了《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不再从笼统的“资本一般”的角度来谈论商品关系和货币关系了,而是直接从“资本的生产过程”的角度来切入。也许有人会说,《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已经从“资本的生产过程”层面来看待货币问题了。但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这一手稿中一上来就是谈论货币转化为资本的问题,而没有从商品、货币的基本内涵谈起,因此,我们在此就不把它作为典型文本来分析了。《资本论》第一卷的解读视域为马克思从社会历史过程的层面来解读商品关系的基础性地位提供了条件,因为此时的“商品”已经不再是处于简单交换关系中的产品,而是作为“资本的生产过程”的最基础性内涵而存在的那种商品关系,即交换关系普遍化条件下的商品关系。它的不发达形式尽管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存在,但是,它的发达形式或者说充分发展了的形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可能真正出现。有了这样的解读视角,马克思便很自然地会想到交换价值不是商品的内在要素,而只是作为商品内在要素的价值的具体表现形式。正是这个深挖出来的价值要素,使马克思在商品关系的分析中打开了一个矛盾分析的窗口。
试想,如果把商品的内在要素直接认定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没有引入商品的价值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才表现为交换价值,那么,对商品关系的解读思路就一定会被价值量的分析所笼罩,而无法从质的层面对价值形式作出解读。这样做的后果必然是仅仅把使用价值当作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分析的某种前提来看待,但真正展开对这种经济关系进行分析时就不需要使用价值的参与了。于是,在仅仅由交换价值所支撑的解读思路中,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本质便成了物与物之间的交换,而对它的批判性思路便建立在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转化成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上。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我们并不是说资本主义交换关系是不物化的,而是说,仅仅从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关系层面来界定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不完整、不准确的。我们知道,能否看出价值形式分析的重要性,能否看出商品的交换价值是其内在价值的表现形式,关系到在劳动价值论上是坚持内在价值论还是外在价值论的问题。“我们的分析表明,商品的价值形式或价值表现由商品价值的本性产生,而不是相反,价值和价值量由它们的作为交换价值的表现方式产生。但是,这正是重商主义者和他们的现代复兴者费里埃、加尼耳之流的错觉,也是他们的反对者现代自由贸易贩子巴师夏之流的错觉”[6]76。
而如果能够把交换价值理解为价值的表现形式,情况就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解读者一定会问:价值是在何种历史条件下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它又是因为什么原因才能够表现为交换价值的?马克思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在一切社会状态下,劳动产品都是使用物品,但只是历史上一定的发展时代,也就是使生产一个物所耗费的劳动表现为该物的‘对象的’属性即它的价值的时代,才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6]77他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
更仔细地考察一下商品A和商品B的价值关系中所包含的商品A的价值表现,就会知道,在这一关系中商品A的自然形式只是充当使用价值的形态,而商品B的自然形式只是充当价值形式或价值形态。这样,潜藏在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部对立,就通过外部对立,即通过两个商品的关系表现出来了,在这个关系中,价值要被表现的商品只是直接当作使用价值,而另一个表现价值的商品只是直接当作交换价值。所以。一个商品的简单的价值形式,就是该商品中所包含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的简单表现形式[6]76-77。
很显然,马克思此时已经清晰地认识到,如果只是基于交换价值而把商品关系的本质理解成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关系,那实际上就把潜藏在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关系消解掉了,并且还消解掉了解读视域中的矛盾分析的路径。事实上,正是这种包含使用价值在内的对商品价值要素的矛盾分析思路,才使马克思打开了一个劳资交换关系中的崭新的理论窗口,并进而完成了从资本主义交换过程向生产过程的理论上的“上升”过程。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即“商品”章中看到,马克思在此章的开篇处并没有像《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所呈现的那样,强调每个商品表现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个方面,而只是笼统地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6]47更有意思的是,此章在对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进行分析后指出,“在本章的开头,我们曾经依照通常的说法,说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严格说来,这是不对的。商品是使用价值或使用物品和‘价值’。一个商品,只要它的价值取得一个特别的、不同于它的自然形式的表现形式,即交换价值形式,它就表现为这样的二重物”[6]76。应该说,马克思的这种观点跟他此时在商品问题上的整体思路是一致的。
那么,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资本论》第一卷相对应的抽象概念又是什么呢?我以为,这种抽象其实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中的那种抽象,即把不同历史阶段所共有的一般规定提炼出来所形成的“抽象”。在谈到“生产一般”这种“抽象”时,马克思说:“因此,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因而,好像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可是,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1]26在我看来,要想准确地理解这段话其实是不容易的。我们必须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马克思讲得很明确,这种“生产一般”是从处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生产阶段中抽象出来的,而不是从各种孤立的生产形式中抽象出来的。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从中抽象出来的东西就一定是某种经验性的存在。譬如,每个生产形式中都有劳动工具,如果我们把这种劳动工具从不同的生产形式中抽象出来,那就只能得出不同生产形式之间的统一性而不可能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1]26。这种思路如果延伸到资本也是一种生产工具的层面,那就很容易得出资本的永恒性的结论了。马克思的解读思路显然不是这样的。正因为他关注的是社会历史过程中的“生产一般”,因此,它必定是随着现实社会关系的历史性展开而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的。我们还是以劳动工具为例。在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中,当农民占有部分生产资料时,这种劳动工具是劳动者对象化其劳动能力的中介和辅助手段。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由于劳动力本身成了商品,因此,劳动工具只是资本的一部分,它转化成了可变资本。在这种解读视域中,劳动工具这种“抽象”如果不依赖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中介,那是无法对某个具体的生产形式加以理解的,因为“劳动这个例子令人信服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1]46。
所以,当马克思完成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理论环节的时候,他实际上揭示的是某个特定的具体生产形式在社会历史过程中的独特属性。而这正是马克思的理论目的。他想要揭示的不是经验层面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其他生产方式之间的不同,而是历史发生学层面上的不同。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这种“抽象”是一种历史辩证法意义上的抽象,因为只有基于内在矛盾运动的社会历史过程,才能彰显出生产一般之各种表现形式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从而才能为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创造现实历史条件。就某个具体的生产方式而言,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能得出对“具体”的历史丰富性及特殊性的深刻解读。而就生产方式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说,把运用这种方法论所得出的各个“具体”连接起来,便能向我们展示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的进程与规律,而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所要揭示的历史进程理论。我们从中也能看到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方法论之间的相通性。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的这种“抽象”还是从矛盾分析的解读视角切入的。也就是说,当他在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时,他并不是从某种无矛盾性的经验存在中硬生生地或者说鬼魅般地上升到“具体”层面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方法论就只能是马克思自己的主观推理的结果了。事实当然不是如此,因为马克思的“抽象”恰恰是包含着内在矛盾的。譬如《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商品概念,它作为整个第一卷所要阐释的资本的生产过程的最抽象概念,就是包含着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在矛盾的。马克思正是从这种矛盾性的“抽象”出发,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的生产过程中由剩余价值的剥削所体现出来的劳资矛盾关系的。正因为如此,他的这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内在矛盾关系之不断发展过程的一种展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它才被界定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方法论而不是主观主义方法论的。
三
其实,马克思在“抽象”上的这种解读思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就有所展示。“所说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在可能范围内完成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1]47这里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当然是指从内在矛盾运动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暂时性的揭示。马克思是想阐明只有把历史发展过程理解为内在矛盾运动的过程,而不是历史阶段的经验性链接过程时,才可能得出关于这种历史过程的深刻理解,否则的话,所得出的就只能是片面的理解了。因此,当他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1]47时,他所谓的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一定是从内在矛盾运动的角度来展开的批判性认识,而不可能是对它的经验性认识。
从表面上看,这一文本中的有些文字跟矛盾性的解读思路是不一致的。譬如,在谈到“劳动一般”时,马克思说:“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美国,这种情况最为发达。所以,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1]46这段话中的“抽象”即“劳动一般”的确不包含内在矛盾的内容,但必须注意的是,马克思此处只是在说被亚当·斯密所发现的“劳动一般”只有在像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才成为真实的东西。他并没有说这种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起点的“劳动一般”就是他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抽象”范畴。
事实上,这里存在着基于价值量分析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与基于价值形式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之间的区分问题。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抽象劳动事实上是与具体劳动处于一种内在矛盾关系之中的,就像他所说的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处于一种内在对立、内在矛盾关系之中一样。从资产阶级经济学所使用的“劳动一般”,过渡到与具体劳动辩证统一起来的“抽象劳动”,这是马克思在商品关系问题上的解读思路的推进。上面提到的马克思在此文本中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的论述,只是他在“抽象”问题上的内在矛盾性解读思路的首次表述。他在这方面的思想更多地体现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关于商品的阐述中。马克思不仅明确地指出了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局限性,“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是一个隐藏在商品相对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这个秘密的发现,消除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纯粹是偶然决定的这种假象,但是决没有消除价值量的决定所采取的物的形式。”[6]292-293而且,他还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阶级属性进行了深刻的解读。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所发现的劳动价值论之所以无法消除价值量的决定所采取的物的形式,是因为“给劳动产品打上商品烙印、因而成为商品流通的前提的那些形式,在人们试图了解它们的内容而不是了解它们的历史性质(这些形式在人们看来已经是不变的了)以前,就已经取得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因此,只有商品价格的分析才导致价值量的决定,只有商品共同的货币表现才导致商品的价值性质的确定。但是,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6]93正因为如此,如果只是像古典经济学家那样对资本主义商品关系进行经验性的解读,或者说只是对交换价值进行价值量维度上的分析,那么,这种分析所能得出的就只能是对商品关系的物化形式的一种经验性剖析,这从本质上讲是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意识形态之中。这显然不是马克思的解读思路,因为此时的马克思是从商品关系的历史性特征或者说商品关系的内在矛盾的解读视角出发的,而这便决定了他不再可能停留在“劳动一般”的层面上,而必然会深入到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辩证统一的理论视域之中。
上述对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抽象”概念的解读,目的在于指出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货币章”中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与物的社会关系的角度对个人受“抽象”统治的论述,只是他在整个《资本论》及其手稿时期对“抽象”问题的第一种论述。这既不代表他在这一问题上的唯一论述,也不代表他对此问题的解读视域就停留于此了。事实上,此时的论述只是马克思从货币关系本身入手来谈论人与人之间交换关系的抽象性,还没有上升到从资本的生产过程的角度来切入对交换价值及其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关系之抽象性的解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论述明确地体现了从商品关系的内在矛盾性而不是社会关系的抽象性的角度来展开的批判理论的逻辑路径。由此,“抽象”便从一种关系性的经验存在转变成了内在矛盾性的历史性存在。这样一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显然也会展现出另一番崭新的理论图景。对上述理论质点的澄清与强调,对于我们在解读《资本论》中的社会批判理论时突破简单的关系主义本体论,并进而深入到基于内在矛盾运动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理论层面,应该说是很有帮助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M].谢永康,侯振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10.
[3]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M].彭曦,庄倩,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68.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附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66.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李兰敏英文审校孟俊一
收稿日期:2016-03-30
基金项目:江苏省“333工程”资助项目“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挑战及其回应”(苏人才办[2014]28号)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唐正东(1967-),江苏常熟人,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及国外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16)03-0001-07
The Concept of Abstract in “Das Kapital” and the Manuscripts
TANG Zheng-do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3, China)
Abstract:In Grundrisse, Karl Marx points out that the individual is ruled by “abstract” by which the social relations are transferred to the relations of objects. It is his first exposition of “abstract” during this period, but not the only and core exposition of it.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preparation in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first volume), Marx makes, in “Das Kapital”,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abstract” from the scientific method of “from abstract to concrete”, and focuses on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 of commodity relations instead of the abstract relations of individuals. It deepens Karl Marx’s arguments of the critical theory of capitalism.
Key words:Das Kapital; abstract; concrete; inherent contradi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