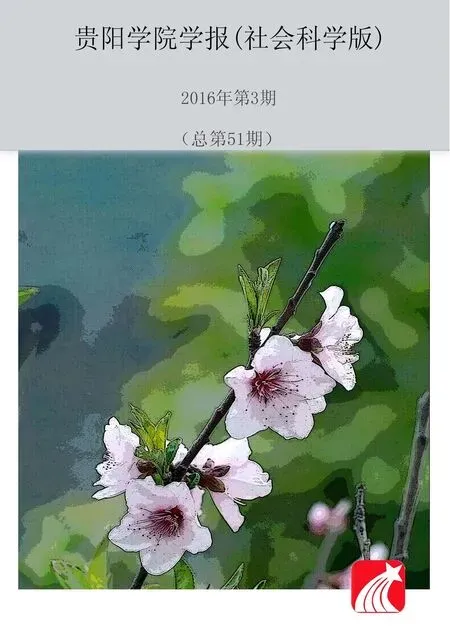罗汝芳的社会参与精神及其思想的政治化倾向*
陈寒鸣
(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天津 300380)
罗汝芳的社会参与精神及其思想的政治化倾向*
陈寒鸣
(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天津 300380)
罗汝芳是泰州王学的中坚,较之乃师颜钧(山农)更具理论特色。其思想源于周易,承继孔孟,会通儒禅,发扬阳明之学与泰州心斋之学。他一生矢力于学术研究外,更热衷讲学,从政辗转太湖、宁国府、云南等,在那污浊的官场,以一颗仁心实施教化,以“赤子之心”剖示“良知”本质而慑服众生无数,充分体现出强烈的社会参与精神。
晚明;罗汝芳;阳明后学;泰州学派;讲学;社会参与
罗汝芳(1515~1588年),字惟德,号近溪,江西南城人,著作今存有《近溪子文集》。这位曾受学于颜钧的泰州学派著名学者,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中进士,知太湖县,擢刑部主事,出守宁国府,以讲会《乡约》为治,后又补守东昌,迁云南副使,悉修境内水利,转参政。万历五年(1577年)进表,讲学于广慧寺,朝士多从之者。张居正恶其讲学,以潜往京师的罪名勒令致仕。归与弟子在江西、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等地讲学,所至弟子满坐,而他自己却未尝以师席自居。
首先,无论是在泰州王学,或者是在阳明后学中,乃至置诸于中晚明思想史上,罗汝芳都是很值得重视的人物。他的学说思想受时代思潮激荡,更承受泰州学派的传统,同时又有自身特色。
罗汝芳“早岁于释典元宗,无不探究;缁流羽客,延纳弗拒”[1] 762。他少时又读薛瑄语录,谓:“万起万灭之私,乱吾心久矣,今当一切决去,以全吾澄然澹然之体”,乃决志行之,闭关临田寺,置水、镜几上,对之默坐,使心境宁静与水、镜无二。这种强制消除心中杂念的方法,非但未能奏效,更带来副作用,久之而病“心火”。一日,过僧寺,见有榜“急救心火”者,以为名医,访之,则聚徒讲学的颜钧也。颜钧说:你的方法是“制欲”而非“体仁”,“体仁”则如“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让它自然透露,不加遏抑。罗汝芳很得感悟,次日黎明遂往纳拜称弟子,不赴廷试。归田以后,年岁已老,颜钧至,仍伺候不离左右,茗果必亲进之。诸孙以为这太劳累,欲代为之,汝芳说:“我的这位老师,不是你们所能伺候的!”其后,弟子杨起元(复所)之事汝芳,出入必以其像供养,有事必告而后行,十分虔敬。顾宪成说:“罗近溪以颜山农为圣人,杨复所以罗汝芳为圣人。其感应之妙,锱铢不爽如此。”[1]806说的就是这种师弟之间的情谊,而这正是泰州学派的一个特点。
尽管并不理解封建社会阶级压迫的残酷,但罗汝芳为官时尽力地以人道主义来对普通劳苦民众作些弥补。相传他做宁国府的时候,“集诸生会文讲学,令讼者跏趺公庭,敛目观心,用公藏充馈遗。归者如市。”[1]763会文讲学的场所竟也是讼者纷纭的公庭,讼者的呶呶乃易为跏趺静坐的冥默,封建政府的公庠居然成为馈赠“罪犯”的财源。这样的知府,不执行封建政府律令,以“罪犯”为良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又传耿定向为刑官,“行部至宁国,问耆老以前官之贤否。至先生,耆老曰此当别论,其贤加于人数等。曰:吾闻其守时亦要金钱。曰:然。曰:如此,恶得贤?曰:他何曾见得金钱是可爱的?但遇朋友、亲戚,所识穷乏,便随手散去。”[1]806这个“要钱”的宁国知府,要了金钱之后,不入私囊,而用以馈赠穷乏之人,“随手散去”。这在封建官吏中也是绝无仅有的。然而,作为泰州学派的学者,罗汝芳的这种从赤子之心出发的救贫恤难行为是可以理解的。
罗汝芳之学尽管有大而无统、博而未纯之弊,但较之阳明大弟子王畿更为清新俊逸,通秀圆融。所以如此,主要在于其学“一因本泰州之传统风格,二因特重光景之拆穿,三因归宗于仁”[2]288,而重要的则是他的学说思想蕴含着积极的救世精神与术士情怀。这可以说是明代理学传统中的非世俗价值源头及世俗主义传统观念的突破与激进。
综观罗汝芳的为学历程,可知其学问境界是由繁琐而简易、由扰攘而清明、由执著而物我两忘。清初黄宗羲概述其为学宗旨及思想轮廓道:
先生之学,以赤子良心不学不虑为的,以天地万物同体,彻形骸,忘物我为大。此理生生不息,不须把持,不须接续,当下浑沦顺道。工夫难得凑泊,即以不屑凑泊为工夫;胸次茫无畔岸,便以不依畔岸为胸次。[1]762
而罗汝芳本人对门下论及其学道之坚决自信、尊严无畏的态度时亦谓:“三十年来,穿衣吃饭,终日虽住人寰,注意安身,顷刻不离圣域,是以披沥天心,号呼世梦中,或触奴生嗔,万死而终,不回避也。”[1] 201—202若就泰州王门弟子造诣的精卓超绝处而论,罗汝芳堪称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的思想内涵沾溉心斋与山农学说特色,实践简易直截之道。
“良知”现成,不假安排,不由思虑造作。罗汝芳以这种理念为出发点,更进一步以不学不虑的“赤子之心”以剖示“良知”心体本质,并以之作为挽救世道人心的灵丹妙药:
“赤子之心,如何用工?”曰:“心为身主,身为神舍。身、心二端原乐于会合,苦于支离,故赤子孩提,欣欣长是欢笑,盖其时身心犹相凝聚,及少少长成,心思杂乱,便愁苦难当,世人于此随俗习非,往往驰求外物以图安乐,不思外求愈多,中怀愈苦,老死不肯回头。惟是有根器的人,自然会早转路,晓夜皇皇,或听好人半句言语,或见古先一段训词,憬然有个悟处,方信大道只在此身,此身浑是赤子,赤子浑解知能,知能本非学虑,至是精神自来体贴方寸,顿觉虚明,天心道信为洁净精微也。[3]764
汝芳尝责难江右诸儒以功夫为先实是不究其端绪,故强调随机悟道,不待言动事为,在此前提下,毅然提倡“赤子之心即是良知”的简易直接的成圣路向。赤子之心既等同于良知,即为心之本体与主宰。若身心合一,则一切自善。赤子之心本非学虚,自心光明,当可观照万象,动触先机。此乃良知心体当下现成,不必经由学识知虑而能直接显明自心的实际反映。
罗汝芳在“赤子之心即是良知”这个命题中,把不学不虑的“赤子之心”说成是良知的本来面目,是人的真性情所在。世人于天命之性漫然莫解,是“把吾人日用恒性全看不上眼界,全不著在心胸”[3]149之故,如此则赤子之心未得妥贴安宁,学者亦易流入“耳目口体之欲,致堕落禽兽妖孽之归”[3]166。为此,他特别强调世人应该保任此与生俱来的良知心体,不仅以此为根源,而且还要征诸庶人之心,以为自用,则此赤子之心,自心显明自心,达致“纯然无杂,浑然而无为”[3]62—63的地步。
正因为“赤子之心”人人皆有,罗汝芳才以此为学理基础,并进一步形成其讲学宗旨。他指出:“天初生我,只是个赤子。赤子之心,浑然天理。细看其知不必虑、能不必学,果然与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的体段浑然,打得对同过。然则圣人之为圣人,只是把自己不虑不学的见在,对同莫为莫致的源头,久久便自然成个不思不勉而从容中道的圣人也。”①*①上书卷上“夫天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者也”条。汝芳讲学的目的在于勉人成圣,强调事事圆融,不须把持,不须凑泊,顺其自然,便是生机活泼。自然之道着著以世俗主义格套。他以此基调论证其“赤子之心”的学理思想,认为人生下来是个赤子,“赤子之心”本体莹洁,未为外物所染,纯是天理。故其良知与良能具有不学不虑,自然流行性质,此正与“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的天道流行浑然无闻,所谓“打得对同过”就是说“赤子之心,浑然天理”之意。由于当下现成的良知良能与天道互为对应,故常人便可“自然成个不思不勉而从容中道的圣人”了。
罗汝芳在其著作中屡言“赤子之心”之重要,其学理基础主要在于说明人性本出于自然,一片生机,赤子之心本身就是良知“无时无处而无所不知”的具体表现。而“赤子之心”在视、听、言、动诸形色上见其性、见其良知,这就是赤子之良知的本来面目。楚中王门中坚薛信(字乡实,1483~1559年)称此“赤子之心”为“圣胎”及“爱亲敬长一点真切的心”,此与汝芳以“赤子之心”指点良知,以见乎良知之妙用流行的理念可谓异曲同工。罗汝芳以“赤子之心”指点良知,目的在于说明良知心体能具体而自然地流行于日用之间,以达至无工夫之工夫的境界。因此,他确信工夫并无定法,只须心中悠然顺适,浑轮到底,眼前即为化境。当其不但反对“戒慎恐惧”之工夫架构,更对“好静恶动”、“贪明惧昏”等辗转于支撑对治的种种追求表示不满。黄宗羲称他以“不屑凑泊为工夫”,可谓一矢中的。事实上,罗汝芳的学术宗旨与实践工夫确是如此,正如他自己所说:
学问须要平易近情,不可着手太重,如精茶淡饭,随时遣日,心即不劳,事亦了当,久久成熟,不觉自然有个悟处。盖此理在日用间,原非深远,而工夫次第亦难以急速而成,学能如是,虽无速化之妙,却有隽永之味也。①*①上书卷下“问晦庵先生谓由良知而充之”条。
同王艮一样,罗汝芳将“乐”归于具体生命之感受,一言以蔽之,即将学问生命化、生活乐趣化,其生活态度是以追求“平易近情”,当下沦顺适为理想的价值取向。当学问与生活融合无间时,鸢飞鱼跃,自自在在,无穷乐趣由此而生。人生朝作夜息,饥餐渴饮,心无烦虑,虽粗茶淡饭,亦足以度日,推而至于爱亲敬长,成仁取义,无非天机流行,丝毫勉强不得。“孔颜之乐”就是这种妥贴安适、了无滞碍之自然境界[1]。
童子捧茶,客人受之,“已而各饮,何等不思不勉,何等从容中道。”[4]182这“不思不勉”、“从容中道”就是罗汝芳教人要自信自立而更下工夫。学者每每剖意将自身活动加以规律化、秩序化,使之执守一定形式,此实犯了作手之病。为此,汝芳在开示门人时,常常指明“当下”即为用功之地,使人排除疑虑,不累于过去、不忖测未来,而直下做真切工夫,并藉此以为“驰求闻见”、“好为苛难”的时下学者“引归平实田地”[4]151—152。毋庸讳言,在罗汝芳看来,“当下”是一种天赋的知觉能力,学者可以直下做逆觉体证,不必事先隔离人伦物用。他这种日用工夫的思想,无疑渊源于王艮“百姓日用即道”观念。“百姓日用即道”观念明显地有着以“道”来规范“百姓日用”的企图,即于日用常行中指点良知。这一点,王艮曾以僮仆的往来行动为例加以说明:
先生(王艮)言百姓日用是道,初闻多不信。先生指僮仆之往来,视、听、持、竺,泛应动用处,不假安排,俱是顺帝这则,至无而有,至近而神。[5] 5上
“百姓日用即道”就是选取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感觉及行为来说明“良知”之“现现成成”,不假安排,人人俱足,故是“至无而有,至近而神”。
罗汝芳论述“当下即是工夫”的话头甚多,只要是顺着“良知”,心体的自然秉性流行于日用之间,无论是童子捧茶或是吏胥进茶,只要“循序周旋,略无差僭”[1] 784,不偏不倚,自然宁静,自然防检。这里,虽未明言戒惧工夫,而戒惧工夫已在当中,若能将此种意识状态贯穿于人的整个生命历程,并有所自觉,由人道上溯于天道,由具体真实之事物以见天地生生之机。此种以当下工夫指点“良知”心体之自然平常,浑然顺适,正是罗汝芳所以超越其他泰州同门之处,同时,亦是他落入“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的异端思想窠臼的主因之一。
罗汝芳二十六岁往见颜山农乃其成学之一大转折点。他曾为了“制欲”而习静,每日与明镜止水相对无二,如此使心如明镜止水,虽穿插于生死、得失荣辱之间,不为所动,心不起,则欲亦不起,然而,山农仍指出此种生死得失之为动心乃“制欲”而非“体仁”;倘若为了“制欲”而“制心”,便成了“害心”,因为“欲之病在肢体”,而“制欲之病乃在心”[6] 82,故山农自信地指出体仁之妙在放心而不在制欲。罗汝芳接受了颜山农这一“体仁”之说,不但大加发挥,而且还作有系统之论述,其门人詹事讲谓:“师之心,仁心也;师之体仁体也。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师其有之矣。”[4] 285由此可见,其对“仁”的重视。
二程常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7]15并以此作为人生最高的精神境界。这种思想影响阳明既深且巨。阳明“万物一体之仁”的学理概念主要侧重在潜存于道德本心的仁体以涵摄感知天地万物,其落实处既不依赖于自隐自显的大道,又不附于一系列的认知活动,只需要反身而诚,复其心体之良知同然,如实推致于天下万事万物便可。
心斋王艮执贽于阳明门下后,“契良知之传,工夫易简,不犯做手,而乐夫天然率性之妙当处受用”[8]5下,更撰作《鳅鳝赋》,将乃师常提的“万物一体之仁”理论活学活用,并以虚明灵觉的良知为“仁”体的显现,从而论证“大人”理应有实现“万物一体”之仁的政治远大抱负。罗汝芳受阳明及心斋的“万物一体之仁”思想沾溉在前,印证山农论直截体仁之法在后,默默勘考、细细抽绎,大畅其“仁者人也”学旨,随机指点,使学者当下即可受用。他尝言:“仁者,人也,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则大矣。《大学》一书,联属家国天下以成其身,所以学乎其大者也。”[4] 3儒家素以“万物一体”为个人修养的终极目的,孔子所说的感通觉、润万物的“仁”汇归在“万物皆备于我”的“良知”心体上,而《大学》一书所述论的孔门宗旨,便是这个“仁念”。
罗汝芳对其师所提掇的“体仁”学理曾下过一番起死回生的寻求工夫,既有原则把柄在手,又纵横作用,无不如意。他还进一步将“仁”念彰显为普天普地无处不在的生机—— “生生之德”。在他看来,天下一切只是悱恻之仁直接呈现的流行之德,此流行之德所呈现之境界只是一片生机洋溢,无封畔与对立,自身与天地万物同体,形骸彻底同化,天性仁德表现于万物而涵摄于心中,如此,通贯天地之道信于己身,参天地之化育,使“混混沌沌之乾坤”变为“条条理理世界”[9]7-11。对禽兽、草木也要有悯恤不忍之心,此乃合“天地万物之生以为生,尽天地万物之仁以为仁”[4] 33。生生之仁的流行化育,使超拔流俗的“良知”呈现,其生生而成成,绵延不绝,乾知坤能之德,妙运默契,而山峙川流,禽兽草木之生意皆不外乎此生生之德的流行显露。人心之灵明不昧,给于天地万物无限生机,可知天地万物实与“良知”心体相感相通,方见此仁体确乎无处不在。
汝芳认为“仁”乃人的真正根源,是“真种子”,仁即是爱,赤子出胎即有爱根,而若推崇这个爱根来做人,虚明灵觉的良知心体便得以保任。赤子之心本来是灵妙能透,不学不虑的,学者若按此赤子之心去学去行,易简顺适,其乐无穷。因此,汝芳论学常将“仁”与“乐”联系起来,以“仁”释“乐”,曰:
所谓乐者,窃意只是个快活而已。岂快活之外复有所谓乐哉?生意活泼,了无滞碍,即是圣贤之所谓乐,即是圣贤之所谓仁。盖此仁字其本源根柢于天地之大德,其脉络分明于品汇之心元。故赤子初生,孩而弄之则欣笑不休,乳而育之则欢爱无尽。盖人之出世,本由造物之生机,故人之为生,自有天然之乐趣。故曰:“仁者,人也。”此则明白开示学者之真,亦指引学者以入道之要。[1]790—791
他以为“仁”乃天地之大德,此仁道精神充塞弥漫于天地之间,在其展现落实时,必须普万物而不遗,因“仁”本身乃自然流行之体,故真乐自见。孔、颜因得此不息之体,不仅“真乐自不能改”,而且“以贫自安而不改”。世人竭力追寻“孔、颜乐处”,这种“乐趣”与生俱来,正如赤子初生“弄之则欣笑不休,乳而育之则欢爱无尽”,此便是“仁”、便是“乐”,参需刻意向外搜寻[1] 790。罗汝芳以“仁”释“乐”的微言妙谛,不但直捣“孔、颜乐处”深处所在,更尽得淮南三王“率性以全其乐”及其师“制欲而非体仁”的学说奥蕴。
儒学发展到宋明,演变为思辨形态的理学,其学问的最终目标不外乎修道成圣。在工夫实践上,各有各自得之处及不同的价值取向。对心体的认知成为关切,诸如以喜怒哀乐为承发之中,发明本心以及静坐养出端倪等明心见性工夫。诚如前述,罗汝芳曾闭关以复澄之体,因不得其法而遘“心火”之疾,由是对良知可成一“光景”之问题体验最深:
人生天地间,原是一团灵气。万感万应而莫究根源,浑浑沦沦而初无名色,只一“心”字亦是强立,后人不省,缘此个念头就会生作见识,因识露个光景,便谓吾心实有如是本体,实有如是朗照,实有如是澄湛,实有如是在宽舒,不知此段光景原从妄起,必随妄灭,及来应事接物,还是用着天然灵妙浑沦的心,此心尽在为他作主干事,他却嫌其不见光景形色,回头只去想念前段心体,甚至欲把捉终身以为纯一不已,望显发灵通,以为宇太无光,用力愈劳,而违心愈远矣。[4] 94-95
汝芳所执定心体之义,是指“一团灵气”之良知心体而言。此心体“如是朗照”、“如是澄湛”、“如是自在宽舒”,这是指其本然状态。他这番论述的意义,在于使人由此而自见本心以方便说法,惟时下学者由此境界感知本心,遂定执此心具此“澄湛”、“朗照”、“宽舒”等状态为一心之炯炯然。如此执定之后,良知本心(知体)被投置成一个对象或意念。此乃良知本体所起之光景,而非感知万象、知是知非的知体,学者将此万感万应、空灵朗照、澄湛自若、宽舒不迫之知体操执把持,无疑是使其原有的灵气生机窒障,是故知体妄起妄灭,遂失其本原。至于如何破除光景而使知体复明便成为汝芳指引学者入道的重大课题,其学之风格席子亦以此为胜场。
若要破除光景,使知体归于顺适平常,罗汝芳指出当从一“悟”字作为用功的下手处。人固可随时随处有体知之呈现,然而此刹那之“良知”闪现往往即生即灭,瞬即湮没于私利欲流之中,而不为人所觉,因此,罗汝芳要求学者直接彻悟知体以发明本心之功,并以浑沦顺适、自然平常至反身当下体证知体于日用之间,眼前即是,当下便有受用。在实际行事中,将炯然若见得知体的抽象光景破除,以期使学者在破除光景与指点道体平常上开启成德之路。他以“不屑凑泊为工夫”,此“不屑凑泊”之工夫必须通过光景之破除而得以畅发。童子捧茶的不假安排就是知体的即感即应,自然平常,“时时照管本心,事事归依本性”[1] 774的具体、真实地流行于日用之间的最佳反映及说明。罗汝芳一再提醒学者切勿留恋光景以为见道,最后走上迷途,误入“鬼窟”而不自觉。从其将讲学重点放在“如何破除光景使归于顺适平常”的前提,可知其对误将抽象的光景作知体(良知心体)之弊领悟已彻,学风已成。
孝、弟、慈是罗汝芳晚年讲学的重要内容。就如“赤子之心”一样,孝、弟、慈为人人与生俱来的良知本心之自然流露,故“不虑而自知”、“不学而自能”。此三事“从造化中流出,从母胎中带来,遍天遍地,亘古亘今。试看此时薄海内外,风格气候万万不齐,而家家户户谁不是此三件事过日子也?”[9] 108古代圣贤能孝亲、敬长、慈幼,使其共相敬爱、共相慈和及至共相安乐,大顺大化,归结起来,莫非“孝、弟、慈”三事,而孔子、“六经”中的嘉言懿行亦无非是此三事的落实与贯彻。
孝、弟、慈是人之性、天之命,本身蕴含着良知流行于人伦日用间的简易顺适特点,若于此推演扩充,尽孝、尽弟、尽慈于日用道德生活中,使人直下宛见一超越于四海古今之上的晚德知体,如在眼前,学者沿此用功,以诚求此同处之日充日明、日广日大,并以此自信自立的理想精神境界。
由于罗汝芳对“孝、弟、慈”三事的印证落实,使得其所确认的“天下未有一人而不孝弟慈”的观点找到了立论根据。若单从汝芳的道德观作一观察,不难发现,他不仅强调“孝、弟、慈”为仁义本心的自然流露,同时,更在其规矩准绳之下凸显了传统儒家的家族伦理优越性。学者学圣,须在圣贤乃至愚夫愚妇所同有之此心此理上立根,无时无刻不自发明其本心,自致其良知,反身见得此道德行为的自证自觉,如此,《周易》的生生之道及《大学》、《中庸》的亲亲之情发挥无遗,跻身于圣域就指日可待了。由此观之,罗汝芳以孝、弟、慈作为学者道德实践的基本原则,既是他早年艰苦成学历程中所获取的宝贵经验,也是他晚年论学专以孝、弟、慈三事开示学者门人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罗汝芳的思想承泰州王学重视孝悌、提倡乐学等传统,对阳明学亦有理论上的深刻了解与认同,同时对阳明心学和泰州王学又有进一步的推衍发展。他所着力阐发的有关“求仁宗旨”、“孝悌慈”、“赤子之心”、“一体生化”、“形色天性”、“全体身躯”、“天心天人”、“能身复礼”、“上帝日监”、“即身言仁”、“形神供妙”等一系列无疑具有自身特质,而这些有着自身特质的论题不仅大大提升了泰州王学的哲理思辨性,而且拓展并深化了阳明心学。[9]
其次,明代中晚期的心学思潮与讲学运动密不可分。阳明及其后学正是藉讲学而使心学思想风靡一时,耸动朝野。并且,心学作为一种思想运动与当时社会基层-----乡村自发产生的教化运动相结合,遂使阳明心学的良知理念迅速渗透到社会下层,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而儒学亦得以世俗化、平民化。《明史》卷载二三一:“正嘉之际,王守仁聚徒于军旅之中,徐阶讲学于端揆之日,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于是,缙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沈德符亦云:
嘉靖末年,徐华亭(阶)以首揆为主盟,一时趋鹜者,人人自托吾道。凡抚台在镇,必立书院,以鸠集生徒,冀当路见知。……于是,三吴闲竟呼书院为中丞行台矣。[10] 510
阳明本就十分重视讲学,其弟子在乃师殁后多热衷讲学,传扬心学。如《明儒学案·南中王门一》说:“阳明殁后,(钱)绪山、(王)龙溪所在讲学,于是泾县有水西会、宁国有同善会、江阴有君山会、贵池有光岳会、太平有九龙会、广德有复初会、江北有南谯精舍、新安有程氏世庙会、泰州复有心斋讲堂,几乎比屋可封矣。”绪山、龙溪被视为阳明嫡传,他们为藉推扬师说不遗余力,尤其是龙溪,“终先生之身,无一日不讲学、不会友,反复淳切,感孚鼓舞,期于必信而后已。而凡嫌似之迹,或冒而居之不辞。故语讲会之所,则有水西、洪都、白鹿、怀玉、南都、滁阳、宛陵,几遍江南之地。而会之人,皆当时同志,几尽一世之英。”[11]“所至接引无倦色,故自西都及吴楚闽粤,皆有讲会,江浙为尤盛。会常数百人,公为宗盟。公年八十犹不废出游。”[12]王学学者的讲学活动不仅在各地广泛展开,而且更盛行于两京。嘉靖十一年(1532年),“自师没,桂萼在朝,薛侃等既遭罪遣,京师讳言学。至是年,编修欧阳德、程文德、杨名在翰林,侍郎黄宗明在兵部,戚贤、魏良弼、沈谥等在科,与大学士方献夫俱主会。于时黄绾以进表入,洪、畿以趋廷对入,与林春、林大钦、徐樾、朱衡、王惟贤、傅颐等四十余人,均定日会之期,聚于庆寿山房。”[13]十二年癸巳,“欧阳德、季本、许相卿、何廷仁、刘旸、黄弘纲嗣讲东南,洪亦假事入金陵。远方志士四集,类萃群趋,或讲于城南诸刹,或讲于国子、鸡鸣,倡和相稽、疑辨相绎,师学复有继兴之机矣。”[14]。
泰州王学诸子生存于斯时,自均热衷于讲学。他们讲学于世时,从之游者动辄千数百人,获得很大成功。王艮入阳明门后不久就曾招摇北上,有过一次震动朝野的讲学之旅①*①关于王艮北上讲学,王艮《年谱》记入嘉靖元年壬午(1522)王艮四十岁时,曰:“一日,(王艮)入告阳明公曰:‘千载绝学,天启吾师倡之,可使天下有不及闻此学乎?’因问孔子当时周流天下,车制何如?阳明公笑而不答。既辞归,制一蒲轮[按:蒲轮,又名轻车,亦名招遥车],标题其上曰:‘天下一个,万物一体,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遵圣道,天地弗逆;致良知,鬼神莫测。欲同天下为善,无此招摇做不通,知我者其惟此行乎?罪我者其惟此行乎?’作《鳅鳝赋》……沿途聚讲,直至京师。……”(《重镌心斋王先虫全集》卷二),阳明殁后则不仅积极参加王门诸子在东南开展的讲学活动,而且更设坛授徒,通过讲学创立起著名的泰州学派。王艮的弟子亦多肆力于讲学。如嘉靖七年,颜钧建立萃和会,召集自家的、家庭的及乡闾间的老壮男妇几近七百人听他“讲耕读正好作人,讲作人先要才弟,讲起俗急修诱善,急回良心,如平时系念父母,常得欢心,……勤勤恳恳,不厌不倦,不私贷以裕己,不怀蓄而薄养”[15] 24。他所讲的伦理道义颇受群众欢迎,遂成立“三都萃和会”,“会及一月,士农工商,皆日出而作业,晚皆聚宿会堂,联榻究竟。会及两月,老者八九十岁、牧童十二三岁,各透心性灵窍,信口各自吟哦,为诗为歌,为颂为赞,学所得虽皆刍荛俚句,实发精神活机,鼓跃聚呈农(即山农)览,逐一点裁,迎几开发,众皆通悟,诰歌散睡,真犹唐虞瑟瑟,喧赫震山谷,闾为仁风也”②*②上书卷三《自传》。。后来,颜钧更提出:“圣人因心以立学,因学而成会。会惟成学,学必立会”③*③上书卷二《明羑八卦引》。,希望通过有组织的定期会讲形式进一步宣讲王艮的“大成仁道”。嘉靖十九年(1540年),他在江西南昌公开张贴《急救心火榜文》,讲学传道,一千多名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听其宣讲“大成仁道”,深深为之吸引,罗汝芳即由此而拜其为师,成为颜钧的著名弟子。其后,颜钧又在大江南北四处讲学,皈依其“大成仁道”者几千百众。又如韩贞居乡间,农闲时即在劳动人民中讲授儒学,致力于发明王艮“大成仁道”,所谓“以明道化人为己责,虽田夫、樵子未尝不提命之”,成为当时一位颇有声望的布衣儒者。耿定向在其所作《陶人传》中说:“先生学有得,毅然以倡道化俗为己任,无问工商佣隶,咸从之游,随机因质诱之,化而善良者以千数。每秋获毕,群弟子班荆趺坐,论学数日,兴尽则拿舟偕之,赓歌互咏。如别林聚所,与讲如前。逾数日,又移舟如所欲往,盖编所交居村乃还。翱翔清江,观闻者欣赏若群仙子嬉游于瀛阆间也。”黄宗羲在《明儒学案·泰州学案·韩贞传》中也描述了乐吾讲学的情形:“秋成农隙,则聚徒讲学,一村既毕,又之一村,前歌后答,弦诵之声洋洋然也。”这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上一幅罕见的农民乐学图。虽然,它不像耿定向所美化的“若群仙子嬉游于瀛阆间”,因为在中世纪的贫困世界绝不可能有人间仙境,但它却展示出十六世纪中国农民渴求文化知识的历史画卷,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封建社会后期人性的觉醒和时代精神。他如王艮的江西弟子、编有《心斋年谱》并两次刊刻《心斋语录》的张玉屏辞官家居后,既建义阳书院,又尝举会于青原,宣讲传播心斋之学。泰州王学后劲焦竑不仅高度关注新安地区士大夫与一般商人百姓的讲学之风,而且还亲赴新安为书院主持讲席,讲学传道十余日。据其学生谢与栋说:新安人闻焦竑至,自缙绅先生至儿童牧竖,四方人众聚集者凡二千余人,咸听其讲学。而焦竑“随机指示,言简意尽,一时闻者咸悚震踊跃”,众人“如旅而归,如寐而觉,如凋饥而享太牢。以此知性之相近,而尧、舜之可为”[16]727。
作为泰州学派最重要的学者,罗汝芳自然也是很热衷于讲学的。嘉靖十二年癸卯(543年),罗汝芳“举于乡,与同志大会滕王阁”;次年,“会试,与同志大会灵济宫”;又次年,在家乡“建从姑山房,以待讲学之士”[17]920。此前,汝芳在家乡就已参与乡会一类的活动:
问:“里中自前峰先生倡碧崖、纯斋诸公讲里仁社会,将数十余年,今更通诸一乡一邑,真是君子之德风也。”曰:“孔子云‘为政以德’,可以无为而治。但观近日之会,昭然可见。吾乡老幼聚此一堂有百十余众,即使宪司在上,也不免有些喧嚷。是岂法度不严?奈何终难静定。及看此时,或起而行礼,或坐而谈论,各人整整齐齐,不待吩咐一言,从容自在,百十之众浑如一人。”[18]139
其父前峰在世时,汝芳家乡已有“里仁社会”——和颜钧所创三都萃和会相类的乡族讲学会,罗汝芳是这乡会的积极参与者。后来,他于嘉靖三十年(1551年)居家,“会乐安、会宜黄、归立义仑,创义馆、建宗祠、置醮田、修各祖先墓,讲里仁会于临田寺”[17]920-921,继承了乃父传统,同时也是对其师颜钧讲学乡里传统的继承。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以后,罗汝芳开始参加乃至组织大的会讲,如二十九年,他“约同志大会留都,秋会江省月余;沂流至螺川,集会九邑同志”[17] 921。三十三年在京中参加同志讲会:“嘉靖癸丑第进士,寓京师,与姜凤阿宝、胡庐山直、邹颖泉善、耿楚侗定向、刘养旦应峰诸先生联同志会,辰夕切靡,各有所得。”[19]853四十一年出守守国府,以“以养会乡约为[联合乡村,各兴讲会]”[1] 760为其主政特色。四十四年入觐,再次“大会灵济宫”[20]861。万历元年任云南副使、参政,先后在武定、临安、弥勒、石屏、通海、大理、永昌、洱海、楚雄等处会讲。万历五年丁丑(1577年)赍捧入京,礼成,与同志会讲广慧寺,未几,被令致仕。①*①据《近溪子集·庭训下》、《盱坛直诠》及《明实录》卷六十六、周海门《圣学宗传》卷十八、沈懋学《郊居遗稿》卷八等,万历五年为会试年。罗汝芳为万历帝祝寿而捧贺入京。他本有归养林下之意,遂上疏乞休,并于礼成后在等待上司结论之期,终日与同志讲学,还移寓郊外寺中,日与僧侣非辈为伍谈禅。张居正遣子往听,汝芳以《太上感应篇》相赠。本以对风靡天下的讲学运动怀有戒心的张居正,对罗汝芳的行为颇为不悦,便“唆使”言官弹劾,降旨“玩旨废职”,责令致仕。有弟子劝道:“师以讲学罢官,盍少辍以从时好?”汝芳答道:
我父师止以此件家当付我,我此生亦惟此件事干。舍此不讲,将无事矣。况今去官正好讲学![3]
此后,罗汝芳一心讲学,足迹遍及江南:“得请致仕,还从姑,开诲来学。遍涉抚、吉、洪、饶、楚、粤、闽、浙、留都、徽、宁诸郡,大会同志。东南之学丕振”[21]856。“致仕,复与诸门人联辙各郡,走安城、下剑江,趋两浙、金陵,往来闽、广,益张皇讲学”[22]。
王阳明曾指出:“世之讲学者有二:有讲之以身心者,有讲之以口耳者。讲之以口耳,揣摸测度,求之影响者也;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者也。如此,则知孔门之学矣。”[23] 75他所提倡的讲学并非只是传授书本知识,而更是一种切身的求道实践(“体道之功”)。中晚明积极从事讲学活动的心学学者们多承阳明此一精神,如王畿强调“讲以身心”必须与“讲以口耳”区别开来。但同样都以讲学为“体道之功”,“讲以身心”,王畿、罗洪先等浙中王门、江右王门的学者讲学中多以学理研讨、哲理思辨为主要内容,参加者亦以“同志”为主,故而他们的讲学活动乃是一种志趣相投的精英学者的学术聚会;而泰州学派的讲学活动则与之不同,有着自身特色。兹略举三端:第一,泰州学派讲论的是“百姓日用之学”,故其讲学不分社会等级、贫富贵贱,凡有愿学者,一律平等待之。王艮以“百姓日用为道”讲学于民间,学生中有农夫、樵夫、陶匠等处于社会下层的民众,如樵夫朱恕砍柴回家必至王艮讲堂阶下听讲,颇得致良知之教。陶匠韩贞敬慕朱樵而从之学,后又卒业于王艮之子王东崖门下。后来他也“以化俗为任,随机指点,农工同贾从之游者千余。秋成农隙,则聚徒谈学,一村既毕,又至一村”[1] 720。王栋对此评曰:
自古士农工商,业虽不同,人人皆共此学。孔门犹然。考其弟子三千,而身通六艺者才七十二,其余则无知鄙夫耳。至秦灭汉兴,惟记诵古人遗经者,起为经师,更相授受。于是指此学独为经生文士之业,而千古圣人原与人人共同共明之学遂泯灭而不传矣。天生我师,崛起海滨,慨然独悟,直超孔子,直指人心。然后愚夫俗子,不识一字之人,皆知自性自灵、自完自足,不假闻见,不烦口耳,而二千余不传之消息,一朝复明。先师之功,可谓天高而地厚矣。[24]
在他看来,古代社会的学术为“士农工商”所共有,而“秦灭汉兴”后却为“经生文士”独占,遂使古代“人人共同共明之学”泯没不传。王艮的功绩正在于恢复了早期儒家“有教无类”的平民教育传统,力图以“愚夫俗子”的“日用之学”去取代“经生文士”的正宗儒学。而其所倡“百姓日用之学”与王阳明赞美的唐虞三代的“五伦之学”②*②王阳明在《答顾东桥书》中说:“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教者以此为教,而学者以此为学。当是之时,人无异见,家无异习。……下至闾井田野、农工商贾之贱,莫不皆有是学,而惟以成德为务。”(《阳明全书》卷二《传习录中》)。迥然有别。第二,泰州学派以讲学为乐,以讲学为人生一大要事,故而他们无论是大江南北,还是穷乡僻壤,行迹所至,周遍乡县,四处讲学。第三,全然不同于传统的章句注疏或宋代书院式的思辨分析,亦与王畿等阳明后学的精英讲学有异,泰州学派的平民儒者依据着现实百姓日用生活,从切身的体道修践立场出发来讲学。“自少不事文义”[25]的王艮,“不喜文词”[26],“鲜所著述”[25]。他“讲说经书,多发明自得,不泥传注。或执传注辩难者,即为解说”[27]。其“言百姓日用是道,初闻多不信。先生指僮仆之往来、视听、持行、泛应动作处,不假安排,俱是顺帝之则,至无而有,至近而神”[27]。王艮弟子韩贞与诸各公卿讲学,中有“称引经书相辩论者”者,闻之即“大恚曰:‘舍却当下不理会,乃搬弄此陈言,此岂学究讲肆邪?’”[28]
罗汝芳继承发扬了泰州学派的讲学传统。他以讲学“自渡”,亦以讲学“渡人”,“七十余年间,东西南北无虚地,雪夜花朝无虚日,贤愚老幼、贫病贵富无虚人”[29]。罗汝芳认为,做学问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觉悟”,二是“践履”,而两者又彼此关联:“觉悟透则行自纯,践履熟则所知自妙。”[30]主张“觉悟”与“践履”不可偏废。关于讲学,汝芳提出:
盖此与天下原是一物,物之大本只在一个讲学招牌,此等去所,须是全副精神,透切理会,直下承当,方知孔、孟学术如寒之衣、如饥之食,性命所关,不容自已。否则将以自爱,适以自贼。故《大学》之道,必先致知,致知在格物矣。[31]
在他看来,所谓“格物”之学离不开讲学,讲学乃是“物之大本”,是与自己性命息息相关的一大要事。若拒斥讲学,与世隔绝,名为“自爱”而实则“自贼”。他倡“今受用的即是现在良知” (上书卷五),有屡言“捧茶童子却是道也”,“圣人即是常人”、“圣人本是圣人”,认为圣人与常人在本质上并无差异(上书卷二)。他还强调指出:“人人现成,尽是格物”之说乃“古今一大关键。细观古人,惟是孟子一人识得,其他贤大儒总皆忽赂过了” (上书卷七)。总之,在罗汝芳看来,天下万物原是一体之存在,所以,“讲学”是自家“性命所关,不容自已”的人生大事,而“格物”工夫不过是“讲学招牌”而已。
最后,就阳明后学而言,讲学多是学者之间的一种学问切磋,而就泰州学派来看,讲学无非是一种面向民众的教化活动。以何心隐为例,他虽反对严嵩专权,且四处讲学,更以讲学为招牌,在京师“辟四方会馆,”[1],颇显儒侠精神,但他在思想上并无意于与作为王权专制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学相对立,相反地,他自觉以体认并实行孔子和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精神为己任。他曾发挥其师颜钧的“亢龙”说①*①颜钧曾自比为“亢龙”,又修改相关定义道:“如此安身以运世,如此居其所,而凡有血气莫不尊亲,是为‘亢’。”(《颜钧集》卷六《耕憔问答·晰大学中庸》),认为一个真正的君子在社会活动的取向中,只有“成功”与“用功”而无潜、见、惕、跃、飞、亢等因时趋避。传统所谓“潜龙勿用”主要指功成身退,如伊尹、周公;或者是“潜以成功”,如伯夷、叔齐。而孔子则不然:“用功而潜,潜而用功者也,非成功也,虽成功亦用功也。况孔子之用功,非惟用功于潜也,推而六位,莫非用功之位也;非成功也,成功于乾也。乾非龙用,龙以位而成也。乾则时乘乎六位,而时乘乎六位者也,不必用功而功成焉者也,大成也”[32]。他认为孔子因其大成而使其道统摄“六龙”。并且,孔子之道生生不息,永远处在“用功”状态,进行不懈努力的过程,此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真谛所在。至于何心隐欲通过讲学而建立的“会”,乃由师友结集而成,“取象于家”,“取象于身以显乎其家”,君子用之“以显以藏”[32]。这虽多少有点社会组织意味,但也很难说就一定是与王权专制政治相对立的,不妨可称之为“孔子家”②*②耿定向《里中三异传》说:“姚江(阳明)始阐良知,而未有身也;泰州(王艮)阐立本旨,知尊身矣,而未有家也;兹(指何心隐)欲聚友以成‘孔子家’。”(《明文海》卷三九九)。
再看罗汝芳,他“居乡居官,常绎诵我高皇帝《圣谕》,衍为《乡约》,以作《会规》,而士民见闻,处处兴起者辄觉响应”[33]24—25。甫入仕为太湖令,即在当地“立《乡约》、饬《讲规》,敷演《圣谕六条》,倦倦勉人以孝弟为先”[17]921。罗汝芳虽然也喜与心学同志谈玄论道、讲究心性,但他认为心学理论中的抽象思辨、士人群体中的心性议论未免与现实的乡村社会治理脱节,普通百姓需要的乃是契合他们实际的教化内容,士人则应用百姓听得懂的语言进行讲学以教化民众。同时,他又意识到生存于既存社会秩序中的人们,不能仅仅以为依着良知行事即可,还必须服从外在的权威,故而有必要运用官方意识形态这一有效的手段来重整乡村社会秩序,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因此,他一生讲学,多以《太祖圣谕》《乡约》《会规》来对民众进行教化。罗汝芳屡屡称颂太祖朱元璋及其“圣谕”道:
高皇帝真是挺生圣神,承尧、舜之统,契孔、孟之传,而开太平于兹,天下万万世无疆者也。[34]278
惟我太祖即真是见得透彻,故《教谕》数言,即唐虞三代之治道尽矣。惟当时无孔、孟其人佐之,亦是吾人无缘即见隆古太平也。[34]330
……孔子倦倦为政以德,只是志大道之公也。试观我高皇《六谕》,普天率地,莫不知日用平常,仰事俯育,此正王道平平、王道荡荡也。宁非遍为尔德哉?[34]208
高皇《六谕》真是直接孔子《春秋》之旨,耸动忠孝之心。不必言距杨、墨,人人知君父之恩之罔极也。宁非世道一大治,而天下后世获苏生也哉![34]312
孔子谓“仁者人也”、“亲亦之为大焉”,其将《中庸》、《大学》已是一句道尽。孟子谓“人性皆善”、“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其将《中庸》、《大学》亦是一句道尽。然未有如我太祖高皇帝《圣谕》数语之简当明尽,直接唐虞之统,而兼总孔孟之学者也。往时儒先每谓天下太干原无景象,又云皇极之世不可复见。岂知我大明开天,千载一日,造化之底蕴既可旁窥,举世之心元亦从直指。尽数九州四夷之地,何地而非道?尽数朝野蛮貊之人,何人而非道?虽贫富不同,而供养父母则一;虽贤愚不等,而教训子孙则一;虽贫贱不均,而勤谨生理则一。故芳至不才,敢说天下原未尝不太平,而太平原未尝无景象。[34]220
然其皇极世界,舍我大明,今日更从何求也哉?故前时皆谓千载未见善治,又谓千载未见真儒。计此两段原是一个,但我大明更又奇特。盖古先多谓善治从真儒而出,若我朝则是真儒从善治而出。盖我太祖高皇帝天纵神圣,德统君师,只孝弟数语,把天人精髓尽数捧在目前,学问枢机顷刻转回脚底。……窃谓论治于今日者,非求太平之为难,而保太平之为急;谈学问于今日者,不须外假乎分毫,自是充塞乎天地。此样风光,百千万年乃获一见,而吾侪出世忽尔遭逢于此,不思仰答天恩,勉修人纪,敢谓其非夫也已!敢谓其非夫也已![34]220
乃幸天笃太祖高皇帝,神武应期,仁明浴日,浊恶与化俱徂,健顺协时通泰,孔、孟渴想乎千百余年,而《大易》、《春秋》竟成故纸!大明转移于俄顷呼吸,而大统真脉皎且当天,况兹圣子神孙方尔振振绳绳,则我臣庶黎元亦可皞皞熙熙。芳自弱冠登第以逮强壮,观京师近省,其道德之一,风俗之同,不须更论,及部差审录而宣大山陕,取道经由,至藩臬屯团而云贵川广,躬亲巡历,不惟东南极至海涯,且西北直临塞外,每叹自有天地以来,惟是我明疆土宏廓。至尊君亲上、孝父从兄,道德虽万里而无处不一;衣冠文物、廉耻内外,风俗虽顷刻而无时不同。故前谓皇极之世,自尧舜三王以来,惟我明足称独盛。[34]197-198
他圣化“高皇”,对现实政治状况充满乐观情绪,认为“高皇”开创的有明一代足以与尧舜三代相媲美,宣称儒家经典中的仁礼思想“二千年来尚未见人说破”,到了我大明太祖高皇帝及其“圣子神孙”们才接绪“真脉”,并由此开出太平盛世,使得普天之下,不论是“九洲四夷”还是“朝野蛮貊”,不论是“东南西北”还是“海涯塞外”,虽然“贫富不同”、“贤愚不等”、“贵贱不均”,但道德风俗“无处不一”、“无时不同”,“此样风光,百千万年,乃获一光”,实在是“天下大同”、“万物一体”的美好景象。生活在这样一个极其美好社会里的臣民百姓,自然只须谨遵《圣谕》和《大明律》就可以了。
杨复所对乃师罗汝芳之学评曰:“罗子之学,实祖述孔子而宪章高皇。盖自江门(陈献章)洗著述之陋,姚江(王阳明)揭人心之良,暗合于高皇而未尝推明其所自,则予所谓莫知其统者也。姚江一脉,枝叶扶疎,布散寰宇,罗子集其成焉。”[35]
从罗汝芳的讲学内容中不难看出其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教化民众,以期更有效地维持既存社会秩序,这就是泰州学派讲学于民间的实质意义所在。然而,即便如此,遍及朝野的讲学,尤其是在底层民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泰州学派讲学活动,难以为厉行文化专制主义的张居正所容。嘉靖丙寅年(1566年),颜钧曾被捕入狱。他是因讲学独忤当道,被官方目之为“少正卯”而想加以诛杀,才遭捕入狱的。所谓“盗卖淮安官船”,是在反复查证,“并无一处指证”其过犯的情况下作出的“强诬”之辞。封建专制政治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颜钧身陷囹圄,受尽折磨(“刑棒如浆烂,监饿七日,死三次,继遭瘟痢,共将百日”),幸喜未死,终经其弟子罗汝芳多方设法,募金“完赃出戍”[36]。而其学生何心隐则无此幸运,不得不因反对明廷文化专制、捍卫讲学自由而献身。谷应泰记之曰:
江西永丰人梁汝元聚徒讲学,讥议朝政。吉水人罗巽亦与之游。汝元扬言江陵首辅专制朝政,必当入都,昌言逐之。首辅微闻其语,露意有司,令简押之。有司承风旨,毙之狱。已而湖广贵州界获妖人曾光等,造为妖语,煽惑土司。事发,遂并入汝元、罗巽姓名于内。且号汝元为五知子,罗巽为纯一真人。云其惯习天文遁甲诸书,欲因彗星见,共谋不轨。汝元已先死,罗巽亦继毙狱,竟不成。湖广抚臣但具爰书以闻。已,下法司审讯,并曾光亦非真也,但据律发遣而已。[37]
邹元标《梁夫山传》亦谓:何心隐“居燕畿聚徒讲学,因与司业江陵张公(即张居正——引者注)屡讲不合,遂构衅端。比江陵柄国,即首斥讲学,毁天下名贤书院,大索公、凡讲学受祸者不啻千计,即唐之清流、宋之朋党是也。公归,葬两尊人,遂庐墓焉。未逾期年,而南安把总朱心学辑之,获解楚。巡抚王夷陵惟知杀士媚权,立毙杖下”[38]。泰州学派另位传人,并对颜钧、罗汝芳、何心隐景仰之至的平民儒者李贽①*①李贽自谓:“心斋之子东崖公,贽之师。东崖之学,实出自庭训。”(《续焚书》卷三)他称颂颜、罗、何的言论甚多,兹难详举。《林李宗谱·卓吾公传》更明确以其与心隐接近。,其遭遇更为惨烈。他“掊击道学,抉摘情伪。与耿天台往复书,累累万言。胥天下之为伪学者莫不胆张心动,恶害己,于是咸以为妖为幻,噪而逐之”[39],以至其一生居无定所,颠沛流离万历二十五年(1601年),明廷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将他逮捕,“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行烧毁,不许存留”[40]。次年,这位76岁高龄的思想斗士在狱中以剃刀自刭。
一个王朝社会连面向大众进行教化的讲学运动都不能容忍,这既表明其专制政治已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同时也表明其自身调节功能已丧失殆尽。
透过以上所述,我们所当思者应是:总结泰州学派平民儒学的历史经验,如何立基当下,在现实的社会生产生活基础上实现儒学理论的现代转换,即怎样突破儒家士大夫的传统之见及其现代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限制,将儒学发展成为适应于当下普通百姓生活日用的平民儒学?笔者以为这正应是我们今天纪念罗汝芳诞辰五百周年时最应思考并努力寻求答案的大问题。
[1]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M].台北:学生书局,1979:288.
[3]罗汝芳.盱坛直诠·卷下[M].台北:广文书局,1968.
[4]罗汝芳.盱坛直诠·卷上[M].台北:广文书局,1968.
[5]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M].袁承业,编校.(清)宣统二年(1909)四月东台袁氏据原刻本重编校排印.
[6]颜钧.颜山农先生传[M]//颜钧集·卷九附录一.黄宣民,编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82.
[7]程颢.河南程氏遗书·卷二[M].[公共版权]:15.
[8]王艮.启名公书略·上昭阳太师李石翁书[M]//王东崖先生遗集·卷一.宣统二年(1909)东台袁氏编校本.
[9][明]罗汝芳,撰.罗汝芳集·近溪子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10]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1]王宗沐.龙溪王先生集旧序[M]//王龙溪文集.[出版地不详].
[12]徐阶.龙溪王先生传[M].[出版地不详].
[13]王阳明.年谱附录一[M]//阳明全书·卷三十五.[明隆庆末年(1572)].
[14]王阳明.年谱附录二[M]//阳明全书·卷三十五.[明隆庆末年(1572)].
[15]颜钧.著回何敢死事[M]//颜钧集·卷五.黄宣民,编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16][明]焦竑.古城问答[M]//澹园集·卷四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95.
[17]杨起元.罗近溪先生墓志铭[M]//罗汝芳集·附录.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18][明]罗汝芳撰.罗汝芳·近溪子集·卷御[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19]谭希思.皇明理学名臣传[M].罗汝芳集·附录.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20][明]周汝登.圣学宗传·罗汝芳[M].罗汝芳集·附录.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21]王时槐.近溪罗先生传[M].罗汝芳集·附录.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22]刘元卿.近溪罗先生传[M].罗汝芳集·附录.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23]王阳明.传习录中[M].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4]王一庵.会语正集[M]//王一庵先生全集·卷上.宣统二年(1909)东台袁氏编校本.
[25]耿定向.王艮传[M]//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四.宣统二年(1909)东台袁氏编校本.
[26]凌儒.祠堂记[M].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四.宣统二年(1909)东台袁氏编校本.
[27]王艮.重镌心斋王先生全集·卷二[M].王元鼎,补遗.宣统二年(1909)东台袁氏编校本.
[28]耿天台先生全集·卷十四[M]//王心斋先生传.今见傅秋涛点校《耿定向集》(上)·卷之十四,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9]李贽.罗近溪先生告文[M]//焚书、续焚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125.
[30]罗近溪.语录[M]//罗近溪先生全集·卷七.今见方祖猷等编校整理《罗汝芳集》(上),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
[31]罗汝芳.罗近溪先生明道录·卷三[M].//京都.中文出版社和刻近世汉籍丛刊本.
[32][明]何心隐.论潜[M]//何心隐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
[33]罗汝芳.罗近溪先生明道录·卷一[M].//京都.中文出版社和刻近世汉籍丛刊本.
[34]罗汝芳.近溪罗先生一贯编[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86册.明长松馆刻本.
[35]杨起元.太史杨复所先生证学编·卷三[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90册:347-348.
[36]颜钧.自传[M]//颜钧集·卷三.黄宣民,编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28.
[37]明神宗实录·卷九五.[M].上海:上海书店,1990:1915-1916.
[38]何心隐.何心隐集·附录[M].容肇祖,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60:121.
[39]钱谦益.列朝诗集·闰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7.
[40]明神宗万历实录·卷三六九[M].[出版地不详].
责任编辑 何志玉
Luo Rufang’s Spirit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the Political Tendency of His Thought
CHEN Han-ming
(Tianjin Trade Union Administrations College, Tianjin300380, China)
Luo Rufang was the backbone of the Taizhou Wang School, and he had mor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than his teacher——Yan Jun(Shan Nong). His thought came from Zhou Yi, inherited Confucius and Meng Zi’s thoughts, mastered Confucianism and Zen, and promoted Wang Yangming and Taizhou Shinsaibashi’s school. In his lifetime, he not only dedicated to academic researches, but also keen to give lectures. And he was engaged in politics around Taihu Lake, Ningguo House, Yunnan, etc. In the dirty officialdom, he took a benevolence to implement education and dissected the essence of "conscience" with an "innocent heart" , therefore, he cowed countless beings into submission, and this fully reflects the strong spirit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Late Ming Dynasty; Luo Rufang; Yangming school; Taizhou school; Lecture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2016-03-17
陈寒鸣(1960-),男,江苏镇江人,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儒学史。
B248.3
A
1673-6133(2016)03-0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