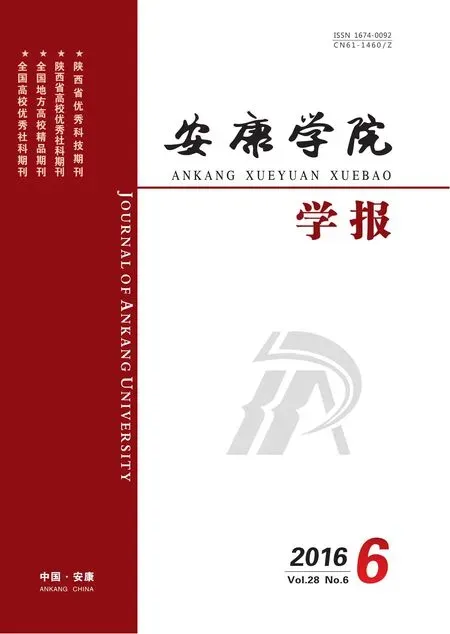论抗战时期作家迁徙与四十年代新文学中心的形成
祝学剑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外语学院,广东 深圳 518172)
论抗战时期作家迁徙与四十年代新文学中心的形成
祝学剑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外语学院,广东 深圳 518172)
抗战时期作家迁徙是四十年代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宏观上看,四十年代作家迁徙使中国现代文学格局重新洗牌,催促了新的文学中心的产生。具体而言,由于作家迁徙,京沪文学中心逐渐沦陷,与此同时,在昆明、延安、重庆、桂林形成了新的文学中心。
作家迁徙;四十年代;新文学中心
1937年爆发的抗日战争,不仅影响了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而且极大改变了中国现代作家的生存方式和人生轨迹,既而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东北华北等地相继沦陷,战争打破了中国现代作家宁静的书斋和日常的写作方式,作家生活的城市沦陷,家园被毁,而不得不被迫进行迁徙。他们或从关内流亡到关外,或从沦陷区迁徙到国统区、解放区。战争迫使作家在四十年代开始了颠沛流离、亡命天涯的迁徙历程。茅盾在抗战爆发后从上海辗转到武汉、长沙、广州、香港等地,又因战争流亡到新疆,最后脱险返回延安,随后迁徙到重庆继续从事革命工作。胡风、夏衍等作家也大多历经颠沛流离,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中国现代作家在迁徙过程中,依然不忘自己肩负的使命,高举文学旗帜,以手中的笔为武器同敌人进行斗争,写文章揭露打击敌人,继续用文艺为抗战服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篇章。作家迁徙是四十年代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亦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作家迁徙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宏观上的影响,使中国现代文学格局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也有微观上的影响,直接影响了四十年代作家的文学创作。
从宏观上看,四十年代作家迁徙使中国现代文学格局重新洗牌,催促了新的文学格局和新的文学中心的产生。自五四伊始,中国现代文学基本以京沪为中心,到四十年代,这种情形有了根本的改变。由于作家迁徙,京沪文学逐渐沦陷,与此同时,在昆明、延安、重庆、桂林形成新的文学中心。司马长风说:“1937年以前,中国的文学始终以上海和北平为中心,但进人凋零期,几乎就没有固定的中心了。没有固定的中心,便出现了临时性的多元中心。”[1]3而这在以前是不曾有的,作家迁徙与四十年代新文学中心的形成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新的现象,值得深入研究。
一、作家迁徙与西南文学中心的形成
四十年代虽然因东南沿海诸城沦陷,京沪等传统的文学中心也逐渐沦陷,但在当时文化并不发达的西南大后方昆明,文学却出现了勃勃生机,形成以昆明为中心的西南文学中心。究其原因,由于战争影响,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迁移到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随着高校内迁,一批文化精英和名作家迁徙到昆明,使昆明的文学繁荣起来,形成西南文学中心。
抗战爆发后,为了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延续中华文化血脉,培育保存民族抗战复兴力量,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先是迁至长沙,组建临时大学,后又决定迁往昆明。临时大学三校2000多学生分三路向昆明迁移。陆路则由身体合格的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采用军事组织形式,闻一多、许维遹、李嘉言、黄钰先、袁复礼、李继侗、曾昭抡、吴征镒、毛应斗、郭海峰等11位教师参加湘黔滇旅行团,跋山涉水3500里,到达昆明。此外,还有老师另辟道路,走另外一条路,乘分程包租汽车从长沙出发,经南宁、龙州、安南,再乘火车到昆明。人员有陈岱孙、朱自清、冯友兰、钱穆、汤用彤、贺麟等十多人,由朱自清任团长。此路虽然乘车,但也长途劳顿,历尽艰辛。第三条是水路,比较方便迅速,经粤汉铁路至广州转香港,然后乘船入安南,再乘火车入昆明,安排女生、教师、体弱学生走这条路。陈寅恪等走的就是这条路。
随着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迁移到昆明组建西南联大,一批学者型作家也随之一起迁徙到西南昆明。这些人有清华大学的朱自清、闻一多、吴宓、钱钟书、闻家驷、叶公超、陈铨等,北京大学的李广田、卞之琳等。这些在高校以教书为职业的作家,他们作为学校一份子也随着学校一起跋山涉水,流亡迁徙到昆明,继续教书育人,也继续从事文学事业。此外,还有青岛大学杨振声、沈从文等也受聘于西南联大,迁徙到昆明。西南联大还聘请了从德国留学回来的诗人冯至,聘请了陈梦家、潘家洵等,这么多的作家迁徙荟萃昆明,西南文学中心初具规模。此外,在这些教师作家的影响下,在西南联大读书的一批学生,文学活动也很活跃,他们是西南文学中心的后起之秀,穆旦、郑敏、杜运燮、王佐良、袁可嘉、赵瑞蕻、杨周翰、罗寄一、马逢华、叶华、俞明传、秦泥、林蒲、周定一、缪弘、沈季平、何达、陈时、汪曾祺、吴讷孙、辛代(方龄贵)、刘兆吉、马尔俄(蔡汉荣)、林元(林抡元)、卢静等为西南文学中心的文学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西南文学中心作家群有一显著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是中国当时的文化精英,大都学贯中西,有着深厚的文化积累和良好的文学素养。西南联大老师大都是学者型作家,诸多人从国外留学回来,并拥有博士头衔,如冯至、林同济、陈铨等。西南联大学生作家也绝非等闲之辈,他们不仅具备良好的文学素养与艺术才情,而且正当风华正茂的文学年龄,他们的文学视野更加开阔,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受到外国文学尤其是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较多,他们的创作更加深入到生命、宇宙、存在的哲学层面。西南文学中心作家群由一群有着很好文化积累和文学素养的知识分子组成,这在四十年代是一个十分独特的存在。
在创作实绩上,沈从文推出生命中最后的长篇小说《长河》,诗人散文家李广田创作了小说《引力》,诗人冯至创作了诗化叙事体小说《伍子胥》,汪曾祺创作了《复仇》 《小学校的钟声》等,这些创作都对中国现代小说可能的发展样式做出了新的探索。不仅小说,西南诗人群还是中国新诗的探索者,这表现在西南联大汇聚了闻一多、冯至、卞之琳、李广田等诸多悉已成名的诗人,英国著名的诗人和新批评家威廉·燕卜荪也加盟西南联大,在这些悉已成名的诗人周围还聚集着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诗人,包括穆旦、郑敏、杜运燮、王佐良、袁可嘉、赵瑞蕻等。这些年轻学生诗人大胆超越传统,具有反叛性和异质性,不仅改变了中国新诗的观念,而且在诗歌创作上使中国现代诗歌达到新的高度。穆旦的《被围者》 《防空洞里的抒情诗》 《从空虚到充实》 《赞美》 《诗八首》等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郑敏的《树》 《寂寞》 《金黄的稻束》和杜运燮的《滇缅之路》等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收获。
在四十年代,如此多的新文学名家聚集西南联大,他们潜心治学,专心写作,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中续写着中国现代文学新的辉煌篇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西南文学中心在抗战时期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它不仅在抗战的烽烟中培养了众多文学人才,而且以鲜明的创作实绩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作家迁徙与延安文学中心的形成
1935年10月,中央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文化建设,出台了优待和吸引知识分子的政策,吸引知识分子到延安从事文学文化工作。如延安颁布实施《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同时还颁布了优待知识分子的相关政策。一时间,来自四面八方的知识分子迁徙荟萃延安,有文学家、文艺理论家、艺术家、哲学家等等。截至1943年12月底,奔赴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有4万余人[2]。许多作家历尽艰辛迁徙奔赴延安,为延安的文学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
作家迁徙到延安使延安文学兴盛起来,延安成为四十年代新的文学中心,成为四十年代文学重要的一极。作家迁徙对延安文学的繁荣影响甚大,是形成延安文学中心的充要条件,如《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总序指出:“解放区的作者队伍大多数是当民族解放炮声响起的时候,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奔赴延安,奔赴各个抗日根据地,奔赴八路军、新四军的爱国青年,加上当地土生土长的文艺战士,和一批先后来自国统区的成名作家所组成……”[3]1936年,丁玲在南京经秘密营救出狱后奔赴延安,成为第一个到达延安的著名作家,“昨天文小姐”变成“今日武将军”,成为延安文学的开拓者之一。周扬在奔赴延安之前就是一个职业革命家,是上海左联的实际领导人。后因两个口号的论争,周扬受到鲁迅的公开批评。为此,周扬的心理压力比较大,觉得自己继续在上海工作很难了。1937年9月,周扬夫妇带着一岁的小孩,和李初梨、艾思奇夫妇、何干之夫妇、周立波、林基路、李云阳、舒群等一行十二人,从上海去了延安。何其芳是著名的汉园三诗人之一,在国统区不满现实的丑恶,但又找不到出路,对国民党统治下社会不满,并进而对自己的懦弱孤独性格和瑰丽的诗歌也产生了不满。于是何其芳与卞之琳等一起奔赴延安,开始了人生新的旅程。陈学昭,浙江海宁人,后入南通县立女子师范学校、上海爱国女子学校等学习,后留学法国十年,1935年获得法国克莱蒙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战火纷飞,随着行医的丈夫何穆四处奔走,生活并不安稳,1940年,因在国统区物价昂贵,没有人身自由,生存艰难,陈学昭破釜沉舟,烧掉她所有的书籍、学位证、照片等资料,与过去说再见,毅然奔赴心中的理想之地延安。王实味1906年出生在河南潢川一个破落举人家庭。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班。因经济上的逼迫与困境,王实味只得辍学离开北大到南京谋生。失学后王实味陷入生活的困顿中,在生活的窘境中苦苦挣扎。1937年,抗日的烽烟已经燃遍整个中国,此时的王实味才决定离开国统区去延安,他带着几位学生一路颠簸到延安。狂飙文人高长虹与鲁迅等人论争后流浪日本、欧洲等地,因生活非常困窘,无法谋生,抗战爆发后,他悄悄经意大利、英国到了香港,又辗转到武汉、重庆、西安等地。1941年秋天,高长虹徒步走到延安。此外,萧军、马加、方纪、萧三、孔厥、白朗、艾青、周立波、成仿吾、孙谦、欧阳山、黄源、周文、陈登科、柳青、严文井、贺敬之、孙犁、吴伯萧、杨朔、李季、刘白羽、马烽、张光年(光未然)、冯牧、吴强、穆青、西戎等一大批文学名家或者文学青年迁徙到延安,给延安文学注入新的活力。无需多举例子,作家迁徙到延安,促使延安文学兴盛起来,延安的文学创作、文艺研究、文学教育、文学期刊形成比较完整的文学链条,成为四十年代文学中心之一。
延安文学作为四十年代文学中心,不仅文学作品数量丰富,而且有着自己的特点和美学风范,它是一种崭新的文学现象。在《讲话》精神指引下,延安作家深入农村与普通百姓同吃同睡,文学与民间结合,多采用陕北民众喜闻乐见的传统文学形式,语言上多采用民众的大众语言。延安作家张庚曾经自豪地说:“我们的秧歌都是用陕北话写的,也用陕北话演,我们在语言上的确比从前那种清汤寡水的普通话活泼生动得多了。”[4]这些都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新的特点。延安文学对根据地军民生产斗争进行了全方位扫描,歌颂了根据地军民英勇顽强、机智勇敢的斗争精神,对日伪的残暴无耻进行了鞭挞。孙犁的《荷花淀》《芦苇荡》,丁玲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雷加的《炮位周围》 《一支三八式》,邵子南的《地雷阵》,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等表现了根据地军民的爱国精神和斗争精神,富有时代的气息。还有表现土地改革、减息减租等方面的,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表现破除封建婚姻方面的,如《小二黑结婚》等等。总之,延安文学都表现了根据地的新人,也表现出新的生活形态风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是迥异于以前的。
延安文学在文学创作、文学教育、文学刊物、文学社团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形成完整的有机体,它是一种新型文学,这种新型文学弥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某些不足,这是比较少见的。
三、作家迁徙与重庆文学中心的形成
为了适应长期抗战的局面,统筹抗战全局,1937 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作为抗战时期中国经济比较落后的西南内陆城市,迁都后重庆一跃成为战时首都。随即,全国高校如复旦大学、国立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院、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等迁到重庆,一些文化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独立出版社、作家书屋等也迁到重庆。
与此同时,大批文化人迁徙到重庆,重庆成为战时文化精英荟萃的文化之城,成为四十年代另外一个文学中心。迁徙到重庆的作家包括郭沫若、茅盾、胡风、碧野、老舍、曹禺、巴金、田汉、梁实秋、洪深、夏衍、阳翰笙、宋之的、方殷、王平陵、潘公展、范争波、吴祖光、葛一虹、杨骚、陈白尘、沙汀、白朗、罗烽、陈白尘、以群、罗荪、姚雪垠、袁水拍、光未然、臧克家、陈晓南、艾芜、吴组缃、姚雪垠、张天翼、张恨水、靳以、杨塑等。据统计,抗战期间奔赴到重庆从事抗战文化文学工作的作家就有121人,被誉为“战时最大的作家集团”[1]6-7。这里可以略举例子一二,具体说明作家迁徙与重庆文学中心形成的关系。抗战前夕,胡风在上海从事抗战文艺工作,创办了《七月》杂志,共出了三期。抗战爆发后,由于“商业联系和邮路受到阻碍,上海的刊物很难发到外地去,作者又纷纷离开上海”,所以胡风“决定把《七月》移到武汉去出版”[5]。因此,胡风带着家人迁徙到武汉继续编辑出版《七月》,还从事诸多抗战文艺工作,如举办木刻展览会,编辑《新华日报》文艺副刊《星期文艺》,筹备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由于武汉离前线越来越近,胡风于1938年9月匆匆离开武汉,坐船途径石首、宜昌等地,辗转到重庆,在重庆继续编辑出版《七月》,使《七月》成为影响四十年代重庆文学的重要刊物。老舍也何尝不是如此。抗战爆发后,老舍在济南平静的写作生活被打破,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最后决定独自离开,依依不舍地逃亡到武汉,后又迁徙到重庆。在重庆领导文协的日常工作,编辑《抗战文艺》,从事抗战文艺工作。抗战爆发后,作家萧红与萧军来到武汉,后又一同辗转到临汾民族革命大学,由于两人感情不和,萧红在临汾与萧军分开后,独自重回武汉。后日军进攻武汉,萧红独自一人坐船迁徙到重庆,继续从事抗战文艺工作。无需再举例子,作家迁徙到重庆,创作文学作品,从事抗战文艺工作,使文学的幼苗在重庆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所以,由于重庆作为战时陪都,得天独厚的环境,使许多作家迁徙奔赴重庆,重庆成为四十年代文学中心。
作为四十年代文学中心之一,重庆作家的构成比较庞杂,既有民主主义倾向的老舍、曹禺、巴金等人,又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梁实秋等人,还有国民党宣传部门的王平陵、潘公展、范争波等人,更多的是左翼作家郭沫若、茅盾、田汉、阳翰笙、宋之的等。所以这些不同倾向的作家汇聚重庆,以“文协”为旗帜从事抗战文学活动,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到前线、到乡村去采访创作,使文学服务于抗战实际。不同派别、不同立场的作家聚集在重庆这个特定的时空从事文学活动,并无共同的创作思想和一致的创作特征,呈现自由绽放的态势。《华威先生》 《霜叶红于二月花》 《腐蚀》 《寒夜》 《火葬》 《淘金记》 《财主的儿女们》 《四世同堂》 《春寒》 《前夕》 《故乡》 《山洪》 《雾城秋》 《雾都》 《新都花絮》等一批在四十年代有影响力的作品脱颖而出。
重庆作为抗战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吸引了大批作家的到来。这些作家以其实际的创作实绩和文学活动,使重庆成为四十年代国统区名副其实的文学中心。
四、作家迁徙与桂林文学中心的形成
桂林,抗战时期又一文化名城,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汇聚了大批从西面八方来的文化名人。武汉、广州、上海等沦陷区的作家纷纷汇聚桂林,随着作家及文化人士的到来,桂林文学活动一下子活跃起来,使原本是文学荒漠的桂林一下子变成了四十年代新的文学中心。桂林的文学活动从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大批文化人涌进桂林开始,到1944年9月日军进攻桂林湘桂大撤退结束,前后长达六年时间。这一时期,桂林的文学创作和文艺运动十分活跃,文人荟萃,少长咸集,当时活动在桂林的文化人士超过上千名,成为抗战时期真正的文化名城,成为四十年代新的文学中心。
抗战爆发后,辗转迁徙到桂林的作家及文化人士,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切实投入到抗战救亡文化运动当中。夏衍出生在浙江杭州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后留学日本,归国后一直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学活动。抗战爆发后,夏衍与郭沫若等一起在上海创办《救亡日报》,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没多久,战争威胁上海,上海沦陷,《救亡日报》无法继续在上海办刊。战争迫使夏衍等人离开上海,迁徙广州,因为“广州则又是一个对外——特别是对东南亚华侨宣传团结抗战的重要基地”[6],且还没有战事。所以,夏衍将《救亡日报》迁到广州复刊。然而,广州并不平静,日军经常来轰炸广州,造成惨案。广州沦陷后,战争又逼迫着夏衍和《救亡日报》一起离开广州,迁徙到大后方桂林继续办报,宣传抗日。夏衍在桂林编辑《救亡日报》,创作话剧《心防》,以及大量政论文章和杂文,给人直接的鼓舞。著名诗人艾青1938年11月迁徙到桂林,参加文协桂林分会筹备等文化工作,在桂林写下了真挚厚爱、饱含热泪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芜1939年1月到桂林,从事文艺创作与编辑工作,在敌机轰炸中仍奋力创作《山野》 《故乡》等小说。此外,迁徙到桂林从事抗战文艺活动的作家还有郭沫若、茅盾、巴金、柳亚子、夏衍、王鲁彦、胡风、邵荃麟、周立波、黄药眠、丰子恺、王西彦、方敬、以群、叶圣陶、田汉、白薇、冯乃超、冯雪峰、司马文森、邢桐华、安娥、李辉英、杨塑、丽尼、吴奚如、何家槐、易巩、谷斯范、林林、林焕平、欧阳予倩、周钢鸣、孟超、胡风、胡愈之、邹荻帆、袁水拍、骆宾基、秦牧、聂绀弩、徐迟、黄药眠、彭燕郊、舒群、廖沫沙、端木蕻良、熊佛西、柳嘉、罗淑等。此外还包括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爱金生、鹿地亘、李斗山等外籍作家。这些作家、文化人聚集在桂林,积极开展抗日文艺运动,以手中的笔为武器,不屈不挠地战斗着,创作了许多四十年代颇有影响的小说。这些小说主要集中在抗战、历史和揭露社会问题等方面。艾芜的《山野》 《故乡》、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谷斯范的《新水浒》、王西彦的《一双鞋子》、何家槐的《雨夜》、蒋牧良的《夜袭》、司马文森的《南线》、易巩的《彬寮村》、骆宾基的《姜步畏家史·幼年》、舒群的《渔家》等作品都是桂林文学的重要收获。
此外,作家迁徙也促进了桂林出版业的空前繁荣,因为作家不仅要创作作品,而且还要出版投入市场。这一时期桂林的文艺出版和文艺刊物的繁荣真正体现了当时“文化城”的特点和成就。散文家丽尼曾在文章中感慨道:“桂林的街头,最容易触目的,是贩卖精神粮食的书报店的增加率,和贩卖粮食的饭菜管等量齐观。”[7]首先,桂林的出版业在抗战时期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勘称抗战时期的出版之城。抗战前,桂林的报刊、书店、出版社仅有几家,随着全国各地的作家与文化人士迁徙到桂林,桂林的报刊、书店、出版社迅速多起来。据统计,这一时期桂林共有书店、出版社一百七十九家,印刷厂多达一百零九家,“共出版发行各类杂志二百多种,其中文艺期刊将近一半,纯文学期刊三十六种,综合性文艺期刊五十二种。报纸也从原来只有一家的《广西日报》,猛增到二十一家”[8]。四十年代在桂林开设的书店出版社包括生活书店、新知书店、正中书局、读书生活出版社、开明书店、建设书店、青年书店、武学书店、科学书店、大千书店、白虹书店、黎明书店、华华书店、时代书店、前导书店、地界书局、北新书局、中华书局、上海杂志公司、前导书局、拔提书店、青年书店、国防书店、中国文化服务社、大华杂志公司、新生图书公司、东方图书公司、文化供应社、三户图书社、西南印刷厂、南方出版社、文献出版社、石火出版社、今日文艺出版社等,这些都比较出名。与之相应,出版了一批比较有影响的文学刊物,包括《野草》 《文艺杂志》 《文化杂志》 《文艺生活》 《文学创作》 《戏剧春秋》 《国民公论》 《中国诗坛》 《自由中国》 《人世间》 《青年文艺》 《创作月刊》 《中国论坛》 《顶点》 《当代文艺》等。这些都说明桂林是四十年代新的文化名城、新的文学中心,这是中国文学的一道特别风景线。
从以上对四十年代四个文学中心的形成的探析,
可以看出作家迁徙对四十年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中国现代文学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作家迁徙使传统的京沪文学中心沦陷,而催促昆明、延安、重庆、桂林等地文学的繁荣,形成了新的文学中心。“这是抗战激流中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和文学的一次绝无仅有的历史性大转移。它不仅导致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和文学中心的转移,更促使中国思想文化和文学发生了质的变化。”[9]作家迁徙,不仅以自己切实的行动,书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歌可泣的篇章,而且催促了中国现代文学格局的重塑,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是不曾有过的现象,这也是作家迁徙带给中国现代文学的冲击和影响。
[1]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卷)[M].香港: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
[2]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79.
[3]殷白.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总序[M]//康濯.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小说编(一).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4.
[4]张庚.鲁艺工作团对于秧歌的一些经验[N].解放日报,1944-05-15.
[5]晓风.胡风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70.
[6]夏衍.夏衍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1996:130.
[7]丽尼.战期中桂林文化的动态[J].(桂林)克敌周刊,1939 (23).
[8]蔡定国,杨益群,李建平.桂林抗战文学史[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1994:3.
[9]张武军.北京、上海文学中心的陷落与重庆文学中心的形成—略论抗战对中国现代文学格局的影响[J].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05(2):78.
【责任编校 曹 刚】
Comment on the Coming of the New Literature Center in the 1940s
ZHU Xuejian
(School ofFofeignLanguages,ShenzhenInstituteofInformationTechnology,Shenzhen518172,Guangdong,China)
Writer’s migrationinThePeriodof Anti-JapaneseWar was animportant literary phenomenoninthe1940s,and had aprofoundimpactonliteratureofModernChineseliterature.Fromamacropointviews,writer’smigrationinthe1940sreshuffledthepattern ofChinesemodernliterature,andbroughtaboutthenewliteraturecenter.Specifically,theliteraturecenterinBeijingandShanghai falledgradually,andat thesametime,theChinesemodernliteratureformedthenewliteraturecenter in Kunming,Yan’an,Chongqing andGuilinbecauseofthewriter’smigration.Writer’smigrationhadaprofoundimpactonliteratureinthe1940s.
writer’smigration;1940s;newliteraturecenter
I206.6
A
1674-0092(2016)06-0053-05
10.16858/j.issn.1674-0092.2016.06.011
2016-04-2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浴火新生——四十年代作家迁徙与文学研究”(15YJC751067)
祝学剑,男,湖北江夏人,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应用外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文秘写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