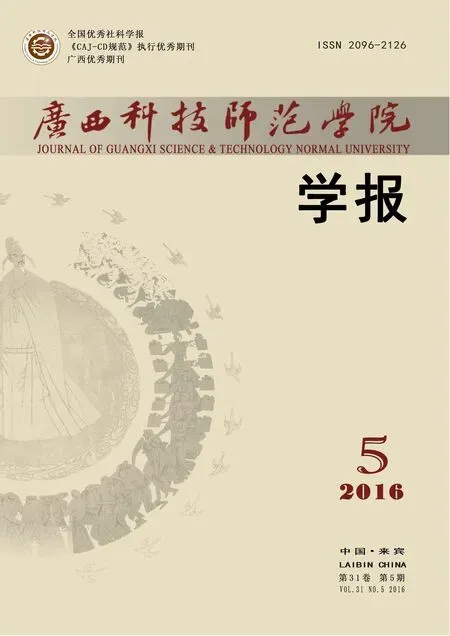汤姆斯中国古典文献翻译惯习解读
(安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安庆 246001)
汤姆斯中国古典文献翻译惯习解读
钱灵杰,操 萍
(安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安庆 246001)
19世纪上半期英国汉学家汤姆斯翻译了大量中国古典文献,他从事翻译活动、确定翻译选材、运用翻译策略等一系列行为均是自身惯习的象征性体现。汤姆斯借助中国文献英译实践实现了从“印刷工”到“汉学家”的身份代码转换。其翻译选材以中国古代文学、历史作品为主,满足了社会政治场域的需要。汤姆斯灵活运用直译、意译与注释等多种翻译策略,能够深化读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汤姆斯;中国古典文献;翻译;惯习
19世纪上半期,英国汉学处于草创与发展阶段,学界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围绕“英国汉学之父”小斯当东、“英人研究汉学一代宗匠”马礼逊、外交官汉学家的代表德庇时等人,认为他们具有开创之功,为英国汉学发展做出了基础性贡献。实际上,这一时期英国汉学的代表人物远不止上述三位。其中,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印刷工汤姆斯(Peter Perring Thoms)尤为引人注目。他因在刊印《华英词典》等出版物的过程中,改进合金活字印刷术,满足了中英文合印的需要而名垂青史。同时,他还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古典文献,客观上推动了中学西传,“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汉学家”[1]133。现有文献介绍汤姆斯时,往往只注意到他的印刷者身份,针对其翻译活动的探讨并不多见,仅有梁启昌[2]、王燕[3]、郑锦怀[1]等学者以汤姆斯《花笺记》英译本为对象开展了相关研究,从文学史、汉学史角度肯定了他对中西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本文关注汤姆斯的译者身份,基于译者惯习理论研究汤姆斯的中国古典文献英译活动,以期弥补学界相关研究的片面性。
一、“惯习”概念解读
早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解释“摹仿”(imitation)时曾说:“摹仿发端于人的幼年,但却对今后的人生影响深远,并最终形成习惯,构成‘第二本性’,进而影响人的身体、声音乃至心智”[4]11,而“惯习”正是在“习惯”和“第二本性”的基础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也曾提出过与“惯习”类似的概念“hexis”,认为其“取决于人的年龄、性格、社会地位等因素,会在个人风格中再现”[5]97。到了近代,德国社会学家埃利阿斯在谈到人类面对的限制时,提出了“自我限制”(Selbstzwange)的说法,与“惯习”十分类似。对“惯习”论述最为系统的当属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自1967年起他屡次详细阐发这一重要概念的意义及功能,并将其与“场域”、“资本”等其他概念贯穿连接,构建了完整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在布迪厄看来,惯习是“让行动者以某种方式行动和做出行为反应的秉性系统”[6]84,“这一系统反映出人在成长、家庭教育、学校学习、工作、交际等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学习、内化并强化了的社会规律”[7]82。惯习“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存在于个体身体之中,具有生成性、建构性,甚至带来某种意义上的创造性能力,表明了主体选择的目的性”[6]83。翻译作为一种人类实践,是译者主体作用于译本客观实体的过程,离不开意识的选择,必然受到译者惯习的指挥与影响。具体而言,译者从事翻译实践、确定翻译选材、运用翻译策略等一系列行为均是自身惯习的象征性体现。本文对汤姆斯英译中国古典文献活动的考察也正是基于上述三点展开。
二、借助中国文献英译活动实现身份代码的转换
1814年9月2日,汤姆斯应英国东印度公司招聘来华,以印刷工身份在澳门印刷所从事书籍刊印工作。作为职业技工,汤姆斯研制了中国第一批铅合金活字,并利用其专业技术印制了《中文作品英译》(Translation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贤文书》(Hien Wun Shoo:Chinese Moral Maxims with a Free and Verbal Translation)等多种出版物。值得一提的是,由汤姆斯主持印刷的书籍,封面上不仅印有著译者或编纂者的名字,往往还可以发现诸如“Printed by P.P.Thoms”(由汤姆斯印刷)之类的明显字眼。由此可见,“为了自我推销,他似乎不肯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哪怕是作为一个印刷者”[3]209,汤姆斯对身份代码的重视逐渐在其个人意识中沉淀、内化,从而形成惯习,指挥调动了他的行为方向,成为他在从事印刷工作的同时主动选择翻译实践的根源。
早在1820年,汤姆斯就已将《三国演义》第一至九回中的章节片段翻译成英文,以《著名丞相董卓之死》(“The Death of the Celebrated Minister Tung-cho”)为题发表在《亚洲杂志》(Asiatic Journal)。同年,汤姆斯翻译了《今古奇观》第十四回《宋金郎团圆破毡笠》,译本《一对爱侣的故事或宋金情史》(The Affectionate Pair or The History of Sung-Kin:A Chinese Tale)以单行本形式在伦敦刊印出版。1824年,汤姆斯英译了《花笺记》全文以及《百美新咏》、《后汉书》中的部分内容,结集为《中国求爱诗》(Chinese Courtship:In Verse)在伦敦和澳门同时出版。在澳门印刷所工作12年以后,汤姆斯返回英国,继续从事中国典籍英译活动。1834年,他将《博古图》部分内容摘译为英文发表在《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报》(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第一卷上。此后,他继续翻译《博古图》并于1851年出版了英译单行本,这时汤姆斯名后的身份标签已不再是“印刷工”,而转变成为“《宋金郎团圆破毡笠》与《花笺记》的译者”。可见,汤姆斯对“印刷工”的职业称谓并不满足,他深知自己出身卑微,仅凭“印刷者”身份显然无法获得显赫的社会地位,只有和马礼逊、小斯当东、德庇时等东印度公司其他职员一样,借助汉学研究著述才能实现身份地位的转变。受惯习的指挥与影响,他适时调整了个人行为方向,选择从事中国文献翻译实践,以文字译著作为其毕生荣耀,实现了由印刷工到汉学家的身份转变。
三、翻译文学、历史作品满足社会政治场域的需要
译者惯习不仅能够解释汤姆斯从事翻译实践的动机问题,还能从宏观方面影响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表面上看,翻译活动自始至终都受到权力话语的操纵与控制,但由于惯习是“人的实践行为的核心,处于客观环境、历史、人的心理倾向三者互动关系的中央”[4]11,译者翻译什么、不翻译什么、选择哪个流派、哪位作家、哪些作品来翻译也必然受到惯习的制约。翻译主体将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历史条件、生活及工作经历内化,经历漫长而反复的习得过程沉淀为惯习,“表现为一种倾向和意向,驱使其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展开自己的行为”[6]86。
惯习概念总是和特定的场域联系在一起。结合汤姆斯所处的历史时代不难发现,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失败后,英国人逐渐摆脱了对中国的狂热崇拜,作为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的商业国家,当时的英国无论在政治还是社会变革方面都体现出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商业利益”[8]3。社会政治场域的变迁会影响翻译场域,塑造译者相应的惯习并突出地反映在翻译选材上。汤姆斯节译的《三国演义》与《今古奇观》等中国古代小说是西方人了解中国世俗人情的重要渠道。《花笺记》作为民间说唱文学的代表在明清时期流行于两广地区,虽是俗文学却包含了丰富的人类文化学价值,形象地描绘了一幅中国社会风俗图,“被当作西方人了解中国语言、社会、文化、经济的综合性读本”[3]211。此外,汤姆斯还选译了与中国商代青铜器有关的《博古图》以及中国各省份税收统计资料,凡此种种“对于增进19世纪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知识与态度,不论是了解、同情或是野心,都产生相当的作用”[9]80。
汤姆斯个人惯习的形成不仅受19世纪前后社会政治场域变化的影响,与他自身工作经历也有着密切联系。他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从事印刷业长达12年之久,最初主要工作是协助马礼逊印刷《华英词典》。出于印刷需要,他组织雕刻了大量中文铅合金活字,并对中国语言文字产生了浓厚兴趣。加之合作伙伴马礼逊本身就是一位精通中文的汉学大家,耳濡目染之下汤姆斯的汉语学习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借翻译汉语文献提高中文水平的动机也越发强烈。变化的社会政治场域与自身强烈的中文学习兴趣相互作用,经过积淀后形成了译者汤姆斯的惯习,驱动他选择翻译以文学、历史题材为主的中国古典文献,这既可以满足英国政府了解中国的功利性需要,也可作为自身汉学成果的总结。
四、灵活运用多种翻译策略深化读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惯习对译者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翻译文本选择等宏观层面,还反映在翻译策略、措辞等具体操作层面上。作为一名英汉双语使用者,汤姆斯在中英文化接触中培养起来的“跨文化惯习”会对其翻译行为产生相应影响,促使他基于一定的文化立场就言语转换方法不断做出抉择,而他所使用的微观翻译策略正是译者惯习的外在表现形式。
一方面,针对源语文本的文体特征,汤姆斯尽量采取直译策略如实呈现。例如,《花笺记》人物情节复杂,具备小说的某些特点,但同时相当讲究韵律与节奏。汤姆斯充分认识到了《花笺记》的诗体创作特征,在英译本前言中详细介绍了中国的诗歌艺术,他指出:“中国大部分诗歌仅有数行,多属即兴之作。相比之下,‘第八才子书’《花笺记》更长。中国人的诗歌艺术成就是伟大的,而且每个文人都会做诗。中国人并非缺乏动力创作优秀诗歌,只是囿于古代流传下来的礼法而已。”[10]iii-iv由此可以看出汤姆斯对中国诗歌所持的褒扬、欣赏态度。这种对中国文化向往与热爱的情结逐渐沉淀为译者惯习,他对异域文化持有的赞颂立场具体反映在翻译策略的运用中。汤姆斯不仅在《花笺记》英译本的书名中特别注明译文为“诗体(verse)”,还在翻译文体的选择上力求通过“以诗译诗”再现原作精神。译本每页上方中文竖排,下方英文与之逐行对应,呈现出诗行特点。汤姆斯采用的直译策略并非字字对应的死译、硬译,如“一点红唇真俏丽,生成模样断人肠”一句,译者将之翻译为“A red dot,on her chin,gave beauty to her person,While her elegant form was enough to break the heart of man.”[10]19译者将“真”译为动词“gave”,体现出他对原文的深刻理解:“俏丽”的是“人”并非“唇”,是“红唇”让人更美。尽管译作出版后主流媒体对译本韵律作出了一些批评,但汤姆斯为推介中国诗歌海外传播所做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另一方面,为便于西方读者理解,汤姆斯在“跨文化惯习”驱动下运用意译策略处理富含中国特色的文化典故。在《花笺记》译本中,译者将“蓬莱岛”译为“the region of bliss”(快乐之地),用古罗马神话中的“nymph”(居于山林水泽的仙女)来形容中国美人,甚至将“三柱沉香拜月神”翻译为“three sticks of fragrant incense was offered to Venus,the goddess of love”[10]110(三柱沉香拜维纳斯爱神),无不体现出译者沟通中西文化的良苦用心。出于同一目的,针对“鸳鸯”、“八斗”、“牛郎”、“织女”等文化负载词,译者在“跨文化惯习”作用下,添加了大量注释作为翻译副文本,有利于深化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五、结语
惯习影响了汤姆斯翻译实践的动机、翻译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运用。为了实现身份地位的转变,他选择从事中国古典文献英译活动并成功达到了既定目标。受制于社会政治场域,汤姆斯选译的作品以文学、历史题材为主。在“跨文化惯习”影响下,他灵活运用多种翻译策略,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中国文化,为“中学西传”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汤姆斯中国古典文献英译中的惯习进行分析,一方面可以透视19世纪上半期英国社会政治场域、汉学场域与翻译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也表明译者惯习会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从社会学的惯习视角出发,研究译者主体及其翻译活动,可以扩大翻译研究路径、拓展翻译研究的深度,这一研究范式具有一定的学科意义。
[1]郑锦怀.彼得.佩林.汤姆斯:由印刷工而汉学家——以《中国求爱诗》为中心的考察[J].国际汉学,2015(4):133-141.
[2]梁启昌.论木鱼书《花笺记》的英译[C]//李元华.逸步追风:西方学者论中国文学.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256-281.
[3]王燕.《花笺记》:第一部中国“史诗”的西行之旅[J].文学评论,2014(5):205-213.
[4]邢杰.译者“思维习惯”——描述翻译学研究新视角[J].中国翻译,2007(5):10-15.
[5]唐芳.惯习中心维度探析——论西米奥尼的惯习观[J].山东外语教学,2011(4):97-102.
[6]魏望东.Habitus与翻译选择[J].翻译论坛,2016(1):83-89.
[7]唐芳.翻译社会研究新发展——Sela-Sheffy的惯习观探索[J].外语研究,2012(5):82-91.
[8]胡优静.英国19世纪的汉学史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
[9]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M].台湾:学生书局,2000.
[10]Peter Perring Thoms.Chinese Courtship:In Verse[M]. London:Parbury,Allen and Kingsbury/Macao: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1824.
Peter Perring Thoms’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A Study Based on Translator’s Habits
QIAN Lingjie,CAO P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Anqing Normal University,Anqing,Anhui,246011 China)
Peter Perring Thoms,a British sinologist in the first half of 19th century,translated a number of Chinese classics into Eng⁃lish.His choice of translation activities,decision of translation texts and employment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ll represent his habits. Thoms changed his identity from“a printer”to“a sinologist”through translation activities.His translation texts are mainly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which met social and political requirements.His employment of literal and fre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s well as annotation deepened readers’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culture.
Peter Perring Thoms;Chinese classics;translation;habits
H315
A
2096-2126(2016)05-0062-03
(责任编辑:雷凯)
2016-09-01
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项目“安庆师范大学英语专业”(TS12154)。
钱灵杰(1984—),男,安徽宣城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