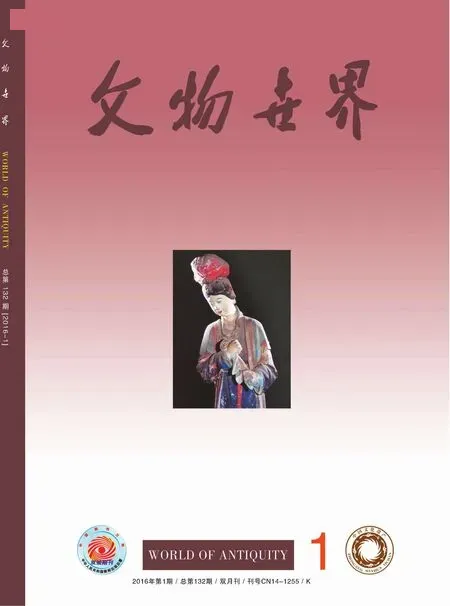唐墓出土的竿木杂技俑
□岳敏静
唐墓出土的竿木杂技俑
□岳敏静
摘要: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言,唐代竿木杂技俑主要来自于墓葬,作为墓主人的随葬品出现,主要包括金乡县主墓、孙承嗣夫妇墓以及新疆阿斯塔那墓。根据上述墓葬出土的竿木杂技俑,可以总结出:一是竿木杂技俑在唐代的流行时间主要为开元年间;二是竿木杂技在唐代的杂技艺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三是竿木杂技俑在表现唐代竿木杂技艺术表演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词:唐墓竿木杂技俑流行时间地位局限性
竿木这种杂技表演形式历代有之,唐代是对历代竿木表演的继承。在汉代,东汉的张衡在其《西京赋》[1]中就曾描写到:“大驾幸乎平乐,张甲乙而袭被翠。攒珍宝之玩好,纷瑰丽以奢靡。临迴望之广场,程角抵之妙戏。乌获扛鼎,都卢寻幢,冲狭燕濯,胸突铦锋。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侲僮程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絓,譬陨绝而复联”。都卢寻幢即唐代的竿木表演,后面一段形象描写了汉代童子表演竿木杂技的精彩情景;北魏时期,《魏书·乐志》[2]记载:天兴六年冬,诏太乐、总章……长趫、缘幢、跳丸,五案以备百戏。"到了唐代,文献中也不乏关于竿木表演的记载,如《旧唐书·音乐志》[3]:“散乐者,历代有之……汉世有橦木伎,又有盘舞……梁有猕猴幢伎,今有缘竿,又有猕猴缘竿,未审何者为是。”正如赵文润在其著作《隋唐文化史》[4]中总结的那样:“(缘竿)传统项目,以表演力量、平衡和空中技巧为主。以竿竖立于地上,或着于人额上(称戴竿),表演者于竿上表演各种造型或险技。”张永禄主编的《唐长安词典》[5]中也总结了唐代的这种表演艺术:“(寻幢)杂技名。又称缘幢,或称顶竿、爬竿、戴竿。汉代即有,唐长安城较为流行。”
关于唐代竿木杂技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在杂技的总体范畴中进行的。具体可以总结如下:一是归纳总结。主要有:如赵文润的《隋唐文化史》和张永禄主编的《唐长安词典》;二是通过文献资料进行研究的,有汪聚应的《唐人豪侠小说中的杂技描写》[6]、聂传学的《唐玄宗与盛唐杂技》[7]等;三是结合某一方面进行系统讨论的:有耿占军的《古代百戏》[8]、《汉唐时期乐舞与百戏管理机构的设置》[9]等;四是结合考古资料对竿木杂技进行研究的,有《阿斯塔那336号墓所出戏弄俑五例》[10]、《敦煌壁画文献中所见的古代百戏》[11]等等。可见,目前而言除了上述《阿斯塔那336号墓所出戏弄俑五例》中作者对“顶竿倒立木俑”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对于其他的竿木杂技俑的研究目前寥寥无几。而随着考古发现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唐代竿木杂技俑被发现,所以完全有必要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
目前考古发现的唐代竿木杂技俑共计14件。主要集中在当时首都长安周围,同时新疆地区也有零星的发现。除个别出土地点不详外,主要是出土于唐墓中,包括金乡县主墓、孙承嗣夫妇墓以及新疆阿斯塔那墓。本文拟将考古发现的唐代竿木杂技俑进行梳理,并结合文献资料的记载,分析其特点。不足之处,还望指正。
一、考古发现的竿木杂技俑

图一 金乡县主墓出土竿木杂技俑第一组竿上表演者
(一)金乡县主墓[12],共7件。
经复原为三组。第一组,头顶竿者(图一),头扎黑色短巾。身躯直挺,双臂均残,从残存双臂的动作看,当是平举展开,其造型如同一个“大”字。头顶残存铁柄。高6.9厘米。另一俑(图二)身穿紧身长裤,双臂展开,头顶有一小孔,当是头顶竿倒悬于空中的表演者。高6.3厘米。第二组(图三),妇人形象,头扎白色短巾,脑后梳一小髻。双腿前后开立,腹部有一圆孔,当插有长竿,左手护于竿旁,右臂残。头略向上仰,注视竿上的表演者。高7厘米。另一俑头扎短巾,脑后露出小髻,身穿紧身衣裤。臀部残存铁柄,此俑当骑坐于竿的顶端。头顶左右各有一圆孔,当时用来插支架的,而支架上通常悬物或有童子表演惊险的高空动作。高5.5厘米。第三组(图四),妇人形象,脑后一髻下垂,双腿前后开立,腹部有一圆孔,当插有长竿。左手护于竿旁,右臂残。头略向上仰,注视竿上的表演者。高7厘米;一俑穿紧身长裤,肩上有一圆孔,当是以肩顶长竿、头朝下、脚朝上的表演者。双手护于竿旁,高5.4厘米;一俑上穿红色衣,下穿紧身裤,肩部有铁柄痕,双臂残,从其动作看,当为肩部着竿,双手向下抓竿,挺腹伸腿侧悬于空中的竿上表演者,其位置估计在竿的中部,高5.4厘米。

图二 金乡县主墓出土竿木杂技俑第一组撑竿者

图三 金乡县主墓出土竿木杂技俑第二组(由一名撑竿者和两名竿上表演者组成)

图四 金乡县主墓出土竿木杂技俑第三组(由一名撑竿者和一名竿上表演者组成)

图五 孙承嗣夫妇墓出土竿上表演者

图六 孙承嗣夫妇墓出土撑竿者
(二)孙承嗣夫妇墓[13],共4件。
标本M12:87(图五),头戴斗笠,扎幞头,身着圆领窄袖缺銙短袍,腰束带,下着麻鞋。双手曲臂前伸,表情滑稽,作表演状。器下有竖孔。通高14厘米。标本M12:92,与上述标本属于同类遗物。标本M12:144(图六),胡人形象。高鼻凸眼,龇牙,络腮胡。头戴尖顶胡帽,身穿圆领窄袖袍,下露袴,腰束带。左臂长伸体侧,右臂弯于体侧,曲膝,前后分腿,作侧首表演状,帽尖、右臂、双足残。残高12.6厘米。三件陶俑虽然未明确是杂技俑,但是从报告中的“器下有竖孔,可能原插支撑物”推断应该是竿木杂技的一部分。
除上述俑外,此墓还出土标本M12:13,头戴黑色幞头,面容俊朗。上身赤裸,凸肚露脐,下身仅刻划三角裤,着麻鞋。右手高擎于上方,作握持状,左臂前伸。右脚单足立地,左脚上抬。通高16.6厘米。我们可以作如下的讨论:第一,这件陶俑从体态来看,应该握持有一长竿形物;第二,从陶俑的衣着来看,仅着三角裤,说明他应该进行的活动比较花费体力;第三,结合金乡县主墓、新疆阿斯塔纳等墓出土的杂技俑资料,一般而言竿木杂技俑都是撑竿者略高于竿上的表演者,如金乡县主墓出土第二组竿木杂技俑,撑竿者为高7厘米,竿上表演者高5.5厘米。新疆阿斯塔那墓出土的竿木杂技俑直接将竿上的表演者塑造成童子形象。再看孙承嗣夫妇墓出土的标本M12:13,高16.6厘米,上文提到的三件竿上表演者通高分别为:标本M12:87 和M12:92,高14厘米,标本M12:144,高12.6厘米,完全符合撑竿者比竿上表演者略高的特点。第四,既然墓中已经出土了三件器下有插孔的百戏俑,那么按照逻辑推理应该有撑竿者与之相对应。这样从以上五点可以看出,标本M12:13属于竿木杂技中撑竿者。

图七 阿斯塔那336号墓出土竿木杂技俑
(三)新疆阿斯塔纳336号墓[14],1组2件。
196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考古队在阿斯塔纳北区发掘了一批古墓,其中编号为ATM336墓葬出土一件木雕顶竿倒立俑。由顶竿人与竿末倒立童子组成。顶竿人短衫,短裈,腰间系带。四肢已残,仅右臂得以修复。原作两足分开直立,双臂左右平伸状。这种姿势便于保持头顶立竿平衡。竿顶倒立的童子赤身,着红色犊鼻裈,除左足右手残缺外,基本可以复原。由于原竿长度难以确知,依现存残木杆修复,残高为26.8厘米(图七)。
根据上述发现的竿木俑,可以总结出,唐代竿木杂技俑按照质地分有陶俑、木俑;按照出土地域分有西安地区和新疆地区。具体到表演形式,主要由撑竿者和竿上表演者组成,有两人一组的、三人一组的不等。
二、相关问题讨论
(一)竿木杂技在唐代杂技中的地位。
唐代杂技种类多样,《唐会要》[15]卷三十三:“散乐历代有之,其名不一,非部伍之声,俳优歌舞杂奏,总谓之百戏。跳铃、掷剑、透梯、戏绳、竿木、弄枕珠、大面、拨头、窟礧子,及幻伎激水化鱼龙,秦王捲衣、茯鼠、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龟赴岳、桂树白雪、画地成川之类,至于断手足,剔肠胃之术。”《旧唐书·音乐志》[16]也记载:“散乐者,历代有之……汉世有橦木伎,又有盘舞。晋世加之以柸,谓之柸盘舞。乐府诗云:妍袖陵七盘,言舞用盘七枚也。梁谓之舞盘伎。梁有长跷伎、掷倒伎、跳剑伎、吞剑伎,今并存。又有舞轮伎,盖今戏车轮者。透三峡伎,盖今之透飞梯之类也。高絙伎,盖今之戏绳者是也。梁有猕猴幢伎,今有竿木,又有猕猴竿木,未审何者为是。又有弄椀珠伎、丹珠伎。”正如赵文润将唐代杂技总结为:拟兽伎、驯兽伎、走绳、竿木、呈力伎、倒立伎等。除此之外,根据上述文献记载,还应包括戏车轮。
竿木杂技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开元以后归右教坊管理。根据唐代的文献记载,《教坊记》[17]序记载:“玄宗之在藩邸,有散乐一部,辑定妖氛,颇藉其力;及庸大位,且羁縻之……翌日诏曰:‘太常礼司,不宜典俳优杂伎。’乃置教坊,分为左右而隶焉,左骁卫将军范安及为之使。”《教坊记补遗》[18]:“上偏私在左厢,故楼下戏,右厢竿木多失落。”从以上两条史料知道,唐玄宗时期将杂技等归入左右教坊,专门训练管理,而竿木位于右教坊。在唐代的文献中,多见对竿木杂技的描写,仅唐诗中,就有王邕的《勤政楼花竿赋》[19]等。在笔记小说中也多次有对竿木杂技的描述。如《教坊记》[20]中记载有专门表演竿木的家庭,称为“竿木家”:“范汉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还有利用竿木表演隐喻人物命运的描写,如:《唐国史补》[21]卷上记载:“《都卢寻幢歌》,讽元载,至危之势,载揽而泣下。”这些表明唐代杂技中竿木表演是知名度较高且非常流行的,在杂技表演中占主要地位。这点也可以和考古发现相对应,据笔者粗略统计,目前发现的唐代杂技俑共计约20件,竿木杂技俑为14件,约占总数的70℅。
(二)竿木杂技俑的流行时间
以上各地出土的竿木杂技俑,除了新疆阿斯塔那墓为武周时期外,金乡县主墓时间为开元十二年(726年);孙承嗣夫妇墓时间为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可见唐代杂技俑的流行时间可能以开元年间最盛。
另据文献记载,《新唐书·礼乐志》[22]记载:“盖唐自太宗、高宗作三大舞,杂用于燕乐,其他诸曲出于一时之作,虽非纯雅,尚不至于淫放。武后之祸,继以中宗昏乱,固无足言者。玄宗为平王,有散乐一部,定韦后之难,颇有预谋者。及即位,命宁王主藩邸乐,以抗太常,分两朋以角优劣。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居新声、散乐、倡优之伎,有谐谑而赐金帛朱紫者,酸枣县尉袁楚客上疏极谏。”《大唐新语》[23]卷十:“开元中,天下无事。玄宗听政之后,从禽自娱。又于蓬莱宫侧立教坊,以习倡优萼衍之戏。”《教坊记》[31]序:“玄宗之在藩邸,有散乐一部,辑定妖氛,颇藉其力;及庸大位,且羁縻之……开元中,余(教坊记作者唐崔令钦)为左金吾仓曹,武官十二三是坊中人。”从以上文献记载可以看出,玄宗和杂技颇有渊源,一方面是个人爱好问题,另一方面玄宗在政治上依赖内伎。所以促进了包括杂技在内的百戏在这个时期的高度繁荣。与此同时,从上述所引《新唐书》记载中“虽非纯雅,尚不至于淫放”以至于“酸枣县尉袁楚客上疏极谏”,《旧唐书音乐志》[24]记载:“(东汉)安帝时,天竺献伎,能自断手足,刳剔肠胃,自是历代有之。我高宗恶其惊俗,敕西域关令不令入中国。”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散乐杂戏在唐代被认为是非雅的,“淫放”的代表,高宗时曾经不令西域表演杂技的人入中国,以至于在玄宗朝之前并没有盛行,到了玄宗时期,皇帝的大力推崇,使得即使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也无济于事了。这种情况表现在随葬品上,就出现了开元年间竿木杂技俑大量出土的情况。
另据姚汝能的《安禄山事迹》[25]描写到:“五月(756年),奚、契丹两藩数出北山口至于范阳,俘劫牛马、子女,至城下累日。城中惟留羸兵数千,不敌。润客筹记无所出,遂以乐人戴竿索者为矫健可用,援兵出战。大败,为奚羯所戮。惟三数人,伏草莽间,获免。其乐人本玄宗所赐,皆非人间之伎,转相教习,得五百余人。或一人肩负首戴二十四人,戴长竿百余尺,至于竿杪人,腾掷如猿穴飞鸟之势,竟为奇绝。累日不惮,观者流汗目眩。于是此辈歼矣。”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开元以后,表演竿木等杂技的人员命运不济,有的甚至“援兵出战”,使得开元以后梨园弟子散落民间,杂技艺术不复盛况。

图八 敦煌莫高窟壁画《宋国夫人出行图》
(三)利用竿木杂技俑表现唐代竿木杂技的局限性
实质上,唐代竿木杂技,还有更精彩的内容。根据唐代文献的记载,《教坊记》[26]序记载:“(玄宗时)凡戏辙分两朋,以判优劣,则人心竞勇,谓之‘热戏’。于是诏宁王主藩邸之乐以敌之。一伎戴百尺幢,鼓舞而进;太常群乐鼓噪,自负其胜。上不悦,命内养五六十人,各执一物,皆铁马鞭、骨梃之属也,潜匿袖中,杂于声儿后立,复候鼓噪,当乱捶之。皎、晦及左右初怪内养麇至,窃见袖中有物,于是夺气褫魄。而戴幢者方振摇其竿,南北不已。上顾谓内人者曰‘其竿即自当折。’斯须中断,上抚掌大笑,内伎咸称庆。于是罢遣。”显然,唐玄宗不满足于单纯的竿木表演,他还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使得表演更具有娱乐性。还有苏鹗的《杜阳杂编》[27]记载:“上(唐敬宗)降日,大张音乐,集天下百戏于殿前。时有伎女石火胡,本幽州人也,拳养女五人,才八、九岁,于百尺竿上张弓弦五条,令五人各居一条之上,衣五色衣,执戟持戈舞《破阵乐》曲。俯仰来去,越节如飞,是时观者目眩心怯。俄而手足齐举,为之踏浑脱,歌呼抑扬,若履平地。”根据上述描写,可以知道在唐代竿木杂技表演远比目前所发现的杂技俑表现得更丰富多彩。同时,在一些壁画或者其他载体上也可以还原当时竿木杂技表演。在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唐代竿木杂技的表演,《宋国夫人出行图》(图八)的出行队伍中,有一组竿木杂技,一位体态硕壮的力士头顶一根粗大的长竿,竿的顶端置有一个圆盘,竿上有四人正在表演各种惊险的动作,有的双脚倒挂,有的单臂悬体,有的只用一只手,一条腿勾住长竿往下滑坠,山木上的人则正在做双臂侧撑平衡动作。值得注意的是,力士的身边还站立一人,手持一长竿,似正在做着某种保护动作。由此可见,唐代竿木杂技表演过程中,有时还会有一人在撑竿者旁边举一长竿,用以保护表演者。
之所以在考古发现的唐代竿木杂技俑中并未表现出唐代竿木杂技的丰富和精彩。这可能与考古发现本身的局限性有关,如在金乡县主墓出土的竿木杂技俑中,第二组竿上的表演者骑坐于竿的顶端,头顶左右各有一圆孔,当时用来插支架的,而支架上通常悬物或有童子表演惊险的高空动作;在新疆阿斯塔纳墓出土的竿木俑中,发掘报告中提到:“另外据发掘者回忆,同墓还出有一件与此倒立童子相似的木雕童子,四肢残,疑与此俑有关。”从以上这两个例子知道,杂技俑在出土时或多多少可能会有遗失,给研究工作带来一定的阻碍,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文献记载和其他载体上的相对照,尽量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同时从以上的讨论中,可以知道,唐代竿木杂技基本组成是撑竿者和竿上表演者,而二者数量不一,撑竿者基本为一至二人,竿上表演者数量从一至数十人不等。表演内容有缘竿上下、在竿上作舞以及在竿上置物平衡等等。
————————
[1] [汉]张衡《西京赋》,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9~420页。
[2] [北齐]魏收《魏书·乐志》卷一〇九,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828页。
[3] [五代]刘昫《旧唐书·音乐志》卷二十九,中华书局,第1073页。
[4]赵文润主编《隋唐文化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143~147页。
[5]张永禄主编《唐代长安词典》,西安地方志丛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341~344页。
[6]汪聚应《唐人豪侠小说中的杂技描写》,《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6月第25卷,第3期,第1-6页。
[7]聂传学《唐玄宗与盛唐杂技》,《杂技与魔术》1994年第3期,第14~15页。
[8]耿占军《古代百戏》,《文博》1999年第2期,第82~ 83页。
[9]耿占军《汉唐时期乐舞与百戏管理机构的设置》,《唐都学刊》1999年10月第15卷第4期,第31~34页。
[10]吴震《阿斯塔那336号墓所出戏弄俑五例》,《文物》1987年第5期,第77~82页。
[11]倪怡中《敦煌壁画文献中所见的古代百戏》,《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9年第1期,第49~51页。
[12]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王自力、孙福喜编著《唐金乡县主墓》,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67~71页。
[1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唐孙承嗣夫妇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2期,第18~28页。
[14]吴震《阿斯塔那336号墓所出戏弄俑五例》,《文物》1987年第5期,第77~78页。
[15] [宋]王溥《唐会要》卷33,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11页。
[16] [五代]刘昫《旧唐书·音乐志》卷二十九,中华书局,第1073页。
[17] [唐]崔令钦《教坊记》,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22页。
[18] [唐]崔令钦《教坊记补遗》,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页。
[19]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356,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987页。
[20]同[17],第125页。
[21] [唐]李肇《国史补》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69页。
[22] [北宋]欧阳修《新唐书·礼乐志》卷二十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75页。
[23] [唐]刘肃《大唐新语》,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51页。
[31]同[17],第122页。
[24] [五代]刘昫《旧唐书·音乐志》卷二十九,中华书局,第1073页。
[25]姚汝能《安禄山事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1-33页。
[26]同[17],第122页。
[27] [唐]苏鹗《杜阳杂编》,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387页。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陕西历史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