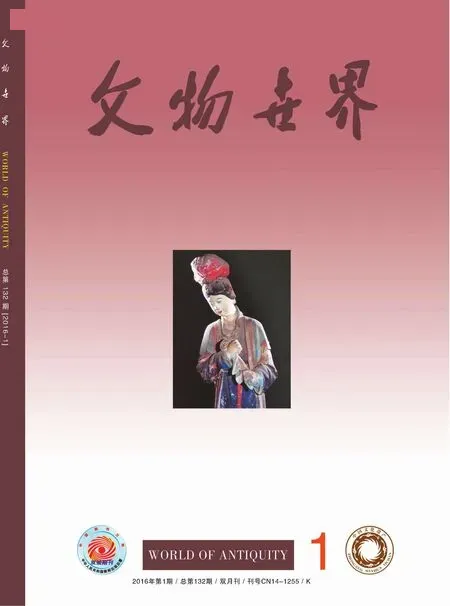西安北周张子开造立佛像相关问题探讨
□刘仕敏
西安北周张子开造立佛像相关问题探讨
□刘仕敏
摘要:2004年西安市东郊灞桥区湾子村出土一批北周佛立像,其中一件有北周大象二年的纪年,因此该造像为北朝晚期佛教造像的研究提供了年代标尺。造像主张子开在发愿文中除了称颂佛法,为父母祈愿之外,还反映出北周武帝灭佛与宣静帝复法事件,以及柱国杨坚对佛教的扶持作用。本文就大象二年等北周佛造像对相关的佛教事件及历史背景,以及北周佛教造像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周武帝杨坚复法佛造像
一、造像情况
2004年5月,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湾子村出土5尊大型佛立像,佛像出土于土塬上靠近崖边的窖穴中,其中一件有明确纪年,即大象二年(580年)[1]。该造像台座正面刻有反映北朝佛教史上重大事件的发愿铭文,价值很高。简报《西安市东郊出土北周佛立像》刊布了该造像基本情况及铭文。少数学者对北朝佛教造像的研究中有所涉及,如王敏庆《北周佛教美术研究》[2]、吴荭《北周石窟造像研究》[3]单体造像篇章中引其作为有纪年的北周晚期单体造像典型例证,并未对发愿铭文等情况做详细研究。

图一 西安东郊出土大象二年造像(魏文斌拍摄)
造像为释迦佛立像,青石质,佛高195厘米。头顶布满螺髻,顶髻稍凸起,弯眉细长,眼窝凹陷,双眼微睁,鼻残,双耳下垂,面部方圆微胖,脸上微露笑意。身着通肩袈裟,衣领下垂较低,衣领刻成凸起弧状。右臂残断,左手持握衣角,手指指甲清晰可见。腹部微鼓,在佛体胸腹和双腿,雕刻数道平行“U”纹来表示袈裟的衣纹,两腿间刻有类似双钩空心Y字型的条带状衣褶。跣足立于莲座上,裙摆外撇,垂于脚面。两边刻出对称的四层衣褶的裙摆,整体看衣纹比较疏朗。佛座高43、长75、宽73.5厘米。四方形基座上雕双瓣仰覆莲,仰莲瓣圆而短,覆莲瓣较大,饱满。基座正面两角各雕有一护法狮子,昂首伏坐,前肢伸直,两爪紧抓座面,胸前布满卷曲的鬃毛。左侧狮一爪抚一小卧狮。基座正面为发愿文,背面两角雕两只相向的大象,其背上各有两个象奴(图一)。
二、发愿文释读
四方形基座正面刻有发愿文,竖列划有分界线,每列12字,共21列,铭文释读如下(图二):
“夫真如沖寂,迈于玄像之表,至/理悕微,出于言论之外,是以玉/宫双树,标记于前踪,沦没显现,/再睹于今日,自非帝主钦明,辅/相睿哲,孰能追寻妙状,兴灭构/立者乎,然苦海爱河,济涉者少,/想欲尘累,生灭难除,如来大慈,/哀深沉溺,以兹慧镜,照我娑婆,/演以一音,随类斯解,迷子醒悟,/方求彼岸,正信佛弟子张子开,/睹佛法崇重,像日再出,内发菩/提,心念胜果,乃镌鉴名山,机匠/绝思,为七世父母敬造释迦玉像/一区,姿容炳质,无异真形,至/心供养,穷劫不尽,其颂曰:/因缘难辨,世界谁寻?潜辉如昨,/再见于今,法皼斯震,玉树敷荫,/众生归仰,万品濯心,穷山拯虑,/啚写真容,合家供敬,瞻奉虔恭,/嵩山可砺,心愿永怀,/大象二年七月廿一日建。”

图二 大象二年造像底座发愿文(魏文斌拍摄)
该篇发愿铭文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6点:(1)用造像表达佛法的原因;(2)佛法湮灭再现及其推动者;(3)造像主需要佛法的原因;(4)佛弟子造像的发愿内容;(5)发愿颂词;(6)造像时间。
该篇发愿文造像主、造像目的及原因、时间非常明了,简报已有释读,此处不做重复。发愿文格式化,结构完备,行列整齐,字体工整,比较容易辨识,这里仅对个别词语进行辨析。真如、双树都是指佛法,双树即娑罗双树,是释迦灭度的地方,佛教作品用这个指代佛法。沖寂,意为淡泊清净,杜光庭《广成集·皇帝为老君修黄箓斋词》:“敷澹然沖寂之宗,行不宰无为之教。”[4]吴淑《江淮异人录·江处士》:“歙州江处士,性沖寂好道,能制鬼魅。”[5]看起来是和道教联系的语境下用得多,此发愿文中借用来描述佛法,对于不精通义理的佛教徒来说其中区别并不明显。
供养人名字最后一字,简报释读为聞[6],经反复识读后本人认为是開(图三),该造像碑与同是北周大象二年的宇文君墓志、时代接近的隋代开皇元年(581年)的诸葛子恒碑的“開”字非常像(图四、图五),字体结构形态还是可以参考,门字框中的“开”字更接近“井”字形。和宇文君墓志中门字框左侧斜笔画写法一样。张子聞、或是张子開,都未见于北朝相关历史文献记载,然而能在静帝复法伊始在都城以个人名义造近2米的立佛像,发愿文篇幅较长、结构完整,推测造像主也是属于中上层人士。在发愿文中语句透出对于当时掌握实权的辅相推动复兴佛法的赞颂,表达出作为佛教徒复兴佛法的喜悦,也迎合了当时的局势,尤其“帝主钦明,辅相睿哲”之句,除表示对皇帝的忠诚外,暗里带有对当时大权在握的辅相杨坚的阿谀之意。

图三 北周大象二年造像碑局部

图四 北周大象二年宇文君墓志局部

图五 隋代诸葛子恒造像碑局部
文中有一句“为七世父母敬造释迦玉像一区”,该佛立像为青石材质,却称为玉像。这样的情况例子很多,李僧智王阿全合邑四面造像碑铭文内容中有“妙哉冲晕,詑体玉质,显像八十,凝然果一”语句[7],该碑为砂岩材质。太平真君四年(443年)弥勒佛立像铭文:“太平真君四年,高阳蠡吾任丘村人菀申,发愿为东宫皇太子造□玉菩萨……。”[8]金铜材质也称为玉。还有戎爱洛造思惟菩萨像铭文:“武定二年太岁在甲子十月廿日,清信士佛弟子戎爱洛,妻赵阿睹,女慈仁,敬造白玉像一躯……。”[9]黄海伯等造像龛下方题记:“天保八年正月廿二日,佛弟子并妻汲为七世内外敬造白玉弥勒像一区……。”[10]这两尊则是大理石的。可见,这里玉表达的意思不受造像本身材质限制,应该就要联系中国人历来崇尚玉的传统心理,本来佛教的七宝之类有是没有玉的。魏晋而后,统治阶级用玉石雕刻佛像、飞天、与佛教鹿母莲花生子相关的持荷童子等,促使佛教越来越向世俗结合的方向发展[11]。缺少玉石材质的地方,或者民间信众用玉造像有困难,就会有别的材质造像题玉像铭,更何况玉在中国人心里是祥瑞的象征,佛教提倡玉的话可以更快融合中国传统信仰,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
这一时期造像铭记中的不少发愿文反映了当时造像者的佛教信仰内容和心理祈愿,西安北郊出土保定三年(563年)的苻道洛造像铭文:“保定三年岁次癸未七月癸亥十五日丁丑,佛弟子苻道洛为亡父母造石像一躯。”[12]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一尊北周造像发愿文:“大象二年岁次庚子三月,佛弟子周纪仁为父母敬造释迦佛像一区。”[13]《全后周文》收录王瓮生造像记:“保定四年岁次甲申十月乙卯朔十五日己巳,佛弟子王瓮生敬造石像一堪,上为天龙八部,下为人王帝主,七世父母,见在父,过去母,合门大小……。”[14]造像的目的无非是为在世或亡父母、七世父母或者其他家人进行祈愿,民众对佛教教义没有深刻的认识,便通过捐资造像这一直接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信仰,合家供养祈福,造像的主要目的祈求自己和家人能过世俗的幸福生活。
三、相关事件分析
该篇造像铭文反映出北周时期两件重要佛教事件,其一为周武帝灭佛,其二是宣、静二帝复法及杨坚所发挥的推动作用。发愿文中“玉宫双树,标记于前踪,沦没显现,再睹于今日”、“睹佛法崇重,像日再出”、“潜辉如昨,再见于今”,都有所暗示。
周武帝的灭佛,经济和军事因素占有很大成分,西魏建立之时经济和军事等条件劣于东魏,北周继承而来,要寻求经济和人力来源与北齐对抗,在资源和势力上日益膨胀的佛教成为理想对象。释昙积《谏周太祖沙汰僧表》中说:“黜放还民,使栋梁空旷……疑谓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深诚可怪……。”[15]侧面反映出武帝此次灭佛的特点,令僧还俗充兵,并收寺庙土地。建德三年(575年),周武帝正式下令毁佛,“……丙子,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并禁诸淫祀,非祀典所载者,尽除之”[16]。根据记载,“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四十千,尽赐王公充为第宅,三方释子灭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慧日既隐,苍生重昏。”[17]周武帝的灭佛政策,初期道教也在禁断之列,并不是单独针对佛教。而且,虽然有毁像焚经,但是并不屠杀沙门僧众,而是令他们还俗,并且寺庙充为宅邸继续利用。武帝毁佛的结果,使寺院土地归国家所有,僧侣还俗,变为编户,达到了取地于佛寺,取民于僧众的目的。在灭佛第二年(576年)便开始大举攻齐,次年灭齐,完成北方的统一。北周除了武帝实行过灭佛政策,其余几位皇帝对待佛教持支持态度,佛教风气还是盛行的。明帝宇文毓曾下诏建立佛寺,“方知鹿苑可期,鹤林无远。敢缘雅颂藉庄严,欲使功侔天地兴歌不日,可令太师晋国公揔监大陟岵、大陟屺二寺营建”[18]。统计《补周书艺文志》附录石刻类中列举的纪年造像及造像碑,仅保定、天和、建德年号的佛教造像数量超过60尊,最迟纪年到建德七年[19]。建德三年之后的数量有所下降,宣、静帝时期又少量回升。因此武帝时期佛教膨胀程度可想而知,只不过武帝的灭佛政策不足以阻挡各阶层信徒对于佛教的热情。
“自非帝主钦明,辅相睿哲,孰能追寻妙状”这一句将辅相和帝主并列提出来,辅相应该就是指杨坚,帝主还要探讨。大象为北周静帝宇文阐(衍)的年号,二年为公元580年,《周书·帝纪》第八“静帝条”:“二年夏五月……己酉,宣帝崩……庚戌……上柱国、扬州总管、随国公杨坚为假黄钺、左大丞相,柱国、秦王贽为上柱国。帝居谅闇,百官总已以听于左大丞相。”[20]“六月……庚申,复行佛、道二教。旧沙门、道士精诚自守者,简令入道。”[21]静帝即位时候不足九岁,五月才即位,到造像的七月,两个月加之在服丧期间,左大丞相杨坚总揽政权,发布的政策极有可能是杨坚的意思。再看静帝之父宣帝,宣帝宣政元年(578年)六月即位,大成元年(579年)二月传位于宇文衍并改元大象,自称天元皇帝,但仍掌控朝权,次年病逝,宣帝朝隋公杨坚为上柱国、大司马,大象元年为大后丞,秋七月为大前疑,柱国,“二年……五月……诏扬州总管、隋公杨坚入侍疾……以隋公杨坚受遗辅政。”[22]杨坚在宣帝朝地位、权势不同一般。《全后周文》中收录宣帝朝发布复兴佛教的诏令,大成元年《旧沙门安置行道诏》、大象元年二月《安置沙门敕》、大象元年四月《陟岵寺行道诏》[23],不过看史书记载:“大行在殡,曾无戚容,即通乱先帝宫人。才逾年,便恣声乐,采择天下子女,以充后宫……耽酗于后宫,或旬日不出,公卿近臣请事者,皆附阉官奏之。所居宫殿,帷帐皆饰以金玉珠宝,光华炫耀,极丽穷奢。及营洛阳宫,虽未成毕,其规摹壮丽。”[24]以及史臣对宣帝的评价:“……卒使昏虐君临,奸回肆毒,善无小而必弃,恶无大而弗为。穷南山之简,未足书其过;尽东观之笔,不能记其罪。然犹获全首领,及子而亡,幸哉。”[25]“……而识嗣子之非才,顾宗祏之至重;滞爱同于晋武,则哲异于宋宣。但欲威之榎楚,期于惩肃,义方之教,岂若是乎。卒使昏虐君临,奸回肆毒;迹宣后之行事,身殁已为幸矣。”[26]只字未提对于佛教有什么贡献,是否可以推测以这位沉溺享乐的帝主名义复兴佛教,实际是杨坚的意思。
杨坚辅政静帝,当年六月就恢复佛教,距推行灭佛政策武帝驾崩(578年)不过两年,支持佛教更直接的是出于维护统治秩序的需要,但杨坚本人的佛教态度也是积极的。《隋书》记载的隋文帝出生后,由尼抚养,“皇妣呂氏,以大统七年六月癸丑夜,生高祖于冯翊般若寺,紫气充庭。有尼来自河东,谓皇妣曰:‘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处之。’尼将高祖舍于别馆,躬自抚养。”[27]史书中对皇帝的出生总会附会一些祥兆,但是由出家尼抚养,杨坚对佛教的态度应该是受到一些影响。宝鸡曾出土一尊宣政元年大司马杨坚造铜佛像,宣政元年六月武帝崩,秋七月杨坚升任大司马,同年便造铜佛像,该造像可以说是杨坚崇信佛教的又一佐证[28]。文献也记载:“隋高祖文皇帝开皇三年周朝废寺,咸乃兴立之,名山之下,各立为寺,一百余州立舍利塔,度僧尼二十三万人,立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写经四十六藏,一十三万二千八十六卷,修故经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造像十万六千五百八十区自余别造不可具知之矣。”[29]佛教得到全面的复兴和推广。《隋唐佛教史稿》论及隋文帝部分,详述杨坚受周禅之后奖挹佛教的种种举措,足见杨坚对佛教的推崇[30]。开皇元年的泾川李阿昌造像碑铭文也提到:“维开皇元年……今蒙皇家之名德,开二教……一愿钟报于帝主……。”[31]其中,“开二教”之语即六月复兴佛、道二教诏书的内容,可见杨坚建立隋朝初便兴佛法,那么在杨坚辅政的宣、静时期的北周,关于复兴佛教的政策,极有可能是杨坚的意思,通过皇帝从国家政策层面推动了北周后期佛教复兴。
四、造像风格

图六 西安东郊出土北周造像(魏文斌拍摄)
结合现已发现的北周佛教造像及已有对北朝晚期佛造像的研究来看,北周单体佛立像,身躯敦实,四肢与躯干的分离程度不明显,身体比例有所失真,颈部短粗,腹部凸出,腿部尤其显得粗直如柱,完全脱离北魏时期的“秀骨清像”风格。头顶和肉髻布满螺发,肉髻低平,面容方中存圆,五官集中。手印方面,右手多前伸,施无畏印,左手抓握衣角。内着袒右僧祇支,以通肩袈裟为主,胸前刻出稀疏的衣纹,用隆起的线条表示,袈裟搭覆双臂垂于身侧,下身衣裙贴体,略显腿部轮廓,晚期两腿间袈裟刻有类似双钩空心Y字型的条带状衣褶,腿部对称分布U字型衣纹,袈裟下露出裙边,裙垂至双脚,脚边衣纹呈竖直并外撇。站于覆莲或仰覆莲上,覆莲由单瓣演化为双瓣,莲瓣肥厚圆润,两侧雕刻有护法狮子。莲台下接方形台座,台座上刻题记或者线图(如图一,图六)。北周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分,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以及河南西部。造像风格所受的影响因素多样,除此之外地域特点也鲜明,北周崇奉的主要对象是释迦佛,从西安的窦寨村、尤家庄、湾子村等地出土北周造像情况可以看出至少长安地区盛行造释迦立像,释迦是北朝时期一直兴盛不衰的礼佛对象。袈裟贴体造像风格受到南朝梁益州造像影响,南朝梁灭亡之时文人僧人北逃,将南朝文化带入北周,佛教造像技艺、风格也随之传入。只不过,这一影响因素不必高估,整个南北朝时期北朝石刻造像数量几倍于南朝,且种类多样,造像活动几乎不曾中断。而南朝几代曾发布过“禁碑令”[32],碑刻以及石刻造像比较少,南朝风格对北周产生的影响也是有限的。造像身体粗壮结实的造像风格在东魏后期便已出现,佛像袈裟贴体,显示出身体结构的特征。北齐与北周民众信仰对象有所差异,北齐的观音信仰盛行。不过,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自建国之日起便处于敌对状态,直到武帝天和三年八月(568年)才与北齐通好[33],建德五年(577年)灭北齐[34]。北周的造像风格已经形成,如纪年为保定三年(563年)的苻道洛造像(图七)[35],佛像头部残缺,左手与愿印,手指微内曲,掌心托有火焰宝珠。右手残,手印不详。身着圆领通肩贴体袈裟,胸前,两腿前侧都是U字形衣纹,两腿间为似双钩空心Y字型的条带状衣褶,跣足站立于单瓣覆莲座上,座两边蹲卧着两只护法狮子,长方形底座,底座前面镌刻有铭文,北周晚期造像风格与此相近,并有所发展。

图七 西安北郊尤家庄出土保定三年造像

图八 上海博物馆藏大象二年造像

图九 美国纳尔逊美术馆藏北周晚期佛立像
另外,北周造像风格呈现与北魏“秀骨清像”不同,这一风格来源,已有学者做过探究,目前形成两种相斥的观点,有学者认为政治上的变革是文帝宇文泰适应当时社会形势而为之,改制范围只限于中央,且在宇文泰之后不久就不再实行,对北周造像风格产生不了直接影响,北周新风格的形成,更多是对南朝造像艺术的吸收[36]。也有学者认为北周的造像风格跟北周复古改制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吴荭在《北周圆雕佛造像及其相关问题》中认为北周造像新风的出现,除与长安佛教发展有关外,更直接的原因当是北周的“复古改制”,北周奠基人物宇文泰“性好朴素,不尚虚饰,恒以反风俗,复古始为心”,古朴风气渗透到北周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北周佛像艺术也会产生不小的影响[37]。罗宗真在《魏晋南北朝文化》中指出:“宇文氏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涉及官制、州郡、礼乐和社会文化相当广泛的方面……佛教造像变得面相丰圆、形体比例缩短、造型结实粗壮,以北方民族的强健有力,一扫南朝世人病态的文弱,但是,在雄浑豪放中却不乏内在细腻的抒情,这就是所谓的‘北周风格’。它与关陇地区的悠久传统紧密结合,糅合了一二百年佛教艺术创作的经验。”[38]多方面改制,提倡简朴引发的社会风气成为北周的造像显得厚重,敦实的内因。另外,高欢迁邺城时带走洛阳40万户人[39],这其中应该也有不少石窟及造像工匠,这一外因也会影响到北周对北魏造像的承袭。
除了受到的影响多样化,再加上地方因素,同样是大象二年的两件释迦佛造像风格上也有明显的差异。上海博物馆所藏周纪仁造像肉髻低平,面相圆润,身体更粗壮。着通肩袈裟,但衣领没有西安张子开造像下垂的程度深,衣纹显得平直,线刻表现,不似西安张子开造像的条状凸起。美国纳尔逊美术馆藏北周晚期佛立像衣纹雕刻方式更接近上博藏周纪仁造像,衣纹较为密集,袈裟搭覆双臂下垂的衣纹近乎竖直,两腿间Y字型的条带状衣褶更显硬朗,两者造像时间、地域上应该也接近,这两尊和西安张子开造像比起来,西安张子开造像线条流畅,衣服轻薄,身体壮实感减弱,莲瓣舒展,已经含有新风格的因素(图八、图九)。
————————
[1]赵立光、裴建平《西安市东郊出土北周佛立像》,《文物》2005年第9期。
[2]王敏庆《北周佛教美术研究——以长安造像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7月。
[3]吴荭《北周石窟造像研究》,兰州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
[4] [五代]杜光庭《广成集》卷五,《道教典籍选刊·广成集》,中华书局,2011年,第76页。
[5] [宋]吴淑《江淮异人录》,中华书局,1991年,第8页。
[6]《西安市东郊出土北周佛立像》中释读为闻,见有引用该造像的文章也称作张子闻造像。
[7]王静芬《中国石碑——一种象征形式在佛教传入之前与之后的运用》,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33页。
[8]林树中、沈琍编《海外藏中国历代雕塑》,江西美术出版社,2006年,上卷第144页。
[9]同[8],上卷第196页。
[10]同[8],上卷第201页。
[11]刘素琴《儒释道与玉文化》,《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4年第1期。
[12]岳连建《西安北郊出土的佛教造像及其反映的历史问题》,《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3期。
[13]发愿文根据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图版编二》第369页造像图片释读。
[14]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4册,《全后周文》卷19,中华书局,1965年,第3973页。
[15]同[14],第3995页。
[16] [唐]李延年《北史·周本纪》下第十,中华书局,1974年,第360页。
[17]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11,CBETA T49,No.2034,94b06。
[18] [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二十八,《后周明帝修起寺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38页。
[19]郭霭春《补周书艺文志》,《文史》第26辑,中华书局,1986年,第91~98页。
[20] [唐]令狐德棻《周书·帝纪》第八“静帝条”,中华书局,1971年,第131页。
[21]同[20],第132页。
[22]同[16],第379页。
[23]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4册,《全后周文》卷3,中华书局,1965年,第3897-3899页。
[24]同[16],第379~380页。
[25] [唐]令狐德棻《周书·帝纪》第七“宣帝条”,中华书局,1971年,第126页。
[26]同[16],第385页。
[27] [唐]魏征《隋书·帝纪》一“高祖条”上,中华书局,1973年,第1页。
[28]高次若《北周大司马杨坚造铜佛像》,《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6期。
[29] [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一百,CBETA T53,No. 2122,1026 b03。
[30]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一章第一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页。
[31]秦明智《隋开皇元年李阿昌造像碑》,《文物》1983年第7期,第49页。
[32]关于禁碑令与南朝造像碑刻的相关内容可以参见《中国史新论:宗教史分册》中颜娟英的研究。
[33] [唐]令狐德棻《周书·帝纪》第五“武帝条”上,中华书局,1971年,第75页。
[34]同[33],第96页。
[35]岳连建《西安北郊出土的佛教造像及其反映的历史问题》,《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3期。
[36]该观点参见王敏庆《北周佛教美术研究——以长安造像为中心》的相关内容。
[37]吴荭《北周圆雕佛造像及其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1期。
[38]罗宗真主编《魏晋南北朝文化》,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71页。
[39] [唐]李百药《北齐书·帝纪第二》神武帝条下,中华书局,1972年,第18页。
(作者工作单位: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