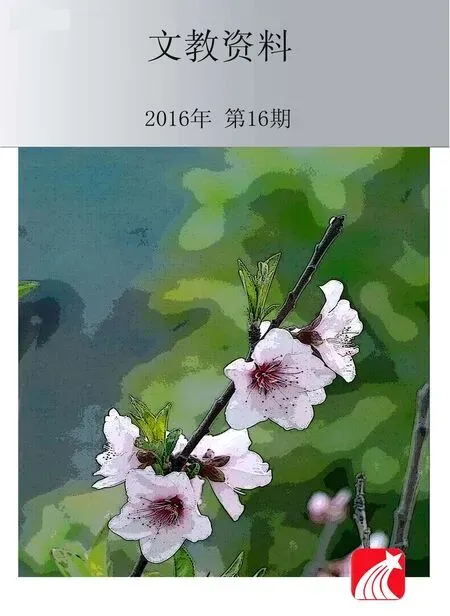浅析民族学视角下艺术文化与文化艺术的关系
——有感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
赵 芳郜智方(1河南理工大学 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河南理工大学 测绘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0)
浅析民族学视角下艺术文化与文化艺术的关系
——有感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
赵芳1郜智方2
(1河南理工大学 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2河南理工大学 测绘学院,河南 焦作454000)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思潮对法国及中西方文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民族学语言构成知识的归纳与概括,对艺术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认真分析,在阐释文化艺术的同时对艺术文化的社会性进行反思,以期对大学生学习《结构人类学》课程特别是公共艺术类课程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民族学结构主义人类文化艺术
在众多人类学的著作中,一个响亮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这就是中国社会人类学的奠基人费孝通教授,时常看到一些有关农村或村落的研究,难道只有对农村这个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进行调查才是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功能学派的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曾评价《江村经济》一书是人类学从研究无文字的部落社会转向研究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和文化的文明古国的一个“里程碑”。之所以在开篇提到《江村经济》,是因为费教授所做的“田野调查”是民族学学科的最普遍研究方法,例如英国不列颠科学进步协会编印发行的田野考察专业手册《人类学的记录和询问》,就是民族学学科产生的一个标志。
在我看来,频频提到的田野调查,其优势在于深入内部、居住体验,这种全面深入的社区调查,主要探讨的是文化各方面的社会功能及相互依存关系。深入民族地区旨在考察了各个民族的社会组织、历史文化、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艺术风格等。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历史”、“语言”、“社会”、“文化”和“艺术”等这几个词,而这些方面也是列维·斯特劳斯在《结构人类学》第一部分首要提到的几个关键,我们试图搞清楚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
一、民族学多重关系的互换
列维·斯特劳斯在“关系”上有明确的定义:民族志是从独特性着眼,对人类群体进行的观察与分析,目的在于尽可能忠实地恢复每一个人类群体的生活面貌;民族学则是利用民族志学家所提供的资料进行比较研究。民族志一语在所有国家里语义相同,而民族学则大致相当于盎格鲁-萨克逊国家里所谓的社会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致力于研究作为表象系统的各类建制,文化人类学则致力于研究各种实现社会生活的技术。很显然,这里我们看到了等同性的关系,似乎是从人类学领域的三元分类法找到的解释。
事实上,民族学这一名称出现在什么时候,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据现有资料,“民族学”一词最晚出现于1787年,关于“人类学”这一名称,它的拉丁文名称一般认为最早出现在世纪初,由希腊文anthropos和logos构成的,前者是指人,后者是科学的意思。我们可以确定,人的科学的涵义面是很广的,在两个名词的关系上,曾有着包含、并列、被包含的发展,但无论它们在历经怎样的转换,不可忽视的是人类学与历史文化有关,就像列维·斯特劳斯在他另一部著作《民族学者的责任》中提到的那样:“正是由于殖民地的存在,人类学研究才成为可能,并且成为必要。”
任何一种结论都是在严谨缜密的研究中得到的,社会类型的转变是在自然科学的实践中发生变化的,历史的推理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而是要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我们可以赞同这样一句说法,也就一下子将民族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拉近,合作研究现代社会才是正确之路。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民族志,关于志的撰写脱离不开语言的描述,可以说,语言学家提供的词源学证据令我们满意,为何?我们最依赖于文字记载的史料,是语言学家通过把那些已经消失的关系在语言里的顽强存在揭示出来,为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出力。语言结构如同社会结构一样深入到研究的内部,通过象征手段发挥着它的作用。语言结构与亲属制度之间存在着一种形式上的对应关系,在这点上,我并不是特别的理解,但是我想说,致力于把结构成分按照系统组织起来的做法是接近的。另外举例,在艺术发展的道路上,只有当我们对图腾的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作出评估时,我们才能看到与社会有关的文化发生。
泰勒就把民族学直接定义为“文化和文明”,这是在他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首次提出的,随后把文化描写成一个复合体,即包括了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及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的经过整合的整体。这里提到的民族学将成为我观察艺术的另一个突破口。
二、结构人类学中对艺术的阐释
历史的维度为我们编织出原始与现代生活,所谓原始的语言是什么,在艺术领域就是在人类学当中反复提到的宗教、巫术、神话、仪式等。我们很好奇,这两者之间的桥梁在哪里?使得艺术没有脱离社会这个大集体。书中婚姻关系这一节内容提到,在人类社会中,亲属关系必然依赖并且通过明确界定的婚姻方式才会得到承认、建立和延续;那么,在人类社会中,艺术解释也必然依赖并且通过显而易见的象征方式才能得到承认、建立和发展。我们都是在跟象征手段打交道,艺术现象等于把“文字、字母、岩画、信号等”转化为符号,成为社会生活中的生命。用作者列维-斯特劳斯的原话:人类学是人与人之间的一场对话;在它看来,一切都是象征和符号,它们都是出现在两个主体之间的媒介。
德国艺术理论家格罗塞认为:“艺术是适应一定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其生产样式与物质的生产样式不可分离,故原始狩猎民族由于图腾集团组织而引起的艺术活动,在任何一时间空间里,都难寻得其同样状态。”即便在神话故事中,我们也能够窥视到一种谱系关系,诸如豪比人就设想神明是有家庭的,像人类一样,分为丈夫、妻子、父亲、女儿等,神话不再是一种连续不断的或周期性的发展进程,而是表现为与构成亲属制度的那些结构相仿的一组两级结构。似乎作者找到了更多艺术与社会之间的联系,结构的存在是对社会整体性的一部分的表达。甚至我们可以把任何一种社会的某某艺术按照语言那样被分解,或许正是基于人类学的角度,我们知道了各要素之间是按照某种对立和关联的结构组织起来的。
我们常听说,艺术科学第一个形式是社会学的,第二个形式是心理学的。心理-生理机制的变化是由什么引起的呢?在原始社会,人们依水草而居,完全依赖自然的赐予,也就是说在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他们更容易相信巫术的观念,一切客观的因果联系不曾为他们所认识,致使认为一位巫师跟超自然力保持着密切关系,或者一切变化都是人类自己动手操作的结果。
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这些巫术仪式包括宗教活动更为明显,它们往往不是被遏制,反而得到众多人类学家的观察和研究,作为民族文化的传统特征被挖掘。就连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中,也没有绕开关于科学与巫术的描述:“当人的力量有限,进而转移至巫术,它不是一个自发的个人行为,而是有组织的制度。礼仪唤起干预,神话维护礼仪。”费老先生通过深入家乡民间活动,为我们讲述了巫术的存在性,在这个体系中,人与自然存在固有的逻辑联系,当出现一种更有效的认为控制自然的办法时巫术才能彻底消灭。
似乎这样的仪式能够被大家所接受,并在整个活动后研究起巫术的次生物,壁画和雕刻等。这不禁拉近了民族学与艺术的关系,在原始美术中,我们会发现岩画上的牲畜被涂刮,很显然,破坏图像是为了达到控制对象的目的。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残留遗迹的研究较普遍。
在《结构人类学》中,较有趣的部分当属神话的结构这部分,文本语言的描述如同唱词,成为一种纯粹的心理治疗,萨满似乎扮演着心理治疗师的角色,唱词对器官则是一种心理操作,人们正是从这种操作中期待治愈。我们当然不能忽视象征的效力,因为这种效力诱发着一种体验,即主体无法控制的外在的自然机制开始自我调节。以前我们只是听神话故事,现在我们可以要分析神话故事。
蛮野社会,神话就是神的话,即神谕,是神对原始民族社会生活所作出的种种规范,没有人去反抗,更不敢反抗,事实上无论神话故事中的物还是神,其所蕴含的观念内容,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这里仅仅列举巫术和神话来深入感受民族文化,与艺术不可割裂的联系滋养着艺术人类学的发展。我们绝没有夸大艺术赋予的象征力,而它的效力恰恰在于形式上彼此对等的结构所具有的诱导性质,这些结构可以用不同的质料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形成:有机过程、无意识心理现象和成熟的思维。
成熟的思维往往要求我们进一步走向文化。
三、艺术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反思
印象派高更的名作《我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给我们留下一连串的哲学思考。人类学所一直围绕的问题无怪乎此,两性的结合,生存的策略,文化的发展?关于这方面的探讨不同的人给予了不同的答案。
社会的变迁,到底是什么在变迁?巨大的疑问落脚在物质的力量上,我们不可否认技术的变革与生产力的提高,但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明确指出文化侵略造成社会风俗及社会制度的结构变迁是关键。文化一词再次出现,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新的文化产业即民间艺术的存留,但与此同时也会伴随某种观念的瓦解。
列维·斯特劳斯为我们很好地指出了文化的非连续性这一特征,工业发展成为社会与历史的一种间接结果,剩余价值与劳动不断转换使文化不断变质。无论文化经历什么样的阶段,我们都必须肯定那个无文字的蛮族社会,肯定那些不曾被我们知晓的形式,但是人类生活不能在一种一成不变的制度下获得发展,而需要通过极为丰富的社会和文明形式。反思文化,首先要反思民族性,由于民族间的闭塞、地理上的屏障,意味着人类交流存在障碍,群体与群体间必然也存在障碍。排除不同民族间的性格差异,实现跨民族交流显得尤为重要。这里让我想到从二分法的角度,民族学曾和考古学、语言学并列存在,那么,我们更要实现民族性研究的科际综合,用系统与比较的方法,研究现存文化的形态及其发展过程。费孝通先生曾不自觉地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观察美国文化的民族性,为我们树立了标杆。
文化反思,重在加强文化沟通,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按照与狩猎仪式有关的巫术形象去诠释旧石器时期遗留下来的岩画。我们可以从这句话上有所启示,文化之间的合作很重要,共处方式往往决定着社会性超级组织的典型形式。文明就是意味着具有最大限度多样化的文化之间的共存,文明甚至就是这种共存本身。在梳理民族学-人类学-艺术学-文化学的过程中,每个问题都需要搞清楚,但事实上关于这些话题的讨论仅仅从理论上进行消化是不够的,必须亲自深入田野调查,正如《人类学的询问和记录》一书所说:“事实和理论不应混杂。”任何有关文化的事实都需要实践证明。
最后,回到我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有人定义,人是运用符号与想象创造生活游戏的文化动物。那么我们从文化中来,最终还要回到文化上去。作为一种被造,我们要么探索,要么被探索。
[1][法]列维·斯特劳斯,张祖建,译.《结构人类学》(1)(2)[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4、475.
[2]费孝通,戴可景,译.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219.
[3]高长江.艺术人类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7.
[4]牛克诚.原始美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47.
[5]赵旭东.本土异域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46.
[6]钟年.文化之道—人类学启示录[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187.
[7]何星亮.关于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问题[J].民族研究,2006:5.
河南理工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015 JG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