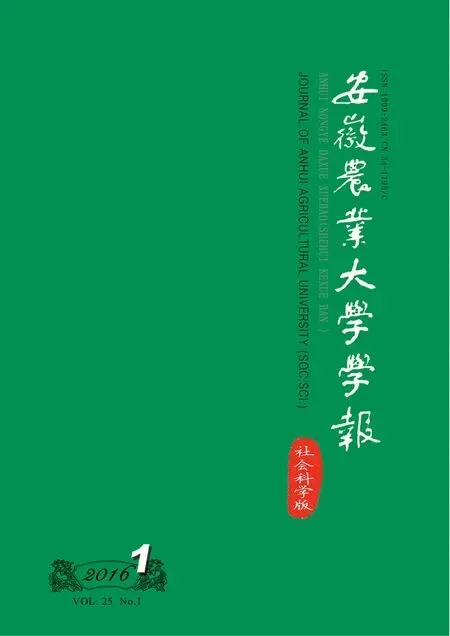“实践美学”的文本架构*——李泽厚艺术思想的西学归宗与本土融创
鹿 咏,张 伟
(1.合肥学院艺术设计系,安徽合肥230601;2.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安徽合肥230036)
“实践美学”的文本架构*——李泽厚艺术思想的西学归宗与本土融创
鹿 咏1,张 伟2
(1.合肥学院艺术设计系,安徽合肥230601;2.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安徽合肥230036)
摘 要:作为20世纪中国美学的典范符号,李泽厚“实践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过程是中西美学与文化艺术理论融汇、提炼的过程,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乃至现代西方文化理论成为这一美学体系的西学符号,“巫史”传统、实用理性以及“乐感文化”则成为李泽厚借鉴西学思想烛照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理论产物,其化合中西、融会贯通的理论驾驭范式不仅成就了20世纪中国美学的奇观,也引发了对美学与艺术理论延展的无尽思考。
关键词:李泽厚;实践美学;主体性;艺术
在20世纪中国美学的演进历程中,发生于50—60年代的第一次美学大讨论无疑是一次颇具影响力的学术事件,作为多元美学思想激烈争议、碰撞的场域,诸多美学流派在这次讨论中崭露头角,凭借自身的学术思想和理论观念跻身中国现代美学的百花园。这次美学大讨论之所以意义重大,不仅是学术争议使得各种美学观念在相互争议和批判中渐趋丰满、成熟,扩大了影响力,进而获得更多共鸣与认同,更为重要的是这次大讨论古未有之,其参与人数之多、争议之激烈、理论贡献之大实属少见,对现代美学的发展富有承前启后之功。所谓“承前”,是指这次美学讨论促使部分学者对自身学术观念进行一次自我反省和总结,而其背后乃是对中国近代美学发展的重新审视和评判,朱光潜、蔡仪是这一情形的代表;所谓“启后”,是指美学大讨论创造了理论衍生的契机,不仅让更多的美学爱好者加盟美学研究,更使得理论的创新乃至新的理论体系在各派观念的争议中得以产生,就这一情况而言,李泽厚最为典型。换言之,是这次美学大讨论催生了李泽厚美学体系的建构,让美学大讨论的余绪延展至下半世纪,并在80年代初期以更加成熟的理论形态佐证了第一次美学大讨论的筚路蓝缕。
作为20世纪中国美学领域的著名学者,李泽厚是不可忽视的富有理论原创精神的美学大师,他以其鲜明的理论性格在美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创立的实践美学体系是中国现代实践美学的缩影,是对各种先哲学术思想的汇集、融通和改造,以特有的理论方式铸就了20世纪李泽厚美学乃至中国美学的鲜明符号,呈现出20世纪中国现代美学的别样景观。
一、西学谱系:李泽厚建构实践美学体系的外化图式
与20世纪的其他美学家一样,化合中西的学术范式照例成为李泽厚建构其实践美学思想的主要方法。尽管李泽厚的美学体系衍生的直接诱因是在美学讨论中对蔡仪“美在客观”及朱光潜“美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等美学观念的调和与修正,但他并非拘泥于此,化合东西方美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思想精华,结合中国传统艺术实践,进而进行理论的建构与创新,绘制富有原创色彩的实践美学谱系成为其化合中西的真正目的。在对西方美学思想的融汇进程中,李泽厚实践美学思想的西学因子很难用一家之说界定之,其理论体系的演进和充实是在不断对中西方美学的时代汇合中完成的,正如他所标举的“社会性”一样,他的美学思想中的西学渊源同样遵循着“社会性”原则。
在李泽厚实践美学的西学谱系中,康德和黑格尔是其美学理论建构的两个“幽灵”[1],康德的美学观点奠定了李泽厚实践美学思想的基调。李泽厚建构的实践美学体系,从理论的外显形态上似乎就遵循着康德美学“知、情、意”的理论图谱,与康德的“知、情、意”体系对应的,李泽厚将人的主体结构划分为自由直观、自由意志和自由感受三种形态,由此审美形态就呈现为感官层面的“悦耳悦目”、情感层面的“悦心悦意”以及伦理层面的“悦志悦神”三种类型。主体性是康德美学的灵魂,康德提出的“自然向人生成”就是要高扬人类实践活动的主观能动作用,改造自然,推动自然向人生成。康德将审美主体的能动性视为解决审美问题的着力点,注重人的主体性和自由创造性对美感的能动作用,认为审美判断取决于审美主体,应该从审美主体自身寻找美的本质。康德对主体性的推崇给予李泽厚极大的启发,李泽厚“主体性实践美学”中所标举的主体性就是从康德美学中继承而来的。在李泽厚的艺术美学体系中,主体性是变动的,在提出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的美本质界定中,主体是属于“类属性”来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李泽厚对主体性的强调源自对康德“主体目的性”的青睐,换言之,“主体目的性”成为李泽厚艺术理论体系建构的基点,在他看来,“要努力去取得自己生命的意义。……它不只是发现自己、寻觅自己,而且去创造、建立那只能活一次的独一无二的自己,所以人不能是工具、手段,人是目的自身。”[2]诚然,尽管康德的主体性成为影响李泽厚艺术思想建构的显性标记,但李氏并非对康德主体性进行直接照搬,康德美学只不过给了李泽厚理论建构的思想导向,提供了他孕化自身理论体系的先在条件和契机,而正是这种孕化,一直成为李氏艺术理论建构的潜在标杆。
相比于康德,李泽厚对黑格尔美学的继承与融汇要明确得多,黑格尔美学中历史主义意识对李氏影响深远。李泽厚认为:“黑格尔的历史感,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的观点是永远值得高度评价与研究的方面,因为他站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高度来认识与观察一切问题。”[3]357在李泽厚看来,艺术观念只有扎根于历史中,在历史的洪流中经受检验,才具有现实意义和理性价值。当然,一个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从大量的历史材料和现象中寻找有益于艺术发展的“规律”,进而完成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是黑格尔哲学的真谛,也是所有艺术工作的真谛。“工具论本体”是李泽厚受惠于黑格尔的又一理论观点,黑格尔曾指出:“手段是一个比外在合目的性的有限目的更高的东西。人以他的工具而具有支配外在自然界的威力,尽管就他的目的来说,他倒是要服从自然界的。”[4]李泽厚接受了这一观点,他认为人类是为了生存的目的而从事社会实践,表面上看自然生产似乎是社会实践的目的,而实际上人类创造了比自然生产更为重要的社会文明。出于对黑格尔理论的过于推崇,有时让李泽厚在黑格尔历史和逻辑统一的论证中迷失方向,不自觉地陷入黑格尔的本质主义和目的论中难以自拔。在美学大讨论中,李泽厚“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本质界定将“美”视为人的“类”实践的结果,将形式与美感视为美的本质力量外化的结果,这一观点明显是黑格尔“绝对理念”的中国图式。诚然,对于黑格尔美学的缺陷李泽厚也有着清晰的洞察:“感性的、偶然的、个体的东西黑格尔就注意不够,这些内容在黑格尔的历史整体感中消失了。”[3]358在李泽厚看来,黑格尔虽然秉持历史主义意识,但他的“绝对理念”却是对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抹杀,其最终的走向是神秘主义,导向最后的精神主体上帝。
康德和黑格尔的美学思想给了李泽厚以理论的启迪,马克思主义则成为李泽厚建构实践美学理论体系的根基。李泽厚认为,要想真正解决康德“自然向人生成”的问题,其最好的方式是借助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倡导的人类实践方式可以实现自然服务于人的目的。李泽厚给自己崇奉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取了个名字“吃饭哲学”,马克思主义注重物质生产本身是一切历史存在的前提,而“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就是强调衣食住行、物质生产对人类生存的决定作用,亦即他所谓的“吃饭哲学”的终极内涵。
秉承“吃饭哲学”的基本观念,李泽厚对马克思主义“自然的人化”这一理论观点展开解读。马克思对美的本质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巴黎手稿》中,这一著作于1956年在前苏联得以出版,随即引发关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手稿热”,在这次研究热潮中,对美的本质探讨集中于两个层面,一是“自然说”,一是“社会说”,所谓的“自然说”主张美的本质源于客观对象的内在属性,审美感受不能离开审美客体而存在。“社会说”则主张美的本质源于人类的生产实践,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李泽厚接受了这两种理论并进行了调和和发展,他认为,美作为自由的形式,是合规律和合目的的统一,是外在自然的人化或人化的自然。他把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自然的人化”细分为两种:“外在自然的人化”和“内在自然的人化”,在他看来,所谓“外在自然的人化”是指人对作为自身生存环境的自然界的改造和自然与人的相互关系的转化,所谓“内在自然的人化”包括人对自身器官的改造以及人的内在心理结构。由此,李泽厚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人化”观建构成为一个涵盖从感性到理性、从感官到心理、从自然到社会的结合体,正是这种“自然的人化”促使历史与现实、自然与社会、理性与感性以及个人与社会实现内在、全面的交融统一。
李泽厚“自然人化”的理论观念概括了美的本质、美感等多种理论实质,但这种“自然人化”注重的是“人类”“历史”以及“社会实践”等宏大叙事范畴,对于美、美感以及艺术如何导向个体生命和感性自由,李泽厚提出了“积淀说”。“积淀说”是李泽厚用以揭橥人类审美心理生成、延展的重要理论学说,是其沟通“工具本体”与“心理本体”的桥梁和纽带,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他指出:“所谓积淀,是指人类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才产生了人性——即人类独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亦即哲学讲的‘心理本体’,即人类的积淀为个性的,理性的积淀为感性的,社会的积淀为自然的,原来是动物性的感官人化了,自然的心理结构和素质化成为人类性的东西,这个人性建构是积淀的产物,是内在自然的人化,也是文化心理结构。”[5]在李泽厚看来,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并非自然的恩赐,它是人类在漫长的生产实践过程中逐渐生成的历史成果。人类的劳动实践活动促进了现实中社会关系的生成,人类在认识自然和认知世界的过程中又发挥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对自然和世界进行了人化的改造,同时在思想意识层面对这一认知和改造进行内化乃至浓缩,进而构筑成人独有的一种文化心理结构,这意味着内在人化自然的形成,标志着人类心理本体的确立,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积淀的过程。无论是“自然的人化”抑或“积淀”说都是李泽厚实践美学体系的基石,都是李泽厚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丰富和发展,同时又是对康德和黑格尔美学观念的自我调适,两者沐浴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理性逻辑中,成就了李泽厚实践美学理论中最为醒目的价值符号。
李泽厚生活的时代是中国文化重启国门,拥抱西方多元文化体系的时代,李泽厚建构实践美学体系的过程也是其对西方文论不断涉猎、参照乃至调适的进程,西方现代心理学、形式主义美学都给李氏以深刻的影响。德国学者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作为西方现代心理学的典范样式倍受李泽厚的追捧,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与李泽厚倡导的“美是社会性和客观性的统一”的理论主张不谋而合,在荣格看来,人类大脑处于不断进化的过程,而人类思想层面的各种无意识则源于人类经历的各种社会经验在大脑结构中的生理遗存,在不断传承过程中形成为个体的“集体无意识”。李泽厚将这一学说从荣格的心理学领域移植到美学领域,他认为,艺术家要善于通过物质材料将人们头脑中隐含的原型唤醒,促使人们感受种族的原始经验,艺术就是这种唤醒人类原始经验的符号,它这一符号并不注重于对观念意识的某种呈示,其本质目的乃是唤醒人们头脑中某种隐藏的东西,亦即某一先定的原型存在。
“有意味的形式”作为一个常态的艺术范畴,源于西方形式主义美学,李泽厚援引这一范畴并对其进行了重新阐释,他认为,贝尔“有意味的形式”提出了艺术形态中形状、色彩以及形状色彩对人的一种感知作用,在艺术的发展进程中,艺术形象层的流变是伴随着创作主体自身的情欲与观念而呈现出的“由再现到表现,由表现到装饰,再由装饰回到再现与表现”的循环变迁,艺术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由内容过渡到形式的积淀过程。同时李泽厚也指出,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割裂了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李泽厚将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从纯粹的形式框架中解放出来,认为这种“有意味的形式”是由具体事物演化而来,换言之,是由再现艺术“意味”的具体形象演化为这一“有意味的形式”。
诚然,李泽厚对西方美学理论的涉猎是颇为宽泛的,中西融通的时代语境创造了他化合中西的契机,促使他站在理论创新的制高点审视西方美学的多元潮流,在融贯中西的理论创构中汇聚诸多的西方审美符号。
二、本土复归:李泽厚对中国传统艺术观念的理论提升
同朱光潜、宗白华等现代美学家一样,化合中西、融会贯通,借鉴西学思想烛照中国本土艺术精神同样也是李泽厚治学的主要路向。李泽厚对本土传统文化的关注是带有现实针对性的,8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物质生活不断丰富,科技的进步以及人们对金钱的聚焦造成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异化的趋势,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遭遇断裂,如何实现个体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共存,如何实现传统社会人情伦理的适度回归引发诸多有识之士的深度思考。依据李泽厚的观点,孔子以“仁爱”为核心的伦理观念和道德理性构筑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框架,它引导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化解人与自然、社会乃至人与人紧张关系的有效途径。更为重要的是,李泽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了其实践美学体系中引起外界攻讦的解码之钥,他前期倡导的“工具本体论”以及“自然的人化”对主体实践力量的过度追捧,导致人与世界的疏离与断裂,而这恰恰授人以攻讦的话柄,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成为化解这一攻讦的灵药,这也引发了李泽厚“工具本体”与“自然人化”向“情感本体”与“人的自然化”的思想转向,因而古典美学与传统文化成为李泽厚后期学术关注的集中地。
李泽厚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理论建构最富代表性的是他对艺术的“巫史之源”理论解读以及对“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的理论衍发。李泽厚对艺术美学中的“巫史”说进行了考证,在他看来,原始时期艺术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就与当时兴盛的巫术活动密切相关。对于艺术史上的“巫史”传统,李泽厚认为两个环节不可忽视,首先是“巫君合一”,在他看来,在古代思想史中,“巫”借助“政教合一”与“巫君合一”而趋于理性与规范,进而成为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巫”也成为管窥古代思想文化的密钥。随着“巫”的理性化加强,非理性的成分渐趋减少,“由巫而史”,“巫术的世界,变而为符号(象征)的世界、数字的世界、历史事件的世界”[6]。正是在“巫君合一”“由巫而史”的双重作用下,“巫史”成为艺术发展的主要源头,渐而也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基本性格的表征。
基于艺术史上的“巫史”说,李泽厚对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展开分析。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天人合一”思想与其实践美学中“自然的人化”不谋而合,“天人合一”源出“巫史”传统,在“巫君合一”“政教合一”的教化中定型。李泽厚认为“自然的人化”就是在古代“天人合一”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理论延伸,此时的“自然的人化”作为“天人合一”的现代衍化,不再拘泥于个人心理,而是整个社会、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和谐统一,这种“天人合一”是“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有机统一。在他的“人的自然化”中,原本“天人合一”观念中那种神秘的光晕已经不再,而是被强化了另一种性质,亦即整体性、社会性和物质性,同时“天人合一”也不再是单层面的理论形态,在李泽厚的理论延展中,它源自中国传统文化,却又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与自然人化论中汲取理论营养,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作为两个审美理论范畴成为架构李泽厚实践美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李泽厚对中国传统艺术观念进行理论修正与思想演绎的独特贡献。在李泽厚看来,“实用理性”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契合了中国传统艺术的主要观念,而“乐感文化”则蕴含了中国传统艺术思想的本质特征与典范形态。李泽厚认为,中国传统艺术观念中的“实用理性”不是绝对的、先验的,而是历史的、变动的,有一定灵活的“度”。这种“实用理性”代表着主体情感与历史经验交融的理性样式,它制约着思辨理性的无边延展,同时也抗拒反理性主义的极度泛滥,它以儒家文化为基础,以是否符合实际需求为标准,以维持平衡和稳定为目标,形成一种清醒冷静而又温情脉脉的中庸心理和民族性格。秉持着“实用理性”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艺术观念呈现出以“乐感文化”为特质的文化面貌。李泽厚认为:“‘乐’不以另一超验世界为依皈,而以追求现世幸福为目标为理想。儒家的礼乐是巫术活动的理性化、规范化。礼是指管理社会、维持社会秩序的规章制度,而乐则帮助人们在情感上和谐起来。”[7]与西方社会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罪感文化”相对应,李泽厚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及其表现形态是迥然有别的“乐感文化”,即尽管相信人生之艰难,但却不依仗上帝的庇护,自信经过自身的努力就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这种依靠自身承载悲乐的本体精神才是最为深刻的悲剧。李泽厚的“乐感文化”是对中国几千年民族文化心理和艺术观念的总结和提炼,这一文化心理倡导凭依自身坚强的意志与进取的精神来延展生命存在,这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蕴含着坚韧的奋发意识和忧患精神,是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的真实写照。
李泽厚对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中“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的揭橥并将其融入自身的美学体系中,可谓把握住了中国数千年文化艺术的精髓和命脉。诚然,对“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的揭示并非代表着李泽厚考察中国传统美学的终点,以“情本体”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本身的情感真理才是这一“乐感文化”理论的最终目的。至今看来,李泽厚提出的“情本体”论,其价值在于制约因“工具本体”的过度膨胀而造成的人与世界的紧张关系,其内涵包含了夫妇、亲子、男女、朋友等诸多情感,甚至蕴含一种普救众生的襟怀、天人交会的归依感以及创造发明的欢欣等等,它涵容世俗社会中人的所有情感体验,呈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理论面貌。作为“乐感文化”的价值核心,“情本体”为徘徊于诸多文化思潮而难以寻觅情感依托的国人提供了安身立命的根本。从“巫史传统”“儒道互补”再到“实用理性”“乐感文化”乃至“情本体”,李泽厚凭借一系列特有的理论范畴建构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的理论认知和审美解读,为自身的实践美学体系添加了浓厚的本土特色,进而最终实现了其美学思想的本土复归。
三、理性定位:李泽厚实践美学思想的诗性反思与艺术点化
作为当代中国最富学术原创性的美学家和思想史家,李泽厚创构的实践美学体系是颇具哲学气质和理论深度的美学思想,他的美学从“实践”出发,演绎出“美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的本质界定,由“自然的人化”肇始,考察美与美感,探讨美感的三种形态,进而为艺术品三个层次的划分提供依据,整个理论体系环环相扣、严谨缜密,构筑成既有独特理论出发点又能相互照应的有机统一体。
作为中国现代美学的主流之一,马克思主义是李泽厚个人自觉的学术追求与价值目标,其实践美学体系秉承历史唯物主义的主流观念,标举“实践”在美学中的重要地位,坚持实践对于人类审美意识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性规定,敏锐地捕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生活的理论对接点,激活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价值,更为可贵的是,抛开70年代时代对康德美学的偏见,将康德美学与马克思主义悄然嫁接,以“自然的人化”作为理论延展的基础,提出外在自然的人化与内在自然的人化并由此衍化为人性生成的积淀说,推导出工具本体向心理本体的演化逻辑,最终导向人性的理想模式——审美本体论。可见,李泽厚在蕴藉马克思主义理论体液的基础上,希冀构筑一个由人类文明源头向未来精神衍化的主体性美学框架,凭依审美本体论的方式标举人类自身的精神存在,从而促使自身美学在马克思主义美学谱系中独具特色。
李泽厚实践美学最大的学术属性应当是人类本体论美学。他提出的“自然的人化”“积淀”“新感性”等范畴都是对人本体探讨的常态语汇。李泽厚的人类本体论的实践美学为当代中国美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学术视野,促使学界从人类文化的宏观视角去解读人类自身的审美行为与价值内涵。
对于艺术的一些基本问题,李泽厚基于他的主体性实践美学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他认为艺术的基本问题就是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换言之,就是艺术形象与典型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美客观地存在于人类的社会生活中,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却很难直接欣赏美、感知美,艺术是对现实的集中反映,因而只有借助艺术才能完满地把社会生活的本质以美的形式呈现出来。当然,艺术对生活的形象反映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一种能动的提炼和集中,“只有当社会美当作被反映的主题,通过提炼集中成为广阔明确的艺术内容,自然美当作被运用的物质手段,经过选择琢磨成为精巧纯熟的艺术形式,在艺术中融为一体,美的内容与形式,社会美与自然美才高度统一起来,成为一种更集中、更典型、更高的美,这就是艺术美”[8]。
其次,形象思维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是李泽厚关注的对象。他认为,形象思维是一个富有自身特征的独立过程,与美感在本质上是贯通的,都是对存在于现实生活的美的一种主观能动反映。形象思维发生的过程同样遵循着从现象到本质、从感性到理性的衍化规律,但在形象思维中,感性活动和想象不可或缺,因而形象思维的特质决定着艺术本身就是一种认知,以形象来反映生活的一种特殊认知。他指出,形象思维中也包含着理性的成分,但这种理性并非以概念的形式存在,在形象思维中,艺术家遵循的是情感的逻辑而不是理论思维的“逻辑”。20世纪后期,李泽厚已然不再拘泥于从艺术与现实生活的视角去剖析艺术的本质,而是转向关注主体与艺术形成的审美经验,以及主体的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建立的审美心理结构。
再次,按照李泽厚对美感的认知,他认为在审美进程中美感呈现为三种形态,亦即悦耳悦目、悦心悦意以及悦志悦神,与此相对应的,艺术品也可以划分为形式层、形象层和意味层。在李泽厚看来,形式层是一定的客观物质材料呈现审美形态的手段,艺术品的质料、体积、颜色、硬度以及这些材料的组合规律如节奏、韵律、均衡等都是形式层不可缺少的因素。至于形象层,它是艺术品呈现的而且可以通过语言指称的具象世界,它展示的是一个意象纷呈、千变万化的幻象场景,其最大的特征在于这些形象层深处潜藏着的人性特质,正是这人性特质,成为人的生命力量在艺术幻想世界的外在呈现,使艺术品有了真正的艺术感染力。“意味层”是寄载于“形式层”和“形象层”之上的一个层面,指涉的是人类情感本体的建构,已然超越于感官和情欲的人化,所传达的是艺术品能够永久绵延的可品味性,因而是艺术品具有永恒魅力的根源。
由此可见,李泽厚对艺术问题的探讨是不断发展、丰富的,其理论的建构如同他的美的本质论一样,遵循着外在自然的人化到内在自然人化的嬗变,其终极指向则是主体性在艺术活动中地位的确立,这是李泽厚艺术观的本质所在。
当然,作为一种富于原创的理论体系,李泽厚所建构的实践美学还存在着诸多瑕疵,对美的本质以及丰富复杂的审美现象的理论解答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但作为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美学界的理论符号,李泽厚的实践美学无疑开创了筚路蓝缕之功,其理论的现代价值不仅是对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的最好总结,也将指引着新世纪国内美学发展的方向,它为中国现代美学发展史无疑会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其理论观点和理性价值将会引发现代学人更多的思考。
参考文献:
[1]吉新宏.多元调适:李泽厚美学的理论性格[J].宁夏社会科学,2004(3):90-95.
[2]李泽厚.美学四讲[M].北京:三联书店,1989:250.
[3]李泽厚.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4][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438.
[5]李泽厚.美学四讲[M].北京:三联书店,1989:114.
[6]李泽厚.己卯五说[M].北京:三联书店,2006:166.
[7]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M].北京:三联书店,2005:54.
[8]李泽厚.美学论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164.
Text Construction of Practical Aesthetics:
Influence of Western Aesthetics and Local Culture on Li Zehou’s Art Aesthetics
LU Yong1,ZHANG Wei2
(1.Department of Art & Design,Hefei University,Hefei 230601,China;2.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Hefei 230036,China)
Abstract:As a model of Chinese aesthetic in the 20th century,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Practical Aesthetics of Li Zehou was constructed by integrating and refining the theories of western and eastern aesthetics,culture and art.Thoughts of Kant and Hegel,Maxism and even modern western cultural theories became the western symbol of the aesthetic system.Necromancer tradition,practical reason and comfort-oriented culture are the theoretical products of Li Zehou’referring western thoughts to illuminate the spiri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t.This theoretical paradigm of combining east and west and“putting all things together”not only yield a wonder of Chinese aesthetics in the 20th century,but also bring about endless thinking about the extension of aesthetics and art theories.
Key words:Li Zehou;practical aesthetics;subjectivity;art
作者简介:鹿 咏(1983-),女,安徽霍邱人,合肥学院艺术设计系讲师,硕士。张 伟(1979-),男,安徽庐江人,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4YJC760079:《绘画中的时间结构研究》)
收稿日期:2015-07-06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63(2016)01-008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