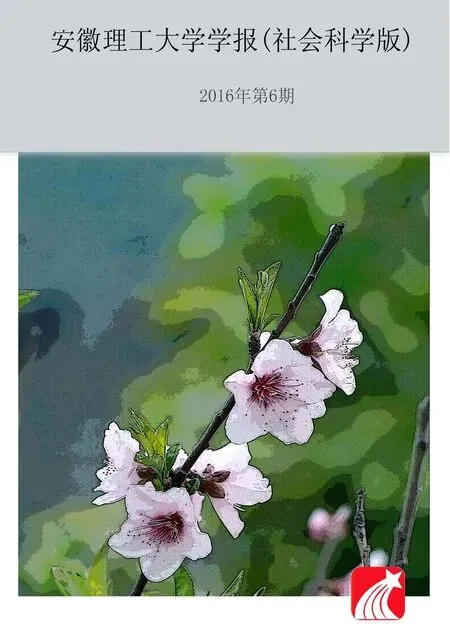论外汉音译的意义关联
刘祥清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长沙 410205)
论外汉音译的意义关联
刘祥清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长沙 410205)
外汉音译与意义密切相关,表现在:外汉音译本质上是利用假借译音代义,译音汉字选择上无法避开汉字的字面意义,译音汉字认知上遵循汉语使用者的“集体无意识”和外汉音译词使用上的有意利用译音汉字的字面意义等。
音译;外汉音译;意义
翻译是意义的语际转换,翻译的作用对象是意义。意义的正确、完全转换是翻译的理想归宿和终极目标。从方法上讲,有意译音译两种。20世纪20年代,意译也称“义译”。很多人认为意译与意义直接相关,而音译的直接相关度不大。实际情况是,音译过程中意义如影随形,外汉音译尤其明显。
一、外汉音译译音代义,以变通方式实现意义语际转换
意义语际转换过程中,我们首先想到的方法是意译。意译是意义语际转换的理所当然的常规方法。但语言之间客观地存在可译性限度[1],意译有其不足或无可奈何之处①关于意译的不足,名家多有论述,笔者亦有归纳,详见笔者《音译与可译性限度的消解》(中国科技翻译,2010( 2) :38-41,60)。中国翻译史上20世纪初那次有名的音译大讨论中,章士钊,朱自清等也有论述,详见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p172-182,249-254)。杨枕旦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上曾以系列科技术语翻译杂议形式提供了大量有利例证。,不可避免地做不到万能,需要一种方法来辅助。于是,音译应运而生。
音译(Transliteration),顾名思义,是通过记录外语词的语音形式借用词语的方法,是“平常一个语言甲借语言乙里的一个词就是取乙的某词改用甲的音系里的可能的音当一个新词来用”[2]。J.C. 卡特福德(J.C. Catford)曾研究过音译,将音译过程分成三步骤:1)用译出语的语音单位代替译入语的字母,2)用译入语的语音单位转写译出语的语音单位,3)将译入语的语音单位转换成译入语的字母或其它书写单位[3]。
从以上赵元任老先生的定义和J.C.卡特福德的音译三步骤可以看出,音译所做的,是在译出语和译入语之间建立语音联系、确定相同或相似语音、用译入语字母或书写单位转换替代译出语语音,形成一个音译词。这个词在译入语中本来不存在,它被译者人为规定为译入语的对等词汇形式(equivalent),被译者“赋予”了与原词全部或部分意义相同或相当的意义。音译词形成后,翻译过程完成,翻译目的达到。
由此可以看出,意译音译的不同点在于意义语际转换方法不一样,意义转换媒介不一样。所谓意译,就是以译出语的文字符号的意义直接作为意义转换媒介来实现意义转换[4]46。它可能的实现途径有:1)在译入语中找到意义相同或相当的词汇形式;2)通过语义再生手段赋予译入语原词一个新的相当的意义;3)利用译入语原字原义组合成一个新词,直接地实现意义语际转换。而音译则是选择译出语语言符号的语音作为意义转换媒介,在译入语中找到与译出语语言符号读音相同或相似的符号来译写,并将最终的译写结果整体地、人为地“赋予”与原符号相同的意义[4]46。它可能的实现途径是,以音似为基础,从译入语原字原词中选择现成的字词或创设新字新词,采用摹其音、借其形、舍其义的方式来对应。概括来说,音译着眼点虽是语音形式,但作用点是意义,落脚点是意义的语际转换。音译是译音代义,是用变通的方法实现意义的语际转换。从这点来说,音译意译殊途同归。
二、外汉音译利用假借机制,译音表义
音译,究其实质,就是假借。
假借是汉字“六书”之一。许慎《说文叙》中说:“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也就是说,古汉语中的某个“词”,本来没有替它造字,依照它的声音“假借”一个同音的字来寄托这个“词”的意义。“从文字学角度来看,音译实际上继承了中国传统六书的假借机制,即所谓‘本无其字,依声托事’”[5]108。
外汉音译,就是以语音为基础,以音同或音似为原则,在汉语中选择现成汉字或创造新汉字来对译外语语词。外汉音译根据译音汉字的来源可以分为选择现有汉字音译和新创汉字音译两种形式[6]242-243。不管哪种形式,所选的译音汉字是都是记音符号。我们选取了这个汉字的字形,利用了它的语音,但去除了它的字义。这样的译音汉字组合起来的汉语新词,是连绵词,本身无法分解。比如,俄语中的“Большевик”,20世纪初介绍引进中国时,汉语中没有对应的词(所谓的“本无其字”),就依其读音,在汉字中选择有相似读音的汉字(所谓的“依声托事”),组成了一个汉语新词“布尔什维克”。这五个字中的任何一个,都只是记音符号。
外汉音译过程中,译者采用依声托事方式,将之假借过来,整体地、人为地规定为原俄语词的汉语对应形式,人为地赋予了与原词相当的意义。音译就这样译音表义,以曲折的方式实现意义转换,达到交际目的。
三、外汉音译词形成和认知无法避开译音汉字字面意义
J.C. 卡特福德的音译三步骤在外汉音译时表现出一种特殊性,即三步骤归结为一点,即音译字选择[7]36。外汉音译词形成中,我们选择汉字作为记音符号。主观上讲,我们选择这个译音汉字,是借其形,摹其音,舍其义。但译音汉字和汉语中的其它汉字一样,音形义三位一体。客观结果上讲,我们选择的或者新创的都是有意义的汉字,是音形义三位一体的语言符号。所以说,译音汉字选择中,我们无法割裂汉字音形义三位一体的本来特征,因而也无法避开译音汉字的字面意义。第31届夏季奥运会将在巴西城市Rio de Janeiro举行。该城市音译为“里约热内卢”,简称“里约”。这里的“约”只是一个记音符号,与它的本来意义无关。2016年巴西里约奥运会女足亚洲区预选赛中中国女足提前一轮获得晋级奥运会资格。网易新闻3月8日、中国青年网3月9日新闻题目分别为“风雨兼程,女足赴‘约’”,“中国三大球齐整赴‘约’”。预选赛最后一轮结束后,中国女足获第二名。北京卫视3月10日“北京您早”节目以“战平澳大利亚,中国女足如愿赴‘约’”为题对此进行报道。“赴‘约’”一词的使用,就是外汉音译无法避开译音汉字的字面意义的例证。
汉语中同音字、多音字占优势。若不计声调,汉语中的一个音节平均对应20个汉字[8]。另外,音译过程中存在音译原词的语音准确性,语言的地域差异(如大陆和港澳台汉语的用字差异),译者个人因素(如所持方言,个人偏好)和译音汉字的修辞取向等问题。这使得译者在确定译音汉字时,有很大的主观自由度。如英语chocolate的音译形式就有朱古力、巧克利、巧格力、巧古力、巧可力、查古列、查古律、勺古力、诸古力等。
译音汉字选择时,一方面无法避开它的字面意义,另一方面又有很多因素导致译音汉字选择的自由度,这就使得汉语使用者(包括汉语译者)在译音汉字的认知上,和一般汉字认知一样,出现因形见义、以形显义、依形索义的思维定式,或称“集体无意识”。“茉莉”的草字头可以因形索义,能起意义提示作用,取代“没利”或“末丽”成为梵语mallika的音译形式。英语Aids的原来的音译形式“爱滋病”中的“爱”“因形见义”后会出现意义误解而被“艾滋病”取代。前不久有一场著名的围棋人机大战,对弈一方为谷歌公司开发的围棋软件AlphaGo,音译成“阿尔法狗”,其中的“狗”字的选择是有意为之。AlphaGo即将拿下第三局,3:1领先时,网易直播中的讲棋嘉宾曾诙谐地说“这只狗又赢了。”“这只狗”三个字是我们汉字认知上的“集体无意识”的又一例证。
汉字认知上的“集体无意识”让我们“就着原来的译音再应用传统的‘飞鸟安禽、水族著鱼’的办法把它们写成谐音字”[9],或形成“音译义”[10],或译音汉字“音译增义”[11],或出现“意义别解”[12]。
四、外汉音译词使用中巧妙利用译音汉字字面意义能够丰富汉语表现手段
综上所述,外汉音译的特殊性决定了外汉音译只取其音、不取其义很多时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既然我们做不到只取其音、不取其义,那就会想着法子,就着我们汉字认知上的“集体无意识”,既取其音,又取其义,巧妙运用译音汉字的字面意义,丰富汉语表现手段。
音译词使用中,巧妙利用译音汉字的字面意义,能使得语言新颖,凸显语言智慧。2016年世预赛中国男足最后一战对卡塔尔,《羊城晚报》3月28日新闻题目是“国足完整备战世预赛 出线靠运气刷‘卡’靠实力”。此处“卡”字来自于音译词“卡塔尔”,本是记音符号的“卡”,因形见义地与现代日常生活中的刷卡相联系之后,“刷‘卡’”一词横空出世,新颖有趣,魅力凸显。在谜语、幽默、笑话和相声等语言文字游戏中,设计特定语境,巧妙利用译音汉字的字面意义,与音译词意义形成对照,相映成趣,语言也因此生动活泼、诙谐幽默。如:“从前柬埔寨有一个老公公,大家叫他阿拉伯。有一天,他带着墨西哥去爬山,当爬到新加坡的时候,突然来了一只头上长着好望角的巴拿马。他吓得出了一身阿富汗,拔腿跑进了名古屋,赶快关也门,结果碰掉了一颗葡萄牙。”(杨畅《巧妙的回答》,《故事会》2000年6期)。
音译词使用中,巧妙利用译音汉字的字面意义,能直接准确地表达言语者的感情色彩。人名地名翻译中,Hugo 音译为“嚣俄”或“雨果”,Yeats 音译为“夏芝”或“叶慈”,Pittsburgh 音译为 “匹兹堡”或“痞子堡”,Maryland 音译为“马里兰”或“马驴栏”,Wahington音译为“华盛顿”或“花生屯”,Oregon 音译为“俄勒冈”或“饿狼岗”,La Jolla 音译为“拉荷亚”或“老虎崖”,感情色彩自是不同[13]179,182-183。杨全红改Loch Ness(尼斯湖)和Loch Lomond(罗梦湖)为“若诗湖”、“若梦湖”,徐志摩改Firenze(佛罗伦萨)为“翡冷翠”,胡适将康奈尔大学所在地Ithaca音译为“绮色佳”,周策纵改威斯康辛大学所在地Madison(麦迪逊)为“陌地生”,原因都在于以此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NASDAG(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 Automated Quotation System)一般音译为“纳斯达克”。它曾因不公正对待中国上市公司而被称为“那厮搭客”,一个“厮”字凸显其感情色彩。
巧妙利用译音汉字的字面意义,能收到很好的修辞效果。关于汉语中译音汉字与修辞效果的研究较多,主要有陈舒眉[14]、潘勃[15]、尹建新[16]、周日安[17]、潘国英[18]、鲍文[11]、徐义云[19]、杨全红[13]、刘丽华、刘祥清[20]等。在此特别说明的是,笔者[6]244称之为诙谐音译的、类似文字游戏的音译,如:fair play:公平竞争、费厄泼赖,husband:丈夫、黑漆板凳,commission:佣金、孔密兄,doctor:医生、多看透,Espranto:世界语、爱斯不难读,gentleman:绅士、尖头鳗,ladies:女士们、累得死,mister:先生、密斯偷,shopping:购物、血拼,sentimental:伤感、酸的馒头,university:大学、由你玩四年,等。这些外语词,在已有较为固定的意译词的情况下,采用其音译形式,所选汉字的字面意义与原词所指称的概念在内容上产生巨大的反差,一方面起到诙谐幽默或讽刺挖苦的修辞作用,另一方面体现了言语者的语言智慧,凸显了语言魅力。
五、 结语
因为汉字的独特表意性和汉语使用者汉字认知上的“集体无意识”,外汉音译区别于其它语言之间的音译,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也更为密切。这体现在外汉音译本质上是利用假借、译音代义,实现意义语际转换,也表现在外汉音译词的形成、认知和使用上。认识外汉音译的这一特殊性,有利于深入理解外汉音译本质,准确把握外汉音译方法,正确认识外汉音译在丰富汉语语言表现手法上的作用。
[1] 刘宓庆. 新编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114-115.
[2] 赵元任. 论翻译中信、达、雅的信的幅度[A]. 吴宗济,赵新那.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C].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2.
[3] Catford J C.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4] 刘祥清.意义转换媒介与意译、音译和形译[J].中国科技翻译,2015(2) :45-47.
[5] 龚雪梅.音译用字的文字学考察[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108-112.
[6] 刘祥清.论音译形式及其丰富与发展—以外汉音译为例[J].湖南社会科学,2014( 6) :242 -245.
[7] 刘祥清.论音译字的选择[J].中国科技翻译,2014,(2):35-38.
[8] 龚嘉镇.现代汉字形音关系研究[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
[9]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 北京出版社,2004.
[10] 潘文国.汉字的音译义[A].胡明扬.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C].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429-437.
[11] 鲍文.外来词音译增值现象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4):54-56.
[12] 杨锡彭. 汉语外来词研究[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3] 杨全红.高级翻译十二讲[M].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14] 陈舒眉.谐译―――一种植根与汉字的修辞方法[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3):92-96.
[15] 潘勃.译名由音转意的修辞现象[J].修辞学习,1999(1):42.
[16] 尹建新. 试论汉语外来词的修辞艺术[J].阅读与写作,1999(1):31-32.
[17] 周日安,向玉兰.音译外来词的临时汉化[J].学语文,2002(1):45.
[18] 潘国英.外来词引起的汉语词语的修辞分化[J].修辞学习,2004(2):74 -75.
[19] 徐义云.英语外来词的修辞功能[J].重庆交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7( 6) :89 -91.
[20] 刘丽华,刘祥清.论音译汉字的选择及其修辞功能[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140-144.
[责任编辑:吴晓红]
Close Relationship of F-C Transliteration with Meaning
LIU Xiang-q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205, China)
F-C transliteration (Transliteration from a foreign language into Chinese)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meaning, which is illustrated by the following facts: F-C transliteration being in nature for the purpose of inter-lingual shift of meaning; the literal meaning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chosen for transliteration not to be ignored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transliterated word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 being subject to the so-called “collective sub-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speakers; and the literal meaning of the character being always deliberately taken advantaged of in the use of the transliterated words.
transliteration; F-C transliteration; meaning
2016-05-1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课题“音译字选择与音译词规范研究”(11YJA740054);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科研项目“音译汉化研究”(HN-0029-A)
刘祥清(1967-),男,湖南祁阳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翻译史。
H315.9
A
1672-1101(2016)06-008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