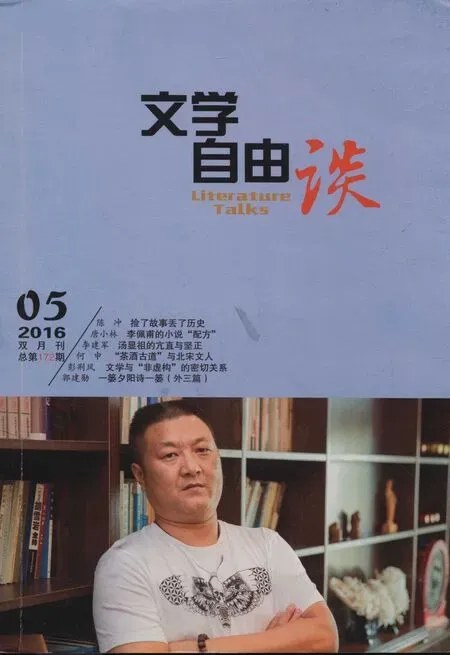王彬散文的“阔大”与“精微”
□王冰
王彬散文的“阔大”与“精微”
□王冰
一
在写作格局上,王彬的散文并不局限于对事物的精致描摹,更在于从一种精致细腻的触点出发,用一条理性的线索将它们聚拢成篇,最终走向广阔的思想和情感领域,从而将一种阔大在他的散文中泛射出来。
在《我对一种树的认知过程》中,我们见到的是一种独有的书写方式,而沉浸在这种方式中写作,必然带有一种无拘无束的力,这种力是宽泛而涌动的。作者从1987年“我从武汉去三峡,顺便去龟山盘桓”,写到1995年去庐山,在南昌青云浦,看到披垂着小提琴式的叶片的枸树,再写到北京“东三环的绿化带上,我又见到了这种树,青翠可爱,小提琴式的叶片,优雅地挽住行人的目光”,然后写到栾树、人行道上的白蜡树、东三环北路的椿树与槐树,以及各种的柳树。将跨越时空的诸多树木凝练成一体,心中没有大格局是断然不能的,其中的文字正是作者隐藏于内的宽广心性的折射,其疏宕袅娜处,自有一片烟波;清朗疏朴的文风,焕发出一种汪洋澹泊、深醇温粹的风格。
《三峡书简》也是这样:在龟山道上林木丛中有一种树,“叶片的形状仿佛是缩微的小提琴。苍暗的颜色缓缓沉坠,给我的印象颇深”,并由此突然想到了“北京秋季的一种树”:“我不知道该叫什么,躯干挺直粗糙,树冠狭长,叶脉硕大,叶缘深刻缺裂。那种火红的颜色,满山满谷都是。”后文又写到沿途列立的杨树、水杉与梧桐,还有一种“不高而丛生着密而厚的墨绿色的带有角质感的叶片”的一种不相识的树。特别是梧桐:“在距汉阳不远的地方,叶片都已枯萎,凝缩如拳团聚在灰褐色的树梢上。而靠近江陵一带的则明朗润泽,虽然已经失去了夏日的光彩,却黄得可爱。是那种贴近于红的黄,黄得热烈,黄得透彻,仿佛栖满了橙红的蝴蝶,真是美极了。”文脉看似散漫,却以一种情绪控制着文章的格局,显示出从容的把握能力,深厚而爽朗,充沛着一种浓郁的阳刚之气。
二
在为文的结构上,我们也可见到王彬散文在格局上的匠心独运,《顾太清》就是这样一篇作品。文章将时空互相连缀,让古今相互交融,将世俗和典雅相接,于是,这里便有了往昔岁月的那次大爆炸,有了破烂不堪的房子,有了倾圮已久的大门,有了霏云山房,以及霏云山房背后的清风阁,清风阁背后的黑色洞穴。作者写道,清代这位女词人顾太清不禁要叹息了:“一段残碑哀社稷,满山春草牧牛羊”,“笑指他年从葬处,白云堆里是吾乡”。如此,作者很巧妙地用诗句还原了顾太清的旅程,脚下的,心上的。
我们知道,古人为文讲“疏可走马,密不透风”。我觉得王彬的散文,文字是简约的,这应该也是“疏”的一种表现。如果这种“疏”运用得当,往往会生成一种内在的心力和文字的笔力。当然,对于一篇散文而言,它的“力”并非浮于表面上笔墨的轻重多少,而在于一种意境与心力的粗淡或细密,在文字的疏密之间,不断地将一种“力”传输给我们,并由此成就了他颇有力道的散文价值。在《蜈蚣脚上的札记》中,王彬并不追求一种文字的繁密,但其中的情感、思想还是在文字之间渗透出来。文中写到,余光中在聆听弗罗斯特朗诵《雪夜林边小驻》以后,“忽然悟出其中一种死亡的象征,而顿时感到鼻酸。希望他在安睡以前还有几百里,甚至于几千里的长途可以奔驰。”仅仅是这些话,就将往事在时间和空间的纵横轴中延宕开了。
《舒群先生在本溪》仍然写得很是简约,初读甚至有一种读个人简介似的感觉,但它依旧结实耐读。这是为什么?丹青难写是精神,因为精神才能“独留千秋纸上尘”,因为文中写出了那种孤独的精神和不屈的心境,确实如“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寂寞身后事,千秋万岁名”诗句中所写的那样啊!“漫天的大雪和弥漫的蒸汽渐渐吞没了一切,可是隐约中,我见舒群胡髭挂满白霜,还在频频地向我挥手。”舒群在这一刻——“胡髭挂满白霜”的一刻,将对战友安危的牵挂与万丈的革命豪情,“定格在本溪火车站挥手的刹那之间,同时也定格在本溪浩荡瑰丽的大湖与静谧安详的小湖,如诗的森林与坚硬的钢铁之间”,而由此写出了舒群先生的魂魄。整个文章是简约的,但其中的心情是密集的,不由得也让人跟着呼吸急促起来。
三
一般说来,中国文艺宜于会意。王彬散文的落脚点,常常是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各种事物相关,或者是以此为圆心的领域,但要到达的地方却是心性中的大境界,并使之产生在思想和文字上的升华。
作为一个散文家,或者是其他的艺术家,内心所属是很重要的,因为当他去观察万物时,就有了一个原点,也是一个基本点。同样的一件东西,会因为位置的不同、视角的不同而差别各异,对于四周景物的态度也会因为自己的品质、情趣、心志、情绪的不同,而千差万别。在新时期之初,许多作家在向内转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面对这些问题,他们对于人性、人情、人生、生命意识、生存状态等等都做了较为深入的反思,巴金老人在《随想录》中曾谈到:“总结几十年来的坎坷经历,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我才明白,我也应该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我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因此,向人性的深层次挺进,进而去发现符合人性的美,鞭挞那些与人性相背离的丑,应该是当前散文所必须坚守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王彬的散文有其独到的发现,真切的体验,以及从内心深处喷涌出的既细微又丰满、既幽深又鲜活的体验,这些都构成了他散文创作的推动力和走向。
他将自己的思索与周围万物的切合与会意,体现在与历史进行的对视中,他的《龚岭禅云》写了龚公山麓的宝华寺,一个马祖道一驻锡的地方。其中有些地方记述得很有禅趣,比如文中写道:道一邀请他的三位高足在月下漫步,询问他们在如此皎洁的月色之下宜做何事?智藏讲的是“焚香、讲经、供佛”,怀海答曰“参禅打坐的好时机”,而普愿一言不发,拂袖便走。对此,道一的评论是:“经入藏,禅归海,唯有南泉普愿独超物外。”王彬理解,智藏耽迷于对佛经的讲解,怀海执着于对禅的修行,只有普愿不迷执法相而超然物外,才能做到“即心即佛、非心非佛、平常心是佛。佛的精神存在一切法相之中,而又不在一切法相之中,只有心无挂碍,才能打破心执,进入真如之界”——难道这不也是作者的一种心界吗?他的《西门津渡》写出了自己对于西门渡口的一种敬重与缅怀的殷殷之情,在《走进尚书第》中,通过位于泰宁古城的尚书第,写出了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和关键的“礼”和“义”。作为有着“依光日月”与“曳履星辰”身份的李春烨,本应走在“礼”“义”为先的中国传统文化之路上的,但是“真实的历史是,这么一个曾居要津的人物,却不见《明史》,也不见于其时的《福建通志》、《邵武府志》和《泰宁县志》。为什么?因为他大德已亏,没有资格进入史家笔端,这些史籍没有把他列进奸佞传,已然算是宅心宽厚”;即使在三百多年以后,为了当地的旅游事业,李春烨却突然风光起来,但“那样整饬的院落,那样高峻的门墙,那样华丽的梁栋,那样精致的雕刻,而且还有那样美丽的花园”,依然在历史的戏台上是那么荒凉和野蛮。《状元故里风清》写了珪后村普济岩至今还供奉着三个人物——当地人尊为“三公”的文天祥、张世杰与陆秀夫。关于他们,那里也有一幅楹联,其文为“协力驱蕃激扬浩然正气,同心报国更见殷后三仁”。将这几篇连在一起看,足见王彬的褒贬之情了。还有《留余堂》一篇,仍然写得细腻而充满张力:“在留余堂,偌大的厅堂里只有一张简陋的方桌,中间放着一具明黄的香炉,两侧是白铁皮盒子。香炉里暗白的灰烬堆成坟尖形状,铁皮盒子里残留着没有燃尽的红色蜡烛。在供奉祖先的神龛左侧放着一只煤油灯。神龛位于两楹之间,仿佛一座小型舞台,黑色的神位涂着朱红的油漆。神龛之上是一支乳白的细长灯管,再上是纤细的浅蓝色电线,电线之上是一盏白炽灯。白炽灯的上面悬挂着留余堂的黑底金匾。神龛里面光线幽暗,难以辨认字迹。”文中写道,张资平的侄子张梅祥从未见过张资平,只见过他的照片,“然而对张的事情还是很清晰,毕竟是有血缘关系的。看到他,我突然想到历史上的邓攸,那样高古的衣冠,他的儿子与侄子。”在战争的挤压之下,历史上,中原的汉人,也就是客家的祖先,不断地向南迁徙,而每一次的迁徙都流播着凄惨骇人的故事。“西晋末年,一个叫邓攸的人,为了逃避石勒的胡兵,带领家小向南方逃亡。起初还有车马可以代步,后来形势紧张,为了跑得快些,邓攸放弃车子,让家小骑上牛马,不料又遇到强盗而将他们抢掠一空。邓攸的儿子和侄子年龄都小,没有了牛马,邓攸便把他们挑在肩上继续逃难。然而,形式紧迫,难以两全,逼迫邓攸做出抉择,必须舍弃一个孩子。邓攸和妻子商量,兄弟早已物故,只有侄子一个后裔。如果舍弃侄子,兄弟就没有后人了。这样的事情不能做。我们将来到了安居之地,还可以生养,扔掉儿子吧。妻子痛哭不已,依从了邓攸。翌日,趁儿子还在熟睡,抱着侄子就跑。没想到,傍晚的时候,儿子哭喊着追了上来。第三天,二人狠心将儿子绑在树上,头也不敢回地跑了。多年以后邓攸在江南安定下来,每忆及此,都如同刀剜一般。这当然只是中原汉人为逃避兵燹的苦难一幕,类于邓攸惨痛遭遇的人当不在少数,只是没有被记录下来而已。我不知别人读到这样的记载,内心会涌起何等波澜,在我是不忍卒读的。”这就令人不得不敬佩邓攸,为了兄弟之“义”而牺牲了自己的孩子。邓攸的做法属于手足之情的“小义”,在民族的“大义”面前,作为国人,尤其是卓有声望的人物,更应该如此吧!但是张资平的抉择却令人失望。抗战爆发后,张资平参加了以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为后台的“兴亚建国会”。1940年3月南京汪伪政府成立,张资平任农矿部技正;“技正”是技术官员,属于闲职,似可原谅。7月,“中日文化协会”在南京成立,张资平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候补理事,任出版组主任,主编《中日文化》月刊;这是一份宣传“中日亲善共荣”的汉奸杂志。“这就难以宽宥了,他怎么会跌进这样的酱缸?”“倭寇的残暴不是写在纸上而是每天发生在人们的身边,面对这样的残暴,难道可以无动于衷吗?”可以看到,面对国家与民族大义时,作者对于张资平的质问铿锵有力。
四
记得林非先生在其论著中,曾多次阐述了自己的理论见解,认为“散文是一种充满了主观色彩的文学体裁”。王彬的散文创作,侧重于表达内心的体验和抒发内心的情感,其散文对于客观的社会生活或自然图景的再现,也往往反射或融合于对主观感情的表现中间,渗透着作者的情感和思考。因此可以说,王彬散文的阔大还来源于其心灵的阔大。
清人刘大魁在《论文偶记》中谈到,“文贵大:丘壑中,必峰峦高大,波澜阔大,乃可谓之远大。古文之大者莫如史迁。震川论《史记》,谓为‘大手笔’,又曰:‘起头处来得勇猛。’又曰:‘连山断岭,峰头参差。’又曰:‘如画《长江万里图》。’又曰:‘如大塘上打纤,千船万船,不相妨碍。’此气脉洪大,丘壑远大之谓也。”其实,道理博大,不如气脉洪大,气脉洪大,不如丘壑远大,丘壑远大,不如胸怀之大。王彬的散文有一种明显的开阔度,这种开阔度是其视野开阔度的体现,是其心灵开阔度的体现。当一个作家的神气、意境、品藻、风格和内在的悟力,在其散文创作中得到展示并慢慢流溢出来的时候,自然会有一种强大的力量通过文字传达给我们,但这并不是刻意而为之。对此,王彬一直是努力于此的,所以他的散文才写得随意挥洒,有胸襟有气度。比如他在《大地的呼吸》中写道:“在大丰创意园,有三件展品引起我的注意。一件是电焊机,一件是塑料椅子,一件是骨瓷茶杯。”就是这些普通平常的物件,在作者的笔下却焕发了别样的光彩:“那两只茶杯。茶杯洁白,杯盖的顶部,也就是杯纽,是一只小鹿,两只杯子一对,一只是金色的,一只是银色的”,“而小鹿的姿态也的确讨人喜欢,四肢跪卧,安安静静地仿佛在谛听大地的呼吸,树枝一样的鹿角丰盛地伸展开来”。文章往后一点点地扩展开,写了南海子的麋鹿,俄罗斯作家普里什文笔下的梅花鹿,南苑这个清朝皇室的狩猎之处的麋鹿等等,纵深渐次展开。《袒露在金陵》在从容之间写出了作者自己的情趣:“燕子矶是个小镇。矶,就在小镇的边缘。虽然称为公园,却并无多少公园气息,也不收门票,在我看来,不过是郊野中的一片绿地而已。园内有几户住家和一家小吃店,我们进园的时候,仿佛煎炸着鹅黄的馓子”,“御碑立于矶顶,一方浅灰色的大理石,笨头笨脑地挤在一只四角微举的小亭子里。御碑雕镌的云龙蔓草已然漫汗,只有乾隆手书的‘燕子矶’依然凝重丰硕,填满了松绿颜色,现露出几分天子气象”。作者写得可谓不慌不忙,在行走之中写出了世间的变化与沧桑。《我对一种树的认知过程》写到了宫柳:“嫩中泛射一种金黄的光泽。一种比黄金还要柔软的光泽。哦,立柳的颜色原来是可以这样漂亮的。我当时的心悸动了一下。尤其美妙的是在接近午门城台的时候,立柳的色彩发生了微妙变化。不再是单纯的金黄,而是丰厚了许多,金黄之中搀杂了柘黄的色彩。”《宙斯的礼物》写到了泡桐总是有些夸张、粗俗感觉的花朵,“香而带有一种微腐的气息”。《冬天的树木》写到了静穆而高雅、尊贵而寂寞的冬天的水杉:“没有了叶子,咖啡色的树冠变得透明清爽起来,仿佛镂花的金字塔”,“在落日的映照下,所有的水杉都放射出绯色的光芒,又纤长又曼妙,努力而幸福着”。当然这些篇什在写作时并不太执着于文章开始的实物,而是讲求超脱会通,在收敛有余、小心翼翼之间任意挥洒,将散文的真精神一点点展示出来。王国维在论及诗词创作中的“有我”和“无我”论点时说,“有我”是指“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也就是说作者主观的感情,移到客观事物上,再由作者将这主客观形成的情感物,用统一的形象表现在作品之中。“无我”是指“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看来,王彬是深谙此道的,所以他的散文才写得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五代后梁画家荆浩云:笔有“四势”,曰“筋、肉、骨、气”。苏轼在《评韩柳诗》也谓:“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讲得也都是一个“大”字,强化神、逸、韵,以及深远无穷之味。王彬自然会揣摩再三,融汇于自己的创作中。古人谓:“神用象通。”又说:“思想为妙,神与物游。”有了这样的境界,才能写出天下万物的神髓,而只有拥有这样的境界,才会具有“大”格局,从而将“阔大”与“精微”结合一道。王彬的散文便是如此,物与理,情与辞相得益彰,俊朗、阔大、精微而感人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