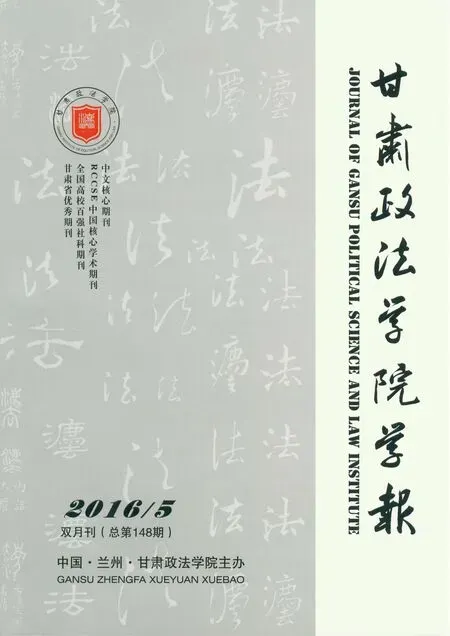评析《国际商事合同法律选择原则》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限制
张丝路
评析《国际商事合同法律选择原则》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限制
张丝路*
2015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通过的《国际商事合同法律选择原则》以最大化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其目的。然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最大化实有赖于立法对其最合理或者最低程度的限制。以此为视角,评析上述原则对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在选法范围以及效力上限制的规定,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上述原则规定合理和进步以及仍存在的缺陷的地方,从而能够为我国在未来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立法上的完善提供借鉴。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国际商事合同法律选择原则》;当事人意思自治
2015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通过的《国际商事合同法律选择原则》(以下简称《法律选择原则》)*《国际商事合同法律选择原则》中文版本参见:https://assets.hcch.net/upload/text40cn.pdf.尽管只具有示范法的效力,*《国际商事合同法律选择原则》序言第2款,“本原则可当作国家、区域、跨国家或国际文书的范本使用。”但仍然代表了国际商事合同领域法律选择规则的最新发展趋势。在这一领域中,国际上普遍接受的法律选择规则是当事人意思自治,*需要指出的是,仍有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不认可当事人意思自治,详参:Maria M.Albornoz.Choice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Contracts in Latin American Legal Systems[J].J. PRIV. INT'L.,2010(6):23.即在具有涉外因素的合同中,当事人可以通过他们之间的法律选择合意选择适用于他们之间合同的法律。*Symeon C. Symeonides.Codifying Choice of Law Around the World: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Analysis[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111.不难看出,当事人意思自治实际是一种授权规则,因而尽管《法律选择原则》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最大化当事人意思自治,*Permanent Bureau of the Hague Conferenc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Choice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 Hague Principles?[J].Unif.L.Rev.,2010(15):885.但从立法规定的角度,最大化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实现,实际上需要从如何最合理或者说最低程度地限制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出发。因此,本文试图结合《法律选择原则》的条款以及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对该原则的官方评述,*Permanent Bureau of Hague Conferenc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Draft Commentary On The Draft Hague Principles On Choice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Contrats[R].Hague:2013.选取《法律选择原则》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在选法范围以及效力方面的限制进行评析。之所以仅限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在于,首先,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在选法范围以及效力方面的限制不仅包括了国际商事合同法律选择领域一些一直存在的国际私法问题,也包含了这一领域新出现的一些国际私法问题,因此对《法律选择原则》在这两方面规定的分析具有理论上的意义。其次,由于我国2011年开始实施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及最高院2013年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 以下简称《司法解释一》)在上述两方面的规定上仍有不明确或者不全面的地方,因而对《法律选择原则》规定的分析能为我国在将来进一步完善《法律适用法》提供立法上的借鉴。
一、对当事人意思自治选法范围的限制
对于当事人意思自治选法范围的限制,国际私法规则主要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所选择的法律是否需要与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具有一定的联系;其次,所选择的法律仅限于实体规则还是可以包括国际私法规则;再次,所选择的法律必须是某个国家的国内法还是可以包括非由国家制定的法律规则(Rules of law),比如国际条约、国际习惯( 国际惯例) 以及各国法律所公认的一般法律原则。*刘仁山.国际合同法律适用中意思自治原则的晚近发展-《海牙国际合同法律选择原则》述评[J].环球法律评论,2013 (6 ):149。《法律选择原则》对前两个问题完全交由当事人决定。*参见《国际商事合同法律选择原则》第2条,第4款,“不要求所选择的法律与当事人或其交易之间有关联。”以及第8条,“法律选择不涉及当事人所选择法律的国际私法规则,除非当事人另有明确规定。”因而,《法律选择原则》对当事人意思自治选法范围的限制主要体现于第三个问题。一般来说,当事人只能将上述法律规则通过并入(incorporation)的方式转化为当事人之间合同条款的一部分,而不能够将之作为当事人之间合同的准据法。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国际经济交往的日益扩大,在国际商事仲裁中,一些法律规则也逐渐成为了当事人所选择的合同准据法,比如,国际商会制定的示范法、国际统一私法会议制定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定的示范法以及一些广为接受的国际公约,如《联合国国际销售合同公约》等。因而,在诉讼程序中,法律规则能否成为当事人所选择的合同准据法,成为了《法律选择原则》起草过程中争议较大的问题。《法律选择原则》起草工作组在提交给特别委员会审议的最终稿中,*2009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总务和政策事项理事会 (Council on General Affairs and Policy of the Hague Conference,简称理事会)邀请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常设局( Permanent Bureau of the Hague Conferenc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简称常设局),成立《国际商事合同法律选择原则》起草工作组。起草工作组于2012 年向理事会为审议该原则而设立的由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成员国政府专家(governmental experts)组成的特别委员会(Special Commission)提交关于《国际商事合同法律选择原则》的最终草案。特别委会审议后,提交给理事会依据前述最终草案为蓝本而修改后的《国际商事合同法律选择原则》最终案文。关于《国际商事合同法律选择原则》更为详尽的起草过程,参见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官方网站:https://www.hcch.net/en/instruments/contracts-preparatory-work.并没有对法律规则作为当事人之间合同的准据法设定任何限制。*Hague Principles on Choice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 (final draft adopted by the Working Group in June 2011) article 2, “A contract is governed by the law chosen by the parties. In these Principles a reference to law includes rules of law.” Available at: Choice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contracts: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draft instrument and future planning, Prel. Doc. No 4 of January 2012.然而,一些专家在特别委员会上指出,这种不加限制可能会导致具有更强议价能力的一方所制定的不公平的法律规则得到广泛适用。另外一些专家也担心,如果不加限制,考虑到法律规则的广泛性,这会导致法律适用问题过于复杂以及随之而来的诉讼程序过于冗长。但是,另外,一些专家指出,既然《法律选择原则》的根本目的是最大化当事人意思自治,那么对于当事人所选择的准据法的范围就不应该加以限制。而对于不公平的法律规则可能会被适用的问题,完全可以交由法院地的强制性规则或者公共政策解决。*Marta Pertegds,Brooke Adele Marshal.Party Autonomy And Its Limits: Convergence Through The New Hague Principles On Choice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J].Brook.J.Int'l L.,2014(39):997.特别委员会最终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妥协,在允许当事人选择法律规则的同时,也对法律规则本身进行了限制,从而形成了现在的《法律选择原则》第3条,即“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可以是国际、跨国家或区域范围内作为一套中性、平衡规则被普遍接受的法律规则,除非诉讼地法律另有规定。”显然,对法律规则本身的限制也就限制了当事人意思自治选法的范围。因此,以下围绕《法律选择原则》对法律规则本身的限制来分析该原则对当事人意思自治选法范围的限制。
依据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对《法律选择原则》的官方评述,第3条对法律规则的限制可以分为来源与性质两个方面。就来源而言,可以被选择为准据法的法律规则必须在国际、跨国家或区域范围内被普遍接受。官方评述指出了三种符合这一要求的法律规则,即《联合国国际销售合同公约》、《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以及《欧洲合同法原则》,并指出符合这一标准的法律规则会逐渐增多,因而上述三个例子并不是穷尽的。*同前引〔6〕,第9-11页。然而,上述限制存在的问题在于,其并没有说明接受的主体以及如何认定普遍接受。就接受主体而言,从官方评述给出的三个例子来看,普遍接受这些规则的主体显然是不同的。此外,考虑到上述三个例子并不是穷尽的,因而可以认为《法律选择原则》并没有明确说明普遍接受的主体。就接受程度而言,如果认为普遍接受是指作为准据法而被普遍接受,由于目前允许当事人选择《法律选择原则》所提及的法律规则作为准据法的国家远没有达到普遍接受通常意思所要求的程度,*同前引〔4〕,第143页。因而在此种情况下任何法律规则显然都不能达到该原则所设定的要求。此外,从法律规则的对立面来看,国家法律显然不一定能在国际、跨国家或区域范围内被普遍接受,因而为何当事人选择法律规则作为准据法时必须施加在上述范围内普遍接受这一限制,官方评述也没有加以说明。
从性质方面的限制来看,官方评述指出,法律规则必须具有“一套规则”(set of rules)、“中立”(neutrality)以及“平衡”(balanced)的特性。就一套规则的要求而言,官方评述指出该特性并不意味着规则的全面性,而只是要求所选择的法律规则必须在国际背景下能够解决一般的合同问题。*同前引〔6〕,第19页。《法律选择原则》的对法律规则性质的这一要求没有必要。原因在于,首先,法律规则通常只规定某种特定类型的合同或者仅规定合同问题的某些方面,因此法律规则通常不是一套规则。*Ralf Michaels.Non-State Law in the Hague Principles on Choice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M]// K.Purnhagen,P.Rott.Varieties of European Economic Law and Regulation. Switzerland: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4:60.即便是官方评述本身,也提醒当事人在选择法律规则作为准据法时需要注意填补法律规则所不调整的事项所遗留的空白。*同前引〔6〕,第19页。其次,考虑到《法律选择原则》允许当事人针对合同的不同部分选择不同的准据法,*参见《国际商事合同法律选择原则》第2条第2款,“当事人可选择:(a) 适用于合同全部或仅适用于合同一部分的法律;和(b) 针对合同不同部分的不同法律。”因而即便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规则不是成套的而仅仅是个别规则,也可以通过再针对另外的部分选定一个准据法的方式来解决。因此,《法律选择原则》对法律规则必须是一套规则的要求没有必要。中立的特性要求法律规则源于被公认的中立以及公正地代表了不同法律、经济以及政治观点的机构。*同前引〔6〕,第19页。从官方评述对中立这一特性的阐述来看,实际上是对法律规则来源而不是性质方面的要求。考虑到《法律选择原则》以及官方评述都没有对普遍接受的主体以及程度进行进一步的说明,对中立这一措辞更为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对法律规则来源要求中未能明确的问题的进一步阐释,即代表了不同法律、经济以及政治观点的机构所制定的法律规则通常是国际、跨国家或区域范围内的,而由于其广泛的代表性,这些机构制定的法律规制一方面可以被认为是中立的,另一方面也表明这些机构的成员国普遍接受这些法律规则。平衡的特性主要是为了防止所选择的法律规则只利于合同的一方。*同前引〔6〕,第19页。这一对法律规则性质的要求同样没有存在的必要。原因在于,首先,《法律选择原则》排除了对消费者合同以及雇佣合同这两类在判断是否只有利于一方明显具有倾向性的合同,*参见《国际商事合同法律选择原则》第1条第1款,“本原则适用于每一当事人进行其行业或职业事务就国际合同作出的法律选择。本原则不适用于消费者或雇用合同。”因此对于原则所适用的国际商事合同,如何判断只有利于合同一方,明显缺乏一个可以适用的标准。其次,即便当事人之间选择了只有利于一方的法律规则,各国法院通常可以通过其他国际私法规则,比如强制性规定或者公共政策来排除准据法的适用。因此,对法律规则本身平衡性的限制是没有必要的。
不难看出,《法律选择原则》的上述规定从一定意义上讲,仅仅反映了将法律规则纳入到当事人可选择的合同准据法的范围内的立法意图,并没有根据国际商事仲裁或者诉讼的实际需要设定一个切实可行的规则。国际商事仲裁通常是当事人合意的体现,因而只要当事人之间达成合意,适用法律规则作为他们之间合同的准据法,《法律选择原则》的上述限制反而是不必要的。*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广为接受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制订的《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就没有对商事仲裁中合同准据法的范围做出限制,该示范法第28条第1款规定,“仲裁庭应当依照当事人选择的适用于争议实体的法律规则对争议作出决定……。”但对于诉讼程序而言,由于《法律选择原则》的规定既有不必要的地方也有不明确的地方,因而使得法院在诉讼程序中很难准确地确定符合该原则要求的法律规则。因而,《法律选择原则》对法律规则的限制对于国际商事仲裁来讲太窄,对于诉讼而言又不太精确,仅仅反映了原则起草者将法律规则纳入到当事人可选择的准据法的范围内的意图。
二、对当事人意思自治效力的间接限制
当事人意思自治在具有涉外因素的合同中体现为合同中的法律选择条款或者单独订立的法律选择协议,尽管有学者指出此种条款或者协议不具有合同的性质,*沈涓.法律选择协议效力的法律适用辩释.法学研究,2015(6)。但不可否认的是此种条款或者协议体现了当事人选择准据法的共同意图,即法律选择合意。*为表述方便,以下将法律选择条款或者单独订立的法律选择协议统称为法律选择合意。因而,在依据该合意确定合同准据法之前,首先需要确定该合意是否成立以及是否有效。因而,对当事人法律选择合意的成立以及效力的认定间接地限制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效力。
《法律选择原则》对法律选择合意的成立以及效力的认定做出了3条规定,首先,《法律选择原则》第7条确立了法律选择合意与其所适用的合同(主合同)在效力上的可分离性。*参见《国际商事合同法律选择原则》第7条,“不能仅以某项法律选择所适用合同无效为由就该项法律选择提出异议。”体现为法律选择协议形式的法律选择合意当然与主合同之间不存在成立或者效力上的牵连关系,应依据《法律选择原则》针对法律选择合意所设定的专门规则来判断该协议是否成立或者有效。而对于体现为合同中法律选择条款的法律选择合意,《法律选择原则》同样规定其效力也应独立于主合同,除非影响主合同效力的事由同样适用于该法律选择条款,反之,主合同的效力却取决于该法律选择条款所确定的准据法,但如果合同双方对主合同的成立存在争议,则首先需要依据《法律选择原则》为法律选择合意所设定的特别规则来确定法律选择条款是否成立,进而依据该条款确定的准据法来判断主合同成立与否。*同前引〔6〕,第32页。确立主合同中的法律选择条款的可分离性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确立法律选择条款的可分离性源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尽管法律选择条款仍属于合同当事人之间合意的一部分,但其与当事人之间就合同中其他问题所达成的合意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内容是为当事人之间的合同争议指定准据法而非直接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特殊性使得将其从主合同中分离出来一方面不会直接影响到当事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另一方面也能够避免由于当事人之间对主合同成立或者效力的争议影响包含在主合同中的法律选择条款的成立或者效力进而导致合同准据法无法确定问题。其次,法律选择条款与仲裁条款以及排他性法院选择条款性质上的一致性,也是确立法律选择条款可分离性的重要原因。仲裁条款的可分离性在国际私法中已经被广为接受,排他性法院选择条款的可分离性也在2005年《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中得到确认。*参见《海牙法院选择协议公约》第3条第4款,“构成合同一部分的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应被视为独立于合同其他条款的一项协议。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的有效性不能仅因合同无效而受影响。”中文版参见:https://assets.hcch.net/upload/text37cn.pdf.而上述条款同法律选择条款一样,都是为了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而非直接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而从这种相同性质的角度,法律选择条款的可分离性也应该得到确认。
第二,对法律选择合意的形式,《法律选择原则》第5条规定,“法律选择不受任何形式要求的限制,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从立法趋势而言,除消费合同或者雇佣合同等涉及到弱者保护需要对法律选择合意的形式进行严格规定的合同外,各国通常如原则这样,通过一个实体规则而非国际私法规则来决定法律选择合意的形式。*Symeon C. Symeonides.Codifying Choice of Law Around the World: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Analysis[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111.更进一步来说,原则之所以不对法律选择合意的形式做出规定,主要是由于各国关于法律选择合意形式的要求,除了上述特殊类型的合同外,并不存在涉及各国根本利益上的冲突,因而为了最大化当事人意思自治,防止当事人法律选择合意由于形式上的瑕疵而落空,也不应对法律选择合意的形式做出限制性的规定。
第三,对于当事人是否同意法律选择合意,*为了避免在其他国际私法立法中对法律选择合意的成立或者效力(existence and material validity)范围上理解的差异,《国际商事合同法律选择原则》将除了法律选择合意形式外所有可能影响到当事人是否做出有效的法律选择的问题交由第6条解决,因而笔者在此同样使用《法律选择原则》中同意这一措辞,不仅指代当事人对法律选择合意是否成立的争议,也指代当事人对法律选择合意是否有效的争议。原则第6条第1款区分当事人通过格式条款(standard terms)指定了不同准据法的情况以及除此以外的其他情况分别做出规定,第6条第2款规定了针对上述两种情况的例外。
对于非经由格式条款所形成的法律选择合意,原则规定,“当事人是否同意某项法律选择,依声称所约定的法律确定。”原则在第6条第2款规定了例外的情况,即“根据第1 款中指明的法律无法合理确定一当事人是否同意某项法律选择的,依该当事人营业所(establishment)所在国的法律作此确定。”*依据《国际商事合同法律选择原则》官方评述,营业所(establishment)是指:“For the sake of legal certainty, Article 12 uses the term “establishment” rather than “place of business”. The Principles do not provide a definition of establishment, but, in broad terms, an establishment means a business location in which the party has more than a fleeting presence. It encompasses a centre of administration or management, headquarters, principal and secondary places of business, a branch, an agency and any other constant and continuous business location. The physical presence of the party, with a minimum degree of economic organisation and permanence in time, is required to constitute an establishment. Hence, the statutory seat of a company without more does not fall within the notion of establishment. Similarly, a party that has its main establishment in State X and directs its business activities to State Y solely via the Internet is not deemed to have an establishment in State Y.”原则之所以采用一般原则加例外的方法判断当事人是否同意法律选择合意,主要是由于,尽管从理论上讲,对于当事人是否同意法律选择合意,可以通过当事人所选择的准据法、法院地法、依法院地国际私法规则所确定的准据法或当事人的属人法来进行判断,但上述任何一种单一的方法都存在自身的缺陷。通过法院地国际私法规则所确定的准据法进行判断,这种方法的弊端在于,如果当事人之间对法律选择合意的成立不存在争议,那么这种方法过于轻易地无视了当事人之间成立的效力具有争议的法律选择合意,过于扩大了法院的裁量权。如果当事人之间对法律选择合意的成立存在争议,此种情况相当于当事人之间未做出法律选择,而各国在此种情况下所采用的确定准据法的方法各不相同,这种方法必然会导致判断依据不具有可预见性。而以当事人所选择的准据法作为判断依据最大的好处在于判断依据的确定性以及最大程度上尊重了当事人意思自治,但从逻辑上讲,不能倒果为因地用法律选择合意所确定的结果来决定当事人是否同意法律选择合意。而以法院地法进行判断当然能够避免上述逻辑上的瑕疵,并且从体系一致性的角度,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权利来源于法院地的国际私法规则,那么通过法院地法判断当事人是否同意法律选择合意也是应有之义。*同前引〔22〕。但此种方法的问题在于,如果合同中不存在排他性的法院选择条款,考虑到原告挑选法院的问题,从一定程度上讲,此种方法剥夺了被告否定对其不利的法律选择合意的可能性。即便合同中存在排他性的法院选择条款,在当事人选择中立法院的情况下,由于合同双方对法院地规则都不熟悉,从行为结果的可预见性来讲,这种方法实际将法律选择合意置于不确定性的状态下。而当双方选择某一方所在地的法院时,则同样会存在对另一方不利的情况。而以当事人属人法作为判断依据的主要优势在于行为结果的可预见性,显而易见的是对于依据属人法所为的行为当事人对结果一定具有最大程度的预见性,特别是对于单方行为或者默示是否能达成法律选择合意的问题。然而此种问题所导致的必然问题是,如果仅适用一方的属人法,必然会对造成对另一方的不公正,而如果考虑所有合同当事人的属人法,这必然会导致法律适用问题的复杂以及诉讼程序的冗长。因而,在上述任何一种方法都不能妥善地单独地解决当事人之间是否同意法律选择合意的前提下,原则所采用的一般原则加例外的方法,尽管从理论上讲仍有缺陷,但从实践上讲不失为一种可取的方法。
对于合同当事人通过使用指定了不同准据法的格式条款来缔结双方之间的合同所产生的形式之争,*在合同当事人只有一方使用的格式条款规定了准据法或格式条款规定的准据法是一样的情况下,当事人之间对于是否同意法律选择合意的争议通过第6条第1款解决。而对于合同当事人使用的格式条款都没有规定准据法的情况,《国际商事合同法律选择原则》没有做出规定。《法律选择原则》第6条第1款b项设定了一个全新的规则,即通过考察合同当事方所使用的格式条款所指定的准据法对于形式之争的规定来确定应适用何种法律解决当事人之间的这种争议。官方评述给出了如下例子,合同a方通过格式合同提出要约,指定X国为准据法国,而合同b方接受要约,但通过其提供的格式合同指定Y国为准据法国,此时依据《法律选择原则》的规定,首先需要确定X国以及Y国对形式之争的规定,如果规定是一致的,那么则适用这种规定来解决形式之争,如果不一致或者没有规定则视为不存在法律选择,由于原则没有对此种情况进行规定,因而需要适用法院地的国际私法规则来决定合同的准据法,再依据该法的规定来解决形式之争。*同前引〔6〕,第29页。需要指出的是,该规则同样要受到第6条第2款的约束。官方评述认为此种方法能够提高法律确定性,在最大化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同时避免确定准据法所不必要的复杂性。*同前引〔6〕,第27页。但从官方解释所给出的例子来看,由于这种方法需要法院考察多国的实体规则,从而不可避免的复杂化了法律适用问题。并且各国的实体规则不一定如官方评述所设想的简单而直接,因而这种复杂化进一步降低了法律确定性,因而原则所设计的这一规则仅仅最大化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即凡是为当事人规定的准据法都需要考虑进去。
综上,原则对认定当事人之间法律选择合意是否成立或者是否有效的规定,在法律选择合意效力与主合同可分离性以及不限制法律选择合意的形式方面有其进步以及合理的地方,但在当事人之间是否同意法律选择合意的判断方法以及形式之争的解决途径上也有其理论上存在问题以及实践中不便于操作的地方。
三、对当事人意思自治效力的直接限制
对当事人意思自治效力的直接限制体现为对当事人所选定的准据法在适用过程中的部分或者全部排除,国际私法规则一般通过强制性规则或者公共政策来实现这种限制。而对于这种限制,国际私法规则需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受诉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考虑哪些国家的强制性规制或者公共政策;第二,如何认定强制性规则或者公共政策;第三,应由何种法律来填补准据法被部分或者全部排除后所遗留的空白。《法律选择原则》对上述问题的规定体现于第11条,由于该原则不调整消费者或雇用合同,因而,该原则对强制性规则的规定仅限于绝对优先强制性规则(overriding mandatory provisions)。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针对绝对优先强制性规则,除了法院地的绝对优先强制性规则外,《法律选择原则》第11条第2款规定,“诉讼地法律决定法院何时可以或者必须适用或者考虑到另一法律的绝对优先强制性规定。”就公共政策而言,除法院地公共政策外,《法律选择原则》第11条第4款规定,“一国法律将在没有作出法律选择的情况下适用的,由诉讼地法律决定法院何时可以或者必须适用或者考虑到该国的公共政策。”《法律选择原则》对能够适用绝对优先强制性规则的第三国范围的扩张从理论上讲不具有合理性,而对能够适用公共政策的国家范围的扩张会给受诉法院在适用上带来困难。此外,上述扩张也与《法律选择原则》本身的目的存在冲突。对于绝对优先强制性规则而言,目前的国际私法规则通常对除了法院地以及准据法国外的能够适用绝对优先强制性规则的第三国的范围限于合同履行地或者与合同存在密切联系的国家。*同前引〔4〕,第159页。这主要是由于第三国绝对优先强制性规则优先适用是为防止在去除了当事人所选择的合同准据法与合同之间关联性的要求后,当事人通过意思自治规避本应适用的第三国法律。*Adeline Chong.Public Policp and Mandatorv Rules of Third Countries In International Contracts.J.Priv.Int'l L.,2006(2):31.因而,第三国的范围必须受到其适用理由的限制,只有与合同具有某种联系的第三国的绝对优先强制性规则才能够适用。因此,《法律选择原则》不加限制的扩张不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此外,尽管绝对优先强制性规则能够提供公共政策所不具有的确定性以及可预见性,*Erin A. O'Hara,Larry E. Ribstein.From Politics to Efficiency in Choice of Law. U.CHI.L.REV.,2000(67): 1194-1196.但其仍然限制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因而《法律选择原则》这种不加限制的扩张与其基本目的存在矛盾。而对于公共政策而言,官方评述没有说明将能够适用公共政策的国家范围扩张到当事人没有做出法律选择时,依据法院地国际私法规则所确定的合同准据法国的原因。从国际私法的通常实践来看,除美国外,其他国家通常仅仅将能够适用公共政策的国家的范围限制在法院地国。*同前引〔4〕,第160页。这主要是由于公共政策概念本身的模糊性,法院在认定上存在巨大的困难,因而通常仅仅允许法院地国的公共政策得以适用。而从美国司法实践来看,法院在认定公共政策上的困难不会随着能够适用的国家的增多而减少。*Symeon C. Symeonides.United States of America[M]// Bea Verschraege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for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Suppl.44.Hague: Wolters Kluwer Law & Business,2015:233.因此,《法律选择原则》对能适用公共政策的国家范围的扩展会给法院地在适用上带来困难,并且从最大化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角度,原则的这种规定同样显得自相矛盾。
对于第二个问题,就法院地法律而言,所谓强制性规则是指不允许当事人通过合同或者其他方式背离的条款,所谓绝对优先规则是指,即便当事人所选择的准据法不是法院地法,受诉法院也必须适用的调整他们之间的合同关系的规则,绝对优先强制规则应被限制在对保护法院地公共利益有重要意义的条款。*同前引〔6〕,第46页。而对于第三国绝对优先强制性规则而言,官方评述指出,应由法院地法律决定某一特定条款是否能够具有绝对优先强制性以及在具体案件中,考虑到该规则的措辞及其他条件,该规则是否实际具有绝对优先强制适用的效果。*同前引〔6〕,第46页。依据官方评述,法院地的公共政策的适用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该政策必须足够重要,使得其在案件中的适用是合理的。官方评述指出,此种公共政策的重要程度必须足以使其适用到具有涉外因素且当事人能够选择准据法并实际上选择了法院地法以外的法律作为准据法的合同;第二,当事人所选择的准据法必须明显与法院地的公共政策不一致。官方评述指出,任何关于适用当事人选择的准据法与法院地公共政策是否不一致的争议,都应以适用准据法为出发点来解决。第三,这种明显不一致必须源于准据法在具体案件中的适用,而非抽象地评估当事人所选择的准据法是否与法院地公共政策不一致。*同前引〔6〕,第48-49页。而对于法院地以外的第三国的公共政策,官方评论指出,除非法院地法律有特别限制,其适用应同样符合上述三个条件。*同前引〔6〕,第50页。不难看出,为了最大化当事人意思自治,最大程度上适用当事人所选择的准据法,《法律选择原则》将绝对优先强制性规则以及公共政策限制在了非常狭小的范围。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法律选择原则》将绝对优先强制性规则的认定以及公共政策的适用完全交由受诉法院裁量或者法院地法律决定,再考虑到上述法院地国在能够适用绝对优先强制性规则以及公共政策的第三国范围上的裁量权,原则的规定实际过于扩大了受诉法院的裁量权,这必然会导致法律适用结果的不确定性以及不可预见性,因而这种规定实际上与原则的初衷存在矛盾。
就第三个问题而言,由于《法律选择原则》试图在最大程度上适用当事人选择的准据法,因而官方评述指出,当事人选择的准据法只在公共政策以及绝对优先强制性规则的效力范围内不适用。对于此范围之外的问题,仍需要通过当事人所选择的准据法来解决。*同前引〔6〕,第45页。还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原则允许当事人就合同的不同部分适用不同的准据法,官方评述特别说明,这仅仅允许当事人分割合同的不同部分适用不同的准据法,而不允许当事人分割准据法选择适用其中的一部分。*同前引〔6〕,第46页。
综上,《法律选择原则》对绝对优先强制性规则以及公共政策的规定,一方面过于扩大了能够适用绝对优先强制性规则以及公共政策的第三国的范围,另一方面赋予了受诉法院过多的自由裁量权,这两方面都不利于法律适用结果确定性以及可预见性的实现,这显然与《法律选择原则》自身促进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根本目的存在矛盾。
四、对我国立法的借鉴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法律选择原则》对国际商事合同领域一些新出现的国际私法问题,比如非由国家制定的法律规则能否作为合同准据法、当事人通过格式条款缔结合同所产生的形式之争,以及该领域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国际私法问题,比如如何认定法律选择合意的成立或者效力,强制性规则或者公共政策对准据法的限制问题,围绕着如何最低程度地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做出了相关规定,这些规定有合理以及进步的地方,同样也有理论上存在缺陷或者实践中不便于操作的地方。而由于我国《法律适用法》同样将具有涉外因素的合同的法律选择规则确定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参见《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因而,吸纳《法律选择原则》规定合理的方面,避免该原则规定存在缺陷的地方,能够对我国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立法上的完善提供借鉴。具体而言,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可以考虑扩张能够作为国际商事仲裁中合同准据法的法律规则的范围。最高院2013年颁布的《司法解释一》第9条已经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非由国家制定的法律规则的一种,国际公约,作为合同准据法*参见《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9条:“当事人在合同中援引尚未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效的国际条约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该国际条约的内容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除外。”。但同《法律选择原则》一样,该条对于国际商事仲裁来讲,对合同准据法的限制同样过窄。因而,可以考虑在立法上扩张在国际商事仲裁中能作为合同准据法的法律规则的范围。
其次,可以借鉴《法律选择原则》的规定,对如何认定当事人法律选择合意做出规定。我国《法律适用法》以及《司法解释一》都没有对如何认定法律选择合意是否成立或者是否有效做出规定,从体系完整性的角度,不得不说这是立法上的一个缺陷。而从《法律选择原则》的立法经验来看,可以借鉴该原则对法律选择合意与主合同效力的可分离性、对形式不做要求以及采用一般原则加例外的方式确定当事人是否同意法律选择合意。至于采用何种方法作为一般原则或者例外,考虑到《法律选择原则》的规定有其理论上存在问题的地方,更为合理的方法应是以法院地法为一般原则、以当事人属人法为例外。原因在于,首先,以法院地法为一般原则不仅避免了适用当事人所选择的准据法作为判断依据所存在的理论问题,而且这种方法在理论上是自洽的;其次,由一方当事人援用其属人法作为例外,不仅能够避免将该方法作为一般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也能纠正适用法院地法可能导致的对一方不利以及行为结果不确定性问题。而对于形式之争,由于其仍属于当事人是否同意法律选择合意的一种情况,考虑到《法律选择原则》所确立方法在适用上的复杂性,在没有针对这一问题形成一个理论上合理、实践中适当的方法之前,更为可取的办法应是仍然适用当事人是否同意法律选择合意的一般规则对之进行规制。
再次,如果需要对第三国强制规则或者公共政策的适用做出立法,需对第三国的范围做出合理限制。我国《法律适用法》以及《司法解释一》都没有对第三国强制性规则或者公共政策能否适用做出明确的规定。是否需要对此问题进行立法规定不属于本文探讨的范围。仅从《法律选择原则》的立法经验来看,如果本着最大化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目的以及实现法律适用结果确定性以及可预见性,如果对第三国强制规则或者公共政策的适用做出立法规定,对能够适用强制性规则或者公共政策的第三国的范围也应做出合理的限制,而不是全然交由法院地裁量。
张丝路,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