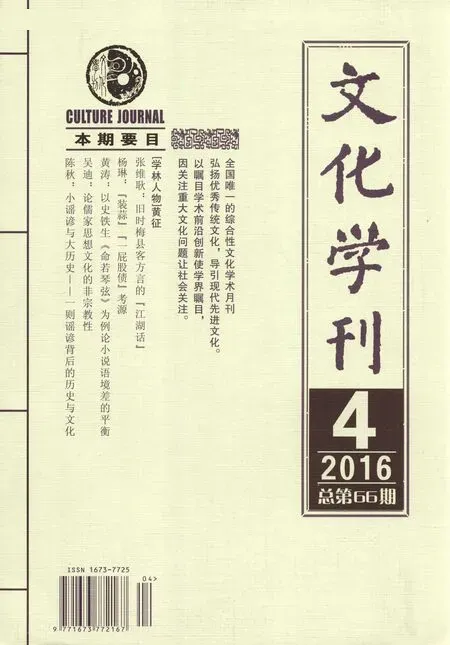重读《杨贵妃入道之年》
王伏牛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100081)
【文史论苑】
重读《杨贵妃入道之年》
王伏牛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100081)
20世纪40年代,陈寅恪、陈垣二位先生分别考证认为杨妃入道之年应在开元二十九年(741)正月二日。南北二陈,遥相呼应,成就学林嘉话。学界曾视陈垣先生文为考据典范。但细检其文,对朱彝尊结论的批驳尚不充分,个别地方亦存在不足之处。
杨妃;入道之年;武断性
一、陈垣先生思路及考证方法
陈垣先生《杨贵妃入道之年》一文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杨妃入道应在开元二十九年(741)正月二日;杨妃入道时当已不是处子。[1]后者仅为前一问题论述时的副产品。下面笔者结合陈先生所提著名的“校书四法”来检视其考证过程。
陈垣先生的考证,依杨氏受册为寿王妃、武惠妃薨、杨氏被取于寿邸、杨妃入道、杨氏受册为贵妃这一时间链条逐步展开,并尤为注意杨氏被取于寿邸、入道、受册的时间间隔。清代一些学者就此问题已展开考证,其中章学诚的结论未获看重,朱彝尊的看法则允称公认。[2]故此,批驳朱彝尊的观点也是陈文的另一主线。
陈先生文采用先破后立的方法,首先针对朱氏结论的根基予以破解。朱氏依新旧两《唐书》《杨妃传》中武惠妃薨于开元二十四年(736)的材料,考证出杨妃入道在开元二十五年(737)正月二日。对此,陈先生以《旧唐书·玄宗纪》《新唐书·玄宗纪》《资治通鉴·玄宗纪》《唐会要·皇后门略》《旧唐书·惠妃传》和《旧唐书·寿王传》等大量史料证明武惠妃薨于开元二十五年。此处,陈先生综合运用了对较法、本较法、他较法等考据方法,并指出朱氏之失在于对史料整体把握缺失,即“知传而不知纪,知此传而不知彼传”。
针对武惠妃之死的时间问题,在陈垣先生所据史料基础上,陈寅恪先生另列一条证据,即玄宗杀三子事。该事件发生于开元二十五年四月十三日,而此事恰是武惠妃的死因。从而为武惠妃死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又提出一条力证。针对朱氏另一条依据,即依照《开元礼》亲王纳妃的规定得出杨氏未入寿王府的结论,陈先生在《开元礼》不可得的情况下,从《通典》中掘出《开元礼》的副本,依据理教法指出杨氏在受册之后很可能被接进寿王府,并指出“且果未归寿邸,则太后忌辰与未婚之妃何涉”,从而推翻朱氏结论。同时,对于章学诚“杨妃当在天宝四年(745)入道”的说法,陈先生以为其全无理由可据,失在认为杨氏入道、入宫与受册为贵妃在同一年。此可谓破的方面,当然破中有立,如对朱氏考得杨妃当在正月二日入道的结论陈先生非常欣赏,并引为自己结论的一部分。
破后当立。陈先生在唯有《新唐书》中记载杨氏入道在开元二十八年(740)的情况下,找出《新唐书》该条所依据的《杨太真外传》的记载,并认定《外传》当言有所据,同时结合朱氏的成果,推出杨妃入道在开元二十九年(741)正月二日的结论。这里可以将之看作他较法的应用。
二、对朱彝尊文章的再解读及陈先生的缺失
笔者认为,陈垣、陈寅恪先生对朱氏文章的解读尚存在不完备之处,需进一步分析。为方便起见,现将朱氏文章相关部分录文于下:
《曝书亭集》卷五五《书杨太真外传后》云:太真外传,宋乐史所撰。称妃以开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归于寿邸。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温泉宫,使高力士取于寿邸,度为女道士,住内太真宫。此传闻之谬也。按《唐大诏令集》载: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遣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李林甫,副以黄门侍郎陈希烈,册河南府士曹参军杨玄敫长女为寿王妃。考之《开元礼》,皇太子纳妃,将行纳采,皇帝临轩命使。降而亲王,礼仪有杀,命使则同。由纳采而问名,而纳吉,而纳征,而请期,然后亲迎、同牢。备礼动需卜日,无纳采受册即归寿邸之礼也。越明年,武惠妃薨,后宫无当帝意者。或奏妃姿色冠代,乃度为女道士。敕曰……属太后忌辰,永怀追福,以兹求度。……其曰太后忌辰者,昭成窦后以长寿二年正月二日受害,则天后以建子月为岁首,中宗虽复用夏正,即正月行香废务,直至顺宗永贞元年,方改正以十一月二日为忌辰。开元中犹循中宗行香之旧,是妃入道之期当在开元二十五年正月二日也。……(下文言杨贵妃当为处子之身,此处不录)
以上论述说明,朱氏意在指明杨妃入道之期在开元二十五年(737)正月初二。前文已述及,两位陈先生均已指出其误在将武惠妃之死定在开元二十四年(736)。结论亦因此致误。然而细读朱文,将武惠妃之死时间定错固是关键,但其致误之由却应归于推论的武断性。细考其推论过程就会发现这样一个细节,即“越明年,武惠妃薨,后宫无当帝意者。或奏妃姿色冠代,乃度为女道士”。固然可以说朱氏由于认定武惠妃死于开元二十四年(736),恰在杨氏被册为寿王妃后一年,从而用“越明年”一词。但这里我们恰恰忽略了一点,即朱氏指出“太真外传,宋乐史所撰。称妃以开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归于寿邸。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温泉宫使高力士取于寿邸,度为女道士,住内太真宫”为“传闻之谬”。此处显见的错误是“称妃以开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归于寿邸”,而“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温泉宫使高力士取于寿邸,度为女道士,住内太真宫”一条,朱氏则在无证据的情况下,轻易否定了这条史料。此故是朱氏的重要失误,然则朱氏在论证这个问题时也同样犯了过于武断的错误。他说开元二十四年武惠妃死,玄宗没有称意之人,便选中杨妃,并让其于开元二十五年出家。这里朱氏缺乏推论的过程,而直接认定在开元二十五年,即武惠妃死后的第二年。假设朱氏并没有将武惠妃的死期推断错,即认定在开元二十五年,那么依朱氏的推理,他是否会再加一个“越二年”从而得出杨妃入道在开元二十六年二月二日?或者说,“越明年”恰恰就是朱氏推论的过程,即杨氏在武惠妃死后第二年入道,而究竟武惠妃死于哪一年并不重要。由此,可以说朱氏的错误并非全部由于错误的前提所致,甚至与前提无关。假使如此,两位先生又该怎样反驳朱氏之观点?笔者认为,唯有引证《杨太真外传》说明尚有书籍记载杨妃入道在开元二十八年,而朱氏若认为在开元二十六年,则毫无证据。当然,必须指出,以上假设并不影响考证杨贵妃入道之年的具体结论。
两位陈先生旨在说明杨妃入道在开元二十五年的结论错误。至于论证,则只指出朱氏前提错误,致使结论错误,而忽视了对朱氏得出此错误结论的武断性的批判。
再者,陈垣先生最后得出结论为杨贵妃入道之年在开元二十九年正月二日的结论所据者何?欲探明此问题,所据基本史料无非是《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中的相关部分。朱彝尊、陈寅恪、陈垣诸先贤考证的主要依托概莫能外。具体来说,《旧唐书》《唐会要》等原始资料均未见杨妃入道时间的确切记载,仅《新唐书》中记为开元二十八年。那么《新唐书》此条新增史料的准确性、可靠性就尤为关键。陈垣先生指出《新唐书》该条史源应是《杨太真外传》,并进一步说明《杨太真外传》为宋乐史所撰,“当有所据”。既然如此,这两条史料即应视为一条。对此关键证据,陈垣先生的论据仅为“当有所据”。我们不免要怀疑陈先生是否犯了“孤证不证”之失。而关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则举出另一条证据即《南部新书》辛条“杨妃本寿王妃,(开元)二十八年,度为道士入内”似可为补充。陈垣先生为何没引出此证当无所见。那么,现在看来,陈垣先生对《新唐书》新增史料来源的判定又是否过于武断?陈寅恪先生则仅指出“正史小说中诸记载何所依据,今不可知”,“以事理察之,所记似最为可信”。更最终得出结论:“姑假定杨氏以开元二十八年十月为玄宗所选取,其度为女道士敕文中之太后忌辰,乃指开元二十九年正月二日睿宗昭成太后之忌日。虽不中,不远矣。”[3]
三、结语
就杨妃何时入道这个问题,陈寅恪、陈垣二位先生所做的工作在于指出朱氏得出的开元二十五年的结论是错误的,并推算出杨妃入道的相对真实时间。就此而言,足见两位先生考据功力深厚,然而,在破与立的过程中却亦存在着缺陷和不足,虽然这并不影响结论的得出,但终归是白璧微瑕,这也应引起今日考据学者们的注意。
[1]陈垣.杨贵妃入道之年[A].陈智超.陈垣史源学杂文[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67-70.
[2]朱彝尊.曝书亭集[M].上海:世界书局,1937.648.
[3]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20.
【责任编辑:董丽娟】
K204.3
A
1673-7725(2016)04-0230-03
2016-02-05
王伏牛(1986-),男,河南洛阳人,主要从事北方民族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