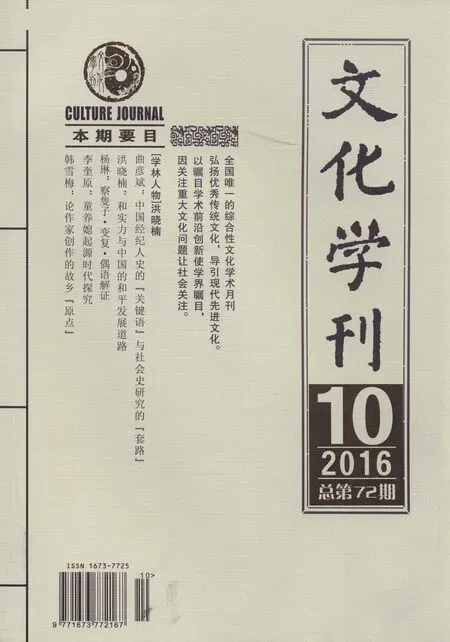《师父》:中国侠文化的式微
黄丝雨
(广西财经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3)
【文学评论】
《师父》:中国侠文化的式微
黄丝雨
(广西财经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3)
中国侠文化起于春秋战国,兴于魏晋盛唐,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特有形态之一。当代影视产业为中国侠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表现舞台,2015年12月上映的武侠电影《师父》就集中体现了导演徐皓峰对民国初年中国侠文化变迁态势的思考。本文试从武人的技艺、品格、生存形态三方面分析这种转变,着力分析冷热兵器交替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传统侠义文化的生存困境,揭示其被迫退隐的结局与命运。
徐皓峰;《师父》;侠文化
中国侠文化萌芽于春秋战国,在当时诸侯割据、战火连绵的乱局之中,逐渐产生了以武力为谋事工具的游侠阶层,他们的行事理念与组织形态可以视为中国侠文化的雏形。此后,侠文化与同时期产生的儒、墨、道文化相互碰撞,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内涵与外在形态,即以匡扶正义为行为准则,以武力技能为立身之本,以自由人格为内在追求。这一文化精神经过历史的冲刷,内化为中国特有的民族文化心理,并体现在形态各异的文艺作品中。
一、武的变迁:冷兵器与热兵器
“武”与“侠”的渊源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彼时正是奴隶制崩坏,向封建制过渡的战乱阶段,产生了许多失去世业的流民,而“上层失业之流民,多成为儒士。其原业农工之下层失业之流民,多成为侠士”[1],这是来自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原儒墨》中的考证。那么,儒士与侠士以何谋生?他们皆以谋略或武力等技能成为各诸侯国新兴贵族门客。这些凭文才武略谋生的阶层在当时各国攻伐的局势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虽然韩非子在《五蠹》中对他们持批判的态度,即“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2],但至少说明“侠”这一阶层从诞生之初便有其必须依凭的技艺——“武”,而这里的“武”,特指以冷兵器为主要攻防手段的武学技能。纵观中国“侠士”阶层的历史,会发现它与整个中国封建制的兴衰息息相关。
二、义的困境:理想与现实
虽然“侠”在诞生之初是出于某种谋生的需求,但不可忽视“侠自身的目的性追求和固有的道德信条,即他们人生追求的终极目的及其所执之‘义’”[3]。当侠士作为一个阶层稳固下来后,其行为方式与处事原则必然形成一套相对固定的模式,用以制约这一群体的言行,并指导侠士的内心旨归。
电影《师父》中将“义”的两难处境主要由男主角陈识来表现。作为南方小拳种的传人,陈识北上天津的目的只有一个,即立身扬名。他找到当时天津武术界最重要的人物郑山傲,在露了一手真功夫之后,后者向其详述了踢馆扬名的秘诀以及整个天津武林行事立身的规矩。这些规矩显然已经与传统侠文化中对“义”的追求相去甚远。天津武馆并不传授徒弟真功夫,招揽徒众的目的主要是扩张势力和收敛钱财,至于对地方事务的干预也是以官府的意志为导向,在冷兵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大背景下,这种寻找政治势力做靠山的倾向愈来愈明显。即使郑山傲本人,对于借助其徒弟林希文在军界的影响力享受特权一事,也是甘之如饴。
三、隐的无奈:自由与逃遁
胡秋原在《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中指出,儒、道、墨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格局,而儒、隐、侠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三大性格要素。作为一个文化统一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三者之间相互融合,在侠文化中就有诸多来自儒家和道家的因素,其中道家思想影响“侠”的生活形态与内在精神。道家主张“道法自然”,即顺应人的心性与自然环境的规律,这与侠客至情至性的生活形态颇为投合。在处事原则上,道家讲究避不入世,与主流政权保持一定距离,这也应和了武林江湖与庙堂政治的对立关系。甚至,很多武林宗派与道教也渊源颇深,如武当派、峨眉派等。历代的武侠作品中,均涉及“侠”与“道”的这种渊源,如唐代传奇中的“聂隐娘”,自小便被道姑带至山中修炼,所学武艺有自然界禽鸟之势,最终也走向了道家的归隐之路。
四、结语
武侠影视为中国侠文化提供了众多鲜活的影像,他们大多高扬中国侠文化的侠义精神。也有少数编导开始反思侠文化中的消极因素,酝酿武侠影视的变革。徐皓峰所执著的是真实再现中国侠文化的最后一段黄金期。他的作品中既有对侠文化精髓的坚持与肯定,又有对历史更迭的清醒与惆怅。电影《师父》是其武侠思想与影响结合的绝佳范例,其中思考对清末民初侠文化变迁的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冯友兰.原儒墨[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35,(2):279-310.
[2]韩非子.韩非子[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76.
[3]韩云波.中国侠文化:积淀与传承[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47.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424.
【责任编辑:周 丹】
J905
A
1673-7725(2016)10-0080-02
2016-08-05
本文系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青年项目“多媒介语境下广西当代文学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5CZW001)的研究成果。
黄丝雨(1981-),女,广西南宁人,讲师,主要从事影视传播、民族文化与文化产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