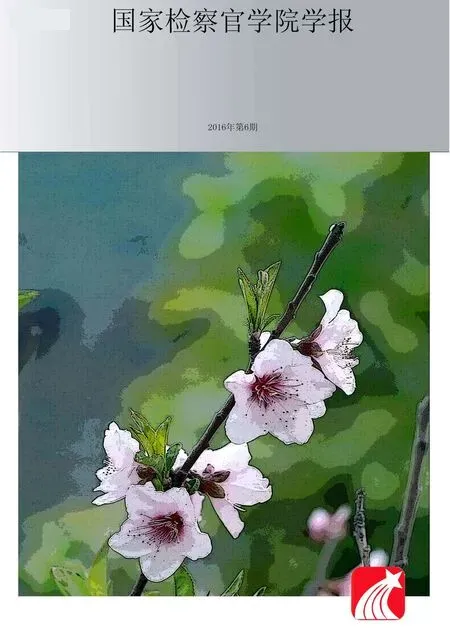中立帮助行为刑事可罚性研究
曹 波
(中国人民大学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
中立帮助行为刑事可罚性研究
曹 波
(中国人民大学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
“中立性”既是中立帮助行为之特质,也是确定行为可罚性的事实根据。基于行为“中立性”的本质特征以及维持刑法自由保障机能与法益保护机能动态平衡的客观需求,即便中立帮助行为对他人实施犯罪具有事实性或物理性因果贡献,也不应无差别地全面肯定其刑事可罚性。然而,限制行为可罚性的既有路径不是限制逻辑存在明显瑕疵,就是限制标准过于暧昧、限制结论过于恣意,不具备相应的操作性和可行性,根本无法担负起限定处罚范围的重任。确定中立帮助行为刑事可罚性,应当立足行为之“客观中立性”特征,通过演绎客观归责理论,规范评价行为升高正犯实行犯罪的风险是否为法所不允许。只有在违反相关刑法前规范升高正犯行为之风险且该规范之目的在于避免行为被用于犯罪时,才应肯定中立帮助行为的刑事可罚性。
中立帮助行为 刑事可罚性 中立性 限制处罚 客观归责理论
在分工高度复杂化的背景之下,个体之间的协作性和依赖性成为个体正常交往之当然前提,任何人只要想有意义地生活于现今社会,就不可能脱离其他个体承担所负之社会职责,鲁滨逊式的离群索居生活模式永远停留于小说之中,而不可能在现实社会中找到痕迹。现实中,不仅个体有意义地生活离不开其他社会成员自觉承担职责,社会自身的发展也要求个体严格依其地位和角色承担所负之社会职责。然而,这些承担所负社会职责的行为完全可能基于偶然原因与他人的犯罪行为联结,从而在客观上为他人的犯罪提供便利。如何妥当评价这些行为,成为晚近刑法学界激烈讨论的议题,即中立帮助行为是否具有刑事可罚性。
通常而言,中立帮助行为客观上确实为他人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与正犯侵害法益的结果具有物理性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对他人的犯罪行为也有相应认知,齐备帮助行为和帮助故意要件,在没有特别的违法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的情形下,以帮助犯处罚行为人并无理论和实践上的障碍,甚至是当然结论。不过,全面肯定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的“全面处罚说”,忽视中立帮助行为的特殊性且造成公民行动自由的不当萎缩,已经被学界抛弃,仅具有历史沿革的意义。时至今日,限制中立帮助行为刑事可罚性已成为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见解,但是具体限制路径却存在诸多令人失望的缺憾,这极大地制约限制处罚说自身的合理性、科学性和实践性。本文认为,究竟应当秉持何种标准、选用何种路径限制可罚性,需要对中立帮助行为区别于普通帮助行为的“中立性”特质的细致剖析以及对中立帮助行为刑事可罚性问题生成机制的深入挖掘。
一、中立帮助行为及其“中立性”
德国学者Wohlleben曾将“中立帮助行为”定义为 :“实施者假使面对与正犯相同情况的其他人也会从事的行为,因为其行为自始是为了实现独立犯罪或犯罪人之外,而且并非法所不许可目的之自我目的。”*转引自洪兆承 :《中性行为与帮助犯》,台湾政治大学法律学研究所2009年硕士论文,第68页。但这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学者对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的讨论通常以描述中立帮助行为的外部特征作为“引子”。例如,有论者将“中立行为”描述为“在外形上看是中立的(不具有犯罪意义)行为而从客观上促进正犯行为实施”。*陈家林 :《外国刑法通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09页。也有学者提出 :“中立的帮助行为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一般来说,是指外表上属于日常生活行为、业务行为等不追求非法目的的行为,客观上对他人(正犯)的犯罪起到促进作用的情形。”*张明楷 :《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2期。鉴于中立帮助行为属于内涵外延相对模糊的日常用语,放弃从正面定义不失为明智之举,但“概念乃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美]E·博登海默 :《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学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04页。出于框定研究对象和范围考虑,作为讨论的基点,有先明确界定中立帮助行为的概念之必要。
(一)作为中立帮助行为特质之“中立性”
中立帮助行为的特殊性集中体现于行为的“中立性”,这是其区别于普通帮助行为之特质,是决定限制可罚性的事实根据。从语词含义来看,“中立”意为“处于对立的双方之间,不倾向于任何一方。”*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685页。将其演绎于“中立帮助行为”之中,则应具有以下三层含义 :
其一,就法律调整范围而言,“中立性”既不是指行为因为法律的谦抑性、抽象性以及不周延性而处于法律调整范围之外的“法外空间”,也不同于“法律不理琐屑之事”中的“琐屑之事”。此两种情形皆因为行为社会意义不大,不值得动用法律予以评价,但是暂且不论中立帮助行为固有的便利社会交往的正当价值,仅以其客观上促进他人实施犯罪来说,行为就可能被评价为可罚的帮助行为而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何况“法秩序不拟规整的范围,法外空间即便存在但也受到极大的压缩”,*[德]卡尔·拉伦茨 :《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50页。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健全的法律体系务求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均纳入法律调整的轨道,游离于法律规范之外的行为必然是少之又少,难以认定中立帮助行为是法律有意保持沉默而不予调整的行为。
其二,以法律评价阶段观之,“中立性”只是行为的事实特征,而非法律属性。“‘违法’与‘不违法(合法)’之间根本就是一种形式逻辑的矛盾对立关系,二者间非此即彼,不存在居中的第三种可能。”*参见王钢 :《法外空间及其范围》,《中外法学》2015年第6期。法律评价的结果只有违法与合法之别,并没有独立于二者的“中立”一说。中立帮助行为之所以是“中立”的,不是指法律对其态度不明,也不是法律将其评价为“中立”,而是由于行为尚停留在待法律评价的阶段,是对行为事实特征的客观写照,行为从根本上属于“前构成要件行为”。一旦法律对中立帮助行为进行规范评价,其结论就只有可罚的帮助行为与不可罚的中立行为之分。
其三,从具体内容来看,作为行为事实特征的“中立性”,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主观侧面的“主观中立性”和客观侧面的“客观中立性”两方面。主观上,中立帮助行为人具有追求正当商业目的或正常交往目的与放任行为被他人利用于犯罪的“对立”。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为他人实施犯罪提供便利条件仍然实施相关行为,但并不具有促进他人实施犯罪的意图,也非出于防止他人实施犯罪的目的,实际追求的是与犯罪无涉或者至少不被刑法所禁止的目的,他人是否会利用自己的行为去实施犯罪根本不为行为人所关注。行为人完全是基于其所处之地位或扮演之角色才实施相关行为,行为事实上对他人权利的影响或侵害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不幸结果,但却非行为人的原本目标。客观上,中立帮助行为是按照惯常交易规则或社会交往规则施行并具有独立且合法正当的社会意义,只是偶然地被犯罪者利用而被动卷入他人的犯罪之中,与他人的犯罪联结,对他人犯罪有着现实的物理性因果贡献。此时,同一行为同时呈现出有益性和有害性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意义,这种客观上的“对立”构成了中立帮助行为“中立性”之主要内容。
(二)中立帮助行为“中立性”之具体展开
根据上述对“中立性”的理解,结合中立帮助行为的有关事例,可以将行为“中立性”的具体表现概括为以下四方面 :
首先,中立帮助行为是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具有职业典型性或日常生活性的“制式”行为,只要满足相应的交易规则或者交往规则的条件,行为就如同自动发生装置般自动触发。“大多数日常行为是自动实施的,‘意志’至多是一个有价值的旁观者,而不是行为人意向的实际执行者。”*[英]威廉姆·威尔逊 :《刑法理论的核心问题》,谢望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3页。行为主体在决定是否做出行为时,除遵循实施行为的有关要求外,无必要、也无义务、更无权力对行为相对人进行审查或者筛选,亦即中立帮助行为的相对人具有普遍性、无差别性,是包括犯罪人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相反,若某种行为的相对人只是违法犯罪者,该行为就是专为帮助他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而存在,其在社会交往中除促进违法犯罪以外别无其他合法正当的社会意义。中立帮助行为的“制式性”和“匿名性”对社会的存续发展具有独立的价值,是社会交往正常开展的前提和基础。谨以加油站工作人员提供的加油服务为例。加油站工作人员为顾客加油的行为无疑是社会生活中具有职业典型性的“制式”行为,对保障交通运输的顺利进行极为重要,是社会交往正常进行的必要条件。此种行为的发生机理是,只要司机按照正常的交易规则和交易价格进行交易,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就不会拒绝为其提供加油服务,当前来加油的司机满嘴酒气,必然已经并且将继续实施危险驾驶犯罪,这时工作人员的加油行为即便对他人的危险驾驶行为具有因果贡献,也只是典型的中立帮助行为。
其次,中立帮助行为的发生具有反复性,通常不具有侵害法益的风险,其促进他人的违法犯罪只是基于偶然因素。有学者指出 :“行为人在面对犯罪人以外的一般人时仍会反复实施该行为,行为只是偶然地被犯罪者利用而被动地为法益侵害的结果提供助力而已。”*金希 :《中立的业务行为与可罚的帮助行为之界分》,《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综览中立帮助行为的事例,行为的反复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反复实施的行为非但没有直接侵害法律所保护的各种利益,反而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是公民职业自由和行动自由的重要体现,之所以需要讨论其刑事可罚性,无非是行为客观上促进他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从而偶然地与违法犯罪联结。例如,五金店店员销售菜刀本是为满足顾客正当需要而反复实施的行为,但在顾客购买菜刀是为了实施犯罪活动时,店员的销售行为就会为顾客的犯罪活动提供便利,只是这种促进犯罪活动仅为偶然现象,而非常态现象。
再次,中立帮助行为是一种职务(业务)行为或者履行义务的行为,其一般由行为相对人请求,中立帮助行为人则基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或具有的社会职责,按照与满足所扮演角色相一致的理由而实施。在中立帮助行为的事例中,行为人通常都负担一定的义务,比如按照顾客的需要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义务,或者偿还债权人欠款的义务,行为人的行为在履行相关义务的同时,又在客观上促进他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这种履行义务的行为是否应当评价为可罚的帮助行为尚不确定。如果行为人不具有相关义务却实施行为,抑或虽然具有某种义务,但其实施行为的目的并非履行义务,其行为之全部意义仅在于促进他人违法犯罪的话,行为便不具有“中立性”。
最后,中立帮助行为人实施行为时通常缺乏促进犯罪的意思。如前既述,中立帮助行为人虽然认识到他人的犯罪意图,也可能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减少他人实施犯罪行为的障碍,但仍然实施该项行为,以行为人自己的“行为决定”表现出对他人利用自己的行为实施犯罪的漠视、放任,足以认定为“间接故意”。然而,行为人主观上认为他人的犯罪与自己并无关联,其实施相关行为仅仅是基于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履行自己所具有的义务,是追求自身利益且为法律所容许的目的,并无促进他人犯罪的意思。相反,如果行为人以促进他人犯罪的意思积极地实施相关行为,行为虽具有“中立性”的外观形式,但因行为之客观意义完全在于促进他人犯罪,已不具有促进社会发展与公民交往之价值,欠缺“客观中立性”,就不能成立中立帮助行为。
基于上述阐释,中立帮助行为可以定义为 :基于偶然原因与他人的违法犯罪行为联结并在客观上为他人的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便利,但却是社会个体为保障社会存续发展以及公民正常交往所需而承担所负之社会职责的行为。
二、限制可罚性路径的梳理与反思
针对中立帮助行为是否具有刑事可罚性,传统理论站在全面处罚的立场上,认为帮助犯之主客观要件是判断帮助犯成立与否的唯一标准,不论行为是否具有“中立性”,只要客观上对他人的犯罪提供便利,主观上明知他人的犯罪意图或者正在实施犯罪,就理所当然成立犯罪。*参见[德]汉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马斯·魏根特 :《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842-843页。然而,单纯剥离出中立帮助行为促进犯罪的意义和行为人主观上的“放任”就肯定行为的可罚性与其说真正解决了疑难,毋宁说是回避了问题的关键。正如德国学者所言 :“如果认为日常生活行为虽然外观上完全合法,但若行为人在个别情况下多少知道或者考虑到了他人会利用他的行为实施犯罪,就应该受到处罚,至少根据法治国的观点,这种看法是不合理的。”*[德]冈特·施特拉腾韦特、洛塔尔·库伦 :《刑法总论Ⅰ——犯罪论》,杨萌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36页。从形式上理解帮助犯的成立要件,全然不顾及中立帮助行为特质之“中立性”,全面肯定中立帮助行为的刑事可罚性,以不值得肯定的方式增加公民正常交往的成本,势必背离刑法保护法益的初衷,打破刑法法益保护机能和自由保障功能的动态平衡。毕竟“辅助性的法益保护才是刑法的任务”,*[德]克劳斯·罗克辛 :《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蔡桂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1页。刑法保护法益不被侵犯不能合逻辑地推导出刑法禁止一切可能侵害或威胁法益的行为。因此,全面处罚说的式微有其必然性,限制处罚说不可避免地成为当前共识,只是学界对限制的具体路径存在激烈争论。
(一)主观限制路径
1.主观限制路径的基本主张
主观限制路径从行为之“主观中立性”出发,以行为人的主观认知状态为基准判断是否成立可罚的帮助行为,从而主张限制行为可罚性。由于对“主观中立性”内容的侧重不同,又分为间接故意否定说和促进意思具备说。前者认为处罚中立帮助行为限于行为人主观上是蓄意或者直接故意的场合,将行为人仅有间接故意的情形排除出帮助犯的处罚范围。例如,德国学者v.Bar认为,不能处罚间接故意所实施的援助行为,否则,即使行为人实施的是没有恶意的行为,但只要抱有可能被他人利用来实施犯罪的想法,就会受到处罚,这不合理。*同前注[1],第611页。后者则将行为人的意志因素作为考查重点,即便行为人认识到他人可能利用自己的行为实施犯罪活动,也不应肯定行为之可罚性,除非行为人具备促进他人犯罪的意思。德国学者Kudlich主张,仅知道他人的犯罪计划还不够,还需要通过自己的行为促进他人犯罪的意识和意思,也就是以具有“促进的故意”为必要。*转引自陈洪兵 :《中立行为的帮助》,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75-76页。由于行为人通常只是为了正常营业或日常生活正常交往才从事相关行为,不是有意地促进正犯者的犯罪行为,基本上欠缺“促进意思”,大多数的中立帮助行为不具有刑事可罚性。
2.主观限制路径的批判及澄清
作为一种早期学说,从主观方面限制可罚性的主张长期饱受批判,批判意见主要集中于 :(1)区分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的做法以及要求具备“促进意思”于法无据。不论德国刑法典还是我国刑法都没有为两种故意规定不同的处理方式与法律效果。帮助犯的成立也不需要帮助故意以外的诸如动机、目的等要素,“促进意思”不是帮助犯成立的主观要素。(2)违反检验构成要件符合性应“先客观后主观”的位阶序列,没有事先确定中立帮助行为之客观性,而“籍由帮助故意确认帮助行为的品质,势必导致犯罪评价逻辑上的矛盾,亦即‘帮助者在实施一个先由帮助故意所确立的帮助行为时,必须具备帮助故意’”。*古承宗 :《中性职业行为与可罚的帮助》,《月旦法学教室》2015年第12期。(3)过早考虑主观层面,可能导致本来客观上适当的行为,单纯因为行为人主观无价值的“恶”而被刑罚处罚,进而陷入反行为刑法的“心情刑法”和“思想刑法”的窠臼,违背刑法之客观主义立场。*刘钰 :《中立的帮助行为刍议》,《鄂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8期。(4)“客观中立性”才是中立帮助行为特质之最主要内容,“放弃从行为本身或者说从帮助犯的客观要件着手解决,而企图从主观方面对中立行为的帮助处罚范围加以限定,无疑是病急乱投医”。*同前注[14],第75页。(5)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中立帮助行为的“中立性”致使“想要通过取证等手段完全弄清正犯者获取相关服务的目的究竟是否包括实施合法举动是异常困难的。”*陈璇 :《刑法中社会相当性理论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58页。
应当承认,部分批判意见是中肯的,尤其最后两点批判可谓一针见血。主观限制路径的确存在某些缺憾,以致国内几乎找不到支持者,但为准确理解该路径的立场,进行下述澄清是必要的 :
其一,“促进意思”是否是帮助犯主观成立要件?本文认为,“促进意思”不是所谓的动机或目的等主观超过要素,而是帮助故意之意志因素的当然内容。故意作为心理上的事实,其认识对象是客观的构成要件要素。在帮助犯的场合,主要包括帮助行为、正犯行为及结果。理论界对帮助行为的理解通常是在帮助犯因果关系中进行的,根据帮助犯因果关系之“实行行为促进说”或“促进的因果关系说”的主流见解,帮助行为必须要么促进正犯行为的实行,要么促进正犯结果或使其变得容易。*蔡圣伟 :《论帮助行为之因果关系》,《政大法学评论》2013年第4期。亦即帮助行为并非是指一切为正犯实行犯罪提供便利的行为,而仅指其中对正犯行为或结果有促进作用的行为,帮助者对此必须有意识和意欲。既然意识因素要强调对“促进作用”的认识,那么意志因素就没有理由不考虑“促进意思”,因此否定间接故意时的可罚性也并非毫无道理。至于是否符合实定法规定的疑虑,如果确有实定法的规定自是最好,但即便没有实定法之规定,亦不妨碍在帮助故意中强调“促进意思”。因为帮助犯总则规定既是对犯罪基本构成要件的修正,这种修正当然不仅局限于扩张其犯罪行为的客观内容,还应包括对犯罪故意的修正,即在故意之意志因素上强调“促进意思”,不宜将单独犯所需之犯罪故意直接套用于帮助犯。
其二,主观限制路径是否违反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逻辑?本文认为,限制处罚说是在行为具备全面处罚说前提下以及帮助犯成立之主客观要件的基础上,结合行为“中立性”的具体内容,限制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的解决方案。若行为不符合传统帮助犯成立的各项要件,自始便不具有可罚性,自然无需限制其可罚性。因此,从方法论来看,限制处罚说不是为行为可罚性奠定基础的积极判断,而是立足于行为特殊性所作的消极判断,只需要将筛选出具有刑法意义的行为特质投射到法教义学的范畴即可。也即,是选择从主观层面限制可罚性,还是选择从客观层面限制可罚性,取决于论者对中立帮助行为之“中立性”的认识,无关构成要件的判断逻辑。
(二)客观限制路径
客观限制路径汲取主观限制路径的教训,根据“客观中立性”的具体表现,通过对帮助犯客观构成要件要素进行严格限缩,以限制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其路径可分为对帮助行为行为属性的限制和对帮助结果可归责性的限制两类。
1.帮助行为行为属性的限制路径
中立帮助行为虽对正犯者的实行行为有客观上的促进作用,但行为固有的“客观中立性”的属性特征决定仅凭客观上的促进作用尚不足将行为评价为可罚的帮助行为。该限制路径以社会相当性理论为其法理根据,亦即单纯的法益侵害结果不足以奠定行为刑事可罚性的基础,只有超出社会相当性范围,以与共同体生活的历史所形成之社会道德秩序要求相悖的行为方式侵害法益,才能够被赋予刑事可罚性。*参见[德]汉斯·韦尔策尔 :《目的行为论导论 :刑法理论的新图景》,陈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页。就中立帮助行为而言,“如果行为没有超出通常的日常行为形态,尤其是行为没有超出单纯的职业行为框架的场合,如买面包给决意侵入他人住宅的人或买斧头给意图伤害妻子的丈夫,都应被排除在刑法的帮助犯范围之外,即这些行为属于社会相当性范围内的行为,不具有帮助犯的要素,应否定帮助犯的成立。”*同前注〔2〕,第612页。然而,社会相当性理论存在判断标准过于暧昧、判断结果过于恣意等缺陷。为提升社会相当性理论的精致性和可操作性,哈塞默尔教授提出“职业相当性说”,主张根据职业领域来判断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在他看来,具有职业相当性的行为并非在中性化刑法规范,而是处于实现国家任务的分工关系来补充、赋予轮廓并具体化刑法规范,且没有与刑法规范相矛盾,反而在特定社会活动领域中与刑法规范发生关系。照此而实施的行为,不能认为是违反刑法禁止规范的行为,不能论以帮助犯。*转引自林育骏 :《从“中性行为”论帮助犯的成立要件——以帮助因果性与帮助故意为中心》,台湾大学法律学院法律系2011年硕士论文,第45页。
2.帮助结果可归责性的限制路径
结果的可归责性是在肯定行为对法益侵害的结果具有事实性因果贡献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该结果规范评价为行为人的“作品”。帮助结果可归责性的限制路径将突破口置于“是否创设不允许性风险”,即肯定行为的可罚性,既需要结果的因果引起或者风险升高,还要求这种被升高之风险为法律所不允许。鉴于中立帮助行为的职业典型性、日常生活性以及反复性等“客观中立性”特征,其虽事实上升高正犯实施犯罪行为的风险,但这种风险往往处在法律秩序范围之内,属于“允许性风险”,缺乏可归责性。“日常生活举止”根本没有制造任何具有刑法意义的风险,或者所制造的仅是‘可容许之风险’而已,无法以刑法相绳。判断是否“制造法所不容许风险”需要审查提供者对于正犯的预定用途或犯罪计划有无特殊认知,“如果正犯摆明了就是要以该提供物来实现违法犯行,而提供者对于犯罪的贡献就已经失去了‘日常生活举止’的特征,提供者就是以帮助故意来资助并贡献正犯故意犯行之人,构成帮助犯。”*林钰雄 :《新刑法总则》,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483页。
3.客观限制路径的遗缺评述
客观限制路径较好地回避主观限制路径存在的问题,在帮助行为的认定上就尽量限缩其可罚性范围,仅将为他人提供助力的行为中不具有社会相当性或升高不允许性风险的部分评价为可罚的帮助行为,这是立足于行为“中立性”的妥当选择,不过这两种具体限制路径或多或少都存在某些亟待补正的遗缺。
运用社会相当性理论对行为属性进行限制,避免刑法惩罚符合社会秩序的行为,具有结论的妥当性,但社会相当性的判断标准相当模糊,判断结论极易因人而异。就此而言,“职业相当性说”以具体的职业规范替代刑法规范,只要行为符合相应的职业规范即肯定行为的社会相当性,从而否定行为的刑事不法,确有相当的明确性和可操作性,但是该说(社会相当性说亦同)完全切断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联系,仅从行为方式、行为属性判断刑事可罚性,不仅有失科学性,也有片面化之嫌。更何况纯粹以是否符合职业规范作为可罚与否的标准,极易陷于在评价相同行为的刑事可罚性时可能因为行为人是否有相应的职业身份而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的尴尬。例如,同样是将意图杀人的人运送至被害人所在之处的运输行为,由出租车司机来实施不具有可罚性,而由不具有出租车司机身份的普通人来实施却具有可罚性。然而,将是否具有出租车司机的身份作为判断行为是否可罚的决定性因素,意味着“职业身份”堂而皇之地成为“免罪符”,这显然直接抵触宪法和刑法要求的平等主义,有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
通过判断中立帮助行为是否“创设不允许性风险”或者是否具有规范的“共同性”,来确定行为的可罚性的路径,是在肯定中立帮助行为对正犯侵害法益具有事实因果关系上的规范性限缩,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作为“客观中立性”的重要方面,中立帮助行为的确为正犯实施犯罪提供便利条件,对正犯侵害法益的结果也有不容否认的因果贡献,如果坚守传统的自然因果关系论,仅从存在论意义上解释帮助行为,中立帮助行为无疑都具有可罚性。然而,中立帮助行为除对法益侵害具有事实因果贡献外,还内含维系社会存续与公民自由交往的正当价值,此种正当价值是否足以抵消行为的犯罪促进作用,以及行为升高之风险是否为法所不容许,需要结合刑法的机能和规范目的展开价值衡量和规范评价才能确定,远非纯粹的自然主义分析路径可胜任。事实上,帮助结果可归责性的限制路径存在的问题恰恰在于价值衡量与规范评价的具体标准。对此,学者们要么回避该问题,不提出相应的判断标准,径直给出诸如“一目了然”这样的最终结论,要么选用假定因果关系或者假定的替代原因作为判断标准,但是可罚的帮助行为原本就不需要属于关键性的因果贡献,也不要求具有不可替代性,利用假定因果关系来否定不被允许性风险的升高必然意味着大多数案件中使构成要件行为变得容易的行为均不具有可罚性,这无异于架空刑法关于帮助犯的有关规定。
(三)混合限制路径
考虑到中立帮助行为的“中立性”,混合限制路径认为应当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限制行为的可罚性,其中尤以德国学者罗克辛教授建立在区分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的基础上进行客观考量的理论最为瞩目。国内大多数学者也赞同主客观混合说,但具体主张不同于罗克辛教授的方案,当然这并没有妨碍两种主张在处理实际问题上结论的相似性。
1.罗克辛教授的限制方案*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 :《德国刑法学总论》(第2卷),王世洲等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45-164页。
根据罗克辛教授的理解,帮助犯之帮助是“对符合行为构成的结果所作的因果性上的、在法上不容许的风险提高”。单纯因果性风险提高的帮助行为不足以评价为可罚的帮助行为,除非所提高的风险属于“法所不容许”,由此便产生中立帮助行为刑事可罚性的问题。而提高风险是否为法所允许的判断,需要区分两种不同案件 :行为人认识到正犯犯罪决定的类型,以及行为人只是估计到正犯的犯罪性举止行为的类型。
具体来说,在第一种类型的案件中,帮助行为是否可罚取决于行为是否具有“犯罪意义上的关系”。肯定具有“犯罪意义上的关系”的情形有二 :其一,行为人通过相应的行为有意识地支持一种具有犯罪性质的行为,此时行为之全部意义在于促进正犯的犯罪行为;其二,在直接支持的行为本身合法时,但行为人实施该支持的唯一目的就是使他人的犯罪行为变成可能或使之变得容易。简言之,不论行为人所支持的行为是合法行为还是犯罪行为,只要其在实施支持行为中认识正犯所计划的犯罪,就完全压倒性地可以得出有刑事可罚性帮助的认定。然而在支持合法行为的场合,存在可罚性的例外,即只要支持行为本身就能够独自说明对正犯是有意义与有用处的,并且支持行为还另外对该正犯是一个与之相对立的、建立在独自决定基础之上的犯罪性举止行为的条件,就缺乏犯罪意义上的关系。比如,在“明知从事材料加工的工厂主违反环境保护规范,仍向其提供原材料”和“款待意欲犯罪之人”的事例中,提供原材料的行为和提供饭菜的行为虽对正犯实行犯罪有意义,但其直接帮助的是合法行为,具有独立的意义,缺乏犯罪意义上的关系,应当否定行为的可罚性。
在第二类案件中,行为人尚未明确认识到正犯的犯罪决定,仅仅怀疑或者估计其行为被用于犯罪的可能性,此时原则上适用信赖原则否定行为的可罚性,因为每个人都可以信赖他人不会实施故意犯罪,除非他人的行为已经显现出“明显的犯罪倾向”。“明显的犯罪倾向”的认定并非建立在以主观印象为基础的“可疑的表现”之上,而是需要“具体的根据性要点,详细说明一种犯罪性使用目的的极其可能性。”在一场由愤怒导致的街头骚乱中,参加者在一家视域之内的商店中购买武器的事例,即属此类。
罗克辛教授的限制方案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获得了相当的支持。台湾学者蔡蕙芬在讨论“P2P网站经营者之作为帮助犯责任”时,全面接受了该方案。*蔡蕙芬 :《P2P网站经营者之作为帮助犯责任与中性业务行为理论之适用》,《东吴法律学报》2006年第1期。黄惠婷教授也持同样的见解,她认为“日常的中性行为虽然与他人犯罪具有因果关系,但欠缺犯罪的意义关联性,且依信赖原则能排除结果的客观归责时,也不成立帮助犯。”*黄惠婷 :《中性行为之帮助性质》,《台湾法学杂志》2008年第10期。晚近,德国联邦法院也全盘接纳该原则,在“律师诈骗帮助案”和“卢森堡汇款案”中有力地贯彻了这一限制方案。
2.国内学者的主张
我国学者也不乏从主客观方面限制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在这个意义上也可将其归结为“混合限制路径”,但与罗克辛教授的限制方案不同,国内学者更多从中立帮助行为具备可罚性需要满足的要件着手综合考虑主客观方面,如张明楷教授主张,“应当通过综合考虑正犯行为的紧迫性,行为人(帮助者)对法益的保护义务,行为对法益侵害所起作用大小以及行为人对正犯行为的确实性的认识等要素,得出妥当结论。”*张明楷 :《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425页。周光权教授也提出客观、主观以及共犯处罚根据三项标准判断中立帮助行为是否具有可罚性。*周光权 :《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5页。但二位教授都是直接给出认定中立帮助行为具有刑事可罚性应当满足的条件,而没有相应的论证理由。张伟博士以犯罪构成要件理论为指导,分别从行为的主观、客观两方面提出了处罚中立帮助行为应当满足的条件。在他看来,认定可罚的中立帮助行为应注意两点 :其一,帮助者主观上仅限于明确的认识,至于是积极追求的直接故意还是漠不关心而放任的间接故意在所不问;其二,从帮助犯的处罚根据出发,实质解释帮助行为,即在中立帮助行为极大地促进正犯的实行行为,使后者的犯罪行为明显方便的场合,成立帮助犯的可能性越大,而在具体判断中,中立帮助行为发生的特定时空范围是重要的判断资料。*参见张伟 :《帮助犯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3-176页。
3.对混合限制路径的质疑
如前既述,犯罪的成立必然要满足相应主客观要件,帮助犯亦不例外。在探究中立帮助行为刑事可罚性时,国内学者以此为出发点,从主客观两方面从严认定帮助犯之构成要件,尤为强调行为侵害法益的明显性和紧迫性,具有合理性。然而,一方面,仅仅给出结论并无具体操作标准无助于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的认定,极有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而使判断结果流于恣意。另一方面,其确立具体的主客观要件的理论基础也值得推敲。帮助犯的成立只需要帮助行为促进正犯实施犯罪即可,何以在中立帮助行为的场合却要求这种促进具备“紧迫性”、“极大”或者“明显方便”等表示程度的要素?况且论者将主观方面限制于“明确的认识”,无非是在强调帮助犯的主观构成要件是故意,但这并不能为限制可罚性提供坚实的基础,因为过失的帮助行为本就不受处罚。可见,国内学者虽然单独讨论中立帮助行为,但其提出的方案无非是以德日刑法之话语体系再度解释一般帮助犯之成立要件,并未对限制中立帮助行为这种特殊行为的刑事可罚性有多少实益。
罗克辛教授的限制方案虽然获得不少支持,但也并非尽善尽美、滴水不漏 :其一,在考察行为客观方面之前即以行为人对于正犯犯罪决定的认知程度为标准将中立帮助行为的情形进行类型化区分,违反了犯罪成立应该进行“先客观后主观”的判断次序。在进行客观认定获得客观事实之前,主观方面的判断必然因缺乏判断资料而无从进行,实难想象罗克辛教授在检验客观事实之前究竟是依据何种资料判断是否认识到正犯的犯罪决定的。更何况以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决定行为的性质和社会意义,不仅合理性有待证成,可行性也值得怀疑,因为判断基准同样不明确。其二,在行为人没有明确认识到正犯犯罪决意的案件中适用信赖原则也不无商榷之处。所谓信赖原则系指“在行为人实施某种行为之时,合理相信被害人或第三人会采取适当行为,即便因被害人或第三人不适当的行为而发生了结果,行为人对此不承担责任”。*[日]西原春夫 :《交通事故与信赖原则》,成文堂1969年版,第14页。转引自林亚刚 :《犯罪过失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页。信赖原则主要针对过失认定而在交通领域萌芽并发展的理论,其适用范围虽有扩大至集体治疗等采取分工合作的职业活动趋势,*林东茂 :《一个知识论上的刑法学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但却尚未超出过失犯罪的领域,将之运用于故意犯罪还存在理论上的障碍。正如德国学者阿梅隆所言,“想要用信赖原则来为帮助犯可罚性的排除寻找根据几乎是不可能的”。*同前注〔14〕,第257页。
三、客观归责理论的基本立场
(一)客观限制路径的证成
整体观之,前述限制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的各种路径不是限制逻辑存在明显瑕疵,不具有科学性与合理性,就是限制标准过于模糊、限制结论过于恣意而不具有可行性和操作性,根本无法真正担起限制处罚范围的重任。不过应当承认,尽管限制处罚的诸说存在的缺憾极大地减损了理论自身的价值,但也正是学说间不间歇的批判与反批判蕴藏的思维碰撞与观点纷呈使得中立帮助行为理论得以逐渐深化而日臻成熟。
在限制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的三种路径中,混合限制路径并未紧密围绕中立帮助行为的“中立性”特质展开,而着眼于可罚的帮助犯的成立要件,从主客观方面寻求肯定行为可罚性所需要的各种要素,但此种正面的积极判断明显疏离限制可罚性的出发点,值得商榷。主观限制路径根据“主观中立性”的内容,从主观层面限制可罚性,这也是以肯定中立帮助行为属于可罚的帮助行为为前提,将凡是客观上对正犯行为及结果有因果性贡献的行为一概评价为帮助行为。在放弃从客观方面严格限定帮助行为后,帮助故意的成立范围必定相应扩张,为避免刑法打击范围过分扩张,通过限制某些主观要素来限制行为的可罚性无疑是当然甚至是不得已的选择,但这种“避重就轻”的做法既不符合刑法之自由保障机能,也与“客观中立性”属于中立帮助行为最主要特殊性的前提相悖,还远不如直接从严把握可罚帮助行为的不法内涵,充分发挥客观构成要件的过滤机能便捷、有效。事实上,“刑法学上之所以将中立的帮助行为单独拿出来讨论,无非是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客观上为正犯行为提供了方便,和正犯结果之间具有——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因果关系,而行为人本人也了解这种情况,否则,根本就不可能将其作为刑法上的问题加以讨论。”*黎宏 :《结果本位刑法观的展开》,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342页。因此,前述主观限制路径以及综合限制路径,均未抓住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议题的关键。
在行为刑法的视阈下,对行为刑事可罚性不论是进行消极判断还是进行积极判断,都应当聚焦于客观犯罪事实,其中又以行为足以被评价为可罚的犯罪行为作为认定犯罪成立之首要且最为重要的前提,后续法律评价都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的。而行为的性质与意义是由行为的客观方面决定的,而非取决于行为人的动机、目的等主观认知和意欲。正所谓“好心办坏事,亦是坏事”,以抱有为他人带去利益的良善心态为他人提供服务却造成违背初衷的损害后果,该“良善心态”丝毫不能改变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客观事实,唯能降低行为的可遣责性从而使自己获得宽容或谅解。中立帮助行为也并不例外,其性质与意义也应由行为的“客观中立性”决定,因为不论是否认识到他人的犯罪决定,行为人实施相应的中立行为都是基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所扮演角色的要求,行为自身原本就具有独立于犯罪的社会意义。更何况,中立帮助行为的“主观中立性”也是建立在“客观中立性”基础之上。行为人之所以认识到他人可能利用自己的行为实施犯罪而仍然决定实施行为,无非是考虑到自己是按照既有交易规则和交往规则实施行为,这非但不为法律所禁止,反而是自己的分内之责。至于行为相对人如何利用中立行为则由其按照自我意志自由决定,由此所带来的后果无论有益还是有害,自应由行为相对人自负其责,而与中立行为人无涉。因此,立足于行为的“客观中立性”的客观限制路径正是限制中立帮助行为的刑事可罚性的妥当路径。
(二)社会相当性理论与客观归责理论的调和
诚然,客观限制路径内部形成依托社会相当性理论的帮助行为行为属性限制路径和借助客观归责理论的帮助结果可归责性限制路径的分野,但就限制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而言,社会相当性理论与客观归责理论并非不可调和的理论,二者之间的对立仅具有相对意义。
具体来说,二者均作为客观限制路径的法理依据,具有客观限制路径的共性特征,即都立足于中立帮助行为的“客观中立性”,在肯定行为对他人实施犯罪行为具有事实性因果贡献的前提下,结合刑法的机能和规范目的,运用规范评价这一教义学工具,合理限定可罚性的成立范围。其二,二者的逻辑进路具有相似性,均认为单纯的侵害法益的风险升高不能奠定行为可罚性的基础,肯定行为的可罚性还需要行为升高风险的方式超出社会相当性的范围或者行为升高的风险为法所不允许。只是在具体的侧重点上,社会相当性理论强调静态意义的行为性质或属性,客观归责理论则重视可否将不法结果归结于行为,然行为性质与行为结果只是同一事物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而已,实行行为导致不法结果的过程就是“实行行为之客观危险性的现实化(实现)过程”。*[日]山口厚 :《刑法总论》,付立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8页。判断行为的性质显然不可能无视行为产生的结果,一个严重侵害法益的行为实难认定为具有社会相当性;相应的,结果也蕴含于行为性质之中,是行为固有之风险现实化所致,只有作为行为风险现实化的结果才可客观归属于行为。其三,二者的具体标准具有对应性,在中立帮助行为的场合,判断行为是否升高不允许性风险需要判断风险是否可评价为刑法意义上的风险和风险是否被允许两个层面,这与判断行为是否具有社会相当性采用的事实上的“通常性和必要性”与规范上的“适当性”也能基本对应。
可见,不论是社会相当性理论还是客观归责理论在限制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上所具有的功能相差无几,采用何种理论均不存在合理性与科学性上的障碍。但是考虑到客观归责理论已经发展出相对健全、成体系化的判断规则并已经为学界广泛接受,通过演绎客观归责理论,判断中立帮助行为升高正犯实行犯罪的风险是否为法所不允许之风险,从帮助结果可归责性的角度限制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将更具有操作性和可行性,因而也是最优的选择。
四、限制可罚性的具体规则
在可罚的帮助行为中,帮助行为需要类型性地通过正犯行为侵害构成要件所保护的法益,如果中立帮助行为与他人的犯罪行为联结并不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或者这种危险并不具有刑法意义,就无法将正犯结果中属于帮助行为贡献的那部分结果按照客观归责理论类型性地归属于帮助行为。中立帮助行为是否足以评价为可罚的帮助行为也理应以客观归责理论为基础检讨是否具备完整的帮助犯不法内涵,亦即确定中立帮助行为之刑事可罚性通常需要判断中立帮助行为是否升高了正犯实行犯罪的风险,并以此为前提规范评价此种风险升高是否属于违反相关行为准则的结果,以及所违反行为准则而升高的风险是否处在规范保护目的之内。
(一)是否升高正犯行为的风险
限制中立帮助行为刑事可罚性应当首先否定没有升高正犯行为风险的行为之可罚性。即便大多数中立帮助行为因为客观上支持了正犯行为而可认定为事实上升高了正犯行为侵害法益的风险,但仍然存在一些没有升高风险的例外情形。例如,明知他人饱餐后要去实施犯罪而仍向其提供美味饭菜的情形,由于提供饭菜的行为属于满足他人正当的生存需要,况且纵使是即将被执行死刑的囚犯也有吃饭的权利,所以向饥肠辘辘的正犯提供饭菜的行为即便促进了正犯行为,也不应肯定风险的升高。又如,明知老板逃税的员工仍卖力工作的事例,卖力工作是社会所希望并鼓励的行为,其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国家税收来源,是对社会有积极意义的创造法益行为,这样的行为无论如何都不能认定为升高了犯罪的风险。事实上,在这些事例中,中立帮助行为所直接支持的都是合法行为,满足的都是正当要求,难以将其认定为升高了正犯实行犯罪之风险。
(二)是否属于违反行为准则所导致的风险升高
在肯定中立帮助行为升高正犯行为的风险的前提下,还要进一步检讨这种风险升高是否属于违反相关行为准则,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就应当肯定升高风险是法所容许的,进而通过排除归责的方式否定其刑事可罚性。在具体判断上,前述哈塞默尔教授的“职业相当性说”无疑提供了思考的线索。基于此,本文将中立帮助行为的事例简要分为具有职业注意性规范的情形和虽然没有职业规范却存在惯常行为规则的情形,以检讨中立行为是否属于法所不容许的风险升高。
在已有各项职业注意规范规制的领域中,这些职业规范虽不能确保完全合乎相关法律规定,但至少可以保证是不违反刑法的,行为人遵守相关职业规范而行为,即便升高了正犯行为的风险,也属于法所容许的。例如,出租汽车司机在运营过程中得知乘客将前往目的地实施杀人行为的事例以及加油站服务员给满嘴酒气的司机提供加油服务的事例中,只要出租汽车司机或者加油站服务员遵守相关规范,即便其最终将乘客载至目的地或为司机加满油,其也是以法所允许的方式升高他人实施犯罪的风险,应当排除归责。
在缺乏职业规范而存在惯常行为规则的情形中,虽然无法以职业规范检讨风险升高是否为法所不容许,但却可依照社会中惯常的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有些已经被认可而成为民事或行政法律规范)进行判断。例如,在明知债权人已经实施犯罪行为而向其归还欠款的事例抑或明知出借人要回猎枪将实施杀人行为而归还的事例中,债务人或借用人都是履行民事上的归还义务,而积极履行民事义务的行为无疑是社会中值得鼓励的行为,即便客观上促进权利人更容易实施犯罪行为,履行义务的行为也为民事法所允许,更不应被刑法禁止。如果因履行义务扩大了法益侵害后果也只是标的物内在风险的现实化,应由权利人自负其责,而不能将其归属于义务履行者。
应当承认,职业规范与惯常行为规则作为各种领域内具体的行动准则,社会应该估计到并且容认依照行动准则产生的风险,故而,行为人遵照各种行为准则行事,即便升高了正犯行为的风险,也为社会所接受而属于法所容许的风险升高。不过需要注意,遵守相关行动准则即可排除归责并不能合乎逻辑地推出违反相关规范就一定可以进行归责而肯定行为之可罚性,是否可以归责还需要判断所升高的风险是否处在规范保护目的之内。
(三)升高风险是否处在规范保护目的之内
客观归责理论限制刑法处罚范围,“主要是借助于规范保护目的来实现的,即结果不在注意规范保护目的范围之内,则这种结果不具有可归责性”。*姜涛 :《规范保护目的 :学理诠释与解释实践》,《法学评论》2015年第5期。在以客观归责理论检讨是否可以将结果归结于行为时,需要在“不允许性风险的实现”中,将“不符合谨慎规范保护目的的后果”的情形排除归责,并且“不允许性风险的实现永远是与限制许可风险的谨慎规范的保护目的有关的,而不是与刑法的行为构成的保护目的有关的”。*[德]克劳斯·罗克辛 :《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56页。据此,在判断中立帮助行为刑事可罚性时也应该将升高风险不在规范保护目的的事例排除归责而否定其可罚性,并且此处的“规范”应指刑法前规范而非刑法规范。
例如,行为人以某种被行政法规禁止的行为为其职业,并因执行该职业而促进他人犯罪的事例中,就需要判断行政法规禁止行为的目的是否在于防止行为被用之于犯罪或者赋予行为人防止犯罪之义务。例如,没有出租汽车运营资格的司机驾驶私家车从事出租汽车运营的情形(俗称“黑租儿”),虽然司机事实上因为非法运营而违反相关行政法规并可能受到行政处罚,也能够肯定司机的行为升高了风险,但是这并不能直接肯定“黑租儿”属于可罚的帮助行为,是否具有刑事可罚性还需要考察取缔“黑租儿”的规范目的。通常而言,行政法规限定出租汽车运营资格之目的无非在于加强对出租汽车的管理,规范出租汽车运营市场,提高出租汽车服务水平,保障乘客、经营者以及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而并非防止出租汽车之运营被用于犯罪。因此,尽管是不具有出租汽车运营资质的司机,只要其事实上长期固定从事有偿载客业务而非专为他人犯罪服务,将犯罪者运送至犯罪现场的行为即便升高正犯行为的风险,也难以肯定其为法所不容许、难以进行归责。若非如此,以帮助犯的形式处罚不具有运营资质的司机,无异于以刑罚的方式强行处罚行政违法行为,必然遭到“行政法规刑法化”的指责。
上述限制中立帮助行为刑事可罚性的三项标准的核心在于判断中立帮助行为升高正犯实施犯罪行为的风险是否为法所不允许,这是在肯定中立帮助行为对正犯实行犯罪行为具有事实性因果贡献的基础上进一步限缩处罚范围。在内部位阶上,此三项标准属于阶层式递进关系,只有满足前项标准后,才有考察后项标准的必要,亦即前项标准既是后项标准的前提,也是后项标准具体展开的基础。如果前项标准已经得出否定结论,则可直接否定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而无需继续检验后续标准。只有同时满足该三项标准,才能得出肯定中立帮助行为刑事可罚性的结论。可以预见,通过操作上述三项标准,大多数中立帮助行为都得以排除客观归责而免于刑事处罚,只有在违反相关刑法前规范升高正犯行为之风险且该规范之目的在于避免行为被用于犯罪的事例中,才能肯定行为的可罚性,进而以相应的帮助犯处罚中立帮助行为人。唯其如此,才能在处理中立帮助行为刑事可罚性的问题上,确保在保障法益不被侵害的同时,最大限度避免对公民行动自由的不当限制,从而实现刑法自由保障机能与法益保护机能的动态平衡。
(责任编辑 :操宏均)
曹波,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D924.1
A
1004-9428(2016)06-0107-15
*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015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