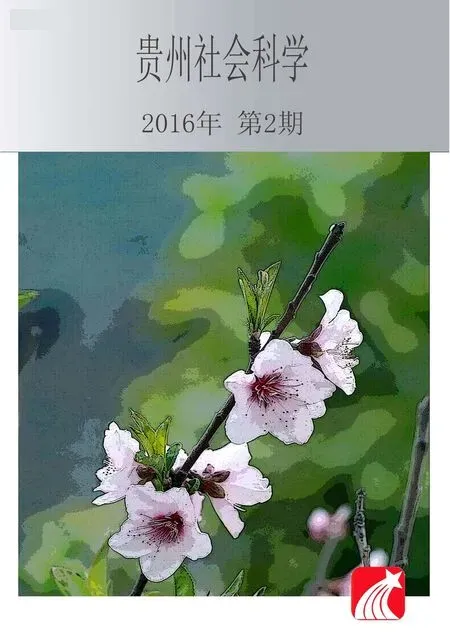透过软法理论看传统礼法合治思想
苏 洁 武丽佳
(重庆交通大学,重庆 400074)
透过软法理论看传统礼法合治思想
苏洁武丽佳
(重庆交通大学,重庆400074)
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礼法合治”思想,实际上体现出“软法”与“硬法”相互辅助配合的关系。通过比对分析即可发现,传统的礼主要以规劝、教育、引导为手段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是典型的“软法”之治。“软法”作为现代“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适当范围内将公认的道德准则纳入规则体系,成为社会运转中不可或缺的“礼”,在“硬法”(国家强制法)不能或不便触及的领域有效实现“德”与“法”的良性互动,将成为推动和保障国家法顺利实施的重要因素。
礼法关系;礼法合治;软法
一、“软法”理论概说
“软法”(soft law)一词原本是西方国际法学的“舶来品”,其与“硬法”(hard law)相对称。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国际法领域,仅限于指代“非条约”性质的协议,后来被引入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学等现代法学学科的研究范围,形成对传统“法”概念的反思和修正,后来这一概念日益被国内学者所认同、采纳、发挥,而后逐渐形成系统理论。在国内,著名法学家罗豪才教授最早提出“软法之治”,他倡导“软硬兼施、刚柔并济”。那么,软法是什么?研究软法对中国法治有什么意义?
就目前而言,学界对于软法的概念尚无较为一致的说法。姜明安教授认为:“软法是法;软法是非典型意义的法。”[1]但其“非典型性”体现在何处,并未言明。罗豪才教授认为:“软法是一个概括性的词语,被用于指称许多法现象,这些法现象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作为一种事实存在的,可以有效约束人们行动的行为规则,而这些行为规则的实施总体上不直接依赖于国家强制力的保障”[2]。比如民间行业协会、自治团体的行为规范,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在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规范作用,可以称之为传统法治概念之外新出现的“软法之治”。梁剑兵先生在其《软法律论纲》一文中认为,所谓“软法”,是在中国社会中客观存在的、主要是由国家认可和社会默契方式形成的、并以柔性的或者非正式的强制手段实现其功能和作用的法律体系。
关于“软法”定义虽无定论,但学者们基本可以达成的共识是,“软法”不是依靠国家公权力强行推行,而是通过当事者双方双向、协商式的方式进行;不是以惩罚面目出现,而是以倡导、引导乃至鼓励、劝诫为宗旨。从主体上看,“软法”的制定者一般不是国家正式立法机关,而是共同体内所有成员自愿达成的契约、协议,每个成员通常都会自觉遵守,这是区别“软法”与“硬法”的重要标志。从形式上看,“软法”既可能以文本形式存在,也可能以某些具有规范作用的惯例存在;从效力来看,它不具有国家强制力,其主要是通过舆论导向、伦理道德等形式来发挥规范作用。
显然,“软法”是属于教育、引导为主的“法”,但是不具有国家强制力,并不等于没有约束力。“软法”一经形成,相应共同体成员必须遵守,如果违反,则会遭到舆论的谴责、纪律的制裁,甚至被共同体开除并因而承担相应的利益损失。事实上,它与强制惩罚性的法律制度并非相抵触而是相互配合。因此,“软法”的“软”字既具有韧性、柔和、和谐之意,又具备一定的威慑力。
“软法”这种“亦法而非法”的特质及其与“硬法”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儒家道德学说中是有根可循的。在中国特有的政治语境下,要讨论“软法”、“硬法”的关系,不得不回归其法文化本源,即古代儒家的礼法关系,因为如果讨论中国的制度,不归本于“礼”,那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精神。
二、礼的软法特质
几千年中国文明史上,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法文化中最具内涵、最具特色的制度资源,“礼法”*“礼法”概念最早由荀子所提倡,实际上就是指发挥出法律作用的礼。也就是说以礼为法。但是后来,中国古代国家机关大力发展律令制度,并以国家强制力加以推行,最终形成了礼法和律法相并列发展的态势。但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礼法”与“礼法合治”中的“礼法”并不是一回事。长期与国家律法共存,且发挥出独特的现实功效。与国家律法以强力执行为主的特征相比较而言,礼主要是以指导人们社会生活的典范法则与行为指南的方式出现,以道德规劝与伦理教化为其主要施行手段,充分借助宗族、乡里等社会组织的力量,对人们的日常行为加以约束,对其中的违规行为加以惩戒。在一定意义上,礼便是一种与国家强制法——“硬法”共生的“软法”,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它是儒家藉此实现理想社会治理模式的有效途径和手段。
首先,从礼的起源来看。礼的起源与发展带有很强的自发性特征,而不是像律法一样由国家机关依靠强制力来推动制定和实施。中国古代社会与西方商业文明不同,它是在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就直接形成“早熟”的农耕文明社会。农耕社会靠天吃饭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人们对自然,对天,对一切自己无法认知的世界充满了神秘和敬畏感,因而出现了各种神灵崇拜。经年累月,人们将这些具有多神崇拜意义的原始宗教和氏族、部落的习俗继承下来,逐渐积累而演化为中国古代国家的社会规范、思想意识、道德伦理,然后将这些规范、意识和道德伦理抽象成一整套行为规范体系,此即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制度文化——“礼”。
三代(夏、商、周)之礼是将各种超自然的山川神灵的崇拜以及超血缘的部落联盟内祖先神的权威崇拜,转化而为具备世俗公共职能的现实宗法信条,从而成为先民行事做人的规范、准则。这种源自神灵祭祀而逐渐演化出来的礼,正是中国传统法的一个重要源头。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和道德、伦理、宗教等社会价值规范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具有较强的社会基础,获得了民众的自发认同。正如先秦法家学者慎到所说的那样:“法者,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慎到:《慎子》佚文。作为“软法”的礼,本身就是从人心中发展出来,因而不需要过多的强制力去推进执行,即可达到相对较为理想化的治理效果。
其次,从礼的推行实施手段来看。由于礼最早源自于宗教祭祀,是从部落到族群自发形成的一种规范体系,最后在国家政权形成之后,由国家加以确认和推行。所以,礼的现实有效性主要源自于人的普遍信仰,它既符合普遍的道德观,又夹杂有宗教神灵的无形庇佑。因而,礼的推行和落实起初并不一定需要国家强制力的介入,它主要是以道德上的观念熏陶和伦理上的规劝教化作为途径和手段。
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学而》这段话精辟地点出了礼与刑之间在操作实施手段以及实践效果层面上的差异。也就是说,不顾及民众百姓的内心感受和伦理观念,一味地依靠国政和刑罚强制推行法律制度,或许可以让老百姓不敢触犯法律,但这并不代表老百姓能够心悦诚服地拥护和支持法律,并且认同国家法律的精神指向。长此以往,必然造成老百姓虽然在行为上不得不遵守法律,而在内心深处却不尊重法律的后果。
与之相反,以礼为治则会有另一番场景。由于“礼”本身即来源于百姓的内在信仰,是民众自幼就逐步受到熏陶和感染的道德伦理观念,同时又有神灵观念的隐形支撑,这些都保证了礼在实施过程中并不存在太多的逆反因素,所以也就不需要运用太多强制的手段来推行。这样做还有一个更值得关注的效果,那就是礼的潜移默化功能,让百姓尊重认同,更能激发出他们内心的自律意识。礼的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功能,显然更利于行为规范的有效落实,这就是作为“软法”的礼,相对于刑、律等“硬法”的独特优势所在。正如褚生所说:“地形险阻,所以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为治也。犹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义为本,而以固塞文法为枝叶,岂不然哉!”*《史记·陈涉世家》事实上,仅靠严刑峻法和国家强制力推行的“硬法”,并不足以保证国家的有效治理。
再次,从礼的内在精神价值来看。礼带有很强的道德规劝和价值引领的特征,在规范人们行为的时候,也主要以教育、引导为主,而其赖以规劝、教化的内在价值资源则来自于先秦儒家特别是孔子仁爱思想的提炼与升华。
春秋时期出现了“礼崩乐坏”的现象,三代之“礼”的权威性一度受到严峻挑战。如何在各种矛盾激化的重要转折时期,重新构建一个稳固的社会秩序,如何利用已有的制度资源灌输和推广更为深入人心的价值观念,这成为留给古代思想家们的重要任务。至圣先师孔子自觉承担起这个历史重任,他将三代之“礼”及其文献载体——“六经”加以整理、抽象,加上自己的道德理解,将“仁”的内在灵魂注入到原本体系繁杂但却存在精神缺失的传统礼制之中,使其再度焕发出勃勃生机。经过这番努力之后,最终形成以“礼”为形,以“仁”为魂的儒家制度文化体系的核心内涵。其中,仁又为礼的精神内核,而礼则为仁的外在表现,二者紧密结合的结果就是,礼的价值引领和具体示范功能都得到极大提高。
这时的礼从三代的宗教、血缘伦理中脱颖而出,将形而上的“天道”崇拜与人们内心的道德法则相结合,用“天道”来指导“人伦”,用“天理”来唤醒“良知”,从而构成了试图补益于世的儒家思想与道德文化体系的核心内容。孔子之后的儒家学者,“以其价值重塑法律,系统地完成了儒家伦理的制度化与法律化,最终成就了中国古代法的完备体系。”[3]“礼”作为天、地、人的总体性原则,成为囊括宗法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整体性制度安排,这样的礼实质就是“法”。经过孟、荀以及汉儒和宋明理学家的发展,围绕着礼,最终形成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法律、艺术等各种社会规范和道德传统。所以,司马光说:“有形可考,在天为品物,在地为礼法。”*司马光:《易说》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最终,礼将天道转化为人世间现实、有效的社会治理途径,而其推行的手段则在于道德规劝与伦理教化。
近代以来,西方法治文明在世界范围内构成了重大影响,法律规范的明确性、严格性、法典化以及其去道德化得到空前的重视和强调。随之,符合这些方面要求的律令法也流行开来,这就导致今人一说起古代法律体系,就自然而然地聚焦于律令格式等硬性的法律规范,却将礼法、民俗、乡间规约等“软法”一概忽略不计。而且,部分学者由于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对前代法制传统进行有选择性的以偏概全式的研究,这不仅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也会给今后的法治建设埋下潜在的隐患。因为道理很简单,任何时代的见解都无法涵盖全部真理,此时有效未必彼时有效,而这也正是我们一定要全面了解、掌握历史,并对时下流行思潮保持反思能力的原因所在。
三、礼法合治:软法与硬法的共治
(一)礼与法的内在统一
从前述可知,在夏商周三代,法律与道德是混而为一的一整套行为规范体系,宗教禁忌、道德伦理、法律惩罚三者紧密结合,无法分离,集中体现为礼,礼则依据宗教的禁忌观念和道德伦理的要求,形成了一套规模庞杂的规范体系。儒家坚持以礼的基本精神亲亲、尊尊为原则,要求和引导人们循规蹈矩,达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状态。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礼”在三代作为一种制度性框架,本就是以法的姿态调整着个人的行为和社会秩序。在孔子那里,它既是世俗伦常的价值体现,又是德的规范性和规定性。孔子提出克己、归仁、正心、去欲的个人道德修养法则,用以规范上到国君、下到臣民的社会举止行为,从而确立了一整套道德规则,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在日常规范、道德伦理方面的指引和模式,即所谓礼制。
另一方面,“礼”本身因以教化为本,强制力有限,因而也就产生了法律的原初形式——“刑”,作为辅助礼制施行的强力后盾,这集中体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律法开始兴起,礼的作用遭到弱化。春秋战国以后,礼乐制度崩坏严重。为了应对社会危机,于是出现了一种撇开道德单纯追求功利且具有很强强制力的制度规范体系,这就是“律”。这个时候,法律和道德发生了分离,彼此也就没有了相互支撑,因而出现了更为严重的社会危机。道德衰败引发罪恶横行的局面,统治者只能以严刑酷法来加以震慑,但是效果有限。
为挽救社会危机,整饬人心,荀子对儒家之礼加以改造。经过荀子改造后的礼,进一步具有了法的性质和内容。荀子本人的著作里就曾经反复提及“礼法”一词。到他这里的“礼法”显然是一个单一含义的词,并非是指“礼和法”,而是单纯指的“礼”,而且是作为“软法”的礼。何以见得荀子就把礼看作“软法”?因为他还提出要“隆礼重法”。在这里,“法”指的是春秋以后兴起的国家强制性法律规范,属于典型的“硬法”,而“礼”则是指继承自三代而来的传统“软法”。在荀子看来,二者彼此辅助,缺一不可。
“礼”作为一种规则性的制度,虽然有别于春秋以前具有血腥味的“刑”,也有别于战国以后强调整齐划一的律法,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礼的强制性和制约力。正如阎步克所言:“礼虽是自发形成的秩序,但是,一旦制度化便具有强制性。因此,就变成一种实在的规则。”[4]只是这套礼制自身是无法独立实施的,需要国家公权力所赋予的强制措施来辅助完成,需要这种赋予强权意义上的律令制度来贯彻实施其意旨,即所谓“法”。礼作为法的一种形式,其社会价值在于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和父系家长特权,如果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礼”作为一种“软法”,自身无法体现其强制性,只有通过各种违礼的惩罚措施来体现,这种运行模式向前可以追溯至三代的“出礼则入刑”(《后汉书·陈宠传》)的操作模式,在秦汉以后尤其是魏晋之后,则体现为“违令有罪则入律”(《晋书·刑法志》)的制度设计。
很显然,在后世儒者的眼里,“礼”和“法”、“德”和“刑”已非水火不容,而是德主刑辅,礼法合治,虽有主次,却互相支持。不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历史上看,礼和法并不是必然对立的,它们既有各自的一套体系,又在一定程度上相统一,在不同的层面维护着社会各阶层的稳定秩序,礼和法在儒家法律体系中也就成为这样一个不能相互脱离的共同体。前者是缺少牙齿的老虎,是价值精神意义上的“法”,后者则是赋予老虎绝对权威的牙齿,是工具和技术意义上的“法”(古代的法主要是律令制度)。前者是后者的创设依据,后者是前者的实施。套用现代的说法就是,前为“软法”,后为“硬法”,前者重在教化引导,将个人心中的道德愿望付诸于道德实践,后者则成为违礼行为之后的另一种惩处。儒家坚信良好的社会秩序既来自于“依礼而治”,也来自于“依法而治”,“礼法合治”于是成为历代统治者延续不息的治国理念。
(二)“软法”与“硬法”的共治
将中国古代礼法关系加以延伸与发展,对比“软法”理论,我们似乎能够找到一条重构当前中国社会秩序的路径。如前述,古代之“礼”实际就是规制人们日常行为的“软法”,而与其相辅而成的“法”,必然是国家律令制度和各种刑罚式的“硬法”。
今日之中国,粗线条的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国家“硬法”之制也已经基本建成,但与此同时,随着社会化的加速发展,法治资源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日益明显,由于国家“硬法”自身的缺陷以及国家“硬法”供给不足、路径不畅、成本太大等各种客观因素,使得法治社会的实现很难由国家“硬法”来单独完成。有鉴于此,我们便不能忽视与国家强制规定的“硬法”同时存在的各种“礼”——民间社会规范、规则制度所汇聚成的“软法”。
以国家法律制度形式出现的“硬法”,由于其制定主体的国家性,天然地具有强制施行的法律效力,公民如违反“硬法”,必然遭受国家强制性法律制裁,这既是“硬法”权威性的要求,也是国家法治建设的需要,“软法”不得突破、违背硬法之规定,正如“礼”不得与“法”相违背,但同时,法律的有效性,不能靠国家“硬法”单打独斗。“软法”推行自治与自律,和古代礼治一样,依靠社会舆论、道德自律、内部监督、同行监督产生的社会压力,以及各种融入“软法”制度中的激励机制,对人的内心加以约束,进而推动公共目标实现。
综上所述,法治不是纯粹的法的统治,也不仅仅是国家法的统治。当代法治建设在一定层面上,需要“硬法”与“软法”相结合的共同治理。一方面,作为现代“法”体系之重要组成部分,以各种社会规范、行业规则、礼俗制度等所构成的“软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有利于缓和“硬法”过分的“普遍性”与“维稳性”可能导致的不公正,因而现代中国法治化进程要完成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软法”尤显不可或缺。另一方面,“软法”以“德”为标准,成为社会运转中不可或缺的“礼”。“软法”在适当范围内将公认的道德观念或情感纳入规则体系,通过内在疏导、教化的方式,在“硬法”无法触及的领域有效实现“德”与“法”的良性互动,促进社会的有序治理。如若我们可以让国家“硬法”与各种民间的“软法”形成互动有序的格局,共同追求公平、秩序、自由,则既尊重了国家法的理性精神,真正做到依法治国,又有利于减少立法、执法的成本,促进公民自觉守法,维护基层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对法治建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而更有利于和谐社会秩序的形成。
[1]姜明安.软法的兴起与软法之治[J].中国法学,2006(2):27-38.
[2]罗豪才.公域之治中的软法[N].法制日报,2005-12-15.
[3]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251-252.
[4]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32.
[责任编辑:李桃]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渝黔毗邻地区仡佬族民族法文化与地方社会管理研究”(2012QNFX043)。
苏洁,法学博士,重庆交通大学思政教研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法律史;武丽佳,重庆交通大学思政教研部,主要研究方向: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D920.0,D909.2
A
1002-6924(2016)02-155-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