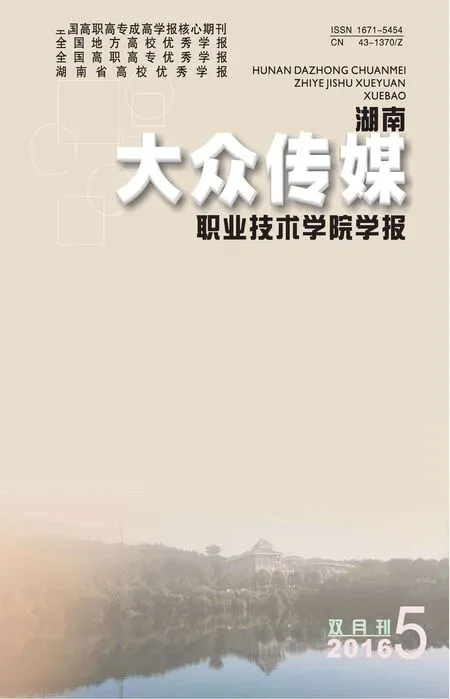现代性视阈下的池田大作德育思想
李 文
现代性视阈下的池田大作德育思想
李 文
(中山大学 南方学院 广东 广州 510970)
现代性是当今人类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在现代性背景下,现代性问题主要表现为道德困境,即一方面世人渴望道德理想,另一方面又往往陷入道德虚无主义的境地。池田大作先生以一种“敬畏”的心态,从道德教育的角度对现代性问题作出了回应,其德育思想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强调个人的心性修养以及教育在个体道德养成过程中的作用。
现代性;池田大作德育思想;道德理想主义
池田大作先生看来,教育不仅仅是神圣的同时也是可怕的事业。神圣是因为教育直面的对象是人类的灵魂,可怕则是因为教育对于人类灵魂的塑造具有直接的影响,善的教育塑造受教育者善的品行,反之,恶的教育则塑造恶的品行,甚至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善的教育,避免恶的教育?从现代性的角度去审视和关照这一问题则显得尤为必要,只有弄清楚问题的症结点,弄清道德问题的由来这一根本性问题,才有可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提出对应的教育之法,以彻底改良人心,达到“德性”的生活,反之则有可能脱离实际,走向道德理想主义。
一、理想与虚无:现代性的道德困境
现代性是当今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之所以会成为一个热点,不是因为现代性给人类带来的福祉,恰恰相反是因为伴随现代性而来的问题。那么,何为现代性以及现代性问题,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就字面意义而言,现代性是指现代社会的总体性的特征,表现为外在的社会制度结构层面的总体性特征以及内在的社会心理层面的总体性特征两个维度。从外在的社会制度结构层面来看,现代性表现为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知识科学化,人的个体化等方面,也就是强调通过理性在诸如经济、政治等世俗生活中构建一整套合理性的或者工具性的秩序规范,因此从这一意义而言,现代性就是合理性,它所追求的是“是然”而不是“应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超越性价值和理想的萎缩。在这种理性原则建构的秩序世界中,“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1]这一状况反应到社会道德领域就是道德文化危机,其中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道德的虚无化,传统的道德观念在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狂潮中土崩瓦解,诸如诚信,友善,公正等价值观念逐渐从世人的视界中淡出,由此而最终导致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滑坡。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追求日渐趋向于物质的满足,追求微小而确定的幸福,选择作一个凡人、追求凡人幸福,成了现代社会的主导价值。
从内在的社会心理层面来看,现代性则主要表现为心性秩序的感觉化倾向,这一倾向则进一步加剧超越性价值的虚无化,反应到个人生活领域就是生活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觉。”[2]这种生活的无意义感,并非现实的生活世界没有提供有价值的东西,而是价值的多元化和虚无化,个体生活是否有价值不在于外在的某种价值规范,而在于个体的主观体验,即以自我感觉来判定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值得指出的是,在这种感觉化的倾向之下,必然会导致个体感性欲望的无限制膨胀,人体生活的全部意义也逐渐趋向于自我感性欲望的满足和实现,或者说个人生活的价值就是感性欲望的满足和实现。但是,如果把感性欲望的满足作为个体行为的出发点甚至是行为的准则,那么,道德与否也就成为一个伪命题。正如黑格尔所言:“如果感觉、愉快和不愉快可以作为衡量正义、善良、真实的标准,可以作为衡量什么是人生的目的标准,那么,真正说来,道德学就被取消了,或者说,道德的原则事实上也就成了一个不道德的原则了;——我们相信,如果这样,一切任意妄为将都可以通行无阻。”[3]很难想象一个把自我感觉作为衡量道德标准的社会是怎样一番景象,也许问题就在于此,把道德上的善恶价值归结为感觉上的快乐与痛苦,使个人沉溺于物质感官世界,这无异于放弃人的神性而重归于人的兽性。从表面上看,在感觉主义之下,个人变得自由而不受约束,实质是在不经意间沦为了兽性的奴隶,受自身动物本能的支配。
当尼采宣传“以感觉为准绳”,“上帝死了”的时候,他或许已经敏锐的察觉到现代性的问题实质。不论现代性表现为外在的社会秩序结构还是内在的心理层面,就其实质问题都指向道德文化危机,一方面精神游离的世人渴望理想道德,努力找寻心灵的归宿,另一面却又在现代性背景下极易背离道德理想,陷入道德虚无主义或功利主义的泥沼,这也正是现代性的道德困境所在。
二、超越与回归:对现代性问题的回应
现代性的道德困境是当今世界和人类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直面现代性的道德困境,不同领域的专家和学者都做出了各自的回应。作为当今著名的教育家,池田大作先生从德育的角度对现代性问题予以了回应。池田大作先生对现代性问题的回应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强调个人对现实的超越,追求人生的“绝对幸福”。其二,强调教育在道德养成过程中的作用,倡导教育应摒弃功利化,回归教育的本真。
直面现代性的道德困境,池田大作先生有着深入的理解,在他看来与人类物质文明发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的精神需求遭到了遗忘,甚至随着物质的丰富,精神方面反而变得越来越贫乏。反观现代社会,人类通过自身的理性创造了比古人更多的东西,但是这些发明创造除了满足人类的物质欲望之外实在看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当世人沉浸于物欲满足的快感之时,人类的精神世界则不断的在现代性展开的过程中消解。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的人”以及马尔库塞所说的“当向度的人”,在世俗化,功利化的作用之下,作为个体存在的人在不经意间已经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本质特性,那就是人的精神维度。那么,如何才能走出现代性的道德困境,重塑人的精神世界?池田大作先生则进一步提出了“人间革命”的观点,即以自律精神来提升自我道德修养,到达善的境地。他说:“为不信与自私所愚弄,为权利欲念所驱使,生命内在之‘恶’,以自律之精神与之斗争,凭借利他与慈悲的双翼。向‘善’的天空飞翔,以自我完善为终极目标的人性的研磨。”[4]人间革命的观点可以说触及到了现代性问题的症结所在,在现代社会不是没有普遍性的伦理价值规范,作为公共领域的个人亦深知这种普遍性的伦理价值规范的重要性,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普遍性的伦理价值规范并不一定具有现实的有效性。“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道德标准最后变成了个人的偏爱和好恶,人的规范并不规范人,人制定了规范却并不遵守规范。”[5]池田大作先生敏锐地意识到,现代社会普遍性的伦理价值规范是否能为个人所遵循,关键还在于个人自身的道德自律。“自律之精神”是主体的一种内在品质,是个体在践行道德过程中一种自觉、自愿的力量。毋庸置疑,“自律之精神”是“人间革命”的要旨之所在,普遍性伦理价值规范在现实层面能否有效践行则有赖于主体人格上的“自律之精神”。通过自律的途径,去除生命内在之“恶”,超越现实此岸世界,以此途径到达“善”的彼岸。
那么,这种“自律之精神”何以可能呢?池田大作先生则强调通过教育的途径从外在层面对主体施加影响,以此养成良好的德性。池田大作先生首先对现代社会功利化的的教育方式进行了批判,他说道:“现代教育陷入功利主义,这是可悲的事情。这种风气带来两个弊病,一个是学问成了政治和经济的工具,失掉了其应有的主动性,因而也失去了尊严性;另一个是认为惟有实利的知识和技术才有价值,所以做这种学问研究的人都成了知识和技术的奴隶。因此产生的结果是人类尊严的丧失。”[6]61不难看出,在池田大作看来在现代性展开的过程中,人类的教育事业亦逐渐的背离了自己的宗旨,陷入功利主义的窠臼不能自拔。传统教育所倡导的个体内在道德修持被掌握各种具体的知识和技术所取代,教育的唯一目的似乎只是传授个体赖以生存的劳动技能,即培养一个合格的“劳动者”。反之,对于人类应当怎样存在,人生应该怎样度过这些人类的终极关怀问题则显得过于淡漠。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现代社会中,教育已成了追逐利益和实现欲望满足的工具。针对教育的功利化弊病,池田大作进一步提出了回归教育本真的观点,他说“无论如何要恢复其原来的宗旨,即学问本来是为了阐明人类的基本生存生态和存在的根本,而教育则是要把这种学问传播开去。”[6]61池田大作先生所强调的回归教育本真,其实质就是寄希望于通过非功利的本真的教育方式来唤起人的本真需求,毫无疑问这种本真需要不是物质性、功利性的,而应当是对精神性、价值性的超越理念的追求,它以人类的基本生存生态和存在的根本为目标指向。除此之外,池田大作先生还强调社会环境对个体“自律之精神”养成的影响,他主张个体德性的养成应该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逐步习得,因此,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大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现代性的道德困境问题上,池田大作从“内外兼修”两个层面做出了回应,一方面他强调通过道德自律的途径,已达“善”的境界,另一方面通过倡导教育本真的回归,以善的教育作用于人心,以此达到改良人心的功效。
三、批判与反思:道德理想主义的扬弃
道德教育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多种因素,在现实的道德教育过程中弄清楚道德的特性,道德的由来以及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才能在做到“有的放矢”,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对社会大众施以影响,以此提高道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在马克思看来,道德是一种“实践精神”,每一个人都有意识,都有感觉,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美感或者道德意识,一个人是否具备美感和道德意识则取决于实践。也就是说,在马克思那里道德不是先验的存在,个体是否具备是非善恶等道德观念则完全有赖于后天的实践,而且道德是个体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主观体验。从此意思而言,道德教育要取得成效,就必然要从个人的主观意识和实践两个方面入手。如前文所述,池田大作先生的德育思想在很多方面就体现了这一点,比如强调心性的自我修养,强调通过教育的实践对个体施加影响以促进“自律之精神”的养成。除此之外,池田大作在谈及德育的途径时,他还反复强调要通过情感教育的方式对个体施以影响,强调个人道德的养成与社会、家庭以及学校的关系,这些道德教育的途径方法是与道德的特性及形成发展过程相吻合的。
值得指出的是,直面现代性的道德困境,池田大作先生寄望于通过“善”的教育以提升世人的道德和精神境界。但是,道德毕竟具有极强的主观性,仅仅寄望于通过善的教育来改良世道人心,难免过于理想主义。道德作为一种理想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其本身就是一种理想,是世人对于现实生活不足的美好期待和追求。正因为如此,道德理想与现实生活之间总会存在一定的张力,古往今来,不论是哪一历史时期或者社会制度之下,几乎没有一个现实社会能让当时的人们在道德上感到满意。正如朱熹所指出的那样,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在池田大作的德育思想中,虽然强调“善”的教育对道德养成的作用,但是所谓“自律之精神”仍然是以一种先验预设的方式来确定道德行为的可能性,即在逻辑上先天的设定人的道德意识和德性人格的存在。从这一意义而言,池田大作的德育思想则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为了实现其教育理想或者说道德理想,池田大作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观念层面,而是采取了实际行动。池田大作是创价学会的创立者,同时也是宗教领袖人物,凭借这一身份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践行自己的理念。问题或许也正在于此,在池田大作的德育思想中,宗教化色彩则若隐若现。比如主张人们通过佛法的修行,以获得“绝对的幸福”。虽然池田大作坚决反对道德教育与政治实践相结合即道德的意识形态化,但是却又存在一定宗教化的嫌疑。把道德理想宗教化从根本上违背了道德自身存在、发展和起作用的规律,因为道德的宗教化极有可能使道德演变为一套外在规范,在宗教化的道德领域,道德不道德的标准完全掌控在权威的手里,这与他所提倡的“自律之精神”相违背,道德自律成为了外在的他律。
(责任编辑 远 扬)
[1]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三联书店,1998:48.
[2]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三联书店,1998:9.
[3]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M].香港:商务印书馆1959:73.
[4]冉毅,曾建平.关爱人生,善待生命——池田大作思想研究[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56.
[5]李佑新.走出现代性道德困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0.
[6][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展望二十一世纪[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61.
Mr Daisaku ikeda's thoughts of moral education in the sight of modernity
Modernity is a common problem which human beings fac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ty, the problem of modernity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ethical dilemma, the world is eager to moral ideal, but often get into the moral nihilism. Mr Daisaku ikeda respondes to the problem of moder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 education, his main argument is to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moral self-cultivation and edu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moral 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 idealism to analyze Mr Daisaku ikeda's thoughts of moral education, his thoughts of moral education become a bit idealistic.
modernity, Daisaku ikeda, thought of moral education, moral idealism
G41
2016-08-19
李文(1984 -),男,湖南永州人,中山大学南方学院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部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和毛泽东思想。
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研究项目“‘思政、通识、学工’三位一体德育模式创新研究”(编号:2014JKDYY22)和广东省2014年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高校思政教育有效性实现模式研究”(编号:GDJG20141284)以及中山大学南方学院2014年度教学改革重点项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通识教育有效结合的路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