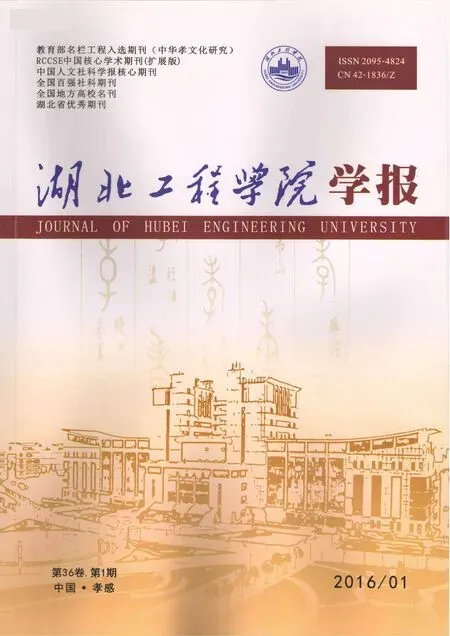现代诗歌中的设问及其审美价值
张春泉,张艺娇
(1.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2.湖北工程职业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现代诗歌中的设问及其审美价值
张春泉1,张艺娇2
(1.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2.湖北工程职业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摘要:现代诗歌中的设问在语义逻辑关系及语气类型方面有其特点,主要集中表现在选择式设问和测度式设问中。现代诗歌中的设问在能指形式的语句和语篇等层级上灵活多样、俯仰生姿,主要通过选择式设问、测度式设问、语用倒装式设问、组合设问、诗节末尾设问显示出来。现代诗歌中设问传达蕴涵丰富的言外之意,“设问”语言机制具有较强的可领会性,其蕴涵的言外之意是一种从容的羡余。
关键词:现代诗歌;设问;能指;所指;审美价值
语言与诗有着内在的天然的不可割裂的关联。诚如朱光潜所言,“诗是最精妙的观感表现于最精妙的语言”[1]。现代诗歌语言的研究亟待加强,当前相关研究成果并不丰硕,在“中国知网”上的检索结果或可在某种意义上说明这一点。在中国知网上搜索题名含有“现代诗歌语言”的文献仅得17条结果(操作时间:2015年12月4日)。其中代表性的文献有:张卫中《大陆与台湾后现代诗歌语言比较论》[2]、周晓风《现代诗歌语言的艺术转换》[3]、胡峰《口语入诗的艰难之旅——对现代诗歌语言特征的一种考察》[4]、欧阳骏鹏《现代诗歌语言研究的基本路径》[5]。另有4篇硕士论文:马飞鹏《现代诗歌语言的量词研究》[6]、周辉《现代诗歌语言语音研究》[7]、张庆艳《现代诗歌语言的词汇研究》[8]、李茜《现代诗歌语言的语义偏离研究》[9]。以上文献或者主要着意于诗歌语言的宏观探索,或者从语法学、语音学、词汇学、语义学的视角专题考察现代诗歌语言。我们以为,还可以从修辞学、语用学、美学的角度综合协同研究现代诗歌语言。这里,我们以现代诗歌中的设问作为切入点,以传统诗歌语言作为潜在的参照系,探讨现代诗歌语言的某些艺术特征。
现代诗歌中的设问在个性化和抒情性方面赢得了空前广阔的天地,其在审美价值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几乎是革命性的,因此是全新的发展。我们关于“设问”的界定从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胸中早有定见,话中故意设问的,名叫设问。这种设问,共分两类:(一)是为提醒下文而问的,我们称为提问,这种设问必定有答案在它的下文;(二)是为激发本意而问的,我们称为激问,这种设问必定有答案在它的反面。”[10]这一界定显然从宽,实际上包括一般所说的设问和反诘,在书面表达形式上既可缀以问号,亦可是感叹号(惊叹号)。
现代诗歌中设问在能指形式上灵活多样,在所指内容上从容羡余,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一、灵活多样的能指形式
现代诗歌中的设问在能指形式的语句和篇章等层级上灵活多样、俯仰生姿,主要通过选择式设问、测度式设问、倒装式设问、诗节组合设问、诗节末尾设问显示出来。现代诗歌中的设问在语义逻辑关系及语气类型方面有其特点,主要集中表现在选择式设问和测度式设问中。其灵活多样的能指形式,概括地说,包括两个大的方面,即设问的语句组构形式和篇章分布形式。
1.设问的语句组构形式。现代诗歌的设问着眼于语句自身,伴随相应的语气,其组织结构形式主要有选择式、测度式、倒装式等类型。
(1)选择式设问。选择式设问于现代诗歌中得以自由运用。由多项选择构成的选择问一般出现于其他文体之中,且多于心中有预设的接受主体,具有强烈的互动性。古诗受其格式特点的限制,不可能使用多项选择问,现代诗歌由于摆脱了大量形式上的束缚,其作品中也出现了这种设问,但诗人往往只是肆意发问,并无明显的接受主体,也并不需要真正作出选择。
例如:我们欢唱,我们翱翔。我们翱翔,我们欢唱。一切的一,常在欢唱。一的一切,常在欢唱。是你在欢唱?是我在欢唱?是他在欢唱?是火在欢唱?欢唱在欢唱!(郭沫若《凤凰涅槃·凤凰更生歌》)
上例划线句子有问有答,由四个测度问构成的多项选择问与感叹句组成。诗人将四个选项并列,并非要得到确切的回答,目的仅在于造成一种气势,将其作为释放激情的一种方式。此问以穷尽性列举的方式发问,是为后面感叹句的发出作语义上的铺陈,诗节末尾的感叹句将前面列出的选项一举否定,以欢呼式的语气喊出答案,铿锵有力,体现了一种情态上的力量美。诗人以此独特的方式诠释了欢快的心情,我们读至此处也会产生一种全世界都在欢唱的感觉,具有较强的心理现实性。[11]或者说,此问不仅形象地传达了诗人自己的情绪状态,而且感染了读者,因此兼具生动、形象的灵动美。
(2)测度式设问。现代诗歌中出现了一种除书面标点以外无其他形式标记的测度式设问,且位于诗节的开端,发挥着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例如: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徐志摩《再别康桥》)
上例划线处为无书面标点以外疑问标记的测度式设问,此问位于整节诗的开端,承接上一诗节末尾处的意象发问,同时也是对本节诗内容的一种概括,其后所有的诗句都是围绕“寻梦”这一主题展开,所以具有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增添了诗歌的流畅美。同时,对下文概括式的发问也使诗节具有了系统性和整体性,具有结构、思维上的缜密美。以测度的方式发问,并将整节诗作为其象征性答语,还有一种意境上的朦胧美。
(3)倒装式设问。现代诗歌继承了语用倒装式设问这种为了满足特殊语用需要而产生的特殊表达方式,但在运用上有了较大的变化。前几个时期诗歌中的语用倒装式设问多为复句中两个分句倒置,而现代诗歌中则是将一个单句的两个部分倒置。
例如:“女郎,A.在哪里,女郎?B.在哪里,你嘹亮的歌声?C.在哪里,啊,勇敢的女郎?”黑夜吞没了星辉,这海边再没有光芒;海潮吞没了沙滩,沙滩上再不见女郎,——再不见女郎!(徐志摩《海韵》)
上例划线处的三个特指问均为将谓语部分前置的语用倒装式设问。例句中三问均以特指处所的疑问代词“哪里”为形式标记,表面上是询问处所,实则传达的是内心对“女郎”的呼唤和思念,是发乎心灵深处的一种召唤;因此将谓语部分前置就显得十分自然,切合了情感抒发的需要,具有朴素美。同时,三问在句式、语气和语义上都趋同,所以还具有和谐美。此外,C句在被拆分开的两部分之间插入了叹词“啊”,更突出了句子形式上的灵活变化,具有一种灵动、跳跃之美。
2.设问的篇章分布形式。现代诗歌中的设问,除了设问自身的语句能指形式外,其在篇章(这里尤指诗节)中的分布形式也值得关注。
(1)诗节组合设问。现代诗歌在组合设问方面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出现了由问句构成的诗节,可在整体上视为一个大的排比问。
例如:宇宙呀,宇宙,A.你为什么存在?你自从哪儿来?你坐在哪儿在?B.你是个有限大的空球?你是个无限大的整块?C.你若是有限大的空球,那拥抱着你的空间/他从哪儿来?你的外边还有些什么存在?你若是个无限大的整块,这被你拥抱着的空间/他从哪儿来?你的当中为什么又有生命存在?D.你到底还是个有生命的交流?你到底还是个无生命的机械?(郭沫若《凤凰涅槃·凤歌》)
上例划线处为一个大的排比式设问,又可分为四个部分。其中,A为三个特指问直接组合而成的排比式设问;B为两个测度问直接组合而成的对偶式设问,又可整体上作为一个选择式设问;C为两个大的假设式设问组合而成的二句组合设问;D的结构与B类似。这四个部分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语义联系,A从总体上进行发问,B为进一步发问,问句中已开始有了具体的猜想,C是对B中两个问句的分述式追问,而D又回到了刚开始充满疑惑的状态,与A形成对应,但不再是盲目发问,而是由询问变成了二选一的选择问。所以,从结构形式上来看,此问具有首尾照应的和谐美、结构严谨的缜密美以及“问句狂潮”带来的气势美。从内容上来看,诗人将设问与拟人辞格相结合,把“宇宙”预设为一个有生命的对话主体,将自己回归到最初级的状态,以这种“问句狂潮”传达对于世界的惶惑,突出了淳真之美。从表达方式上来看,诗人将这些问句作为一种情绪发泄的方式,用整节疯狂发问又无解答,具有荒诞之美。
(2)诗节末尾设问。现代诗歌中的设问在位置上形成了突出的特点,即多于诗节末尾设问,意在营造一种余味无穷的隽永之感。这些位于诗节末尾的设问在类型上也具有一定的特点,以特指式设问、测度式设问和反诘问为主。例如:
① 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五百年来的眼泪倾泻如瀑。五百年来的眼泪淋漓如烛。流不尽的眼泪,洗不尽的污浊,浇不熄的情炎,荡不去的羞辱,我们这漂泊的浮生,到底要向哪儿安宿?(郭沫若《凤凰涅槃·凰歌》)
② “天天下雨,自从你走了。”“自从你来了,天天下雨。”两地友人雨,我乐意负责。第三处没消息,寄一把伞去?(卞之琳《雨同我》)
③ 太阳啊,六龙骖驾的太阳!省得我受这一天天的缓刑,就把五年当一天跑完又何妨?(闻一多《太阳吟》)
例①划线处为以特指处所的疑问代词“哪儿”为形式标记的特指式设问。其中,表深究义的副词“到底”与疑问代词“哪儿”配套表达了一种质问的语气,传达出一种愤怒之情,还夹杂着一种近乎绝望的无奈之感,释放出巨大的情感力量,具有突出的力量美。同时,以询问句收尾,表现出强烈的互动需求,因此兼具动态美。例②划线处为无书面标点以外形式标记的测度式设问。此问的发出完全出于诗人的想象,诗节的前两句记录了两位朋友的话,把雨的有无和诗人的来去相联系,流露出一种浓浓的友情,所以诗人突发奇想:我离别的第三个朋友没有消息过来,是不是那里也下雨了呢,要不要我寄一把伞给他。此问的设置展现了诗人于生活小事中发现的无限情趣,同时二四句尾字押韵,因此具有灵动美和情韵美。例③中的问句为让步关系与递进关系相结合的紧缩式设问。其中,以表“即使”义的让步连词“就”作为让步条件的标志,以帮助表递进关系的副词“又”与表反诘语气的词组“何妨”一起作为进逼式反问的标志。此问由字面上传达出来的是一种不屑的态度,实为于困境中对一切挫折与苦难发出的宣战式呐喊。由让步条件可看出,问句中作出的选择应该是最坏的打算,因此又折射出诗人的一种绝望。以上三例均以问句传达多种言外之意,因此具有更为突出的含蓄、蕴藉之美。
二、从容羡余的所指内容
用设问制造含蓄、蕴藉之美是传统诗歌的文体特点之一,现代诗歌也继承了这一基本特色,但由于其在形式上更加灵活,且极力追求个性化和抒情效果,所以传达的言外之意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丰富性和可领会性。一般说来,现代诗歌中设问传达蕴涵丰富的言外之意,“设问”语言机制具有较强的可领会性,其蕴涵的言外之意是一种从容的羡余。下面大略概括四种审美价值较为突出的言外之意。
1.同情义。现代诗歌中常有向无生命的物体表达同情之感的设问,这种情感的传达往往通过与拟人辞格的结合来实现。作者将其预设为与人类有着相同情感的对象物,并把自身与对象放在同一环境中,去感受它们的喜怒哀乐。
例如:红烛啊!匠人造了你,原是为烧的。既已烧着,又何苦流泪呢?哦,我知道了!是残风来侵你的光芒,你烧得不稳时,才着急得流泪!(闻一多《红烛》)
上例划线处为基于一般条件发问的递进式设问与两个感叹句构成的问答句。其中,表反问语气的词组“何苦”与语气词“呢”配套表劝告义,但并非真的劝说,而是通过这种方式传达自己不忍看此情景的感受;答句以断然醒悟的极确定的语调对“流泪”的原因进行了说明,显然是为其编造了一个理由,给予其悲伤的权利,用一种别样的方式传达出了同情。至此,问句与答句相互配合,以不同的形式传达了同一种情感,体现出和谐之美。将无生命的红烛预设为与人类有着相同情感的对象,并在自己与对象之间建构虚拟的对话模式,具有灵动之美。
2.自豪义。一问一答的作用并不仅仅在于信息的传递或语义上的过渡,也可用于传达一种自豪之感,这种自豪往往源于答语所涉对象的形象。
例如:目前,我们陷在地狱一般黑的坑里,在我们头上耸着社会的岩层。没有快乐,幸福……但我们却知道我们将要得胜。我们一步一步的共同劳动着,向着我们的胜利的早晨走近。/我们是谁?我们是十二万五千的工人农民!(殷夫《我们》)
上例划线处为特指问与感叹句构成的问答句。设置问句的目的在于引出答语,答句以口号式的感叹句呈现,传达的是作为工人农民的一种无比自豪的感情,一言以蔽之,“舍我其谁”。此处的问答句单独作为一个小节,铿锵有力地将革命激情喊了出来,具有激昂、雄浑的力量之美。同时,以一问一答的方式传达政治激情,具有突出的形象性和动态感。
3.挚爱义。现代诗歌中有时会通过设问的方式表达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与单纯的感叹式不同,它往往通过曲折迂回的途径实现情感的抒发,似乎越深婉曲折就越能展现内心复杂情感的交织,传达出来的挚爱之情也越深沉。
例如: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我来了,因为我听见你叫我;鞭着时间的罡风,擎一把火,我来了,不知道是一场空喜。我会见的是噩梦,哪里是你?(闻一多《发现》)
上例划线处为以疑问代词“哪里”为形式标记的反诘问。此问在字面上表现的是一种近乎惊诧的否认,否认是由于内心的不愿接受,进而传达一种逃避的态度,而逃避是因为不忍看见这满目疮痍。以近乎厌恶的口吻传达的却是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且这种厌恶在形式上表现得越突出,表达的情感就越深沉,因此在形式和内容上产生了激烈的撞击。在这种撞击之下,语言迸射出强烈的情感力量,一种悲怆的力量美油然而出。
4.无奈义。如果说以上所指内容主要着眼于积极方面,那么无奈义则多少有些消极意味。例如:“教我如何不想她?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月光恋爱着海洋,海洋恋爱着月光。啊!这般蜜也似的银夜。教我如何不想她?/水面落花慢慢流,水底鱼儿慢慢游。啊!燕子你说些什么话。教我如何不想她?/枯树在冷风里摇,野火在暮色中烧。啊!西天还有些儿残霞,教我如何不想她?”(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她》)
整首诗共四节,多次出现“教我如何不想她?”,皆于末尾发问。从问句本身而言,特指方式的疑问代词“如何”与否定副词“不”连用,传达了一种从思念到无奈的强烈情愫,看似是内心的纠结,实则表明的是极为坚定的心迹,朴实自然与含蓄蕴藉相互交织;从诗歌的结构来看,多次发问,首尾呼应,引人深思而意味悠长,突出了诗歌的情韵之质。这些也说明,“诗的语言是非实用性的语言,是诗人奇妙的心灵的反映”[12]。
总之,有机结合了内容和形式的设问,是一种表达技巧,而又远远超越了技巧。现代诗歌中的设问在形式上不再戴着镣铐跳舞,而是充分利用了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在内容上充实丰富,其言外之意耐人寻味。设问是能指形式和所指内容的完美结合,颇具审美价值。
[参考文献]
[1]朱光潜.诗论[M].北京:三联书店,1998:308.
[2]张卫中.大陆与台湾后现代诗歌语言比较论[J].华文文学,2013(4):101-105.
[3]周晓风.现代诗歌语言的艺术转换[J].当代文坛,1992(3):37-41.
[4]胡峰.口语入诗的艰难之旅——对现代诗歌语言特征的一种考察[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125-129.
[5]欧阳骏鹏.现代诗歌语言研究的基本路径[J].湖南社会科学,2010(4):165-167.
[6]马飞鹏.现代诗歌语言的量词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1.
[7]周辉.现代诗歌语言语音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8.
[8]张庆艳.现代诗歌语言的词汇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7.
[9]李茜.现代诗歌语言的语义偏离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7.
[10]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134.
[11]张春泉.论接受心理与修辞表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8.
[12]张炼强.修辞论稿[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261.
(责任编辑:张晓军)
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824(2016)01-0068-04
作者简介:张春泉(1974-),男,湖北安陆人,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BYY067)
收稿日期:2015-12-18
张艺娇(1990-),女,重庆潼南人,湖北工程职业学院助教,文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