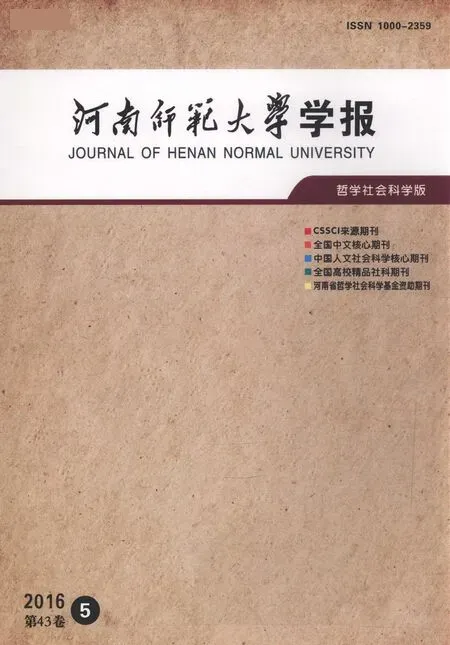魏晋六朝作家群郊游活动及文化精神表达
郭伟锋,郑向敏
(华侨大学 旅游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魏晋六朝作家群郊游活动及文化精神表达
郭伟锋,郑向敏
(华侨大学 旅游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魏晋六朝是一个政治动荡、精神自由、创作激情旺盛的时代,孕育了一批批成就斐然的作家群,而郊游活动为这些作家群的性情抒发和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作家群以文章赏会的形式进行郊游雅集,不断丰富和创新先秦以来我国游仙文学、玄言文学和山水文学的内容和形式,艺术地展现个性和人生。郊游活动通过文学创作表达出的乐生、超越、自由等独具时代特征的文化精神,赋予了更多的生命价值和文化内涵,建构了一个多元和自觉的文学时代。
魏晋六朝;作家群;郊游活动;文化精神
魏晋六朝时期,国家从一统走向分裂,社会动荡,文化霸权丧失,学术走向自由,文人雅集的郊游活动频繁,较有代表性的有南皮之游、西园之游、竹林之游、金谷之游、洛下之游、新亭之游、兰亭之游、乌衣之游、西邸之游等。他们“以文章赏会”,在活动中寻找灵感,进行文学创作,诞生了多个成就斐然的作家群,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葩。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不仅在体裁和内容上充满着创新和活力,而且在风格上也开始主张艺术地表现个性和人生,进入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进而建构了一个统领文化思潮的时代精神。
一、问题的提出
一个时代的文化,彼此之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一个有机整体。魏晋六朝,知识分子“膏腆贵游,咸以文学相尚”(《南史·王承传》)。可以说,郊游与文学创作是魏晋六朝文化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郊游是古代人类的一种游憩方式,先秦时期已成为人们的习俗,经过魏晋的推广和发扬,唐宋空前兴盛。与踏青不同,郊游没有时令限制,不过,端午、重阳、中秋等重大节庆期间,郊游场面较为宏大。《东京梦华录》记载:“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次第春客漫野。暖律暄晴,万花争出,粉墙细柳斜笼。绮陌香轮暖辗,芳草如茵,骏骑骄嘶,香花如绣,莺啼芳树,燕舞晴空。红妆按乐于宝榭层楼,白面行歌近画桥流水。”[1]而且,郊游项目较为广泛,如登高、划船、观潮、朝觐等。人们走进大自然,在踏青、交友、游赏过程中陶冶情操、享受生活的愉悦和快乐。对于知识分子而言,郊游活动也是一种创作的过程。魏晋六朝时期,郊游活动频繁、形式多样,在作家群引领下,从休闲郊游走向创作郊游,走向思想抒发。这一时期,郊游活动的兴起源自于主体生命意识和客体审美意识的觉醒[2],并且,郊游活动对于魏晋六朝作家群来说,具有修身养性、寻美追奇、提高素养和参佛悟道的价值[3],或形成畅神说的文化审美观[4]。应该承认,在古代社会,受社会、经济、文化、交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人类交往囿于较为狭小的时空领域,无法形成大规模的郊游活动。因此,在今天看来,魏晋六朝郊游活动主体往往仅限于帝王将相、王公贵族及文人雅士等群体。然而,文化往往是文化群体的整体活动。文化的创新、输出和引进,都是依靠某个文化代表集团来完成的[5]。魏晋六朝作家群作为高雅文化的代表集团,他们创造游仙文学、玄言文学及山水文学,塑造乐生、自由和超越的文化精神,同时把我国古代社会的郊游活动推向了一个高潮。本研究据此提出“文化精神”这一问题域,目的在于丰富郊游活动的内涵,把魏晋作家群文学创作转向文化向度的人生思考,这样,郊游活动的时代意义和文学价值在文化精神的阐发中得到了体现。
二、魏晋六朝作家群的郊游活动
魏晋六朝在历史上通常是指从东汉瓦解到隋朝建立,前后约400年的时间。这一时期的郊游活动是丰富多彩的,已达到“渐趋大众化的休闲规模”[6],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文人雅集”。文人雅集是魏晋作家群之间以文学创作为主体的郊游活动,开启了“游创结合”的时代,超越了先秦以来郊游活动的功利性目的,逐渐回归到文化性和愉悦性的本质属性上来。为避开社会纷扰,这些文化素质较高、情趣相投的文人雅士携手共游,从“比德”走向审美。在郊游过程中,清谈、饮酒、赋诗、啸歌,以联吟的形式进行文学创作,呈现了一个典型意义的文化自觉。
(一)郊游与游仙文学
游仙不仅是我国特有的郊游形式,而且是特有的文学题材。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曹魏时期的游仙文学数量大、题材广、内容新,赋予了更多的时代意义和文化内涵。其作家群的主要代表是环聚在曹氏父子周围的“建安七子”,因长期居于邺城,被称之为邺下作家群。建安游仙文学根祗在道教,曹操的《秋胡歌》《善哉行》《陌上桑》表达出寻“真人”、邀“神人”、羡仙慕道的游仙意识。“驾虹霓,乘赤云,登彼九疑历玉门。济天汉,至昆仑,见西王母谒东君”(《曹操·陌上桑》)。游仙诗与其说是文学创作,不如说是生命意识的文化自觉。我们读曹植诗作如《游仙诗》《远游篇》《五游诗》《仙人篇》等,郭璞、何劭、张华的《游仙诗》,“诗杂仙心”,字里行间流露出作家们羡仙延命、乐生求存的一种精神寄托。如: “九州不足步,愿得凌云翔。逍遥八纮外,游目历遐荒。披我丹霞衣,袭我素霓裳。……王子奉仙药,羡门进奇方。服食享遐纪,延寿保无疆。”(曹植《五游》) “羡昔王子乔,友道发伊洛。迢递陵峻岳,连翩御飞鹤。抗迹遗万里,岂恋生民乐。长怀慕仙类,眇然心绵邀。”(何劭《游仙诗》)
游仙文学表达出魏晋作家对生命不息的渴望,对延长生命长度的希冀,是一种“重生思想、养生、避祸观念、齐一生死的自然生命观”[7]。而郊游活动表现出的乐生精神是一种生命本体论的哲学思考,突破现实与理想、生与死的二元对立,把乐生长存的精神寄托在游仙的过程中,以实现与仙同体的超然存在。
从现实逻辑上判断,曹氏父子身份特殊,恐难遍游群山,寻仙访道。不过,园囿之间的郊游活动仍十分频繁。曹魏时期,邺下作家群郊游活动多以游宴聚会、联吟唱和为主。“朝日乐相乐,酣歌不知醉”(曹丕《悲哉行》),朝游夕宴,行则连舆,盛况空前。南皮之游和西园之游在文坛上被传为佳话。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曹丕、吴质、阮瑀、徐干等邺下作家群在沧州南皮举行游宴活动:“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宴饮之即,诗赋酬酢,为文坛留下“南皮高韵”之佳作。与之相同,西园之游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唱和之作”[8]。西园位于邺城西,“魏曹丕同弟植宾从游幸之地也”[9],邺下作家群经常在此宴饮游览,同题唱和,后人称之为“邺下宴集”。曹氏兄弟曹植、应玚、阮瑀等人在此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如: “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曹植《公宴诗》) “巍巍主人德,嘉会被四方。开馆延群士,置酒于新堂。辩论释郁结,援笔兴文章。穆穆众君子,好合同欢康。”(应玚《公宴诗》) “阳春和气动,贤主以崇仁。布惠绥人物,降爱常所亲。上堂相娱乐,中外奉时珍。五味风雨集,杯酌若浮云。”(阮瑀《公宴诗》)
邺下作家群游宴于山水园囿之中,酒筵的目的是抒发性情、谈经论义,“辩论释郁结,援笔兴文章”,通过辩论产生文学灵感,进行诗赋创作。通过作家群的郊游活动也可以看出,作家群在游宴过程中,并不是追求沉醉和逃避,而是以一种超脱的精神去实现人性的复归。“无味风雨集,杯酌若浮云”,表达着游仙般的生命情怀。毫无疑问,魏晋六朝时期,社会动荡和生命短促激发了知识分子的忧生意识,孕育了他们的乐生精神。乐生精神是人类对“生死问题”的本能反应,也是人类的身体表达。
(二)郊游与玄言文学
玄言文学是一种以老庄思想为基础,通过诗、文、赋表达道家玄学义理的文化形式,与知识分子的政治命运、人生态度、价值观等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汉末的大动荡已引发觉醒的士人产生思想意识的冲突,强调名教伦理的儒家道统与崇尚个体价值的道家学说不可调和。正始年间,何晏、王弼、夏侯玄等名士力图通过玄言文学将名教与自然糅合在一起,缓和人的生命诉求和动荡社会之间的矛盾。遗憾的是,王弼的英年早逝与何晏的被杀夭折了这次开拓性的尝试,文化鼎新的使命落在了竹林七贤作家群肩上。竹林七贤是这一时期最有影响力的玄言文学团体,其中,嵇康和阮籍的文学成就最大。《文心雕龙·才略》曰:“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翩而同飞”[10]。二位作家以“师心遣论”、“使气命诗”的形式探究玄学义理,作品中蕴涵着超生死、超功利的文化精神,表现出个人价值的“意义觉醒”。“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阮籍《咏怀诗》),东汉末年的社会大动荡从心灵深处唤醒了人的自我意识和存在价值,并在道教的人本论思想中找到了文学表达的理论依据。回归自然,通过诗歌表达他们的文化诉求,勾勒自由和超越的精神家园,为觉醒的自我找到归宿。如: “离合云雾兮,往来如飘风。富贵俯仰间,贫贱何必终。留侯起亡虏,威武赫荒夷。邵平封东陵,一旦为布衣。枝叶托根柢,死生同盛衰。”(阮籍《采薪者歌》) “琴书自乐,远游可珍。念道独往,弃智遗身。寂乎无累,何求于人?长寄灵岳,怡志养神”。(嵇康《赠兄秀才入军》) “绝智弃学,游心于玄默。遇过而悔,当不自得。垂钓一壑,所乐一国。被发行歌,和气四塞。歌以言之,游心于玄默。”(嵇康《代秋胡歌诗》)
去社会,近自然,实现“人性复归”是老庄哲学之精髓,也是魏晋玄言文学的理论基础。玄言作家主张在政治上“外身”、物质上“去欲”、文化上“绝学弃智”,摆脱“生死”、“时命”和“情欲”所带来的困境,做到身体归隐,精神逍遥。玄言文学表达的不是对命运的抗争,而是对生命意义的反思。在魏晋这个“祸福无常主,何忧身无归”的动荡年代,“人不如放弃抗争以听任自然安排”,人性复归意识日渐强烈[11]。因此,玄言文学表达的是外物绝欲、弃圣绝学的避世思想。
郊游活动是竹林七贤的生活实践和文学创作主要途径,他们希望通过“游山泽,观鸟鱼”找到创作的灵感,通过“万物为一,四海同宅”,实现身心自由。“魏晋政变之际,何晏被诛,曹社将屋,得志者入青云,失志者死穷巷,而庸庸者显赫,高才者沉沦,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此志士之所同悲”[12]。他们生活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当现实和理想剧烈冲突时,选择了逃离和遁世,在竹林深处寻找灵魂的救赎和对自由的表达。嵇康、阮籍、山涛、阮咸等人,常游乐于山阳县竹林下,“或率尔相携,观原野,极游浪之势,亦不计远近,或经日乃归,复修常业”(《世说新语·言语》),林下郊游成为他们在风雨如晦的泥沼中开辟出的精神家园。竹林七贤是一个较为松散的文学创作群,个体差异较为明显,但有一个共同喜好让他们“不计远近”,“携手入林”,那就是好老庄,蔑礼法,饮酒清谈,注重个体权利和意志自由。竹林七贤这个志趣相投的作家群在青山绿水的大自然中饮酒赋诗,抚琴啸歌,“从异化的名教牢笼中解放出来,超脱原对世俗是非、荣辱、得失价值的执迷,将精神上的悲苦升华为无限的玄美”[13]。在他们看来,束缚身体自由的缰锁是“富贵尊荣”。嵇康曰:“富贵尊荣,忧患谅独多。古人所惧,丰屋蔀家。人害其上,兽恶网罗。”(《代秋胡歌诗》)只有“外物去欲”,才能实现身心自由。在“人与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富贵、功名、荣禄等名缰利锁编织的“社会牢笼”将人们的身体和精神困守笼中,自然之性随之丧失。毫无疑问,嵇康、阮籍所提倡的“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的自由精神是郊游活动的至上境界。因此,在中国文学史上,林下作家群的郊游活动能够体现、表达玄言文学本质属性和价值内涵。
(三)郊游与山水文学
山水是人类生命的音符,自古以来,我国劳动人民对山水有着特殊的情愫。原始信仰的山水崇拜、先秦时期的山水比德,魏晋时期的山水诗赋,它们以不同的形式讲述着多样化的山水文化,启迪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创造灵感。不过,严格来说,山水从生活元素过渡到充满生命价值的文化元素是从东晋开始的。“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文心雕龙·明诗篇》),作家们从“丝竹之娱”走向“山水之乐”,以“山水”代替“玄言”,晋宋之际发生了一次人文思潮的大转变。文人们媚道山水,形成朴实自然的山水文化,把中国古代的山水文学推行了一个高潮。
山水文学作家群的流派众多,两晋时代,形成了以陈郡谢氏和琅琊王氏两个家族为核心的文人集团。至南朝,“山泽四友”、“竟陵八友”作家群的出现,把山水文学推向高峰。山水诗的兴起源自于作家们内心对山水的热爱,如谢安、王羲之发起的“兰亭雅集”:暮春之初,“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世说新语·企羡》兰亭禊会不同于前期的郊游活动,它把自然山水作为活动的中心,体察山水、描绘山水、感悟山水,把创作的灵感安置在山水之中,通过郊游活动和文化交流释放出来。《世说新语·言语》载: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着”。
洛水郊游的文学主体是西晋王济、王衍、裴頠、王戎等人,文学创作途径是“以文章赏会”,这似乎是作家群雅集或游宴时达成的共识。《南史·谢灵运传》载:“ 灵运既东,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睿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 又,《南史·谢宏微传》载:“ 混风格高峻,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晦、曜、弘微以文义赏会,常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混诗所言昔为乌衣游,戚戚皆亲姓者也。” 乌衣郊游是南朝初年谢氏家族成员组织的一次游乐聚会。谢氏子弟不仅多能吟诗,而且喜郊游。谢灵运“出郭游行,或一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南史·谢灵运传》),而宰相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晋书·谢安传》),这些频繁的山水郊游活动,作家们不再把山水简单视为逃逸现实的避难所,而是将自己的人生体验融入到自然山水之中,以形媚道,躬亲体验山水所蕴含“道法自然”的生命价值,感知“与道同体”的超越精神。章必功指出,“永嘉乱后,名士南渡,美丽的自然环境和他们追求自然的心境结合起来,于是山水美的发现便成了东晋这个时代对于中国艺术和文学的绝大贡献”[14]。山水郊游成为魏晋作家群“越名教而任自然”价值取向的行为表达,“投身大自然的怀抱,在领略山水美景的玄趣中,才能实现心灵的真正解放”[15]。
三、魏晋六朝作家群郊游的文化精神
魏晋六朝是我国继春秋战国之后第二个社会大动乱的时期。多数文人面临死亡威胁的极端困境,逐渐放弃汉代以来儒家积极的“入世观”,崇尚老庄无为的“自然观”,开启了一个“文化自觉”的时代,作家们的郊游活动孕育了魏晋六朝的文化精神。
(一)乐生精神:“有闲”和“觉醒”
魏晋六朝郊游主体是帝王将相、王公贵族及文人雅士等,他们有“闲时”、“闲钱”和“闲趣”,这部分群体被美国学者凡勃伦称之为“有闲阶级”[16]。他们脱离生产劳动,啸歌山林、游仙访道、谈玄清议、游宴赋诗,过着悠闲的生活。
魏晋六朝作家群沉迷郊游活动的群体意识因于生命的觉醒。从心理学角度看,有两个要因:一是对死的恐惧。汉末以来的战乱及统治阶级的杀戮无法让人们走出死亡的阴影,曹魏的孔融、杨修、荀彧,东晋的何晏、夏侯玄,西晋的张华、陆机、潘岳、陆云、郭璞、刘琨等一批批文人被杀,知识分子人人自危,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二是对生的渴求。“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曹植《薤露行》)人生的飘忽叹逝是文学创作的母体,从先秦诗歌到魏晋文学无不流露着长生不死的希冀。曹操《秋胡歌·愿登太华山》:“飘摇八极,与神人俱。思得神药,万岁为期。”汉末以来,战争频仍,白骨露野。对死亡的恐惧必然导致对生命价值的思考,既定的传统、事业、功业、学问、信仰又并不怎么可信可靠,那么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突出出来了[17]。曹操《秋胡行·晨上散关山》云:“名山历观,遨游八极,枕石漱流饮泉。沉吟不决,遂上升天。”诗人的天性是乐生的、积极的。世俗拖累之后是体妙玄心,超凡脱俗,李泽厚把这种自然观的转向称之为“人的觉醒”。
作家群的文化倾向与自然山水呈现结构上的同源。面对动荡的社会和多舛的命运,回归自然是乐生延命的最好选择。“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稀”(孔融《杂诗》),作家群往往会在郊游活动中审视自我的生存价值,寻找新的生命表达方式。同时,道教的兴盛,鼓吹“乐生延命”之学和修身成仙之法。“放神青云外,绝迹穷山里”(王康琚《反招隐诗》),作家群形成了重道统、轻势统,生命为本的价值取向。在各种郊游活动中,“诗杂仙心”,乐生意识逐渐强化和升华,希冀在郊游活动中展露生命的欢娱,并逐步转化为文学创作的激情和源泉。总之,郊游活动为文人阶层打开了一个重新乐生求存,找到生命价值和意义的窗口。
(二)超越精神: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是作家群文化精神的人格隐喻,最早由鲁迅先生提出,代表着魏晋六朝名士群体的独特人格精神[18],具体表现为药、酒、游等文化形态。服药是文人雅士的一种风度,是相互推崇的一种生活时尚。他们所服的药叫“五石散”,具有较强的毒性,为了加速毒素的散发,需多吃冷食,故又叫做寒食散。服药之风的兴起基于三点原因:其一,超越生命时限。作家们希冀通过服药延年益寿。曹操《与皇甫隆令》云:“闻卿年出百岁,而体力不衰,耳目聪明,颜色和悦,此盛事也。所服食施行导引,可得闻乎?”二是超越身体局限。嵇康《游仙诗》云:“采药钟山隅,服食改姿容。”魏晋时期人物品评之风盛行,仪容之美受宠。《世说新语·容止》记载:“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三是超越生活阈限。生命无常,及时行乐。服药作为当时一种“求长生”、“求美誉”、“求享乐”的文人风度,雅好服食者甚众,魏晋的何晏、王弼和夏侯玄等名士被称为服药的祖师,郗愔与姊夫王羲之、高士许询等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等等(《晋书·郗愔传》),这种服散的风气一直持续到隋唐。
饮酒是魏晋六朝作家群的一种文化精神,凝聚着他们对生存向度的思考。首先,酒与仙。《世说新语·任诞》载:“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成名士。”其次,酒与乐。饮酒也是为了增加生命的密度,做到及时享乐,“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世说新语·任诞》)。最后,酒与醉。正如尼采把“醉”形容为情绪的高涨和释放,人在酣醉中可以超越形体,感受到生命的狂喜,忘记人生的惨痛[19]。魏晋时期,醉不仅是一种情感上的宣泄,而且是明哲保身、避祸求存的一种方式。叶梦得《石林诗话》云:“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懼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耳。”阮籍为避司马昭之子司马炎与女儿的婚事,沉醉六十余日,司马昭只好作罢,阮籍成功摆脱了这场婚事和政治纠葛。
药、酒、游三者作为超越精神的文化行为代表,是作家群的生活必需品。文人们任性而又放达,药、酒、游与他们崇尚的玄远、高逸气质相吻合。服药者一方面外出郊游活动,“行散”解毒,另一方面,多喝热酒、好酒,以酒解毒。这样,药、酒、游建立了必然的联系。郊游变身为宴游,无酒不成宴,无宴不成游,药、酒、游为代表的魏晋风度也顺理成章成为了超越精神的代名词。
(三)自由精神:越名教而任自然
“生命自由”是魏晋六朝作家群的社会价值观。可以从哲学、社会、政治、人生态度四个维度进一步诠释为:崇无轻有;重个人、轻社会;重道统(知识分子的良知)、轻势统(封建统治)和重审美,轻功利[20]。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价值观是由老庄思想发展而来的玄学思想。“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干宝《晋纪·总论》)。老子是最早提出天地万物均由自然生成的思想家。老子“不尚贤”、主张与世无争,使人们回到无矛盾、无斗争的“无为”境界。自由精神的外在表现是“越名教而任自然”。余英时将魏晋“名教”称之为“整个人伦秩序”[21],也就是统治阶级所推行的以儒家伦理秩序为道统的社会组织形式及行为准则。“越名教”意指淡泊名利、生命自由,是对礼教规训的一种反叛。“自然”是未经人工雕琢的原初状态,汤一介称之为“宇宙本体、世界本源或者说宇宙万物本来的样子”[22]。若与儒家积极入世的价值观相比,“任自然”则表现为放弃主观努力和抗争,顺其天性,清静无为。从社会背景来看,魏晋时期,名教成为统治阶级玩弄权术的遮羞布,加快了儒家伦理的式微,进而激发了士人对自然的回归和对自由的向往。魏晋六朝作家群通过两种途径表达这种文化精神:其一,生命内质的文学表达。通过诗词歌赋表现对伦理藩篱的突破,蔑视礼教,崇尚自由,性情得到真实地抒发。《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云:“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酒会诗》云:“淡淡流水,沦胥而逝。泛泛柏舟,载浮载滞。微啸清风,鼓楫容裔。放棹投杆,优游卒岁。”嵇康的诗让我们看到了魏晋作家群摆脱名缰利锁,追求生命自由的人生观。住陋巷、教子孙、饮浊酒、抚玉琴、放棹投杆等不仅是一种快乐生活,而且是一种玄妙之道。魏晋作家群把复归自由之境作为文学体裁进行生命本体的价值思考,是玄言文学对老庄思想的升华和再造。应该说,自由精神是魏晋六朝作家群真正觉醒的生命表达。其二,践行自由的身体表达。魏晋时期,作家群集体意识的身体表达是啸歌与裸裎。啸歌和裸裎是崇尚自然,践行自由的行为表达。《江左名士传》曰:“(谢鲲)通简有识,不修威仪,好迹逸而心整,形浊而言清。居身若秽,动不累高。邻家有女,尝往挑之,女方织,以梭投折其两齿。既归,傲然长啸,曰:‘犹不废我啸歌。’其不事形骸如此。”[23]啸歌乃“自然之至音”,是役心御气,渐近自然的身体外在表达。从谢鲲“折其两齿”,“犹不废我啸歌”足以看出啸歌在其生活中的重要性。除啸歌外,裸裎也是作家群集体意识的身体表达。《世说新语·任诞》载:“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这些个体感性价值的行为表现,是人类主体与自然客体的生命律动相通达,身体行为与心理诉求相体合的一种情感表达。也可以说,啸歌、裸郢是魏晋作家群生命放纵情态中的一个“局部或片段”,是彰显“个体生命自然存在价值”的一种方式[24]。总之,魏晋六朝的玄学思潮为作家群自由精神的形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结语
郊游活动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特定时间、特定空间的一种社会产物。魏晋六朝社会特征表现为政治动荡、命运多舛。作家群主体的自我觉醒,开始对生存客体进行重新文化审视和价值判断,形成了一种集体认知的“乐生”、“超越”和“自由”的文化精神。宗白华指出:“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25]篾礼法,越名教,进而实现自然无为,老庄思想的根基支撑起了魏晋六朝作家群所构建的文学大厦,而游仙文学、玄言文学和山水文学是该大厦的主要支柱。魏晋六朝时期,郊游活动成为作家群文学创作的途径,让魏晋六朝作家群在文人雅集的游宴中寻找创作灵感,并在文学内容中表现出乐生、超越和自由的文化精神,这是对我国古典文学理论的一种创新,并对现代文学产生着深远影响。因此,作家群郊游活动的研究对于古典文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文化价值。
[1]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外四种)[M].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38.
[2]周思琴.魏晋旅游文化繁荣之二重因素[J].宁夏大学学报,1998(3).
[3]黄平芳.六朝旅游思想初探[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5(4).
[4]余东林.“畅神说”旅游审美观之意蕴[J].湖北大学学报,2007(5).
[5]王岳川,胡淼森.文化战略[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12.
[6]张群.魏晋南北朝时期旅游休闲活动分析[J].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3).
[7]于春媚.道家思想与魏晋文学——以隐逸、游仙、玄言文学为中心的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8:77.
[8]俞绍初.“南皮之游”与建安诗歌创作——读《文选》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J].文学遗产,2007(5).
[9]卢弼.三国志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2:522.
[10]范文斓.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700.
[11]包兆会.论庄子之游[J].南京大学学报,2003(4).
[12]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3.
[13]曾春海.竹林七贤与酒[J].中州学刊,2007(1).
[14]章必功.中国旅游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119.
[15]李文初.中国山水文化[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9-10.
[16]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6.
[17]李泽厚.美学三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93-94.
[18]卫绍生.“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J].中州学刊,2009(4).
[19]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91-92.
[20]宁稼雨.魏晋风度——中古文人生活行为的文化意蕴[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243-244.
[2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403.
[22]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52.
[23]张万起,刘尚慈.世说新语译注:赏誉引[M].北京:中华书局,2006:438.
[24]曾小明.魏晋风度的身体表达[J].湖南大学学报,2012(1).
[25]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68.
[责任编辑 海 林]
10.16366/j.cnki.1000-2359.2016.05.024
2015-10-11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5BJL119);国家旅游局“研究型英才培养项目”(WMYC20151038)
I206.35
A
1000-2359(2016)05-0139-06
郑向敏(1954-),男,福建泉州人,华侨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旅游文化;郭伟锋(1975-),男,河南许昌人,华侨大学博士研究生,武夷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古典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