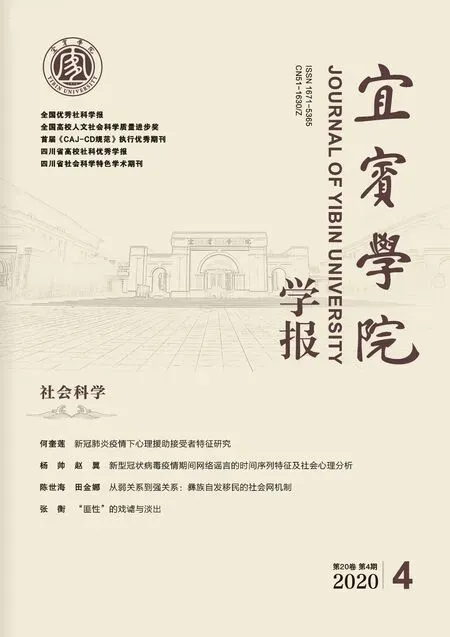新世纪“小区域作家群”论
刘成勇
(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周口466000)
新世纪以来,在地理空间上小于“文学豫军”“文学陕军”“文学晋军”等大区域作家群的、以地级市为主的小区域作家群呈现出集体涌现的态势,学界对此创作现象也已有关注,对代表性作家作品及小区域作家群共性特征也进行了一定程度探讨,但仍有一些问题亟待挖掘,比如何为“小区域作家群”?其在新世纪的出现原因何在?其与“文学陕军”“文学豫军”“文学晋军”等大区域作家群关系怎样?如何看待这一创作现象的文学意义?本文试图就此展开论述,以引发学界更多的思考。
一、 新世纪“小区域作家群”扫描
从学界研究来看,受到关注的“小区域作家群”一般以地市级为主,如周口作家群、昭通作家群、兴化作家群、聊城作家群、曲靖作家群、绍兴作家群、大连作家群、保定作家群、嘉兴作家群、贺州作家群、许昌作家群、玉林作家群、温州作家群、遵义作家群等。也有地级市作家群是以该地区文化特征或地理特征进行命名,如衡山市的衡岳作家群、达州市的巴山作家群、梧州市的西江作家群、大同市的雁北作家群等。一些以大区域方位命名的作家群实际也是以某一地级市区域为基本的“小区域作家群”,如孙向阳对“黔东作家群”的界定:“黔东文学实指整个铜仁市的区域文学”,[1]何光渝认为:“‘黔北文学’……其实就是区域的遵义”,[2]“桂西北作家群”的另一个说法是“河池作家群”,[3]“湘西青年作家群”是出生、成长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作家。[4]
以县级行政区域命名的作家群也不在少数,如霍邱作家群、鹤峰作家群、利川作家群、马边作家群、都安作家群、嘉定作家群、北流作家群、龙山作家群、嘉兴作家群、钟祥作家群。乡镇一级的作家群也不容忽视,如周口的新站镇有中国作协会员9人,孙方友的“新笔记体小说”及其弟弟墨白(孙郁)的先锋气质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有着独特的叙事价值。恩施红土乡有两名中国作协会员、九名省级作协会员、近百名文学爱好者,获得全国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两次。恩施景阳镇的谭功才和向迅的作品于2014年双双入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六安姚李镇1999 年创办了全省唯一的乡级文化站刊物《漫流河》杂志,成立了50多位骨干作者组成的“漫流河文学社”,走出了“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徐贵祥、“打工诗歌”代表诗人及“打工文学”的提出者柳冬妩等。
“小区域作家群”不仅表现出地域空间的一致性,而且在主体身份、作品主题、文学风格等方面表现出突出特征。比如少数民族“小区域作家群”较有影响的有以福建宁德为代表的畲族作家群、多民族作家为主体的康巴作家群、维吾尔族作家组成的莎车作家群、楚雄彝族作家群、贺州瑶族作家群、恩施土家族作家群等。再如以农民作家命名的有湖北钟祥农民作家群、安徽定远农民作家群、江苏丰城农民作家群等,以女性作家为主的有湖州80后女作家群、甘肃庆阳女作家群、苏州女作家群、大同女作家群、南宁女作家群等,以创作网络文学为主的有嘉兴网络文学作家群、温州网络作家群等,以文体见长的有惠州小小说作家群、常德武陵微型小说作家群、小凉山诗人群,桂西北作家群、陕西富平作家群则以长篇小说为特色。
新世纪“小区域作家群”有三个现象值得关注:首先是大部分“小区域作家群”处在经济较为落后、交通不太发达的地方,也就是地域政治视野中的“边地”和“外省”,如西南、西北、东北以及河南、安徽、湖北等地。在云南,具有影响力的“小区域作家群”有昭通作家群、曲靖作家群、小凉山诗人群、楚雄作家群。而在“小区域作家群”内部则又可以细分出独具个性的“小小区域作家群”,如楚雄州可细分为彝族作家群、农民作家群、网络作家群、女作家群等,恩施州则有利川作家群、鹤峰作家群以及活跃在中山市的建始作家群等。
其次是少数民族“小区域作家群”的崛起,较有影响的有以福建宁德为代表的畲族作家群、多民族作家为主体的康巴作家群、维吾尔族作家组成的莎车作家群、楚雄彝族作家群、贺州瑶族作家群、恩施土家族作家群、西海固回族作家群等。有些少数民族在多个区域展现出文学风采,如重庆、恩施和湘西的土家族作家群,大小凉山区域、楚雄的彝族作家群、广西都安和贺州的瑶族作家群等。少数民族“小区域作家”群既有对主流文化的叙事认同,同时也表现出独特的族群记忆和族群文化表达方式。
最后是“小区域作家群”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和乡土气息。在信息化、全球化侵袭下,“大区域作家群”的壁垒已然打碎,承接大区域文化传统和民族传统的任务落到小区域文学写作中来。与“大区域作家群”“回望乡土”的写作视角不同,“小区域作家群”更多是以“在地”的姿态叙写来源于乡土之上的生活经验和生命经验。
总的来看,在新世纪的文学版图上,“小区域作家群”灿若群星,密布在塞北江南、都市乡村等各个地理空间,他们以鲜活的本土素材和粗粝的审美趣味体现了新世纪文学的多元化和丰富性。
二、 何为“小区域作家群”?
那么,该怎样理解“小区域作家群”呢? 首先,何为“小区域”?在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领域,“小区域”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但其边界弹性极大,一般是按照人口规模、面积大小、经济总量等因素进行相对划分,不太适合标示历时生成的“作家群”。从文学角度而言,要理解“小区域”,还得从“地域”和“区域”这两个文化地理学概念出发。
2016年1月至2017年2月,我们对66例AD患者实施分阶段延伸护理干预,取得满意效果。现报告如下。
“地域”和“区域”之间有诸多交叉重叠的地方,比如一般都以自然地理环境而定,所以二者经常可以混用,尤其是在文学领域有时并未严格区分。但二者之间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地域具有自然形成性,受地形地貌、气候风物的影响;而区域则是主观建构的结果。其二,地域没有清晰的边界线,而区域的范围则非常明确,在地图上边界清晰准确。其三,地域的范围一般大于区域,区域一般最大至省,小则到村庄、社区。历史上我国行政区划综合考虑自然地理、历史传统、民族分布、风俗习惯和军事、政治、经济等要素而设置。一般如果不是大的变化,比如朝代的更迭,行政区划体现出一定的历史稳定性,即使有变化也是微观调整。另外,按照学者的考证,历史上我国地方行政区划单位中,最高一级的单位最不稳定,如郡、州、道、路、省等;最基本的一级单位最稳定,如县。[5]
应该说,“小区域”这一概念兼顾了行政规划意义上的“区域”和自然人文环境的“地域”的内涵,兼顾到了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对作家的双重滋养,是地理环境、文化传统、语言习俗、行政规划的社区综合体,更具有历史和空间的稳定性,能够适合语言、习俗等文化要素的生成、发展和稳定。
那么,又该怎样理解“作家群”呢?应该说,因为目前文学体制的关系,各区域应该都有作家作品的存在,但并不是所有小区域都能产生作家群。能够称得上“小区域作家群”的,除了特定的地理环境外,还应具备如下特征:领军人物的出现、一定数量的创作人员、共享的文化底蕴、相似的文学风格等。除此之外,文学刊物、获奖数量、作品转载、理论研讨等也是重要的考量指标。举例来说,在云南昭通文坛,有领军人物夏天敏和雷平阳,有从事业余写作的作者七千多人,在省级以上公开刊物发表作品的有两百多人[6],文学作品多采用现实主义手法,表现了昭通的自然景观、乡风民俗、历史传统。鉴于昭通文学创作实绩,2006年 11 月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主题报告提出“昭通作家群”。
正是考虑到如上文学空间、文化传统、组织形态、文学活动、作品风格、创作成就,“小区域作家群”一般指的是以市、县级行政区命名的作家群。也有学者以“地域作家群”(陈永华等,2011)、“地方作家群”(杨梦媛等,2015)、 “区域作家群”(扣颖,2016)、“县域文艺”(尹才干,2016)、“县域文学”(窦开龙,2019)来指称这种文学创作群体,相比之下,“小区域作家群”这一指称更具有外延的边界感和研究对象的明晰性。比如扣颖的“区域作家群”既包括“文学湘军”“文学陕军”“文学豫军”等大区域作家群,也含有“巴山作家群”“商洛作家群”“南阳作家群”等小区域作家群。将两者并置在一起论述,难免会遮蔽“小区域作家群”的主体性,也无法处理“商洛作家群”与“文学陕军”“南阳作家群”与“文学豫军”之间的主从关系。
最早使用“小区域作家群”这一概念的是陕西评论家李星。在为邰科祥等所著《当代商洛作家群论》一书所做序言中,李星认为这部研究商洛作家群的著作“开创了我省乃至全国对于小区域作家群研究的先河”。尽管他未能就何为“小区域作家群”展开更细致的论述,他所提出的一些观点还是具有启示意义,比如他认为应对地域性作家群进行综合的分析,应该对地域作家群的突然出现进行深层次的原因探讨[7],对“小区域作家群”进行明确界定的是周口师范学院的任动。在2011年的一篇文章中,任动认为:“小区域作家群指的是地市级及以下行政区域的作家群体。”[8]这一定义注意到了“小区域作家群”的特殊性,开始有意识地将其从“文学陕军”“文学豫军”“文学晋军”“文学桂军”“文学湘军”等省级行政区作家群中剥离出来。这种现象学的定义从新世纪以来地域文学创作的新变提炼而来,比较符合实际。
三、 “小区域作家群”产生原因
“小区域作家群”并非是新世纪才出现的文学现象,比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即有南阳作家群、商洛作家群活跃在文坛。但这么多的“小区域作家群”能够在新世纪出现,其背后一定有多种缘由在起作用。与“大区域作家群”的生成相类似,“小区域作家群”也是文学体制规约、权威命名、理论倡导、政府主推、文化支撑的结果,但又有了某些新的变化或决定性因素。
“小区域”的地理空间因为学缘、亲缘、业缘的关系,人际互动较为频繁和密切,也就更容易形成作家群。相比较之下,大区域作家之间的自然交往就不如小区域作家方便自由。同样因为地域上的关系,“小区域作家群”绝大多数由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作家组成。空间的固化使作家可以持续体验地方性并接受地方的身份定义,与地方的不断互动使他们在作品取材、艺术手法、创作理念、文化底蕴方面更具有趋同性,地方个性更为明显。在国家视野和大区域视野的双重遮蔽下,小区域文化的独特性隐然不彰,其文学个性消泯于大区域主流文学之中,或成为大区域文学的边缘化存在。因为经济、文化、社会的不同及自然景观、地理位置的不同,“大区域”内部文化多样异质。赵德利认为,陕北、陕中、陕南就无法形成地缘文化一体性,[9]费振钟也认为,“江苏文学”也不是单单属于一个“文化个体”[10]1。但在“文学陕军”“文学豫军”的统摄下,它们被描述为均质化的整体。如果以此化约区域内作家,就很有可能抹平作家的艺术个性和文学风格。
政府在新世纪“小区域作家群”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更积极的作用,从文学政策、资金扶持等方面积极扶持本土作家创作。常德市武陵区区委书记罗少挟说:“我们将把武陵小小说打造成具有全国性重大影响的常德文化品牌,尽快推动武陵小小说走向世界,为文化强市建设增砖添瓦!”[11]全球化时代,地方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如“非遗”的申报、地方文化节的举办、对地方历史名人的属地之争、传统文化建筑的保护、地方文化丛书的出版等,这与地方政府大力发展文化软实力相关。地方文化资本成为区域软实力的重要支撑,文学作品则无疑是最能体现地方特色的文化名片,是建构地方知识和想象地方共同体的重要力量。政府拿出资金出版作家丛书、设立文学奖项、组织召开研讨会、举办文学培训班、创办文学刊物、设置创作基地、开发文学产业等。政府的文学作为固然有着功利主义目的,但客观上对于地方文化保护和发展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强化了地域认同感和情感向心力,在维护文化多元方面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也促进了文学创作的自觉和多产。
对文学写作的兴趣与热情是“小区域作家群”的内生力量。大部分作家受过中等程度以上的教育,有较为稳定的工资收入。①因此,他们的写作不像二十世纪的地域文学作者那样,追求民族文化再现、民族国家建构等宏大叙事。他们从区域内部观照地方文化,地方性知识只是一种非自觉的再现,写作行为更多指向自我性情的抒发,写作目的是获得读者认同,激发读者的共同心理。李祥对“昭通作家群”进行问卷调查,其中“创作的最主要目的”的调查表明,有58.7%的作家从事写作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心声”,“为了个人成功”和“为了实现自我”各占2.17%、13.04%。而“为了激浊扬清”的有着明显社会责任感的写作仅占4.35%。[13]无独有偶,温州作家东君认为:“在我们这些写东西的人看来,写作并没有比吃喝玩乐更高尚,所以,我们的写作更多的是带有游戏的成分,几乎没有什么功利性。”[14]温州另一位作家程绍国说过: “我写小说意义何在……是满足自己在温州这个小地方的虚荣心而已。”[15] 191这种鲁迅所说的“余裕”的创作心态,使小区域作家在取材、叙事、文体、艺术手法等方面尽管显得芜杂,但也显示出文学表达的丰富和可能。
应该注意的是,有些“小区域作家群”不像大区域作家群那样是研究界基于文学创作实绩基础之上提炼命名并进行了充分研讨的结果,多是被政府或某些权威人士命名的结果。这样缺少学理支撑的命名方式是身份焦虑和时代需求之间合谋的结果,对其文学生态、文学形态尚须进行严谨的剖析。
四、 “小区域作家群”与基层写作
“小区域作家群”在组织形态上犹如金字塔,立在塔尖的是创作群体的“领头雁”,他们不仅代表了这一创作群体创作的最高水平,甚至也是时代的标杆人物。但处于金字塔基座的却是一大群作家,在文学史上,他们处于“无名状态”。但正因为有了他们,“作家群”才得以成立。与“领头雁”相比,这些在“基座”的作家也许更值得重视。因为他们的存在,既衬托出“领头雁”高飞的姿态,更反映了全民文化素质所能达到的高度,同时也反映出民间写作的审美趣味。就像丹纳所说:“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我们隔了几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但在传到我们耳边来的响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像一大片低沉的嗡嗡声一样,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只因为有了这一片和声,艺术家才成其为伟大。”[16]5-6
任东华提出过“文学土壤学”的概念,也是对此种状况的说明。按照任东华的阐释,所谓的“文学土壤学”指的是构成中国当代文学基本存在形态的“底层”部分。他认为,文学史上除了那些显性的大人物之外,“还有着许多潜伏在底层的、不为人所知的作者们,他们也在勤奋地创作,也可能出过不少作品,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终生与所谓的文学史‘无缘’,然而,文学史却绝对少不了他们”。任东华从四个方面归纳了这些文学“底层”的“土壤学”意义:
第一,他们虽然不以文学成就成为文学史的亮点,但他们却人数众多,无比钟情于文学,没有任何功利心理,只是文学而文学。第二,他们处在许多读者、著名作家与文学大师之间,并成为其不可或缺的联系纽带,既深接地气,又为文学界输送新鲜血液,从而延续了当代文脉。第三,他们以自己的不懈创作,诠释了文学的基本含义。他们的遭遇,呈现了文学在地方的生态基因,如读者、文学批评、文学环境、作品发表、专著出版等因素,从他们的身上,可以溯源当代文学的最初萌芽。第四,他们的意义,不在于本身的文学成就,而在于他们就像蓄水池,既容纳了文学发展所需的几乎全部条件、动力,又孕育了文学的无限可能性。他们是以沉默的姿态显示自己的存在的,也是以期权的方式,展示自己的伟大力量和意义的。他们就是广泛的文学土壤,任何伟大的文学都可以溯源到他们身上。[17]14-15
在每个作家群内部,作为“和声”或“土壤”存在的作家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在各自个性差异表达的同时又表现出较为稳定地在主体思想、艺术风格、审美特色等方面的一致性,从而赋予“作家群”以超稳定的结构框架。如果离开这些“无名”作家,“作家群”便不复存在。比如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的“都安作家群”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10人、广西作家协会会员有53人、河池作家协会学员有86人,还有一大批文学爱好者活跃在全县各个领域。都安作家群的庞大与创作的实绩使他们获得“广西作家半河池,河池作家半都安”的美誉。再比如大连作家群中,大连作协在册会员239人,省级会员71人,国家级会员21人。[18]“撑起云南文学的半壁江山”的昭通作家群中经常在省级以上公开发表文学作品的有一百多人,而从事业余写作的有七千多人。[6]
“无名”作者来自各行各业,身份不同,经历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但都有着对文字的喜好和对文学的热爱。陆汉迎在都安一所中学做了28年门卫,在全国20多家报刊发表文学作品200多篇(首),出版个人作品集《大山重叠》。周巨卿是保定交通系统的一名养路工,“他的诗集《金相册》捕捉平凡工作中的诗情画意,以新奇的想象、贴切的意象,歌咏了勤劳朴实的养路工的生活”[19]。石兴泽在一篇文章中肯定了聊城作家群对文学秉持的纯正态度:“聊城作家如张军、臧丽敏、李金龙、乌以强、李立泰、谭登坤、李明芳、赵红杰、王涛以及企业家范玮等,都有体面的工作,都不指望创作改善生活、谋求发展。而他们的执着和虔诚,追求的纯粹和坚持的恒心,悲情精神和信念操守,丝毫不亚于文学尊贵的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20]其他如陕西的草根派作家群、新洲草根作家群等的创作都是自发的文学行为,体现出基层文学爱好者对文学的热爱和赤诚。
一些在今天看来“有名”的作家,最开始也起始于“无名”。他们自办刊物、自组社团,在集体组织中相互交流,相互砥砺,最终脱颖而出。商洛的慧玮起步之初参加了一个叫丹江诗社的民间组织,宁有志、李高信、方英文、刘少鸿、鱼在洋聚拢在商洛文艺创作室的《商洛文艺》,京夫、陈彦稍有成就后即为组织或同行招揽集聚,结束了单枪匹马打天下的状态。邰科祥认为:“不管怎样,他们最初都是在县、地区一级的文化部门或一定的圈子中摸爬滚打、蓄积力量,没有这样的组织和氛围,也不会有他们现在的作为。”[21]
这些“土壤学”意义上的作家大部分坚守在乡土,这种文坛“边缘”状态常常使他们既能对那些恒常的风土民俗有现场感和介入感,又能切身感受到风土民俗之变以及时代和社会的痛点。这样的双重视点使他们能够提供出新鲜而独特的乡土经验和人文景观。
2012年,刘川鄂在《光明日报》撰文指出,在全球化、城市化、高科技化的世界性潮流中,地域性作家群越来越失去地域特征,相比较而言,小型(小区域)作家群多少具有题材、风格等方面的创作共性。他认为,“文坛近些年关于作家群的话题,也更多地集中在对小型(或曰小区域)作家群的关注上……小区域作家群应是今后关注和研究的重点”[22]。几年过去了,对单个的“小区域作家群”及其单个的作家作品的研究已比较充分,但将“小区域作家群”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分析其生成演化、创作共性、文本特征的不是太多。如果“小区域作家群”有可能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的话,尚有理论深化、研究视野扩大、建构知识范型等学术空间拓展的必要。
注 释:
① 李祥在2012年7月至11月自制问卷对昭通市十一县区部分基层作家进行问卷调查,在收回的146份问卷中,主要经济来源为工资性收入的有129人,占93.48%。(参见李祥《昭通市基层作家生存状态、创作状态研究》,载于《昭通学院学报》,2013年1期,64到70页)
——以广西高校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