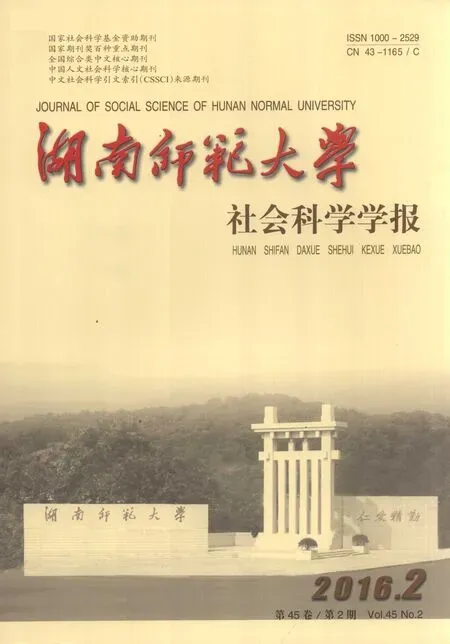影像盛宴中的苦涩柔情
——对近年“剩女”题材电影的思考
李琦,刘欢
影像盛宴中的苦涩柔情
——对近年“剩女”题材电影的思考
李琦,刘欢
摘要:作为一面折射当下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隐形棱镜,电影对受众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均会产生重要影响,它虚构了关于现实的影像乌托邦。“剩女”电影通过建构都市爱情神话,描摹“剩女”独特的生命体验与欲望图景,在光影的编织与重构间,将潜藏的两性话语无声传递,以都市的声色与躁动湮没大龄未婚女性的生存窘境,对诸多现实问题悬置或遮蔽。影片并未传达具体的社会隐喻与忧患意识,大众媒介精心缔造的拟态环境充斥着男权中心话语的“询唤”与“规劝”,现实中的“剩女”在质疑与声讨中依然举步维艰。
关键词:“剩女”电影;拟态环境;社会标签;性别叙事;刻板形象
大众电影的确切性质以及它作为一种话语的效力之秘密,在于它抹去了话语陈述的一切标记,并伪装成为一种故事形式①,将符码信息隐匿在光怪陆离的影像世界中,潜移默化地引发受众深层心理认同。当“剩女”身披羽衣霓裳,在后现代都市语境营造的视觉情境中大行其道,都市“剩女”的社会形象却被刻意凸显或遮蔽,不着痕迹地将“剩女”建构成最熟悉的“异类”。当“剩女”的生存窘境衍伸至光影世界,影片叙事借助何种母题展开?影像如何构建“剩女”形象?隐性话语如何传递且生成意义?“剩女”题材电影(以下均简称为“剩女”电影)又隐形书写了何种性别焦虑?本文拟从影视叙事学、婚姻社会学与文化研究等多维视角来深入解析近年的“剩女”电影。
一、乌托邦幻象:爱情母题的演绎与变奏
作为艺术创作的永恒母题,爱情呈现出长远的生命力与当下的时效性,其情感诉求具有共通性与普世性。在好莱坞经典爱情电影中,情感成为影片人物追求的终极目标,这一叙事模式使无数观众争先恐后地涌入影院,寻找欲望的客体与心灵的慰藉。一直以来,我国都市爱情电影在题材选择上极力向西方商业电影靠拢,但受制于文化差异与地缘因素,对人物的展现却并未照搬,始终流露出别样的人文风貌。近年来,“剩女”形象虽在不同作品中遭遇多重解构,但在主题的阐释上却相对一致,即爱与被爱。
1.“剩女”的情感诉求
《尼罗河上的惨案》中的大侦探波洛言,“女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被人爱”。在都市爱情电影中,“剩女”是极度渴望被爱的群体,对爱情近乎癫狂的追求成为其人生哲学,也是其异于常人之处。纵观当下热映的“剩女”电影,大多遵循“憧憬(挫折)—追寻(自省)—收获(重生)”的单一叙事脉络,在此原始叙事框架中衍生出形色各异的爱情童话。据此叙事模式,笔者将都市爱情电影中的“剩女”细分为“追寻者”与“自省者”两大类别。这两种类型仅存在女性个人经历及价值观的差异,在叙事中仍沿袭乌托邦式的爱情母题。
《女人不坏》中的欧泛泛为俘获异性,不惧违反实验室规定,擅自研制“费洛蒙”,取得寻爱路上的有利保障。《爱情呼叫转移2》中的情感专家聂冰在30岁生日前,先后邂逅12名风格迥异的男性,在与不同男性的接触与碰撞中,对伴侣的认知日渐明朗。《撒娇女人最好命》里的张慧不惜改变自我,在上海撒娇女王的鼓动下,展开了爱情保卫战。这类影片充斥银幕,在制作团队的合理包装下,成就了追寻中的“剩女”。
“自省式剩女”则强调对自我的重塑,心理挫折与生理病症产生了决定性作用。以“借精生子”为叙事内核的《有种你爱我》中的建筑师左小欣借助一夜情怀孕,并决定独自抚养小孩,经历抚养权争夺,最终与孩子父亲达成和解,回归正常家庭。而《我愿意》中,拥有高学历、高薪资、高职位的“黄金剩女”唐微微7年前遭男友抛弃,在前男友与扮穷寻真爱的富豪之间,最终卸下心防,决然抉择。《我的早更女友》更是让失恋“剩女”戚嘉“早更”,身心饱受摧残,终在“暖男”袁晓鸥的帮助下,重获新生。即便电影从生理到心理,皆为“剩女”的真爱之旅设置重重阻碍,但万变不离其宗,电影都以大团圆结局,带来残酷现实中的温情抚慰。
每当“剩女”遭遇困境、倍受煎熬时,总会适时出现一位男性,他们体贴入微,能与女性建立良好的沟通与提供充足的安全感,这便是所谓的“暖男”。
2.“剩女”的欲望载体
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分支,电影亦遵循娱乐性原则,弥合受众对爱情的憧憬,加之消费文化蓬勃发展,直接促成电影主创设置互补型人物,以期实现观影满意度与经济效益的共赢。“剩女”与“暖男”的结合,可以视为巧合,抑或是社会结构变更所呈现的新型性别关系。如此一来,银幕内外的“剩女”便可在虚拟与现实间萌生信念,获取短暂的精神愉悦。
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具有独特人格魅力的“暖男”出现在“剩女”电影中,充当守护神、倾诉对象或心灵导师的社会角色,将女性从都市困境中予以解放,用真诚感化处于崩溃边缘的“剩女”。这迥异于新都市电影中直接裸露男性身体的感官刺激,指向更深层次的心理补偿。她们“并不会直接从男性形象的欲望化呈现中获得快感,而是先要将这种男性形象情感化、浪漫化或者精神化,才能免除观看的焦虑而获得快感”②。故“暖男”的选角并非拘囿于容貌俊朗的当红小生,丰盈的“暖男”形象为“剩女”提供了欲望的温床和远离世俗纷扰的避风港。《一夜惊喜》中的张童宇便是一位标准“暖男”,有着优越的家庭与教育背景,年轻帅气,善良真诚,深爱着32岁的上司米雪,不时为其化解危机。这样的男性若在大银幕扎堆出现,势必导致受众的审美疲劳,“暖男”形象的多样化已成为必然。反其道而行的有《101次求婚》,叶熏选择建筑工人黄达为人生伴侣;《我愿意》中的唐微微与青蛙王子杨年华互生情愫。“暖男”形象构建的饱满充盈在为“剩女”提供好男人的多元样本的同时,亦增强了叙事的多样性,制造了难以预估的戏剧效果。
两者的相互关联契合了当下“剩女”的生存现状。“剩女”独立意识强烈,自身条件优越,但主导型人格让男性望而却步,不断遭受婚姻挤压,进而被贬抑为“剩女”。而“暖男”的出现对“剩女”的意义在于,即便难觅高度匹配的异性伴侣,也要寻找善良体贴的另类男性,这是“剩女”个性与尊严的坚守,也是自我欲望的投射。再者,受现实生活中消费欲望的策动,民众更在乎物质消费能力所带来的情感维系,“在消费文化蔓延的都市空间里,男性不被鼓励去利用口头表达情感,而是被鼓励用消费去表达。消费势必将两性的互动表达绑架起来,以消费物质来衡量情感”③。物质与情感的双重焦虑成为都市男女挥之不去的梦魇,置身于“剩女”电影的爱情幻境,体验“暖男”的纯粹,何尝不是最佳消遣方式。乌托邦式的爱情幻象成为都市人群治愈现实失意的精神良药,诱人的裙摆遮蔽了浪漫笔触下对终极意义的探寻,在“剩女”电影持续繁荣之际,商业性与娱乐性持续升温,而真正的美学意义却黯然失色,徒剩迷惘与狂欢。
3.情感美学的变奏与缺失
爱情的叙述是跨越地域与种族的。电影在叙述这一母题时往往呈现出两种趋势:或倾向于纯粹的爱情故事,将浪漫演绎到极致,直观展现爱情奇迹;或与其他影片类型杂糅,表现出主题的复杂性与形式的多样性,传递沁人心脾或撼动人心的审美效应。观照当下“剩女”电影,我们只能用“震撼”二字来予以形容。
以现代都市为叙事背景的“剩女”电影与高度发达的商品社会不谋而合。商业元素成为包装爱情的必要手段,物质欲望附着于文化的躯壳之上,进而影响受众的消费行为,大众模糊了消费与文化的界限,在物质欲望与精神享受间陷入迷茫困顿。由此可见,“剩女”电影的艺术性必然大打折扣,更谈不上“爱情本位”的情感审美意义。从本质上而言,“精神化的审美理念从超功利化和精神升华的传统模式走出来,转向满足人们日常欲望释放和快感的追逐,短暂性、平面化和时常化就代替了韵味悠长和个性独特”④。这正是“剩女”电影的通病,影像“剩女”脱离了一般市民阶层,对其外在形象与情感生活的过度包装,超越了普遍的身份认同,徒有视觉刺激与感官愉悦,只是一种脱离现实语境的虚拟满足。影像营造的视觉奇观将“剩女”化作扁平且“空洞的能指”,漠视了现实社会大龄未婚女性的申诉与辩驳,影片本应具有的人文关怀荡然无存。
二、视觉符码:污名化的书写与包装
视觉艺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画框内主体的意义传达,“剩女”成为影片重要的语义阵地。对近年的“剩女”电影做深度文本分析,我们发现,“剩女”的构建模式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在观影过程中,观众受限于影院的观赏环境,对画面信息的解码倾向于妥协接受,进一步强化了传受关系,使影片潜藏的话语意义得以内化。对人物形象的负面化误读、气质容貌的过度渲染与奇观化的场景段落成为影片惯用的叙事策略。
1.负面化的个体解读
“剩女”形象遭遇不同程度的抹黑与扭曲,大龄未婚女、孤傲挑剔、自卑且心灵受创、神经质般的臆想等都成为“剩女”的特定标签,甚至被视为背离社会婚恋伦理与破坏社会控制力的“越轨者”。影片以此为卖点,以戏谑的方式对人物进行解构,对“社会越轨者”进行羞辱与规劝,而这显然不易让观众轻易察觉。
社会伦理被视为大众的道德底线,当编剧蓄谋让“剩女”践踏这一精神原则时,影片的商业性骤然提升,也迫使“剩女”遭遇“被污名化”的尴尬处境。如《有种你爱我》便是由“借精生子”引发的一出闹剧,这一敏感话题直接与“剩女”相关联,左小欣对孩子的热切渴盼超越了构建常规家庭的世俗观念,引发社会热议,莫须有的罪名着实令人无奈。这无非是以原有的社会成见为基础,将“剩女”继续妖魔化。《一夜惊喜》中的米雪意外怀孕,将原因归结为生日当晚的酒后乱性,误打误撞中发现始作俑者竟是对自己爱慕多时的助理张童宇。故事情节被荒诞与巧合塞满,在糖衣炮弹的粉饰下,“一夜情”所影射的对情欲的放纵,对肉体的糟践,价值观的扭曲与“剩女”又形成某种必然的联系,让观众在潜意识中接受这一道德评判,进而招致日常生活中对“剩女”的误读。对“剩女”形象的歪曲并未仅停留在伦理层面,对其智商与生理的改造更令人惊诧。《非常完美》和《非常幸运》安排女主角苏菲一味扮傻,刻意营造“剩女”病态的精神世界。《我的早更女友》更是让“剩女”更年期提前,处处强调女主角怪诞的生活情境,将病症极端化处理,以达成强烈的戏剧张力。
2.视觉化的形象铺陈
眼球经济以病毒入侵般的姿态蔓延至电影创作,眼花缭乱的蒙太奇成为叙事残缺与意义浅薄的遮羞布,视觉上的愉悦远超影片话语的深层表达,关乎生存的反思与自我的审视则倏忽不见。电影本应关乎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精神对话,而对视觉化的过度诉求已成为“剩女”电影难登大雅之堂的首要原因,“剩女”的能力与学识在影片中被予以遮蔽,观众更乐意从视觉快感中得到消遣娱乐。
审美与审丑,“剩女”以两极分化的姿态呈现于银幕。男权社会,女性存在的价值与容貌身材直接相关。男性观众以“凝视者”的视角审视“剩女”群体,也包括画面内男性演员的“双重凝视”,画面内外的视觉压迫不仅是传统性别文化的需要,也是男权中心意识形态的集中映射,男性由此重建自身话语霸权。无论是《101次求婚》中的叶熏,《一夜惊喜》中的米雪抑或是《我愿意》里的唐微微,在演员的选择与造型上都极具美感,每个画面都极富观赏性。导演不遗余力地营造“剩女”生活环境与工作场所的都市时尚氛围,华服披身,多维度地构建其视觉形象,以迎合受众的观赏品位与审美情趣。另一种较为普遍的叙事策略则是扮丑,这是很多影片屡试不爽的不二法门。“美丑对照原则”认可丑中有美,且视丑为美,有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既强化戏剧冲突,又使人物更具看点。周迅在《撒娇女人最好命》中饰演的张慧是标准的“女汉子”,不解风情,性格刚烈,与传统女性形象背道而驰。影片从对立的审美观出发,设置台湾女生蓓蓓为情敌,完美的身型相貌,娇嗔造作,符合多数男性的心理期待。在两个女人的较量中,蓓蓓最终因性格缺陷败下阵来,张慧重获真爱,对立彰显出人物精神内核的崇高,却无意间唤起大众对“剩女”的刻板成见。
在电影的具体创作中,编剧注重对“剩女”隐私的挖掘,尤其是呈现具有曲折性、冲突性且能满足受众情感消费的故事,这意味着影片整体风格向奇观化倾斜。
3.奇观化的影像呈现
在图像为王的视觉文化时代,奇观成为票房灵药,电影亦从对叙事结构的探索转向热衷于对奇观的构建,狂热追求视听效果,影像的话语因素被淡化。奇观化的呈现手段使得一切元素都受制于令人震撼的视觉景观,理性思辨向快感文化转变。影像语言和制作手法上鲜明的奇观化风格,造就了对“剩女”电影的观影热潮。
在“剩女”电影中,典型的奇观场面包括场景奇观、动作奇观与身体奇观。《女人不坏》中,“费洛蒙”被具象地表现出来,渲染出一个光怪陆离的情感世界。《爱情呼叫转移2》运用高科技手段营造的虚拟景观为影片划上浪漫的句点,成为满足观众视觉快感的重要手法。动作奇观往往借助演员惊险刺激的动作来予以实现,《非常幸运》里的苏菲与严大卫在躲避追击时不仅有激烈打斗,还从大厦顶楼速降,惊喜不断。《女人不坏》中,患有突发性僵硬症的欧泛泛在与男伴共舞时,僵硬的肢体被随意摆弄、抛接,完成一系列难以想象的荒诞动作,夸张程度可见一斑。调动各种影视手段来展示和再现躯体的身体奇观在影片中也尤为突出,“电影为女人的被看开辟了通往奇观本身的途径。电影的编码利用作为控制时间维度的电影(剪辑、叙事)和作为控制空间维度的电影(距离的变化、剪辑)之间的张力,创造了一种光、一个世界和一个对象,因而制造了一个按欲望剪裁的幻觉”⑤。《撒娇女人最好命》将镜头对准蓓蓓身体,《女人不坏》中唐露的万种风情,《一夜惊喜》里米雪躺在床上,性感地挑逗着镜头外的观众。毋庸置疑,这些女性身体吸引了男性的目光,极大地满足了受众的“窥淫癖”。
“剩女”电影虽为观众铸造了视觉的盛宴,但若奇观化的感官刺激逐渐消退,徒留空洞的剧情与浓厚的商业气息,炫目的符码肆意堆砌,无视人文关怀与社会思考,只会将电影推向一条远离艺术的覆灭之路。
三、影像桎梏:悲情叙述与话语编织
“剩女”电影的滥觞使得“剩女”作为一种全新的女性形象点亮银幕。丰富的画面语言,乌托邦式的爱情幻境,多样化的女性脸谱,一切都被佯装得顺理成章,而华美躯壳所掩盖的事实却是,电影中的“剩女”依旧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包袱,行走在男性视线之中。
1.苦涩柔情:悲情化的遮蔽与游离
大众媒介以不同传播策略重塑客观世界,其所构建的拟态环境与现实社会存在一定差距。自然,“剩女”形象也会被迫予以改造,以符合影片言说的意义。影像“剩女”恣情追梦,欲望的狂欢遮蔽了现实的苦涩与悲凉。
当受众的观影体验与现实处境极为相似时,文本所传达的讯息会进一步增强,从而产生情感共鸣。“剩女”电影以都市爱情故事为叙事框架,展现的爱情观、价值观都与日常生活密切关联,通过“共振效应”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剩女”电影建构的刻板形象麻痹了影院中的观众,形塑出定型化的思维逻辑,易导致社会大众对“剩女”的误读与偏见。影像“剩女”在职场上春风得意,在生活中却往往失败;若坚守情感,便极富个性,耽于幻想与偏执人格。不同文本轮番轰炸,将“剩女”打磨成异类,产生了消极的社会影响。
影像“剩女”不断生成意义,用狭隘的程式化演出取悦观众,隐藏的价值倾向昭然若揭。粗线条的人物勾勒仅符合影片的叙事节奏,并未昭示积极正面的精神价值。影片凸显与强化的是“剩女”符码意义的丰富性与事业情感的话题性,画面的展现仅停留在提出问题层面,且以逗趣形式再现,在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与拼贴中,意义的阐释被视觉所遮蔽,有关“剩女”的现实思考被中断或忽视。影片对“剩女”形象的选择性加工,也是大众媒介对这一群体主观化的改造与描摹。在编码与解码的过程中,话语机制将“剩女”电影带离了艺术的轨道,剥离了社会思考,彻底沦为消遣的娱乐工具。
2.话语机制:权力博弈下的意义传达
“剩女”电影热的持续升温是否意味着女权时代的来临?其实不然,就当下而言,中国现阶段的电影话语体系仍属男权话语系统。作为“第二性”,女性被动接受现有社会性别秩序,长期处于话语边缘,即便被不同程度的改写与创造,也无法跳脱这一苦涩现实。
男权中心意识形态在物质高度发达的今天也未见崩塌,女性长期陷落于集体无意识。在大众媒介营造的拟态环境中,“女性话语受到严重挤压。许多的‘拟态事件’,如语言、观念、生活或者行为方式等等,最初并不见得有代表性或普遍性,但是一旦进入大众传播的领域,就会被无限地放大,演化为社会流行,成为随处可见的社会现实,女性话语由此失去社会的支持”⑥。从影片的策划到放映阶段,行业内部之间、受众群体之间长期处于两性话语权的争端中。电影行业内的各部门均以男性居多,题材内容的选择往往依据男性自身的社会经验,决策的制定与实施自然向男性话语偏移。即便有部分女性导演和工作人员参与其中,单从数量上而言,也难以与男性力量抗衡。商业电影对利益的狂热追求,从侧面警示了制作者对受众观影习惯的把握。大部分观众对“剩女”的银幕形象早已通过其他媒介建立,文本指涉其他文本的整个过程创造了一种“拼凑式的杂烩”⑦。在满足观众视觉快感之余,也必须服从社会性别所带来的刻板成见,影片若“篡改”观众的生活体验与心理期待,必然导致观众的“对抗式解码”。
“剩女”群体社会事业的优越与物质生活的独立,必然引发男性的危机意识。行业内的女性精英呈上升趋势,这是男权社会所抗拒的,因为“剩女”的“神话”意味着父权制的解体。于是男性话语权的巩固只能建立在对“第二性”的压迫之上,于是传统伦理观、污名化标签接踵而来,以维护男性自身的话语机制。大众电影作为绝佳的宣泄出口,影像“剩女”被彻底物化、符号化、性对象化,沦为男性爱情的奴婢与生活的俘虏。观众在嬉笑间欣然接受传统性别秩序,深化对女性的负面评价,成为男性社会虔诚的信徒。“剩女”电影精心编织的“美丽神话”只不过是虚幻的存在,在两性话语的博弈中,女性再度失声,持续阵痛。
3.二元对立:“剩女”的抉择与焦虑
“剩女”电影以丰富的视听、普世的爱情观吸引着众多观众,商业利益的极大满足驱使大量片商投资此类影片,直接导致叙事结构的雷同与人物形象的同质化。“剩女”电影所承载的社会价值与个体反思意义极为浅薄,难以衍伸出更具深度的现实启示,千篇一律的情感闹剧成为影片最直观的呈现方式。我们可以“通过人物在关键时刻所做的选择来发现叙事逻辑,因为故事的进一步发展正是由人物在关键时刻的选择决定的”⑧,因此找出故事内部基本的二元对立关系,便能推演出完整的叙事模式。“幸”与“不幸”的二元对立,“事业”与“家庭”的两难抉择,是“剩女”电影最为常见的冲突结构,这些对峙构成了影片叙述的原始内核。
追求幸福是“剩女”电影展开叙事的基本动力,只有得到幸福才能完成叙事。影片伊始,“剩女”往往被赋予各种消极因素,上一段恋情的失败、自身女性魅力的缺失、错误价值观的坚守、近乎苛刻的择偶标准等均为其“不幸”埋下伏笔。影片有待解决的问题则是如何跨越障碍、自我反省,由“不幸”到“幸”。爱情苦旅结束之时,“剩女”的身份通常从“异族”转换为符合社会期待的普通女性,矛盾的化解意味着主流意识形态对“剩女”的成功“询唤”,进而完成意义的表达。“幸”与“不幸”的二元对立还常常演化为“家庭”与“事业”的冲突,这也是影片热衷呈现的社会议题。“剩女”工作的优越性,良好的文化素养与审美趣味迫使她们逃避婚姻,家庭事业孰轻孰重?影片通常避重就轻,将纠葛轻易化解,一笑而过,但现实的坎坷与无奈却无人知晓。
影像“剩女”受困于狭隘的造梦空间,对现实纠葛的搁置与游离是商业电影惯用的伎俩,也是服从于消费市场的无奈之举。二元对立的叙事句法在此类文本中的设置极为简单,矛盾冲突具有暂时性,无法引发深入探讨。“剩女”的现实困境被遮蔽,影片也并未传达具体的社会隐喻与忧患意识,影片仅仅只是主流话语善意的“规劝”,而现实中的“剩女”却在质疑与声讨中举步维艰,面临进退维谷的窘迫境遇。
四、现实窘境:多维视域下的精神囚徒
影像“剩女”经由视觉化的改造与包装,隐藏了对社会语境的深层探寻,浮于表象的模仿难以厘清这一复杂的女性群像。现实生活中的“剩女”面临层层壁垒,承受事业与情感的双重焦虑。社会结构的剧烈变更,消费文化的推波助澜,舆论环境的积极引导,女性独立意识的强化,多方因素造就了当下“剩女”的生存窘态。“剩女”的美丽与哀愁,均是女性社会际遇的写照,映现出社会主流价值观对当代女性的无情审判。
1.女性气质的规约
当今社会,社会性别的基本形式由男性主导,对女性的贬抑与诋毁成为社会文化的惯习。男性以掌舵者姿态赢得认同,女性只能束缚于琐碎的家庭事务中隐忍坚守,沦为象征性符码。父权制的性别属性强制预设了不同的两性气质和特征,对女性行为与价值观展开规训与引导。细腻体贴、服从谦卑、缺乏主见的温柔女性被男性社会欣然接受,成为标杆式的性别范本与理想化的“他者”,对女性构成严苛的限制与凌虐。
影像“剩女”容颜出众、薪酬丰厚、个性潇洒,光鲜亮丽的银幕形象掩盖了其现实生活的尴尬,背负“越轨者”的沉重包袱,与预设的女性气质背道而驰。她们具备男性气质所涵盖的勇敢、坚毅、创造力和自主精神,引发了男性社会的认同危机。社会性别制度要求“每个个体必须具有与其生理性别对应的气质,如果有人超出了社会性别领域的规范,即具有女性气质的男性和具有男性气质的女性则都被认为是不正常的、遭人排斥和被主流社会所不接受的”⑨。被动地接受和讨好成为女性逢迎父权社会的生存法则,偏离“女性气质”的航道则象征着男性奴役的失败,男性需要的女性就是服务于男性的客体,所谓的女人味只是一个虚伪荒谬的幌子。正因如此,质疑声纷至沓来,“剩女”成为众矢之的,在被歧视与污名化的路途上踽踽前行。
显然,“剩女”的生存之道在于正确认识自我,敢于面对世俗审视,只有顶住激流,到达彼岸方能重获尊重;强化自身,冲破父权制度的樊篱,消解“女性气质”的精神魔咒,方能赢得自为的存在。
2.婚恋困境的窘迫
“剩女”的婚恋择偶观具有鲜活的时代色彩,呈现出反传统的审美价值,男性的“硬件”退居其次,女性在情感领域中的意识明显增强。“剩女”电影对爱情的阐释远不及现实残酷,与日俱增的大龄女性因自身条件的优越而被婚姻市场边缘化。生育能力、世俗偏见与都市场域束缚了她们对情爱的自由追逐,身陷婚恋困境的“剩女”群体,在排挤与偏见中失语,沦为遗珠。
“男性在选择配偶时最注重女性的繁殖价值,而年龄是反映女性繁殖能力的最有力的指标”⑩,在一个强调婚姻生殖功能的社会,“剩女”自然被适婚男性剔除在视线之外。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相应的“婚配指数”也逐渐降低,择偶危机导致部分女性放宽择偶条件。年轻女性以青春为资本,注重男性的物质能力与婚后的生活保障,而大龄未婚女性则倾向于以稳定婚姻关系为诉求,物质标准退居其次,无形中增加了择偶难度。年龄与外貌永远是男性择偶的首要标准,即便“剩女”群体拥有更好的社会条件,在择偶竞争中依然力不从心。与此同时,婚恋资源是有限且不可再生的,大量社会精英向都市流动,地域封锁的彻底解除成为资源挤占的诱因,社会又将“剩女”与“唯婚姻论”者等同起来,现实际遇与社会偏见造就了都市“剩女”的悲凉处境,成为时代变奏散落的音符。消费市场的均衡,意味着供需平衡的一种相对静止状态,“剩女”的涌现意味着婚恋市场尚未出清,存在短缺或过剩。“这种过剩并不是女性婚姻挤压导致的绝对过剩,只是由于要价过高导致的相对过剩,或者说价格下降的刚性即不愿意降低价格导致的相对过剩。”⑪现实生活成本的增长,“剩女”对生活品质的执拗,过度追求完美的超价观念,被剩下也就不足为奇。正因如此,“剩女”为摆脱负面的社会标签,“纷纷弱化自己在职位、学历、收入方面的优势;同时,倡导女性‘降低职位追求’、‘降低学历追求’和‘降低收入追求’成为了主导性的舆论潮流,这种舆论潮流与‘女子无才便是德’、‘男高女低’等传统观念形成了传承与呼应,因而强化了对公众和社会所产生的负面、消极涵化效果”⑫。
社会偏见尚未消除,大众媒介就以话语领导者的姿态发声,对“剩女”形象过度渲染与包装,在大众媒介缔造的拟态环境中,受众潜移默化接受并认同“剩女”的负面媒介形象,误解持续加深。诸多社会因素的合力围剿,否定了“剩女”的人生价值,阻碍了个体享受幸福的权利。
3.生存压力的激增
“剩女”的婚恋压力与就业环境直接关联,父权制文化中家庭内部性别分工始终是男外女内,性别歧视使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女性只有在事业上倾注更多精力,才能获得与男性相同的发展机遇。情感与事业在当下严峻的就业形势中难以两全,“剩女”要么为爱病入膏肓,要么坚守职场远离爱情。
生产力与社会的进步重塑了女性的社会角色,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发生改变,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危及男性社会的统治话语,如是说,“男人贬值,其怒甚于地狱”⑬。影像“剩女”大都以社会管理阶层形象出现,在职场拥有诸多决策权。而现实是,在同一行业中,女性的升迁存在无形的障碍,性别成为阻碍女性发展的绊脚石。女性获得物质资源和工作机遇的不平等,体现了各种社会制度及其运作方式对女性发展的严格制控,女性很难跻身男性主导的决策层,即便有个别女性奋力闯入,也是被男性“同质化”的“类男人”。“进入领导层的妇女已不再具有女性的同情心与性别认同感。但或许更根本的原因是,当一个女人进入领导阶层之后,其身为领导者的身份比作为女性更为重要,从而使其阶层意识压倒了性别意识”⑭。此时的女性已具备男性的价值观与工作作风,也不会考虑制定维护女性员工权益的决策。压抑的工作环境对“剩女”心理产生极大影响,偏执的工作狂成为多数“剩女”的宿命,试问,缺少相处与沟通,爱情又从何而来?
生产技术和社会的发展激化了工作与家庭间的对立,“在家庭情感缺失的时候,主体会倾向于从工作场所获得补偿”,“工作家庭矛盾的根源在于工作与家庭的分离以及工作与家庭在交融过程中处理的不妥当”⑮,这是当代女性必须直视的社会事实。“剩女”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迷惘与困惑,落后的性别文化束缚了女性的多元发展,剥夺了女性实现社会价值的理想与抱负。
“剩女”电影在商业化的包装下,将女性身体异化,以戏谑的方式呈现“剩女”的生存状态,背离了电影写实性对人性世情的深切观照,遮蔽了对“剩女”独特情感体验的揣摩与对现实社会的反思,将苦涩视为笑柄,用嬉笑伪饰一切真相。情感成为“剩女”梦寐以求的精神良药,乌托邦式的爱情将真相解构得支离破碎,对“剩女”世界冰山一角的好奇窥伺暴露了影片的软肋。“剩女”的现实困顿涉及多重因素,女性意识的觉醒宣告了“他者”对自我的重新审视,而社会文化与世俗偏见却又束缚了她们即将张开的羽翼,性别冲突将长期存在。作为大众娱乐消费产品,电影本不具备特别的社会教化功能,但我们坚信,深入探寻潜匿于视觉符码下的隐形书写,社会进步与思想停摆间的矛盾才有迎刃而解的可能。
注释:
①(法)C·麦茨:《历史和话语:两种窥视癖论》,李幼蒸编:《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226页。
②吴菁:《消费文化时代的性别想象:当代中国影视流行剧中的女性呈现模式》,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63页。
③王志成:《暖男:新世纪都市语境中影视剧的男性形象建构》,《文艺争鸣》2015年第2期。
④傅守祥:《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悖论》,《兰州学刊》2006年第10期。
⑤(英)劳拉·穆尔维:《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张红军编:《电影与新方法》,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220页。
⑥张双昊、刘颖异:《论传播学视野下的新世纪女性电影》,《电影文学》2010年第3期。
⑦Fredric Jameson:“Postmodernism and consumer society”,London:Plato Press,1985,pp.114.
⑧罗钢:《叙事学导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0页。
⑨宋岩:《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社会性别分析》,《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⑩田芊:《中国女性择偶倾向研究——基于进化心理学的解释》,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第21页。
⑪高丙吉:《“剩女”现象的经济学思考》,《经济研究导刊》2010年第16期。
⑫刘利群、张敬婕:《“剩女”与盛宴——性别视角下的“剩女”传播现象与媒介传播策略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13年第5期。
⑬(美)罗伯特·麦克艾文:《夏娃的种子:重读两性对抗的历史》,王祖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页。
⑭王小波:《试析中国女性群体的分化与分层》,《妇女研究论丛》2005年第5期。
⑮金窗爱:《中国当代女性就业问题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第18页。
The Cruel Tenderness Behind Vision Feast——An Analysis of the“Leftovers Lady”Films in Recent Years
LI Qi,LIU Huan
Abstract:As a symbol of dominant ideology,films create an utopia that contains reality-concerned images,as a result,films usually have an influence on ordinary people’s value and life-style. The films about“leftover lady”describe love stories about leftover ladies in cites,telling audience that“leftover ladies”have an unique experience about their desire and living pattern,but ignoring the real problems of overage female youth. These films fail to reflect on social issues and humanity quality. Being advised by patriarchy in a“kind-hearted”method made by mass communication,“leftover ladies”in real society find it is hard to live in their own ways.
Key words:“Leftover lady”film;Pseudo-Environment;social labeling;sexual narrative;stereotype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大众媒介中的大龄女青年形象及其传播效果研究”(12CXW035);湖南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剩女’形象的媒介建构与引导策略研究”(14YBA271)
作者简介:李琦,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湖南长沙410081)刘欢,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南长沙410081)
(责任编校:文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