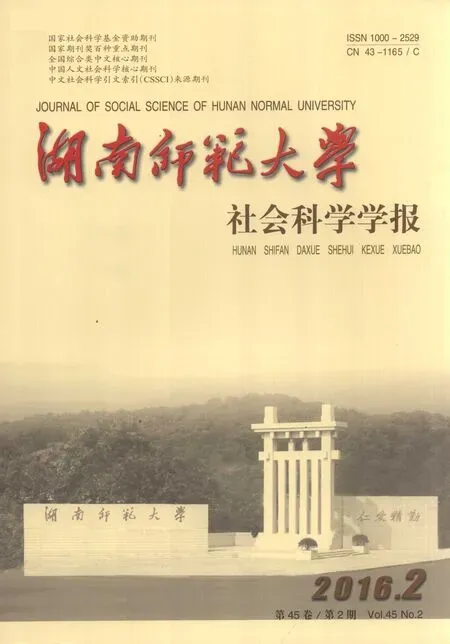晚清时期西方政治学引入的两种学术体系
——以伯伦知理与小野塚喜平次为中心的讨论
王昆
晚清时期西方政治学引入的两种学术体系
——以伯伦知理与小野塚喜平次为中心的讨论
王昆
摘要:1899年4月,《清议报》刊载的伯伦知理《国家论》译著,是西方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近代中国引入的滥觞。在此之后,各类政治学著述便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其中最主要的代表性著作即是小野塚喜平次的《政治学大纲》。伯伦知理与小野塚喜平次的相关著述,代表了这一时期引入的两种不同类型的政治学学术体系。前者建构的学术体系是以“国家”、“宪法”为基础,围绕与国家相关的诸问题形成的“国家学”学术框架。而在小野塚喜平次《政治学大纲》一书传入中国后,西方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从理论层面拓展到了公民社会,并特别强调对政治现象的研究,提倡引入社会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多种学科手段对政治学进行研究。这种变动与调整体现了政治学研究视野的扩展、研究体系的扩大与研究方法的扩充。
关键词:晚清;政治学;伯伦知理;小野塚喜平次;学科史
虽然政治学学科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经历了数次较大变动,但学者对其萌发、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史实和一般脉络还缺乏充分的研究,相较于民国年间政治学发展的研究,晚清时期西方政治学传入中国的历史追溯就显得更为含混不清①。本文主要梳理在民国建立前,西方政治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状况,并以文本为基础,探讨西方政治学在引入过程中所建构的学术体系,以及这种学术体系的变动与调整,由此展现出西方政治学在近代中国的不完全“传播”与“移植”。
一、晚清时期西方政治学著述传播的基本情况
对于政治学研究的本质认识,学界的看法并不统一。但有一点是被普遍认同的:即政治学的源起与国家(城邦)密切相关。如果把这种说法拓展开来,我们可以认为,不论是其源起,还是其最终的研究归宿,政治学都是一门研究国家与社会的学问。“政治学是各种各样的国家以及社会为了弄清直接面对着的于自身所处时代的诸课题,并把提示出的解决方法和策略作为自己的任务的科学”②。
西方政治学在近代中国的引入,实际上是清末民初西学东渐这一历史进程的一部分——换而言之,西方政治学并不是直接从西方传入中国;相反,日本成为了西方政治学传入中国的中转站,通过日本所转译而成的西方政治学译著,便成为了中国人了解西方政治学最早的理论来源。从1899年《清议报》刊载伯伦知理《国家论》译著开始,西方政治学的理论通过留日学生的翻译活动,在晚清知识群体间进行初步传播;其中,1899~1903年间,西方政治学译著大量涌现,而之后的七八年间,译著的刊载则相对平均。此外,1899~1903年间所译介的西方政治学著述的题材与内容,一定程度上影响或是说决定了此后七八年间晚清学人对西方政治学的理解与认知③。1899~1911年间,所译介的著述大多与“国家”、“宪法”有关,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清末时期学人所接受的西方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与学科内容。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伯伦知理的《国家论》译著便是西方政治学在近代中国传播的滥觞?
目前学界关于西方政治学在中国传播起点的界定,大多都采用王一程先生的说法,即“第一本政治学教材是一位德国教授讲演录的翻译本(1898年)”④,但这一说法并非确凿有据。在此,笔者以时间为序,对“第一本政治学教材是一位德国教授讲演录的翻译本”这一说法进行了学术梳理:
中国最早开设政治学课程的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1903年),第一本政治学教材是一位德国教授讲演录的翻译本(1898年)⑤。
在政治学研究方面,中国最早开设政治学课程的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1903),第一本政治学教材是一位德国教授讲演录的翻译本(1898)⑥。
在中国最早开设政治学课程的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1903年),第一本政治学教材是一位德国教授讲演录的翻译本(1898年)⑦。
中国从1898年出现第一本政治学教材——一位德国教授讲演录的翻译本和1903年在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最早开设政治学课程开始,就非常注重教材建设⑧。
在1903年时,京师大学堂的课程共分八科,其中就包括“政治科”,使用的第一本政治学教材是一位德国教授的讲演录翻译本,这是中国大学首开的政治学课⑨。
在中国,政治学课程最早于1903年出现在京师大学堂,其所用教材为1898年一位德国教授讲演录的翻译本⑩。
在上述笔者所列举的所有论述中,均没有指明“第一本政治学教材是一位德国教授讲演录的翻译本(1898年)”这一论断的出处,但与此同时笔者却关注到智效民先生的一个说法:“赵先生还说:既然要开政治学课,就需要政治学教材。中国第一本政治学教材是一位德国教授的讲演录(翻译本),出版时间大约是在1898年戊戌变法前后”⑪。引文中所说“赵先生”即是我国政治学界的泰斗——北京大学的赵宝煦先生。此外笔者还发现,赵宝煦先生曾在自己的回忆性文章中这样叙述过:“1898年……在北京成立了京师大学堂……到1903年……这是中国在大学中开设的第一门政治学课”⑫。事实上,也只有智效民先生明确指出了这种说法的确切来源,因而笔者进行大胆推测,上述学者所引用“第一本政治学教材是一位德国教授讲演录的翻译本(1898年)”的这种说法,可能来自赵宝煦先生的个人回忆,或者说极有可能是部分学者与赵宝煦先生交流后,采信了赵先生的说法,因而有了目前学界这一基本界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1998年编写的《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系史(1898~1998)》一书中,对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的起点界定也存在矛盾之处。例如该书认为“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的历史可以上溯至京师大学堂的仕学院”,但在1898年12月京师大学堂开学时,“课程仅设诗、书、易、礼四堂,春秋二堂”;直到次年,方才“另立史学、地理、政治三堂”;此后在1902年1月,京师大学堂又设立七科三十五目,其中“政治科下分政治学、法律学二目”⑬。因此,简单将1898年京师大学堂仕学院的设立作为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的起点(或者说是西方政治学在近代中国引入的起点),或许并不恰当、准确,且这一界定与上文中赵宝煦先生“这是中国在大学中开设的第一门政治学课”的表述相互矛盾。
此外,根据笔者已有的考证,尚未发现1898年出版的西方政治学译著,也没有发现相关的抄本和讲义录,因而笔者依旧把西方政治学在中国传播的时间界定为目前可以考证清楚的基本史实:即从1899年4月,《清议报》刊载伯伦知理《国家论》译著开始,西方政治学通过日本作为中介载体,逐步传入中国。
但是,由于晚清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冠以“政治学”之名而出版的各类著述为数众多,其流传与影响也相去甚远。西方政治学在清末的传播,除了以报刊、杂志刊载的著述作为媒介外,更多的是通过“单行本”的方式进行宣传。而报刊、杂志在很多情况下便成为了这些“单行本”译著的销售平台和著述内容的“试读”部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刊印的政治学著述并不是都畅通无阻地进行了售卖,并对知识群体产生影响。事实上,只有少数几本译著被清末知识群体广泛阅读,而其产生的实际影响也值得进一步商榷。有些译著因为经费原因,只进行了少量刊印甚至以抄本传播;而有些译著虽然已经印刻排版,但其实根本没有刊印销售;更有些译著,仅有销售的广告传单,但其实并未真正成书。
基于上述这些缘由,笔者根据熊月之先生编写的《晚清新学书目提要》,并结合周振鹤先生编写的《晚清营业书目》,将晚清时期各类报刊、书局主要刊印的政治学著述列表如下:

表1 1899~1911年各类报刊、书局主要刊印西方政治学著述一览表
通过表1所列书目我们可以发现,晚清时期主要传播的西方政治学著述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国家学”与“政治学”。而伯伦知理的《国家论》与小野塚喜平次的《政治学大纲》,则是这两类不同政治学著述的代表。事实上,这两本著作所体现的西方政治学学术体系也不完全相同,对政治学的定义内涵和研究路径也存有较大的差异。在下文的论述中,笔者将以这两本政治学著述的文本为基础,试图展现晚清时期西方政治学引入的两种不同学术体系。
二、伯伦知理与“国家学”学术体系
1899年《清议报》刊载的《国家论》译著,是伯伦知理“国家学”学术体系在近代中国的最初传播。这一学术体系主要涵盖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分析国家沿革的历史,从政教分立的视角阐释近代国家的形成过程;第二,提出“神道政治”的概念,对亚里士多德国体、政体的分类标准进行补充;第三,强调国家“有机体”学说,对卢梭的政治理论加以批驳。
伯伦知理关于国家理论的论述,首先是从宗教与政权分离的历史展开的:“至中古之世界,事之大有关系者,有二端焉,即基督教徒与日耳曼人之崛起是已。基督教徒,起而抗犹太罗马二国,自后遂蔓延于诸国。该教之兴也,原非藉王公之力,其主权又非受之于国家,不过托渺不可知之所谓天神者,以立宗旨。故自罗马国中有此教,而政教遂分为两途”⑭。
为了更加详细地论述西方国家政教分离的过程,伯伦知理甚至用1/5的篇幅来介绍王权与教权的艰难斗争。但令人诧异的是,伯伦知理《国家论》在清末的传播过程中却只字未提这一问题,而只是在开篇提到“迷溺宗教”的历史。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或许是因为中国从来没有政教分离的历史,因而也没有长篇大论的必要。
关于国体、政体的类型划分,伯伦知理的理论来源则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伯伦知理据此将国体、政体分别划分为三类,“古代希腊人别政体为三种,学者至今皆依据焉,曰君主政治,曰贵族合议政治,曰国民合议政治是也。亚利斯土路(即亚里士多德,引者注)稍改其名称,曰君主政治、贵族政治、合众政治。又别其变体,曰暴主政治、权门政治、乱民政治。盖主权者,能自制私欲,以谋公利,则目其政治曰正体,反之曰变体。世人多据主权者员数,以别政体,一人握政柄,误谬亦甚矣。夫政体之别,愿其政府之构成何如耳。凡天下邦国,必推一人以为无上之官,使之专当国事,唯此最上官之人品,可以决国体之种类。希腊人别国体各由其主宰者之种类,以附名称,亦以此故也”⑮。
但是,伯伦知理并没有全然接受亚里士多德对于国体、政体的划分理论,而是提出了“神道政治”的概念:“此三种政体之外,宜加集合政体一种,此说古代既有之,而今人亦往往倡之……盖三种外,更加神道政治一种,则始备矣……凡他政体,皆以人为君主若主宰者,独神道政治,以天神若人鬼为国之真主……议者或曰,神道政治,虽以鬼神为真主,然其实则奉命之人,代行其政,故亦不异于自余政体……以余观之,神道政治,元是一种异样政体,假令其实有纯然君主若贵族之代理者在,未可遽断以为君治政贵族政。何则以国家之主权归之于人,与归之于鬼神,与国家规模,固有大相径庭者也”⑯。
事实上,伯伦知理对“神道政治”却异常痛恨,认为其“鄙陋有害”⑰,因为“神道政治”就是让民众“迷溺宗教”的元凶,与近代国家的民主历程背道而驰。但值得注意的是,伯伦知理着墨众多所论述的“神道政治”在近代中国并没有产生重要的影响,众多学人采取“忽视”的态度对待之,这或许因为中国恰恰属于伯伦知理所说的“神道政治”的国家吧。当然,伯伦知理本人在其论述中也多次表达过对东亚国家政体选择的不满与不认同。
伯伦知理对于近代中国政治学发展最为重要的贡献则是其提出了“有机体”学说,这是伯伦知理针对卢梭学说的创造性发明:“国家有生气之组织体也……国家者,盖有机体也。然又非动物植物之出于天造者比也,实由屡经沿革而成者也……人之造国家,亦如天之造一种有机体也……国家之为物,元与无生气之器械相异。器械虽有枢纽可以运动,然非若国家之有支体(即肢体,引者注)五官也。且器械不能长育,唯有一成不变之运动耳。岂同国家可随其心之所欲,有临机应变之力乎”⑱。但从政治学学术发展的历史来看,在小野塚喜平次的《政治学大纲》出版后,伯伦知理“有机体”学说的影响力就每况愈下。
需要指出的是,伯伦知理并非是“国家学”学术体系的唯一代表,在学术体系上承接伯伦知理国家学说的,当属同为德国政治学学者的那特硁。目前国内学界对于那特硁的研究甚少,那特硁几乎成为一个被忽视的历史人物⑲;但从其实际的学术影响力来看,则非常有研究的必要,特别是那特硁的《政治学》一书,在清末时期有多个译本流传。那特硁在其著作的封面便直接指明“政治学(一名国家学)”,事实上,那特硁《政治学》在论述体例、内容阐释与研究视角等方面,基本都是伯伦知理《国家论》的扩充。
但是,那特硁对于伯伦知理的学说亦有补充,比如那特硁也提出了“神权国家”的概念,不过他把“神权国家”与“市民国家”、“封建国家”共同归类为家族国家的三种形式,这与伯伦知理所说“神道国家”的概念大不相同。此外,更为明显的就是那特硁提出了“善良政体”这一说法,并把“文明开化”程度作为政治自由的一个前提条件,这是伯伦知理所没有关注的地方,“夫政府形式美恶,但观历史发达之程度,与现在成立之事情可矣。假令形式不备,而能切中其程度及事情者,是亦善良之政体也。假令形式极为完备,而不切中其程度及事情者,是亦决非善良之政体也”,“故政治上之自由,只抵行于文明人民,彼未开化者,决难行之”⑳。除此而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伯伦知理《国家论》一书中,“公民”、“国民”等词汇的使用较为频繁,而那特硁则更乐于使用“臣民”这类表达方式,究其缘由是因为那特硁对于君主立宪政体的推崇,要比伯伦知理更加激进;立宪之国,当然会有君臣之别。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以伯伦知理与那特硁为代表的“国家学”学术体系内,“政治学”与“国家学”实际上具有相同的含义;而在这一阶段,“政治学”或是说“国家学”的研究视角主要是国家本身,例如国家的沿革与定义、国体与政体的划分等。而对于政治行为、政策研究这些我们今日熟知的政治学研究内容,“国家学”体系却没有涉及。相较于小野塚喜平次在《政治学大纲》中对于政治学研究体系的划分,笔者将西方政治学在近代中国引入的这一阶段称之为“国家学”体系时期,而小野塚喜平次则是西方政治学在近代中国引入的另一阶段最为重要的代表性人物,笔者将这一阶段称之为“政治学”体系时期。
三、小野塚喜平次与“政治学”学术体系
前文所述,伯伦知理的《国家论》与那特硁的《政治学》,都是以国家理论为基础,从国家的定义、沿革、分类等方面展开论述,基本上就是各种版本的“国家论”。而小野塚喜平次的《政治学大纲》则更多从学术体系的角度,对政治学学科本身进行了严格的定义,并特别地将国家政策列入政治学的研究范畴,试图解释社会现象背后的政治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小野塚喜平次的《政治学大纲》实际上呈现出另一种学术体系,即“政治学”学术体系。
晚清时期,小野塚喜平次的《政治学大纲》一书出版的次数与版本数都相对较多,其中商务印书馆刊印的《政治学》、北洋法政学报刊载的《政治学大纲》等译本传播较广。丙午社刊印的小野塚喜平次《政治学》的译本,在凡例中详细记述了该书的由来:“兹编为日本法学博士小野塚喜平次口授之讲义,更据同氏所著《政治学大纲》参证之,其他之增补,悉依同氏《帝国大学讲义》”㉑。但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刊印的小野塚喜平次《政治学》的译本则指明,该书是小野塚喜平次《政治学大纲》的升级版,相较于原来的内容进行了增补:“小野塚博士所著政治学大纲久已,风行于时第,详于国家机关而未及于国民行为,且于此学知应用亦引而不发,未达学者之望,是犹为其五年前之旧著也。侯官郑君篪归自东瀛出示其所述讲义二篇,则为博士最近之绪论,研究益精所以为此学。观察判断之标准者益详,且备东方”㉒。但笔者经过细致比对这两个版本的《政治学》译著,从体例到内容并无太大区别,因而不存在商务印书馆所说的“研究益精所以为此学”。至于上海商务印书馆为何这样介绍,或许是出于刊印和销售的考虑吧。
小野塚喜平次在开篇便回答了这一时期政治学研究的基础性、前提性,同时也是根本性的问题,即:何为政治学,政治学的定义与范围是什么,政治学与其他诸学科的关系为何。这是西方政治学在近代中国的引入过程中,晚清学人首次对上述这些概念进行系统化、理论化、学科化的了解与认知,这对于中国现代政治学学科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伯伦知理“国家学”的学术体系内,“国家学”等同于“政治学”;而小野塚喜平次则利用“广义政治学”与“狭义政治学”的概念,对“政治学”的定义进行了区分,“广义政治学者,合关于国家之种种学而成者也;狭义之政治学者,以国家事实之说明,及其政策基础之学也”㉓。
为了论述“广义政治学”的学科定位,小野塚喜平次以图表的形式明确指出了政治学与历史学、社会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的边界、区别与联系,并特意区分了法学与政治学的学科关系。事实上,西方政治学在近代中国引入的最初阶段,“法政”抑或是“政法”的这种说法,实际上并未对法学与政治学进行学科区分。而在小野塚喜平次进行“政治学”与“法律学”的概念区分后,“政”、“法”分科的趋势也愈加明显,这对于近代中国的学术转型而言,是影响深远的。
小野塚喜平次认为“国家学”与“政治学”的体系区分,实际上代表了“政治学”发展的不同阶段,“人类社会之现象,其关于国家者,即政治学也。日本所谓政治学、国家学诸名词,悉属广义;而广义政治学,与国家学同一解者。致有精理,盖关于国家现象之学,即为政治学。……自研究日精,而法律、经济等学,分枝别类,各成一科,而政治乃渐成狭义。……政治之学,苟其以相关各学,兼容并色,则研究愈难精密,此所以今之所称政治学”㉔。
换而言之,在小野塚喜平次“政治学”的学术体系中,“国家学”与“政治学”已不再具有相同含义的替代关系。“国家学”与“政治学”的概念区分,实际上标志着西方政治学在近代中国的引入进入了第二阶段,即“政治学”学术体系的初步构建阶段。
除此而外,“政治学”学术体系的另一个特征即是强调对政治现象的关注与研究。小野塚喜平次明确提出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是政治现象,“政治现象,即政治学之目的物也”㉕。在政治现象的研究中,小野塚喜平次认为需要重点关注国民在政治上的表现,即国民的舆论和政党的运行。虽然小野塚喜平次对政党的定义进行了学术化的规范,也试图用政治实践的实际去代替空洞的理论阐释;但其对政党运行的学术探讨,却没有太多涉及,因此也并未形成系统性的政党研究的学术体系与基本理论。
与此同时,小野塚喜平次还对国家的内治政策进行了特别的论述,并主要研究了社会劳工问题。小野塚喜平次在对社会劳工问题进行阐释时,引入了大量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例如“阶级”、“资本家”、“私有制”、“土地资本”、“均富主义”等词语,这是以往西方政治学在近代中国引入过程中所没有涉及的。但小野塚喜平次对社会主义并不持赞成的态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破坏少数之有财产者,使悉归于平等”,来达到“劣者为同等”㉖的目的。小野塚喜平次以“优劣”来划分社会群体,具有明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倾向。而事实上,在小野塚喜平次《政治学大纲》的第一、第二部分,对“阶级”概念的引用已然非常频繁。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学者在研究西方政治学时,对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和讨论,要远远早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认知;社会知识群体对社会主义初步印象的形成,也要早于苏联的十月革命与之后在中国发生的五四运动。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小野塚喜平次在《政治学大纲》中特别强调利用统计学的方法研究政治学,强调从政治现象、政治行为背后发掘深层的政治学因素,这些尝试与西方在20世纪上半叶所提倡的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有很多相同之处。“政治学研究之资料,即社会上之事实也,有统计学取社会事实而荟萃之,则便利孰甚。例如计某国某种犯罪之数,则可知其政教风俗;计某国财政上以某事经费与某事经费,比较其额之多少,即可知其政策之轻重之点”㉗。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不能因为小野塚喜平次在《政治学大纲》中强调实证研究就简单将之定性为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的“先行者”。但是小野塚喜平次特别突出了政治行为、政策研究的重要性,这在当时“国家学”体系的学术背景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正是这种研究视野的“下移”,为民国时期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范式的正式建立,提供了学术基础。
小野塚喜平次把政治学的研究从简单的理论阐释,转向了对社会政策、政治现象、国民行为的关注与探讨,而这些做法在“国家学”学术体系中是从未有过的。在小野塚喜平次“政治学”的学术体系内,西方政治学从“广义政治学”的研究视野渐变为“狭义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从对政治学理论的阐释渐变为对政治现象的关注,最终实现了从“国家学”的学术体系到“政治学”的学术体系的转变。
四、“国家学”与“政治学”的转换
需要指出的是,最初传播西方政治学的报纸杂志并不是抱有学术推介的初始目的,它们最主要的目的依旧是价值启蒙与政治变革。这种现象,可以通过冯自由的《革命逸史》窥见一二:“庚子以后,东京留学生渐濡染自由平等学说,鼓吹革命排满者日众,《译书汇编》、《开智录》、《国民报》缤纷并起,《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新湖南》、《江苏》各月刊继之,由是留学界有志者与兴中会领袖合冶为一炉”㉘。
同样,这一时期形成的特殊政治学传播连接载体,即“报刊——单行本译著——另一单行本译著”的连锁传播体系,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虽然清末社会知识群体所接受与认知的西方政治学相对单一,但是却很好地把握了两种不同体系与视角的西方政治学理论;进一步来说,西方政治学在近代中国的引入完成了从伯伦知理到小野塚喜平次的转换。当然,这种转换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清末部分学人的价值认同。或者我们可以认为,小野塚喜平次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伯伦知理在清末社会知识群体中的认知地位。
笔者在此需要特别指出,关于小野塚喜平次本人的学术定位,日本政治学界的看法并不统一。其弟子腊山政道认为小野塚喜平次的政治学研究体系已经从“德意志国家学中分离”,而私学系的学者例如吉村正则认为小野塚喜平次的著述“没有抹去国家学的痕迹”。笔者在本文的论述中,更加倾向于腊山政道的观点。虽然小野塚喜平次的《政治学大纲》仍有“国家学”的印迹,但是该书最大的学术贡献恰恰在于其特别强调了政治行为、政策研究的重要性。在小野塚喜平次其后修订的《政治学大纲》(1914年、1919年)中,这种学术取向则愈加明显。基于此,笔者认为,小野塚喜平次把政治学的研究视角从“国家”下移至“社会”、“团体”甚至是“个人”。
1901年,两广总督陶模在《奏请变通科举折》中明确指出,“今之所急莫如政治,宜专重政治一科,内分两门:一曰内政,所以学为理事亲民之官也;一曰外政,所以学为交涉专对之官也”㉙。这种分科方式与伯伦知理“国家学”学术体系对“政治学”的划分,基本一致。而在1907年京师法政学堂的教育章程中,则对“法律”与“政治”进行了分科教学,“臣等公同商酌,其课程拟分为预科、本科及别科。预科两年毕业后升入本科,分习法律、政治二门,各以三年毕业,俾可专精”㉚。此时使用的学科划分方式,则是小野塚喜平次的“政治学”学术体系。
事实上,“国家学”与“政治学”的转换并非仅限于政治学学科本身,其对于近代中国学术转型而言,亦有重要影响。学术分科的初步形成,则是这种影响的表现之一。随着西方政治学的深入传播,在“政治学”的学术体系中,学科的分类和边界愈加明显。中国传统的学术分科,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分类依据;西方政治学的引入,使得传统“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开始逐步向西方现代学术分科转变。但这两种分类标准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在学术转型的最初阶段,晚清学人往往是把西方的学术分类标准嵌套进“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模式中。
因此,“国家学”与“政治学”的转换实际上与西方政治学在晚清时期的传播程度有关。两种学术体系的转换,从另一个层面也可以看做是晚清学人对西方政治学理解的进一步深入。在此过程中,人们试图平衡“中学”与“西学”的主次关系。当然,西方政治学在近代中国的引入历程,以及“国家学”与“政治学”的转换,或许也可以当成是中国现代政治学学科形成的“史前史”。这一转换过程,为真正具有独立学科意义的政治学,在中国土地上的正式开展,提供了知识准备和学术基础。
五、结语
西方政治学在近代中国的引入应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在政治学学术体系建构中的表现,则是从“国家学”学术体系向“政治学”学术体系的转换。从《清议报》刊载伯伦知理《国家论》译著开始,西方政治学正式在近代中国引入。虽然目前学界将这一时间界定为1898年德国教授的政治学讲义录,但因为目前尚未有明确的历史材料加以支持与确认,因而笔者依旧把1899年《清议报》刊载伯伦知理《国家论》译著看成是时间界定的起点。
伯伦知理的《国家论》与小野塚喜平次的《政治学大纲》代表了两种不同范式的西方政治学学术体系——前者是“国家学”的学术体系,而后者则是“政治学”的学术体系。在“国家学”的学术体系中,政治学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国家本身,国体、政体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这种学术体系实际上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延续;而在“政治学”的学术体系中,小野塚喜平次则强调对政治现象的研究,提倡引入社会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多种学科手段对政治学进行研究,这其实也代表了西方政治学研究的范式转型。
西方政治学在近代中国的引入过程绝不是精英知识分子在清末各类报刊上刊载译著的简单罗列,而是知识分子群体对西方政治学的整体认知与价值选择。早期的精英知识分子试图建立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再到伯伦知理的完整的政治学学术渐变谱系,但实际上社会普通知识群体并没有这样的理解与体认。事实上,西方政治学在近代中国的引入应是一个移植与下渗同步进行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在政治学学术体系建构中的表现,便是“国家学”体系与“政治学”体系的转换。
但是,“国家学”体系与“政治学”体系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两种学术体系。在西方政治学传入清末的十年间,这种学术体系的转型是渐变而非突变。后者实际上是前者在研究视野层面的补充,将政治学的研究“下移”至政治行为与政策研究层面。由于伯伦知理与小野塚喜平次的著述在清末的广泛流传,因而事实上对民国初建后政治学研究范式的正式分野起到了作用。正是基于这样的缘由,笔者将这两本著述的内容,称之为两种“学术体系”。
晚清时期国人所接受的“西方政治学”主要是“日本政治学”的一部分(当然也有美国政治学的影响,例如伯盖司等人的著述);而“日本政治学”在学术体系上,又很好地承接了“德国政治学”。此外,与日本政治学的发展脉络相一致,近代中国政治学也出现了向美国政治学转向的趋势。当然,这种转向自然要比日本稍晚。民国时期,大量归国的留美留欧学生,为这种美国政治学转向的最终确立,提供了知识基础与理论准备。但实际上,西方政治学在近代中国引入的最大使命,并不仅限于此,它对近代中国思想文化、政治走向和社会思潮的启迪,要远甚于它在学术层面的影响。在清末的时代背景下,西方政治思想与西方政治学作为“新知”,在这个面临多重危机的“旧国”内生根,继而又发芽、成长。它们两者所产生的碰撞、冲突与矛盾,最终“挟持”着这个国家走向另一个新的时代。
注释:
①国内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主要有: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王向民:《民国政治与民国政治学——以1930年代为中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孙青:《晚清之“西政”东渐及本土回应》,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
②(日)内田满:《早稻田与现代美国政治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序言。
③相关研究见王昆:《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研究:1899-1905年》,《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2期。
④王一程:《当代中国的政治学及政治发展》,《政治学研究》2005年第4期。
⑤林尚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政治学》,见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参考资料选编》,北京:学习出版社,2006年,第457页。
⑥王邦佐编:《新政治学概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页。
⑦黄浩涛编:《人文社会科学100学科发展报告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07页。
⑧张明军编:《政治科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页。
⑨许耀桐编:《政治学》,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页。
⑩沈文莉编:《政治学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页。
⑪智效民:《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243页。
⑫赵宝煦:《中国政治学百年历程》,《东南学术》2000年第2期。
⑬萧超然、宁骚、王浦劬、关海庭编:《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系史(1898-1998)》,北京:北京大学,1998年,第1页,内部资料,未刊印。
⑭⑱伯伦知理:《国家学纲领》,广智书局,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第3页,第7页。
⑮⑯⑰伯伦知理:《国家学》,东京善邻译书馆,明治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第46页,第47页,第49页。
⑲目前国内学界对那特硁的研究极为少见,相关研究见孙宏云:《那特硁的<政治学>及其在晚清的译介》,《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3期;钟仕伦:《概念、学科与方法:文学地理学略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
⑳那特硁:《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光绪二十八年七月,第3-4页。
㉑小野塚喜平次:《政治学》,丙午社,光绪三十三年,凡例。
㉒小野塚喜平次:《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三月,序言。
㉓㉔㉕㉖㉗小野塚喜平次:《政治学》,《北洋法政学报》,光绪三十二年八月,第16页,第14页,第27页,第195页,第12页。
㉘冯自由:《革命逸史》(上),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21页。
㉙㉚璩鑫圭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5页,第569页。
Two Academic Systems Introduced from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Late Qing Period——Discussion Centering on Bluntchli Johann Caspar and Kiheiji Onozuka
WANG Kun
Abstract:In April 1899,Allgemeine Staatslehre,a book translated by Bluntschli,was published on The China Discussion,mark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into modern China as an independent subject. After that,various kinds of translated books about political science began to spread in China. Among them the representative work was Outline of Political Science by Onotsuka Kiheiji. Relevant writings of Bluntchli Johann Caspar and Kiheiji Onozuka represented the two different types of political science academic systems introduced in this period. The academic system constructed by the former was based on the“state”and the“constitution”,and it formed an academic framework of“theory of the state”focusing on relevant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state. While after Outline of Political Science,a book written by Kiheiji Onozuka,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es on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was expanded from a theoretical level to the civil society. Kiheiji Onotsuka emphasizes researches on political phenomenon,advocates studying on political science by introducing multiple disciplines such as sociology,statistics,economics. Such kind of change and adjustment indicate the expansion of political research perspective,enlargement of the research system and enrichment of the research methods.
Key words:The Late Qing Period;political science;Bluntchli Johann Caspar;Kiheiji Onozuka;disciplinary history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初建:1911-1929年”(16XNH070)
作者简介:王昆,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责任编校: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