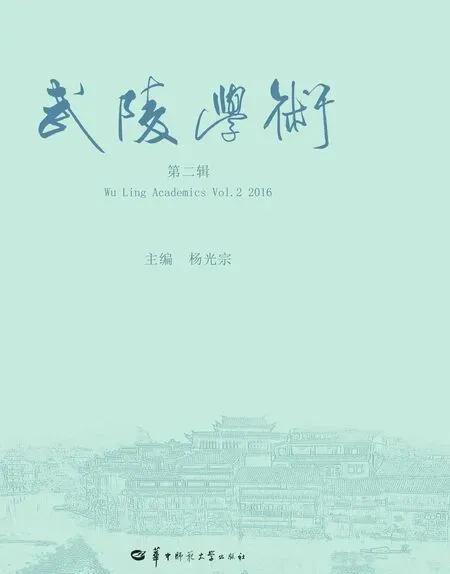从《尘埃落定》中的神话传说看藏族民间文化
毛 丹
(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湖北恩施 445000)
从《尘埃落定》中的神话传说看藏族民间文化
毛丹
(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恩施445000)
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大量引入并改写了藏族神话和藏族传说,这些藏族神话和传说深刻体现了藏族的民间文化,同时也体现了藏族的思想习惯和审美特征。如此既追溯了藏族古老而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与历史渊源,形成了作品厚重的藏族民间文化背景与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息,也成功地拓展了小说的思想、文化与话语空间,提高了小说本身的文化与艺术价值,同时向外宣扬了作者的本民族文化。
《尘埃落定》民间文化神话传说
民间文化是人类一切文化的源泉,各个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也都源自民间文化。民间文化指的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体现劳动人民的性格和情感的、从古至今一直存在于民间传统中的自发的通俗文化。从小受藏族民间文化熏陶的阿来具有较高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在他的小说《尘埃落定》中特别注重吸取藏族的民间文化。阿来在民间文化中寻找创作灵感与源泉,同时,他也以小说为载体来继承与发扬藏族民间文化。
一、 《尘埃落定》中的藏族神话
神话所叙述的是神或半神的超人所行之事,是古代先民对人类起源、万物的诞生的一种天真的想象和美好的向往,是各个民族或种族的生活和文化的反映。
藏族的神话种类丰富,与藏族的民族文化密切相关。阿来在《尘埃落定》中,由于创作本身的需要,他不仅大量引入了藏族神话,而且还以现代人的意识重新审视了这些民族神话。阿来在文本中继承了藏族有关宇宙起源与人类起源的两个神话,同时,为了让这两个神话更利于小说主题的表达、故事情节的安排以及叙事视角的确切,他又以自身的主观意识和文学的批判意识对这两个神话进行了一定的艺术加工和改编。
(一) 藏族的宇宙起源神话
宇宙起源神话是在人类文明萌芽时期,人们以一种原始观念对宇宙、天地、万物用天真的想象和幻想所作的虚构和描述。在众多藏民族的口传神话中,“五源说”神话是关于宇宙起源的神话中最广为流传的。小说《尘埃落定》的开篇便说道:“世界是水、火、风、空,人群的构成乃是骨头,或者是根子。”*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1页。除了“五源说”中的“地”没有提到外,其他的四种物质都在这里一一呈现出来了。第二次引用“五源说”是在描写傻子二少爷第一次与卓玛有男女之欢时。小说写道:“在关于我们世界起源的神话中,有个不知在哪里居住的神人说声‘哈’立即就有了虚空。神人又对虚空说声‘哈’就有了水、火和尘埃,再说声那个神奇的‘哈’,风就吹动着世界在虚空中旋转起来。”*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6页。这里作者对关于世界起源的“五源说”神话进行了适当的加工与缩写,作者运用了傻子的口吻进行叙述,使其具有随意性和口语化,除掉了宗教严肃性的色彩,这种改变增添了故事里人物形象的真实性和生动性。这看似信手拈来地对神话的引用,却是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上承第一次对神话的引用,以“尘埃”代替“五源说”中的“地”,为后文凸显主题奠定基础;而傻子与卓玛交欢又下启故事发展的情节:正是因为这男女交欢给傻子带来了无限的满足与愉悦,激发了傻子争取满足这尘世间的欲望和争取一切想要得到的东西的热情。所以,对于整个小说的主题来说,藏族宇宙起源神话的引入是具有深刻意义的。
阿来在继承藏族宇宙起源神话主体内容的基础上,由于创作主题和结构安排的需要,对神话进行了适当的改编。小说中,作者用“尘埃”代替了“五源说”中的“地”。之所以做出此种改变,原因在于小说的题目和主题,小说的题目是“尘埃落定”,作者借“尘埃”终将“落定”大地这一自然现象,来表达内心关于人生的哲学思考。尘埃是飘浮的、不稳定的。大地由尘埃构成,无论尘埃怎么漂浮和飞扬,最后的结局都是落入大地的怀抱,这是不可更改的命运,尘埃就如小说中的土司们,他们的矛盾纷争无论怎么激烈,权势无论多么强大,最后也免不了消亡的命运,尘埃落定于大地,便是他们的命运。
作者借宇宙起源神话故事文本奠定了小说的基调,同时,在小说中借助神话思维叙事,表现西藏特有的风情民俗、宗教传统和民族思维习惯,既可以避免对神话的继承仅仅停留在神话故事的层面,还可以使神话化为一种笼罩全文的神秘气氛,使整个故事具有了更鲜明生动的民族色彩。
(二) 藏族的人类起源神话
人类起源神话是在宇宙起源神话之后产生的,在汉族的人类起源神话中,人类是由女娲用泥土捏成的。然而在藏族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中,对人类的来源有着本民族独特的解释,即“卵生说”。“卵生说”称人类的始祖来自一个由五宝形成的蛋,苯教文献中最早出现了这种说法。
《尘埃落定》也引入了藏族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这些神话的引入,凸显嘉绒藏族的历史记忆,解释了藏族土司起源,包括土司起源的时间、地点、迁徙,以及土司和土司之间的兄弟关系等。不过,小说中所引用的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与文献所记载的及嘉绒藏族地区普遍流传的在叙述上有所不同,小说糅合了藏族关于人类起源于的“卵生说”神话,并加入了大鹏鸟在巨卵中“哈”出了九个土司的情节。作者根据情节构成和叙述方式的需要、做出了这样的改变,进行了适度的艺术想象。
从家族起源的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文中为了权势而争斗的土司们有着共同的祖先,身上流淌的是相同的血液。他们本是同为手足、相互依存、非常亲密的,为了家族的繁衍与发展,又互为姻亲,使这种家族关系更为紧密。这些有着相同祖先的土司们,他们既同为兄弟、互通姻亲,却因为土地和百姓相互对立、相互仇杀,权势与欲望使人性被扭曲,亲缘关系在权势的支撑下可以根据强权者的需要而改变,后来的茸贡土司把女儿嫁给傻子,也是为了使土司家族势力得以延续与扩张不得已做出的决定,并非是塔娜出于对美好爱情的向往。这些土司们为了虚妄的权势,而忘却了人的美好天性,在一切皆归于空的尘世追逐中,尔虞我诈,骨肉相残,上演了一出荒诞的“人间喜剧”,显示出权力争夺或欲望追逐带来的人性与亲情的蜕变。
作者对神话的加工一方面是出于情节安排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出于叙述方式的需要。只有改变文献中神话叙述的严谨性,使之变得更为随意,更加口语化,才更符合小说中“傻子”的叙述口吻。阿来的这一创造性处理,增强了作品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不仅如此,揭示权力欲望对人性腐蚀的主题,表现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典型性,增强了对文章普世意义的表现力度。
二、 《尘埃落定》中的藏族传说
传说是对民间长期流传的人和事的叙述。内容有的以特定的历史人物、事件为基础,有的纯属幻想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
神话与传说是民间文学中的两个不同概念,“从这两个词语的本义来看,神话作为初民以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作为原始社会整个神话时代的意识形态,其本身不仅带有极其强烈的时代色彩,而且在思维形式方面,也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即以艺术的维形式为限的。传说在严格的意义上说来,虽然也是指在文字尚未广泛使用以前所流传下来的各种事情说的,但它在今天的含义,显然已经打破了专指文字通行以前的时间界限,其意义已扩展到泛指过去所流传的事迹的记述和评价的范围”*知愚:《神话与传说的区别》,《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
(一) 藏族起源传说
“猕猴繁衍说”是在众多藏族关于其自身起源的传说中最广为流传的一个传说——即猕猴与罗刹女结合衍生藏人。此传说不仅在民间广泛流传,而且被载诸史册。据说在远古时代,藏南地区的一座山上住着一只猕猴,观世音菩萨点化这只猕猴和岩罗刹女结为夫妻,繁衍后代。生下来的小猴们吃了不种而收的野谷,逐渐演变成人类。
时至今日,提到这则神话时,当地的藏族人还能指出有关这则神话的遗址,包括猴子们采食野谷的山是索当贡布山,猕猴和岩罗刹女居住的山洞,群猴曾经在一起游戏玩耍的孜塘一带等,仿佛历史上真有此事发生似的。事实上,猕猴与罗刹女结为夫妻的传说不仅活在藏人们的口头上,也出现在藏族的英雄史诗《格萨尔》中,在西藏布达拉宫大殿里,色彩艳丽的壁画上,也有一幅猕猴与罗刹女结合繁衍后人的壁画。
在《尘埃落定》中,当僧人翁波意西被施行割去舌头的刑法后,发出第一声含混的叫唤时,小说里是这样描述的“有人说,黑头藏民是因为一个人受到罗刹魔女诱惑而产生的种族,也许,祖先和魔女的第一个后代的第一声叫喊就是这样的吧:含混,而且为眼前这样一个混乱而没有秩序的世界感到愤懑”*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50页。。翁波意西是一个爱思考且佛性很高的僧人,作者用藏族传说中的第一声含混的叫喊来表达翁波意西被割掉舌头后的痛苦和愤懑,然而,恰如传说中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以一声叫喊为标志,这一声含混的叫喊也预示着翁波意西在经历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之后的重生,尤其是第二次被割去舌头时,他已完全失去了语言的能力,然而他的思想不但没有受到抑制,反而越发强大和敏捷起来,整个人也显得越发地遍体生辉了。这凤凰涅槃般的重生,正如人类起源与进化的艰难和漫长的过程。同时,作者在小说中安排翁波意西这一形象也是别有用意的,人们在翁波意西身上仿佛看到了傻子二少爷的另一面,二者身上都有沉默寡言和喜欢思考问题的特点。
(二) 藏族人物传说
人物传说是以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为中心,通过想象、虚构等艺术手法来叙述这些人物的生平和事迹,以表达人们的某种愿望和对人物的评价。在人物传说方面,《尘埃落定》主要化用了“聂赤赞普的传说”。
“聂赤赞普的传说”的内容大致如下:相传第一代赞普是天神的儿子,他顺着天梯即彩虹降到人世。当他降临人世的时候,山川、树木、飞禽走兽等世间万物都在向他行礼致意。接着,12牧人以颈脖子作轿舆将他抬回帐篷里,并且推他为赞普。聂赤赞普得名在于藏语中的“聂”是“颈项”的意思,“赤”是“宝座”的意思,因他是12牧人以颈项为宝座被抬回去的,因此人们就叫他“聂赤赞普”。后来,他被推为了六牦牛部(另一说是六河谷部)的王,就成了吐蕃王朝的始祖,在藏族历史上称得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尘埃落定》将这则传说中的“聂赤赞普”化用在“傻子二少爷”身上。根据小说的描写,当傻子二少爷到边境地带赈济灾民、收获人心而又将自己家的粮食卖出了合理的价格后,他遭遇了来自爱情的考验。为避免与茸贡女土司正面接触后变得软弱,他躲到了草原的温泉中,寻欢完毕,两个贴身小厮用肩膀抬着他往宿营地走。然而,傻子并不知道,藏族高原上的第一个王在第一次来到人间的时候,竟也是被人以肩为舆抬回去的。类似的情节,小说后面还有一次,当傻子在边境地带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凯旋时,被彻底割掉舌头的翁波意西居然开口说话了,他告诉大家二少爷是能带给大家奇迹的神灵。然后,傻子二少爷又被两个壮年扛在肩上回去了。在这里,傻子二少爷就像藏族的第一位王聂赤赞普一样,赢得了百姓们的信任和拥戴。然而,因为他是傻子,最终也没能如历史传说般当上土司。
作者在这里化用民间传说,使傻子成为土司看起来是民心所向、天望所归。然而,小说的主题是土司制度不可逆转的灭亡的命运,是权力、欲望与尊荣在时间的销蚀中如尘埃消散的了然无痕。“傻子”在小说中既置身其间又超然物外的角色定位决定了他终于没有成为实实在在的土司。
从整体上看,民间传说所具有的情节离奇,充满浪漫的想象力与创造性的特点,这为小说《尘埃落定》的情节构造提供了借鉴。如果说,藏族神话为小说创作提供了一种哲学思维,使故事的开头在这种哲学思维的指导下具有了普世的意义的话,那么民间传说则为小说情节的离奇、丰盈与曲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创作方法。在小说中,作者对“傻子”神性的刻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如此。小说中的傻子像一个先知,在事情还未发生时,他就能够有所预见。西藏新教僧人翁波意西还远在天边,傻子就知道他牵着骡子就要到了。汪波土司派来的勇士的头在地下笑着,傻子便知道那笑容里有蹊跷(果然那耳朵里藏着种子)等等,他仿佛有一种先知的特异功能,众人都以为他是神灵附体。正是傻子身上的神性使得他具有了一定的传奇性。
《尘埃落定》是作者阿来借民间传说的手法来写藏族部落的发展史。把民间传说和历史现实结合起来的写作方法不仅增加了小说的神秘性与传奇性,而且使文本以历史史实为大背景,走进历史,较为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历史。阿来的这种创作手法,极大地拓展了作品的艺术想象与创造的空间,具有瑰丽的民族色彩,亦真亦幻,为文本增添了不少的艺术魅力。
三、 结语
阿来在小说《尘埃落定》中引用并有意识地改编了藏族有关宇宙起源的神话和人类起源的神话,表明作者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对民族民间文化的继承。作者在小说中借助神话思维叙事,表现西藏特有的风情民俗、宗教传统和民族思维习惯,使对神话的继承使用不是仅仅停留在神话故事的层面,而且使神话化为一种笼罩全文的神秘气氛,使整个故事具有了更鲜明生动的民族色彩。不仅如此,他还以自身的主观意识和文学批判意识对这两个神话进行了一定的艺术加工和改编,拓展了小说表达主题的艺术想象空间,让小说主题的表达更确切、更明晰。
同时,阿来在小说情节的安排上借鉴了藏族传说的离奇、浪漫、充满想象力与创造性的特点,使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神秘性和传奇性,增添了文本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如果说,藏族神话为小说创作提供了一种哲学思维,使故事在这种哲学思维的指导下具有了普世的意义的话,那么民间传说则为小说情节的离奇、丰盈与曲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创作方法。
毛丹(1988—),女,苗族,湖北恩施人,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文艺学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