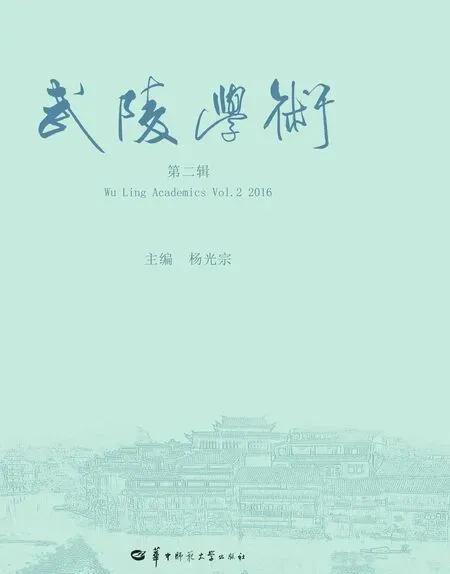“文学是人学”命题辨正*
佟建伟 李志宏
(吉林大学文学院 吉林长春 130012)
“文学是人学”命题辨正*
佟建伟李志宏
(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文学是人学”的表述不够严谨、准确。“文学”和“人学”是两个虽有交集但不相同的学科,不可混为一谈。“文学是人学”的说法是钱谷融先生对于高尔基“文学是‘人学’或‘民学’的源泉”表述的创造性阐释。这种说法旨在强调:文学是以“人”的社会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是对人的社会属性的审美表达。但不能因此而把该论断的语境和前提虚化,也不能把文学以“人”为中心置换为以“人学”为中心。“文学是人学”的提法所强调的“文学”要以“人”为中心、为主体,要重视“人”的价值,而不是将对人的描写作为“工具”和“手段”的启蒙理想却是不刊之论,在当下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文学是人学文学本性
“文学是人学”的观点因钱谷融先生的文章《论“文学是人学”》的发表而广为人知,并为大多数读者认同,影响深远。许多前辈学人已对命题的产生背景、理论意义和影响等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做出了肯定性的回应。但有生命力的理论命题都是开放发展的,需要深入探讨,因此这里不揣浅陋提出自己对“文学是人学”观点的一点质疑。
一、 “文学是人学”命题的缘起
提及“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这一观点是钱谷融先生直译和转引自高尔基的观点,因而有必要加以一定的历史回溯。
1957年2月8日,钱谷融在当时知名的《文艺月报》上发表了《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产生了轰动效应,“文学是人学”的观点为人们广为传颂。2001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钱谷融先生的专著《散淡人生》。钱先生在专著中的《且说说我自己》一文中对自己当年撰写《论“文学是人学”》的详情做了说明:“我原来在题目上是既未加引号,也没有‘论’字的,就叫做:文学是人学……引号也只打在‘人学’上,从来没有打在‘文学是人学’上过,那么,后来题目怎么会变成《论“文学是人学”》的呢?那是因为接受了徐杰先生的意见而改成的。”*钱谷融:《散淡人生》,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95页。而当我们翻阅钱谷融先生1957年的文章时,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高尔基先生曾经做过这样的建议:把文学叫做‘人学’”*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年第5期。。而诸多学者*如,吴泰昌发表在1962年7月18日的《文汇报》上的《高尔基的文学是“人学”辨》,刘宝瑞在1980年第1期《新文学论丛》上撰写的《高尔基如是说——“文学是人学”考》,发表在《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上的《关于“文学是人学”问题》。在翻阅查找相关资料并进行认真研究后,都撰文表示高尔基未曾说过“文学是人学”,而只是有过相关意思的表述。如1928年,高尔基在苏联方志学中央文员会议的答词:“首先,很感谢同志们给我这个荣誉,使我成为‘方志学’中的一员。但是,我仍认为我的主要工作,一生的主要工作是人学,而不是方志学。”*Горьлий Алексей Максимович.Ответное слово [на торже ствен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центра брюро краеведеоия ] // Собрания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ти томах.М.,изд.ГИХЛ(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 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 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49-1956.том 24,стр.373.而钱先生自己也说自己不懂俄文,只是知道高尔基有过相关意思的表述,而这相关意思的表述也是他从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中看到的*见钱谷融先生发表在1981年第1期《新文学论丛》上的《关于〈论“文学是人学”〉——三点说明》一文。。而1959年由莫斯科教育教学书籍出版局出版的季摩菲耶夫《文学原理》的修订版才注释说,这一提法出自高尔基的《论技艺》:“不要以为我把文学贬低成了‘方志学’,(顺便说一句,‘方志学’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不,我认为这种文学是‘民学’即人学的最好的源泉。”*高尔基:《论技艺》,《论文学续集》,冰夷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85页。但这里并没有说“文学是人学”,因而这一注释是不确切的。吴泰昌先生对这一论述做了语法分析后认为,“文学是‘人学’或‘民学’的源泉比文学是‘人学’的涵义确切、具体”*吴泰昌:《高尔基的文学是“人学”辨》,《文汇报》,1962年7月18日。。这就说明钱先生只是感觉高尔基有过这样的想法,而不是说自己真的是在阅读相关文献时亲眼看到过“文学是人学”的字样。换言之,“文学是人学”的观点是钱先生对高尔基观点的一种主观的归纳和解读。
二、 “文学是人学”应该在什么层面和意义上理解
“文学是人学”命题尽管似乎已成为文艺理论中的常识,但很多人并不是真正地理解其含义,不理解其提出的背景,也不知道“文学是人学”应在什么层面、什么意义上理解才不褊狭。“文学是人学”命题的确切指涉并不是从一般的角度谈论人,而是从文学意义上谈论人,从文学的表现对象和反映内容谈论人,因此不能把这个结论无条件的泛化。如果在理论和实践上以人学取代文学;以人学研究的对象,来要求文学的表现对象以及描写的对象;以人学意义上的人来规范文学意义上的人,这势必会影响文学的健康发展,因而,懂得“文学是人学”是在什么层面、意义上来说的很有必要。“文学是人学”说法的实际意义之一,是在表现对象层面上说,文学要以人为主要的表现对象,之二是在反映内容的层面上说,文学是对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的整体的审美的观照。
作家创作文学作品,赋予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以艺术生命,成功的文学作品中每一个具有艺术魅力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无疑都凝结着作家的心血,因而读者在阅读和鉴赏文学作品时,就会和作品中的人物息息相通,而这与文学艺术独特的表现对象有直接的关系。
文学作品一般都把描写的对象和表现的对象放在“人”上,文学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鲜活的、活生生的具有鲜明特色的人。这一点从理论家们以不同的视角对文学表现对象的相关论述中可见一斑。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摹仿者表现的是行动中的人”*[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8页。,“摹仿通过行动中的人物进行”*[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63页。,黑格尔在《美学》中很强调理想艺术的表现,认为理想艺术的对象是人。“使个别人物有余地可以向多方面流露他的性格……把一种本身发展完满的内心世界的丰富多彩性显示于丰富多彩的表现。”*[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04页。因为,人是自在自为的,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因此,要想使理念能够充分的显现,那就看怎么表现人,把人表现得完美的才称得上理想的艺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了以往的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的经验,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提出了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683页。的重要论断,强调文学首先应该是深入生活、表现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要把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及其生活当成文学艺术的特殊表现对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观点可以说是受了黑格尔的典型理论的直接启发。黑格尔的典型理论通俗地说就是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一旦成为具有典型性艺术形象时,共性一定要通过个性来体现。艺术形象是具体可感的人而不是抽象的概念化的人。如果人物形象没有自身的特殊性,那艺术本身的价值也是微乎其微的。也就是说,作家不应该是用概念来表述本质,而是以各种特殊形态来体现本质。也就是说,文学艺术不以概念为中介,不需要抽象概念这个间接性环节,它从感性的个体开始,向理性的内容深化,但理性却始终寓于个体表象的特殊形式里,偶然中包含着必然。
文学表现对象是关涉“人”的,文学可以通过塑造典型人物的形象思维方式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的真相和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这个层面和意义上我们用“文学是人学”来肯定文学的认识功能是言之成理的,但是我们不能离开这个前提和语境以偏概全把“文学是人学”的观点泛化。
文学艺术独特的反映内容是同它独特的表现对象联系在一起的,但二者又不完全是一回事。概括地来说文学艺术反映的内容是作家从审美的角度出发,经过作家艺术处理的,蕴含了作家社会意识、社会理想、审美意识、审美理想的,表现在作品之中的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的整体。进一步深入思考,我们还不难发现文学艺术的反映内容除了表现的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生活的整体性之外,其特点还在于文学艺术是从审美角度,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审美观照来表现人的生活和人生的诗意。
人是联结社会生活整体的中心和纽带,文学艺术写人,就必然会表现以人为主体的带有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社会生活。所谓社会生活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就是在社会生活中,诸如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改革等变革社会的实践以及科学、艺术等人类实践活动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诸如生产关系、阶级关系、伦理关系、友谊和爱情等人们的各种社会关系也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文学反映的是作为自然界的和社会生活的主体的人的生活,反映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及其错综复杂的实践活动和社会关系,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与自然科学研究内容的人以及社会科学研究内容的人相区别的,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物质的人,是研究人的自然生理构造和机能;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是抽象的人,是人的全部生活的综合与抽象,文学不像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内容那样,仅仅局限在某一个特定的领域,只研究某一特定的方面。文学反映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整体,并不是把文学作为反映的工具,并不是忽视这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恰恰相反,是以这个人为中心来反映整体的现实生活。
对于文学艺术反映社会生活的审美把握,别林斯基曾有较为合理地分析,他认为文学艺术内容具有诗的性质,而这诗的性质同生活本身所固有的诗的因素是分不开的。别林斯基说:“谁要想成为纸上的诗人,他必得首先在心灵里是一个诗人,能够本于自己的天性从现实的诗的一面去看现实。”*[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梁真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第111—112页。“大自然和生活,如果不被诗意所彻底浸透,也只能激起冷淡的惊异罢了。”*[俄]别林斯基:《文学论文选》,满涛、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435页。别林斯基的意思是明显的,文学要对社会生活进行“诗意”的把握,通过活脱脱的人的心灵反映社会生活,而不是从实践的角度、纯理性的角度。
人们的活动过程通常是伴随着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的共同参与,人的自觉的意识、明确的目标、目的、思想通常被称为理性因素,而人的感觉、感受、情绪等被称为非理性的因素。在文学活动过程中,人们按照一定的目标和动机来指导自己的写作,写作活动的性质主要是自觉的、目的明确的理性的活动,但同时在写作的过程中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作家当时创作心境、感情、情绪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传统认识中,人们一般把理性称为理智,对之抱有好感,表示肯定,而感觉、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被认为是浅层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因而受到贬低、否定。其实人类社会活动既需要理性因素也需要非理性因素,理性可以使人的活动合规律,使人接近和抵达幸福;非理性的因素使人的活动合目的,直接体验和享受快乐。文学活动的超越精神可以统合心灵世界中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实现感性的解放,使人活得更像人,这也正是文学艺术反映内容的独特性之所在。对于这种内容的特点,别林斯基称之为“诗意的”,我们今天称之为“审美的”,它是关乎人的心灵、情绪和情感的愉悦和满足。文学虽然也像科学一样,具有认识社会和自然的能力,甚至在特定历史时期,文学在社会上越俎代庖发挥了相当大的政治宣传、哲学反思、意识形态动员等众多复杂的社会意识形式的作用。但是,文学毕竟是文学,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因此出于强调文学审美地反应以人为中心的生活内容的整体性和全面性角度,我们可以略带夸张地说“文学是人学”,但文学毕竟溢出了“人学”的研究范畴。因为文学不是纯理性的科学研究,除了反思人的意识和理性,它还关注人的无意识和非理性所能涵括的情绪、情感、本能、欲望等各种关乎人生意义和幸福的复杂命题。
三、 辨正分析:“文学不是人学”
“文学是人学”命题在中国文艺理论界已成共识,该命题影响甚深,传播甚广,但如果在对之合理性进行考察、审视后,可以发现它并非毫无瑕疵,具有天然的合法性。
“文学”和“人学”是有着泾渭分明的内涵差异的两个概念,是两个具有不同属性、不同研究范畴,拥有不同表达形态的不同学科。文艺理论界对“文学”含义的界定不尽相同,但古今中外,却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广义的文化含义和狭义的审美含义”*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页。,广义的“文学”泛指一切口头或书面语言行为和作品,是一种广义的文化现象。而现代世界,狭义的“文学”通常是指具有审美属性的语言行为及其作品。而“人学”的含义比较确定,就是指“关于人的学问和科学”*王双桥:《人学概论》,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页。。
“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是由“文学”和“是人学”构成的主谓句、判断句,主语是“文学”,谓语部分是由判断动词“是”和宾语“人学”构成。“是”放在主语和宾语之间有多种作用,一般表示事物等于什么或属于什么,表示两个事物在属性上的相通之处。例如“老舍是《骆驼祥子》的作者”、“牛是反刍动物”,按照正常逻辑,从语法关系上看“某某是什么”这一句式,前后两项须是具有相同属性的已知项,而在“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中,是试图把“文学”变成“人学”这两个不同属性、范畴的已知项,这就违背了正常命题的逻辑。也就是说,“文学”不能“是”“人学”。文学就是文学,具有区别于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不能是其他的别的什么事物。相同的道理,人学也只能是人学,不能是其他事物所“是”的,“文学”与“人学”二者是不同的“事物”,不同的学科,不同的领域,如果“文学”“是”“人学”,那么,就无所谓文学和人学了,二者就成为一个东西、一门学科了。正如刘为钦先生所言“‘文学’和‘人学’不是谁包含谁,谁隶属于谁的两个集合,也不是两个全等的符号,而是两个相互交叉的系统”*刘为钦:《“文学是人学”命题之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第171页。。
“文学是人学”命题在中国文艺理论界确实曾有重要的意义和巨大的影响,但不能对之过度阐释。特殊的政治年代,文学也有着特殊的身份和地位,终于在改革开放后回归自己的本位,文学理论繁荣发展,学术百家争鸣,百花开放。有的学者说“‘文学是人学’命题牢固确立了文学的人学基础”*朱立元:《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文学是人学”命题的再阐释——兼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学基础》,《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9期,第7页。,那么如果文学真的是以人学为基础,那我们将置审美性和意识形态性于何处呢?严格说来文学应以“人”为基础,而不是“人学”,这应是“文学是人学”命题表述不准确的症结所在。正如钱谷融先生自己所言:“文学要达到教育人、改善人的目的,固然必须从人出发;就是要达到反映生活、揭示现实本质的目的,也还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年第5期。
站在新的世纪,对“文学是人学”命题进行审视,其学理性依据的缺乏以及自身局限性也是较为明显的。“文学”不能“是”“人学”,文学有其自身遵循的特殊规律。审美性是“文学”的一个本质属性。即便文学在进行心理描写时要按照心理的法则去描写,描写自然时,按照自然的规律去表现,但是整体上创作文学作品要按照文学自身的规律——“美的规律”去合理安排结构,从而使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达到有机统一。
如前所述,说“文学是人学”是从文学的表现对象和反映内容两个层面上来说的,文学的表现对象要以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为中心,文学通过塑造一系列的形象化体系来体现自身的本质规律。但只能说人是文学描写的中心,而不是文学描写对象的全部,文学的描写对象除了“人”之外,还有更广阔的天地。“文学是人学”命题本意在于强调文学特别重视研究人的社会性。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特殊内容和特殊形式的辩证统一,文学和人学也不例外,都有其各自特殊的内容和形式。“严格意义上来说,作为一门学科的‘人学’在中国是发轫于文学界,而形成于哲学界”*刘为钦:《“文学是人学”命题之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第168页。,致使“人学”与“文学”等部分涉猎“人”的学科一直纠缠在一起,文学对本属于“人学”的具体内容也曾孜孜不倦的研究过,但文学对于“人学”的部分信息和学问有研究不到的,也没有必要非要研究到。不论怎么说,文学也不可能把“人学”完全地都研究到,毕竟这是两个学科。只能说二者有交集,构成了一定的互文关系,而不是说二者可以相互等同和替代。文学是对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关系整体的审美反映,不能说“文学”是关于人的科学即“人学”的全面研究。因此“文学”只考察和关涉“人学”的审美维度,因此不能等同于“人学”。只能说“人”是文学的出发点、联结点和归宿点,而不能说“人学”是文学的一切。在人文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一切都容易贴上“人”的标签,似乎未能贴上“人”的标签就是错误的,这只是一种矫枉必须过正的权变的逻辑。对“文学是人学”命题进行反思,可以纠正人们认知的偏激。当然我们应该正视“文学是人学”命题在特定时代曾发挥过积极的历史影响和思想启蒙作用。
四、 “文学是人学”命题提出的深层动因及对现时期文学的启示
我们已经对“文学是人学”命题进行了合理分析,“文学”不能是“人学”。“文学是人学”命题提出的应有之义是要说“文学”要以“人”为中心,为主体,要重视“人”的价值,而不是将对人的描写作为“工具”和“手段”。正如钱谷融先生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中所说的那样,要“把人道主义作为世界观中对创作起决定作用的部分,作为评价文学作品最基本的、最低的标准,作为区别各种创作方法的主要依据”*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文艺研究》,1980年第3期,第9页。。钱先生是从文学的任务、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等角度论述“人”在文学中的中心、主体地位的,只是当时好多人都曲解了钱先生《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本义,而对之展开了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敌我问题的批判。如果按照钱先生的思路走下去,接下来就应是正面阐述“文学”以“人”为中心、为主体的意义以及对于文学创作的现实意义。
新时期以来,文学以“人”为中心,成为文艺理论界不言自明的金科玉律。人性、人情、人道主义在新时期之前一直是理论研究和艺术创作的“禁区”,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权利长期得不到关注,甚至是长期的被压制、残害和践踏。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普遍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随着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大讨论,文学逐步确立了“人”的中心地位,回到正常的轨道。正如一些学者所言“‘文学是人学’的命题重提并再度张扬,是树立在新时期文学回归自身的新生之途上的第一块路碑,也是新时期文艺学主体伸张的第一个标志”*张婷婷:《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四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98页。。
历史地看,“文学是人学”提法确实起到了极大的积极影响和作用,确实展现了理论的概括力,它把文学的出发点看成是描写人和人性,认为文学的基本要求是弘扬人道主义精神,但它使文学牢牢确立的并不是“人学”基础,而是“人”为中心。它为文艺学的研究清理出了必要的场地,从而促进了文艺学的整体推进和突破创新。
回顾过去,审视当前,面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文学以“人”为中心,有鲜明的现实意义。而且,在当前的社会主义社会,文学以之为中心的“人”不是抽象的,不是具有低劣情欲、落后意识的人,而是现实社会中作为“人民”的人。
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和中国市场经济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成熟。随着包括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形式的大众传媒依托电子技术、微电子技术、光纤通信技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真正开始面向大众传递信息,大众传媒已超越时空的局限,汇集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日益显示出文化传递、沟通、共享的强大功能。这致使许多文化问题已经大大超越阶级、阶层、经济、政治制度,带有“文化全球化”的色彩,加之西方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文化市场的自发性和传媒的商业性使得文学以“人”为中心再度迷失,变成以感官刺激、官能欲望、经济利益为中心。有些部门和单位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为了能吸引观众的眼球,不顾社会效益,肆意生产、销售品位低下的文学作品;有些作品借消遣娱乐的名义,以荒诞、庸俗的内容,迎合低级趣味;有些作家单纯追求轰动效应,热衷于捕风捉影的“炒作”,不断产出各种打着创新名义实则打破道德底线的作品。“文学”不再丰富人的精神,启迪人的情感,不再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物形象,不再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一切致使文学一步步走向“边缘”,淡化在人们的视野,使得文学界出现“文学死了”、“文学会消亡”的呼声。
在文学领域内,钱谷融先生说:“一切都是为了人,一切都是从人出发的”*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文艺研究》,1980年第3期,第9页。,也就是说文学必须以人为中心、为主体。我们所提倡的,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灵魂的人道主义精神。文学只有坚持以这样的“人”为中心,才能保障文学的审美性,注重对人的美好心灵的塑造,促进文学、文艺理论的蓬勃发展。
结 论
“文学是人学”命题的产生有特定的政治、文学生态和历史语境,这一命题在后来的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和研究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重大的作用,我们对其意义和地位是加以肯定的,但是在对其进行审视、反思时,还是应注意这一命题应有的本义是文学要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人学”,应注意该命题要在什么层面上来说,要注意它的意义与局限,谨慎地对待其使用的对象范畴,“文学”毕竟不是“人学”,人是文学描写的中心,但却不是文学描写对象的全部;人是评价文学的一个尺度,但并不是唯一的尺度,文学还有其自身应遵循的特殊规律,不弄清文学意义上的“人”与一般意义上的“人”之间的区别,将“文学”与“人学”相等同,就容易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以人学取代文学,以人学研究的对象来要求文学描写的对象,以人学意义上的人来规范文学意义上的人,以人学的社会功能来衡量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不能是“人学”,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其特殊内容和特殊形式的辩证统一,文学也不例外,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含有“人学”以外的其他成分和领地。
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不可避免暴露出表述和内容上的瑕疵,对待文学理论不能抱残守缺,而是应结合新的实践对之进行新的阐发。对“文学是人学”命题缘起和应有本义应有确切的理解和认知,这样才有利于在新世纪、全球化的语境下扎实推进我国文艺理论的当代建设。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期文艺理论建设与文艺批评研究”(项目编号:12&ZD013)的成果。
佟建伟(1991—),男,蒙古族,黑龙江泰来人,吉林大学文艺学硕士,专业方向为:文艺美学。李志宏(1953—),男,山东淄博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