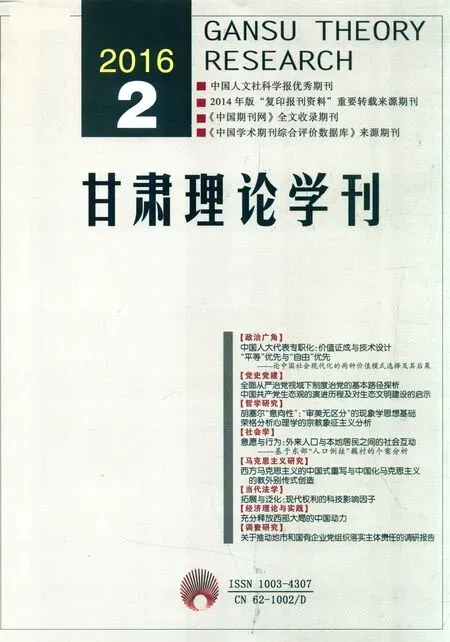拓展与泛化:现代权利的科技影响因子
征汉年
(南京师范大学 法学院,南京 210023)
拓展与泛化:现代权利的科技影响因子
征汉年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南京210023)
[摘要]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使得现代权利主体、内容也随之膨胀与扩张,涌现出大量的新型权利纷争和诉讼,通过司法确认或社会认可的方式促进了“权利生成”。权利拓展中,具有正当性、合理性、现实性的诉求,经过实践的沉淀,转化成新型权利,同时也伴随着权利泛化、虚化和空化,或者说是权利发展中“非常态”的一种权利,是人的道德情感和权利意识对权利的“超前”诉求。科学技术实践是权利生成的基础,权利生成是科学技术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权利拓展的一种积极性肯定。
[关键词]权利;拓展;技术;逻辑
权利现象是法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核心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实然上对人们的工作环境、生活方式、思维模式以及精神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必将使得现代权利发生“应然性”的变化。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必然对权利体系的拓展产生积极的推动力,“公民获得参与社会治理的更多权利”[1]151。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权利意识的增强转向,为现有法律权利的实现提供了基础,也“为新兴权利的产生提供了赖以孕育的土壤”。[2]225可以说,科学技术进步与经济文化发展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动因,也是权利拓展的基础性因素。现实生活社会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产生了众多变化,“民众权利意识和维权行动更加显性化”,[3]66涌现出大量的新型权利纷争和诉讼,以致法院审判价值功能产生了“实然性”转向,即从传统的从“解决纠纷”与“维护权益”转向现代的“定分止争”与“实现正义”的价值取向,并“承担一种以对权利救济为目的的‘生成权利’的功能。”[4]42通过司法确认或社会认可的方式促进了“权利生成”,成为丰富和完善现代权利体系的重要途径。
一、现代权利的科学技术因子
21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在提升人们的工作技能和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的同时,对传统的权利问题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权利生成”、“权利拓展”、“权利泛化”和“权利虚化”等现象交织在一起,权利的主体、客体和内容出现了扩张、拓展和泛化的趋势。在没有网络的时代里,不可能出现所谓网络侵权、网络诈骗、网络金融、网络政治、网络群体事件等问题,也不存在与网络关联的相关权利。当今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现代社会里一种重要的公共权力,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为人们带来便利,还能营造更舒服的生活环境。“由于技术进步的作用,发达工业社会虽是一个不自由的社会,但毕竟是一个舒舒服服的不自由社会。”[5]4现代技术对现代民主政治产生了必然的影响,形成了新型的民主共识载体,即把人们所掌握的技术力量,“使用于从事生产的和进行交谈的公民的共识”。[6]54在现代社会中,人的社会化实际上变成了人的工具化和人的技术化,“技术变革的民主化愈味着赋予那些缺乏财政、文化或政治资本的人们接近设计过程的权利”。[7]8某种意义上讲,人性的“贪欲”无形之中激发了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追求,科学技术成了“为满足人的欲望而设,”[8]28并刺激着人们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而推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
无论是从哪个角度,其所追求的是能够解析人及人所处于的世界。回顾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对人类社会管理和权利扩张的撞击:1948年美国数学家诺波特·维纳(Norbert Wiener)提出了控制论,1949年美国的另一位科学家克劳德·艾尔伍德·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提出了信息论,1968年奥地利科学家路德维希·冯·贝塔兰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 )提出了一般系统论,1969年比利时科学家伊·普里戈金(I.llya Prigogine)提出了耗散结构理论……等等;近年来,西方科学家还提出混沌理论、非线性理论等等;最近,物理学家宣布探测到引力波的存在。[9]随着现代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科学家可以“克隆”山羊、修复细胞、合成生命;谷歌的无人驾驶技术、苹果的语音识别技术“SIRI”、IBM的“沃森”计算机,智能机器人代替人的工作,数字技术成为推动社会的主动力,科技成为人们生活、工作、学习等各个方面离不开的助推器。从某种意义上讲,生物遗传工程技术(细胞再生与复制、基因识别与克隆等)使人类“生命体”变成了“DNA编码序列”与“蛋白质的碱基序列”的剪接、合成、调序与重组,“科学+技术““实现着对生命本身的控制。”[10]8正如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使得现代权利主体、内容也随之膨胀与扩张,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控制性”、“工具性”与“联动性”导致整个现代生活全球殖民化、目的合理化。因此,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浪潮之中,“有必要将技术进步与生活实践之间的边界和联系加以反思。”[11]26
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对政治环境和法律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早在1947年,德国著名社会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马克斯·霍克海默(M. Max Horkheimer)(1895-1973)在《启蒙辩证法》中,断言科学技术也是一种意识形态。[12]122其后,德裔美籍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指出,科学技术进步像意识形态一样控制人们的行为。[13]6-101986年尤尔根·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系统阐述了“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14]11991年,美国技术哲学家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也译为费恩博格)在《技术批判理论》中指出,技术系统是一个“政治批判和行动的客体”。[15]26安德鲁·芬伯格在1995年在《可选择的现代性》中指出,随着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民主与政治文明必然需要科学技术“工具理性”呈现其“现代性”,“社会民主化需要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的保障,”。[16]23科学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新型文明形态,特别是科学技术与社会民主诉求在机结合起来后,为民众产生更为广泛的社会权利客体,并且通过立法程序或司法裁定将这些权利“客体”转化为法律权利。当然,某项“新兴权利”的产生往往是拥有此类技术的人员首先享有,但“随着这项科学技术的大众化而为众人所拥有。”[17]2-8
观察人类社会发展史,科学技术产生于与社会环境以及社会条件相关联,科学技术所产生的效果也“被特定的社会系统吸收、转化、扩散和实用化。”[18]19在特定社会环境中,还从技术理性变成政治理性,“技术理性的思维方式中蕴含着对人的统治逻辑。”[19]19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型政治力量,将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进行“改造”与“变革”,以“现代法治化”的国家治理模式成为社会极权的“聚合物”,形成了科技化、信息化、网络化社会治理结构,控制着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认为,知识包括科学技术是一种“特殊权力”,体现了统治的内在需要,并成为统治意志的表达工具,“知识和权力”操控着整个社会,“现代社会就是一个大监狱”。[20]343-348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既是生产要素,也是生产发展的动因,体现了权力、资本和利润的某些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性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目的合理性和科学技术的工具性,科学技术的现代性没有本质的差异,科学技术发展成为新型“公意”影响着现代社会的权力结构。科学技术的应用面对理论与实践交叉选择的“囚徒式困境”,当人们利用科学技术创造性“征服”大自然,获得了生活方式的改善,却由于“过度”滥用技术造成“生态失衡”反而降低了生活品质。在现代社会里,赋予生态环境种种权利,使得人们尊重自然环境的权利成为了不可回避的论题。
人与科学技术是什么样的关系?从科学哲学的视角来看,人与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主体”与“手段”的关系,工具性、现代性与科技性成为当今人类社会生活的主要特征,“技术与人的存在具有共生性。”[21]29在人与自然、人与科学技术方面,主要依赖于人类谋生能力包括科学技术水平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谈不上科学技术时,那时的权利与义务是无法分清的;当科学技术还处于“幼稚”状态时,人们主要认识和利用自然界提供的现成条件而生活,此时人类基本上是自然界的奴隶,人类所拥有的权利是非常的微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的到来,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人类利用体力和智力(形成的劳动能力)向自然界“索取”,而是以物化了的科学技术向自然界“索取”。生产力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类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同时,人们的权利客体和所指向的对象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毫不夸张地说,科学技术革命就是权利革命的推动力,也是权利拓展的技术因素和决定因素。
二、权利主体与客体的拓展
(一)权利主体拓展——以“环境权”为例
权利是一个动态的、共享性的概念,权利体系需要不断的丰富和发展。随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类开发和应用自然资源的能力日益强大,人们生活水平也得到了稳步提高,人类在提高和改善自身生活质量时,也带来了对自然环境滥用和破坏的负面效应,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在我国,粗放增长型经济运行方式使得我们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当今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 个城市,有13 个在中国”,[22]51“资源耗竭、环境恶化”的危机敲响了警钟,特别PM2.5、雾霾以及空气质量污染问题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近几年,人民群众对环境污染的关切度非常高,对保护环境的呼声愈加高涨。然而,将生态环境作为权利的主体,还是权利的客体?学术界和实务界仍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学术观点的分歧使得环境法学呈现多样化,“学科的多样化有助于民族文化素质和思维水平的提高”。[23]59
从西方国家发展史来看,西方工业革命后,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资本的扩张,对环境资源掠夺式的开发,引发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也引起西方学术界对环境生态的高度重视,西方生态环境主义者认为,与人类一样,生态环境也拥有权利。基于对生态环境问题关注视角与分析工具的差异,目前形成了两种理论研究路径:一种是伦理学的生态主义(有学者翻译为:环境伦理学或生态伦理学),另一种是生态技术批判主义。伦理生态主义的理论主旨从批判人类“支配自然”的理念入手,主张把人类的伦理范围延伸到大自然(生态环境)。生态技术批判主义的理论主旨从科学技术造成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侵害式开发为切入点,指出生态危机的根源于资本主义发达的科学技术。[24]64-65对环境生态问题的理论研究,实质上是在致力于建立一种新型生态哲学范式,形成“以自然存在论为基础的生态世界观”、“以环境价值为核心的生态价值观”、“‘以生命同根’为前提的生态伦理观”的范式框架。[25]14-17
从学术史的视角来看,1869年威廉姆·勒基(William E . H . Lecky )在《欧洲道德史》中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应当被视为一个受伦理控制的道德问题。[26]35这一思想的提出,成为自然权利的启蒙理论基础。1916 年美国生态学家弗雷德里克·克莱门茨在《植物演替》中,论证了植物群落是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27]175,自然环境有着自身的规律和特征。1923年法国哲学家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或译:史怀哲)在《文明的哲学——文化与伦理学》中,提出了生态环境伦理学的主张。[28]111971年,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法律哲学教授克里斯托弗·斯通在《南加利福尼亚法律评论》上发表了题为《树木拥有法律地位吗》的论文,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应当“把法律权利赋予森林、海洋、河流以及环境中其他所谓的‘自然物体’——即作为整体的自然环境”。[29]155进一步提出了“环境权(生态权)”的存在问题。1974年,澳大利亚哲学家J·帕斯莫尔在《人类对自然的责任》中指出,人类具有保护大自然的义务和责任。1975年,美国联邦法院将Byram Rive“河流”作为权利主体出现在司法文书中。[30]231986年美国环境哲学家保罗·泰勒(Paul Taylor)在《尊重自然:一种环境伦理学理论》中,阐述了以“天赋价值”为中心的“生物平等主义”伦理学。1987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罗德里克·纳什博士(Roderick Frazier Nash)在《大自然的权利》[31]1-166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有关大自然权利的伦理、道德、思想和法律。1996年,日本学者山村恒年在《自然的权利》中,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自然权利有关的主张和观念,提出了保护自然环境的内在价值。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学术界开始掀起对大自然(环境)权利研究的热潮。早在 1982 年,蔡守秋先生提出环境权是法律上的权利,[32]29-39其后在《环境政策法律问题研究》、《环境资源法学教程》和《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反思与补充》中对“环境权”进行系统论证和研究,蔡守秋教授认为,“所谓自然体权利,又称环境的权利,包括自然个体和自然整体的权利”,[33]403并立足于大自然权利的角度,对传统法理学理论进行反思,提出了调整论,构建了“主客一体”范式。1995年,吕忠梅教授提出环境权“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的新型权利。”[34]63其后,2000年吕忠梅教授进一步指出,“公民环境权是一项独立的、基本的人权。”[35]129同年,汪劲教授在《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 一书提出了现代环境立法主要围绕保护人类的“环境权”与生态世界的“自然的权利”这两大目的。[36]132-135同年,刘敏在《论环境的法律地位——从“伦理的权利”到“法律的权利”》的博士论文中论证了在人类域界内“环境“以其特定形式享有“固有的权利”,[37]9-98并“具有法律主体资格及相应法律地位”。[38]272003年,周训芳先生在《人权视角下的环境权研究》一书中强调,环境权是现行法律权利家族中的特殊权利,是人类社会权利结构中的一种权利。[39]156-1822004年,中国海洋大学徐祥民教授指出,“环境权是自得权”,是以“自负义务履行”保护“自然环境的人类权利”。[40]138其后,学术界对环境权研究形成了“井喷”现象, 2006年于忠春在其《人权视角下的环境权研究》博士论文中指出,环境权是一项独立的人权,环境权的精神是人与自然相和谐 ;[41]1-1102012年王开宇在其《生态权研究》博士论文中指出,“生态权是一个新兴的权利形态。”[42]20-92近年来,部分高校的博士论文还围绕环境权司法保障、环境相邻权等为主题进行了深入细仔的研究。[43]9-112
综观国内关于环境(生态)权利的研究,有不少学者认为:由于受人类中心主义和主、客二分法的影响,传统的环境法律关系中,“人和人的共同体或集合体”是法律关系的主体,环境(生态)始终处于法律关系的客体或内容的地位,“人类始终是世界的主宰和评估”,因而,人们制定和实施的法律始终保护着“人类的权益”,所谓的“环境权益”是建立在人类利益保护的基础上的一种特殊保护形式。综观迄今为止的国内法律,始终没有能改变“环境”是“客体”的境界,即使2014年4月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起施行)中,环境在法律关系中依然是“客体”或“内容”,这是人们在环境保护立法方面的主要缺陷。在“人类中心论”的视野下,“人”的“主体性”成为不容置疑的法律关系的“主体”,尽管这些与环境相关的法律有着许许多多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止污染和保护生态的条款,甚至《环境保护法》第六条规定了“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但是,这些条款都是以“人的利益”为核心,力求维护人类的“长远利益与现实利益的最佳结合”、“实现人类的根本利益最大化”的需要而制定的,最根本的是体现:“人是环境权利的主体,”“环境权是人所享有的,”[44]77人及其“人与人的共同体”永远是世界的主体。
我们认为,任何一个概念都有内在的界域及限度。“大自然拥有权利”的概念是环境哲学提出的一个与时俱进的崭新思想。“自然本身是一种权利主体”,[45]92是对“物种歧视主义”和“人类沙文主义”的最为现实的解构,“构成了权利扩展的下一个逻辑阶段”。[46]171从某种程度上讲,传统法学理论中,环境是法律关系的“客体”地位,容易导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蹂躏”、“宰制”环境而毫无“道德上”的负罪感,面对“史上最严厉”《环境保护法》,再狠的“重罚”,本质上仍然是“经济为主的行政处罚”。从系统论与控制论的视角来看,人与环境(包括大气、海洋、河流、土地、矿藏、植物、草原、湿地、野生生物等等)构成一个开放式、互动式的系统工程,整个系统中的每个要素都相互依存的,具有“共生互存”的内在逻辑关系。“顾此失彼”式的保护和维权方式,使得“人与环境”“同构”的世界系统“整体性”与“利益性”受到抑制和损害,从而使得世界系统失衡和折损。可以这么讲,法律应当具有公平正义的灵魂,秉持“实质正义”和“分配公正”并重的理念,真正起到“社会关系的调节器”与“利益福祉的天平称”的功效,努力让“人与环境”之间构建起和谐、纯朴、友善、良性的“共生互存”的新秩序,以全面维护“人与自然”系统的平衡与有序。为此,有必要进行法律理念的革命和司法理念的转向,赋予环境及生态系统在法律上的主体地位,使它们获得应有的法律权利,从而保障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五大新理念”得以实现的一个有效途径。
众所周知,任何权利都是一定社会主体的权利。在法治社会里,社会主体往往体现为特定的法律关系主体,而法律关系主体的“再生”和“重塑”是权利主体拓展的重要表现形式。法律权利应具有 “正当性”、“利益性”与“自由性”的“本体”实然,而不是简单的“主体”、“免于外界侵害”、“积极行为”三个要素[47]201互证式的“话语循环”。环境作为权利的主权,无论从环境伦理学的“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其目的是重构自然环境在人类社会中的固有地位和价值取向,重新培塑起人与自然环境的新秩序,同构起“天蓝”、“山清”、“水秀”和“人善”良性运行的愿景。人类应当以更加“理性”与“平和”的心态,将环境与人们自身放到“同等”地位上进行“对话”与“互动”,以人类的“自我束缚、自我规制”来求得人与自然的“共同解放、全面解放”,在法律上赋予环境的主体地位,重构起际域之间的“规则体系”,作为解决“人与环境”困境的重要路径。就现阶段而言,可以通过拓展法律主体来实现和保护环境权利,扭转传统哲学思维影响下的法律关系架构的认识偏差,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互动、友善与同构,从而促使人与(生态)环境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将生态环境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仅仅将人类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
人类中心主义将环境伦理归结为以(生态)环境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行为规制和责任担当,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在人与(生态)环境的价值理念认同基础上,维护(生态)环境的权利和整体利益,尊重和实现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内在价值,归根结底就是:为了人类利益必须遵循环境的内在逻辑。从生态伦理学的视角来评判环境作为权利主体,更多地是立足于“敬畏生命”的人类中心主义,正如法国著名哲学家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又翻译为“史怀哲”,1875-1965)所言:“善就是保存、促进和提升生命,而毁灭、伤害和阻碍生命则是恶”。[48]314辩证地看待西方环境伦理主义,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它们之间并非存在实质意义上的冲突和张力,“在生态伦理中通过人的主体性的升华实现了两者的统一”。[49]78为此,构建环境权利,强化人类对生态环境权利的保护,形成对自然界的尊重和热爱。对环境权利的正当性而言,在社会规则体系中存在着一个不以法律为惟一根据或先决条件的权利,这就是“应然权利”。应然权利“有着深沉的人类学基础和道德意味。”[50]11人类为了实现自身的发展,不断向自然界攫取资源,工业革命以后,特别随着科学技术不断提升,对自然资源攫取和破坏的程度更加严重,从而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状态。因此,人类摆脱环境危机的根本途径应当将环境享有权利主体地位,赋予内在的价值和生存权利,这样才会有对生命和环境的尊重,才会有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从现代权利理论上讲,赋予(生态)环境法律主体地位,重新建构起复合型的权利关系,这种新型的权利“不仅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还将调整人(社会)与自然之间关系”,更重要的是凸现了环境的内在价值和生态善治,“在环境保护问题上摒弃以人为中心的法律价值观,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51]71-72在环境权利理论构建方面,我们要警惕机械地“把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套用到人与环境之间”,防止“把从人所信奉的法律或道德规范中推导出来的权利”简单地“标识为自然体所具有的价值。”[52]69不能仅仅将“权利”进行“符号化”和“标签化”,随意到处“乱”粘“乱”贴,使得“权利”成了解决“人类”与“它类”之间“万能的钥匙”,否则,“权利将不成为权利。”[53]26应对人类面临的新问题——环境危机,需要更多的理性思维,在对环境作为权利主体的证成中,应当更加客观、全面、务实地构建环境权利理论体系,诠释环境作为权利主体的必然和应然,并从环境公益诉讼等司法途径来构建具有现实意义的环境权利,防止人类对自然资源掠夺式的开发和污染式的应用,努力构建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绿色、共享的社会关系。
(二)权利客体拓展——以“网络虚拟财产权”为例
随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尤其是网络技术进入千家万户,人们拥有了“现实世界”和“网络世界”(又称:“虚拟世界”)。网络世界产生了全新的虚拟生活方式,出现了网络通讯账号、网络游戏账号、网络游戏装备、网络虚拟货币等诸多新生事物,当然也产生了新的问题、新的矛盾与新的纠纷。从司法上来看,追溯至2003年9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网民(李某某)诉网络游戏运营商(北京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侵犯私人财产”案件,即,国内首例“网络虚拟财产”纠纷争议案。同年12月,一审法院作出判决,认定网络游戏“生化武器”具有价值要素,[54]3-4使得“网络虚拟财产”进入司法保护的视野。其后,在江苏、陕西、广东等地法院也出现类似的“网络虚拟财产”的诉讼,经过法院的审判,确认和保护“网络虚拟财产”诉求得到了支持。当今,承认“网络虚拟财产”具有法律关系上的财产性,已经成了主流观点,欧盟、美国、印度、日本、韩国等国家都有相似的判例,通过司法裁判的方式确认“网络虚拟财产”的现实价值。
就学术界而言,对“网络虚拟财产”是何种权利属性?是知识产权客体,是新型的财产,还是特殊的物,至今仍然众说纷纭,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和意见。综而观之,关于“网络虚拟财产”法律属性的学说主要有:
一是电子数据说。此理论认为,所谓“网络虚拟财产”不过是存储在网络服务器中基于电子数字技术载体形成的数字、文字、符号、图形、字母等各种数据和资料,是一组在网络之中进行交换的电子数据流。在网络游戏过程中,网民玩家通过“积能”、“升级”等方式取得游戏人物的“装备”和“武器”,是一种网络“娱乐”过程,不能视为“劳动”过程,不具有现实的价值意义。因为作为网络游戏计算机编程来讲,这些网络游戏中的“武器”“装备”是一系列“二进制的数据”,这种数据一旦编制完成,就可以大量复制。此理论认为,“网络虚拟财产”在现实世界中没有明显的效用和功能,它在网络虚拟世界中的效用和功能具有虚拟性,与真实财产有着本质的差别。[55]150
二是知识产权说。此理论认为,“网络虚拟财产”是一种新型的知识产权客体类型,因为虚拟财产存在着其固有价值,网络游戏中的“武器”和“装备”决不是简单的一堆数字编码,它包含着一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就是包含着一定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商家们开发网络游戏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智力和物力,开发出具有新颖性、娱乐性、创造性且具有可复制性的“游戏装备”等,并期盼通过“网络游戏”获取现实利益,因而游戏玩家们想获网络游戏“武器”和“装备”,主要是花钱从网络游戏开发商处直接购买、或者是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网络游戏“积累”获得、或者从虚拟的货币交易市场上获得,这种具有可以买卖、馈赠和转让的网络游戏“武器”和“装备”具有商品的属性,具有类似于知识产权及其使用权转让的特征。
三是新型物权说。此理论认为,“网络虚拟财产”区别于数字财产、虚拟财产、知识财产、信息财产和实物财产,主要是指“存在于网络环境中,能为人们控制和支配,具有有用性和独立价值的电磁记录”,[56]87包括网络游戏装备、网站网页……网络空间账号、网络虚拟货币等。虽然“网络虚拟财产”具有“无形性、虚拟性和可复制性”,可是“网络虚拟财产”与民法上的“物”的所有权具有相同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基本权能。此理论认为,可以将“网络虚拟财产”确认为一种特殊的物,归入物格,可以理解为存在于网络虚拟空间的“抽象物格”,完全可以纳入物权的范畴。[57]96-97
四是债权凭证说。此理论认为,从法律属性上看,“网络虚拟财产”是一种网络环境下的网络游戏开发服务商与网络游戏用户之间形成的合同债权(Contract Creditor's Rights),即:网络游戏玩家拥有网络游戏的使用权,实质上是游戏玩家与游戏服务商之间通过合同而确立的特定请求权,这种虚拟财产权的行使需要相对人的履行义务作为前提,“网络虚拟财产”并不能独立存在,只是这种债权呈现动态扩张的趋势和物权化特征。将“网络虚拟财产”权利作为债权的“凭证”,并予以“物权化”的法律特征,“通过物权特征与债权属性的功能互补”,力求将“网络虚拟财产”上体现的各种社会关系得到更为全面的保护和实现。[58]
五是信息财产权说。网络虚拟财产“产生”、“存在”、“流转”、“使用”和“处分”于网络空间中,表现为特定的信息、符号或者数据形成数字编码。从法律实务界来看,在现代社会中,财产除了实物形式(有形财产)之外,还有非物质的(无形的)财产,在不以创造性、新颖性、实用性为基本条件的信息(数据)成为财产时,在此类“新型财产”面前不能简单地用“知识产权”加以描述,它区别于传统的“知识产权”,是权利客体在网络时代而产生扩张导致了传统财产观念变化的结果,应当将“网络虚拟财产”从传统“知识产权”、“新型物权”的体系中“剥离与细分”出来,应当将这种融合“知识产权、债权和特权”[59]84的财产,“名至实归地作为信息财产权的保护对象。”[60]2-6
尽管“网络虚拟财产”具体的法律属性尚无定论,但是网络游戏等“网络虚拟财产”的发展突飞猛进,据宇博智业市场研究中心发布的《2014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称,2014年我国网络游戏市场规模达1144亿元,网络游戏用户约5亿多人[61]。2015年12月,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等发布的《2015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称,2015年我国网络游戏销售收入达1407亿元,同比增长22.9%。[62]虽然“网络虚拟财产”市场交易总量不断屡创新高,但是“理论上对于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仍没有定论”。[63]2142015年,中国游戏(包括客户端游戏、网页游戏、社交游戏、移动游戏、单机游戏、电视游戏等)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1407.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9%。2015年,中国游戏(包括客户端游戏、网页游戏、社交游戏、移动游戏、单机游戏、电视游戏等)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1407.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9%。2015年,中国游戏(包括客户端游戏、网页游戏、社交游戏、移动游戏、单机游戏、电视游戏等)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1407.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9%。2015年,中国游戏(包括客户端游戏、网页游戏、社交游戏、移动游戏、单机游戏、电视游戏等)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1407.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9%。 近年来,“有 61%的游戏玩家有过网络虚拟财产被盗的经历”,[64]22而且网络游戏盗号现象已经成为网络新型“盗窃”形态,[65]57不可否认,随着网络技术发展和普及,这样的“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还会不断的增加。
我们认为,“网络虚拟财产”是一种依赖于网络环境而存在的权利,网络“虚拟”仍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有”,而非“无”。 从权利的保护角度来讲,对传统意义上并不认为是财产的权利,应当进行重新的审视和分析,对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型财产赋予权利,给予更多的关注和保护。从权利要素构成进行解析,“网络虚拟财产”具有权利的属性、要素和维度,它具有主张、资格、请求、利益、自由和能力等权利要素,且从道德、社会和经济三个维度证成“网络虚拟财产”权利本原的应然性和实然性。
第一,“网络虚拟财产”具有权利的道德维度。“网络虚拟财产”是“科学技术发展促进社会分配正义新常态”的必然结果,具有“社会正义”生成的内在逻辑,更是科学技术发展对人类社会生活影响并固化下来的“正当诉求”。作为权利的道德属性,必须是“正当的事物”,而且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理念要求,在权利理论学上讲,所谓权利的道德维度——正当性,是指权利的行为自身或行为所依据的准则是应然的,或者“行为结果的非道德因素的‘善’大于‘恶’”。[66]129现实社会中,人们对“网络虚拟财产”进行占有、管理、控制、利用和处置,是由于“网络虚拟财产”具有特定的使用价值,从而基于该“网络虚拟财产”的形成,而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符合人们的生活追求和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在社群主义视野里,“权利是一种生活或生存的方式。”[67]7虽然“网络虚拟财产”的表现形式是基于网络虚拟世界,但是,当事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客观、真实、正当的。
第二,“网络虚拟财产”具有权利的社会维度。英国新黑格尔主义主要代表人物T.H.格林和B.鲍桑葵认为,“权利是通过承认而形成的”。[68]61作为权利,需要得到社会或法律的确认、或者人们的普遍认可。在科学哲学的视域上,“网络虚拟财产”不仅作为社会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也是有自我意识的社会产物。西方新意志主义认为,权利体现在特定的人际或域际关系中,主张或者请求在法律上和道德上,某人的“意志”或“选择”优越于他人的“意志”或“选择”,“权利即为权利主体在意志选择上的优越性。”[69]281倘若禁止其他人实施实施这种特定行为,且仅仅允许某人可以这样去“做”的资格,这是权利的实然形态。简而言之,“权利是法律赋予主体的能力或者是意志的支配力”。[70]169比如,网络游戏的“武器装备”是特定网络游戏主体专用的“物品”,其他人未经“网络虚拟财产”所有者的允许或者同意是不能使用其“武器装备”的,这体现了在特定人群中网络游戏玩家对“网络虚拟财产”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上的“意志选择的优越性。”
第三,“网络虚拟财产”具有权利的经济维度。网络虚拟财产具有一定的稀缺性、价值性、独立性和可支配性。“网络虚拟财产”能够满足主体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需求。“网络虚拟财产”具有一定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在现实生活中,比如网络游戏的玩家为了获得“武器装备”,通常需要投入时间、精力、智力以及金钱。在交易市场上,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 “网络虚拟财产”因“需求”的存在而实然地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并形成相应的市场细分与繁荣,从而反证网络虚拟财产“具有交换价值,从而具有变现的有用性。”[71]97当然,“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还具有一定程度的非稳定性、非确定性和非客观性,有时表现为一种“潜在的财产”而未必得到实现。[72]149“网络虚拟财产”随着科学技术发展,自然会形成相应的技术管理措施和权利实现系统,特别是在数字技术环境下,权利人通过编码程序在网络“数字作品”、“游戏装备”、“虚拟技术”、“网络平台”以及“云计算商业模式”等中设定权利管理系统,可以“控制用户使用作品(游戏、技术、平台、空间等)的方式”,[73]49使得权利的利益方面得到有效的保护。
我们认为,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对权利的经济属性形式“载体”发生了变化,过去将财产主要看成是物质的,后来认为财产以货币(贵金属)来体现,而在现代社会里,社会价值才是财富的本质属性。在网络时代里,新闻模式、搜索引擎、知识分享、传播渠道、电子商务、即时通讯、社交模式、娱乐应用等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网络社会以TCP/IP协议(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Internet Protocol)为基础并借助UDP服务技术(User Datagram Protocol)和OSI(Open System Interconnection)对网络中生成的权利进行管理、控制和实现。虽然“网络虚拟财产”以数字化形式(编码)存在着“特殊性、概然性、复制性、弥散性”的特质,但是并不影响其本身的财产权属性,这仅是其存在的“介质”而已。科学技术给人类的权利载体创造了更丰富的“介质”、方式和路径,权利的存在并非是由于“介质”或“载体”的变化而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权利的本原依然是“正当、利益、自由”的融合,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网络虚拟财产蕴含精神价值和经济价值”,是权利人所拥有的在法律上给予合理保护的财产。[74]75从某种意义上讲,网络虚拟财产是现实世界中人类劳动和财富的科技化,这种科技化主要表现为网络化、数字化、信息化。
综之,“网络虚拟财产”具有财产属性,是法律意义上一种新型权利,表现为一种债权化的物权,应受到现行法律的保护。因此,早就有学者对保护网络虚拟财产提出了立法建议:将网络虚拟财产归类于法律上“其他合法财产”,并通过修改现行法律条文,增加关于虚拟财产保护的内容,[75]77抑或扩大司法解释将网络虚拟财产纳入保护范围。[76]142随着网络技术不断发展,以网络为载体的新型财产表现为多元化和多样化,为保护网络虚拟财产,“时机成熟”时可以对“网络虚拟财产法”进行单独立法。
三、 “权利”主体和客体的泛化
近年来,权利泛化是一个学术热门话题,但是对权利泛化的概念尚未有公认的界定。权利泛化是公民权利意识提高的表现之一,权利意识提高体现为人们对权利现象理性探索与非理性诉求的同步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讲,权利泛化是人的权利情感中对权利的“过度”诉求,表现为人们在“超前”权利理念的影响下,对法定权利(含法律权利、道德权利等)以外的利益或者主张或者要求,“诉”以法定权利的救济方式来寻求救济的现象。[77]73权利泛化现象主要表现为主体泛化和客体泛化,最典型是“动物权”和“泛人格权”的问题。这类泛化的“权利”,有一部分拓展了现有权利体系,也有一部分泛化的“权利”因缺乏经济、政治、社会及法律的理性支撑而走向了“权利”的虚化。
(一)权利客体泛化——以“泛人格权”为例
随着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加快,人民群众期盼全社会“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尤其是随着文化教育的大众化,人们对法律基础知识有了一定了解,甚至可以通过电视、报刊等媒体,潜移默化地对法律意识的不断强化,必须导致整个社会的权利意识日益高涨。法律被人们看成是“正义”的化身,司法人员被看成“守望正义”的捍卫者。在发生纠纷时,人们越来越喜欢“拿权利说事”,“人们的行为总是在一定的权利意识下,”[78]67用法律维护其权利与利益。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对“什么是权利”、“权利是什么”似乎并不重要,关键是“权利”到底能带来什么?[79]7从现代功利主义视角来分析,在权利意识不断觉醒的过程中,必然引发权利观念日益膨胀,在“法无禁止即自由”理念的影响下,[80]27旨在实现其在私人自治原则容许最大的自治空间,[81]121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人们的“权利诉求”的扩张化、普遍化、草根化、时尚化、戏剧化甚至是娱乐化。
近年来,在我国法院的民事诉讼中,陆续出现了诸如“初夜权”、“祭奠权”、“安静权”、 “相思权”、“眺望权”、“聊天权”、“拥抱权”、“性福权”等诉讼案件*近三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受理案件数超过了1500万件,特别是从2015年5月1日施行立案登记制后,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大幅上升,具有“权利”诉求的案件增幅最大,当事人有的“权利”是纯粹“独创”出来的,有的“权利”是逻辑“类推”出来的,还有的“权利”是想像“虚构“出来的……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新型“权利”之诉,“为了权利而诉”成为当今司法不得不面对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考量着法官的司法智慧和创新魄力,为当下社会“创造”出一系列“新”权利。,在宪法和行政法学术界,有学者提出“请愿权”、“公职权”、“公决权”、“营业权”、“发展权”等“权利”入宪的建议,还有民法学专家提出了“声音权”[82]103-109、“形象权”[83]51-58等人格权,这些不仅拓展了学术理论探讨,而且也激发人们对此类新兴“权利”的企盼,在社会现实与人们想象之中“碰撞”许多“新奇”的权利“诉求”。在司法实务界,对此类所谓“权利”之诉的受理、审查和裁判给人们很多的启迪,也产生了不少的“困惑”和“迷茫”。在学术界,对于阐述、解读、证成此类所谓“权利”的学说和理论,成为学者们课题立项和论文发表的“新的增长点”,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的学说和观点,但也不乏存在一些“奇谈怪论”的“权利学说”,以“猎奇”式、“叛逆”式论证路径来解读这类所谓的“权利”。
我们认为,这类所谓“权利”的提出,需要道德或法律的证成与证否,特别那些与人格权相关联的时尚“权利诉求”,其中,部分“权利”可以通过立法或司法判例转化为法律权利,但是也有部分所谓“权利”只是人格权“泛化”甚至人格权“虚化”和“空化”的具体表现。何为“泛化”?“泛化”原指由特定事物扩大到一般性“类元”的过程。何为“人格权泛化”?是指将“权利”标签“贴”到尚未完全成长为“权利”的某些人格利益上,标榜自身为“权利”。从权利实现的角度讲,有些所谓的“权利”并非都能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护,有些所谓“权利”将只能停留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之中,缺乏法律法规和社会常识的支撑,成为“虚化权利”,并背离了权利体系发展的内在逻辑,成为昙花一现的“时尚传奇”式的权利“愿景”。
自然权利植根于传统自然法之中,具有“应然性”,而不是简单的“天赋人权”衍生出来的“现代性”。有些“所谓权利”只是某些利益集团或某些个人的利益诉求,没有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甚至部分“所谓权利”缺乏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基础,在现有的经济、社会、科技条件下,不宜转化或上升为法律权利。不断高涨的现代权利意识,推动新兴“权利”的生成、发展和完善,同时也衍生出权利的泛化、虚化和异化。“概然性”权利经过国家意志或社会“共同意志”的确认,才有可能成为“实然性”权利。这种“共同意志”最根本特征就是表现为“公意”。[84]71美国著名法学家德沃金指出,“法律是社会共同意志的体现”,“是社会共存的基础”。[85]15在当代社会里,特别是在公权力高度集中的现今,以“权利保障和法治化”的名义,公权力越来越强的渗入和控制着家庭、学习、娱乐和游戏等领域[86]12,当权力借助“权利”泛化的由头,通过立法形成“权利”保护和“社会”治理的法律,往往导致法律越多而越背离现代法治轨道的“怪胎”。在法治建设中,倡导对个体价值的重视,同时还应当关注社会价值,在社会系统工程中构建和谐、平等、互动的权利与权力“对话体系”,尤其是“需要反对权力和权利的绝对化倾向。”[87]16-17
从社会发展史的视角来看,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促进了人们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以至当今社会成为权利社会,权利成为时代的“强音”。尤其在权利意识淡薄的传统社会里,社会治理传统思维以及权力(命令)意识的“惯性”,影响了权利的生成、成长、完善和发展。但也应当看到的是,为了博取社会公众的眼球和媒体的关注,当事人过多的以“所谓权利”被“侵权”为由而提起诉讼,或者以“时尚”的“权利诉求”来获取利益,不仅会造成社会司法成本的增加,还将会导致司法公正性的扭曲与伤害。在社会治理体系中,以规则体系为核心,但是整个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法律规则的功能,还包括道德规则、民间规则的互动。虽然有些所谓的“权利”,具有主观价值判断上的“正义”性,但是还不宜通过法律手段进行调整,可以让其在民间评判与社会辨别之后进行筛选与培植,过多国家强力的介入以及司法裁判的干预,并不一定有利于“新兴”权利的成长和保护。
就公权力而言,权利离不开法律的确认和保护,法律是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规范,权利体系不是在真空中运作的,无论是积极权利还是消极权利的确认,常常需要借助国家强力的再现和介入。在现代社会里,公权力同样具有不可逆转的扩张性和滥用性,正如米歇尔·曼(Michael Mann) 指出现代国家通过法律、规则、制度、行政等方式对公民生活、产业布局、经济调整、社会发展实现了全面介入,对社会全方位的“国家干预”[88]56-57前所未有。国家公权力的有效实施,除了国家层面的强制力度大小、传导体系以及实施方式之外,还受国家与社会组织、民间机构之间的“融合结构”的影响,并受到民众对权力的普遍信赖程度的制约。从对国家权力制约主体上来看,普通民众、社区精英、民间组织和区域社团等等对国家权力的制约程度呈现一种递增函数关系,同时“他们有着与国家机构不相一致的效用函数和运行逻辑。”[89]121
从权利发展的视角来看,正当利益的法律维护具有必然的正当性,虽然有些超前的利益或主张或要求,尚未转化为法律权利,但是通过不断的“主张”和“斗争”,最终被道德和法律所接受。权利泛化者试图用“权利”标签来证明其主张的“权利”具有正当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权利泛化恰恰是现代权利的一种生长机制。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权利生成往往经历从“风俗的默认、伦理的承认、社会的确认到法律的认可”的过程。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权利生成受社会生产力决定、受社会生产关系影响,并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完善。虽然权利泛化与异化使得权利发展“蓬勃状态”呈现“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负面,但这也是权利生成的初始表现形态,“权利泛化是权利发展史上的普遍现象。”[90]7-8权利泛化具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和权利生成的必然逻辑,这是权利泛化积极意义的根本体现。
就“悼念权”、“亲吻权”、“送葬权”等泛化的权利而言,这些所谓“权利”的纠纷案件,通常是发生在家庭成员内部,是家庭成员之间对具体家庭事务处理上的权利和义务的认识偏差而导致的纠纷,从社会价值分析上讲,很难权衡彼此的对与错。从形态上,更多地体现为:“传统与现实的冲突、习俗与新风的纠缠、认知与情感的张力”。认真对待人格权的泛化,是从实质理性向形式理性转向的一种现实选择,而对所谓的“权利”作出公权力确认程序,应当给予必要的限制,这是理性社群生活和现代法治理念的必然选择。
(二)权利主体泛化——以“动物权”为例
十九世纪,伴随着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的兴起,倡导将人类的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涵盖整个自然界。尤其是当人们的道德关怀视野从传统的人类自身扩展到人域之外的存在物时,“动物权利首当其冲地成为了被考虑的对象”。[91]142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动物福利也随之成为立法领域的热点话题,例如1966 年美国的《动物福利法》、1974 年挪威的《动物福利法》、1988 年瑞典的《动物福利法》、1991年丹麦的《动物福利法》[92]343-351、1995年葡萄牙的《保护动物法》、1998年台湾地区的《动物保护法》、1998年德国修订的《动物福利法》、2004年英国的《农畜动物福利规定》[93]等等,目前全世界已经有100多国家或地区颁布了动物福利法。这些国家的《动物福利法》确立的基本原则是:保护动物的生命、健康、生活和心理福利,满足其自然生存天性的需要。在这些立法中,在根本上仍然是关怀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立法仅仅授予动物以客体地位,明确动物享有的福利形式和范围。”[94]198近年来,网络上“活熊取胆”、[95]228“流浪狗”、“虐猫”等虐待动物的事件频频曝光,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动物是否是权利的主体问题的讨论。
关于动物权利之争,在美国学术界典型代表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哲学教授汤姆·雷根与密西根大学哲学教授卡尔·亨特,他们共同发表的《动物权利争论》一书对动物是否有权利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尽管两位作者的观点存在着严重分歧,并在各自的篇幅内都用非常坦率的语言表达了这种分歧,但是对动物具有道德生活上的“资格”和人类对动物的道德关怀等方面存在着共识。[96]1-2在国内,公众越来越肯定保护动物的积极意义,成立了动物保护协会,2014年5月经中国标准化协会批准的《农场动物福利要求 猪》正式颁布,但没有确立动物的权利主体地位,只是要求人们对“猪”给予生活、卫生、环境等“养殖”方面的福利条件。而且,还有不少人强烈反对动物福利,以致在修改《畜牧法》草案时,删除“动物福利”的表述[97]45。在学术界,关于动物能否成为权利的主体,支持者和反对者也是互不相让,至今仍然是众说纷纭。
肯定论者的观点:“万物有灵”, 动物和人一样,都是生命的主体,“是有欲求、有意识、有记忆、具未来感和幸福感的,能感知快乐和痛苦的生命”,[98]109拥有某种程度上的意识和精神,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苦乐”内在道德意义,并具有内在的道德价值,即:拥有不被剥夺大自然所赐予它们的权利。对动物拥有某种权利,从1892年亨利·塞尔特(H·S·Salt)在《动物权利: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中就明确提出,动物与人类一样拥有生存、快乐、自由等“天赋权利”。[99]28-291983年美国哲学家汤姆·雷根(Tom Regan)在《为动物权利辩护》》(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中明确指出“动物权利运动是人权运动的一部分”。[100]173“只要道德主体拥有固有价值,那么他们的固有价值就是平等的。”[101]2001993 年澳大利亚哲学家彼特·辛格在《关于大猩猩的宣言》中,要求给猩猩以“生存权利”、“自由”并提出了“解放运动”的口号。[102]150-154其后,美国学者玛丽·沃伦提出了“弱式动物权利论”。[103]75G·L·弗兰西恩(Gary L. Francione)在《动物权利导论: 孩子与狗之间》中指出,动物与人之间的差别仅仅是“物种差别”。[104]1612002 年,德国宪法修正案中明文写上“保证动物权利。”在我国台湾地区,有的学者用宗教“众生平等”、“万物轮回”论证动物拥有与人一样的权利。在大陆地区,有学者认为,人、动物以及大自然都是 “天赋”之物,拥有“天赋价值”,动物应当获得“平等对待的权利。”[105]34还有学者认为,在法律主体上,动物是类似于“比人类弱势群体(儿童、残疾人等)还要脆弱的群体”。[106]249更有学者认为,“人类应当承认动物有自己的内在价值”[107]117等等。
否定论者的观点:在宇宙世界里,有着应然的逻辑顺序以及人与动物的主体与客体关系,世界的主体永远是人类。从法律渊源上看,古罗马法只承认自由人的主体地位,即使至今,法律也未确立“动物”为法律“主体”,人类是世界的主体,也“证明了人类主宰地球的合法性。”[108]390美国学者卡尔·科亨(Carl Cohen)认为,动物不具有人类理性或伦理判断的能力和资格,不是权利的主体,“权利的概念在本质上只属于人。”[109]213英国学者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认为权利包含着义务,权利与义务是“一体两面”,“权利的代价就是义务。”[110]100-107动物世界里没有自身的“道德判断”,即使所谓动物内在道德也是立足于人类的观察和理解而形成的“推论”,只有人类能够享在权利和履行义务。马肯(Tibor R. Machan) 指出:“道德生活是人类独有的领域。而其他低等动物不能被赋予这样的道德生活所要求的尊重和保护基本权利的对待。”[111]177-187西方学者认为提倡动物拥有权利是“自由世界观内最奇怪的文化转变”。[112]431L.杜安·威拉德(L.Duane Willaed)认为,动物权利论者的错误在于把权利归因于利益或道德。在我国,有学者认为,动物是一种特殊的“物”,“不可能成为人类道德和法律的主体。”[113]64“动物只能是动物保护法律关系的客体而非主体。”[114]190-191综之,动物权利否定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制定法律、限定人类行为、给人类施加更高的保护动物义务等途径更好的达到保护动物的目的,而不是动物自身拥有天然的权利。
折衷论者的观点:我国在考察和借鉴发达国家法律制度过程中,中华文化内在“中庸”精髓对法律思想的汲取和评判,形成了独特的“揉合-折衷”之道,在动物权利问题上,国内有不少学者提出“拟权利主体”观点。我国著名环境法学家蔡守秋先生在《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反思与补充》中提出了将动物权利置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把动物(包括其它自然主体)类似于无行为能力的婴儿、无自然人意志的国家或社区法律实体,提出“代理”制度的理论延伸。[115]469-520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提出了动物的“拟权利主体”,即在传统哲学上的“主体”、“客体”二元体系之间,设置一个独立的“存在域”(介于“人”与“物”之间,但具有权利主体地位)。此外,荷兰著名应用伦理学家Mar-cus指出,动物具有内在的道德价值甚至尊严,“动物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类似于人类的道德地位。”[116]127从伦理学的角度,将动物视为“拟人类”,以此来演绎在法律关系上的“拟权利主体”从而保护动物的法益。对动物的法益保护,可以比拟民法上“限制行为能力”制度进行设计,可以通过“动物保护组织”代为提起“动物权利”的公益诉讼,以实现和保护动物权利自身的价值。
我们认为,在近几十年关于动物解放、动物关怀和动物权利的辩论中,法学通过对动物权利的必要性和正当性的论证,使得动物获得了其法益的保护,国内外相继建立了不少动物福利、动物保护和动物权利的社会组织和民间团体,还先后颁布了有关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这将促进人与动物友好相处以及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丰富了基础法学理论和环境法学理论的内涵,并引发了许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倡导动物权利主体地位,这是对传统人类沙文主义的批判和否定,对推动自然环境资源的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传统二元哲学视角和传统法学理论没有被突破时,在特定的情况下,赋予动物在法律关系的“类主体性”,是值得进一步探索和探讨的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人类具有实践理性,能够承担义务,才能成为道德和法律主体。“人作为主体首先是因为人能意识到自己作为人的独立人格的存在。”[117]27这样“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118]162动物权利论提出动物具有道德伦理资格和诉求,但并未为这种资格和诉求提供充分的本体论证明。纵观中外法律制度,由于动物没有人类主体意志,中外法律责任制度中涉及动物损害责任,承担责任的主体是人而非动物本身。“动物不具有理性思维能力,其行为不具有道德性,因而不能成为社会的主体,”[119]63而且“动物之间不存在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120]161必须要明确的是,动物的利益和痛苦推导不出必然的法律权利。动物伦理学倡导的“动物与人之间平等”的价值观,是动物权利论的逻辑起点,但是这是“动物权利”在伦理上的追求,并不必然导致“动物权利”在法律上的确认。
在现代社会里,对动物进行保护具有十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这不必然演绎得出动物“拥有”权利,而通过法律赋予动物成为权利主体必然导致逻辑上的矛盾,这种方式也未必是保护动物的最佳路径。在些学者“在呼吁人与动物平等和睦相处的同时抛弃了人类生命的特殊性和神圣性。”[121]115“权利高于利益”,利益只是权利正当性的物质基础,利益不会因重要而变成权利,人类保护动物乃生态环境保护的必然需要,并非是动物之权利的诉求。奥地利、德国、瑞士等国对民法典中涉及动物法律关系的修正,主旨是进一步强化人们对动物的保护,“并未认同动物的权利主体地位。”[122]233只是提出了“动物应该成为体现了人类价值关怀的特殊客体。”[123]97
从某种意义上讲,环境伦理学的主张并不等同于法学的主张,权利主体扩张至动物缺乏自主性和正当性。倘若,当动物拥有与人类相当的“权利”,那么,狮子、老虎饿了要吃“人”具有“不可置否”的“正当性”,人类是否成为“食肉性”野兽的“午餐”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平衡再次“被”“动物”所打破,以致让伦理学走上了“悖论”的诡道。对于“保护动物”理应通过人类的呵护去实现,将动物视为权利主体,反而使得动物失去了人类保护的法律义务,动物在人与社会的环境中是无法完全实现自身自给自足,失去人类应当承担的保护义务也许不是动物的一场“自然和谐的愿景”而是一场“道德沦失的灾难”。因此,现阶段将动物权替换为动物受保护权,也许更为切合动物保护的实际需要。
四、在文化与科技的互动下的现代权利
当今社会是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社会,创新创业的浪潮随着科学技术的工业化,“相应地带来了一些此前所未曾想见到的权利形式,”[124]9必然引发对权利体系的重新布局。这个世界上有着无处不在的科学技术对现实生活的影响,特别是以数字计算和最优化为载体,以微电子、数字技术、航天航空技术和现代生物工程技术为代表,科学技术所塑造的不仅是技术设备和工业系统的自身变革,最终还重构了个体意识、社会意识包括人们的权利意识。现代社会正在技术物化,“人的现实性能够重新肯定本身并改变社会”。[125]4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对社会各个方面必然产生深远的影响。“法律,就像技术代码一样,在社会生活中建立起稳定的规则性”。[126]137科学技术促进法律体系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是由于技术文化的构建中形成一种内在张力,推动社会关系以及法律关系的变革。
科学技术体现了工具理性价值,而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关系主义的社会,“传统的法律是斟酌情理的法律。”[127]122特别是中国社会几千年“礼法” 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历史沉淀力和传承力,以致从清末民国初期的法律近代化的过程变得“滞慢”,也使得现行法律不仅未能彻底改变几千年沿袭下来的“中华传统”,反而以“潜规则使法律在现实运行中“大为逊色”。文化传承在权利生成体系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作为文化的力量体现在道德评判上,而这种道德评判具有一定的“惯性”甚至是“惰性”,影响着法律运行的效能。传统文化包括风俗习惯文化对科技发展和权利体系都具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任何一个社会,法律权利在本质内涵上发生的变化,都是社会“公意” 在政治制度层面上的体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28]305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社会利益关系的多元化、多样化,通常会引起整个社会对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与配置,当社会成员某些权利诉求具备社会发展的必然、获得社会的高度认同、甚至维护和巩固现有的政治权力的时候,这些诉求常常会借助立法“公意”、法律确认、司法解释、法院判例等形式对其权利属性进行确认与转化,并通过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的制度设计来表达与体现,使得原先的权利体系对相关法律规定的权利内涵挖掘与权利主体延展或限缩,以致新兴权利诉求由此取得了合法地位而成为了法律权利。
对权利现象的认识,与对新型法律权利的解析,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对所谓“权利”进行法律上的确认与转化,必需体现其正当性原则,符合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和科学技术的成长规律,遵循事物客观发展规律,并具有共同意志基础上的“公意”,因为“公意”是法律的基础和灵魂。权利的生成历经道德认同、利益诉求、社会承认、立法或司法确认等过程,从价值理性“成长”为工具理性,以平等、互利、公正的姿态成为法律权利。传统上,人们对待权利问题的解析,常常思维程式化,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固格化,有时还无法超越原先的理论预设,否定了法律体系的多元结构和多形态,陷入了一种国家法条主义的陷阱。其实,生活中,规则体系中不仅包括法律规则,还有道德规则、习惯规则、礼仪规则、商贸规则和技术规则等等多元成分,即便是法律规则,自身还是存在“活的规则”的问题,存在着法律规则与其他规则的互动问题。可以说,“规则并非法律的全部,还包括其他更基础性要素。”[129]97权利的生成和演变也具有相似的逻辑路径和成长痕迹。
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尤其是科学技术高速发展推动了人们的法治理念和权利意识的转向与强化,权利观念与权利主张的兴起,具有社会客观性和历史必然性。权利泛化、虚化与权利拓展和权利生成相伴随,是人类的道德情感和权利意识对权利的“超前”诉求。从某种意义讲,权利的扩张、泛化,主要是源于权利的“符号化”的外在特点和权利本身“预设”的功能。在社群主义的公共生活中,人的尊严和人的权益主要依靠国家义务或职责来实现,如果这种义务或职责未能导出相应的“新兴”权利,那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家的态度,在集权制国家里,政治家的良心与风格影响权利的确认。“对于宣称或主张权利的人来说,权利本身可能并非目的,而可能是表明他们自己的存在,也可能是引起国家对自己或一个特定的群体的关注,甚至可能是凸显一种个体的独特性。”[130]9通过司法审判来确认和创造权利是现代权利发展的重要路径,[131]7某些特定利益或资格的诉求,在判例法国家,常常以案例形式而予以确认;在大陆法系国家,经过多次司法个案的积累,形成具有指导性的行为规则,以司法实践的形式确认其诉求的正当性,以致这些“诉求”跻身于权利之列,将其视为正在成长中的 “权利”也无不可。[132]63
司法在权利拓展过程中,司法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面对所谓的“权利”诉求的案件激增现象,法官应当采取务实、谨慎、客观的态度。美国法学家曾建议,对于那些不适宜由司法过程裁决的“权利泛化”的纠纷,可以适当将之转移到政治过程或市场上去,[133]1-12让政治原则和市场规则,对其进行内在的筛选和淘汰。同时,立法者价值取向和道德追求影响着对权利拓展与泛化的选择和确认,“那些获得立法承认的权利同时也承载着特定价值,”[134]67现代权利的生成始终处于从“无”到“有”的价值承认与确认之中,“当今认为理所当然并为法律所认可的许多权利,在历史上刚提出来的时候,往往被认为是无稽之谈,甚至斥之为荒谬。”[135]8权利拓展是促进权利的生成和成长的正能量,推动权利体系的不断丰富、完善和提升。
应当引起人们重视的是,有些泛化的权利,在现实生活中,并未能真正体现出法治平等精神,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美国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倡导种族权利,“到1990年代末,黑人学生进入白人主导学校的比例下降了13%。”[136]296人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在现有的司法环境中,权利泛化现象也对社会生活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过量的所谓“权利” 甚至是戏剧化的诉求,给法律严肃性与权威性带来一定的损伤;大量出现“新型权利”案件的滥诉,不仅增加司法成本,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而且还影响司法正常的效能。总之,聚集权利发展正能量,遏制无节制的“权利诉求”扩张冲动,这是权利时代与法治社会共同企盼。
在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新型权利诉求、对新型权利的确认以及权利自身的拓展与泛化都会长期存在。权利拓展不是天生的,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和人们对权利意识的发展水平而决定的并且是被社会认可的“正当”的自由或“正当”的利益,权利拓展不可能无限制地超出道德规则和法律规则,权利拓展必然有“边界”。权利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系统内的权利之间相互平等、互相制约,而且权利系统根植和融合于整个社会之中,“社会认可权利的方式主要是法律,因而真正的权利既与义务相连,”[137]62权利的行使必须以履行的义务为前提,权利与义务具有某种意义上的“能量守恒”关系。从社会责任角度来看,权利是社会的、共生的,是社会里具有“正当性”的自由或利益的反映,“没有只有权利的权利”,权利的享有者同样必须承担着相应的社会义务。
现代社会是理性社会体系,由于中国属于外源性法治现代化类型,现今过于强调工具理性,容易将权利“拓展与生成”程式化、抽象化和标准化。在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清醒地面对科学技术的“理性”,坚信生命和存在的意义,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有机融合起来。法律本身应当具有的最低道德品性需要法学家和伦理学家共同捍卫,人类法律在规则体系之中,应当散发独有的人文情怀与明晰的逻辑关系。防止以权利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形式化、教条化和品质异化,特别要防止“无情”、“纯粹”、“机械”的工具理性掏空了法律应当具有最起码的道德底线和伦理品质,将科学技术引领下的权利拓展变成法治现代化的“奠祭品”。防止科学和技术理性的工具化,尤其是在当今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里,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发生张力与冲突、甚至是彻底的撕裂与对抗,“手段取代了目的,形式否定了内容”,技术“工具理性”的猖獗,导致人被物欲所牵制,“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138]143人被物化且丧失了自我本真。为此,要扬弃科学和技术理性的统治功能,克服科学技术物化、异化的背离,融合技术理性、科学理性同价值理性、艺术理性,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最终达到人和自然的共同解放、全面解放的美好愿景。
五、结束语:权利拓展正在进行时
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科学技术革命,都预示着权利领域的拓展与创新。“科学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社会解放,是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没有统治的交往关系和取得一种普遍的、没有压制的共识。”[139]201科学技术是伟大的力量,也是神奇的力量,特别是掌握在不同的利益集团手中,必然成为其进行利益竞争的有力工具,他们常常以科学技术的名义经过立法的方式使得阶级集团的利益固化。科学技术发展给整个人类带来了效率、便利和自由,权利意味行动上的自由维度,马克思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40]46权利拓展体现在对个体权利和个体自由的拓展上,“以个体权利为核心的政治秩序补充和拓展了自然正义。”[141]46因此,权利拓展的重要性不在于其奠基于何种本体论之上,在于追求个体自由和个体价值的实现与保护的过程中,以此推动人类社会共同繁荣与人类最大福祉。
在当今权利观念高涨、权利主张不断张扬的时代,科学技术实践是权利生成的基础,权利生成是科学技术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权利拓展的一种积极性肯定。可以这么讲,科学技术发展与实践永无止境,权利生成与拓展永远止境。科学技术既是人类的实践活动,也是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产物,没有脱离人类的科学技术,自然也没有脱离人类的科学技术的自主性。“技术总是社会性的设计,”[142]224促进了社会的交往,而且,科学技术给人与人之间交流提供了更加便利迅捷的工具,“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全球化,是一个多文化并存的格局,”[143]126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形成了多元视角,产生多彩多样的权利诉求,拓展和丰富了权利体系。
权利现象及其拓展与泛化的问题,是人们必须“认真对待”的真问题。“权利问题是人类自身发展和国家权力构建的基础……必然成为人类所要思考的首要问题”。[144]43科学技术具有扩大效能的作用,提升资源开发所取得的利益,并促进形成新的利益配置模式,产生了新型的权利载体,同时,权利在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的作用归根结底来源于权利人自身利益的驱动力,使得科学技术和权利体系不断发展。
对于法律人来说,关注当代法治现实,解析权利拓展现象,“逐渐形成具有鲜明的中国印记的法治话语系统,这无疑是一个不可推卸的法学学术责任”。[145]11在权利拓展过程中,不存在具有永恒意义的理想的权利体系,无论在权利拓展的路上,跋山涉水多久,坚持真实的生活立场,策应科学技术发展,权利拓展始终是进行时,前进,前进,再前进!
参考文献:
[1]江必新,王红霞.法治社会建设论纲[J].中国社会科学,2014.(1).
[2]杜承铭,吴家清等.社会转型与中国宪法自由权制度的完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冯玉军.法治中国发展的趋势研究[J],学习论坛,2015,(1).
[4]杨秀清.论司法过程的权利生成功能——以民事权利救济为视角的分析[J].法律适用,2007,(11).
[5][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6][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M].李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7][美]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M].陆俊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8]宋清华.海德格尔对技术时代的世界观的批判[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5).
[9]韩显阳,邓晖.科学家宣布探测到引力波 广义相对论最后预言获证[N].光明日报,2016-2-23(1).
[10]郝继松,韩志伟.马克思现代技术批判的历史维度[J].学术研究,2014,(8).
[11]李宝刚,陈跃飞.哈贝马斯对于技术理性的批判及其反思[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
[12][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3][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14][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15]Andrew Feenberg.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16]Andrew Feenberg. Techn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M].Blooming: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5.
[17][美]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M].陆俊,严耕,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8]刘科.陈昌曙的技术批判思想评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
[19]陈俊.技术文明与人的解放——马尔库塞论弗洛伊德及对技术的批判[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
[20][法]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21]李国俊,魏炟,韩天澍.技术批判语境下哲学的生态范式转向[J].学术交流,2013,(5).
[22]李晓羽,盛鹏飞,杨俊.中国环境污染与人类发展的实证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23]乔清举.中国哲学研究反思:超越 “以西释中”[J].中国社会科学,2014,(11).
[24]万希平.从技术理性批判到社会制度批判——兼论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转换批判主题的逻辑意蕴[J].理论探讨,2009,(1).
[25]刘福森.新生态哲学论纲[J].江海学刊,2009,(6).
[26][美]罗德里克·纳什.大自然的权利[M].杨通进,译.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
[27]韩秀霜.蕾切尔·卡逊对施韦泽和利奥波德生态伦理观的运用[J].理论月刊,2013,(10).
[28]周围.生态伦理学的若干热点问题[J].环境教育,2010,(4).
[29][美]罗德里克·纳什.大自然的权利[M].杨通进,译.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
[30]Roderick Nash.The Rights of Nature: A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M].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6.
[31][美]罗德里克·纳什.大自然的权利[M].杨通进,译.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
[32]蔡守秋.环境权初探[J].中国社会科学,1982,(3).
[33]蔡守秋.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反思与补充[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34]吕忠梅.论公民环境权[J].法学研究,1995 ,(6).
[35]吕忠梅.再论公民环境权[J].法学研究,2000,(6).
[36]汪劲.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环境立法目的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37]刘敏.论环境的法律地位——从“伦理的权利”到“法律的权利”[D],北京:北京大学法学院,2002.
[38]刘敏.人与环境同构法初探[J].法学论坛,2006,(2).
[39]周训芳.环境权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40]徐祥民.环境权论——人权发展历史分期的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04,(4).
[41]于忠春.人权视角下的环境权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法学院,2006.
[42]王开宇.生态权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法学院,2012.
[43]朱雯。论环境利益[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2014.
[44]杨建学.对环境权的再审视——以“人类-自然”环境系统为视角[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0,(2).
[45]陈忠.城市权利:全球视野与中国问题——基于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的研究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14,(1).
[46]彭光华.论环境权利[J].江西社会科学,2009,(6).
[47]汪习根.免于贫困的权利及其法律保障机制[J].法学研究,2012,(1).
[48][法]阿尔贝特·施韦泽.文化哲学[M].陈泽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49]郭菁.列维纳斯与布伯关于生态伦理的分歧及启示[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11).
[50]杨通进.争论中的环境伦理学:问题与焦点[J].哲学动态,2005 ,(1).
[51]征汉年.后现代法学对现代法学权利理论解读与批判[J].重庆社会科学,2008,(6).
[52][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M].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53]刘卫先.自然体与后代人权利的虚构性[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6).
[54]杨立新,王中合.论网络虚拟财产的物权属性及其基本规则[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4,(6).
[55]侯国云.再论虚拟财产刑事保护的不当性——与王志祥博士商榷[J].北方法学,2012,(2).
[56]张永兵,冯玥.网络虚拟财产法律性质探析[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4,(2).
[57]陶信平,刘志仁.论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保护[J].政治与法律,2007,(4).
[58]徐丹.网络虚拟财产的民法属性[N].人民法院报,2009-8-25(4).
[59]刘惠荣.虚拟财产法律保护体系的构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60]陆小华.信息财产权——民法视角中的新财富保护模式[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61]凤凰网.2014中国游戏产业报告:国内游戏收入1144.8亿元.[EB/OL]http://games.ifeng.com/yejiehangqing/detail_2014_12/17/39814719_0.shtml.
[62]搜狐网.2015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游戏总收入1407亿.[EB/OL]http://mt.sohu.com/20151215/n431336948.shtml.
[63]王梦,王者洁,论网络虚拟财产的权利属性[J].山东社会科学,2013,(12).
[64]吴佳斌,宋帅武,盗窃网络虚拟财产的定性[J].人民司法,2013,(17).
[65]田宏杰,肖鹏,周时雨.网络虚拟财产的界定及刑法保护[J].人民检察,2015,(5).
[66]征汉年.权利正当性的社会伦理思考[J].江苏社会科学,2009,(2).
[67]汪太贤.权利泛化与现代人的权利生存[J].法学研究,2014,(1).
[68][美]贝思·J·辛格.实用主义、权利与民主[M].王守昌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69][德]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M].王晓晔,邵建东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70]Bennardo Windseheid.Diritto del Pandette Volume Primo[A].Dvvocati Carlo Fadda.Paolo Emilio Bensa[C].Torino,1992.
[71]于志刚.网络空间中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
[72]李长兵,彭志刚.网络虚拟财产刑法规制的理性思考[J].江西社会科学,2013,(4).
[73]陈庆,周安平.论数字权利管理的本质及其两面性——“技术措施=电子锁”国内通说及其立法实践反思[J].知识产权,2014,(6).
[74]马一德.网络虚拟财产继承问题探析[J].法商研究,2013,(5).
[75]房秋实.浅析网络虚拟财产[J].法学评论,2006,(2).
[76]汪美侠.浅析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保护[J].江淮论坛,2010,(3).
[77]林孝文.论法定权利的实现――以法社会学为视角[J].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
[78]征汉年,马力.论权利意识[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
[79]汪太贤.权利泛化与现代人的权利生存[J].法学研究,2014,(1).
[80]王利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私法自治[J].中国法学,2014,(5).
[81]易军.“法不禁止皆自由”的私法精义[J].中国社会科学,2014 ,(4).
[82]杨立新,袁雪石.论声音权的独立及其民法保护[J].法商研究,2005,(4).
[82]杨立新,林旭霞.论形象权的独立地位及其基本内容[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2).
[84]丁南.权利意志论之于民法学的意义[J].当代法学,2013,(4).
[85][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M].信春鹰,吴玉章,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86]陈林林.反思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权利泛化[J].法学研究,2014,(1).
[87]陈金钊.对法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个人价值观的诠释[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5,(1).
[88]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II: 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States[M]. New York: Cambridge UP, 1993.
[89]陈方南.中国乡村治理问题研究的方法论考察——“国家-社会”理论是否适用[J].江海学刊,2011,(1).
[90]汪太贤.权利泛化与现代人的权利生存[J].法学研究,2014,(1).
[91]魏小强.社会纠纷解决中的利益衡量与规范协调——以一起民间纠纷为例的分析[J]. 江汉论坛,2011,(3).
[92]常纪文.从欧盟立法看动物福利法的独立性[J].环球法律评论,2006,(3).
[93]刘火.是否有必要立一部动物福利法[N].中国畜牧兽医报,2014-6-22(3).
[94]常纪文.“动物权利”的法律保护[J].法学研究,2009,(4).
[95]黄芳.从“活熊取胆”谈动物权利思想的演进[J].人民论坛,2012,(12).
[96][美]汤姆·雷根,卡尔·亨特.动物权利争论[M].杨通进,江娅,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97]田雨,邹声文.畜牧法草案删除有关“动物福利”的条款[J].中国禽业导刊,2005,(24).
[98][美]罗德里克·纳什.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M].杨通进,译.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
[99][美]罗德里克·纳什.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M].杨通进,译.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
[100][美]罗德里克·纳什.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M].杨通进,译.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
[101][美]汤姆·雷根.动物权利研究[M].李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02]余谋昌.生态哲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103]武培培,包庆德.当代西方动物权利研究评述[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3,(1).
[104][美]加里·L·弗兰西恩.动物权利导论: 孩子与狗之间[M].张守东,刘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105]杨通进.环境伦理:全球话语权,中国视野[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106]邱仁宗.生命伦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07]张燕.谁之权利?何以利用?——基于整体生态观的动物权利和动物利用[J].哲学研究,2015,(7).
[108][美]斯蒂文·M·怀斯.动物的法律物格[A].郭晓彤,译.吴汉东.私法研究(第3卷)[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109][美]汤姆·雷根,卡尔·科亨,动物权利论争[M].杨通进,江娅,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110] Roger Scruton. animal Rights[J].City Journal,2000,10(3).
[111] L.Duane Willaed. About Animals“Having” Right[J].The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 1982, (3).
[112] Applying Ethics.A textwith readings,Jeffrey Olen &VincentBarry[M].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113]陈本寒,周平.动物法律地位之探讨——兼析我国民事立法对动物的应有定位[J].中国法学,2002,(6).
[114]侯猛.人类学语境中"镶嵌"的权利[J].法学研究,2009,(4).
[115]蔡守秋.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反思与补充[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116]袁明敏,李建军.动物伦理学与面向绿色未来的权利——第六届“中荷生命伦理学研讨会”综述[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11).
[117]谭培文.社会主义自由的张力与限制[J].中国社会科学,2014,(6).
[1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9]严存生.“动物权利”概念的法哲学思考[J].东方法学,2014,(1).
[120][美]加里·L·弗兰西恩.动物权利导论:孩子与狗之间[M].张守东,刘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121]郑琼现.论生命权法律性、权利性、神圣性的坚守——对生命权伦理化、义务化、生物化话语的批判[J].政治与法律,2015,(1).
[122]崔拴林.理性的遮蔽与主体的迷失——对汤姆·雷根之动物权利论的再批判[J].江海学刊,2012,(4).
[123]崔拴林.私法主体范围扩张背景下的动物主体论批判[J].当代法学,2012,(4).
[124]姚建宗.新兴权利论纲[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2).
[125]Andrew Feenberg.Heidegger and Marcuse: The Catastrophe and the Redemption of History[M], New York:Routledge,2005.
[126][加]安德鲁·芬伯格.从技术批判理论到合理性的理性批判[J].哲学分析,2010,(2).
[127]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12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9]高鸿钧.德沃金法律理论评析[J].清华法学,2015,(2).
[130]汪太贤.权利泛化与现代人的生存[J].法学研究,2014,(1).
[131][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M].王亚新,刘荣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132]梁迎修.权利冲突的司法化解[J].法学研究,2014,(2).
[133][美]尼尔·K·考默萨.法律的限度——法治、权利的供给与需求[M].申卫星,王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134]梁迎修.权利冲突的司法化解[J].法学研究,2014,(2).
[135]汪太贤.权利泛化与现代人的权利生存[J].法学研究,2014,(1).
[136][美]戴维·奥布莱恩.风暴眼:美国政治中的最高法院[M].胡晓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137]严存生.权利观念的再澄清[J].学习与探索,2014,(6).
[138][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139][德]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M].郭官义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14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1]周濂.后形而上学视阈下的西方权利理论[J].中国社会科学,2012,(6).
[142]Herbert Marcuse.Industrialization and Capi-tilism in the Works of Weber[M].Boston, MA:BeaconPress ,1968.
[143]计海庆.用丰富的经验克服形而上的命运——唐·伊德对海德格尔技术哲学的批判及意义[J].哲学分析,2013 ,(1).
[144]征汉年,章群.西方自然法学派主要权利理论解读[J].思想战线,2005,(6).
[145]公丕祥.法治中国进程中的区域法治发展[J].法学,2015,(1)
[责任编辑:康继尧]
Development and Generalizatio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luence Factors of Modern Right
ZHENG Han-nian
(SchoolLaw,NanjingNormalUniversity,NanjingJiangsu210023,China)
Abstract:The swift and violent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brought very great impact to human life, having proposed new thinking to the traditional right question, a lot of are not that the right of the right has appeared , the subject , object and content of the right have presented the trend expanded . Right is it it takes to be companion living beings that right expand to suffused with, or right a kind of right alienation on development “ not the normality ”, demand “ leading ” of the right in the people's right emotion. Expand the rights of these demands among the legitimacy, rationality, reality demands,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precipitation, converted to the new rights, there are some so-called rights of appeal are still in a fight against. Looking at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the right to expand still on the road.
Keywords:Rght; Epand ;Technology;Logic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307(2016)02-0101-17
[作者简介]征汉年(1968—),江苏盐城人,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江苏省盐城市大中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高级检察官,盐城师范学院兼职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法史)学、刑事法学。
[收稿日期]2016-0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