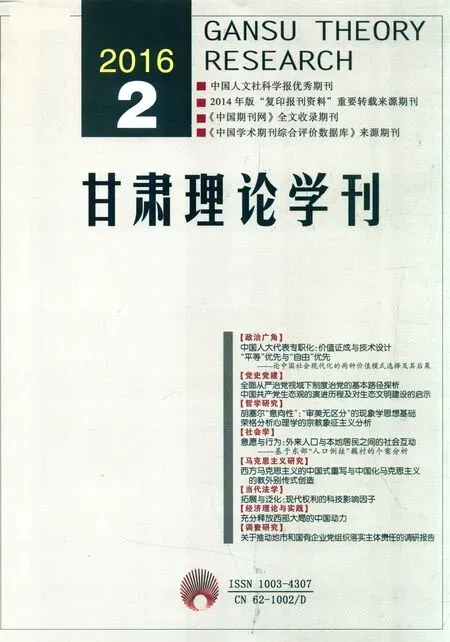意愿与行为: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互动——基于东部“人口倒挂”藕村的个案分析
杨富平,杨尔飞
(1.中共路桥区委党校 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浙江 台州 318050;2.合肥师范学院 数学与统计学院,230061)
意愿与行为: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互动
——基于东部“人口倒挂”藕村的个案分析
杨富平1,杨尔飞2
(1.中共路桥区委党校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浙江台州318050;2.合肥师范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230061)
[摘要]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互动,是考量外来人口适应并融入城市社会的重要指标。基于浙江省L区“人口倒挂”藕村的调查,研究发现:本地居民对外来人口的主观评价总体正面偏上,但接纳意愿较低,不愿与外来人口建立比较亲密的关系;外来人口对本地居民的主观评价总体负面偏下,但接纳意愿较高,希望与本地居民建立比较亲密的关系;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互动行为,总体具有偶尔性、封闭性、浅层性的特点,互动情况不容乐观,但彼此基本相安无事;无论是互动意愿还是互动行为,年轻一代相比年长一代总体具有更多积极表现,但是也具有更强的互动张力,即年轻一代之间更易于发生矛盾冲突。本文认为,当前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互动在某种意义上是“纠结型互动”,相比“摩擦性互动”,这是一种处于变迁之中的新型且积极的关系形态。
[关键词]外来人口;人口倒挂;社会互动;互动意愿;互动行为;纠结型互动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动,在城乡、区域之间“推拉力量”[1]的作用下,东部沿海地区开始涌现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庞大外来人口群体,当前浙江的外来人口就有2000多万人。那么,这些外来人口又该如何融入当地城镇并实现市民化呢?学者认为,需要完成三个依次递进的适应,即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社会适应主要包括日常生活模仿、闲暇时间安排、与城里人交往,其中以与城里人交往最为关键,这是外来人口适应城市、融入城市的主要途径。[2]由此,研究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交往互动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学界对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互动已有一定研究,但也有需进一步探讨之处。一是在研究场域上,重“面上”研究,轻“点上”研究。现有研究往往是基于整个城市区域的外来人口或本地居民,进行相应的问卷调查或个案访谈,比如:刘林平于2006年在广州市以随机抽样方式,先后抽取4个老城区、8个街道、16个居委会,共调查了496位城市居民[3];杨黎源于2005、2006年对宁波市8个县(市)、十多个乡镇进行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共调查了534位外来人口和519位本地居民[4]。遗憾的是,在当前东部沿海村居“人口倒挂现象”*所谓“人口倒挂现象”,是指某地或某村出现外来人口超过本地人口的特定社会现象。比较普遍的特定背景下,缺乏对这样一个“人口倒挂村”中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互动进行个案式深度研究。二是在研究视角上,重“单向”研究,轻“双向”研究。社会互动需要双方甚至多方共同作用,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现有研究大多采用“单向”的研究视角,仅研究外来人口或本地居民一方的态度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互动的“双向性”。理论上讲,只有采用“双向”的研究视角,既分析外来人口对本地居民的互动意愿和互动行为,又分析本地居民对外来人口的互动意愿和互动行为,才能充分展现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互动情况。
综上,我们试图基于浙江省L区的“人口倒挂”藕村,采用“双向”的研究视角,重点研究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互动意愿与互动行为,探讨两者互动的新特征、新变化,特别关注年轻一代与年长一代的差异性*本文认为,分析年轻一代与年长一代的差异性,要比分析不同性别、不同教育程度的差异性更有意义,因为从年轻一代与年长一代的差异性,可以看到一种纵向的社会发展变迁情况。,旨在全面展现“人口倒挂村”中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互动图景。
二、研究的方法
首先了解一下个案-藕村。L区是东部沿海民营经济先发地区,以商贸繁荣著称。目前,全区有外来人口31.95万人,占全区常住人口总数的41.9%,区内有不少“人口倒挂村”,藕村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藕村位于L区西南部,紧邻主城区,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2002年藕村响应省委“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并于2004完成了整村重建,现占地面积119亩,房屋485间,全体村民都住上了新楼房,从一个传统农村变成了现代社区。藕村因重建后有大量房屋空置,且靠近主城区和吉利汽车城,近年来吸引了大批外来人口租住,目前本地居民有240户、868人,而外来人口则有2002人,是本地居民的两倍多,占到了全村常住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
对于“人口倒挂”藕村的调查,我们主要采用了以下两种研究方法:
一是问卷调查法。调查问卷分为两套,一套针对外来人口,另一套针对本地居民。问卷内容主要涉及个人基本情况、社会互动意愿、社会互动行为、互动阻碍因素。问卷由调查员进入藕村后随机发放,由调查员通过询问方式填写并当场收回,共发放问卷200份,有效回收率100%。调查对象的构成情况如下:外来人口100位,年轻一代(1980年及之后出生)63位(占63.0%),年长一代(1980年之前出生)37位(占37.0%);本地居民100位,年轻一代(1980年及之后出生)48位(占48.0%),年长一代(1980年之前出生)52位(占52.0%)。
二是个案访谈法。采用结构式访谈方式,主要访谈以下几个问题:对外来人口(或本地居民)的主观评价和接纳程度;与外来人口(或本地居民)社会互动的频度、广度、深度、张度情况;与外来人口(或本地居民)难以实现良性互动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共访谈个案16位,构成情况如下:外来人口8位,年轻一代(1980年及之后出生)5位(占62.5%),年长一代(1980年之前出生)3位(占37.5%);本地居民8位,年轻一代(1980年及之后出生)4位(占50.0%),年长一代(1980年之前出生)4位(占50.0%)。
三、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互动意愿
我们主要从两个维度对互动意愿进行测量:一是主观评价,即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是如何评价对方的,考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二是接纳程度,即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能接受对方成为何种程度的关系,考察是排斥的还是亲近的。
(一)主观评价*在测量主观评价时,我们设计了一个多选题:“在日常生活中,你对外来人口(或本地居民)的总体印象是什么样的?(可多选)”预先提供了六个选项,前三个选项是正面评价,后三个选项是负面评价;前三个选项每被选一次获+1分,后三个选项每被选一次获-1分;最终分值的正负即代表评价的正负,分值的大小即代表评价程度高低。
1.本地居民对外来人口的主观评价
我们发现(表1),本地居民对于外来人口,认可最高的是“勤劳节俭”(占78.0%),指责最多的则是“生活邋遢”(占71.0%),另外从分值上看,本地居民对外来人口的主观评价平均分值为+0.250(即+25/100),说明主观评价总体是正面偏上的。
同时发现,年轻一代本地居民对外来人口的主观评价平均分值为+0.375(即+18/48),而年长一代本地居民对外来人口的主观评价平均分值为+0.135(即+7/52),表明年轻一代本地居民对外来人口更有好感、更加包容。访谈个案“本地-3”(本地人,男,26岁,高中毕业,工厂技工):“我在一家汽车厂上班,厂里外地人很多。长期接触下来,我认为,他们比较勤奋,比较节俭,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没素质’什么的,其实是蛮好相处的。”

表1 本地居民对外来人口的主观评价情况 单位:人
2、外来人口对本地居民的主观评价
我们发现(表2),外来人口对于本地居民,认可最高的是“诚实守信”(占64.0%),指责最多的则是“自以为是”(占73.0%),另外从分值上看,外来人口对本地居民的主观评价平均分值为-0.270(即-27/100),说明主观评价总体是负面偏下的。
同时发现,年轻一代外来人口对本地居民的主观评价平均分值为-0.159(即-10/63),而年长一代外来人口对本地居民的主观评价平均分值为-0.459(即-17/37),表明年轻一代外来人口对本地居民的评价要更好一些。年长一代外来人口对本地居民的差评,与其在工作生活中遭受更多的社会歧视有关。访谈个案“外地-7”(安徽人,男,49岁,小学毕业,建筑工):“本地人比较自以为是,经常歧视我们外地人,叫我们“外路鬼”,看不起人啊,其实本地人的素质又能高到哪里去?”

表2 外来人口对本地居民的主观评价情况 单位:人
(二)接纳程度*在测量接纳程度时,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下列与外来人口(或本地居民)的关系,哪些你能接受?(可多选)”并提供了“成为同事”、“成为邻居”、“成为朋友”、“成为亲家”等四组关系程度依次递进的选项,如选择后面的选项越多,则表明接纳程度越高。
1、本地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接纳程度
我们发现(表3),本地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接纳程度总体较低,愿意与外来人口“成为朋友”的只有47.0%,愿意与外来人口“成为亲家”的则仅有13.0%。这里似乎存在一对矛盾:本地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总体评价是正面的,但却表现出较低的接纳意愿,难以接受与外来人口建立较为亲密的关系。
同时发现,年轻一代本地居民对外来人口的包容性更强,愿意与外来人口“成为朋友”的将近三分之二(占62.5%),愿意与外来人口“成为亲家”的达到20.8%,约是年长一代的4倍。年长一代本地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排斥,除经济、习俗、语言等因素外,更多还是心理上感觉“抹不开面子”。访谈个案“本地-6”(本地人,男,51岁,小学毕业,自主经营):“与外地人一起做事倒也没什么,交朋友也勉强可以,但如果我女儿与外地人谈对象,与外地人结成亲家,我是坚决不同意的,这个要让别人家笑话。”

表3 本地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接纳程度情况 单位:人
2、外来人口对本地居民的接纳程度
我们发现(表4),外来人口对本地居民的接纳程度总体较高,愿意与本地居民“成为朋友”的有59.0%,愿意与外来人口“成为亲家”的占到33.0%。这里好像也存在一对矛盾:外来人口对本地居民的总体评价是负面的,但却表现出较高的亲近意愿,比较希望与本地居民建立较为亲密的关系。
同时发现,年轻一代外来人口对本地居民的亲近意愿更强,愿意与本地居民“成为朋友”的占到63.5%,愿意与本地居民“成为亲家”的达到39.7%,约是年长一代的2倍。外来人口这种更强的亲近意愿,可能与个人现实利益的考虑有关。访谈个案“外地-5”(江西人,女,24岁,初中毕业,服务员):“可以与本地人谈对象啊,现在都是自由恋爱嘛,只要你情我愿,何必在乎是哪里人呢?本地人也是蛮好的,他们的经济条件也相对更好些。”

表4 外来人口对本地居民的接纳程度情况 单位:人
四、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互动行为
我们主要从四个维度对互动行为进行测量:一是互动频率,即分析两者的互动是偶尔的还是经常的;二是互动广度,即分析两者的互动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三是互动深度,即分析两者的互动是浅层的还是深入的;四是互动张度,即分析两者的互动是紧张的还是融洽的。
(一)互动频度
我们发现(表5),在回答“工作上的交往除外,你与外来人口(或本地居民)的交往互动多吗?”*之所以设置“工作上的交往除外”,因为我们认为,工作性互动往往是被动的,生活性互动更多是主动的,由此生活性互动越多越能体现两者的亲密融洽程度,也更能说明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程度。时,86.0%的外来人口表示与本地居民是“较少”或“很少”交往互动,同样也有83.0%的本地居民表示与外来人口是“较少”或“很少”交往互动,可见两者之间的交往互动是比较少的,总体上具有偶尔性特点。访谈个案“外地-8”(湖北人,男,43岁,小学毕业,工厂普工):“我平时与本地人交往是很少的,因为工作挺忙挺累,一回来就是休息睡觉,哪有这个时间,另外能与本地人说什么呢,他们也不愿与我们交往啊。”
值得关注的是,9.5%的年轻一代外来人口表示与本地居民有“较多”或“很多”交往互动(年长一代只有2.7%),10.4%的年轻一代本地居民表示与外来人口有“较多”或“很多”交往互动(年长一代只有5.8%),这表明年轻一代相比年长一代具有更加积极的交往互动。访谈个案“外地-3”(河南人,男,28岁,初中毕业,出租车司机):“我不轮班出车的时候,与本地人交往也蛮多,认识几位本地朋友,经常一起打打牌什么的,感觉也没什么隔阂,对这里的生活挺适应的。”
(二)互动广度
我们发现(表6),在回答“工作上的同事除外,你有几位外来人口(或本地居民)朋友?”时,67.0%的外来人口表示没有本地居民朋友,75.0%的本地居民表示没有外来人口朋友,这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疏离与隔阂的,交往圈是相对封闭的,都主要局限于各自的血缘圈与地缘圈。访谈个案“外地-6”(四川人,男,43岁,小学毕业,工厂普工):“在平常生活中,我主要是与在这边打工的亲戚,还有老乡交往,一起吃个饭,聊聊家常。与本地人交往很少,感觉讲不到一块去,所以没有本地朋友。”

表5 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互动频率情况 单位:人
与此同时,39.7%的年轻一代外来人口认为自己有本地居民朋友(年长一代只有21.6%),35.5%的年轻一代本地居民认为自己有外来人口朋友(年长一代只有15.3%),可以看出年轻一代具有更加开放的思想,更加愿意与来自不同区域的人士进行交往并建立朋友关系,交往圈开始不断突破血缘和地缘关系。访谈个案“本地-1”(本地人,男,25岁,大专毕业,工厂技工):“我认识几位外地人,关系挺不错,经常一起聊天娱乐,打打球什么的。感觉没什么隔阂,没有像有些本地人那样,带着异样眼神去看他们。”
(三)互动深度
我们发现(表7),在回答“你与外来人口(或本地居民)的交往互动有以下哪几类?*我们设置了“业务往来”、“家常聊天”、“共同娱乐”、“经济帮助”、“情感关心”等五种交往互动类型,越往后情感越深,越具有互动深度。(可多选)”时,本地居民表示对外来人口有过“经济帮助”或“情感关心”的分别只有23.0%、11.0%,外来人口表示对本地居民有过“经济帮助”或“情感关心”的分别只有17.0%、12.0%。可见,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互动主要还是工作层面的业务往来,生活上的交往互动也主要是浅层性交往,比如简单的家常聊天,而深层次的交往互动则比较少。也就是说,两者之间的互动更多是工具性交往,而非情感性交往。访谈个案“本地-7”(本地人,女,48岁,小学毕业,自由职业):“我与外地人的交往,主要都是因为租房之类的事情,一般没啥事也不会找外地人聊天,感觉外地人挺辛苦的,但是对他们其实也没什么关心。”
与此同时,相比年长一代,年轻一代的交往互动更为深入。年轻一代本地居民表示对外来人口有过“经济帮助”或“情感关心”的占到了31.3%、16.7%,年轻一代外来人口表示对本地居民有过“经济帮助”或“情感关心”的占到了20.6%、14.3%,均是年长一代同类数据的2-3倍。访谈个案“外地-2”(安徽人,女,22岁,初中毕业,服务员):“我感觉与本地人没什么不好相处的,没什么特别的身份差别。我与认识的几位本地姐妹,就经常一起逛街什么的,也曾相互借钱给对方,挺有感情的。”

表6 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互动广度情况 单位:人
(四)互动张度
我们发现(表8),在回答“你与外来人口(或本地居民)发生过矛盾冲突吗?”时,73.0%的外来人口表示与本地居民“较少”或“很少”发生矛盾冲突,72.0%的本地居民表示与外来人口“较少”或“很少”发生矛盾冲突,这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基本是平和的。也就是说,尽管两者之间的互动频率、互动广度、互动深度都不大乐观,但总体处于相安无事的状态。但需要关注的是,外来人口对本地居民的反歧视意识较为强烈*杨富平在《进城农民工的反歧视意识与反歧视行为——基于浙江省L区的调查分析》(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2期)中,认为当前进城农民工的反歧视个体意识比较强烈。,也就是说,两者之间存在发生矛盾冲突的较大潜在可能性。访谈个案“外地-4”(湖南人,男,34岁,高中毕业,工厂技工):“我与本地人发生冲突比较少,我们打工的赚钱为主,平安最重要,干嘛闹事呢?但是,有时候我对本地人的自以为是,挺看不惯的,是有怨气在的。”
同时发现,年轻一代似乎更易于与另一方发生冲突,19.1%的年轻一代外来人口表示与本地居民有过“较多”或“很多”矛盾冲突(年长一代是8.1%),同样也有18.8%的年轻一代本地居民表示与外来人口有过“较多”或“很多”矛盾冲突(年长一代是11.5%)。这里好像又存在一对矛盾:年轻一代的互动频率、互动广度、互动深度都是更加积极乐观的,为何却比年长一代发生更多的矛盾冲突呢?这也许与他们的年轻气盛有关,也许与年轻一代外来人口具有更强烈的平等意识、权利意识有关。访谈个案“外地-1”(安徽人,男,26岁,初中毕业,工厂工人):“有时候,我挺容易与本地人发生争执与冲突,感觉本地人好像都高人一等,看不起我们外地人,实际上本地人比我们好到哪里去呢?还不是差不多嘛,我们干嘛要低人一等。”
五、总结与讨论
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互动,既是考察外来人口是否融入城市社会的重要指标,也是观测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关系是否和谐融洽的重要指标。关于两者之间的社会互动特征,学者提出了一些相互竞争又相互补充的研究观点。2001年朱力提出“摩擦性互动”[5]观点,认为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互动是不融洽的,具有摩擦性和冲突性。2007年杨黎源提出“复合动关系”[6]观点,认为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是一种强弱兼有、若即若离的“复合的、动态的”关系。2009年关信平、刘建娥认为,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近乎是“平行生活”的状态,是“没有互动的共存”[7]。与关信平观点类似,2012年李培林、田丰也认为,流动农民工的社会互动主要集中在农民工群体内部,缺乏与城市人群的社会互动,比较类似于所谓的“区隔型融入”[8]。
然而,我们在研究中有一些新的发现。根据上文分析,当前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互动存在多处“矛盾”或“纠结”:第一处,本地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总体评价是正面偏上的,但接纳意愿却比较低,难以接受与外来人口建立比较亲密的关系;第二处,外来人口对本地居民的总体评价是负面偏下的,但却表现出较高的亲近意愿,或者说,比较希望与本地居民建立比较亲密的关系;第三处,年轻一代在互动频率、互动广度、互动

表7 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互动深度情况 单位:人

表8 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互动张度情况 单位:人
深度上都表现出更加积极的一面,但是年轻一代的互动却更具张力,比年长一代更易于发生矛盾冲突。对于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这么一种互动状况,我们暂且可称之为“纠结型互动”。所谓“纠结型互动”,是指外来人口或本地居民在与对方进行交往互动时,面对外部客观环境,面对诸多选择顾虑,在评价与接纳、意愿与行为、行为与行为之间出现不一致、相矛盾的现象,有点类似于“口是心非”,这背后实际反映出外来人口或本地居民在互动过程中的纠结、矛盾、犹豫的复杂心态。
我们认为,当前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纠结型互动”具有积极意义。相比“摩擦性互动”与“没有互动的共存”,“纠结型互动”表明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态度、交往、关系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比如:本地居民尽管还不愿意与外来人口建立亲密关系,但至少在态度上开始对外来人口给予理解与肯定;外来人口尽管对本地居民仍然有较大不满,但开始希望与本地居民交往并建立良好关系;年轻一代相比年长一代,互动频度、广度、深度都呈现了更加积极一面,尽管易于发生矛盾冲突,这除了年轻气盛的生理个性特征,另一层面则说明年轻一代外来人口开始具有更加强烈的平等意识与权利意识。可以这样说,“纠结型互动”是“摩擦性互动”向“融洽型互动”转变的一种积极的过渡关系形态。
尽管如此,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互动,总体而言仍然不大乐观。此外,人口急剧流动带来的“人口倒挂现象”,也对当前村治模式提出了直接而现实的挑战。我们建议:在户籍制度尚未破除的情况下,应当建立一种开放式的社区参与机制,让外来人口积极参与到各类社区活动中来,增加与本地居民的接触和互动,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与偏见,提升外来人口的归属感与责任意识,以此推动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实现良性互动并建立融洽关系。
参考文献:
[1]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3,(1).
[2]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江海学刊,2002,(6).
[3]刘林平.交往与态度:城市居民眼中的农民工——对广州市民的问卷调查[J].中山大学学报,2008,(2).
[4]杨黎源.宁波市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关系状态评析[J].南京社会科学,2007,(7).
[5]朱力.群体性偏见与歧视——农民工与市民的摩擦性互动[J].江海学刊,2001,(6).
[6]杨黎源.外来人口社会关系和谐度考察——基于对宁波市1053位居民社会调查分析[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7,(3).
[7]关信平,刘建娥.我国农民工社区融入的问题与政策研究[J].人口与经济,2009,(3).
[8]李培林,田丰.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J].社会,2012,(5).
[责任编辑:马莉]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307(2016)02-0067-08
[作者简介]杨富平(1984—),浙江台州人,中共路桥区委党校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讲师,主要从事社会发展与流动人口研究;杨尔飞(1982—),安徽宣城人,合肥师范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应用社会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省党校系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第十六批规划课题(ZX16215)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5-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