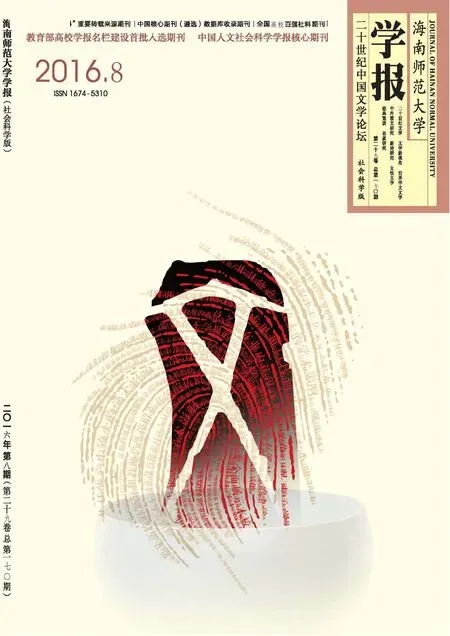“小脚”里的大家族
——读冯骥才《三寸金莲》
甘 瑞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海南 海口 571158)
“小脚”里的大家族
——读冯骥才《三寸金莲》
甘瑞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海南 海口 571158)
冯骥才的《三寸金莲》不仅写出了文化的反常,也写出了一个反常的家族。论文从佟家这个大家族中的家长、家族继承者和女性等成员与小脚的关系入手,分析这一家族的反常和颓败。
冯骥才;《三寸金莲》;小脚;家长;女性;阴盛阳衰
冯骥才的中篇小说《三寸金莲》发表于1986年,是其“怪事奇谈”系列小说之二,小说主要涉及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劣根之一“小脚”。这篇小说的出现带来了评论界的众说纷纭。从《三寸金莲》刚发表到现在,关于这篇小说的研究一直没断过。目前关于《三寸金莲》的研究主要有民俗解读、文化批评、批评的批评、语言特色和审美意象等几个方面。评论界对这篇小说的态度有一个变迁的过程:否定文本、批判其不足到肯定文本、探索其价值。而否定这篇小说的研究论文多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如陈墨的《失败的文本——评小说〈三寸金莲〉》①陈墨:《失败的文本——评小说〈三寸金莲〉》,《文学自由谈》1988年第2期。和邹平的《且说〈三寸金莲〉——阅读反应批评》②邹平:《且说〈三寸金莲〉——阅读反应批评》,《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6期。,前者认为小说思想混乱,存在叙事方法的危机和缺乏艺术张力,以致整篇小说“走了调”;后者认为小说的“书前闲话”着墨太多,罗嗦。而肯定这篇小说的研究论文多集中在本世纪以来十几年,如杨蓉的《试论“三寸金莲”意象的审丑意味》③杨蓉:《试论“三寸金莲”意象的审丑意味》,《剑南文学(下半月)》2015年第1期。,吕娜的《缠放的历史,扭曲的人生——〈三寸金莲〉赏析》④吕娜:《缠放的历史,扭曲的人生——〈三寸金莲〉赏析》,《金田》2014年第6期。,吴静的《从读者反应批评视角解析〈三寸金莲〉的尴尬境遇之原因》⑤吴静:《从读者反应批评视角解析〈三寸金莲〉的尴尬境遇之原因》,《安徽文学》2015年第6期。,吕颖的《〈三寸金莲〉民俗解读》⑥吕颖:《〈三寸金莲〉民俗解读》,《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和孟玉红的《赏析〈三寸金莲〉的语言特色》⑦孟玉红:《赏析〈三寸金莲〉的语言特色》,《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等论文。这些论文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三寸金莲》的文学价值。
对于这篇小说里所描写的关于裹脚的细节和“莲癖”们对小脚的种种态度,笔者初次接触的感觉是想吐,觉得恶心。而在之后的多次重读后,笔者不仅没有觉得恶心,反而进入小说之中开始了思考,也许这就是这篇小说的魅力吧。冯骥才先生在与周立民的对话中曾说:“有一位女作家对我说,我读了《三寸金莲》,感到恶心,想吐。我说,你的反应很正常,因为《三寸金莲》写的正是文化的反常,如果你感到大饱眼福就真的有麻烦了。”⑧冯骥才,周立民:《冯骥才周立民对话录》,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07页。其实,《三寸金莲》不仅写出了文化的反常,也写出了一个反常的家族。关于这篇小说的文化批判的论文很多,而且研究成果颇丰,本文就从《三寸金莲》塑造的佟家这个大家族中的人物入手来分析这一家族的反常和颓败。
家族是一个不断被言说的话题。“家族,既是现代作家情感的家园,又是精神的牢笼。”*李永东:《颓败的家族:家族小说的文化与叙事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1页。家族这一话题在现代作家的笔下不断出现,无论是鲁迅的《狂人日记》、林语堂的《京华烟云》,还是巴金的《家》、萧红的《呼兰河传》、张爱玲的《金锁记》等,这些作品都离不开一个家族故事的叙说。当然,到了当代,家族的话题并没有被作家们所抛弃,不然怎会有陈忠实的《白鹿原》、苏童的《妻妾成群》、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等家族叙事小说?虽然冯骥才先生的《三寸金莲》是围绕着“小脚”而展开的文化批判,“小脚”这一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劣根之一,象征和隐喻着封建文化的自我束缚力,但不应忽视的是,小说的叙事核心写了一个大家族——佟家,这个大家族是凡事离不开“小脚”的家族,在分析和阅读这篇小说的时候,必须把这个家族了解透彻,才能真正地读懂这篇小说。
一、充满淫欲而腐朽虚假的家长
佟家在天津卫是有名的有钱,“娶媳妇比买鱼还容易”,*冯骥才:《乡土小说》,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49页。就是这样一个阔家,却反常地非要娶戈香莲这个穷家小户里养出来的闺女,原因竟然是香莲有一双小脚。“中国传统社会最基本、最牢固的基层组织与生活单位是家族(庭),它有着严格的宗法等级关系,而高居权力塔尖的就是作为一家之主的家长。家长是威严专制的,对于家庭其他成员有着生杀予夺的绝对大权,因为父权至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家族的首要伦理原则。”*杨贤美:《20世纪家族小说人物论》,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6页。在佟家,佟忍安是家长,他在这个家里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他是一个“莲癖”,不仅喜欢玩弄小脚还懂得小脚的神韵,所以佟家的女人们,上到过世的太太、四个儿媳妇,下至老妈子潘妈、丫环桃儿、杏儿,哪个进入佟家不是因为自己的小脚?
文中虽然没有出现佟忍安的太太,却时刻有着这位太太的影子,她是一个小脚女人,她有一双绝世无双的小鞋,而且佟家“赛脚”的规矩也是她想出来的。她是佟忍安发泄淫欲的对象,她生前有一双小脚可以供佟老爷玩弄,她还琢磨出“赛脚”来哄佟老爷开心。进了门的这些儿媳妇们也是围着丧偶而饥渴的佟老爷转,香莲进门不久就在睡午觉时被佟老爷摸了小脚,香莲却不敢有任何反抗。在第一次赛脚二少奶奶白金宝得胜后,佟老爷天天进她的房,竟致使白金宝不叫二少爷佟少华进房门。这是什么道理,妻子不叫他的丈夫进门,“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女人怎么有这么大的能耐,还不是她背后的权力大?在这个家里,佟忍安最大,谁得他的宠,谁就可以胆大包天。家里的女人全是他的,所以没有了正常的伦理,只有满屋的淫欲,女人的威风也是他的,今天威风在白金宝身上,明天权力又会在戈香莲手中。因为有一双男人喜欢的小脚,连脸长得瘆人的潘妈都是佟老爷的秘密情人,由此可见“先看脚后看脸”的佟老爷是多么的变态,他把小脚当作性器具来玩捏以满足自己的淫欲。
佟家的这个家长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养古斋”古玩铺的掌柜。佟老爷天天辨认真假古董,而且只卖假,不卖真。他是一个腐朽虚假的人,整天与一些腐朽的老古董打交道,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明明是假古董,却叫伙计们告诉卖家都是真货来欺骗卖家,只要买就一定上当。他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威望,他身边的人对他来说都是越笨越好,这样才能被他利用和使唤。佟掌柜自己“火眼金睛”,可以轻易地辨认出真古董和假古董,所以他铺子买来的古董必须由他亲自来辨认,假的就拿到铺子上当真的来卖,而真的就留着。但是这个过程是秘密的,只有自己人在场,而活受也在场,那是因为“对看库的活受,绝非信得过,而是这小子半痴半残”和“拿死的当活的用,也拿活的当死的用”*冯骥才:《乡土小说》,第241页。。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佟掌柜反常的作风。佟掌柜造假画也与众不同,“他雇的伙计,跟一般古玩行不同,不教本事,只叫干活干事儿”*冯骥才:《乡土小说》,第246页。。所以,在养古斋这个古玩铺,除了掌柜,大家对古玩都是一窍不通的,在古董面前都像傻子一样,佟掌柜可以很放心地做生意,反正只要卖出去就会只赚不赔。
在这个家里,佟老爷是一个充满淫欲而腐朽虚伪的封建家长,他有着专制的理由和绝对的权威,他的生意是财源滚滚,他的生活是无比惬意。而且在佟老爷快断气的时候还专制地要求下一辈开始裹脚,不看到失踪的莲心回来一起裹脚还硬撑几天不肯断气和闭眼。如果用鲁迅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吃人’的家庭,连孩子也不放过,所以救救孩子……”。然而“聪明反被聪明误”,佟老爷最后却死在“真人不露相”的活受手里,还被香莲欺骗送走了孙女莲心。
二、阴盛阳衰的家族继承者
古人常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中国家族极为重视家族的延续,而长子作为儒家济世理想的承载者,负有继承家族传统的责任,家族兴亡系之于一人,责任奇重。”*杨贤美:《20世纪家族小说人物论》,湖南师范大学2005年度硕士学位论文,第26页。“佟家没闺女,四个儿子,俗话叫‘四虎把门’,排绍字辈,名字末尾的字,一叫荣,一叫华,一叫富,一叫贵。”按这样来说,佟家是后继有人了,但是偏偏“可这四个儿子,一半是残”,因为大儿子佟绍荣是傻子,四儿子佟绍贵自小有病,已经叫阎王派小鬼给抓走了。而二儿子虽说在“养古斋”古玩铺当个少掌柜,但是却不成器,没有父亲佟老爷辨认真假的本领,整日就想着叫自己女人的小脚给自己添点儿自信,帮着二少奶奶与香莲争风吃醋,最后竟荒唐地与活受一起偷了家里的财物远走他乡而被活受害死。三儿子佟绍富在外地做生意,回来探亲都能因为出点意外而回不来,在父亲佟老爷下葬的时候又因黄河淮河发水无法通知而没有回来奔丧,这个儿子的存在就像没有一样,没有为这个家做过什么。佟家四个儿媳妇,三个守了寡,真是阴盛阳衰,没有了男人,女人的价值就在于她们的小脚了,佟家的女人们凭着自己的小脚而有一席之地。
年轻一代是阴盛阳衰,孙子辈更是没有一个男孩,几个儿媳生的全是女孩。二少奶奶白金宝有两个闺女月桂和月兰,三少奶奶尔雅娟有一个闺女,四少奶奶董秋蓉有一个闺女,而大少奶奶戈香莲想生个小子,给佟家留后,却偏偏也生了一个闺女莲心。儿媳妇们想通过生儿子来“母凭子贵”的道路行不通,只能通过拾掇自己的小脚来上位了。白金宝和戈香莲为了争权而想要用小脚来打败对方。无论是白金宝、董秋蓉还是尔雅娟,不管是主动或受人教唆,她们都和香莲比过小脚,因为在阴盛阳衰的佟家,女人的小脚就是争权夺势的资本。
在佟家,一家之主佟老爷一死,全家人都没了主心骨。香莲大叫一声:“老爷子,您可不能扔下我们一大家子孤儿寡母走啊!”*冯骥才:《乡土小说》,第363页。连平时最冷静最有主意的大少奶奶此时都已没了主意。此时,佟家没有一个男人来主持大局,白金宝盼着佟少华回来独掌佟家,而戈香莲盼着佟忍安还阳,原来女人还是渴望依靠男人。“无论谁如了愿,佟家大局就一大变”,但是她们都没有如愿,佟家就是一个阴森森的地方,没有男人的生存之处,只是小脚的兴盛之地。所以,最后所有的事还是由小脚女人做主,小脚女人主持大局。佟老爷死了,香莲主持大局;香莲死了,月桂主持大局。
在这样一个家族里,男人却没有用武之地,男人没有一个成气候的,这真是一个反常的家族。现实中似乎是不存在这样的情况的,但是正如冯骥才先生所说:“小说的真实有几个层次,一是生活的真实,一是环境的真实,一是人物的真实,一是情理的真实,一是感觉的真实。中国人在文学艺术的高超之处正是抓住情理这一更高层次上的真实,因此无论邪魔、鬼狐、精魅,都写得入情入理。”*冯骥才:《我是冯骥才:冯骥才自白》,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年,第194页。由此可见,这里“似乎不存在”的“真实”,正是“情理的真实”。
三、困在“小脚围城”的女性成员
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女性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并且女性是被压抑、受欺辱的代名词。而且中国传统社会的女性一直被控制在家里,“养在深闺人不识”的处在深深庭院之中。“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规约也是不容质疑和更改的。所以家务、传宗接代等都成了女性的生活重心,女性是甘愿受礼教束缚而自觉维护礼教和社会规约的一个群体。
《三寸金莲》中有一个女性不容忽视,她就是香莲的奶奶戈老婆子,这个老婆子是一位“大能人”。“这些邪乎事、邪乎话,满城传来传去。人嘴歪的比正的多,愈说愈邪乎可传到河北金家窑水洼一户姓戈的人家立时给挡住了。”*冯骥才:《乡土小说》,第230页。挡住这些邪乎事、邪乎话的正是戈老婆子,她竟然将这些邪乎事说成喜事,说是“大吉大利大喜大福”。由此看来,事情是什么样子并不重要,关键是人们如何去理解和消化它。就是这样一位老太婆,她给自己的孙女戈香莲裹了一双小脚,凭着这双小脚,香莲真的“飞上枝头变凤凰”了。戈老婆子狠心地给孙女裹脚,说是因为香莲母亲临死的嘱咐,其实何尝不是戈老婆子自己对“裹脚”这一风俗的认同,有了小脚,孙女才会嫁得好。在戈老婆子心中,小脚竟然如此神圣,当她知道香莲第一次赛脚失败后竟气闭过去,悔恨作古了。在这里,小脚就是女人的命。
“能人”背后有“仙人”,奶奶死后,潘妈来帮香莲裹脚,教香莲裹脚,香莲发现潘妈是会裹脚的“仙人”。但是“仙人”背后还有“神人”,裹脚的虽然是女人,但是真正懂“小脚神韵”的却是男人,玩弄小脚的是男人,给小脚定标准的也是男人,而佟忍安正是这位神人,为了成全一双有神韵的小脚,公公佟忍安竟给儿媳香莲下跪。潘妈这位人老珠黄、长相奇丑的老太婆却是佟忍安的秘密情人,原因就是潘妈有一双小脚,小脚上还有伺候男人的好功夫。潘妈安静、吓人,就连养的猫都瘦得吓人。就是这样一个老太婆,她却会裹脚。手上功夫很好,全家的小鞋都由她来打理,她帮谁,谁就准胜。第一次赛脚,白金宝能够夺魁就是因为潘妈的帮助。而且在香莲母女要死的时候,潘妈来到了,她要帮助香莲重新裹脚,与其说她要救香莲,不如说她要救小脚。潘妈对香莲说:“您为您自己,我也为我自己。可都得用您这双脚。”*冯骥才:《乡土小说》,第287页。潘妈本与香莲没有往来,却因小脚来帮香莲,在潘妈眼里,小脚比什么都重要,可见小脚已经是潘妈这个老女人生命中的一部分了。不仅是男人束缚女人,女人也束缚女人,女人也在束缚自己。最后,在佟老爷死时,潘妈与自己屋里的几百双小鞋一起葬身火海了。在这里,小脚、小鞋就是女人的命。
香莲与白金宝争权夺势的筹码也是小脚,香莲获胜掌管了这个大家庭,最终却又因小脚而死。“三寸金莲”,白金宝是“金”,戈香莲是“莲”。但无论谁都没有逃过小脚的围城。到了民国,全城在闹“放脚”,就连“莲癖”陆达夫也摇身一变而成了“闻着小鞋,写讲稿”的陆所长,站在佟家大门外讲演“放脚”。然而佟家的当家人香莲依然要佟家所有的女人继续缠脚,日夜都不能放脚。这是为何呢?香莲不是曾偷偷地把自己的女儿莲心送出去而让女儿躲过裹脚这一劫吗?香莲这一生不是已经看透了吗?香莲曾说:“我喜欢这‘空’字!”*冯骥才:《乡土小说》,第323页。香莲曾自言自语:“一切一切不过那么回事儿!”*冯骥才:《乡土小说》,第402页。现在外面大闹放脚不是正好可以如愿了吗?但这不是香莲的心思。香莲的一生毁在了裹脚上,也就是香莲的宝全押在了小脚上,小脚要是没有了,香莲的战果也就没有了,因“小脚”而赫赫有名的佟家也就完了。“缠放缠放缠放缠”的小脚,不仅是佟家的荣,还是佟家的命。香莲带领“复缠会”的女人们与“天足会”的会员们进行的比赛竟然也是赛脚,而且资本依旧是小脚和不断变样的小鞋。香莲还花了心思做“万象更新鞋”,都与小脚分不开。而且,无论是香莲、白金宝、董秋蓉,还是月兰、月桂,佟家的女人个个都逃不出小脚的围城。莲心逃掉了,再也回不了佟家了,却仍旧是小脚女人戈香莲的女儿,依旧站在小脚围城边,“甚至也不知自己是谁,姓牛还是姓佟。”*冯骥才:《乡土小说》,第416页。所以在香莲的丧礼上,月兰竟以为莲心的出现是“黄鼠狼给鸡吊孝,准不安好心!”*冯骥才:《乡土小说》,第415页。在这里,小脚就是佟家所有女人的生命。没有了小脚,就不再属于佟家。
总之,“小脚”这一象征着中国封建文化自我束缚力的意象,小到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大到一个国家,都是不容继续存在的,也最终被大家所抛弃而不愿再提起。但是,在现代“放足”的社会里,它却并没有完全被大家遗忘,也没有完全消失,“小脚”以另一种形式或多种形式在社会上兴风作浪。看看一些女人为了取悦男人而节食减肥导致器官功能退化的现象,看看女人为了迎合现代的审美要求而穿高跟鞋导致走姿下滑的现象,再看看一些女人为了丰胸美容而去做美容手术导致自己成了“鬼样子”的下场,这不都是另一种“裹脚”吗?所以《三寸金莲》的社会意义和现实价值不容忽视。
(责任编辑:毕光明)
Feng Jicai’sFemales’BoundFeetatFeudalAgeInterpreted
GAN Rui
(SchoolofLiberalArts,HainanNormalUniversity,Haikou571158,China)
Feng Jicai’sFemales’BoundFeetatFeudalAgenarrates not only the cultural anomaly but also an unusual famil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anomaly and decadence of the Tong family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ound feet and such family members as parents, family successors and females.
Feng Jicai;Females’BoundFeetatFeudalAge; bound feet; parents; females; empowering women and waning men
2016-04-20
甘瑞(1988-),女,河南新蔡人,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I206.7
A
1674-5310(2016)-08-0033-04
——由“三寸金莲”而催生出的弓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