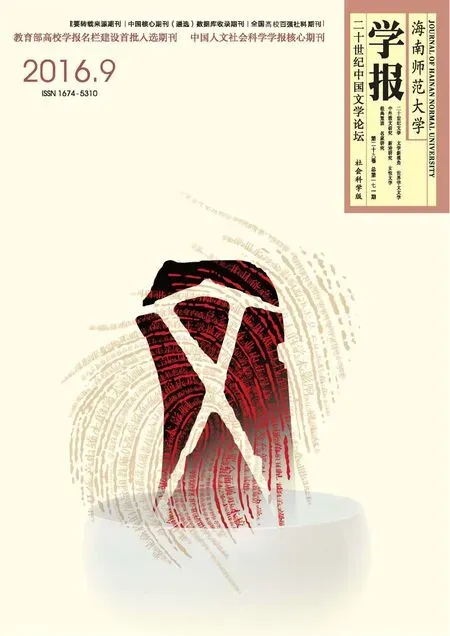中国诗史中的“湘怨”情结
——以唐诗宋词为中心
潘链钰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6)
中国诗史中的“湘怨”情结
——以唐诗宋词为中心
潘链钰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6)
“湘怨”情结是中国诗歌史中值得关注的特殊文化现象。自娥皇女英与屈宋以来,湘怨情结在诗歌史中有着一条明晰的发展线索。其中,湘怨情结在唐宋发展中又有着明显的转变过程。如果说唐代湘怨情结承接唐前湘怨的无限哀思与悲愤之感的话,那么宋以来的湘怨情结则开始转变为词风清丽的风景之叹、离别之悲与失意之怨。唐宋湘怨内涵与特征的转变其实是整个中国诗学审美内涵转变的一个维度。
湘怨;唐诗;宋词
引言
子曰:“诗可以怨。”自孔子此句后,诗之用来抒发内心的愁苦与哀怨则变为一种正统而精到的诗论法则。诗之怨,包含有两个方面,一是自《诗》《骚》而来的“怨刺上政”的传统,二是自辞赋而来的个人感念之怨。中国诗歌史中大量的情怨抒发,即以证明“诗可以怨”乃是古人诗作之大观。文学地理学显示,“诗可以怨”在古代疆域版图中皆有迹可循。西北边疆有“塞客衣单,孀闺泪尽”的征人之怨;江南之地有“春风又绿,明月难还”的失意之哀;至于“和氏哭璧”、“长史悲愤”、“蔡姬恨嫁”、“韩囚马轻”、“植悲丕叹”等等,皆在华夏各地以怨垂名。然而,中国诗歌史中却少有因一地而形成一种固定的悲怨情结,那便是源自禹舜、继乎屈氏的“湘怨”。
“湘怨”,因潇湘之地而产生的悲怨。最开始以娥皇女英哭舜之死便蒙上了一层悲哀之色。继之而起的伟大诗人屈原,因谏获罪,放逐潇湘,以致悲愤自沉,更使得潇湘之地升腾起一种悲凉之气。如果说,娥皇女英尚且因个人之情与女性之节而怨,那么屈氏则更因邦国之乱、谋世之贼与怀才不遇而产生强烈的激愤之怨。双妃之节与屈氏之怨,直接成为中国诗歌史中湘怨情结的最主要的源头。屈氏之后,诗人每每莅临潇湘,或因个人遭际,或因境遇感伤,或赞叹双妃忠贞之洁,或哀感屈氏自沉之愤,由此留下的诗作不胜枚举。战国之宋玉、景差,汉之司马迁、班固、扬雄、贾谊,六朝之刘勰、钟嵘,唐之李杜王孟,宋之东坡、山谷、文忠、介甫,明之七子,清之格调神韵诸派,皆以诗道情,或论双妃,或述屈子,皆以怨充情,长歌当哭。
刘勰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实际上,屈子之后“湘怨”情结在历代诗歌中之审美特征已然并非一致。若细而论之,则汉之“湘怨”真彻哀泠,六朝之“湘怨”文深情茂,唐之“湘怨”悲丽明净,宋之“湘怨”清雅理沈,明清之“湘怨”思理精缜。仔细分析诗歌史中的“湘怨”情结,实际不难发现,自汉至清,中国诗歌中的“湘怨”情结有着从少到多、从冷到热、从悲婉到自得、从外感到内叙的发展过程。其中,尤以唐宋变革为契机,“湘怨”情结的审美内涵也以此为分野,有着明显的变化。
一、唐诗与唐诗的“湘怨”
唐朝武德四年,高祖置潭州总管府,湖南现在的市县都基本归其管理。当时分为潭州、衡州、永州、郴州、连州、南梁州、南云州、南营州8州。后武德七年改总管府为都督府,统辖潭州、衡州、永州、郴州、 连州、邵州和道州共7州。唐太宗时,始设道,道下设州(或郡),州下为县。湖南分属山东南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黔中道黔州都督府。唐广德二年又置湖南观察使,“湖南”之名自此始。潇湘之于湖南,湖南之于大唐,一点一面,皆血肉相连。唐之文化深入影响着湖南潇湘。因此,欲分析唐之“湘怨”,不得不先明析“湘怨”之唐。
(一)唐诗湘怨的文化背景:事功心态与抱负不得
大唐瑰丽万有之气势,尤其是初盛唐之雄强隆盛之万象,让这个国度的人民充满了自信。然而,正如狄更斯《双城记》所谓:“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英]狄更斯:《双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页。盛世带来的巨大发展让唐人充满了机遇,同时也充满了挑战。尤其是唐人实际乃是极具事功心态的。唐人的致用意识,比之前任何时代都要强烈。初唐之“四杰”、子昂,直指“文章道弊”,直接目的正是扭转绮靡文风,一改齐梁脂粉之气,以新的面貌迎接大唐诗歌的来临。李白、杜甫又何曾悠然于世外而纵享陶潜之隐?李白一世都以强烈的追求功名的欲态呈示。杜甫直接喊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伟大志向。至于中唐权德舆的文道中兴、韩柳之文以明道、“郊寒岛瘦”的良苦用心无一不是直接指向致用。这是经学经营致用之思在大唐环境下的明显表现。大唐强盛与发展培育了文士诗人的事功心态,此乃经之致用所为。然而,理想一端的饱满往往在触碰现实之枯软之后,呈现出无比的残酷面貌。所以初唐人王勃失意时直接吟唱出“高台西北望,流涕向青松”*[唐]王勃:《王子安文集》,[清]蒋清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78页。(《铜雀妓二首·其一》)。诗仙李白不得志时,以史自我疗救,感叹“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唐]李白:《李太白全集》,王琦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887页。(《行路难·其二》)。甚至李白在怨恨之际直接想到了吴楚两地两个孤独而悲愤的人伍子胥和屈原,所以李白直接写诗道:“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唐]李白:《李太白全集》,王琦辑注,第739页。(《行路难·其三》)如果说这些尚处于平常诗人的境遇有悲有怨尚可理解,那么开元之际的宰相张九龄,以其宰相之尊,其诗其人也饱含着浓浓的哀怨之情。“朝阳凤安在,日暮蝉独悲。浩思极中夜,深嗟欲待谁。”*[唐]张九龄:《曲江集》,刘斯翰校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7页。(《感遇诗·其十二》)诗人以蝉自比,想要作凤朝阳飞舞,却发现昏云遮日,不能自知。所以诗人更加感慨道:“神理日微灭,吾心安得知。浩叹杨朱子,徒然泣路岐。”*[唐]张九龄:《曲江集》,刘斯翰校注,第157页。(《感遇诗·其三》)如果列举唐代悲怨诗人的诗句,这段文字将是长长的走廊,一眼望不到头。诗人之心乃是家国之心、天下之心。面对现实的沉重,无人不暗自悲愤伤情。所以,陈子昂那首有名的《登幽州台歌》所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不仅仅是子昂一个人内心彷徨无助的吟咏,更是那个时代每一个伟大而孤愤的灵魂内心真挚的呐喊!要而言之,唐代文士在怀才不遇、抱负不得的时候,其“诗可以怨”的心理认知就会表现得非常的明显。所以,可以看出,事功心态与唐人明显的功利意识,是造成唐人诗之有怨的主要因素。
(二)唐诗湘怨的地理因由:缘起东南与告别长安
中古文学演变史简而言之,实际是庶族阶层崛起而士族阶层衰微的演变史。自汉魏六朝至隋唐两宋,庶族阶层的逐渐强大改变了原先士族阶层垄断文化的局面,一股新鲜血液的涌入让整个文化鲜活起来,不再似贵人慵懒的颓败之景。唐初高祖与太宗正是借助了庶族阶层的力量,才能与老旧的陇西、山东等旧部抗衡。而这些庶族阶层大多都是东南文士。也就是说,这股新兴力量的代表,正是源自东南。
唐初关中、山东、江南三大地域不仅存在明显的地缘政治差异,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区域文化差异。唐人称山东为“河洛”,称江南则为“江左”。《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传中》直引唐人柳芳《氏族论》做以上三者之别道:“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姻,其信可与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与也;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达可与也。”*[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769页。论江左之人,以一“文”字概括,可谓尤确。文德贵政,因而唐帝国统治者未将治国大任全然交予尚雄之关中人与尚质之山东人,而是倚仗尚智之江左人,应该是十分正确的选择。后来的历史证明,东南文士对唐代文治政治局面之形成影响的确十分深远。
江左驻于神州东南,自六朝便是经济富庶、人才荟萃之地。江左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加上久远流传的“耕读传家”之处世理念,造就了极为浓郁的文化氛围。而东南这种学术世家的传承实际自东汉后便逐渐兴盛。东汉后之学术不再以政治中心为传播之重,而以地方大族为传播之倚。正如陈寅恪先生指出的:“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名都大邑。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31页。江左作为唐初政权根基的三点之一,与关中、山东相较自然势力不敌,但三者同在由隋入唐政权转变浪潮中贵气渐失的境遇里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关中尚武,武力出雄能在乱世颇有建功 ,但政权渐稳的阶段则极易引发皇权争斗的危机以及太平时期的武无所用之尴尬,自然不会受到特别的重视。山东重婚姻,血缘关系一方面能带来政权中心的相对固定化,但固定化的另一面便是僵化,这会导致政治活力之丧失与骄逸心态之渐涨。太宗卓识,早在秦王时期便意识到这些问题,且因深谙世事累迁之律故慧眼识得江左才是唐政权稳固之重点。太宗的远见卓识一方面开启了唐代以文治国的道路,另一方面也让东南文人在政权构建中能够发挥才能,为王权所用,为苍生谋福。从后历史的角度考察,东南文人学术的确在大唐文治建设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东南文人造就了初盛唐博雅隆盛的宏大局面。
当代表新兴力量的东南文士告别故土、依附政权的时候,他们的内心是以反客为主的心态看待整个由南往北的迁徙过程的。所以当庶族阶层认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身才干,效仿先贤辅佐明君之时,他们的态度是自信的,甚至是高傲的。告别了江南之地的春花秋月、鸟语花香,天地春色成为他们心中构想的理想社会的蓝图的底本,明君贤臣之理想成为他们心目中为之奋斗的不竭动力。所以,当李白接到了入秦的旨意之时,他自信地喊出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豪迈诗句。在大唐,像李白这样先自信满满后无比失意的文士不胜枚举,但李白应该是最为典型的诗意人才。自以为人中龙凤的青莲居士,最后成为帝王的倡优臣子,理想的高远与现实的冰冷造就了李白等文士内心极大的反差。那么,忧国忧民在人之常情里自然而然变为清愁深怨了。所以,每一个诗人在遭遇贬责之后,尤其是在告别长安之时,内心之离愁别绪可想而知。所以,刘禹锡离别长安之时才会吟出“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柳道离别”*[唐]刘禹锡:《刘禹锡全集》,瞿蜕园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54页。的无奈之叹。李白被贬时感伤悲怨道:“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唐]李白:《李太白全集》,王琦辑注,2011年,第769页。(《与史郎中饮听黄鹤楼上吹笛》) 李山甫更咏叹出“年年今日谁相问,独卧长安泣岁华”*中华书局编辑部:《全唐诗》卷五四九,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寒食二首》) 的悲凉之句。甚至一向闲适自居的白居易,在长安几经别离之时,也喟然说出了“君不见,外州客,长安道,一回来,一回老”*[唐]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三十九,四库全书本。(《长安道》) 的无限感怀之语。听白居易这样伤怀,简直有着“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之悲怨。这是大唐空间转变下心态与情境转变的典型。
由“山水方滋”的江左而来,到与“河朔贞刚”的关中相别,一来一别,也许已经包含诗人们无限的情愁与感伤。那么在途遇湖南的潇湘之水,窥临洞庭的秀丽君山之时,湘妃与屈原即当燃起于每一个惆怅之客的内心。或与之话语,或与之慰藉,或与之轻叹,或与之共泪。这便是“诗可以怨”再一次袒露的悲凉之力,也正是这样的地理因由造就了唐代诗人一旦莅临潇湘,前愁后绪一涌而发的“湘怨”情结的真实来源。
(三)唐诗“湘怨”的美学风貌:“文温以丽,意悲而远”
公元737年秋,值玄宗开元二十五,诗人王昌龄获罪被谪岭南。行至潇湘境内,遇到好友胡大。胡大热情款待王昌龄。临别王昌龄赠胡大诗一首,名《送胡大》:“荆门不堪别,况乃潇湘秋。何处遥望君,江边明月楼。”*[唐]王昌龄:《王昌龄诗校注》,李国胜注,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第126页。不久,王昌龄又与好友谭八在潇湘分别。秋风萧瑟,离别为艰。面对湘水秋景,王昌龄又赋诗一首《送谭八之桂林》:“客心仍在楚,江馆复临湘。别意猿鸟外,天寒桂水长。”*[唐]王昌龄:《王昌龄诗校注》,李国胜注,第128页。无论是送别哪位好友,王昌龄的内心都充满着无限的惆怅。然而惆怅的心情不能以惆怅的表达写出。因为在唐代,尤其是盛唐,对诗歌意境的追求已经是普遍的时尚。因此,以景写情无疑是更为高妙的抒情手段。面对相逢之后的再次离别,诗人只能按捺心中悲凉之意,何况秋风无情,叶落飘零。所以,当好友远去湘水之外,能够远远瞻望的,只有在江边孤寂的阁楼上看着皎洁的明月。而此身所在的秋色,鸟啼猿叫,天寒桂冷,更将凄清幽怨的内在之情展露出来。王昌龄手法高超,无怪明代诗论家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将王昌龄比于李白,称:“昌龄得之锤炼,太白出于自然,然而昌龄之意象深矣。”*[明]陆时雍:《诗镜总论》卷一,四库全书本。王昌龄两首诗歌虽然没有明写“湘怨”,但深读之,实际句句体现出作者内心无限的悲凉之情。贬谪之人,平生失意,或为宦海沉浮,或为人生多艰,或感慨帝王心深,或评叹路途寥落,其实多少饱含着哀怨的情思。
如果说王昌龄作为唐代较早写“湘怨”的诗人,其怨尚不明显,那么稍晚的刘长卿则借潇湘之事表达出了内心的哀怨之情。公元760年春,值唐肃宗元年,诗人刘长卿因事入狱,被贬潘州南巴尉,也就是今广东电白。由北至南,诗人一路惆怅失意,面对江南无限春色,或姹紫嫣红或草长莺飞,诗人无心观赏风景。然而,当行至潇湘境内时,无限感怀的诗人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波澜,因感念湘妃而写下两首五言绝句。一首名《湘妃》:“帝子不可见,秋风来暮思。婵娟湘江月,千载空蛾眉。”*储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35页。另一首直指《斑竹》:“苍梧千载后,斑竹对湘沅。欲识湘妃怨,枝枝满泪痕。”*储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第137页。自屈氏之后,香草美人之意象已然不单只其本身。香草指代忠贞之气,美人指代帝王贤臣。所以,刘长卿因事被贬,借斑竹与湘妃事自比。刘长卿言帝子不可见,多少带有暗指帝王不明贬谪忠臣之怨。所以,想要真正明了湘妃之怨,且看那斑竹上的满身泪痕。刘长卿实际想要表达的恐怕是,自身与湘妃一样,一腔之怨只如湘妃一般,可以空洒斑竹。刘长卿此时之思,跟千年之前的湘妃与屈氏行步潇湘而泪洒江水有何不同?大致是千古湘怨在刘长卿之身重演而已。
继王昌龄与刘长卿之后,唐代诸多诗人凡莅临潇湘必抒以己怀。稍晚于刘长卿的戴叔伦,约在公元764年写过著名的诗作《过三闾庙》怀念屈氏:“沅湘流不尽,屈宋怨何深。日暮秋烟起,萧萧枫树林。”*中华书局编辑部:《全唐诗》卷六九零。诗人施肩吾写过《湘竹词》:“万古湘江竹,无穷奈怨何。年年长春笋,只是泪痕多。”*中华书局编辑部:《全唐诗》卷五九三。郑谷《望湘亭》云:“湘水似伊水,湘人非故人。登临独无语,风柳自摇春。”*中华书局编辑部:《全唐诗》卷六八一。杜牧《龙丘途中二首》(一作李商隐诗)道:“水色饶湘浦,滩声怯建溪。泪流回月上,可得更猿啼。”*中华书局编辑部:《全唐诗》卷七一七。李群玉《客愁二首》有:“客愁看柳色,日日逐春长。凭送湘流水,绵绵入帝乡。”*中华书局编辑部:《全唐诗》卷七四九。李商隐《夜意》吟:“帘垂幕半卷,枕冷被仍香。如何为相忆,魂梦过潇湘。”*中华书局编辑部:《全唐诗》卷七五三。翁宏《秋残》叹:“又是秋残也,无聊意若何。客程江外远,归思夜深多。岘首飞黄叶,湘湄走白波。仍闻汉都护,今岁合休戈。”*中华书局编辑部:《全唐诗》卷六五七。
看看这些跟潇湘有关的诗作,就会明显发现,诗人都是以一种情怀惆怅与哀思难泯的心绪来表达的。这些诗作最主要的意象归纳起来是:湘江、斑竹、深秋(残秋)、日暮、树林、柳色、明月、猿啼、思客、深夜。世人只知晚唐诗僧意象凄冷、诗作孤幽,殊不知在大唐隆盛繁华之起,便有诗人一旦行至潇湘而感念至深,诗作悲怨而情景萧然!显然,湘怨在唐代成为一种情结是不容置喙的。唐人写湘怨,没有了屈氏的明显的悲愤,没有汉代湘怨诗的质朴,而是典型的唐诗之象:情景交融、借景抒情。无论诗人在潇湘有多少感怀与失意,诗人都是将满腔的情感化作可见的景色,或残秋或明月,或江枫或竹泪。没有狂躁的呐喊与过激的咏叹,而是声色兼容的哀怨,是情景相融之后升华的淡然的情愁。所以,唐诗中的湘怨,像极了汉末号称五言佳作的《古诗十九首》。因此,用钟嵘《诗品》评《古诗》以比唐诗湘怨之体,则最为恰当。要而言之,唐诗中的“湘怨”乃是“文温以丽,意悲而远”。
二、宋词中的“湘怨”
宋至道三年(公元997年)置荆湖南路,治潭州(今长沙市),领七州:潭州,衡州,道州,永州,邵州,郴州,全州。此格局与唐实际并无太大差别。北宋诗人面对唐诗高峰,欲以理论诗,宋诗风貌大变。且有宋一代更具特点的文体是词,甚至可以说,在宋代,词之繁华与诗已然平分秋色。因此,以词中之潇湘而论诗中之潇湘,一则更具宋风,二则于文体而言,词中之“潇湘”与诗中之“潇湘”已大有区别。以宋词之角度研究宋代潇湘情结,据不完全统计,“潇湘”之象出现在宋词中多达164次,而以“湘”为间接意象的描写甚至多达596次!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唐诗中“潇湘”意象的出现。
(一)宋词“湘怨”的三种类型分析
陈寅恪先生言华夏文化之顶峰乃在赵宋之世。宋代精致的士大夫文化的确与雄强刚健的汉唐文化有着极大差别。宋人对内在精神的追求以及生命哲理的透彻思考,让整个宋代文化有着一种理性之光。同时,因为商品经济的极大发展,宋代市井文化得以极大突显,词的兴盛正是顺应此种文化氛围而得到长足发展。词中或抒长叹,或论小情,或悲离别,或怨负心,与诗之表现无异。在将近六百次的意象描写中,宋词中的潇湘情结大致分为三种类型:风景之叹、离别之悲与失意之怨。
1.风景之叹
宋代江南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诗人词人由北往南,眼见异于北地的山河风光,自然加以感叹。再加上词本身细腻融情的表现手法,因此诗人词人目触潇湘之景,自然加以感叹。而宋代边患危机持续惊扰,因此有良知的士大夫即使面对风景极佳的江南之景,也已然悲叹有余。在宋词里面,对潇湘之景的描写随处可见。比如晁端礼《满江红》描述精致优美的潇湘之景:
五两风轻,移舟向、斜阳岛外。最好是、潇湘烟景,自然心会。倒影芙蓉明镜底,更折花嗅蕊西风里。待问君、明日向何州,东南指。*唐圭璋:《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88页。
词人以一种清淡的笔调描绘出潇湘之地漫烟如雨的情状,如画中书意,直指人心。然而明显的是,这样的景色却是江湖漂泊中常见而不愿见的,因为故国他乡的无限思量在内心徘徊,以至于无法驻足一地而长久厮守,所以才自然而然有了羁旅可堪之叹。而象这样类似的景色之叹在宋词中随笔皆是。词人怨从何指?盖是此是风景俱佳,然而心境不佳,即使美景相伴,亦以怨而感慨人生世事。
2.离别之悲
潇湘地处华夏之中,南来北往,东去西向,皆通潇湘之地。唐人多有伤别之句描述潇湘分离,宋人亦然。宋人面对离别,少了唐人之坦然自信,不是“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之澄澈宁静,而是“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的凄清。离别之怨,在唐诗中并没有过多的以潇湘作为描述的背景。而在宋代,以潇湘作为分别地点而加以哀怨咏叹的不计其数。更重要的是,宋词中离别的“湘怨”多以一种述情于景的手法,把已经固定的“潇湘”意象以一种熟知的哀冷情调展示出来,没有过多的笔墨描述潇湘之悲,只要点出潇湘之别,全词中就有了一股浓浓的哀怨之情。比如,冯延巳的《归自谣·寒山碧》就典型地表现出了宋人风致的潇湘离别之悲:
寒山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远送潇湘客。
芦花千里霜月白,伤行色,来朝便是关山隔。*唐圭璋:《全宋词》,第376页。
山碧且寒,霜月更白,这样清冷的环境下,还有绵绵不断的哀怨之笛。几个简单的意象就将全词托到一种幽冷凄清的境界。词之结尾甚至还明言,扁舟将远,不久就是“轻舟已隔万重山”的千般不舍。全词没有直接去刻画潇湘之景,因为宋代的“潇湘”已经是凄冷哀婉的意象代名。
3.失意之怨
“潇湘”作为怨叹在宋代其实已经成为一种非常固定的情绪意象。因为宋代词人不再直接提出屈宋之名,而是直指“潇湘”,甚至将别处风景也比作成“潇湘”之景。这实际上比直接点出“潇湘”从而透露其中的哀怨之情要更深沉一些,因为词人一旦失意,人生处处都是潇湘之景,“晚景萧疏,堪动宋玉悲凉”,也就是失意人生处处都有着屈宋之怨。所以,宋人尹洙才在《水调歌头·和苏子美》中有着“莫问平生意,别有好思量”*唐圭璋:《全宋词》,第395页。这样直接而沉重的感慨。
然而,宋人感慨潇湘失意,与唐人相比要宽和一些。因为宋人具有明显的思理文化,因而面对屈宋之情,其心境已然不似唐人悲愤。所以,即便是莅临潇湘而有屈宋之怨,词人也只将自己作为一种高情的隐士而卓然独立于潇湘。这其中典型的比如宋代的圆禅师之《渔家傲》:
本是潇湘一钓客。自东自西自南北。只把孤舟为屋宅。无宽窄。幕天席地人难测。顷闻四海停戈革。金门懒去投书册。时向滩头歌月白。真高格。浮名浮利谁拘得。*唐圭璋:《全宋词》,第401页。
即使四海停止了干戈,他都对于投书册表示懒惰。人生世事变迁,哪里有在滩头闲适歌叹清风明月来得痛快透彻呢?所以,就算是潇湘之客,这种客居之愁没有了悲凉失意的浓郁,词人自谓自己乃是世间之真高格,人生名利谁又能奈何?其实,这样一种“放浪形骸”或许在西方人看来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悲哀。然而不妨将之看做中国传统文化中佛道精神的宋代展现。一个于世事不再关心的人,能了然于尘世纷繁之外的人,其失意之心,已经不局限于屈宋而是超越屈宋了。
(二)唐宋“湘怨”的内涵转变
1.地异情殊
“湘怨”情结由唐至宋有一个明显的转变就是由深入浅。而其首要原因则是因为京都地理位置的不同。京都地理位置的不同,也就是政治与文化中心的不同,这会直接影响到唐宋诗人的审美心理。或得意或失意,心理距离与阶层审美占有重要的因素。唐之都城在长安,生活在国都之内,与天子最近,权贵的环绕与经济的富足,自然让每一个文人内心都充满了自信与斗志。所以,孟郊《登科后》才会得意地写出诗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诗句。然而,唐之潇湘与长安之地相比,当然处于一个地位较低的地区。且不论潇湘之地的地理环境和生活水平与长安有着极大差距,单论关乎国家命脉的科举而言,唐之湖南地区并非十分显达。清代皮锡瑞直接指出唐代湖南地区科举进士人数之少:“湖南人物,罕见史传。三国时如蒋琬者,只一二人。 唐开科三百年,长沙刘蜕始举进士,时谓之破天荒。”*[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04页。显然,在经学大家皮锡瑞看来,湖南地区在唐代的科举情况是不容乐观的。而在长安地区,进士则多达几十人。这样的文化差异背后正是地位的差别。文人才士入居长安则自信满满,一旦贬谪迁出,无论东南西北,皆已与中心背离,绝大多数都怀抱着无限的惆怅之情。
但是到了宋代,随着国家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由北宋至南宋的历史变迁,南人的热情得到极大高涨。以杭州为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的南宋,文人雅士没有了流放西南或者北域的可能。东南一隅在文士心目中实际成为了安邦定国的家园,不再是与长安遥遥相望的孤地,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的“潇湘”在文士中没有了距离上的无限哀怨。因此,其情随着地理位置的变化而有了极大不同。
2.世易心迁
刘勰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世道变迁容易带来文化与认知的变迁。“湘怨”在唐与在宋也典型地反映出变迁后的不同。中唐之前的文化崇尚雄强劲健,中唐之后的文化偏于冷暗幽思,已经与宋代文化注重筋骨思理内在吻合。所以,中唐之前的士人对于“湘怨”之孤愤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感性认知。他们以“湘怨”为怨,既是对屈氏与二妃的怀念哀悼,也是对自己生在时代夹缝中感到无限悲凉。其情冷热与屈宋大体可谓一致。然而经过安史之乱,中唐文化表现出了反思与回归的倾向。韩柳领导的古文运动,不仅仅只是将古文变革作为一种文本内容的强调,而是将之纳入整个儒学复兴的系统之中。所以,中唐至宋的经学呈现出来的精于内在思理的特质直接赋予中晚唐尤其是宋人一种内敛、平淡、从容与反思的文化特征。又因为前文提到的潇湘在宋代已然不是一种相对偏远与孤僻的地理位置,所以,“潇湘”和“湘怨”在宋代基本上没有了唐人那种深沉的哀怨与不满,反而很多时候,宋代词人的词作中体现出了潇湘地位的崇高,成为了他处比拟的对象。比如宋代词人张先有词名《河满子·陪杭守泛湖夜归》:“溪女送花随处,沙鸥避乐分行。游舸已如图障里,小屏犹画潇湘。人面新生酒艳,日痕更欲春长。衣上交枝鬥色,钗头比翼相双。”*唐圭璋:《全宋词》,第365页。游船所到之景,竟令词人想到如同潇湘之景。“小屏犹画潇湘”,“潇湘”在这里实际成为了美丽的风景,是美景的代称。还有宋人尹洙的词:“不用移舟酌酒,自有青山渌水,掩映似潇湘。”*唐圭璋:《全宋词》,第298页。(《水调歌头·和苏子美》)苏轼和张先的词《水调歌头》也写到:“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念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唐圭璋:《全宋词》,第332页。可见,潇湘乃是一个让人回忆和思念的地方,不再是被排斥与使人失意放浪之所。
3.辞丽怨浅
正是因为文化与地理因缘的改变,所以在宋代文本中“潇湘”不再成为失意与孤寂的代名词。也正是因为地位与意象内涵的改变,所以宋词中的湘怨在文辞上显得比唐人和唐前之人要清丽得多。同时,因为文辞的清丽,自然内在消解了词作中所包含的作者的个人感情。词人因为心态的改变、文化的更容与时代的发展,对于“湘怨”没有了痛彻心扉的二妃与屈氏之怨,有的只是离人、思妇、游子等等人物的那种淡淡的哀愁与清浅的哀怨。如果把宋词中的哀怨之情与汉末《古诗十九首》做出对比,很明显会发现,二者虽然同是表达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离合,都是一种轻愁淡绪,但是宋词要多一些绮丽的文士色彩,而古诗多一些素朴的民间味道。比如宋代词人秦观的《画堂春·年十六作》:
东风吹柳日初长。雨馀芳草斜阳。杏花零乱燕泥香。睡损红妆。
宝篆烟消龙凤,画屏云锁潇湘。夜寒微透薄罗裳。无限思量。*唐圭璋:《全宋词》,第418页。
全词写的是一个日夜颠倒生活规律错乱的闺中思妇。淡淡的哀怨中体现出清绮的忧愁。这样一个思妇,看着香炉中的烟消,潇湘中的云雾,跟《古诗十九首》中所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以及“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其相似?然而二者的哀怨与汉之《长门》、唐之《思妇》相比,实在是文辞雅艳而哀怨清淡得多。这正是唐宋“湘怨”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结 语
清人叶燮有“中唐之中实乃百代之中”的说法。中唐作为中国诗歌史的重要分期,将诗史概括为前汉唐而后宋明大致两个部分。实际上,中唐亦是中国经学中汉唐经学与宋明经学的大致分期,是中国文化汉唐重“境”与宋明重“意”的大致分期,是中国思维中汉唐重“虚”而宋明重“实”的大致分期。经学与诗学都是世情文化的重要表征。所以,与唐宋世情同时而变的则是一系列意象内涵的演变,这当中自然包括非常重要的“湘怨”情结。所以“湘怨”情结自唐至宋的转变,不仅是中国诗歌史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文化史发展的一个缩影。“世情”与“文变”血肉相连,“文变”与“世情”息息相关,窥一斑而知全豹,文情之理不可不明,“湘怨”之变不可不彰。
(责任编辑:王学振)
The“Xiangjiang River-related Complaint” Complex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etry——A Case Study of Poetry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PAN Lian-yu
(CollegeofLiberalArts,HunanNormalUniversity,Changsha410006,China)
The “Xiangjiang River-related complaint” complex is a special cultural phenomenon worthy of attention in the Chinese poetic history. Since Ehuang and Nuying portrayed respectively by Qu Yuan and Song Yu, the Xiangjiang River-related compliant complex has seen a clear clue of development in the history of poetry, and has undergone some obvious transform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poetry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f the feeling of infinite grief and indignation unique to poetry in pre-Tang dynasties is explicit in poetry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Xiangjiang River-related complaint complex in poetry of the Song Dynasty has witnessed a gradual change to some elegant and beautiful admiration for natural scenery, sorrows for parting, and sentiment of frustration. In short, the transformation in the connotation and features of the Xiangjiang River-related complaint complex is virtually a dimension in the change of the entire Chinese poetic aesthetics.
the Xiangjiang River-related complaint;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Ci poems of the Song Dynasty
2016-07-10
潘链钰(1988-),男,湖北鄂州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
I206.2
A
1674-5310(2016)-09-006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