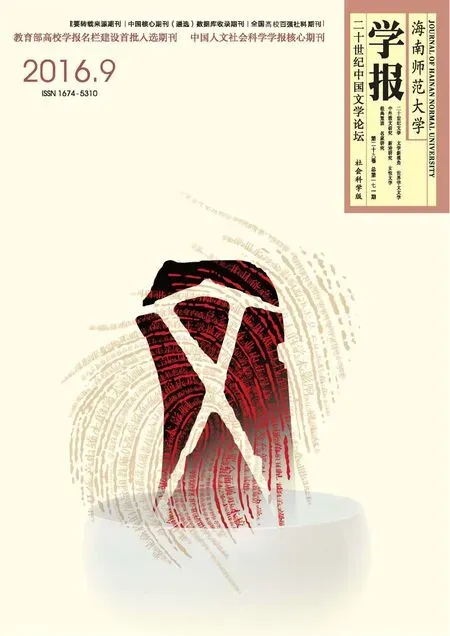在揭真相与泯仇恨之间
——谈张悦然《茧》
唐诗人
(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275)
在揭真相与泯仇恨之间
——谈张悦然《茧》
唐诗人
(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275)
张悦然的《茧》,是书写“文革”历史阴影继续作用于后代人的创伤问题。名为“茧”,故事也就是在剥“茧”。小说一方面是探求历史真相的剥茧,同时也剥人物因为知晓了真相而生成的仇怨之茧。这种“对剥”,既是探究后代人的“文革”历史记忆问题,同时也思考后代人该以何种心态面对历史伤痕。这是一种纠缠在揭示真相与消泯仇恨之间的写作。
《茧》;张悦然;“文革”;历史记忆;伦理责任
一、共同的心理经验
阅读张悦然的《茧》,是一个不断检视自己心理经验的过程。小说中主要人物程恭,尤其令人不安。程恭的爷爷在“文革”中被批斗,被迫害为植物人,这引起了我对于我爷爷的情感记忆。我爷爷亦是“文革”年代的教师,被学生批斗,迫害至瘫痪。在我的记忆里,他一直躺着。我不到5岁时,他就去世了。我已记不起他更多的表情,更想象不了他的声音。我亦没能从我爷爷那里得知任何历史细节,只有他躺着的病躯,以及我父亲零零散散的受害史讲述,这些塑造了我对那段历史的愤慨认知。
对“文革”这种祖辈、父辈们所经历的历史,以受害者的后代身份来看,必然会有愤怒、怨恨的阶段,但这种情感态度有无问题?很早开始,我通过阅读各种描写“文革”的作品,想寻找到最恰当的路径,来理解那段历史、体谅那些罪人。但是,众多小说提供的故事,要么是在揭示罪恶中发泄着讲述者内心的愤怒,要么是走向了超脱,不问罪,于是不纠结。我不满于这两类作品。增强我们的仇恨感,这不可取,宽恕才是最好的归宿;可是,轻易地放弃问罪问题,又是纵容罪恶、逃避责任。在宽恕与问罪之间,作为后代的我们,该如何选择?它们之间有无兼顾的可能?很巧,80后作家张悦然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茧》表明作者亦有我这样的精神难点。
实言,我个人一直想书写自己的家族故事,以“发泄”或“缓解”自小就压抑在内心里的愤懑情感,但我困惑于寻找不到理想的处理方式,也未能抽出时间去挖掘更多的历史细节,一直耽搁着。为此,阅读《茧》,我既欣喜又担忧,欣喜于终于有80后青年作家开始严肃、集中地书写“文革”,开始正视祖辈们遗留在我们内心的阴影。但同时,我也担忧于青年作家的历史反思也会落入俗套,在简单的控诉或超越中草草结束。
张悦然的《茧》,面对的正是我们这一代该如何面对罪恶历史和家族阴影这一“怎么办”的复杂问题。《茧》所建构的人物图谱和故事性质,是为了揭示历史阴影并未因时间过去而烟消云散,它们其实还继续作用于后辈的生活与精神,也是为了探讨后辈们该以何种心态面对不堪历史遗留下来的伤痕。
在《茧》里,我特别留意到一些探问句:“我们怎么可以这么快乐和安逸?”“你怎么就能活得那么舒坦?”“可是怎么能如此地轻易呢?”类似问句还有很多,它们经常跳出来,刺激着埋藏于我内心多年的不满与困惑。在我们这一代,言说“文革”其实没多少空间。除开一种公开表达上的忌讳,更严重的还是同龄人之间的知识和心理隔膜。非文史专业的同龄人,普遍不知道“文革”意味着什么。即使知晓历史者,也都持着过去了就不要再提、不必纠缠的态度。还有大量类似于小说中唐晖形象的知识者,持着看似公允理性的观念,实是纵容着人们继续参与到漠视和遮蔽历史真相的行动中。纠缠于过去有何用?即使探求了真相、当年参与迫害运动的作恶者忏悔了,又能如何?这些实用主义的思维,控制着这个时代的人心。面对这种语境,感慨或审问人们怎么能够这么快乐和安逸、怎么就如此轻易地忘却了过去,都注定了是自作多情。
二、历史远去,伤痕依旧
今年是“文革”爆发五十周年、“文革”结束四十周年。1976年被普遍视作新时期的开端年份。*旷新年:《1976:“伤痕文学”的发生》,《文艺争鸣》2016年第3期。1976年之后,书写“文革”历史罪恶的作家逐渐出现阶段化、代际化现象。开始时的伤痕、反思文学,以及后来一些知青题材作品,普遍属于揭示和控诉,反思亦是有限的反思。如刘再复当年所言:“无论在政治性反思还是文化反思中,我们的作家主要的身份还是受害者、受屈者和审判者。因此,主要态度还是谴责和揭露。”*刘再复:《论新时期文学的主潮》,《论中国文学》,北京:作家出版社,1988年,第270页。另外,这些作品,基本都有着光明和谐的收尾。比如张贤亮的作品,典型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写作。这些作品所传递的观念相对简单,认为历史灾难已经过去,“恶”就已被克服,过去的“恶”就能转化为当前发展的动力。这种思维,在今天看来,已显幼稚。“恶”并没能随着“四人帮”等恶势力的消失而消失,尤其是“文革”历史之恶遗留在人内心深处的伤痕、阴影,它们其实一直影响着后世人们的生活和精神。
“文革”影响深远,那些经历过、对“文革”历史有着切身感受的“50后”“60后”作家们,不管是写作本身,还是生活方式上,都有着“文革”的痕迹。莫言、阎连科等人狂欢式的文学语言,以及他们小说中的人物命运,都有着“文革”的浓烈影响。小说中,阎连科“受活庄”的民众,“文革”结束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即开始了宁静的生活;贾平凹“古炉镇”的日常生活,“文革”造成的破坏是致命的,死去的生命不可挽回,创伤永远驻在幸存者内心。在余华、苏童、毕飞宇等人的作品中,“文革”历史遗留下来的,尽是被破坏的大地和被损害的人心。在残酷的历史环境里成长出来的一代人,由小说作品来看,人心普遍变得坚硬,潜意识都被黑暗笼罩。
“70后”“80后”作家作品中,“文革”开始转变成父辈经验的呈现。他们书写的“文革”,普遍会从家庭、从父辈出发。李浩一直在书写父辈的身体和心灵遭遇。《镜子里的父亲》用魔幻的方式集中展现“文革”给父辈以及整个家庭带来的阴影。徐则臣的《耶路撒冷》,父辈之间的恩怨,家乡的那些黑暗历史,给小说中的人物带去了不可抹除的心理创伤。后人的生存和价值取向,直接跟父辈的历史遭遇相关。乔叶《认罪书》中的个人,一直萦绕着父辈“文革”时期的罪恶,而后辈的行径,也有意无意地“重蹈覆辙”。
“80后”书写“文革”历史的作品不多。少数的篇章,比如陈崇正《碧河往事》、王威廉《绊脚石》等,也表现“文革”历史灾难对当代人造成的伤痕。历史其实并未真正远去,它对当下的影响依然深重。老一辈经历者生活在内心的罪感和恐惧之中,而年轻一代人又该如何看待历史罪恶?如何兼顾记住历史与消弭仇恨?这些都是历史遗留物,永远是我们生活中的“绊脚石”。
很多作家作品,都表达了“文革”历史并未远去的现象和观念。《认罪书》还书写出新时代的“文革”性质的罪恶,它们变了面貌还在继续上演。这些表明,伤痕、反思文学所相信的光明前途并没能实现。而通过张悦然的《茧》,我们又进一步理解到,“文革”造成的伤害其实还在继续,祖辈、父辈们的罪与恨,还潜伏在作为孙辈的80后青年们的内心。
《茧》里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是80后,都代表着一种典型的身份。程恭的爷爷是受害者,李佳栖、沛萱的爷爷是“文革”批斗运动中的施害者。程恭作为历史受害者的孙子,是受难家庭的孩子,他的成长历程就是逐渐了解历史真相、延续家族仇恨的过程。被仇恨填充,内心被扭曲,于是他对他所生活的世界充满愤怒,对自己身边的人不再善意。他导致了沛萱的脸伤,强暴、欺辱陈莎莎,欺骗好友大斌……程恭的形象表明,延续家族仇恨,只会造成更多的罪恶。而作为施害者孙辈的李佳栖和沛萱,虽是堂姐妹,却意味着不同的历史形象。祖父李冀生的罪,使得李佳栖的父亲李牧原一直生活在负罪感中。罪感心理使得李牧原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对家人表现出自私的一面,厌恶自己父亲,也没能给李佳栖以父爱。李牧原跟从内心的罪感,同李佳栖的母亲离婚后,与当年参与迫害后负罪自杀的汪良成的女儿汪露寒结婚以赎罪。这种结合导致了更为痛苦的生活,负罪与失意,酗酒、车祸身亡,这些都给李佳栖造成极深的心理阴影。而沛萱,一直不愿意相信祖父曾经的罪恶,并希望用纪录片为李冀生正名。但她其实也是历史的受害者,脸部的伤残是程恭导致的,她的个人生活也完全被祖父的形象所束缚,是一个被虚假形象迷惑而失去了自我的形象。
历史远去,伤痕依旧。伤痕通过家庭、家族情感,在人的心理层面一代一代地传递,成为每一代人的心理阴影。伤痕也塑造了后代人的性格,以至于影响到他们的行为方式。直面这些伤痕,就要追溯历史,而追溯又涉及到揭示真相与消泯仇恨的问题。
三、“80后”与“文革”写作
当“80后”作家开始直面自己的这些问题来自哪里时,必然会遭遇家庭出身,会涉及父辈经验的书写。由此,“文革”亦成为一道不可轻易跨越的坎。而我们这一代,对“文革”的认知,必然完全来自历史材料和家族记忆。没有历史现场经验的历史书写,同见证者们的写作相比,必定是另一种面貌。
对于青年作家的“文革”书写,陈思和曾指出:“随着作家的年龄层次的下降,他们面对‘文革’的个人经验越来越稀薄,记忆也成了越来越空洞的形式。”*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与“文革”记忆》,《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08年第2期。个人经验的稀薄,记忆的空洞化,这对于直接书写“文革”历史的小说而言,是致命的缺陷。而如何克服这种天然的缺陷?我以为,只通过历史资料考证是无法弥补的,青年作家需要寻找到历史与当下的切合点。进入历史的同时,有作家对当下问题的切身感受,作品才有温度,故事才更具感染力。这在乔叶《认罪书》里有过尝试。《认罪书》中的父辈,当年为了解脱,为了重新生活,看着因受迫害而发疯了的妻子奔向河里被淹死。儿子辈的梁知,为了官场前途,无耻地牺牲了和自己相爱的梅梅。更晚一辈的“我”自己,被梁知狠心抛弃后,阴谋报复,欺骗无辜的梁新……这里,每一代人的罪恶,都很近似。历史的罪恶并没有结束,只是换了表现方式继续着……《认罪书》将以前的历史罪恶跟当下的罪恶链接起来,兼顾着过去与现在,历史的“意义”在小说中也得到直接体现。
我们再看看其他“80后”作家的“文革”书写。陈再见的《迎春》讲述的是“文革”故事,但很明显,陈再见并不是特意要讲述“文革”历史的荒诞或者罪恶,而是在书写父辈时不得已的需要。“文革”在这里不是叙事的理由,银春,或者说小说中“我”的父母辈的成长经历才是叙事的理由和目的。另外,小说反映的“文革”,迫害形式等也不存在什么特殊性。甚至于红卫兵所带来的灾难,在作者笔下,和“文革”时陈铁柱兄嫂们造成的灾难都很类似。“文革”对于湖村,它只是灾难的一种,是小说中人物、家庭遭际的一类事故而已。叶临之的《我们的牛荒岁月》,也是讲述“文革”故事,但小说要讲述的,也并非指向“文革”历史本身,而是讲述权力欲望如何把人异化。显然,这种叙事指向,可以和“文革”有关,也可以同“文革”无关,“文革”只是个故事背景,是作家呈现思想的历史框架。另外,王威廉的《获救者》,他所虚构的城市地下王国,是现代世界的黑暗面。这黑暗面的地下故事与“文革”时期的历史面貌极为相似,尤其在统治逻辑和人心狡诈方面,能看出作者有意的隐喻。这个故事源自“文革”,但也远离“文革”,是在更广义的层面对极权政治和权欲人心进行反思和批判。
这些“80后”作家作品,都没有直面“文革”,“文革”作为小说的背景,与他们所要表达的东西,属于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而在张悦然《茧》里,则是直面我们这一代人内心的“文革”痕迹。小说名为“茧”,而故事也就是在剥“茧”。但张悦然的独到之处在于,她的故事并非简单地探求真相式的剥茧,而是在探寻真相的同时也剥开我们因为知晓了真相而生成的仇怨之茧。小说中程恭有一段内心独白:
很多年以后,每当回忆起那个冬天,眼前立即会出现我们并排走在大雾里的画面。沉厚的、灰丧的雾,没有尽头。或许那就是最真实的童年写照。我们走在秘密织成的大雾里,驱着步伐茫然前行,完全看不清前面的路,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多年以后我们长大了,好像终于走出了那场大雾,看清了眼前的世界。其实没有。我们不过是把雾穿在了身上,结成了一个个茧。*张悦然:《茧》,《收获》2016年第2期。
一方面,是剥萦绕在他们家族伤痕中的历史之“茧”;另一方面,也剥开他们内心的爱恨之茧。这种兼顾,使故事从正反两个方向实现了“对剥”,但出发点都是“80后”这一代人,或者说作家自身所意味的那一代人。相向而行,于是小说所观照的问题更为丰富。
剥开历史真相,这种剥,在很多人看来,其实是在揭伤疤,揭开自己家族史上的是与非,也揭开埋藏在他人心中的罪与痛。程恭极力希望获取的灵魂对讲机,是要掌握那枚刺入他爷爷头脑里的钉子因何而来、由谁而钉。灵魂对讲机是不可能存在的,程恭可以从其他地方获得作为历史事实的罪恶真相,但他并不能同作为植物人的爷爷进行灵魂对话。获知历史真相,生成新的仇与罪,而没能获得父辈们的灵魂内容,程恭也就无法从一开始就领悟到处理历史仇恨的正确方式。因此,对于程恭,他剥家族苦难的茧,得到历史真相的同时,他的内心又蒙上了一层新的仇恨之茧。他打开历史的方式是对的,但合上历史的方式却出现了错误。要理解和更正这种错误,就成为了另一种剥茧。
同样,小说中李佳栖也是剥茧时生成新的茧。剥开父亲的真实面目,了解到父亲赎罪生活的痛苦,亦了解到自己爷爷的罪孽,但同时也生成了对自己爷爷的愤恨感。但李佳栖剥历史真相之茧的同时,更是在剥自己内心之茧。她的恋父情结,以及自小于生活中表现得极端自私等性格问题,与她缺失父爱有关。她解开父亲的谜之后,也解开了这些情结。追随父亲的旅程结束时,她同唐晖的爱情也结束了。和唐晖分手时,李佳栖内心说:“唐晖是唯一一个愿意教我去爱的人,但他放弃了,把一直抓着我的那只手撤走了。我感觉到身体在失去重量。在下坠,不断下坠,坠入深渊。我跪坐在地板上,把手放在心口。也许那是我一生之中最接近懂得爱是什么的时刻。”*张悦然:《茧》,《收获》2016年第2期。她同父亲当年的朋友约会、上床等等不顾唐晖感受的行动,是自私任性的,必然伤害唐晖。她所谓接近懂得爱是什么,也即明白自己过往的行为之自私,明白了所谓爱也并不是没有条件的。她懂得了历史,也懂得了爱。她能够回去和爷爷见面作为终点,即是剥开各种茧的表现。
可见,张悦然同众多青年作家近似,并不直接讲述“文革”历史,而是从后代人内心阴影这类角度进入其中。但《茧》也可算做正面直视“文革”的写作。故事虽然是当前人的故事,却处处指向“文革”历史之罪。所有的茧,都因“文革”年代的残酷和荒诞而来,所有剥茧的疼痛,都因为那段历史罪恶得不可理喻。
四、真相之上的和解
小说最后,小时候即开始相互恋慕的李佳栖和程恭,用多年的时间各自剥茧结束之后,重新在一起,实现了受害者与施害者孙辈的和解。或许,我们依然会纳闷,这种和解真的能够实现吗?这里面还有一个最大的思想问题没有解决,这也是萦绕在小说内部的精神困局,即知晓真相与消弭恩仇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处理。颇有点遗憾的是,小说《茧》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其实着力不够。
李佳栖和程恭知晓了真相,但这种知晓也仅仅是停留于自己内心的知晓,真相并没有走向更广阔的公众视野,就连沛萱也依旧不相信真相、沉浸于对祖父的崇拜。李佳栖只追问,却放弃讲述,这会加深误解。唐晖这类人物形象依然会坚持自己不问历史罪过的“理性”观念。而陈莎莎呢?这一不明真相却不断受害的人物又意味着什么?她好像仅仅是配合程恭形象而来的“木偶”。这里并不是说张悦然的书写,必须让李佳栖、程恭主动向世人宣告罪恶真相,而是说小说或许可以有更全面复杂的考虑。在我看来,理想的、更宽阔的结局,可以是既考虑李佳栖和程恭两者之间和解结局,也思及一种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公众效应。当然,这种公众效应可直接来自现实生活中的读者心理,我们从李佳栖和程恭的故事就能知晓消泯仇恨的重要。
或许,我所不满意的地方只是,真相并未真正揭示,除开程恭和李佳栖,其余人物,不知者依然不知,不信者依旧不信,不愿正视历史者照样不愿意正视。这就是当前社会对待“文革”等罪恶历史的最大问题。年轻一代,对于“文革”,要么是纯粹不知,要么是完全不感兴趣,要么是知而不谈、不究。
对于知晓真相与消弭仇恨,在理论上其实有着相关观念。以色列学者玛格利特谈论宽恕与记忆时说:“如果只是依靠简单的忘记,就不是真实意义上的宽恕。宽恕是一种有意识的决定行为,因此可以改变人的态度,真正克服愤怒和仇恨。忘记或许是克服愤怒和仇恨的最有效的办法,但因为它是一种遗漏而不是一种决定,因此它不是宽恕行为。不过,像在回忆的情形下,作为决定的宽恕是一种间接的方法,它能够同时产生忘记的效果,从而完成宽恕的过程。宽恕的决定可以使人停止对历史的斤斤计较,停止向其他人倾诉,其结果是忘掉或忘却一度对你来说很重要的往事。这样一种类型的忘却关乎大道德和伦理等方方面面。”*〔以〕阿维夏伊·玛格利特:《记忆的伦理》,贺海仁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83页。(按:记忆囚禁的隐喻,是源自弗洛伊德心理学,被压抑的记忆,释放是宣泄,有治疗效果,但它也可以是破坏、是更多的伤害。)玛格利特这里谈宽恕与忘记的关系,忘记并非宽恕,探寻和记住罪恶事实之后的宽恕才是真正的宽恕,否则就是无视罪恶。善良不是漠视罪恶。在知晓和牢记罪恶的层面上,宽恕意味着我们对罪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德里达说:“唤起记忆即唤起责任。”*〔法〕雅克·德里达:《多义的记忆——为保罗·德曼而作》,蒋梓骅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页。反之,放弃对历史真相的探寻、抹除历史记忆就是放弃、漠视责任。玛格利特还强调说:“抹去罪恶等同于删除,遮盖罪恶类似于划掉。与抹去罪恶相比,遮盖的隐喻是概念上的、精神上的,在道德上更为可取,划掉比抹去更具有意义。总之,我主张宽恕的基础是看淡罪而不是忘记罪。”*〔以〕 阿维夏伊·玛格利特:《记忆的伦理》,第186-187页。看淡是一种选择,这种选择是有所取舍的伦理决定,而纯粹的不谈、不究或者删除则是不负责任。
为此,回过头来审视:和解真的能够实现吗?李佳栖和程恭能够实现完美的结合吗?会不会又是新一代汪露寒与李牧原式的结合?他们若有孩子,会不会延续他们各自的内心阴影?这些问题不可预测。但这正是小说《茧》要我们这代人正视的问题。不管是历史受害者的后代,还是历史作恶者、负罪者的后人,知晓历史真相是一种责任,但知晓并非延续仇恨和加深伤痕,而是在共同直面和牢记历史真相的基础上,用心于防范新的罪恶,避免我们的家庭和社会重蹈历史覆辙。
(责任编辑:王学振)
Zhang Yueran’sTheCocoonInterpreted
TANG Shi-ren
(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SunYat-SenUniversity,Guangzhou510 ,China)
Zhang Yueran’sTheCocoonis about the continuous traumatic impact of the historical shadow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future generations. As it is entitled “the cocoon”, the story is like peeling “a cocoon”, for the novel aims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truth on one hand while simultaneously trying to rid characters of their hatred caused by their awareness of the truth on the other hand. Such a technique is meant not only for probing into future generations’ mem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ut also for considering how future generations should face up to the historical trauma. In short, the novel is a piece of writing entangled between truth revelation and hatred removal.
TheCocoon; Zhang Yuera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istorical memory; ethical responsibility
2016-06-22
唐诗人(1989-),男,江西兴国人,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批评理论研究。
I207.4
A
1674-5310(2016)-09-005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