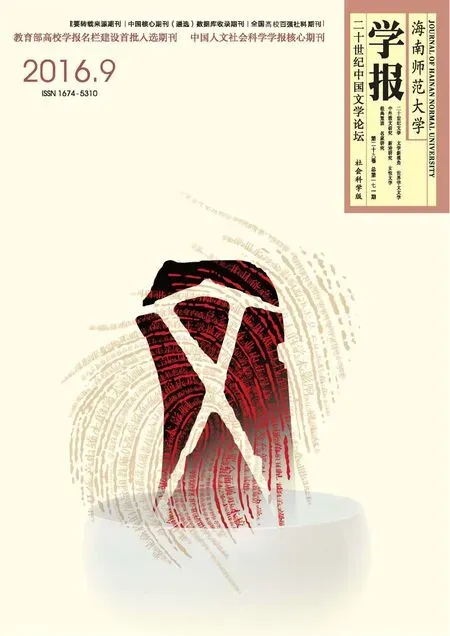往何处去
——方方作品中女性的困境及其出路
石俏杨,付祥喜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往何处去
——方方作品中女性的困境及其出路
石俏杨,付祥喜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方方的作品不同于当代女性书写流行的纯粹私人化写作,不拘泥于个人情感的表达,而是把现代女性遭遇的困境,放在人的价值中进行思考,在压迫与反叛、理想与现实的思辨中前行,由此开辟了当代女性书写的独特路径。
方方;女性视角;女性出路
自“五四”运动开始,中国女性文学写作走上了自觉的道路。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的“个性解放”和“民族自由”,使一部分女性打破了传统的束缚,一大批女性作家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从石评梅、凌叔华、庐隐到丁玲、萧红、张爱玲,从陷入爱情与知识苦闷中的露沙,到处于灵肉冲突中叛逆而困惑的莎菲,从夹杂在新旧交替间无所适从的大小姐,到接受新知识却仅是以此作为筹码的川嫦,20世纪中期前的女性书写更关注于新旧社会交替时女性的生存困境和女性的个性与思想解放。七八十年代,女性写作转向,出现了新的高潮。社会环境、文化思想的发展变化,促进了新时期女性意识的觉醒,一大批女作家如张洁、王安忆、铁凝、迟子建等“浮出历史地表”,以各自的话语方式,挖掘女性经验,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女性在社会发展中的处境和女性的命运。被归入“新写实”作家的方方,正在此时以其独特的思考角度和哲理探索崭露头角。
与许多女性作家不同,方方的写作视角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生存体验和爱情婚姻等传统女性问题,而将着眼点放在更广阔的社会人生和世俗生活中,通过对不同阶层女性个体的描写,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现了女性的生存状态、爱情挣扎、家庭困境和命运无常。正如她在《说“女性文学”之可疑》中提到的:“老式的女人以往面对的生活,排除掉爱情婚姻家庭的内容,就没剩下什么了。但是现在时代已经完全变了样,妇女面对的问题同样也变样得天翻地覆。她们和男人一样,得面对整个世界,而不只是面对一个家庭。”①方方:《说“女性文学”之可疑》,《南开学报》2006年第4期。方方的作品描写了大量不同阶层、不同社会地位的女性,通过刻画芸芸众生在平凡世俗中的凡庸忙碌,描绘现代女性深陷在各自处境中的挣扎徘徊,突出了女性困窘、挣扎的生存状态,并向人性的纵深处挖掘,产生了一系列关于人生和哲理的思考。本文试图分析方方女性题材小说中的女性生存困境,并解读其深层的悲剧情怀和对于宿命人生的哲理探索。
一、对理想爱情的坚守与对世俗爱情的反叛
方方说:“女性文学始终充满着反叛意识,对男权意识的反叛……我觉得我的小说的反叛是一种精神上的反叛。”*叶立文、方方:《为自己的内心写作》,于可训编:《小说家档案》,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35页。与传统女性书写的关注点不同,方方的作品弱化了女性在物质世界中世俗化的追求,而着重探讨女性精神上的困境和诉求,尤其是对理想爱情的坚守与对世俗爱情的反叛。其突出展现的是新时期女性坚守心中的爱情理想,却被无情现实摧毁,陷入无法摆脱的悲剧藩篱中。
情爱题材是中西方共同的、经久不衰的文学母题,爱情是人类永恒的精神追求,也造就了无数的千古佳话。但在方方小说中,美好的爱情往往是悲剧性的结局,理想的追寻常被世俗的规则桎梏。正如萧红所写的“理想的白马骑不得,梦中的爱人爱不得/……/我的胸中积满了沙石,因此我所想望着的,是旷野、高天和飞鸟”*萧红:《梦中的爱人爱不得——黄金时代》,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45-147页。,方方作品中的女性终其一生追求着高贵而致命的爱情,却在想望着“旷野、高天和飞鸟”的梦中一次次无可奈何地失望和退守。
方方小说中的女性大多坚守着心中的理想爱情。《树树皆秋色》的华蓉是美丽的单身女教授,被一次意外的电话搅乱了平静的心湖,从此想象着电话那头对方的音容笑貌,编织着一个个美丽的爱情的梦;《船的沉没》中活泼开朗、敢爱敢恨的徐楚,坚定勇敢地爱着大她八岁的吴早晨,从不惧外人眼光,甚至对自己的爱人许下终身;《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的瑶琴更是追求理想化爱情的极致,年轻时她爱上了同厂的杨景国,但一场车祸带走了爱人,十几年间瑶琴一直怀念和深爱着他,忽视了身边的陈福民,当陈福民伤重时,她却爱上了他,扬言要守护他十年,她活在回忆之中,时时刻刻怀念着爱人过去的温存,但她的爱却只能存在于理想之中。
但是,诚如方方所言,“真正的爱情是很难得到的,而且,我现在很怀疑什么是真正的爱情”*李骞、曾军:《世俗化时代的人文操守——方方访谈录》,《长江文艺》1998年第1期。。从华蓉、徐楚到瑶琴,尽管她们怀抱着美丽的爱情理想,追求着完满高贵的爱情,却无一不被残酷的现实无情摧毁。有意思的是,方方往往通过现实生活中男性的懦弱和女性的自强自立这样一个对比,来摧毁女性心目中的理想爱情。
方方小说中的女性,多为有一定经济独立能力和社会地位的知识女性。相比之下,男性或自以为是,或弱小自卑,将女性束缚在自己身边,在碰到现实的阻挠如父母的压力、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选择退缩,留下女性独自面对。《船的沉没》中的徐楚美丽勇敢,在年龄差距和舆论压力等重重现实阻碍面前仍然坚守,吴早晨却自卑而自尊,不愿她读大学,担心旁人夺走她,最终却因母亲不喜欢而离开了她;《桃花灿烂》的星子是大学生,矜持含蓄地爱着陆粞,而陆粞深觉配不上星子,和水香发生关系,又和上司的妹妹结婚,给星子带来了沉重的打击;《随意表白》的靳雨吟爱上有妇之夫肖石白,愿意等待肖石白离婚,肖石白却因为要保住自己的前途而最终选择了放弃。这些作品中的女性是敏感而坚强的,她们对纯净的爱情永恒执着,对精神理想不懈追求。而男性总是退缩的、固执的,一方面视女性为己有,一方面又不愿承担责任。于是,女性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屡屡碰壁,理想的爱情完满高贵,世俗的爱情却千疮百孔,上天入地也无处寻找心中的火光,惟独看清了对方的自卑自私,看清了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如靳雨吟所言,“我最清楚不过的是你不可以对他们提出太苛刻的要求。你最好只是不在影响他们正常生活的前提下与他们和平共处,在无人知晓的状态下偷欢片刻……你像一辆出租车,挥之可去,招之可来”*方方:《随意表白》,《当代》1992年第6期。。男性的懦弱和女性自强自立的对比,突出了女性的现实困境,又勾勒了在困境中女性对理想爱情的执着坚守,并进一步走向对世俗爱情的反叛。
在《船的沉没》中,方方写道:“我承认我很难理解中国有文化的男人。他们在爱情上的自尊和虚荣强烈到一种变态无知的地步。他们许多人公开提出女朋友第一条件或为青春美貌者或为贤妻良母型。他们从不在意智慧的女性……我们的许多才情十足的女人在阳光和灯光下孤零零地走着自己的人生。他们才能的光照使浅薄的男人自卑和委琐。她们影单形只。但她们追求智慧依然锲而不舍。她们把精神生活看得高于肉欲,而男人们正好相反。”*方方:《船的沉没》,杨柳编:《方方·中篇小说系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162页。即使所爱之人是如此孱弱,即使所处之境是如此艰难,她们也从未放弃对爱情理想的坚守,哪怕飞蛾扑火般陷入爱情漩涡,永不能得到美满。吴早晨狭隘多疑,徐楚却一次次向他表白心意,抵抗着来自母亲的压力;老五漫不经心,仅仅将华蓉当成玩伴,华蓉却认真地对待着这种暧昧,担心着他的安危。困惑也好,痛苦也罢,她们所做的不是自怨自艾,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毅然决然地选择追寻爱情,选择在泥沙俱下的大潮中坚守一方净土。这种选择常常是痛苦的,甚或是悲剧性的。追求理想而不可得,亦不愿投身于平庸世俗,便惟能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中挣扎失所,在无数的情爱失望中走向悲观绝望。女强男弱的不对等模式,造成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导致爱情走向必然性的悲剧结局——要么如徐楚、华蓉选择不婚,要么如靳雨吟、黄苏子堕落于情欲快感之中,更极端者如叶桑选择死亡。这种选择是她们渴望爱情而不得的无可奈何的退守,是她们寻求共鸣而无望的痛彻心扉的悲鸣,是她们挣扎失败而决绝的自我毁灭。
这是一种对于世俗爱情的反叛,更是一种超然高蹈的勇气。坚守着理想爱情,不愿与现实同流合污,不甘于世俗中泯灭初心,纵使只能走向毁灭,也绝不轻易妥协。方方作品中所展现的,不是女性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中生存和物质性的追求,不是理想被世俗磨平的悲哀,而是精神上的执着反叛,是哪怕玉石俱焚也要坚守的高贵信仰。在这些作品中,方方表现出了强烈而愤懑的女性意识,体现了鲜明的女性立场。对男性的刻意弱化是她蔑视男权统治、颠覆传统话语的书写策略,对女性的不吝褒扬是她内在价值的自我认同。作品中所构筑的高尚理想和精神追求,虽时有不可为,但毕竟提供了别一种可能,以超然高蹈的精神为物欲横流的社会开辟了清流,体现了一个作家的清醒意识和别样勇气。
二、男权压迫下女性抗争的悲歌
新时期以来的女性写作多关注于私人化写作和消解男权社会的话语规则,表现强烈的女性意识,鲜明地坚持女性立场,自觉地书写女性个人经验。而方方在关注女性精神困境的同时,却将笔墨转移到农村的边缘女性身上,试图为这些在男权社会和封建观念中被长期压迫的失语女性发声,谱写了在男权话语统治下女性不屈抗争的悲歌。
1980年代,经济开放和商业繁荣卷起了新一轮发展浪潮,当城市急剧变化时,农村仍然停滞不前。经济发展拉大了城乡差距,暴露了农村思想的滞后,封建思想和男权思想仍深深烙印在农村文化中。闭塞的环境和物质贫乏使她们难以接受高等教育,难以独立谋求社会出路,大多数农村女性成年后的选择就是嫁人和生儿育女。而长期以来的男权中心观念,又使女性丧失了与男性平等的自我,以夫为纲,个性自由被家庭、婚姻、孩子等等传统条件束缚,纵使尝试独立,亦遭受着无数非议与挫败,只能逐步被推向边缘地带。
小说《奔跑的火光》讲述的正是这样一个农村女性的悲剧。英芝是一个美丽活泼、有主见敢拼敢闯的乡下女孩。高中毕业后,她回到乡下唱歌赚钱。因未婚先孕,她被迫嫁给了隔村青年贵清,并因此遭到公婆的歧视,婚后公婆甚至常常毒打她。她没有就此屈服,在一次次的阻挠中,坚持自己挣钱造房子却数次失败,最终在走投无路之下杀死了丈夫。方方笔下的英芝是鲜活而饱满的。她受过教育,却缺乏深刻追求;她有独立想法,却仍因循守旧依附于丈夫;她屡遭毒打,几经侮辱,却从未放弃抗争。她渴望着自立自强,没有人打她骂她,没有人翻白眼,用自己的力量养活自己;她选择妇女节建屋子,想要讨个好彩头作为翻身的象征;她甚至喊出了“凭么事这就是我的命?我的命未必就不能由得我自己去变?我要离婚”*方方:《奔跑的火光》,《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2年第3期。这样“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呼声。但是,不屈反抗的她却在一次次的毒打谩骂和血本无归中被家庭的重压击倒,由希望一步步走向绝望,最终在狂怒中选择了同归于尽。英芝不是唯唯诺诺泯然于环境中不敢发声软弱无力的女性,不是一味怨艾社会不公现实黑暗的女性,却在无尽抗争中希望破灭,在无望挣扎中绝望爆发。矛盾性的人物使作品愈发复杂深刻,渐进式的剧情发展又使全文情绪在悲剧性的结尾达到了顶点,更添上了悲壮的色彩。
英芝的悲剧,一方面源于自身因素,莽撞冲动,遇人不淑,眼界太浅,只懂得考虑物质,又始终为家庭所束缚。但另一方面,英芝的命运又是男权社会压迫和封建传统观念下的必然。正如方方自己所说:“有时候我觉得一个女人倘出生在一个贫穷的乡下,就注定了她一生的悲剧。她要么无声无息地生死劳作都在那里,过着简单而艰辛的生活,对外部生机勃勃的世界一无所知;要么就要为自己想要过的新的生活、为改变自己的命运付出百倍千倍的代价,这代价有时候比她的生命更加沉重。”*方方:《我们的生活中有多少英芝?》,《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虽其一概而论或有偏颇,但亦阐述了男权话语中心和女性反抗意识、封建传统观念和突破传统的新思想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处在这样的社会中,要么沉寂至死,一生安于贫苦,生儿育女;要么拥有反抗意识和抗争想法,在环境、家庭和婚姻的多重打压中走向毁灭。
英芝所在的老庙村,正是男权至上的农村封建社会的缩影。一方面,男性支配整个家庭,“既嫁从夫”,女人在外要给丈夫面子,在内要无条件服从丈夫,劳作养家做牛做马,没有任何自我和尊严可言。男权话语下的农村社会,将女性的辛苦劳作看作天经地义,将女性无条件服从看作女人必备的品格,甚至纵容教唆男性以暴力手段维持家庭。而女性没有自己的家园,无法经济独立,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庸而存在,成为生育机器和苦力,失去话语权,更遑论平等、自由、尊严?!另一方面,更为悲哀的是,在长期的男权压迫中,女性逐渐形成了对男权话语的自我认同,重塑其自我价值观,并外化为生活的行为规范。她们认同男性中心地位,认为女性生来就要逆来顺受、忍气吞声,为了家庭和睦牺牲自我利益,将所有痛苦无奈都抹去,只剩下一句“女人就是这么做的”,女人的定义就是柔顺和服从,女人的意义就是照顾家庭和服务于男性。
自封建社会确立以来,男权话语就是社会文化的主体,女性总是被遮蔽、被书写的。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女人》,桑竹影、南珊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17页。男性建立了传统的父权体制,规定了话语标准,从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到三从四德的行为规范,女性只能依照男性所规定的标准存在,女性价值尺度也因而被男权社会捆绑确立。但是,女性的悲剧不仅仅来源于男权话语中心的标准规范和禁锢捆绑,亦是女性潜移默化的自我认同,女性价值在向男权话语中心靠拢的同时不断被消解淹没,直至重塑为男性标准。《奔跑的火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刻画了农村女性的生存状态,向传统男权社会发声,表现了强烈的女性意识。当大多数女性作家将笔墨放在私人化写作、性问题探讨时,方方却将目光转移到了农村边缘化的失语女性身上,尖锐地抛出了对社会的质疑——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为什么农村女性仍然要耗尽一切代价,去追求哪怕最基本的生存自由?
对于农村边缘女性的书写,一方面是对贵族女性主义的反拨,体现了方方鲜明的平民立场;另一方面,方方指出了在进步时代边缘化地区的停滞与落后,展现了深陷其中的边缘女性的挣扎,更表现了深层的人性关怀。方方以一腔同情和激愤,批判了传统男权社会和封建观念,表达了当代女性对于基本生存空间的渴望和自由平等的渴求,以杀夫的极端形式决绝地对传统社会提出了挑战,谱写了一曲男权压迫下女性抗争的悲歌。
三、宿命意识与女性出路
方方在以小说展现现代女性在爱情、婚姻等方面所面临的困境的同时,又对女性出路作出了探索。令人讶异的是,方方对女性出路的探索,总是笼罩着浓郁的宿命意识。《船的沉没》中吴早晨的英文名AN’ALKN的含义是宿命,他从不相信“如果”,他说“命运对于每一条生命都是没有如果可言的。他怎么摆布你,你都得认。你认了,你才能活得不那么累”*方方:《船的沉没》,杨柳编:《方方·中篇小说系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162页。;《万箭穿心》的李宝莉千苦万难一忍再忍,面对公婆的百般刁难,她认为“你是媳妇,你嫁给他们的儿子,这就是你的命”*方方:《万箭穿心》,《小说月报》2007年第7期。。在命运面前,剧情发展已被注定,冥冥中仿佛有只大手在摆弄一切,既然不可更改,惟一能做的就是承认和接受。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是任由摆布的玩偶,眼睁睁地走向命定的悲剧。
正因命运之不可改变,人生之不可为,悲剧性的人物多慨叹生命的脆弱和渺小。徐楚慨叹着即使有了美满的家庭与惊人的成就,有了巨额的财富和稳定的工作,生命也仍然是渺小如尘而又微不足道的。强烈的悲观色彩导向剧情的悲剧性发展,人物多走向分裂、虚无乃至死亡。分裂者如黄苏子,表面是腼腆安静的高级白领,内里却是歇斯底里的妓女,性格的极端分裂是被社会所迫,悲剧性的自我救赎和更进一步的彻底毁灭。人性的光亮面由此被方方尖锐的笔狠狠割开,露出内里的阴暗、复杂和脆弱——每个人都是分裂的,有的人分裂的是身体,有的人是灵魂。虚无者如叶桑,在与婚外情对象宁克发生关系时想的是莲花花瓣打开的一瞬,内里却什么都没有,极致的绚烂带来的不过是更强烈的虚无,虚无仿佛成了生命的本义,引向极端。向着茫茫江水的叶桑,在精神的空无中选择了悲剧性的死亡。
寻求出路而不可得,由物质到精神的追寻无果,只能归于空无,一切都是命定,一切都是必然。方方笔下的女性,就是在这宿命中挣扎徘徊的芸芸众生。她们向往着天空,却无一不背负着沉重的枷锁;她们追寻着理想,却在悲剧的漩涡中越陷越深,犹如无止尽的轮回循环。这样强烈的宿命意识背后,一方面,是方方自身观念中挥之不去的悲观色彩,她的作品总是表现出对理想爱情的追求和坚守,体现出一种执着反叛世俗爱情的高蹈精神,因其或不可得,便只能走向悲观性的宿命;而另一方面,是方方对现代女性的困境抱有的深深同情,进而试图探索女性出路。由此引起我们的思考:为何方方对女性出路的探索,总是有着浓郁的宿命意识?这是否反映了中国当代女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悲观看法?是否说明,受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影响和男权压迫的当代中国,要真正实现男女平等、摆脱女性悲剧命运,仍然任重道远?方方没有正面回答这些问题,不过,她在创作谈《只言片语》中曾通过转述他人之言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我的同学童志刚在他的评论文章《“泛悲剧意识”与第三种声音》中说:‘其实悲剧的确不总是社会的,政治的和时代的,就像伤痕文学所惯常表现的那样,特别是在平淡的日常生活当中,悲剧更多的是个人自我选择的结果。而这种选择的依据从根本上说在人性的层面,决定于人物的既定性格——它是人物生活经历、文化遗传、观念意识和时代烙印的产物——人物也许能够摆脱某些外来的阻碍,却由于强烈的自我遮闭而难以超越自身。’”*方方:《只言片语》,《小说月报》1991年第10期。如斯言,现代女性或许因为随波逐流而被时代左右,或许因为某种社会压迫(如男权)而挣扎反抗,但即使她们摆脱了这些外部原因,也难免会因为“个人自我选择”而陷入矛盾困苦之中。方方对女性出路的探索,引发我们进一步的思考:如果物质与精神需求都不是真正的归宿,如果现代女性“由于强烈的自我遮闭而难以超越自身”,那么,女性的出路究竟在何处?
方方的作品没有给出答案。这正是方方作品的文学魅力所在,即在不断探索拷问中迂回,在反复书写中激起读者的深思。文学是人学,女性书写的文学价值不仅仅在于揭示女性悲剧,更是超越女性自身,超越婚姻爱情的个人格局,最终创造“大写”的人,寻求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由此而言,方方的作品虽不能提出宿命和人生探讨的解决方案,但却超越了女性意识本身,向更广阔的人性维度探索,引出了关于人的价值的哲学思考。文学之于人生的意义,或正在于此。
四、结 语
方方的作品跳脱出了当代女性书写流行的纯粹私人化写作的窠臼,不拘泥于个人情感的表达,而从更广阔的社会环境角度,多层次地描写了不同阶层女性的生存困境,通过悲剧形式展现了女性的反抗精神和不懈追求。这其中既有固有的男权社会压迫,亦有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更有对宿命和人生的探索追寻,从而跳出了传统女性意识的藩篱,扩展了女性写作的深度;她把现代女性遭遇的困境放在更为广阔的人的价值中进行思考,在压迫与反叛、理想与现实的思辨中前行,由此开辟了女性书写的独特路径。
美国女评论家玛格丽特·富勒曾言:“妇女所需要的,不是作为女人去行动,去主宰什么,而是作为一种本性在发展,作为一种理智在辩解,作为一种灵魂在自由自在的生活中无拘无束地发挥女子天生的能力。”*转引自〔美〕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程锡麟、朱徽、王晓路译,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5年,第76页。“五四”思想启蒙运动至今已逾百年,女性的天空却仍旧是低沉的,女性的羽翼仍旧是薄弱的。男权社会下的传统话语秩序和文化规则,制定了男性标准的话语模式,潜意识地默许着对女性的歧视和不平等对待,女性的言语被封杀,女性的渴求被禁止,女性的身体也被束缚在各式各样的社会符号中。经济、婚姻、家庭、爱情,每个关键词背后都是女性无助的哭喊,即使想要高高飞翔,寻求个人的独立和自由,却无不在枷锁之中,必须在无尽钳制中付出相当的代价。由此,女性的利益诉求和所呼唤的自由平等,或非时下极端的以女性为主体的中心话语权,而是在广阔天空下自由呼吸的权利,是基本的作为人的尊严和自由。方方的作品虽追求过于理想化的爱情,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却以其独树一帜的女性视角,阐述了当代女性的困境,将女性书写放在更广阔的“人的文学”的领域,扩展了女性书写的深度和广度,具有切实的当代意义。
(责任编辑:曾庆江)
The Plight and Outlet for Females in Fangfangs’ Works
SHI Qiao-yang, FU Xiang-xi
(SchoolofHumanities,GuangzhouUniversity,Guangzhou510006,China)
Different from the pure personal trend in the current female writing, Fangfang’s works, instead of focusing on the expression of emotions, tend to consider the plight of females in the context of mankind value and forge ahead through speculations on oppression and resistance as well as ideality and reality, thus having initiated a unique way for current female writing.
Fangfang; female perspective; the outlet for females
2016-05-05
石俏杨(1995- ),女,广东惠州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付祥喜(1977- ),男,湖南绥宁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I206.7
A
1674-5310(2016)-09-004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