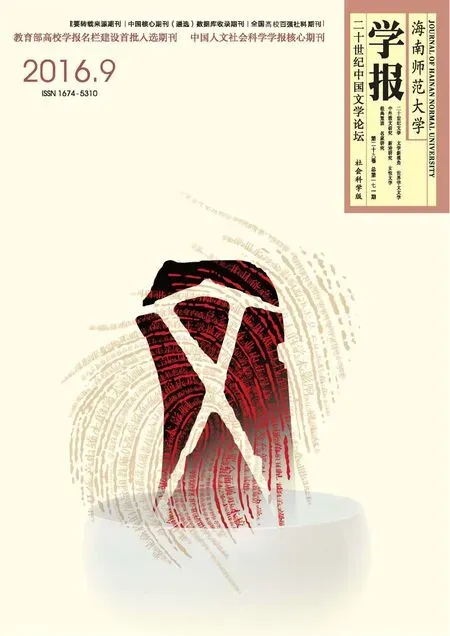行动者的鲁迅与自由之“人生、政治与文学”
胡梅仙
(广州大学 文学思想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006)
行动者的鲁迅与自由之“人生、政治与文学”
胡梅仙
(广州大学 文学思想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006)
革命与文学是鲁迅的两个基本视点。鲁迅曾说过,革命是革新的意思。当然,革命于鲁迅的意思比较复杂,也不排斥政治革命。革命文学与鲁迅的关系不是那种依附的关系,或者说鲁迅不是在革命文学的理论圈子里来看革命文学,而是在局外来看革命文学。这就把革命文学特别是一些苏联作家的作品当作文学中的一翼,而不是全部或者惟一的真理。鲁迅从不属于某一个政党,不信主义,更不做主义的奴才,即使是在加入左联时期,他也是根据自己的思想、观点发表意见,而不是盲目地苟同某一种政治学说。拒绝意识形态的束缚是鲁迅保持真切现实感和复杂性的一种思维方式,其掌握和反思世界的方式是感性的复杂的,而不是靠理论来解决的。
鲁讯;革命;文学;人道主义
一、文学与人生、革命
文学表现人生,与人生脱离的艺术就像花砵里只能长出绿豆芽而长不出参天大树一样。艺术如果不和现实人生相接触,最终会堕落到“为艺术而艺术”的那一路,最终会显现出空虚和顾影自怜来。纵观人类文学、艺术,无论是什么派的,最终都来自于现实生活,即使是最早的神话也是现实生活的影子。鲁迅的重视人生的艺术是与他把创作与民族解放运动、民众启蒙联系在一起相关的。文学为人生这对鲁迅来说是无可非议的,可文学与革命的关系对于鲁迅来说就复杂得多了。
革命与文学是鲁迅的两个基本视点。鲁迅曾说过,革命是革新的意思。当然,革命于鲁迅的意思比较复杂,也不排斥政治革命,但是最基本的思想是革新,不是像成仿吾们摆出的面孔,仿佛革命就是要人死。“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①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7页。以下《鲁迅全集》引文皆出自此版本。革命于鲁迅的意义不一定是政治武力、流血牺牲,只要是一切革新的措施,在鲁迅看来都是革命的。革命文学也不是打打杀杀的文学,鲁迅对革命文学的理解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文学革命”时期的启蒙文学,二是指革命人做出的文学。而鲁迅却认为革命前是叫苦鸣不平的文学,革命中没有余暇做文学,革命后的文学是颂歌和挽歌的文学,中国革命尚未成功,所以中国没有革命文学。他对于革命文学的看法是很矛盾的,在不同的阶段对于革命文学有不同的理解。而且鲁迅并不认为当时有真正的革命文学存在。并且说,在革命前、后以及革命中都不可能有革命文学存在。“所以巨大的革命,以前的所谓革命文学者还须灭亡,待到革命略有结果,略有喘息的余裕,这才产生新的革命文学者。”*鲁迅:《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鲁迅全集》第4卷,第137页。
革命文学不会产生于风起云涌的革命时代,当是产生于革命胜利后的间隙。“现在所号称革命文学家者,是斗争和所谓超时代。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倘自己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又要挂革命的招牌,便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条路的。身在现世,怎么离去?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社会停滞着,文艺决不能独自飞跃,若在这停滞的社会里居然滋长了,那倒是为这社会所容,已经离开革命。”*鲁迅:《文艺与革命(并冬芬来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84页。鲁迅认为革命文学不是超时代的构想浪漫,能在停滞的社会滋生并为社会所容的文艺决不是革命文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于革命文学是否在当时真正存在的疑惑。换一种意思说,鲁迅怀疑当时的革命文学与现实是否是密切相关的。苏联的革命诗人叶赛宁、梭波里还是终于自杀了,他们是碰死在对于革命的绝望上。鲁迅固不反对革命,只是提醒革命的发热症者,要有充足的思想准备来承受革命的曲折、失败等。他说:“我因此知道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而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则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但叶遂宁和梭波里是未可厚非的,他们先后给自己唱了挽歌,他们有真实。他们以自己的沉没,证明着革命的前行。他们到底并不是旁观者。”*鲁迅:《在钟楼上》,《鲁迅全集》第4卷,第36页。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革命的动态、复杂和多种可能性的孕育。这也体现了鲁迅在路上的观点,一切都是未成形的,在行走之中形成。第一,革命诗人很有可能碰死在革命上;如果现实的革命不能让革命诗人碰死其上,倒不是真正的革命。第二,革命诗人碰死在革命上,才是真正和革命一同前行的诗人。不与革命一道前行的革命诗人,不会碰死其上;如果革命只是让他们唱赞歌,世间没有这样至善至美的革命。革命就是在打破永远的不完善中不断前进的。革命诗人的幻想是在被无数次的革命破灭之后才能逐渐实现的。现实中的革命一定是会破灭革命诗人的幻想的。这说明,“革命诗人”之名称本身就含有永不满足、永远革命的意义。第三,革命诗人的幻想会在革命的现实中破灭,革命是残忍的,如果想趟在革命的河中,决不能把革命想象成是坐在一旁喝咖啡高谈革命的事情。
革命文学与鲁迅的关系不是那种依附的关系,或者说鲁迅不是在革命文学的理论圈子里来看革命文学,而是在局外来看革命文学。这就把革命文学特别是一些苏联作家的作品当作文学中的一翼,而不是全部或者唯一的真理。虽然他曾说过无产阶级文学“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第128页。。这只是一种对于未来的构想,就像马克思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一样。在实际的历史、现实层面上,鲁迅并没真正地完全认同当时的革命文学。且不说他与创造社、太阳社的纷争,他对一些“革命诗人”的警醒,他担心那些“茄花色”的所谓革命者是否是真正的革命者,还有他与左联领导人之间的真正隔膜。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人在战,不会为任何组织、任何主义所圈住,按照自己的所看所想说自己的话,做自己的事。即使是左联的任务,他也会分辨。在和“第三种人”“自由人”论争时,他表现出了一个真正的思想者的分辨力,他的有名的一句话是:“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鲁迅:《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第128页。鲁迅始终是一个独立思考的思想者和文学探索者。有些研究者把他归于某一种主义或者是单纯的个人主义或者是单纯的人道主义或者是共产主义,这都是不恰当的。特别是共产主义者之说,这对于鲁迅无疑是一个考验。作为一个从旧营垒中来的知识分子,鲁迅不可能一下子脱胎换骨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本质上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李长之称鲁迅是“诚实无伪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第154页。。1928年,鲁迅说:“我则不但‘根本不懂唯物史观’,且未曾研究过卢梭和托尔斯泰的书,所以无从知道那一说对,但能附载于此,以供读者的参考罢了。”*鲁迅:《<奔流>编校后记》,《鲁迅全集》第7卷,第182页。从鲁迅对托尔斯泰的肯定性的文字中,我们也不敢说鲁迅是完全认同马克思主义是绝对正确的。他只是实实在在地说自己不懂,对新的事物他抱着学习的态度。
冬芬(董秋芳)曾给鲁迅写信说:“在现在,离开人生说艺术,固然有躲在象牙塔里忘记时代之嫌;而离开艺术说人生,那便是政治家和社会运动家的本相,他们无须谈艺术了。由此说,热心革命的人,尽可投入革命的群众里去,冲锋也好,做后方的工作也好,何必拿文艺作那既稳当又革命的勾当?”*鲁迅:《文艺与革命(并冬芬来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79页。鲁迅既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离开人生说艺术,也不是如冬芬所说,完全投入到革命的群众中去,“冲锋也好,做后方的工作也好”,鲁迅希望自己能找到真正的革命文学的精髓,然后像高尔基暴风雨里的海燕一样与风浪搏击。正像对任何事物他都会持着观察迟疑的态度,对于革命文学,他是欢迎认同的,他却不能不表现出他的一些与革命文学家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耐人寻味的,是在‘那巴斯图’派因怕主义变质而主严,托落兹基因文艺不能孤生而主宽的问题。……这问题看去虽然简单,但倘以文艺为政治斗争的一翼的时候,是很不容易解决的。”*鲁迅:《〈奔流〉编校后记》,《鲁迅全集》第7卷,第173页。“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7卷,第115页。鲁迅非常清晰地看到文艺与政治的冲突以及不可调和。但他还是抱着对新生事物实验接收的态度,翻译介绍革命文学作品。1930年前后,鲁迅翻译苏联的文章开始占据很大的比重。
文学与人生、革命的关系也是记得与忘却、正视与回避的问题。有些历史和事实需要记忆,忘却反而是一种懦怯的行为。鲁迅曾说中国是一个善于忘却的民族,所以才有相似的历史一次一次地循环。而他写那些文字就是为了那些不该被忘却的前驱者的灵魂,那些流血的魂灵。为了让人们记住他们,为了他们不再寂寞,为了纪念他们的血,希望后人偶尔还会想到他们,也是为了依稀的微薄的亮色,而给予继续生存者的慰藉。在国民党清党期间,鲁迅自称是被血吓得目瞪口呆了,鲁迅的一切思想和想法来自于他的所见所闻和自身体验,而不是来自于所谓的这个主义、那个理论。当他看到他在北京女师大的学生刘和珍倒在血泊中,他在中大的学生毕磊,青年朋友柔石、殷夫,民盟战友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比什么堂皇的理论都让鲁迅感到中国失去了最有为的青年和战友。鲁迅的文字和他的思想一样,来自真情实感、生活的深切体验,即使是鲁迅的杂文,都是夹带着他的狂风暴雨的感情或者是冷峻清醒的批判,是把自己的爱憎情感融入里面的。一直到今天,鲁迅文字的深沉、热烈情感仍然以一种巨大的力量打动着我们。这是一次生者对于死者的纪念,也是一次对于淋漓的鲜血的正视。“真的猛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忽视那些流过的血,或者那些流血的勇士是否值得去死?这是鲁迅一直说自己多疑的原因。鲁迅的思想是复杂多面的,他说过知识分子喜欢思考,就会失去勇,可是他又说,因为不知道自己所走的路正确与否,“到现在还是乱闯。倘若闯入深渊,自己有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鲁迅:《两地书·二》,《鲁迅全集》第11卷,第15页。
“对鲁迅来说,即便是革命的思想,它本身归根到底也是非现实的,无法立即保证其有力的地方立即实现;另一方面,在文学领域,倘若写了一部好作品,完成了一件有良心的翻译、介绍,这本身会是一件给中国的现实以多大影响的现实行动啊。”*[日]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丸山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王俊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1页。丸山升这句话的意思是不管是文学还是思想于鲁迅都是无力的,以此来推翻所谓的“文学无力论”,表示思想也是无力的,唯有行动(包括政治行动)才是有力的;或者可以理解为不管是政治还是文学的现实性只能从他们各自独有的存在样态里去寻求。这样就把鲁迅关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以各自职责的分担而分开,从而看到鲁迅关于政治与文学关系及其改造力量的复杂理解。
二、在革命与不革命之间
鲁迅虽提倡为人生的文学,却还是被革命文学家批评为写“历史小说”,讲“趣味”,揭露黑暗却不指导光明。在鲁迅的眼中,像徐志摩那样的创作才是趣味文学,这一观点表现出鲁迅与革命文学、“为艺术”的文学的审美、道德伦理取向的不同。我们从他们的论争中可以了解到当时革命文学家和鲁迅关于革命文学的看法,这是中国革命文学史上的一笔宝贵的财富。不管是对于革命文学还是对于自由主义文学,或在这之间已经无法创作纯文学作品的鲁迅,我们都能从前人探索的足迹中得到我们关于文学、革命的有益的借鉴。
针对鲁迅在《“醉眼”中的朦胧》中所说,“倘使那时不说‘不革命便是反革命’,革命的迟滞是‘语丝派’之所为,给人家扫地也还可以得到半块面包吃,我便将于八时间工作之暇,坐在黑房里,续钞我的《小说旧闻钞》,有几国的文艺也还是要谈的,因为我喜欢”*鲁迅:《“醉眼”中的朦胧》,《鲁迅全集》第4卷,第66页。,钱杏邨认为鲁迅的“因为我喜欢”而去做什么典型地表现了鲁迅的个人主义,是“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者的丑态”*钱杏邨:《“朦胧”以后——三论鲁迅》,孙郁、黄乔生主编:《回望鲁迅——围剿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74页。。成仿吾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中认为“趣味是苟延残喘的老人或蹉跎岁月的资产阶级”*仿吾:《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孙郁、黄乔生主编:《回望鲁迅——围剿集》,第25页。。鲁迅说:“我要更加讲趣味,寻闲暇,即使偶尔涉及什么,那是文学上的疏忽,若论‘动机’或‘良心’,却也许并不这样的。”*鲁迅:《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102页。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鲁迅对于革命文学家所摆出的庄严、唯自己是真理的面孔的愤激之词,也有着“偏要”与之对立的意思。其实鲁迅一直是反趣味文学的,他很反感徐志摩那一类风花雪月的文章,后来又反对林语堂的幽默性灵文字,也是警惕人们不要“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鲁迅:《“论语一年”》,《鲁迅全集》第4卷,第582页。。他曾说:“无论是学文学的,学科学的,他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但如果他专讲天王星,或海王星,虾蟆的神经细胞,或只咏梅花,叫妹妹,不发关于社会的议论,那么,自然,不看也可以的。”*鲁迅:《随便翻翻》,《鲁迅全集》第6卷,第143页。趣味性历来不是鲁迅文学追求的目标,可是在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文学家们看来,鲁迅是一个无政治意识只讲究个人主义趣味的作家。钱杏邨认为鲁迅只能“狂喊几声”、“彷徨歧路”,“我们也可以说完全是所谓自由思想害了他,自由思想的结果只有矛盾,自由思想的结果只有徘徊,所谓自由思想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一个骗人的名词,鲁迅便是被骗的一个”*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 时代》,孙郁、黄乔生主编:《回望鲁迅——围剿集》,第41页。。自由思想必然来自于独立思考,独立思考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徘徊,因为世间万物都是矛盾的、相对的,从来没有绝对的真理。似乎革命文学不许有徘徊矛盾,只许有一个坚定的理想和信心。鲁迅的徘徊是思考的徘徊,而不是原地踏步的徘徊,他对于这些革命诗人的浪漫谛克早就有着深刻的体察和提醒。而革命文学家不仅要求暴露社会的黑暗,还需要“创造社会的未来的光明。文学作家不应该专走消极的路”*钱杏邨:《“朦胧”以后——三论鲁迅》,孙郁、黄乔生主编:《回望鲁迅——围剿集》,第80页。。钱杏邨认为暴露不是盲目的暴露,不是个人主义的暴露,而是“出发于集体”。*钱杏邨:《“朦胧”以后——三论鲁迅》,孙郁、黄乔生主编:《回望鲁迅——围剿集》,第80页。意思是一种集体需要的暴露、统一意志下的暴露。这个集体需要又是怎样衡量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此后的一系列专制作风、专制文风的源头。鲁迅却认为革命文学家是“对于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视”*鲁迅:《文艺与革命》,《鲁迅全集》第4卷,第85页。,制造一种虚妄的光明来麻痹自己。
对于革命、流血牺牲,鲁迅有过这样的比喻:“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鲁迅:《空谈》,《鲁迅全集》第3卷,第298页。又说:“远地方在革命,不相识的人们在革命,我是的确有点高兴听的,然而——没有法子,索性老实说罢,——如果我的身边革起命来,或者我所熟识的人去革命,我就没有这么高兴听。有人说我应该拼命去革命,我自然不敢不以为然,但如叫我静静地坐下,调给我一杯罐头牛奶喝,我往往更感激。”*鲁迅:《在钟楼上》,《鲁迅全集》第4卷,第30页。除了不愿他人流血牺牲外,鲁迅也不愿自己熟悉的人去革命,自己也更愿意坐在一旁喝牛奶而不是“拼命去革命”。鲁迅并不害怕流血的革命,但是他希望:“要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须买卖相当。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从最新的战术的眼光看起来,这是多么大的损失。”*鲁迅:《空谈》,《鲁迅全集》第3卷,第298页。血不能白流,更何况鲁迅不知道血该不该流?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兵之所以勇敢,就在没有思想,要是有了思想,就会没有勇气了。现在倘叫我去当兵,要我去革命,我一定不去,因为明白了利害是非,就难于实行了。”*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第8卷,第224-225页。一方面鲁迅主张革命,一面又说希望自己坐在房间里喝喝咖啡乐得安宁自在。这也可以看出鲁迅思想的矛盾之处。鲁迅一面认为言语宣传很重要,比如辛亥革命的成功,当是宣传的成果;而另一面,他认识到是因为没有党人实力使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篡夺。他一面说,知识分子的无用,笔的无用,一面还是表示“不放下”*“我明知道笔是无用的,可是现在只有这个,只有这个而且还要为鬼魅所妨害。然而只要有地方发表,我还是不放下。”参见鲁迅:《两地书·二四》,《鲁迅全集》第11卷,第80页。笔。一面称自己做不了领导者,一面又说改革最快的是“火与剑”,这就是一个矛盾的鲁迅,却又是不矛盾的。在一个社会、文化转型的复杂动荡时代,一个成长中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考,是包含着多方面看起来相互碰撞其实是内在统一的思想的。我们也可以把鲁迅对于革命的态度当作“被迫革命”、“保留革命”。实在需要革命的时候,还是要革命的。政治上合作又分开,分开又合作,可是那些曾经流出的血呢,难道是白流的?而且流血之后得到的政权是什么样的,有可能和以前的性质一样或者在某些方面比以前的差,就像鲁迅所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鲁迅:《忽然想到·三》,《鲁迅全集》第3卷,第16页。。一种幻灭的悲哀,血像被欺骗着流了。
我们一般认为早期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论争的时候还未了解马克思主义,晚期加入左联后就成为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化的“后设的历史本质论”。我们看鲁迅一路走来的历史,鲁迅可能赞成激进,不一定赞成随意流血;可能赞成左翼,不一定赞成左翼领导人的决策。那么,鲁迅的左倾到底是“投降”还是鲁迅一贯的思想行动必至的结果?梁实秋说过,鲁迅只有一种主义没骂,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有多种到达方式,鲁迅是在赞成共产主义的前提下投身于左翼的,参加左翼对于鲁迅来说也不过是一种他实现自己改造国民的理想途径。问题是鲁迅后来加入左联与前期的文学思想或者是对于革命的看法有根本的不同吗?我认为是没有的。在任何时候,鲁迅都反对专制独裁,崇尚自由写作。关于革命和革命文学,他仍然还是以前那些观点(见前文)。鲁迅还是以前的鲁迅,唯有一点不同的是,以前的鲁迅是孤独的个体在战斗,现在是和组织一起在战斗。后来鲁迅发现了组织的专制苗头,他当时还只是把它看作与左联的领导人有关。其实这也是鲁迅的自由思想与组织的政党专制的根本冲突。这在当时还不是很明显,鲁迅只是凭着他对自由的需要的本能感到了“工头”、“英雄”、“元帅”、“奴隶总管”的役使奴隶的皮鞭。从后来鲁迅与左联领导人的分歧,哪怕就是冯雪峰,他执笔写的文章鲁迅都说一点不像他的。鲁迅是一个独立的无人能代替的个体,他的孤独、反抗,来自于他作为一个历史中的个体生命的独特体验感受与自我选择。
鲁迅从不属于某一个政党,不信主义,更不做主义的奴才,即使是在加入左联时期,他也是根据自己的思想、观点发表意见,而不是盲目地苟同某一种政治学说。左翼文化也只是鲁迅的另一种文化设想,并不表示鲁迅认为它一定就是周全的或者说是至上的真理。鲁迅对于苏联的心情也很复杂,只是像梁实秋所说,从没骂过,却是怀疑过。他对苏联一方面有支持、同情、歌颂,另一方面对于苏联出现的一些压制、独裁其实是心里有所感觉的。比如他在《<奔流>编校后记》中就有这样的话:“这有名的《小鬼》的作者梭罗古勃,就于去年在列宁格勒去世了,活了六十五岁。十月革命时,许多文人都往外国跑,他却并不走,但也没有著作,那自然,他是出名的‘死的赞美者’,在那样的时代和环境里,当然做不出东西来的,做了也无从发表。”*鲁迅:《<奔流>编校后记》,《鲁迅全集》第7卷,第187页。
“他没有拒绝做左联的旗帜。他怀着对当时黑暗政治的反抗和对自由的憧憬做出朝向左翼的政治选择,他也需要周围有一些人,有一些青年。那年代,胡适周围是集拢着一些人的,而如今被封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始终有官方资源、公共资源做平台。鲁迅有什么资源呢?他的资源只是他自己。”*刘纳:《谈唐弢老师,并谈开去》,《随笔》2010年第1期,第182页。鲁迅是因为对于当时的黑暗政治的反抗和对自由的憧憬加入左联,追求自由和另一种政治理想让鲁迅加入左联组织中,可有了组织,他仍是“独战”,还需“横站”着战。他说:“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鲁迅:《341218·致杨霁云》,《鲁迅全集》第13卷,第301页。“我的确常常感到焦烦,但力所能做的,就做,而又常常有‘独战’的悲哀。”*鲁迅:《341206·致萧军、萧红》,《鲁迅全集》第13卷,第280页。鲁迅名义上是左联领导,实质上与组织专制格格不入。“英雄们却不绝的来打击。近日这里在开作家协会,喊国防文学,我鉴于前车,没有加入,而英雄们即认此为破坏国家大计,甚至在集会上宣布我的罪状。我其实也真的可以什么也不做了,不做倒无罪。然而中国究竟也不是他们的,我也要住住,所以近来已作二文反击,他们是空壳,大约不久就要消声匿迹的:这一流人,先前已经出了不少。”*鲁迅:《360504·致王冶秋》,《鲁迅全集》第14卷,第90页。鲁迅认为他们要销声匿迹,指的是这些所谓的英雄工头们的专制作风,也可看出鲁迅对左联是有着自己的一番看法的:第一,鲁迅认为左联是一个很好的联合战线,并希望扩大战线;另一方面,鲁迅把左联的一些专制作风当作是一些人的个人行为,或者说,鲁迅心中的左联和左翼文学应该是另一种样子。从鲍罗廷、瞿秋白对中国土地革命的另外的思考,也可看出中国革命其实是有着多种可能性的途径和表现形态的,*据蔡和森写于1927年9月的一分报告记载,1927年“马日事变”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度出现“精神……混乱”,鲍罗廷曾重新解释土地革命,认为“土地革命不即是没收土地”,其内容应包括:减租减息,乡村自治,保护佃农,武装自卫,办农运讲习所,从新养成不幼稚、不过火的农运人才。当时独秀说:“老鲍这种办法好是好,但是修改了国际土地革命的意义。”瞿秋白说:“这不是修改国际土地革命意义,按照中国目前的情况只能如此做。”参加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2-93页;参见张宁:《无数人们与无数远方:鲁迅与左翼》,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0页。何况左联主要是一个文化组织,其中左翼文化的多种发展趋向和表现形态也会因历史、现实和人而呈现着多种表现面貌。不过这只是一种小范围的不同,把什么都纳入组织,纳入一个政党,专制作风必然会产生。
那么鲁迅对于自由的追求在当时到底是否切实可行?这是一个关联着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最重要的是鲁迅的追求的状态,是永不满足于现实,永远在寻求更能让人生存的路和更充分的自由。鲁迅一生的思想有两个基本点,一是生存,这使他关注底层的贫者弱者,一是自由,这又让他对个性主义情有独钟。鲁迅的一生一直都交织在对这两种状态的追求中,也即是他在对许广平的信中所说的“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的起伏”。对于革命文学家所嘲笑的人道主义,他自道不舍放弃;对于革命文学家更要抛弃的个人主义,他也承认自己确确实实是应该划在资产阶级行列,是个人主义的。看到国民党的清党,鲁迅的心不免哀痛:“虽然明知道这是‘浅薄的人道主义’,不时髦已经有两三年了,但因为小资产阶级根性未除,于心总是戚戚。”*鲁迅:《通信(并Y来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98页。从鲁迅早期崇尚尼采似的“超人”、“天才说”到目睹辛亥革命被篡夺果实一系列历史现实,鲁迅的希望由最有力的孤独的个人转向对于组织的依靠,在后来对于无数人们无穷远方的怀念中,鲁迅似乎又回到了五四落潮后“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孤独状态中。
三、鲁迅的人道主义与“壕堑战”
鲁迅的反抗是对一切强权、专制、压迫的反抗,这条反抗的线贯穿鲁迅一生。
从反抗清廷、军阀到国民党,从反对封建礼教、传统文化到恶俗弊习,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弱者的呻吟,哪里就有鲁迅的反抗。在北洋军阀时期,他反段祺瑞政府的枪杀学生,那时,他是支持国民党的,而到了国民党清党统一全国时,他又和国民党作对,加入左联。左联在当时相对于国民党来说是弱的、被压迫的一方。鲁迅当时的处境就如他所说:“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铁窗斧钺风味’,而在青天白日之下又有‘缧绁之忧’了。”*鲁迅:《通信·致小峰的信》,《鲁迅全集》第3卷,第468页。拒绝意识形态的束缚是鲁迅保持真切现实感和复杂性的一种思维方式,其掌握和反思世界的方式是感性的复杂的,而不是靠理论来解决的。鲁迅最让人动容的两篇文章《纪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纪念》分别写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这两个不同的历史政权时期,而这两篇文章都同样表现出了鲁迅的剧烈的愤怒和沉重的悲哀。似乎应了鲁迅所说的“人生或者有正轨吧,但我不知道”*鲁迅:《两地书·二》,《鲁迅全集》第11卷,第16页。。现在有些人认为鲁迅心中有不平之气,似乎此风不可长。退一万步说,即使现在的人不读鲁迅的书,将来也会再有读他的时候的。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有时会处在一种无法挽救的套子中,那个时候,只有凭着偏激的真理、决绝的反抗才能摆脱罗网,看到希望。从1918到1924年,鲁迅对于国民性的批判还是抽象的,1925年北京女师大事件之后,鲁迅的批判就倾向于具体的人和事了。“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国民党的清党和独裁统治,使鲁迅的目光更加关注于那些现实中发生的人和事。
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曾说:“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鲁迅:《两地书·二四》,《鲁迅全集》第11卷,第81页。多种思想糅合在一起的矛盾纠缠才是一个真实的鲁迅。鲁迅写这封信的时间是1925年,在当时,鲁迅主要受这两种思想影响,到后来,鲁迅的思想杂入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之类的东西,但决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晚期鲁迅主要是这三种思想的糅合物,在每一个时期,其中的某一方面可能会突出一些。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是鲁迅的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其实也是一种人道主义,“但总的来看,前一因素(人道主义)比后一因素(个性主义)要更为基本,尽管从表面看来(例如常引尼采等)情况似乎相反”*李泽厚:《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汪晖等著:《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论鲁迅(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9页。。李泽厚认为鲁迅的人道主义比个性主义更为根本这一点在鲁迅晚期应该比早期更明显。鲁迅同情贫苦人、下等人的生存处境,愿为他们争得生存的权利,而在实际的生活和工作中,他是绝对承受不了失去自己的自由的。这也是一个平等与获得自由的路途之间到底有多远的问题。*“鲁迅把平等的要求放在自由的前面,其实是为了追求一种终极的自由,他实际上从未真正放弃过自由,都可以看作是鲁迅早期个人主义的一种表现。那么,如果,这个专制的时间较长,鲁迅能忍受多久?是一劳永逸地去获得最大的自由,况且还不知道这种自由的黄金世界到底能允诺多大的自由?还是在永远以人为本、为最高利益的自由民主制度中一边享受个人的自由,一边创造大众的幸福条件?鲁迅在这里所希望的与他所感受到的出现了冲突,也在某些方面表现出终极自由的虚幻性和平等与自由的不可两存。”参见拙著:《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话语之建构(1898-193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33页。
鲁迅小时候听完“水漫金山”的故事后,心里一直压着一座雷峰塔。后来,在大舅父那儿看到了一部弹词《白蛇传》,上边印的法海的绣像,全叫他用指甲把那眼睛给掐得稀烂。*参见林贤治:《人间鲁迅》,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年,第10页。增田涉回忆:“他(鲁迅)对我说,流传着中共杀害附近农民的风闻,也许只是一种风闻吧,但杀害农民,不管因为什么都不好,我们派人去调查,如果是真的,一定要劝告共产党不可杀害。他没有加入共产党却是同情者,因为他自称是同路人作家。但是仍然在听到杀人的事情时,他就无论怎样也不能默视了。他用坚决的态度说,调查结果,如果是真的,就得进行忠告。在这时候,我好像看见了他那人道主义者的真面目。”*[日]增田涉:《鲁迅的印象》,钟敬文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3页。不管你什么政策,什么主义,鲁迅只凭自己的感觉感受、慈爱之心来对待生命。他说,那些“卖血的名人”常常“开出一个大题目来”*鲁迅:《341210·致萧军、萧红》,《鲁迅全集》第13卷,第286页。,就把人的性命送掉了。对于那些毁谤儿童被人指使卖国的言论,他以一颗纯白之心和对青少年爱国热情的理解感叹说:“至于少年和儿童,则拼命的使尽他们稚弱的心力和体力,携着竹筒或扑满,奔走于风沙泥泞中,想于中国有些微的裨益者,真不知有若干次数了。虽然因为他们无先见之明,这些用汗血求来的金钱,大抵反以供虎狼的一舐,然而爱国之心是真诚的,卖国的事是向来没有的。”*鲁迅:《保留》,《鲁迅全集》第5卷,第151页。鲁迅待人待事不想首先就被一些所谓的公理、正义、强权罩住,他以自己的感同身受来理解、同情那些被压迫者、反抗者。鲁迅希望革命(尽量是革新的革命)但不流血,享受自由但不革命(指政治流血革命)。自然,这是矛盾的,鲁迅也希望能调解这种矛盾,可这是个无法调和的矛盾。
鲁迅曾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
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但恐怕也有时会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鲁迅:《两地书·二》,《鲁迅全集》第11卷,第16页。
所以我想,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倘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这就是我所以主张“壕堑战”的原因,其实也无非想多留下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鲁迅:《两地书·四》,《鲁迅全集》第11卷,第21页。
鲁迅这两次的信中都谈到了壕堑战,这表明了鲁迅对于战斗的看法。壕堑战不是突击战,中国人的传统封建思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造的。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事件使鲁迅改变了以往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持的某种程度上的肯定态度,这也更增强了鲁迅的韧性的战斗的看法。“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鲁迅:《两地书·八》,《鲁迅全集》第11卷,第32页。笔战成为鲁迅最好的武器。虽然他有时也认为笔无用,也许鲁迅就是在“相信笔”和“笔无用”、相信武力却又不知武力建立的政权是否更好之间,还是不断地用自己的笔与一切专制、压迫、残暴作斗争。何况,鲁迅“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鲁迅:《两地书·八》,《鲁迅全集》第11卷,第33页。,并说“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鲁迅:《两地书·八》,《鲁迅全集》第11卷,第33页。。“如果你上了他的当,真的赤膊奔上前阵,像许褚似的充好汉,那他那边立刻就会给你一枪……骂一声‘谁叫你赤膊的’——活该。”*鲁迅:《不负责任的坦克车》,《鲁迅全集》第5卷,第139页。在给《榴花社》的信中,鲁迅持一贯的壕堑战法,只在保存力量,慢慢进击。他告诫说:“万勿贪一种虚名,而反致不能出版。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鲁迅:《330620·致榴花社》,《鲁迅全集》第12卷,第409页。对于铤而走险、徒然牺牲一类的事,鲁迅一向迟疑。据增田涉回忆:“他在晚清搞革命运动的时候,上级命令他去暗杀某要人,临走时,他想,自己大概将被捕或被杀吧,如果自己死了,剩下母亲怎样生活呢?他想明确地知道这一点,便向上级提出了,结果是说,因为那样地记挂着身后的事情,是不行的,还是不要去罢。”*[日]增田涉:《鲁迅的印象》,钟敬文译,第30页。鲁迅并不是吝惜生命,一是他认为刺杀不一定能成功,即使成功也并不能真正达到革命效果;第二,以小的牺牲来换取大的利息一直是鲁迅的原则。试想,如果鲁迅在那时牺牲了,有可能中国革命的面貌又是另一种样子。鲁迅反对那种只想用短时间便想取得胜利的的思想。传统腐败思想的清除和革新需要假以时日,鲁迅甚至说这是几代人的事情。“要一人兼做两三人,四五人,十百人的工作,……奋斗三十年。不够,就再一代,二代……”*鲁迅:《忽然想到·十》,《鲁迅全集》第3卷,第96页。事实上,我们现在还在做鲁迅要求做、未做完的事情。
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虽然“我又无拳无勇”,“在手头的只有笔墨”,“但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鲁迅:《两地书·八》,《鲁迅全集》第11卷,第32页。。对于旧社会旧文明,鲁迅是不甘沉默的,他在信中说准备在将来等待机会联合战线战斗。当创造社准备和鲁迅联合时,鲁迅是有合作意向的。鲁迅后来加入左联组织,也应该是出于联合战线可以加强力量的意思。对这不是像有的文章所说是仅仅为了他心中的杜尔尼西亚——许广平而战,更是鲁迅一生的抱负,只是他们确是知己而已。许广平曾在给鲁迅的信中表现过这样的想法:“所以小鬼之意,以为对于违反民意的乱臣贼子,实不如仗三寸剑,与以一击,然后仰天长啸,伏剑而死,则以三数人之牺牲,即足以寒贼胆而使不敢妄动。为牺牲者固当有胆有勇,但不必使学识优越者为之,盖此等人不宜大材小用也。”*许广平:《两地书·一一》,《鲁迅全集》第11卷,第44页。鲁迅回信不赞成许广平的想法,认为此事不很容易成功,而且一两回这样的事件,“实不足以震动国民”,并且说这乃是小鬼“性急”之故,“要治这麻木状态的国度,只有一法,就是‘韧’,也就是‘锲而不舍’。逐渐的做一点,总不肯休,不至于比‘踔厉奋发’无效的”*鲁迅:《两地书·十二》,《鲁迅全集》第11卷,第47页。。“谈到在辛亥革命前夜死了的同乡秋瑾女士的时候,他和社会上的评论不同,却是批判的,认为那是天真的做法。我是这样理解的。”*[日]增田涉:《鲁迅的印象》,钟敬文译,第63页。虽然承认刀与火的效力,但鲁迅最终认为人类的事情是靠一步一步去做的。即使把乱臣贼子杀了,倘若国民不改变,还会有别的乱臣贼子冒出来。“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的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鲁迅:《通讯》,《鲁迅全集》第3卷,第23页。鲁迅认为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鲁迅:《两地书·一〇》,《鲁迅全集》第11卷,第40页。,并表示对于攻打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为,现在还不想放手”*鲁迅:《两地书·一〇》,《鲁迅全集》第11卷,第41页。。鲁迅也深知他可能看不见这些改革的效果了,但他认为还是得去改造国民中的劣根性,捣乱搅动这一潭死水。“此后我还想仍到热闹地方,照例捣乱。”*鲁迅:《260617·致李秉中的信》,《鲁迅全集》第11卷,第528页。可见出于一个热衷于社会实践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不甘沉寂。此时,他与许广平的爱情已确定,心情也乐观很多。“我近来忽然还想活下去了。为什么呢?说起来或者有些好笑,一,是世上还有几个人希望我活下去,二,是自己还要发点议论,印点关于文学的书。”*鲁迅:《260617·致李秉中的信》,《鲁迅全集》第11卷,第528页。爱情赋予鲁迅继续活下去的勇气,捣乱、发议论是鲁迅继续活下去的工作,爱情使他生命后期的斗志更旺。
鲁迅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要求作家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238页。要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238-239页。鲁迅列举了俄国诗人、作家叶遂宁、毕力涅克和爱伦堡的例子,因现实情形与他所想象的革命不一样,终于因对革命的失望而自杀,所以要革命就要做好长期艰苦的准备。
左联五烈士牺牲后,鲁迅主编的《前哨》上发表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文中指出:“国民党摧残文化和压迫革命文化运动,竟至用最卑劣最惨毒的手段暗杀大批革命作家的地步了!”“国民党在虐杀我们的革命作家以前,已经给我们革命文化运动以最高度的压迫了;禁止书报,通缉作家,封闭书店;一面收买流氓,侦探,堕落文人组织其民族主义和三民主义文学运动,以为如此就可以使左翼文化运动消灭了,然而无效。于是就虐杀了我们的作家。然而这也是无效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前哨》第1卷第1期。鲁迅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面谴责统治者是“灭亡中的黑暗的动物”*鲁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鲁迅全集》第4卷,第289页。,一面相信被压迫的“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仍然滋长”*鲁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鲁迅全集》第4卷,第290页。。在两年后的写的《为了忘却的记念》里,对于左联五烈士的牺牲,鲁迅更深的只是感到一种无言的悲切。他只是“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才明白“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鲁迅全集》第4卷,第502页。。“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鲁迅全集》第4卷,第502页。这一次鲁迅遭遇到了无法言说的境地,但他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鲁迅全集》第4卷,第502页。。鲁迅曾写信给朋友说:“黑暗之极,无理可说,我自有生以来,第一次遇见。但我是还要反抗的。”*鲁迅:《341231·致刘炜明》,《鲁迅全集》第13卷,第325页。看着青年在风沙里渐渐粗暴的灵魂,他说“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鲁迅:《一觉》,《鲁迅全集》第2卷,第229页。。是青年的流血和隐痛的灵魂使鲁迅意识到自己是在人间活着,或许是这种疼痛太剧烈了,让鲁迅深切地感到了生的存在,却是沉痛的存在,但也是使自己更加成为叛逆反抗的猛士的存在。这是鲁迅隐痛慈悲的一面,谁人又能懂?周作人把鲁迅的左倾称作“老人的胡闹”,胡适在回苏雪林信中说:“青年不左倾,谁当左倾?”*胡适:《致苏雪林信》(1936年12月14日),孙郁、黄乔生编:《回望鲁迅——围剿集》,第157页。言下之意是鲁迅不该左倾。关键是“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鲁迅全集》第3卷,第279页。,青年的血不能白流,这是一个近似于真理的事实,可是真理有时又是被戏弄的,那些政治家在杯酒间言欢,青年的血在调和声中白流。所以,鲁迅为什么一直反对徒手请愿,反对不要轻易赤膊上阵,要用欧洲壕堑战的战法,不到万不得已时不主张短兵相接,要用生命的最小的利息获得最大的本钱。鲁迅一生与反动势力斗,就是用的这种迂回的战术。他在危险的时候蛰伏装死,是为了养精蓄锐再加入另一轮的战斗,一生用了一百多个笔名,曲曲回回地把自己的抗争思想传播到千万人心中。如果他不讲究战术,他早该被国民党暗杀或者失去发言的权利。这就是一个智者的深沉韧性的战斗战术。“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但太觉疲劳时,也无妨休息一会罢;但休息之后,就再来一回罢,而且两回,三回……。血书,章程,请愿,讲学,哭,电报,开会,挽联,演说,神经衰弱,则一切无用。”*鲁迅:《杂感》,《鲁迅全集》第3卷,第52页。不管是人,还是社会都怕这种韧战,只要有坚韧的精神,“那么,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鲁迅:《忽然想到·七》,《鲁迅全集》第3卷,第64页。。
在革命文学兴起时,鲁迅的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就成为了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创造社和太阳社攻击的目标。冯乃超在《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说:“开端‘要救治像我(鲁迅)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其次‘要改变他们的精神’,结局他‘依旧讲趣味’。看吧,人道主义者的裸体照相,就是这个样子。”*冯乃超:《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孙郁、黄乔生编:《回望鲁迅——围剿集》,第55页。在冯乃超看来,鲁迅的人道主义的结局就是“讲趣味”,而革命文学是需具有阶级意识和斗争意识的,鲁迅的人道主义显然解决不了改造社会、救助民众的问题。钱杏邨称鲁迅是“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者”*钱杏邨:《“朦胧”以后——三论鲁迅》,孙郁、黄乔生主编:《回望鲁迅——围剿集》,第75页。。无论从鲁迅的个人主义还是人道主义或者彼此的消长起伏,钱杏邨这句话都是有一些道理的。彭康把鲁迅的人道主义称之为“老婆心”*彭康:《“除掉”鲁迅的“除掉”》,孙郁、黄乔生主编:《回望鲁迅——围剿集》,第67页。。正如成仿吾所说:“在革命运动的现阶段,社会的内在的矛盾已经尖锐化了的时候,一切的抗争不得不由阶级意识出发,人道主义者的假哭佯啼直是拙劣的丑角,可以招人冷笑罢了。”*石厚生(成仿吾):《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孙郁、黄乔生主编:《回望鲁迅——围剿集》,第85页。鲁迅只怕“‘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惟有中国特别,知道跟着人称托尔斯泰为‘卑汙的说教人’了,而对于中国‘目前的情状’,却只觉得在‘事实上,社会各方面亦正受着乌云密布的势力的支配’,连他的‘剥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剧的假面’的勇气的几分之一也没有;知道人道主义不彻底了,但当‘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剥去和抗争,也不过是‘咬文嚼字’,并非‘直接行动’。”参见鲁迅:《“醉眼”中的朦胧》,《鲁迅全集》第4卷,第62页。。这是鲁迅的担忧,“暴君的专制使人民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民变成死相。”*鲁迅:《忽然想到·五》,《鲁迅全集》第3卷,第45页。鲁迅既看到了国民党的血,看到了一些青年革命文学家的不敢正视现实,也看到了一些政府诤臣实质上的奴才性质。所以,他说过,“自由主义么,我们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讲几句话也为难;人道主义么,我们人身还可以买卖呢”*鲁迅:《“来了”》,《鲁迅全集》第1卷,第363页。。在当时的中国,是没有自由的,人道主义更是没有过时,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于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责任编辑:王学振)
Lu Xun as a Doer and His Freedom in “Life,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HU Mei-xian
(LiteraryIdeologyResearchCenter,GuangzhouUniversity,Guangzhou510006,China)
Revolution and literature are two basic viewpoints of Lu Xun, for revolution meant reform, as once uttered by Lu Xun. And as for Lu Xun, revolution is definitely something complex, even including political revolution. As su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nd Lu Xun is not one of dependence, or Lu Xun approached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n outsider rather than from that of a member in the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theory circle. By so doing, Lu Xun managed to regard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esp. works of some Soviet Union writers,as a component of literature rather than its entirety or the sole truth. As he was not with any political party and had no faith in any doctrine, much less being enslaved by any of them, Lu Xun could also voice his opinions in accordance with his thought and view instead of readily subscribing to some certain political theory even during his participation in the Left League Writers Federation. The rejection of ideology bondage is a mode of thinking for Lu Xun to maintain his sense of true reality and its complexity, for his mode of comprehending and reflecting on the world is perceptual and complicated, which can’t be solved through theory.
Lu Xun;revolution; literature; humanitarianism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鲁迅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研究”(批准号:15FZW059)
2016-04-20
胡梅仙(1969-),女,湖北咸宁人,文学博士,广州大学文学思想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06.6
A
1674-5310(2016)-09-00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