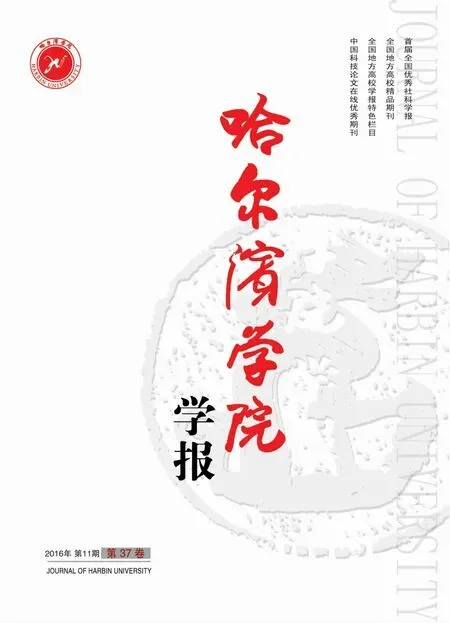《聊斋志异·寄生》篇的艺术魅力
郭玉琼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聊斋志异·寄生》篇的艺术魅力
郭玉琼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寄生》是《聊斋志异·王桂庵》的附篇,讲述了一个有关青年男女婚恋的故事。其中人物形象的鲜活生动,文本形式的对比艺术,叙事语言的别致精巧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些也构成了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
寄生;人物;对比;语言
《寄生》是一则趣味横生的爱情故事,它讲述了王桂庵的儿子寄生同姑母家的女儿闺秀以及同郡妙龄女郎张五可之间的婚恋过程。该篇小说后来被改编成评剧《花为媒》,成为荧幕上深受观众喜爱的优秀剧目。此文是附在《王桂庵》之后的独立一篇,作者蒲松龄把该篇命名为《寄生》,显然是带有强烈的情感倾向。正如异史氏在结尾部分说的那样,“父痴于情,子遂几为情死;所谓情种,其王孙之谓欤?不有善梦之父,何生离魂之子哉”,可见王孙身上寄托了父亲钟情、痴情、为情而梦、因梦而成情的特点。笔者将从三个方面对这篇小说的艺术魅力具体展开论述。
一、圆形人物
描写人物,是小说的显著特点。圆形人物则主要是指文学作品中那些具有复杂性格特征的人物。它的塑造打破了过去人物出场定型,好人全好、坏人全坏的脸谱化倾向,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刻画人物形象,从而更真实、深入地揭示人性复杂、多变的一面。这种人物的性格较扁平人物而言更为丰满、立体。在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复杂的矛盾中完成人物性格的塑造,使得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呈现出一种流动感。《寄生》里面存在着许多这样的人物形象,其中寄生和张五可的性格最为突出。
寄生作为郡中名士,长相俊美并且饱读诗书,当他见到姑母的女儿闺秀时,立即被其慧艳绝伦的风姿给迷住。对于正值青春的寄生来说,心生爱慕实属正常。然而,姑丈的拒绝让他心生郁闷。此时,同郡张五可因偶然的机会在车中见到了寄生便托媒媪来求亲,一开始寄生是拒绝的,直到梦中与五可相会,态度才稍稍改变。当他觉得自己和闺秀的姻缘已经不可能的时候,他动摇了,心中暗暗思量“五可果如所梦,何必求所难遘”。从倾心到苦闷,从苦闷到坚守,再从坚守到动摇,大致可以看出寄生的心理变化过程。但是他对梦中所见始终是迟疑的,因此他派邻妪潜相五可。等邻妪回来告诉他五姑娘和梦中所见完全相符时,寄生一开始很高兴,但当兴奋之情退却时,他又起了疑心,害怕邻妪欺骗他,因此决定亲相五可,寄生多疑的性格在这里表露无遗。也正是在故事的发展中寄生的形象一步步走向丰满,从一开始的傻气到后来的多变,生动地刻画出了青年男子陷入爱情时的诸多反常举动,而这些行为看似可笑实则是恋爱中男女的真实写照。
五可,作为同郡大姓张氏最小的女儿,自幼深受父母的疼爱。当她第一次见到寄生时,便钟情于他。因此她主动告诉母亲并请母亲替自己做主,反映了女主人公对待爱情的大胆、直白。然而,五可的热情并没有换来寄生的回应,相反王家不同意这门亲事。可即便如此,女主人公也没有放弃,她通过入梦的形式和寄生见面。后来王家来提亲,五可却通过同样的方式报复寄生。待郑氏把女儿送往王家以后,五可仍不放弃,她沉着应对,毅然前往王家。这些行为都反映了女主人公聪明、冷静、积极、主动的性格特点。嫁入王家之后,五可对闺秀稍有不服,但看到闺秀确实风姿怡人,便心甘情愿地称对方为姐姐,这又突出了五可的豁达、率真。总之,张五可这个人物形象不同于传统大家闺秀的精神风貌。在传统封建社会里面,大家闺秀端庄、含蓄,她们不会轻易地表露自己的心迹,即便自己有情有爱,也要克制,完全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长期处于这种社会氛围的女子是没有个性的,她们知书达理、通晓世故,但她们却没有真性情,更谈不上可爱。而张五可这个人物形象却突破了传统闺秀的性格规范,在她身上张扬着新女性的精神风采,因此可以说她具有超越时代的典范意义。
二、对比手法
文学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它们之间就像灵与肉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优秀的文学内容需要优秀的文学形式来承载,而优秀的文学形式又进一步丰富完善了优秀的文学内容。任何精神作品都有它的存在形式,否则内容便无法体现。文学追求真善美的统一,而形式创造是这种追求的最后完成。宗白华曾经说过:“艺术家往往倾向以形式为艺术的基本,因此他们的使命是将生命表现于形式之中。”蒲松龄在《寄生》中为了充分地塑造人物形象,在形式上主要采用了对比烘托的艺术手法。他把人物大致分为几个类别,让这些人在对比中显示自我的独特意义。
小说中对比手法的运用是多方面的,例如,王家父母同郑家父母、张家父母的对比,张五可同闺秀的对比,媒媪同寄生的对比,寄生同五可的对比,郑氏夫妇之间的对比,等等。笔者将主要选用其中三个对比进行展开分析。
首先,郑氏夫妇的对比。郑秀才和二娘这两个人是故事中性格反差最为明显的一对夫妇。他们两个在女儿婚事上的态度也是三家中意见最为不统一的一家。郑秀才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保守、迂腐,充满了学究气。当王桂庵遣媒人来说亲时,他“以中表为嫌”断然拒绝,当知道二娘和王氏的计划后他勃然大怒,甚至破口大骂。这些反映了他固执、守旧的老夫子形象。当女儿听闻寄生要迎娶五可的消息一病不起后,郑秀才对此更是气愤之极,他宁可女儿死掉也不愿她有辱家门,这又反映了他残暴无情的一面。相比郑秀才,二娘的性格倒是灵活多变一些。当她知道女儿和寄生相互爱慕之后,总是力图想办法来成全这两个人,甚至在寄生要迎娶五可的紧要关头,她用计让女儿先到,把生米做成熟饭以此来帮女儿完成现实心愿。从中看出了她对女儿的关爱,这种爱不是专制、残暴的,她能站在女儿的立场上替女儿思考。郑秀才也爱女儿,但他更爱礼法,他的爱是狭隘的、冷漠的甚至是摧残人性的。郑秀才受封建的八股取士制度残害,正像二娘说他的那样“吾侄亦殊不恶,何守头巾戒,杀吾娇女”,可见八股取士对读书人心灵的毒害。蒲松龄运用这样的对比手法,用意也便在此。
其次,寄生与五可的对比。作为故事中的两大主角,这一男一女性格差距极其明显。女主人公大胆、机智,男主人公则懦弱、多疑。在以往的婚恋题材作品中,男追女是爱情发展的主要模式,但该篇却一反常态,作者有意把它安排成了女追男的爱情故事。在这里,五可处于主动地位,而寄生处于被动地位。最初寄生心系闺秀,五可只因在车中偶然看了寄生一眼,便萌生爱意。当获悉寄生已经心有所属之后,她仍不死心,通过离魂的方式也要同寄生在梦中相见,设法让对方爱上自己,终于寄生向她来提亲,可她却推脱自己已经许配别家了。在这场爱情角逐里面,分明是五可一直处于有利地位,寄生则步步落入她的“圈套”。正如故事的最后,寄生问五可却媒之故,她却笑着说:“无他,聊报君之却于媪耳。尚未见妾,意中止有闺秀;即见妾,亦略勒之,以觇君之视妾,较闺秀何如也。使君为伊病,而不为妾病,则亦不必强求容矣。”从中可以看出女主人公直爽、机智、自尊自爱的性格特点。离魂入梦本是不切实际的,作者有意安排了这样离奇场景无非是要告诉我们:情深至极便可离魂。五可通过梦境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爱情理想。然而在现实世界里,又有多少痴情女子可以像五可这般,她们不过是被摧残、被损害的对象。面对爱情,她们只能认命,丝毫没有选择的权力。蒲松龄借助张五可这个人物形象,表达了他对弱势女性的尊重与同情以及对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呼唤,体现了蒲松龄进步的女性观。
最后,媒媪同寄生的对比。这两个人的对比主要集中在两处,一处是媒媪为五可说媒,一处是媒媪帮寄生娶妻。在这两个事件中媒媪对寄生的评价都用到了一个字“痴”。最初寄生心中装着闺秀,不愿意接受五可,媒媪说他“执其人以求之,守死而待之,不亦痴乎”。后来五可拒绝了寄生的求婚,寄生一气之下,卧病不起,媒媪说他“痴公子!前日人趁汝来,而故却之;今日汝求人,而能必遂耶”。这两个人一个是郡中名士,一个是市井妇人,前者饱读诗书,后者熟谙生活。但面对日常琐事、人情世故,博学的寄生竟输给了说媒的妇人,在这里作者讽刺了读书人的眼高手低以及同生活脱节的毛病。然而这种现象在封建科举制度盛行的时代,又岂止寄生一人。
通过以上这三个对比不难发现:在蒲松龄眼中女性的地位高于男性,读书人在小说中成了被讽刺批判的对象。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认识?结合蒲松龄的生平经历,他一生科举不顺、生活潦倒。这样的处境使他更容易见识人间百态,深切地体会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所以,面对不满意的现实世界,作者有太多的怨言和苦水需要宣泄。
《寄生》之所以能打动读者并在《聊斋志异》整部小说中占有重要位置,与它自身的魅力是分不开的,它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正像黑格尔在《美学》中说:“内容和完全适合内容的形式达到独立完整的统一,因而形成一种自由的整体,这就是艺术的中心。”
三、语言活泼
《寄生》是文言小说《聊斋志异》的其中一篇,它的语言从总体上保持了文言体式的基本规范。叙述语言较一般文言浅显,行文流畅自然。人物语言则灵动活泼,口语化色彩突出,并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语言风格。
该篇小说的人物语言主要是采用对话的方式,在话语中展现人物性格。首先是张五可的语言风格,当她与寄生在梦中第一次相遇时,寄生问其姓名,她开口便说:“妾,五可也。君深于情者,而独钟闺秀,使人不平”,这短短的几句话就把自己的姓名、来意说清楚了。通过上文的分析已经知道最初寄生并没有见过五可,所以拒绝张家的求亲也无甚过错。五可却不高兴,觉得自己堂堂的大家闺秀,不该输给寄生心心念叨的闺秀,故而入梦来见寄生。其中“使人不平”这四个字用得好,一方面它写出了女主人公性格中好胜、要强的特点,另一方面把贵族小姐娇嗔、任性、直率的脾气描写得活灵活现了。“妾,五可也”,简洁的四个字就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没有赘余,可见这位小姐做事干脆利落,绝不拖泥带水。“君深于情者,而独钟闺秀”,这两句话去掉“者”和“而”也是四字句,语言对仗工整,符合贵族小姐的用语习惯,十八个字整体读起来生动活泼、饶有趣味。
其次是媒媪的语言风格,她的语言大多机智幽默,富有生活哲理。媒媪第一次劝寄生时说,“但问医良否耳:其良也,召和而缓至,可矣;执其人以求之,守死而待之,不亦痴乎”,她用良医给人治病,只要病能治好而不在乎医者是谁的道理开导寄生,可谁料寄生偏偏固守己见,这时媒媪又说“何见之不广也”,语言通俗易懂,并且略带批评的语气。从中可以感受到媒媪作为过来人对生活的深刻认识。后来寄生得知五可另配他家,滴米不进,媒媪胸有成竹地告诉他“早与老身谋,即许京都皇子,能夺还也”。这短短的三句话突出了媒媪对自己办事能力的绝对自信,显然这种自信是建立在她丰富的人生阅历基础上的。可是寄生的父亲桂庵对此却心有顾虑,他害怕唐突的行为会遭到张家拒绝,媒媪却说:“前与张公业有成言,延数日而遽悔之;且彼字他家,尚无函信。谚云:‘先炊者先餐’,何疑也”,通过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媒媪丰富的社会经验以及她从容机智的应变能力。此外,媒媪帮寄生亲相五可时说:“机幸可图。五娘向有小恙,因令婢辈将扶,移过对院。公子往伏伺之,五娘行缓涩,委曲可以尽睹矣”,更是充分显示了她老道的处事能力。毫无疑问,媒媪作为红娘经历过各种突发事件,深谙男女双方的婚恋心理,并且多年的人生阅历能让她把生活与哲理很好的结合起来,从而形成自己高效的办事风格。作者选用符合媒人身份的语言,而这些语言从媒媪嘴中说出又是那么的贴切、自然,读起来幽默而富含智慧。
此外,寄生、郑氏夫妇等人的语言也大都生动活泼、饶有趣味。如寄生一开始坚持所爱时说“但天下之医,无愈和者”,“媪休矣,此余愿所不及也”,写出了青年男子刚入爱河时的痴情心理,后被五可的风姿倾倒之后,他又说“生平未见颜色,故目中止一闺秀。今知罪矣”,男子“好色”的本质心理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又如二娘的语言“吾侄亦殊不恶,何守头巾戒,杀吾娇女”,郑秀才的语言“若所生女,不如早亡,免贻笑柄”,更是充满了浓郁的口语化色彩。
以上三方面的论述对《聊斋志异·寄生》篇的艺术魅力大致做了一个浅显的分析。蒲松龄在创作此篇小说时对文本内容和形式的选择都是经过深入思考的,他用自己别出心裁的艺术手法展现了一幕“才子佳人”式的婚恋轻喜剧。
[1]蒲松龄.聊斋志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2]袁世硕,徐仲伟.蒲松龄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4]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5]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6]黑格尔.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7]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8]马振方.聊斋艺术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9]吴祖湘.聊斋志异欣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10]林植峰.《聊斋》的艺术魅力[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张 庆
The Artistic Charm of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Parasitism”
GUO Yu-qiong
(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0,China)
“Parasitism” is an additional story in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It is a love story of a young couple. The figures are very vivid. The text structure reflects the art of comparison. The narrative language is interesting and novel,which makes deep impression. All of these factors construct unique artistic charm for this novel.
“Parasitism”;figure;comparison;language
2016-02-29
郭玉琼(1988-),女,河南许昌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1004—5856(2016)11—0086—04
I207.3
A
10.3969/j.issn.1004-5856.2016.1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