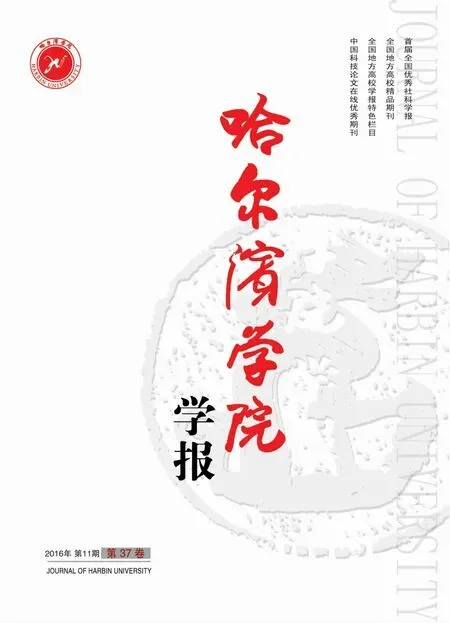从“子为父隐”到“窃负而逃”
——儒家伦理亲亲与仁民之困
唐 桃
(曲靖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曲靖 655011)
从“子为父隐”到“窃负而逃”
——儒家伦理亲亲与仁民之困
唐 桃
(曲靖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曲靖 655011)
儒家伦理以孝悌为行仁的起点,以一体之仁为行仁的终点,其中,爱路人是行仁的关键节点。但由于儒家一贯强调差等之爱,因此,在亲亲与仁民发生冲突时,“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的道德教训往往形同虚设。由《论语》“子为父隐”、《孟子》“窃负而逃”这两个案例可以看出,从孔孟开始,“私恩”与“公义”孰轻孰重的天平已经错误的倾斜,孝道近乎无条件优先的情理逻辑最终导致了行仁的起点背离了关键点,由此暴露出儒家伦理的狭隘与矛盾。
儒家伦理;私恩;公义;矛盾
自2002年复旦大学刘清平教授发表《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以来,儒家伦理在多大程度上要对中国式腐败负责这一关切现实的问题得到学界的热烈讨论和持续关注。儒家伦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组成部分,其思想魅力需要重新审视,但作为诞生在小农经济时代服务于封建宗法制度的意识形态,儒家伦理在今天有其不合时宜的地方,其在私恩与公义之间的不当立场尤其值得人们警惕。本文遵循历史同情与现实批判相结合的原则,重读《论语》“子为父隐”、《孟子》“窃负而逃”这两个经典案例,以期厘清儒家伦理的深层矛盾和理论缺陷。
孔子在周游列国时曾遇隐士劝其弟子子路归隐,子路回告孔子,孔子感叹: “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在人群中实现自身的存在价值,是儒家一直坚守的人生立场,因此,深入研究并且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成为儒家哲学的鲜明特色。
从孔子开始,儒家就主张“仁”。《论语》出现频率最高的概念就是“仁”,共出现109次,其内涵极其丰富,涵盖孝、悌、忠、恕、恭、宽、信、敏、惠等具体德目,但其核心要义在于“爱人”。“孝”是子女爱父母,“悌”是弟弟爱兄长,“忠”是臣民爱君主,“宽”是上级爱下级,“恭”是晚辈爱长辈,“恕”是人与人之间的同情与友爱……因此,当悟性不高的弟子樊迟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的时候,孔子直截了当地回答:“爱人”。(《论语·颜渊》)
由《论语》记载的多则事例中,可以亲切体知孔子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贯彻实践“爱人”的理论主张。
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论语·乡党》)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论语·述而》)
“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甚至面对礼崩乐坏的乱世,孔子所能提出的救世良方——“克己复礼”,其本质依然是“仁”——“爱人”。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
可见,孔子学说可归于仁学。仁者爱人,孔子主张的“仁”的实践,以“孝悌”(家庭伦理)为起点,以“一体之仁”(自然伦理)为终点,其中,对天下苍生、普通民众的爱(社会伦理)是“行仁”过程中的关键节点,对此,孔子极为看重“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人,因而被孔子视为最高的人格理想——“圣人”。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
因此,在评价背叛旧主(公子纠)、辅助谋害旧主的新主(齐桓公)、“一匡天下”的历史人物管仲时,孔子能无视管仲“不忠”的罪行,超越世俗成见,独树一帜地给予其“仁”的评价。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
但是,孔子主张“仁民”必须以“亲亲”为起点,并且,“仁民”不过是“亲亲”的推恩,即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首孝悌”“孝悌为仁之本”的思想主张在《论语》首篇《学而》第二章就说得很明确——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是理解儒家仁学思想的关键。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引用程子之言解释道:“孝弟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弟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有人追问:“孝弟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程子回复:“非也。谓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曷尝有孝弟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
宋儒认为,“仁”与“行仁”不同,“仁”是性,“行仁”是用,孝悌是行仁而不是仁本身,“仁”才是孝悌之本,由于人具有“爱莫大于爱亲”的天性,因而儒家主张“行仁自孝弟始”。但是,他们其实很明白,“孝弟”仅仅是“仁之一事”而非全部。一个人仅有孝悌的美德不足以称为“仁人”,“仁人”之爱不限于父母兄弟等血缘至亲,还应该把爱的对象扩大至天下苍生,对与主体毫无血缘关系乃至根本不认识的普通民众(路人)的爱才是仁者的标识。
儒家伦理道德主体把对天下苍生的仁爱之心,最终归因于人与生俱来的“天性”“良心”。但是,此“良心”本就分了厚薄,定了先后。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可见,孟子虽然主张对亲属、路人、禽兽都应有爱,但面对不同对象,君子所付出的爱在程度和表现上绝不能没有区别,否则,一视同仁、无差等的爱就成了孟子所激烈批评的墨家“无父”是“禽兽也”的兼爱。王阳明对此说得很清楚:“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把草木去养禽兽,又忍得。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宴宾客,心有忍得。至亲与路人同是爱的,如箪食豆羹,得则生,不得则死,不能两全,宁救至亲,不救路人,心又忍得。这是道理合该如此。……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不可逾越,此便谓之义。”[2]儒家的仁义观大抵如此。在理想的层面上,亲亲与仁民互不妨碍,当然皆大欢喜。但是,在现实的情境中,令人遗憾的是“亲亲”难免有与“仁民”抵牾之时,当亲属的不正当利益与路人的正当利益发生尖锐冲突,道德主体于此间避无可避,只能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时,对血缘至亲有“良心”,就是对普通民众的“狠心”。《论语》和《孟子》中的两个案例恰能说明问题。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
直躬的父亲攘羊,直躬亲自告发,叶公赞美直躬为“直”(品行正直),孔子虽未断然否定直躬之“直”(“异于是”而非“反于是”),但却通过正面称颂“子为父隐”之“直”暗地里贬斥了直躬之“直”。孔子的价值判断自有其文化传统,《礼记·檀弓》就主张“事亲有隐而无犯”“事君有犯而无隐”“事师无犯无隐”,郑玄注:“隐,谓不称扬其过失也。无犯,不犯颜而谏。”[3]父亲攘羊,子女隐而不告,即便有人不乐意承认,但它的确是人之常情。但问题在于,就是这种在亲属不正当利益与路人正当利益之间倾向于维护亲属利益(即便明知这种利益是不正当的)的所谓“人之常情”,在稍有公共理性的人看来,这就是人性的弱点,不值得标榜和颂扬。遗憾的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后世奉为“至圣先师”的孔子恰恰这样做了,对“子为父隐”作出“直在其中”的价值判断在某种程度上无异于“颠倒曲直”乃至于“扭曲为直”。
宋儒虽然明知“父攘羊,子隐而不告”既非传统意义上的“直”,也不是一般意义上值得称颂的“直”,但却依然硬是把此“人情”归入“天理”,以“天理”证明其“直”进而肯定之:“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谢氏曰:‘顺理为直。父不为子隐,子不为父隐,于理顺邪?瞽瞍杀人,舜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当是时,爱亲之心胜,其于直不直,何暇计哉?’”[1](P137)“爱亲之心”固然是人情,但在这里如何突然成了天理,如果天理不过是“天然的道理”“自然的法则”,非善非恶,可善可恶,那么,荀子在《性恶》篇提出的能引发人与人之间无止境争斗的“好利”“疾恶”“好声色”也就是“天理”了,如此,“天理”又何足为凭。“爱亲之心胜”是当下直觉,是人的本能反应,即便它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乃至必然性,但它肯定不是真正的“直德”,把“人格正直”置换为“依直觉行事”,把 “对他人的诚实”置换为“对自己的诚实”,宋儒通过偷换概念,为孔子的颠倒曲直的“歪理”辩护。
如果攘羊罪小,对路人利益损害虽则无可抵赖但毕竟程度有限,最起码没有直接伤害人的生命本身,而如果攘羊的父亲被告发却可能面临被诛杀的刑罚,“两害相权取其轻”,被评为“时之圣”的孔子主张“隐而不告”,虽然有损于社会“公义”,有害于自身“直德”,但基于对人性弱点的理解与同情,批评者也不宜站在道德的高地对其进行过于严苛的道德审判。但是,“孝”与“忠”,“情”与“法”,“亲亲”与“仁民”的固有冲突被《孟子》推到绝境后,孟子替圣人作出的取舍充分暴露了儒家伦理的缺陷。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
直躬之父攘羊是历史事实,舜之父杀人却是理论假设,但在这里,问题不在于瞽瞍是否真的杀过人,而在于如果一个儒家道德楷模(如,舜),他的至亲(如,父亲)毋庸置疑地严重损害了路人的利益(如,杀人),他应该如何应对、抉择?
孟子首先否定了舜有利用天子身份阻挠皋陶执法的权利,“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这表明孟子是深知此间公义(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与私恩(父母恩重,徇私枉法)的冲突,并恪守“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礼记·丧服四制》)的告诫。但是,当弟子桃应不甘一直被孟子塑造为天下孝子之典范的舜,在面对父亲杀人即将被严惩极有可能以命偿命的关键时刻居然无所作为,因而进一步质问“然则舜如之何”时,孟子果然忍不住为“大孝”之舜选择了“窃负而逃”这一条道路。按照对儒家经典的正面理解,当然知道孟子在这里的主观意图是歌颂舜的至孝,宁愿放弃尊贵的天子之位来保住对己不慈的父亲的性命,而做出在寻常百姓看来如此重大自我牺牲的舜,却能做到“视弃天下犹弃敝”,在隐居的海滨能与逃过一劫的父亲相处共对,“终身然,乐而忘天下”,这完全吻合孟子竭力塑造的舜的形象:“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孟子·万章上》)
但遗憾的是,倘若文本接受主体并非是以捍卫儒家传统为己任之人,他们不可避免会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去评判舜的作为。作为这件虚构但意义深远的官司的旁观者,部分读者固然可以从舜为人子的立场去同情理解甚至歌颂赞美舜的“窃负而逃”,但肯定有更多的读者会从被害人亲属的角度去批判舜的徇私枉法,蔑视公义。根据文本,读者完全有权利合理设想,当舜在实行“窃负而逃”之前,他并未公告天下自己放弃了天子之位,这无形中会导致看管瞽瞍的狱卒放松对舜的警惕,因为天子既是天下公义的象征,也是天下公义的维护者,这就有利于舜实施“窃负而逃”。再有,当狱卒发现了舜的“劫狱”,在追捕的过程中,由于顾虑舜的天子身份,其决策行动难免受到影响,这无形中加大了舜背负父亲逃到法网之外隐居起来的成功率,这些都不能不说是舜变相的以权谋私,即便他并非故意。所以这件公案被刘清平、邓晓芒等学者判为“腐败”案例,[4-5]虽然让以尧舜禹为圣王生活了几千年的中国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但却揭示了儒家伦理的真相。
当孟子为舜设计“窃负而逃”的时候,他可能只考虑作为人子的舜,在个人权位与父亲生命之间的取舍。但是,此案的核心冲突不是被告父子利益之间的冲突,而是原告正当利益与被告不正当利益之间的冲突。孟子没有深入考虑到,舜即便放弃了受百姓爱戴而得来的天子之位,他依然是被儒家树立为人伦典范的圣人;即便舜连“圣人”都不愿去做,他还是对天下兴亡负有责任的“匹夫”。当舜主动劫狱帮助父亲逃避惩罚时,他就在选择“亲亲”的同时放弃了“仁民”,在拥抱“私恩”的同时背弃了“公义”。当舜“窃负而逃”,他所“窃走”的不仅是一个理应偿命的要犯,还是一个“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大同世界;当舜“乐而忘天下”,被他所“遗忘”的不仅是被害者亲属激愤的眼泪和痛苦,还有身为天子“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的神圣职责,身为君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律令、身为凡夫“杀人偿命,天经地义”的是非判断。
庆幸的是,作为历史人物的舜并没有真的遭遇父亲杀人的道德困境,当然也无需背负“窃负而逃”的罪恶。但是,令人痛心的是,作为儒家亚圣的孟子为假设置身于父亲杀人困境的舜选择了“窃负而逃”的腐败行为,并且在字里行间讴歌了这种行为。培根说:“一桩误判比多桩犯罪还更有害,因犯罪只是搅浑河水,可误判却是搅浑水源。”[6]孟子不公正的道德评判,却在无形中鼓励了后世千千万万人以孝为名对公义进行肆意践踏。此案的意义在于,孟子在理论假设的“亲亲”与“仁民”之间的尖锐冲突中,丢弃了“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这一重大道德戒律,在“门外之治”依然“恩掩义”而非“义断恩”。
综上,“子为父隐”“窃负而逃”这两件公案,被告与原告之间的关系是没有血缘关系的路人关系,理应属于“门外之治”。但是,由于其理论背景是农耕经济、家族社会,“儒家思想中的一大部分是这种社会制度的理性论证,也就是它的理论表现”,[7]这就必然导致了儒家伦理过分强调血缘亲情。“百行孝为先”的行为逻辑致使从孔孟开始对“私恩”的维护始终重于对“公义”的伸张,由此暴露出儒家伦理的狭隘(家族利益至上)与矛盾(行仁的起点背离关键节点)。这是我们今天继承、重构儒家伦理时必须重视的问题。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孙希旦.礼记集解(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4]邓晓芒.儒家伦理新评判[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
[5]刘清平.忠孝与仁义[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6]培根.曹明伦.论法官的职责[A].培根随笔集[C].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7]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张 庆
The Deep Contradiction in Confucian Ethics of Loving Families or All People
TANG Tao
(Qujing Normal University,Qujing 655011,China)
Confucian ethic takes filial piety as the start point of benevolence and takes the union of the virtue and nature as the end of practicing benevolence,in which loving strangers is the key point. When there is contradiction the moral teachings that love is over justice for family controversies and justice is over love for public controversies. From the cases in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we can see the balance of “private kindness” and “justice” have biased. Filial piety seems to be prior to justice and rationality,which exposes parochialism and contradiction in Confucian ethic.
Confucian ethics;private kindness; public righteousness;contradiction
2016-03-01
唐 桃(1978-),女,广西梧州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1004—5856(2016)11—0082—04
I207.6
A
10.3969/j.issn.1004-5856.2016.11.019
——以朱熹对《论语》“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诠释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