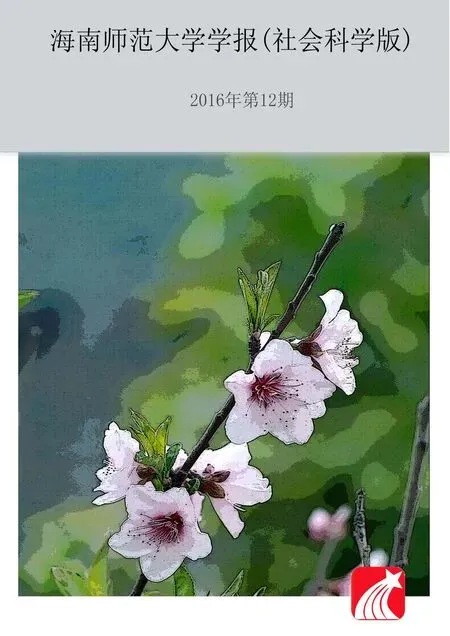法·法治·合法性
——韩非子政治思想的现代诠释
陈 鑫
(1. 复旦大学 哲学博士后流动站, 上海 200433;2. 海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海南 海口 571158)
法·法治·合法性
——韩非子政治思想的现代诠释
陈 鑫
(1. 复旦大学 哲学博士后流动站, 上海 200433;2. 海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海南 海口 571158)
从“法”、“法治”、“合法性”这三个相互关联又逐层递进的概念出发,重新审视和思考韩非子政治思想的意义和价值。韩非子的“法”只在极为狭窄的意义上可以和现代政治学中的“法律”重合。韩非子政治思想中“法制”有余,而“法治”缺席,前者损害后者。韩非子对政治合法性问题也未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因此,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对于我们时代的意义主要在于批判和反思,而非直接运用。
韩非子;法;法治;合法性;政治思想
如果我们不澄清概念在语境中的含义,思想的混乱将永无止境。比如,韩非子究竟是法治的建构者还是解构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在何种意义上理解和使用“法治”这个概念,也有赖于我们是否以及如何对“法治”与“法制”作出区分。在本文中,我们将尝试围绕政治学中三个相互关联、逐层递进的概念——“法”、“法治”、“合法性”——思考韩非子政治思想的原初意义和现代价值。其间会有中西古今若干观念相碰撞,我们不妨将其视为思想在纵横交错的道路之间的自身展开。
一
思考“法”的意义不可脱离人的行为以及在这些行为中显示出来的人性。在多数情况下,道德规定了人类行为的上限,其基本句式是:你应当……法律规定了人类行为的下限,其基本句式是:你不可……“应当”和“不可”(即“禁止”)这两个道义逻辑模态词分别指向善恶两端。如果人性本善且人持续行善,则法律无必要;如果人性本恶且人持续作恶,则道德成梦幻。现实地看,人性是复杂的,善恶相混,且善与恶的比重不均。
韩非子身处“争于气力”之乱世, 《韩非子·五蠹》:“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①[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45页。以下凡引《韩非子》原文皆出自此书,仅以夹注形式标示篇名。春秋以后封建多国体系走向大一统集权帝国的趋势日渐明显。韩非子更多地从历史趋势和现实处境来思考人性与政治。作为荀子的弟子,他既不相信他老师的“化性起伪”可引人向善,也不相信孔孟“仁政”可以息乱止争,而是以法家式极端的功利主义取代了儒家的理想主义。他从对各种现实的社会现象的观察出发,指出趋利避害的自保本能先于为善去恶的道德本能。
且万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适子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爱则亲,不爱则疏。(《韩非子·备内》)
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子父至亲也,而或谯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夫妻虽是至爱,但毕竟没有血缘关系意义上的亲情,因此后妃和夫人都希望君主早死;而作为骨肉至亲的父母和子女,若养育或供养不力,也会彼此怨恨。韩非子撕去了笼罩在人性之上温情脉脉的面纱,让基于其经验观察的某些赤裸真相直接暴露出来:即使在至亲至爱之间也没有什么善意可言,何况他人?而真正支配人与人之间情感和关系的无非是一个“利”字。
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韩非子·备内》)
无论希望人富贵的车匠,还是希望人短命的棺材匠,其目光都聚焦于一己之私利。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用韩非子的话说就是“皆挟自为心”(《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如果说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荀子主张“人性本恶”,韩非子则主张“人性本私”,这恰似一个“正题——反题——合题”的历史与逻辑演化过程。
作为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的韩非子把能否“去私就公”与国家的治乱和强弱联系起来:“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故公私有分。”(《韩非子·饰邪第》)“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韩非子·有度》)在《二柄》篇中,韩非子进一步明确地说:君主只要操德刑“二柄”,利用人臣好利畏威的心理赏功罚罪,就可以扬公抑私,实现治安。这两个权柄若落入人臣手中,君主则会陷入“危亡”境地。君臣之间,以利相合,以权相博,其关系仿佛霍布斯世界里“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制人而不制于人”(《孙子兵法·虚实篇》)是君主驾驭人臣的基本法则。
因此,韩非子对“法”的含义的界定是以公私之辨、赏罚之道为基础的。“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韩非子·定法》)韩非子在此揭示了“法”的三大特征:一是“法”的公开性,“法”是政府明文公布的规则和命令;二是“法”的强制性,“法”必须被执行且深入民心;三是“法”的操作性,“法”在现实的赏罚行为中实现自身:守法者赏,犯法者罚。
韩非子的“法”在何种程度上和范围中可以与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法律”的含义相合呢?我们不妨将其与西方的法律概念作些比较。
最宽泛意义上的“法”(法律),孟德斯鸠认为是“源于事物本性的必然关系”,上帝、物质界、动物、神灵、人类等都有其法律。其中,就人类法律而言,先于一切规则的、在社会形成之前的法是“自然法”,包括和平、填饱肚子、两性亲近、共同生活等;而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状态促进了“人为法”的产生,包括调节公民间关系的公民法(民法)、调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政治法(即公法,特别是宪法)和调节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万民法(国际法)。*[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9-16页。
在自然法方面,西塞罗曾有如下论述:
最博学的人们决定从法律开始,而且如果根据他们的界定——法律是植根于自然的、指挥应然行为并禁止相反行为的最高理性(reason),那么看来他们是正确的。这一理性,当它在人类的意识中牢固确定并完全展开后,就是法律。因此,他们认为法律就是智识,其自然功能就是指挥(command)正确行为并禁止错误行为。……那么正义的来源就应在法律中发现,因为法律是一种自然力;它是聪明人的理智和理性,是衡量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但在确定正义是什么的时候,让我们从最高的法律开始,这种法律的产生远远早于曾存在过的成文法和任何曾建立的国家。*[古罗马]西塞罗:《国家篇 法律篇》,沈叔平、苏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58-159页。
对于习惯法,古罗马著名法学家查士丁尼有一个经典定义:“古老的习惯经人们加以沿用的同意而获得效力,就等于法律。”*[古罗马]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法学阶梯》,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1页。
经过简单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从范围上看,韩非子所谈的“法”大致相当于孟德斯鸠所说的公法、特别是宪法和刑法(“刑罚必于民心”);从形式上看,韩非子所谈的“法”属于成文法(“宪令著于官府”),对于法的起源,韩非子止步于官府制定,而未上溯到更为本源的自然法;从内容上看,因为自然法和习惯法维度的缺失,西塞罗、孟德斯鸠所谈法律之理性原则、正义标准、习惯渊源等,在韩非子那里都付诸阙如。所以,韩非子所说的“法”只有在成文法和公法的交集上与“法律”一词相重合,纵然其与“术”和“势”紧密配合,并宣称以“道”和“理”作为根据,也不过是君主欲望和意志的现成存在,缺乏终极视域的构成性。因此,韩非子虽与道家思想颇有渊源,但终究是“得人势而未得天势”。*参看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第264-268页。
二
“法治”不同于“法制”,“法治”是rule of law,即“依法治国”;“法制”是rule by law,即“以法治国”。在“法治”中,法律是统治的原则,其基础是权利(right);在“法制”中,法律是统治的手段,其基础是权力(power)。英国法学家戴西在《宪法研究导论》中曾提出法治的三个特征:1.法律平等地适用于所有社会成员,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2.除非经由法院判定确实违反了法律,任何人不得受到惩罚;3.法院在判决时独立于且不受制于政治干涉或控制。*[英]戴西:《宪法研究导论》,转引自[英]杰弗里·托马斯:《政治哲学导论》,顾肃,刘雪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9-130页。
从范围上看,法律无差别地普遍适用于所有人;从程序上看,司法权只能由法院行使;从原则上看,司法必须独立。法治的特征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就是法律至上,从消极的意义上说就是反对一切特权凌驾于法律之上。
《韩非子》文本中无一处使用过“法治”或“依法治国”,而用到“法制”一词者凡有四处:
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义也。(《韩非子·饰邪》)
释仪的而妄发,虽中小不巧;释法制而妄怒,虽杀戮而奸人不恐。(《韩非子·用人》)
不弃者,吏有奸也;仁人者,公财损也;君子者,民难使也;有行者,法制毁也;有侠者,官职旷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刚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誉,人主之大败也。(《韩非子·八说》)
行义示则主威分,慈仁听则法制毁。(《韩非子·八经》)
提及“以法治国”者凡一处:
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辟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韩非子·有度》)
由以上五条引文可见:韩非子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君主如何利用法律(即上文所说“公法”)驾驭臣民和巩固权力,其主要思路是“法制”之操作,而无关乎“法治”之精神。君主是法律的操纵者,他自身凌驾于法律之上,原则上比司法机构更有资格进行审判,即使绝大部分案件由司法机构来审判也不可能摆脱来自君主的政治干涉和控制,全面地违背了上文所引述的法治三原则。其中,“有行者,法制毁也……匹夫之私誉,人主之大败也”、“行义示则主威分,慈仁听则法制毁”两段更是完全将个人的德性与法律对立起来,其实质是把人民的权利与君主的权力看作此消彼长而非和谐一致的关系。
众所周知,“法治”或“依法治国”的本义是限制国家(政府)的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利(自由权、生命权、财产权等)。但是,在韩非子描绘的政治图景中,“依法治国”之萌芽未显,“以法治民”之大势已彰。法律是手段,“强国”是目的:“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韩非子·有度》)由于韩非子的理想国家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型的,君主本人就是国家主权的化身——“朕即国家”,所以“强国”与强化君主权力是一致的。又由于他预设了国与民即君主与臣民以及集权政府与民间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因此,若想“强国”,必须通过严刑峻法来“弱民”:“峻法,所以凌过游外私也;严刑,所以遂令惩下也。”(《韩非子·有度》)“强国弱民”是典型的法家式政治理念,从商鞅到韩非直至李斯,一脉相承。*《商君书·弱民》篇:“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21页。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后来采用了法家统治术的秦制时代:专制君主与酷吏合力向底层汲取资源,逼迫散沙社会中的原子化个人将源自封建时代的德性抛掷于蛮荒之外。所有人(除了君主)之间都是平等的,但不是法治下的人格平等,而是严刑峻法下的奴隶式平等。本应为“法治”奠基的“法制”在法家那里成了破坏“法治”的强大力量。所谓“外儒内法”揭示了法家虽然不像儒家那样被安放在历史舞台的醒目位置,但其事实上长期发挥着结构性的深层支配作用,这构成了我们传统文化缺乏法治传统的一大病根,正如当代著名历史学者刘仲敬所说:“法家的本土性主要体现于酷吏和马基雅维利主义,这种精神足以摧毁任何法条主义的藩篱。”*刘仲敬:《守先待后:思想、格局与传统》,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9页。
三
或许,在“法”的含义偏狭、“法治”精神匮乏的法家统治中寻找政治的“合法性”,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马基雅维利”式的问题。
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不完全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合法”,后者指立法合乎程序或公民守法,前者指政治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衡量一个政权是否具有“合法性”,要看民众对此政权是否普遍支持与认同。*燕继荣:《政治学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2-136页。马克斯·韦伯从社会学角度探讨了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认为人们之所以愿意接受某种政治体系的支配,是因为他们拥有这种政治体系“有权统治的信念”,即相信其“权威”,权力转化为权威就是“合法化”过程。政治合法性包括“传统型权威”、“克里斯玛(charisma,魅力)型权威”和“合理-合法型权威“三种类型。“传统型权威”的合法性源自被神圣化的历史和已经规则化的习俗,“克里斯玛型权威”的合法性源自统治者个人的人格力量和魅力,“合理-合法型权威”的合法性源自界定清晰的法律规则。其中,“合理-合法型权威”是现代政治合法性的主要形态。*[英]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张立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0-132页。
法家素尚变革,韩非子也从未把历史和习俗等“传统”看作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他主张“世异则事异”,一切传统都有其特定适用范围,超出此范围则失效,比如“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韩非子·五蠹》)。因此,他把宣传先王仁义之道(传统型合法性)的学者视为一种“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韩非子·五蠹》)的国家蠹虫。
对于统治者个人魅力,韩非子认为是无足轻重的。他引用慎子的话“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蚓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韩非子·难势》),说明治乱兴衰与领袖个人的德性和能力关系不大,关键在于统治者能够“处势”:“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韩非子·难势》)
如前文所述,韩非子的“法”从来就不是用来限制君权的,它只在限制“吏”(治人而治于君者)的行为方面有效,而民众只需向吏学习即可:“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在服从法律的意义上具有“合法律性”,而这法律本身的正当性是未经批判和反思的。这里看不出对法律规则的尊重,只有表面上对法律、实际上对权力的单方面服从。
可见,韩非子唯一能提供给民众承认统治合法性的理由就是君主拥有权势(“处势”),专制君主维持其权势的工具只能是国家暴力机器,“当今争于气力”即其明证,而暴力的合法性是最弱的。从政治学角度看,暴力保障安全,权力维持秩序,权威实现正义。从权威到权力再到暴力,合法性递减。
可见,在如何使一个政权获得“合法性”问题上,具有高度“唯暴力论”倾向的韩非子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
四
法家虽以“法”名世,实则最缺乏“法治”精神。这一结论由上文可证:法家之“法”含义偏狭,法律仅为治民(而非治国)工具,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统治最缺乏政治合法性。
韩非子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集商鞅之“法”、申不害之“术”、慎到之“势”于一身,且颇有所损益。他认为君主若“抱法”、“用术”、“处势”则“国治”,却忽略了他老师荀子的教导:“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清]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44页。最信奉法家的秦朝貌似强大,实则羸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上文已谈到,除了韩非子与大儒荀子有师承关系外,法家与道家思想也颇有渊源,韩非子本人的《解老》《喻老》也堪称诠释老子思想的杰作。但是,在政治统治层面,法家从未把“道”作为治理国家的终极根据,甚至从未曾将其列入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韩非子可谓得于术而失于道,得于法而失于德,得于势而失于理。《庄子·天道》篇的一段评论可谓切中其弊:
骤而语形名,不知其本也;骤而语赏罚,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说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骤而语形名赏罚,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谓辩士,一曲之人也。*[清]郭庆藩:《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71页。
以“辩士,一曲之人”的身份活跃在战国至秦朝历史舞台上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韩非、李斯等都不得善终,他们有一个共性,即过于相信自己的理性设计,而毫不相信天道、神明、先王、往圣等一切神圣性或传统性的东西,“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史记·项羽本纪》),以致对格局和路径做出误判,对自身的命运也无法正确理解和把握。
今日不同于往昔,公民不同于臣民:臣民只尽义务,没有也不要求权利,公民则要求权利与义务对等。“依法治国”所治对象首先且主要是国家(政府),也就是说,首先要求政府的公共权力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之内来运作,不得阑入社会和私人领域。这样才可以切实地保障人民的各项权利。人民有了权利之后,才可以被判定是否守法。现代社会中,人民与政府不应是统治-被统治的单向控制关系,而应是自治-共治的双向互动关系。这些是两千多年以前的韩非子所无法预料和理解的。我们当然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强求古人,也切不可试图用古方来医治今病。
然而,韩非子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政治思想资源——虽然其中大多数是供批判和反思,而非现成可用的。
今之学术奠基于古之思想。学术或时有损益,思想之光永恒。
(责任编辑:胡素萍)
Law, Rule of Law, Legitimacy—a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Han Feizi’s Political Thought
CHEN Xin
(1.Post-doctoralMobileStationofPhilosophy,Fudan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 2.SchoolofMarxism,HainanNormalUniversity,Haikou571158,China)
This paper reexamines and reflects on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Han Feizi’s political thought based on three related and progressive concepts—“law”, “rule of law” and “legitimacy”. As is discovered, Han Feizi’s “law” is coincidental with the “law” of modern politics in a narrow sense, for in Han Feizi’s political thought “rule by law” is overemphasized while “rule of law” is underemphasized, thereby resulting in the damage of the former to the latter. Moreover, Han Feizi has not given a convincing reply to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Therefore, the significance of Han Feizi's political thought lies in its criticism and reflection rather than its direct application in the modern era.
Han Feizi; law;rule of law; legitimacy; politics
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唯识学与现象学比较”(项目编号:HNSK(QN)15-97)
2016-11-11
陈鑫(1982-),男,内蒙古海拉尔人,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在站博士后,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
B226.5
A
1674-5310(2016)-12-009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