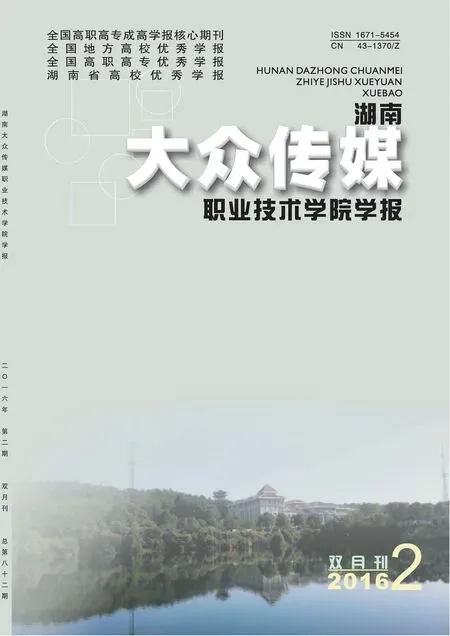从《归来》《黄金时代》看2014年中国文艺片回暖现象
陈玉
(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扬州225002)
从《归来》《黄金时代》看2014年中国文艺片回暖现象
陈玉
(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扬州225002)
在2014年的中国电影市场,一向冷门的文艺片呈现出不同的气象。《归来》和《黄金时代》这两部影片皆为影视与文学的成功联姻,在叙述模式上展现出传统与创新的各领风骚,影片主题深刻而多元,且放低姿态,高调宣传,一反常态地引起社会热议,甚至宣示了文艺片元年的到来。
文艺片;《归来》;《黄金时代》
根据2015年1月6日艺恩咨询发布的《中国电影市场影响力研究报告》,2014年中国电影市场文艺片的数量稳中有升。所谓文艺片,在概念上是参照商业片的类型而言。如果说商业片力图将观众引入他们营造的极具戏剧性的虚构世界,文艺片仅仅是尝试促使观众去联想平凡的生活,但它又不同于欧洲的艺术电影及美国的独立电影。通俗而言,区别于商业片的、具有人文关怀和现实色彩、暗示道德内涵与美学期许且又别具风格的电影,我们姑且将其定义为“文艺片”。独特的影片风格使得文艺片的境遇一直尴尬丛生。2014年《归来》和《黄金时代》两部影片以“文艺大片”的姿态横空出世,象征着中国文艺片的回暖。
一、影视与文学的成功联姻
文艺片,单纯从字面去解读就是“文学与影视的综合”。关于影视与文学的生存状态,丹尼尔·贝尔曾在“文化”的维度下予以判定:“我相信,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1]而将文学和影视明确界定为小说和电影的表现形式时,对于二者的比较又有了更为清晰的说明。安德烈·勒文孙说:“在电影里,人们从形象中获得思想;在文学里,人们从思想中获得形象。”[2]爱德华·茂莱则补充道:“电影的再现事物表象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然而,在需要深入人物的复杂心灵时,电影就远远不如意识流小说家施展自如了。”[2]时过境迁,在视觉文化盛行的今天,依赖于文学著作而生的影视作品早已屡见不鲜。虽然文学提供平面化、想象性的语言,而影视创造立体化、视听性的影像,二者的转译存在难度,但它们在描写叙说上都有着不限时空的自由性。文学中抽象的艺术描写给予影视具象化表现以足够空间,继而影视将以视听形式展现的艺术真实直观自然地奉献在观众面前。国内外获奖影片也大多脱胎于成熟的文学作品。实践证明,影视与文学联姻是影视创作的一条成功道路。
影片《归来》就是此种联姻的产物,它改编自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无论是近年来的《第九个寡妇》、《金陵十三钗》、《小姨多鹤》,还是早年间享有国际殊荣的《天浴》、《少女小渔》,都表明严歌苓的作品在影视圈里具有极强的适应性和可塑性。张艺谋早前就曾毫不讳言自己对小说的依赖:“文学是所有创作的母体,只有文学的繁荣才有各个门类艺术的繁荣。不是我们依赖文学,而是文学是整个的‘基座'。”[3]此次张艺谋延续一贯风格,采用经过市场验证过的作家风格和作品题材,已然给影片《归来》本身预先上了一道保险。其次,《陆犯焉识》这部作品本身有着极大的时空容量,从动荡不安的解放前到物是人非的文革后,从荒芜苍凉的大西北到车水马龙的大上海,张艺谋机智地将这部全景史诗改成一幕话剧,只截取原著后30页的内容,围绕“归来”将大时代中一个知识分子跌宕起伏的际遇转换成平凡夫妻相望相守的爱情。“沸腾年代、生离死别、旷世之恋”,就是导演从文学文本中提炼的要点。最后在影视和文学的转译问题上,导演由小处着手,力求意蕴无穷。小说最后一章曾这样描述焉识和女儿对婉瑜独特的怀缅:“他们是通过婉瑜亲密起来的。是通过回忆叙述婉瑜,跟对方谈得无比投机的。也是通过爱婉瑜,他们重新爱起对方来。”[4]转换到影片中,导演将其置换成焉识不断地为婉瑜读信,不断地陪婉瑜去车站等“自己”。“爱婉瑜”和“等焉识”,此时在艺术效果和情绪感染上是一致的。
反观《黄金时代》,则采取了另外一种联姻方式,即用影片去展现文学创作者的生存境遇及担负的时代责任。据说剧本在最初构思的时候是写萧红、丁玲、张爱玲三位文学女性的,后来考虑到审查难度,只留下一位萧红。导演许鞍华看中编剧李樯的《黄金时代》,主要是因为她对这位女作家由衷的喜爱。既然有着这样诚挚的初心,影片自然力求每一句旁白和台词、每一处场景和情节都是有史料出处的,以保证人物形象的真实性。鲁迅说着《鲁迅文集》,萧红念着《萧红文集》,部分影评人将它定义成“被史料压垮的论文”,其实作为一部传记电影来说,这至少担得上“忠于史料、治学严谨”了。影片里有这样一段:日子过得捉襟见肘的二萧某日去小馆子打牙祭,酒足饭饱后回家的路上,萧红调皮地翘起脚叫了句“鞋带断啦”。于是萧军蹲下来,捡了块玻璃把自己的鞋带割断,给萧红系上。两个人憨憨地笑着,挽着胳膊大摇大摆地消失在冬季哈尔滨的夜幕中。此时屏幕上出现这样一段文字:“电灯照耀着满城的人家,钞票带在我的衣袋里。就这样,两个人理直气壮地走在街上。”电灯照耀的希望,钞票在身的踏实,爱人相伴年轻气盛的无惧无畏,文学的内在张力在这样的影视场景里得到尽情展露。
可见不管采用何种联姻方式,两部影片都充分展示了文艺片中“文”的特点,攫取了“文”的精华,且以这样的准文艺片形式立足于市场,吸引着观众。
二、叙述模式传统与创新的各领风骚
两部影片同以文艺片自居,却在叙述模式上大相径庭,各有所取。
《归来》在剧情架构上被导演裁剪为更易掌控的家庭伦理片,父亲、母亲和女儿是这个家最为基本的三个元素,剧情重点也放置在父亲归来、母亲失忆的时间节点。几十年的风雨浮沉浓缩在一个小家来呈现。影片包含了大量的近景镜头和特写镜头。如丹丹质问母亲为何要去见逃跑的父亲,以及后来被母亲拒之门外的丹丹向父亲倾诉自己的痛苦。这两个近景镜头放大了丹丹此时的面部神情,使观众一下子逼近现场,直面女儿此时的困惑与焦虑,对其无奈而又委屈的心境感同身受。而代表母亲失约的那把空椅子,也通过三次的特写镜头不断充实了导演想要表述的话语:母亲抗拒着背叛的女儿,女儿委屈着母亲的执拗,而哄闹的现实暗含这残忍才仅仅是个开始,构成了信息的复调性。[5]传统的叙述模式为导演熟稔地运用其中,赋予老套简单的故事更多经典的韵味。
相比之下,《黄金时代》的叙述模式难得一见。影片开头便是萧红在一种遗像式的镜头下自述其短暂的一生。而后近三个小时的时间里,相关人物轮番上阵,在演绎过程中却又时常出离情境,直面镜头述说心声。萧红自己、舒群与罗烽、聂绀弩等都是影片旁白的叙说主体,话语权几度易手。特别是对待二萧分手的问题上,导演借聂绀弩之口转述了几位当事人不同的说法,以期公正客观。这样的叙说方式产生了一种间离效果,就像一个个注脚,不断地在男女恩怨、爱恨情愁的故事主线之外,为萧红的故事赋予历史的深刻性。[6]东北作家群以及左翼文坛的先锋们处于其中却又出离在外,以冷峻疏离的目光审视彼时的自己,从而达到独特的陌生化效果。此外,影片在以尽量客观的多角度展现萧红一生的同时,亦穿插萧红自己笔下描绘的人生,两套语言系统互为补充,使得萧红的人物形象和心理状态逐步趋于丰满。导演大胆运用此种叙述形式,成功地将《黄金时代》与一般故事类影片区分开来,具有极强的先锋意义和实验价值。
除去不同的叙述模式,二者都同样成功地利用气氛营造及细节铺陈来辅助影片内容的表述。《归来》以灰白的暗色调为主,雨夜和冬雪的背景极具留白的写意色彩。影片末尾焉识和婉瑜宛如雕塑般的等待,使得人情的纯粹平淡及时代的压抑悲怆直面而来。《黄金时代》则在细节上尤为用心,哈尔滨的大水、鲁迅家的万年青、武汉文协的过道等都在影片中得到呈现。二萧从东北撤离时,萧红凝视着象征二人同甘共苦的空脸盆,不由得眼中含泪,一个悲苦女作家的敏感顿时跃然纸上。诚如普多夫金所言:“只有在银幕上出现比较深刻含蓄的细节,电影才能高度地把其外在表现威力表现出来。”[7]叙述手法上的传统与创新,有着“欲说还休”或“直抒胸臆”的表达效果,都旨在为观众构建一个真实自然的生活化情景,以期强化观众的观影感受。
三、影片主题的深刻性和多元化
作为国内首部以4k技术展现的文艺片,张艺谋在宣传伊始就号召观众去电影院看巩俐和陈道明如何演绎一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删去了原著中多情焉识早年对于婉瑜的忽视以及心安理得的出轨,影片中的焉识成了专情有礼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个符合中国传统认知的理想男性形象,和失忆的贤妻一起,诠释了“相濡以沫、携手白头”的婚姻境界。观众们感慨于这个“归来、等待、相守”的爱情故事,但事实上,“爱情”的定位仅仅是《归来》的前奏。
原著中的男一号到了影片中其实已经退居二线。影片连贯展现的,其实是婉瑜和丹丹的人生遭际。因为一个早已消逝在记忆中的逃犯父亲,丹丹由天之骄女“吴清华”变成了蜗居于集体宿舍的工厂女工。她做了当下最符合其阶级立场和时代要求的选择,却遭到母亲的拒绝和组织的抛弃。在生活洪流里风尘仆仆的她,甚至还来不及排遣自己际遇的委屈和人生的失落,就要怀揣对父母的愧疚和不忍,默默帮助归来的父亲去唤醒母亲的情感记忆。丹丹的身上隐含了中国传统伦理世界的忠孝矛盾,她对时代的忠诚对立着她对家庭的背叛,她对组织的信任换取的是现实对她的欺骗,矛盾的现实映射出时代的荒诞,而她自己显然无法消化这样的苦楚。直至时代的狂热退去和父亲的归来,丹丹才得以认真反思父母人生的艰难,完成自我良心的救赎。而绝对女主角冯婉瑜,温顺沉静的背后却有着超乎寻常的执拗。20年的时光里她竭尽全力维护一个缺失的家庭,忍受方师傅之流的欺凌,一心等待丈夫的归来。这样的隐忍在焉识逃跑后变成了不管不顾的疯狂,又在疯狂过后演变为固执的等待。贯穿这一转变的,除了婉瑜对焉识的爱,还有一份悔意。她忏悔着自己对忠贞爱情的失守,忏悔着女儿对父亲的背叛。恰好此时“失忆”拯救了她,她终于可以用一颗真挚纯粹的心去等待焉识,去向焉识表明她至死不渝的爱意。
值得玩味的是,《归来》中的爱情和亲情似乎被放置在了对立面。平反后回城,陆焉识在女儿局促的集体宿舍里只想着回家;回到家中,满心满眼挂念的也都是太过爱他而至失忆的婉瑜。对于那个因稚嫩而被现实愚弄的女儿,他沉默良久,讷讷难言。甚至在丹丹被婉瑜拒之门外、将满腹委屈尽数发泄时,他也仅仅是希望丹丹可以体谅母亲的病况,便再无二话。而对于婉瑜来说,支持女儿跳舞是顺从丈夫的意愿,拒绝母女相认是由于女儿对丈夫的背叛。影片末段,丹丹借了一袭红衣在家中为父母跳“吴清华”,女儿的内疚在父母欣赏的目光中得到安慰,曾经的过错在母亲久违的关切中获得宽恕。这种和解,也只是因为焉识在信里原谅了丹丹,婉瑜才尽释前嫌,不再苛责。对于焉识和婉瑜而言,为人夫为人妻的觉醒压倒了为人父母的责任。时代纷乱,本该奢侈而谈的男女情爱竟然越过了血脉相连的骨肉亲情,而且是父母对子女的反向情感遗弃,这在中国传统的伦理认知中确实少见。这样一个隐含的设置,可以视作对伟大爱情的称颂,也可以看成在极限环境下人对于自我本体的情感认知和反思,谁说血缘相亲就一定高于荷尔蒙的吸引呢?何况在那样疯狂的年代,一切反常规的情感表露都可视作是对时代的反讽和嘲弄。所以在《归来》中,爱情只是引子,亲情是血肉,忏悔和宽恕是筋骨。至于时代创伤下普通人的挣扎彷徨、认知反思,特别是个人本体意识的情感觉醒,才是值得每个人体悟的气韵。
再看《黄金时代》,上映前期发布了一组态度版海报,以“想……,就……,这是……的时代,一切都是自由的”的“自由体”尽情颂扬影片描绘的“自由”。片方的宣传文案曾这样描述这组海报:“一张张鲜活坚毅的面孔、一句句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的话语,展现出片中角色那种自由自在、无惧一切的态度,也呼应了‘一切都是自由的'的电影主题。”那么影片真的展现出时代的自由了吗?也不尽然。也许是为了规避旧式评判标准对萧红的偏见,影片并未对彼时风云诡谲的大时代有宏大的描述,反而是在一些细枝末节上用尽笔墨。
当横眉冷对的鲁迅都成了随性谈论衣着的长者时,世俗的琐屑消解了时代的冷酷,为萧红的处境增添了几抹温情。童年的萧红依赖着年迈的祖父,藏身在桃花源般的后花园。长大后的她几乎一生都在追寻这种年幼时的安全感和自由。可自由是需要资本的。婚姻的自由、爱情的自由、写作的自由,陆舜哲、汪恩甲、萧军都没能给她。片中的萧红几次谈到自己对政治的不理解,仅仅希望过着正常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能有个安静的地方写作。这些端木蕻良曾经给过她希望,却又让她在巨大的不甘中离开人世。肉体上的萧红需要自由,但是这自由被经济和男人所左右;精神上的萧红需要自由,但她的凭感觉书写并不能满足社会主流的需要。影片主创所谈论的“自由”,萧红始终没有得到。她的追求被巨大的现实压力所压垮、所解构、所边缘化。影片中武汉沦陷,萧红在枪林弹雨的废墟中寻求安身之所。镜头一转,睡在文协阳台上的她主动请大家去饮冰室吃冰。前面是大时代的动荡,后面是小时代的愉悦。看似矛盾的背后,是生活的细碎掩盖了战乱的不安,是小时代解构了大时代,最终还是落在了世俗生活和生存的层面。
而在生存的角度上,巧合的是,该片中的萧红也遭遇了父母与子女间的情感遗弃。少年的她是孤独的,所以她背弃了父母和情人一走了之。事败后父亲出于颜面将她遣回,是她自己再次抛弃了原生家庭并且再无回头。世道艰难,她和两位男性育有两子,一个出生后看都不看一眼直接抱走,一个出生几日后意外夭折。身为子女的萧红抛弃了父母,身为父母的萧红也抛弃了子女。世间情意万种她罔顾亲情,人生束缚良多她只要自由,这样的孤绝之态在文艺创作中并不多见。但细思之,她的孤绝也可理解。父亲的冷淡促使她一次次投入爱人的怀抱,生活的困窘慌乱让她下意识推开了怀里的孩子。在附属与个体间徘徊的萧红屡屡受挫,变成了既期盼依靠又追求自由的矛盾体。这种对于自我认知的矛盾,直接导致她对于生命延续体的排斥,孩子就成了意识里的累赘。找寻不到自我的人,就伸不到人生的源头,也触不到生命的延续。孤零零的人如果抓不住立足的根须,就只能任时代的风潮摧残以至瘫落。所以说,《黄金时代》的主题并未停留在“追求自由”上,准确来说,它的主题是“追求自由而不得”,氤氲着个体生命无所依傍的悲凉感。绚烂的作家群体也只是些背景和佐证,影片要凸显的,是在“民国范儿”里,“让生命感到无助、凄惶的那一面”。[6]
大时代的背景是影片主题得以展开的依托。两部影片都将目光投射到存在其中的小人物或小时代,加之文艺片特有的人文关怀和现实色彩,使得二者的主题有了拓展的可能性。先以“爱情”与“自由”去契合观众的期待视野,再让观众自己去感受个体生命的情感觉醒和人生追求,体味影片主题的深刻性和多元化,那么观影过程中的惊喜才能得以实现。
四、放低姿态,高调宣传
区别于以往文艺片的“养在深闺人未识”,《归来》和《黄金时代》在宣传上突破了文艺片惯有的文化优越感,放低姿态,一路高歌猛进。在演员阵容方面,两部影片都采取“当红小生+老戏骨”的模式,这种明星效应一定程度上为影片宣传减轻了压力。
落实到具体的宣传策略,《归来》继承了文艺片一贯的“由国外走向国内”的路线。虽然没有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但《归来》获得了非竞赛单元展映的机会。据说在法国首映时,观众座无虚席,泪洒涟涟,全场甚至起立鼓掌致敬近十分钟。于是戛纳成了片方和媒体借势宣传的高起点,连“张艺谋在电影节上首次将女儿张末介绍给巩俐”的私人事件都成了影片宣传的踏板。与此同时,片方依靠导演的私人情谊,邀请到数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名人诉说观影感受。李安认为影片结尾“平静内敛”,全片的味道在这里慢慢显现;斯皮尔伯格和莫言都在观影过程留下了感动的泪水,认为其有真情、有深度。对于一部即将上映的文艺片,这几位大腕的评价俨然可视作影片质量的保证。此外,片方选定新鲜出炉的第二季《我是歌手》“歌王”韩磊来演唱主题推广曲,再加上传统的电视、纸媒宣传,《归来》成功在数部好莱坞大片中突围,维持着较高的话题热度。
和《归来》相比,《黄金时代》的宣传模式更为“任性”一些。一般的文艺片会被包装成某种类型片,让观众建立起对此种类型片的预期,如《归来》就从“文艺片”变成了“爱情片”。但是主人公“萧红”能构建的观影预期毕竟有限,宣传团队于是另辟蹊径。“‘我们没有强化类型这种概念,因为我们把它包装成一种心理需求。'程育海解释,就像电影宣传语:一切都是自由的。‘人对自由的渴望和对非凡生活的需要,这是中国当下所有人的心理追求,我只是让《黄金时代》往心理需求来靠'。”[8]态度版海报就是这种策略的直接体现,并且确实吸引了观众注意。此外,《黄金时代》充分利用了时下最热的网络营销。合一影业(视频门户网优酷土豆旗下公司)和星美院线开启“联合超前预售”的模式,微信电影平台对影片的鼎力资助,以及百度众筹项目“百发有戏”的“消费+金融”模式,包括先期爆出的电影纪录片《她认出了风暴》和由罗大佑、林夕创作的宣传曲《只得一生》,都在互联网平台上为影片带来很高的关注度。再加上影片周边产品,如明星见面会、现场探班、观影纪念品等,《黄金时代》在长达8个月的宣传期中未有一丝疲软停歇之象,热度一直持续至影片放映期。
得益于这两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文艺片”这个话题在2014年的电影市场有了旺盛生命力,仿佛让中国电影人看到了文艺片元年的到来。
(责任编辑陶新艳)
[1]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156.
[2]吴子林.图像时代的文学命运——以影视与文学的关系为个案[J].浙江社会科学,2005(6):192.
[3]张明.与张艺谋对话 [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171.
[4]严歌苓.陆犯焉识 [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401.
[5]戈德罗,若斯特.什么是电影叙事学 [M].刘云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10.
[6]杨远婴,张颐武,吴冠平,等.黄金时代 [J].当代电影,2014(11):51.
[7]张涵,王冠华,戴剑平.影视美学 [M].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90.
[8]熊元,邱月烨,阿细.《黄金时代》一场关于票房毒药的试验[J].21世纪商业评论,2014(Z1):55.
J905
A
1671-5454(2016)02-0008-05
10.16261/j.cnki.cn43-1370/z.2016.02.002
2016-03-28
陈玉(1992-),女,江苏泰兴人,扬州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一本能够让你对人生有另一种认知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