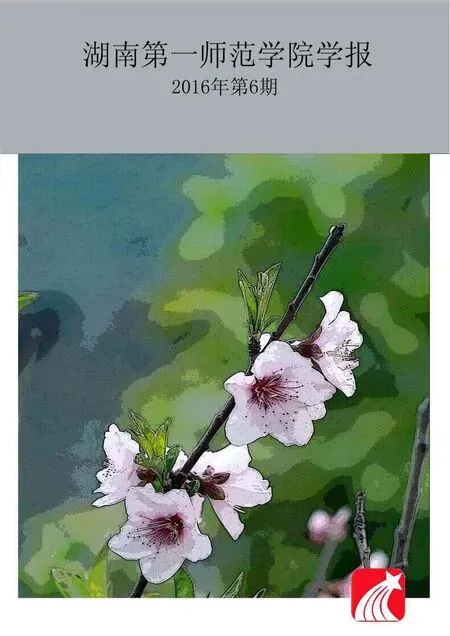东晋思想主脉与罗含《更生论》的再理解及其他
龙永干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东晋思想主脉与罗含《更生论》的再理解及其他
龙永干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罗含是东晋时期的文学家与思想家,其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更生论》中。他认为“有”是世界本源,“更生”为世界恒有无穷之缘由,“更生”本身有着不失其旧,自然贯次的特性与规律。从其对“更生”方式、向度与特性的认识来看,其思想与东晋玄学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联,将其归因于佛家“轮回”观的影响,是失之偏颇的。
罗含;《更生论》;玄学
耒阳地虽偏僻,但建置很早,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文化。东汉时,耒阳大凑山下贫民出身的蔡伦积极改进造纸一术,为文化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时至东晋,出生在耒阳的罗含同样是人中麟凤,以“湘中琳琅,江左之秀”的美誉为世人所称道。作为东晋时期的名臣,罗含不仅有着高尚的节操与可贵的品行,且在文学、哲学等方面皆有不俗建树,对后世文学与思想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相较而言,其文学才情更泽被深远。唐代诗人杜甫在《舍弟观赴蓝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中写道:“庾信罗含俱有宅,春来秋去作谁家。短墙若在从残草,乔木如存可假花。”杜甫素来仰慕庾信,将罗含与其并称,可见罗含文学才情之高。非但杜甫,刘禹锡、李商隐等著名诗人同样对罗含文才给予了高度肯定。令人遗憾的是,罗含《湘中记》及其诗歌大多散佚,仅存断章遗句,让人无法窥其全貌。幸运的是,他的《更生记》流传了下来,让人们在想象其文学才情的同时,可直观其哲思之深。学界对《更生论》早有论及,但本文旨在从东晋思想主脉与《更生论》的关联角度切人,以期推动对《更生论》的再理解。
一
相对于两汉学术而言,魏晋思想主流为“玄学”。思想主流由经学向玄学的转变,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与历史文化的原因。政治动乱的频仍与时代语境的严峻,严重地影响到魏晋士大夫的思想认识与言说方式。在政治上由先前的积极介入、砥砺名教与直击时弊,一改而为不问政治、逃避现实与明哲保身。当然,这中间虽有着具体时代的差异与个体态度的不同,但整体上来看,他们对越来越流于繁琐、偏于荒诞,甚或流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儒学产生了怀疑,不仅在思想上有着“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倾向,更在日常言行上有着极为任诞与荒唐的表现。东晋政治上并无好转之势,其思想主脉依然是“玄学”。但士大夫阶层风气有所变化,放荡任诞倾向大为收敛,而逐渐形成了礼玄双修、清谈与政务两不相误的情形。作为士大夫,罗含的仕途可说较为顺畅,历任郡主簿、郡从事、州主簿、征西参军、尚书郎、郡太守、郎中令、散骑常侍、廷尉、侍中等职。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朝廷为官,能上下相孚、勤政恤民,政绩不俗且有令誉。表现出东晋知识分子一面尚好玄学,一面注重实务的新风气。但就罗含思想而言,他对“玄学”显然是有着极大的兴趣,从《更生论》来看,所言是天地万物更生演变之“玄之又玄”的抽象之思。为论述方便,现将其文抄录如下:
善哉!向生之言,曰:“天者何?万物之总和。人者何?天中之一物。”因此以谈,今万物有数,而天地无穷。然则无穷之变,未始出于万物,万物不更生,则天地有终矣。天地不为有终,则更生可知矣。寻诸旧论,亦云:“万兆悬定,群生代谢。”圣人作《易》,已备其极。穷神知化,穷理尽性。苟神可穷,有形者不得无数。是则,人物有定数,彼我有成分,有不可灭而为无,彼不得化而为我。聚散隐显,环转于无穷之途;贤愚寿夭,还复其物,自然贯次,毫分不差。与运泯复,不识不知遐哉,邈乎其道矣。天地虽大,浑而不乱,万物虽众,区已别矣。各自其本,祖宗有序。本支百世,不失其旧。又神之与质,自然之偶也。偶有离合死生之变也,质有聚散往复之势也。人物变化,各有其性,性有本分,故复有常。物散虽混淆,聚不可乱,其往弥远,故其复弥近。又,神质会期,符契自合。世皆悲合之必离,而莫慰离之必合;皆知聚之必散,而莫识散之必聚。未之思也,岂远乎若者?凡今生之生为即昔生,生之故事即故事。于体无所厝,其意与已会,终不自觉,孰云觉之哉?今谈者徒知向我非今,而不知今我故昔我。尔达观者,所以齐死生,亦云死生为寤寐。诚哉是言[1]。
通读全文,就其所论天地,形神,有无、今昔等范畴来看,无不在玄学之域。而玄学与经学最为不同处,就是其论述不再停留在伦理道德与名教纲常之域,也不再汲汲于治国理政与世俗实务,而表现出对天地之本,形神关联,有无转化,名实之辩等抽象问题的极大兴趣。但在玄学的发展进程中,在对万事万物本源思考上逐渐生成了两条不同路向:一是贵无论,一是崇有论。对于天地宇宙,万物本源,《老子》认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2]226“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2]73。王弼、何晏作为“贵无论”代表,对《老子》将“无”视为万事万物的根源予以完全接受。王弼以“无形无名”论“道”,以有形有名指“物”。《晋书》称:“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3]与他们的观点不同,罗含的《更生论》不是“贵无”而是“崇有”。在《更生论》中,罗含未设定一个“无”为其根本,而是认为天地宇宙,本就有万物存在,不是由“无”而生“有”,而是由“有”再生万物,也就是说“有”为天地之始。就此而言,罗含的观点应是源自玄学中的“崇有论”。这一观点与裴頠相同,可以说作为玄学后辈的他对裴頠“崇有论”直接接受与继承。与《崇有论》中“夫总混群体,宗极之道也。方以族异,庶类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体也;化感,理迹之原也……是以生而可寻,所谓理也;理之所体,所谓有也。”相对照,在世界本源认识上可说是高度一致的。
对于事物本源的探讨,是玄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作为玄学基本理论支撑的《周易》《老子》《庄子》都曾对宇宙天地之本进行了形而上的思考。魏晋玄学遵其导向,亦是如此。无论是王弼主张的“贵无论”还是裴然頠倡导的“崇有论”,都在探究宇宙万物的本源。王弼的“以无为本”,认为万有都有其具体的规定性与有限性。于是,他进而认为万物之所以成为万物,必然有一个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无”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无”最终也就被其设定为万物的根源。但裴頠并没有把万物的本源推至“无”,认为“偏无自足,故凭乎外资”,也就是说万有自身有限,但它依然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而这种变化与发展的条件则是各种事物与因素的相互支持,所借助的条件还是“有”。即其所谓:“有之所须,所谓资也。资有攸合,所谓宜也。择乎厥宜,所谓情也。”为了进一步说明万物的根源,也就是“有”的所源所本,裴頠设置了一个“自生”说。认为王弼、何晏的“无”,没有任何具体的内容与形式,它不可能产生复杂纷繁、品类多样的万有。万物之所以能够产生,是因为在起始处便是物自身的生成,自我的生成,也就是所谓的以有生有。作为“崇有论”者,罗含在承认世界以“有”为本的时候,也对万物何以有本,如何运行进行了探讨,也就是说其与王弼、何晏、裴頠有着同样的逻辑致思路径。但罗含与同为崇有的裴頠不同,他在探究世界何以为有,品类何至于繁盛多样的时候,不是就事物本身的自我生成上寻找根由,而是见到了事物本身的转化与更生。“然则无穷之变,未始出于万物,万物不更生,则天地有终矣。天地不为有终,则更生可知矣。”天地之所以绵绵无期,万物之所以多样丰富,那都是源于事物本身的“更生”,是来自于事物不断变化的新陈代谢。事物的更生,是自然界的一种普遍规律,太阳升降,四季轮回,草木枯荣,人类无穷繁衍,都是在自我更生中完成。可以说,更生,是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也是天地世界能始终“有”的根本原因。
二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到,罗含不但认同了玄学的“崇有论”,而且对“有”之所以“有”进行了自我的思考,并进而提出了“更生”这一命题。非但如此,罗含还进一步在《更生论》中对“更生”的方式、向度与内在规律进行了深入具体的把握。
首先,他指出事物“更生”不是混杂淆乱的,而是有其特定方式与向度的规定,即“人物有定数,彼我有成分,有不可灭而为,无彼不得化而为我”。各种事物在其更生之时,是按照其固有的属性与特质、具体的方向与路径进行的。有着其各种条件规定的“定数”。“彼”与“我”之所以不同,那是既定的“成分”不同;“有”是恒定的有,它不会变化为“无”。天地万物品类繁多,变化看似纷纷扰扰,但“天地虽大,浑而不乱,万物虽众,区已别矣。各自其本,祖宗有序。本支百世,不失其旧。”可以说万事万物以“更生”完成其代谢更替,但万事万物的“更生”总是按照其原有的属性与既定的向度不断地衍化,虽有着代际的区分,当下与过去的不同,却是“自然贯次,毫分不差”的。
其次,罗含对“更生”本身进行了形而上的理解与把握。与对事物的“更生”认识不同,“更生”的认识要更为复杂与玄奥。他认为“聚散隐显,环转于无穷之途”,更生是无穷无尽,持续永恒的。同时,“更生”有着时间与空间,性质与数量的规律的。“远”与“近”是相承的,是“神”与“质”相期的。事物发展变化到了其尽头,其更生到来也就越迫切,变化也就更直接。形式与内容,物质与精神,现象与本质,一旦相契相合,有机统一,更生也就自然出现并最终得以完成。也即所谓“其往弥远,故其复弥近”“神质会期,符契自合”。
可以说,罗含的《更生论》将世界视为“有”,并将世界万物始终“有”的缘由建立在“更生”的基础上,并对更生的规律、向度、限度与路径进行了相应的探讨,是有着朴素唯物辩证法的色彩,这在魏晋玄学对于天地本源与世界本体的讨论上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罗含的《更生论》虽提出了更生的观点,但它又同时认为更生时“人物有定数,彼我有成分,有不可灭而为无,彼不得化而为我。”那则意味着人与物在更生的过程中,不会改变性状、质地,那么也就意味着这种更生不会有着质地与属性的变化,更生也只是自身的更生而已。富贵贫贱,贤愚寿夭,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也即“今我即昔我”。那么这种更生,也就只是简单的重复与循环而已,而不是充满变化、富于活力与创新的更生。罗含认为万事万物的变,不是本质变化,只是形式的变化、表面的变化。由此来看,有与无、我与彼,不能转化,事物只是聚散隐显,往复循环,其不断改变的不是形与神的改变,只是形式的改变,也正因如此,其“更生论”的形而上学色彩十分鲜明。因为,在世界的新陈代谢过程中,事物不但在不断更新与变化,而且变化与更生过程中也有着灭亡与新生,发展与衰退,变异与优化等等复杂的情形。
三
更生之论,其实并非罗含首次提及,《老子》中“大曰远,远曰逝,逝曰返”[2]169就有着事物更生变化的认识,《易经》中有“一元复始,万象更生”的观点。但因魏晋时期佛学有渐炽之势,有些学者由此而认为罗含“更生论”所说的反复更替、前后循环的认识上推论他的观点受到了佛教“轮回”观的影响。但从其逻辑推论,以及其更生方式,立论的旨归来看,《更生论》与佛家所说的“轮回”观有着较大的出入。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在魏晋动乱不安、残酷严峻的社会环境中,逐渐被广大民众所接受。而就其受众来看,却是上层甚于下层,并不断传播开去。罗含作为上层知识分子,当对佛教及其相关思想应该有所接触。其“更生论”中的昔日之我与今日之我相互轮转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与佛教的轮回观有着某种相同性,但两者在理论基础,循环方式与生命态度上都有着极大的不同。从罗含《更生论》的思想来看,它是从世界之有为逻辑起点,由此而追究其何以恒有,以至于无穷而展开的,进而得出万物与人类的繁衍生息循环不绝的观点。其基本的理论观点则是“天人合一”,物我趋同。而佛教的轮回观是从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与依存来展开的。《杂阿含经》中说:“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中阿含经》中也说:“若有此则有彼,若无此则无彼,若生此则生彼,若灭此则灭彼”。轮回是诸多因素因缘和合而成,是诸缘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即“业”与“果”。具体来说,早期佛教提出了十二因缘之说,形成了佛教基本成分。后来小乘佛教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改造和发展,提出了“三世两重因果”的轮回理论。所谓“三世”指过去、现在和未来。所谓“两重因果”指无明、行作为过去二因,招感识、名色、六处、触、受这现在五果,还指爱、取、有作为现在三因招感生、老死这未来两果。轮回观趋于完整严密,成为佛教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同时,罗含《更生论》虽肯定万事万物不断更新循环,循环无穷,并不复杂,是遵循既有属性与本来特质进行的,即所谓“人物有定数,彼我有成分,有不可灭而为无,彼不得化而为我。聚散隐显,环转于无穷之途;贤愚寿夭,还复其物,自然贯次,毫分不差。”但佛教轮回则是在“六道”(即为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人、天)中轮回,并且对六道轮回做出了极为具体而详细的业果界说。佛教认为六道轮回有二项是有形的,即是“人道”和“畜生道”而“天道”“阿修罗道”“恶鬼道”“地狱道”则是无形的。有形的称为“有器”,无形的称为“无器”。人在世间的种种业缘,让其在来生有种种业报。非但更生与轮回方式与途径不同,彼此立论的指向与社会价值也是各不相同,《更生论》是引导人们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生与死,视生死如同寤寐,从而拥有达观的生命态度,也即“尔达观者,所以齐死生,亦云死生为寤寐。”这一点,与庄子对生死的认识有着高度的一致。《庄子·知北游》认为:“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之徒,吾又何患”[4]380,认为生死如同气之聚散,从而人不必为之而忧患不已。对于生死,应当以达观心态对待之,如《庄子·养生主》中所说“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4]52。虽有今生昔生的说法,且潜在地具有来世的结构,但它依然是道安所批评的:“谈遗过去,辩略未来;事尽一生,未论三世。”[5]与此同时,它也并无佛家所说的因果业报思想。而佛教的轮回观则不是如此,它是通过地狱与佛国的两相对比,给人以巨大的威慑与希望,使人从强烈的反差中认清不同的道路与前途,借此来对众生进行劝诫与引导。业报,让人们对自我的言行与造作担负起应有责任,从而达到劝恶行善的目的。
可以说,佛教的轮回说指向伦理道德,更作用于社会劝诫。而罗含的更生论则更多的是指向个体的生命态度。从上面的分析可以见到,东晋时期虽然佛学较为兴盛,罗含也可能对其有所接触与研究,但从《更生论》的理论资源,言说方式,立论旨归等来看,它应是玄学范畴,而非其他。
[1]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M].北京:商务应书馆,1999:1408.
[2]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6:1236.
[3]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张耿光.《庄子》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5]石峻,等.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4:358.
On the Main Stream of Thought in Eastern Jin Dynasty and the Rereading of Luo Han’s On Regeneration
LONG Yong-ga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205)
Luo Han was a writer and thinker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whose philosophical thought was mainly shown in his workIn the book,he proposed his ideas about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with the concept of“having”and“regeneration”.His thought had close relation with metaphysics 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At the same time,the idea of“regeneration”wa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e“reincarnation”idea of Buddhism.
Luo Han;
I207.2
A
1674-831X(2016)06-0071-04
[责任编辑:葛春蕃]
2016-10-16
龙永干(1974-),男,湖南醴陵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