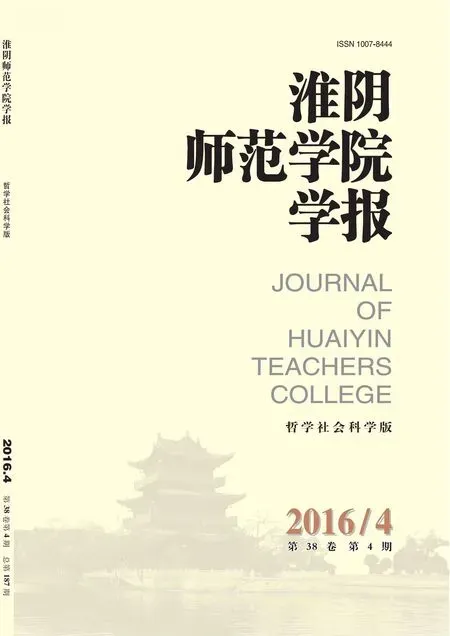“方宅”还是“方泽”
——与范子烨先生商榷陶诗的一处异文
葛志伟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方宅”还是“方泽”
——与范子烨先生商榷陶诗的一处异文
葛志伟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摘要:陶诗异文甚多,对其进行辨析向来都是陶诗研究中的难点。其《归园田居》第一首“少无适俗韵”诗中,有“方宅十余亩”句,因语意浅显自然,历来鲜有关注者。范子烨先生指出,陶诗此处应从《艺文类聚》作“方泽十余亩”,“方宅”系同音致讹产生的异文,而所谓“方泽”,“实际就是湖田”。然此处异文的选择、辨析及释义,不仅与中古史实多有不符,且似已改变陶诗之原意,故有商榷的必要。
关键词:陶渊明;方宅;方泽;异文
《归园田居》是陶渊明最有代表性的田园组诗,古今论之者甚众。近日偶读范子烨先生《诗意地栖息与沉静的激情——对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的还原阐释》一文(刊于《文学遗产》,2011年第5期,以下简称“范文”),可谓受益良多。然范文认为,《归园田居》第一首“少无适俗韵”诗中,名句“方宅十余亩”原文应从《艺文类聚》作“方泽十余亩”,“方宅”系同音致讹产生的异文,而所谓“方泽”,“实际就是湖田”。对上述结论,笔者似不敢苟同。故撰此拙文,略申己意。
一、范文指出,按古今田亩的折算方法,陶家“方宅十余亩”的总面积超过5 000,而“草屋八九间”面积大致500,“比例上的严重失调,未免使人感到困惑”。我们认为,不应用今人的宅屋观念去衡量彼时的社会情形。按晋时数亩之宅对应数间之屋,乃常有之事。盖古人之“宅”,不仅包括所居屋舍,更涵盖其周围所有经营依托之处。故《释名》云:“宅,择也,言择吉处而营之。[1]”《说文解字》亦云:“宅,人所托也。”[2]考《晋书·孔愉传》云:
在郡(会稽)三年,乃营山阴湖南侯山下数亩地为宅,草屋数间,便弃官居之。[3]2053
又《晋书·良吏·吴隐之传》云:
归舟之日,装无余资。及至数亩小宅,篱垣仄陋,内外茅屋六间,不容妻子。[3]2342
孔愉为守正不阿之臣,隐之系清操踰厉之吏。史官当是赏其高洁,故书其宅地、屋舍以明之。然晋时“数亩之宅”何以称小?考《晋书·食货志》云:
若乃一夫之士,十亩之宅,三日之徭,九均之赋,施阳礼以兴其让,命春社以勖其耕。[3]779
盖“一夫之士,十亩之宅”,或为其时宅地分配之一般标准。又《太平御览》卷一百八十引盛宏之《荆州记》曰:
襄阳范蠡祠南,有晋河南尹乐广宅,周回十余亩。[4]878
乐广本出自寒素,后虽久历四方,然冲约之性终生未渝,故其宅不过“周回十余亩”。由此可见,对“爵同下士,禄等上农”(颜延之《陶征士诔》)之渊明而言,“方宅十余亩”并不能算广大,亦不过是刚好达标而已。可见此句的言外之意,实与渊明“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杂诗》)式的自足保真心理暗合。而彼时真正的大宅、豪宅,当如周处、郗鉴等士族名流之所居。考《晋书·周处传》云:
追赠平西将军,赐钱百万,葵地一顷,京城地五十亩为第。[3]1571
又《太平御览》卷一百八十引刘祯《京口记》曰:
唐颓山周回二里余,山南得路,得郄鉴故宅五十余亩。[4]877
一般而言,古人于宅地之上除正常建屋舍外,尚可根据自己生活需要,或成菜圃,或作园林,或砌假山,或凿水池,亦即《释名》所谓“营之”之意。考《艺文类聚》卷六十四引《襄阳记》云:
李衡每欲治家,妻辄不听。后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龙阳洲上作宅,种橘千树。[5]
又《梁书·庾诜传》云:
性托夷简,特爱林泉。十亩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治产业。[6]
就渊明诗歌而言,其间即有“东园”(《停云》)、“南圃”(《咏贫士》其二)、“北园”(《咏贫士》其二)、“西园”(《和胡西曹示顾贼曹》)等地*本文所引陶诗,皆出自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为避免注释繁琐,下引陶渊明诗文不再一一出注。。据此可见,渊明宅地之上,除八九间草屋之外,四周园林必居其大半。而《艺文类聚》将渊明此诗置于卷五十六“产业部·园”之下,或正循此意。
二、范文认为,“方宅”在陶诗乃至先唐文献中仅此一例,“这种情况就更使人费解”。诚然,“方泽”一词多见于先唐文献。然考其使用语境,多是与“圜丘”相对出现,即作为祭祀之场所而言。如《晋书·江逌传》云:
群祀之所,必在幽静。是以圜丘方泽,列于郊野。[3]2174
又《宋书·礼志》云:
古者丘郊不异,宜并圆丘方泽于南北郊,更修治坛,兆其二至之祀,合于二郊。[7]
即便在南朝士大夫的诗文中,“方泽”似乎也都与祭祀相关。如庾信《周祀方泽歌》云:
曰若厚载,钦明方泽。敢以敬恭,陈之玉帛。[8]
又徐陵《劝进梁元帝表》云:
云和之瑟,久废甘泉。丝竹之管,无闻方泽。[9]
因而,把“方泽”释为晋宋时期的“湖田”,似乎并无依据。就先唐文献而言,“方泽”一词真正具有野外陂泽之意的,亦仅东汉张衡《归田赋》“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一例。范文据此认为,渊明诗句必典出于此。然此观点不可通处在于:就先唐文献中量词与名词搭配实例看,“泽”似无有与“亩”搭配的先例,而与“里”搭配则最为常见。如《山海经·大荒北经》云:
有大泽方百里,群鸟所生。[10]
又《汉书·沟洫志》云:
有泽方数十里,环之有堤。[11]
又《华阳国志》卷四“滇池县”条云:
有泽水,周回二百五十里。[12]
又《拾遗记》卷六“宣帝地节元年”条云:
名曰融泽,方三千里。[13]
又《魏书·序纪》云:
宣皇帝讳推寅立,南迁大泽,方千余里。[14]
又《水经注》卷二十五“泗水”条云:
墟有漏泽,方十五里。[15]
就面积单位而言,“方……里”的宽广程度自然远甚于“亩”。而“泽”在古人观念里,又是个较大的水域概念。如《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云:“深山大泽,有龙有蛇。”[16]故在上引诸条文献中,无论是大泽、融泽、漏泽,还是那些无名之泽,其大小多用“方……里”来描绘,以示其大。而相比较而言,“宅”则是个较小的土地概念,故多与“亩”搭配使用。如孟子所谓的“五亩之宅”、吴隐之的“数亩小宅”等,更多例证已如上所引。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渊明纵使天才横溢,似乎也难以超出约定俗成的时代语言规范。考颜师古《后汉书·郡国志》“秭归本归国”条注引《荆州记》云:
县北一百里,有屈平故宅,方七顷。累石为屋基,今其地名乐平。[17]
据此,则渊明诗中所谓“方宅”,或许并非指方正的宅地,而是“宅方”之倒装,亦即宅地面积有十余亩之意。故“方宅”之“方”,当是就其面积而非形状所论。
三、范文认为,“方宅”是大概念,而“草屋”是小概念,前者涵盖后者,“既然在逻辑上不能并列,也自然就不能构成对偶关系”,因而“对‘方宅’这种文本就不得不有所怀疑了”。众所周知,对偶是陶诗中常见的修辞技巧,且方式多样化。诚如范文所言,《归园田居》中“方宅”是大概念、“草屋”是小概念。然大、小概念对举在陶诗中并非孤例,如: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归园田居》其二)
玉堂凌霞秀,王母怡妙颜。(《读山海经》其二)
“野外”与庙堂相对,自然涵盖“穷巷”;“人事”指世俗交往,亦当包含“轮鞅”;“玉堂”又为“王母”怡颜之处。三者对举成文,皆可见大、小概念之别。显然逻辑上不能并列的意象,并不能构成修辞层面上的矛盾,且经渊明妙手点化,愈见其诗艺之高超。宋释惠洪《冷斋夜话》曰:
东坡尝云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视有奇句。[18]
事实上,“少无适俗韵”诗中的奇句,正由那些看似散缓的对偶意象组成。每个意象都源自一个短暂的心理情绪,我们将它按日常生活经验延伸,并赋予它自由而美好的意义: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园,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此诗系年各家虽有争议,然作于渊明辞彭泽令归隐后的第二年春夏之交,则几众口一词。可见此诗之“归田园居”,似非泛泛而论归隐,而是一次具体的开荒暮归体验。这与下文“对话桑麻”(其二)、“种豆南山”(其三)、“山泽之游”(其四)、“游归行乐”(其五)等事件描写,如出一辙。因而,“方宅”以下数句,皆是归家情形的描绘。盖空间视角的变化,构成了此番诗情画意般的归途之旅。在此归途中:(1)首先映入诗人眼帘的,是园林环绕的十余亩宅地。近宅后方可看到草屋。意象由大而小转换间,可以想见诗人归家心切、步履匆匆之神情。此情此景,当与“乃瞻蘅宇,载欣载奔”(《归去来兮辞》)略同;(2)榆、柳为落叶乔木,枝干较高,而桃、李为落叶小乔木,枝干较矮。故诗人靠近草屋之时即可看到后园之榆柳,而进入庭中方能得见堂前之桃李。意象由高而低转换间,可以推知诗人身影变化之概况。此番过程,当与“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归去来兮辞》)略同。又“榆柳荫后园”,不少版本作“后檐”。考《齐民要术·种榆》云:“榆性扇地,其阴下五榖不植。种者,宜于园地北畔。[19]”盖将榆树种植于园地北畔,可不荫园中五谷,此为彼时农人种植经验。据此,则渊明之榆柳似不当植于“后檐”之下。可见陶诗非为一般写意,而是当日生活经验的再现;(3)“远人村”非远离村落之意。盖渊明所居常有近邻共来往,如“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归园田居》其五)、“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等。因而“远人村”,实是诗人于庭中环顾四周所见之景象。按“远人”一词在秦汉两晋文献中,涵义较孔子所在的春秋时代有了很大变化,即“从地域距离的‘远人’,衍变到文化距离的‘远人’,向春秋时‘夷狄’的意义靠拢”。[20]故诗人自称所居为“远人村”,颇有自我调侃的味道。从村落之朦胧到炊烟之袅袅,一为粗线条描绘,一为细线条刻画,一静一动,秩序井然;(4)“鸡鸣”二句,历来论者皆指出系渊明化用汉乐府《鸡鸣》“鸡鸣高树巅,狗吠深巷中”而来。然细细品读,似犹未尽渊明之意。《孟子·公孙丑》云:“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东汉赵岐注云:“鸡鸣狗吠相闻,言民室屋相望而众多也。”[21]69又《桃花源记》云:“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鸡鸣”二句不仅以乡村生活最为常见之景物来表现和平安定的社会图景,更是强调诗人所居为诸多邻人屋舍所围绕之客观情形。联系上文“暧暧”两句看,诗人的视角仍停留在“墟里”之上。“屋舍俨然”既为诗人提供归隐园田的乐趣,又好似层层铠甲呵护着诗人无俗的心性;(5)如此栖息之所,自能远离世俗尘杂之事,任真养性,保持心灵的宁静与闲适,而这正是诗人最为向往的生活方式。诗人的视角在环顾四周后,最终还是落到对自己所居宅屋的赞叹之上。诚所谓“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其一)矣。
四、范文认为,“与‘方泽’有关的描写多见于陶诗”,并列举“洋洋平泽,乃漱乃濯”(《时运》)、“迥泽散游目,缅然睇曾丘”(《游斜川》)为证。我们认为,这种举证是对陶诗的误读所致。按“洋洋”,乃水势盛大之貌。“平泽”,《尔雅·释地》云:“大野曰平。”刑昺《疏》云:“大野之泽一名平。”[21]197此条材料早已为学界所共知。若将其视为十余亩“湖田”,何其小哉,故必不可信。另外,“洋洋平泽”句本有异文作“平津”,范文并未辨析。又“迥泽”当为远泽之意。如王粲《登楼赋》云:“路逶迤而修迥,川既漾而济深。”[22]考《游斜川序》云:“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临长流,望曾城……”诗中之“迥泽”正与此“长流”相照应。若将其视为十余亩“湖田”,何其短哉,亦不可信。更何况,《时运》《游斜川》二诗,皆涉及诗人出游一事,且游览之地、观赏之景自远离家园,不当限于门前的十余亩“湖田”之中。如《时运》“洋洋”句后径言“邈邈遐景,载欣载瞩”,《游斜川》亦云“班坐依远流”,似皆可为证。
对文本异文的辨析,向来是陶诗研究中的难点。但渊明此诗原文作“宅”还是“泽”,恐怕已非单纯的版本问题。王力先生曾指出,“从汉代到南北朝,韵部有分,有合,有转移。总的来说,已经接近《切韵》音系”[23]。而《切韵》系韵书及《广韵》中,“宅”“泽”二字皆同音。如宋濂跋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王三”)“宅”“泽”同在陌韵宅小韵,音枨百反。[24]又《广韵》中,二字也都在陌韵宅小韵,音瑒伯切。[25]因而王叔岷先生认为,此处“宅”“泽”当是正、假字,并引陆德明《经典释文》注《庄子·则阳篇》“比于大泽”句“本亦作宅”为证。[26]按“宅”“泽”同音相假现象既可在隋唐文献中存在(虽是孤证),那么首现于《艺文类聚》中的陶诗异文,或可作如是观。此其一也。如果《艺文类聚》所引陶诗“方泽十余亩”之“泽”,不是出于上述现象(此种情况可能性更大),那么异文“泽”的产生当是由与“宅”字同音相混所致。此其二也。但无论是“相假”还是“相混”,我们都可以肯定“方宅”才应是陶诗的原文。另外,“方宅十余亩”也与陶渊明在占有适量生活资料前提下“知足常乐、安贫乐道”的隐居哲学深相契合。故倘若仅据《艺文类聚》孤证,遂判定“方泽”为是、“方宅”为非,并将其推论为“湖田”,则此举不仅与中古史实多有不符,且似已改变陶诗之原意。
参考文献:
[1]任继昉.释名汇校[M].济南:齐鲁书社,2006:284.
[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338.
[3]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李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5]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1143.
[6]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751.
[7]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423.
[8]倪璠.庾子山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434.
[9]严可均.全陈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44.
[10]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424.
[1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693.
[12]刘琳.华阳国志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4:396.
[13]上海古籍出版社.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529.
[14]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
[15]王先谦.合校水经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376.
[1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9:1061.
[17]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3480.
[18]惠洪.冷斋夜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8:13.
[19]缪启愉,缪桂龙.齐民要术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330.
[20]李飞.陶诗“远人村”新解[J].文史知识,2009(3).
[21]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标点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2]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100.
[23]王力.汉语语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52.
[24]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M].北京:中华书局,1983:521.
[25]周祖谟.广韵校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4:514.
[26]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7.
责任编辑:刘海宁
中图分类号:I207.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16)04-0535-04
收稿日期:2016-03-23
基金项目:2015年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门阀制度与中古五言诗的演进研究”(15ZWC004)。
作者简介:葛志伟(1985-),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