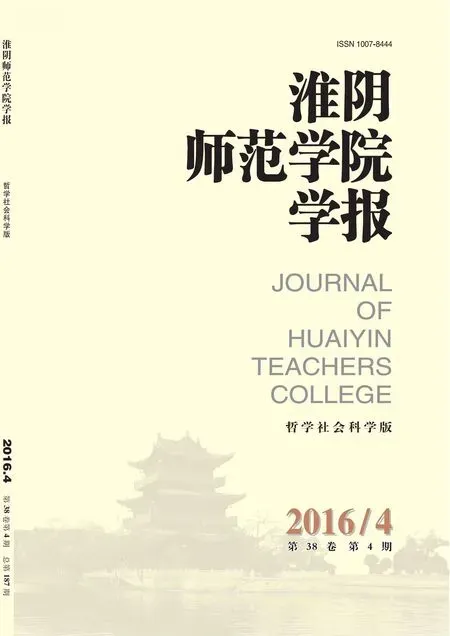如何认识科学(十九):科学与社会系统
——大卫·凯里对露丝·哈伯德的访谈
露丝·哈伯德, 大卫·凯里
如何认识科学(十九):科学与社会系统
——大卫·凯里对露丝·哈伯德的访谈
露丝·哈伯德,大卫·凯里
摘要:露丝·哈伯德认为,科学并不总是好的,它导致了武器、化学物质、毒气等诸多的危害,科学造成了科学是社会制度一部分的事实。过去的科学遵循它自身的议程,明显没有社会的或政治的议程推动这项工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正在被改变,科学家所发现的东西时常是他们想要去寻找的东西。社会结构至少以两个主要方式影响科学:首先它粉饰了我们对自然界的感知——将我们对社会安排的理解映射到自然界中;其次它影响占据首要地位的科学——从社会认为值得做的意义上——的选择问题。基因交换在殖民地和实验室中大规模地做到了,基因学家依照好像他们能预言结果和预知其是否有益的方式行事。科学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变成现实。新技术已被迅速和不加鉴别地应用,这相当于在人身上做实验。从某种意义上看,基因技术的发展不是为了公众利益,而是为了私人利益;生物学已变成大企业追逐利益的场所。科学不可避免地成为社会的一个创造物。科学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系统有关,它是政治;作为一个科学家,你真的无法摆脱它。
关键词:科学;社会系统;政治议程;选择;利益
肯尼迪:我是保罗·肯尼迪,这是《思想》的“如何认识科学”节目。
哈伯德:很明显,科学并不都是好的。说“我在解答有趣的问题”这还不够好,说“我在解答不对任何人构成任何伤害的问题”也不够好。因为很明显,曾经有一些被问的和被解答的问题导致了许多危害:武器、化学反应、毒气、用脱叶剂粉饰出来的场景。因此,科学过去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事实,并不能让我看不见如下事实:科学是社会制度的一部分,这已变得至关紧要,我必须正视这一事实。
肯尼迪:露丝·哈伯德花费她科学生涯最初近20年的时间用在从生物化学的视角调查实验室的工作台上。她后来的丈夫,乔治·瓦尔德(George Wald),指导该项研究,因他的团队发现眼睛是如何工作的,因此而荣获诺贝尔奖。在19世纪60年代的越战期间,她的工作扩展到包括科学政治学的领域。她领衔参与了新兴的对科学中女性状况的女性主义批评。并且,对于生物学在新的遗传和生殖技术方向的发展,她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在她看来,这相当于在人身上做实验。
哈伯德:还记得吧,第一个试管婴儿于1997年诞生,这没什么。实际上她现在还不到30岁。那么,对此我们知道些什么呢?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并且谈论它是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处在有许多试管婴儿的世界中。
肯尼迪:露丝·哈伯德是哈佛生物学退休荣誉教授,是《女性生物学的政治》一书的作者,还与她儿子伊利亚·沃尔德(Elijah Wald)合著了《破裂的基因神话》一书。在今天的《思想》栏目中,她将回顾她的职业生涯,以作为我们“如何认识科学”系列节目的继续。《思想》栏目的制作人是大卫·凯里。
凯里:1938年3月,纳粹军队占领了奥地利并使之成为德国的附属国。当时哈伯德14岁,她是犹太人,生活在维也纳,她父母都是那里的医生。三个月后,全家逃到美国并在波士顿开始新的生活。在波士顿,哈伯德读了中学和大学,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一年,她进入拉德克利夫学院学习。当时她想追随父母的足迹进入医学院,但最终却进了生物学系。30年后,哈伯德成为第一个获得哈佛生物学终身教授的人。她现在是哈佛大学的退休名誉教授,2007年春,我们在哈佛大学她的办公室里见面,她向我讲述了她是如何开始她的科学事业的。她说,那开始于一位教授的实验室的一份工作——那位教授乔治·沃尔德后来成为她的丈夫。
哈伯德:那是一段真正有趣又非常令人兴奋的日子。我的意思是,被科学迷住太容易了,因为我们设计了我们自己的所有仪器。我们制造了我们需要的每样东西——你知道当时正处于战争时期——乔治去了位于布鲁克林的一所高级技术学校并因此可以使用那里的仪器。我们亲力亲为。我们时常不得不请人做些修理,不过,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感觉不错。
凯里:这个实验室所进行的研究是有关眼睛能看到的生物化学反应,该工作最终使沃尔德获得1967年的诺贝尔奖。哈伯德说,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她加入了实验室的工作,当时研究小组正在跟踪一项发明,这个发明是1932年沃尔德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后不久获得的发现。
哈伯德:当时他获得研究员职位去了德国。他实质上发现了维生素A的作用。当时已经有人认为,维生素A必定与视力有联系,因为如果你缺乏维生素A就会出现夜盲症。但是,他发现,不知什么原因维生素A与眼睛吸收光的视网膜中的色素有联系,并且光吸收释放出维生素A。他还发现别的与维生素A有关的化合物,因为它在视网膜里,故他称之为视黄素(retinene)。他把它描述为在视色素[即视网膜紫质(rhodopsin)或视紫红质(visual purple)]与维生素A(即漂白产品)之间的媒介。所以,漂白首先产生这种他称为视黄素的黄色物质,然后产生维生素A。它们是胡萝卜素,视黄素和维生素A的分子结构与β胡萝卜素有关(β胡萝卜素使胡萝卜呈黄色或橙色)。于是,我开始在视红素这种黄色物质如何转变成维生素A方面展开工作。从本质上说,我当时做的是酶化学。乔治已经弄懂了这一循环,我们以相对短的周期展示的是这一循环的实际化学过程,在其中,你能获得在黑暗中增多了的视网膜紫质。当你沐浴在光线之下,你就获得了视黄素,视黄素转化为维生素A;当你回到黑暗中,维生素A或视黄素能退回到视网膜紫质中。所以,我们试图弄明白这一过程的化学过程。我们做到了。我做这件事花费了很长时间,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
当时,我实际上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敏感性。我的意思是说,我当时非常感兴趣于世界上发生的其他事情,完全没有想过科学问题来自何方或者世界的状况是如何影响科学的。在内在论者的范式中我感到非常舒服,在这一范式中,你提出一个问题并尝试着找到答案。如果你幸运的话,你会发现一个答案,然后你提出下一个问题,等等。你无法真正做到左顾右盼、看得很远,以至于想去弄明白为什么一些问题比其他问题更为重要、或者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而不是那件事、或者也许不做这件事而是做那件事。甚至涉及像原子弹这样的事情……显然,我的意思是说,我对此事所持有的观点是:我不会去想我应该去做什么样的某种科学,我也知道有人在原子弹被投下之后退出物理学而进入社会学或科学史或其他一些领域,但这对我而言的确没有显得那么突出。
凯里:露丝·哈伯德称为“内在论的范式”的观点认为,科学遵循它自身的议程,提出并回答内在于各类科学中的问题。这是一种对她在实验室中所从事工作的相当准确的描述,明显没有社会的或政治的议程推动这种工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作为推动科学发展的一般性描述似乎越来越不能令她满意。她说,改变其思想的是妇女运动的涌现和越南战争。
哈伯德:越南战争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是否可能有其他更为重要的问题需要人们去研究。为什么我要做这个问题?而且,科学卷入了战争。所以,很明显,科学不都是好的。你知道,说“我在解答有趣的问题”这还不够好,说“我在解答不对任何人构成任何伤害的问题”也不够好,因为很明显有些被提出和被解答的问题造成了诸多伤害:武器、化学反应、毒气、用脱叶剂粉饰出来的风景。因此,科学过去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事实,并不能让我看不见如下事实:科学是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做科学仅仅因为它真的非常有意思且好玩,只要我做好的科学并解答有趣的问题就好,这就足够了……也许这并不足够。所以,在这方面我变得非常不安。当然,妇女运动以更直接的方式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它真的逼着我去思考——不是我们如何思考视力的问题,因为这并不是一个特殊性别的问题——而是我们如何思考生物学、我们如何思考女性生物学、我们如何思考进化的问题。妇女运动已经向我们展示,文学、历史和心理学都受如下事实的影响:由于群居的原因、由于社会的原因,重大问题是由男人而不是女人问及的。并且,男人们所问及的问题主要是引起他们兴趣的问题。所以,当女性开始更具批判性地着眼于这一问题时,她们指出,有一些一直没有被提出的问题,或者它们被提出、它们以陌生的方式被提出,以至于男人给出与女性的体验不一致的陌生回答。很明显,科学——我的意思是指生物学,我过去一直涉及的科学——并不是这样的,在生物学中必定也是如此。
于是,我就决定去休假。我的意思是,我当时还没有工作——这是我在当时突然意识到的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我是一个助理研究员和讲师,而我同一时期的男士们要么已经获得教授职位要么在获得的路上,怎么会是这样?有段时间,我非常天真——我理解我如何才能获得教授的职位——以至于我认为,我当时的状态真的相当不错,我不必去做那些男士在获得教授职位的过程中所要做的许多事情。我不必去参加那些无聊的会议。我可以挑拣我想教的内容。我可能是一名讲师并做这或做那。所以这没有什么不好的——然而在一段时间后,当我有点老了并且我的孩子正在长大时,我才意识到,你知道的,我没有了安全感,除非借助我与之结婚的那个男人,并且当时我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一整体情况。
就在这时,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刚刚来到哈佛并成为助理教授——因为哈佛当时规定女性可以是助理教授——的两位年轻女子召集了一个所有拥有大学任命书(我们所有女性都有)的女性参加的会议。我发现我所在的会议室里挤满了女性,许多人与我同龄——你知道,她们不是20岁和30岁的年龄,而是40岁或许是50出头的年纪,在学校里已经待了很长时间,做了许多很棒的工作,除了我们拥有那些非职务性的工作,我们没有任何正式工作。这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是开了眼界的。我们一直就天真地认为,哦,哈佛让我们在那里工作,这不是很好吗?我们获得资金并做我们想做的工作,这太好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更为有趣的是——虽然不是作为实践的方面——我认识到,如果科学——比如说我作为一位生物学家所从事的生物学——像文学、历史、心理学等所有这些学科一样,受到大部分一直是由男人来完成的这一事实所影响,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将如何来理解这一点?我将如何来验证这一点?我突然意识到,生物学中的基本工作毕竟是《物种起源》一样的事情。自从我研究我的专业以来,我没有读过《物种起源》,那么,如何看待《物种起源》并理解它是否显示了男性的偏见呢?我找不到更好的书来说明这一问题。它不仅是男性的偏见,还是社会的偏见。我的意思是说,首先,有一个动物的王国。这个王国是怎么来的呢?然后,它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中运转,以至于其中所有的生物体在一类物种中和各种物种之间相互竞争。这种观点来自哪里?它是显而易见的吗?这是在你查看自然界时你能看到的唯一事情吗?而你发现有一位俄罗斯王子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他恰好以相反的方式讲述这类故事,难道这不是很有趣吗?我们在英格兰获得这一由英国人搭建的观景台,他生活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中,那里有所有生物体对生物体的竞争。而你也获得了无政府主义者俄罗斯王子的观点,在其中,你正生活在一个合作的世界中,且正是合作让事物在起作用。
当然,在达尔文那里,你也可以获得性选择理论。你得到这一不可思议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脚本,雄性竞争性地获得有生育能力的雌性而进行自我繁衍。所有雌性生物都在一旁坐着,像坐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舞场中一样。它们试图挑选出它们能挑到的最好的雄性/雌性以便在它们的世界中增强它们自己的发展状况。你知道,这类变化的事情对于我的意义,在那一刻我决定去教一门生物学和女性问题的课程。它是一门讨论式的课程,但我决定从做一件进化和达尔文方面的事情开始,由此我写了《只有男人进化?》。该论文被多次转载,也是它让我们真正开始着手出版这方面的第一本书,我们称这本书为《女性看着眼于女性的生物学》(Women Look at Biology Looking at Women)。这很有趣,因为就在我们用一个奇怪的名字出版这本书时,在英国有一个共同体出版了一本名叫《显微镜下的爱丽丝》(Alice Through the Microscope)的书,该书实质上提出了同一类问题。所以,这是这一故事的开始。
凯里:露丝·哈伯德反对查尔斯·达尔文的性选择和普遍的生存竞争理论的原因,不是说它一点也不真实,只是说它编造了整个故事。她提到比达尔文年轻一代的俄罗斯王子彼得·克鲁泡特金挑战了英国人的理论,原因是该理论完全忽略了进化中社交和互助的作用。露丝·哈伯德说,自然界为许多理论提供了谷物,而我们所发现的时常是我们想要去寻找的。
哈伯德:如果你观察动物模型,你会发现动物习性的各种例子。确实有这样的例子:雌性大而雄性小,雌性更具竞争性而雄性缺乏竞争性。你能发现这一切。但是,动物模型就在那里,就是孩子们在学校里学的东西,你知道的,就是关于某类……
凯里:……两只把它们的头撞击在一起的大雄鹿。
哈伯德:是的。当你发现不以这样方式起作用的例子时,那它就变成了问题。为什么它不按这种方式起作用呢?为什么不是这种方式呢?于是,我们就在动物和植物界中阅读到我们人的社会性安排:从构成王国的最简单层次着手,从作为兽中之王的狮子和诸如此类的事物着手。结果证明,母狮做它们想要做的所有事情,而所有雄狮知道要去做的就是大声吼叫。
凯里:在露丝·哈伯德的观点里,社会结构至少以两种主要方式影响科学。首先,它粉饰了我们对自然界的感知——她把这个过程称为“将我们对社会安排的理解映射到世界中”。其次,它影响占据首要地位的科学的选择问题——从社会认为值得做的意义上——该问题是她在生物学中特别关注的。
哈伯德:从对已被人们接受的科学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的效果的观点看,我既非常专注于优生学,也很专注于DNA重组,在其中我看到了冒犯,这种冒犯不是对其内部和本身,而是其被追逐的方式。之前,在自然界中,从未有或可能很少有过基因交换,但在殖民地和实验室中大规模地做到了这个,人们按照他们仿佛能预言结果和预知利弊的方式行事。
凯里:DNA重组涉及将DNA从一个有机体嵌入到另一个有机体的基因组中。这一工作在1973年首次实现。露丝·哈伯德所担心的是,DNA重组会被无节制地追逐。并且,当其他基因技术出现时,她的担心进一步增加。比如,她开始注意到,孕妇基因扫描技术如何有损于一场运动的目的,她认为其本来的目的相当于一场妇女健康运动。
哈伯德:妇女健康运动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其口号是“把身体还给我们”。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停止对妇女健康的医疗化处理。对妇女健康的医疗化处理是指:在19世纪,当部分医生发现了社会中有利可图的市场时,他们提出了一些理论和技术,他们认为这些比助产士和用宗教信仰方式给人治病的术士所能帮助人类的最基本能力(即生育能力)更具优势,并用来取代为数众多的助产士、非医疗性的学校、训练用宗教信仰方式给人治病的术士大学,他们吹捧说:姑娘们,我们知道为你们做这事的正确方法。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甚至是从50年代开始,就真正有了将把身体还回给我们和只要有可能就把医生赶出产房的努力。当时,你开始发现各种各样的试图通过各种方法在胎儿出生之前预测胚胎和胎儿健康状况的技术和理论得以发展。于是,这使得医疗职业重新在这个领域兴起,因为孕妇所关心的是,如何在医生可能预测到的那些可怕事情不可能发生的情况下让妇女自己在家生产。于是,你首先被接管——再一次地——并且你也有了优生的压力,就是说,如果你不关心趋于恶化的物种,那么你将不可能拥有那些能避免所有缺陷并得以保护的孩子。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所说的是,医学与社会、科学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变成现实并非常明显。你得到了如人工授精这样的伟大发明物,而且你立即抓住像我一样的人们并说: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当你经历你无法知道其效果的操作时,你怎么能说是在提供一种福利呢?在这里,我的意思是指,在妇女体内使用性激素以便产生超数排卵(multiple ovulations)。对于这种做法会产生什么样的状况你一无所知。于是你就在试管内进行人工授精——你操纵这个胚胎,把胚胎放回到子宫中去,你希望以正确的方式为准备就绪的子宫做了正确的事,你希望在合适的掌控下拥有一个正常的妊娠过程,虽然那已经不是出自你自己在心理上全力以赴做好准备的掌控。当然,如果你想要现在偶尔会发生的多胞胎的终极事情,你可以大大增加多胞胎率。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某人想要双胞胎,很明显,你是希望双胞胎的,而去求助于增加多胞胎——双胞胎、三胞胎、四胞胎——发生率的技术,并出于改进健康的目的而做这样的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所有这些事情中,我还没有提及、但对我而言又是最重要的事情,无论对DNA重组还是对生育操控而言,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利益。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远远走在前面的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在其他西方国家,你有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国家医疗体系或国家健康保险,事实上它昂贵得令人诅咒,以至于限制了它的利用以及让它重新振作的方式。
凯里:自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以来,超过10万个孩子在子宫外怀孕并在美国出生。英国人的一项完成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研究报道说,到该研究展开那一年,在英国有7 000名试管婴儿出生,几乎有一半是多胞胎。露丝·哈伯德说,新技术已被如此迅速和不加鉴别地应用,这相当于在人们身上做一个巨型实验。
哈伯德:要记住第一例试管婴儿出生在1979年。这没什么。她现在还不到30岁。他们当时还没有使用现在使用的所有性激素。他们还没有任何运气可以获得婴儿,所以他们决定最好不用荷尔蒙,他们做了这样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获取一种能排卵的蛋并使之继续发育。那么,我们现在知道什么呢?我们什么也不知道。这成了一件非常难以谈论的事情,因为我们处于一个有许多试管婴儿的世界。
凯里:露丝·哈伯德认为,有几种新技术将女性健康重新医疗化了,人工授精就是其中之一。另一项是遗传检测,现在这项技术能够让妇女知道在她们怀孕期间的各种可能:这个胎儿在多大机会上是健康的,那个胎儿在多大机会上是健康的,等等。露丝·哈伯德说,麻烦的是,这些概率性事件仅仅是概率而已,对她们实际的怀胎情况并没有任何明智的忠告。
哈伯德:我认为,这对妇女是极为残忍的。我认为,告诉妇女那些毫无意义的信息、让她们相信她们必须在此基础上作出判断,这是极其残忍的。你瞧,我想到一件如此可怕的事情——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在几十年前你对自己的直觉是怎样的——如果那些测试已经可用,你和你的家庭、或者我和我的家庭是持赞成态度还是有勇气说“离开”呢?或者我们莫名其妙地感觉到有点是被迫的呢?如果是第一个孩子,这样做还可以理解,但如果是第二个或第三个孩子,你会怎样做呢?如果……会怎么样?等等。现在,所有我知道的是:你根本不能开始。如果你开始,如果你说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每件事情也都会继续。你如何知道在哪里停下来呢?你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说,不,赶紧离开,好不好?别来打扰我。当然,在我自己的生活中,这就是我所学会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些谈话。它们不再是有关生子的事了,而我也不再敢给年轻的妇女提出忠告了,除非某人真的带着问题来找我并的确需要我的观点。我真的是不敢了。但是,对于我自己的朋友和年龄大的妇女、甚至年龄不是太大但又不太年轻的妇女,所有我能说的就是,不,我不主张一年一度的身体检查。不,我不知道我的胆固醇是什么情况。不,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说,其他每个人知道他们自己的所有事情,而我不知道。如果我确实知道它,我又能做什么呢?它是什么意思呢?
凯里:露丝·哈伯德问,知道对你而言可能发生什么或者你没出生的孩子可能有什么问题,这意味着什么呢?没有人知道实际的情况是什么。人们只知道有风险。在某种数量足够大的全体公民中,X可能被预期为以一定的频率发生。你能干什么呢?这是露丝·哈伯德难以识别其含义的问题。
哈伯德:它的含义不是我理解不了的统计学问题。你有一些做了那些测试的聪明的人,她们说,是这样的,但它意味着有90%的机会是这个、那个和别的。是的,那又怎么样呢?有10%的机会是不可能。如果这样想的话,那么30%的机会就比10%的机会大。但是,90%的机会也是极为罕见的。它很可能就是10%或15%。不过,你知道的,这些人不可能容忍这个。所以她们要走向下一步骤。
凯里:当它是产前筛选出的一个问题时,下一步骤只可能是流产,因为至今仍然没有宫内治疗的办法。在将来,这样的决定能被在黑暗中的几个很少的镜头决定吗?露丝·哈伯德说,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有这样的承诺:医学将有一天能为私人定制基因组。但是,人们如何解释个人的基因组呢?她这么问。
哈伯德:他们有可能告诉你,你的DNA序列是什么,但这个含义还是概率性的。它没有办法可能使其成为别的东西。所以,如下的说法是欺骗:哦,我们这么做不仅是基于统计学,而且基于你自己的DNA轮廓。那么,你如何知道如何翻译我自己的DNA轮廓呢?仅仅是通过看看我自己的DNA轮廓吗?那太要命了。你必须查看许多不同的DNA轮廓并理解它们是如何叠加在一起的。于是,我们恰好又回到了概率问题,不是吗?
凯里:哈伯德对基因筛检技术倾注许多关注。他们强化了不可能的选择。他们使得妇女依赖那些执行并解释测试结果的专家。而她极为关注的所有其他方面是,基因技术现在发展了,不是为了公众利益,而是私人利益。
哈伯德:我认为,在所有这些事情中真正重要的是,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利益,在每一步骤中都有钱可赚。要点是,一旦你拥有一台能提供统计数字或者预测其他任何信息的仪器,你就要通过使用它来分摊购买成本。所以,一旦你不得不在每个医生办公室或者其他医生办公室里做其中的一项,那么,你就陷入那个医生或健康中心或诸如此类的经济利益中(对于你来说不仅仅是利益而是必要的),医生说服你、你、你、你,以便让我们大家都去用它,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对它付钱的原因。
凯里:“优生学”一词来源于人类的遗传适应性或其部分能够和应该可以改进的想法。该术语由查尔斯·达尔文的堂兄弟弗朗西斯·道尔顿于1883年杜撰。1921年第二届国际优生学大会把它定义为“人类进化的自动引导”,并且这一定义非常贴近道尔顿作为达尔文主义运用的一种新科学观的精神。在说英语的世界里,优生学吸引了许多著名的追随者,包括H.G.威尔斯(H.G.Wells)、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结果,在许多行政管辖区内,那些广泛散布的强制节育的思想并不适合生殖。纳粹德国也用优生学的术语定义自己——国家社会主义,该党的一个领导人,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说它是“应用生物学”。但是,结果令人恐惧的事情是,在一个时期,德国人完全不相信这一整个思想;并且在二次大战后的一个时期,优生学总体上被看做一个缺乏开明性的过时的东西。今天,基因技术已创造了优生学的一种新形式,虽然只有反对者应用了这种充满高度情感性的标签。露丝·哈伯德一直是这些反对者中最直言不讳的一个。就在分子生物学努力将人类作为他们基因的产品来理解之初,哈伯德就看到,这一事业必将导致提出“谁应该和谁不应该生活在世界中”的问题,在《女性生物学的政治》一书中,她提出了这个问题。当遗传信息积累时将会发生什么,该问题至今仍未见分晓;并且研究者开始去识别暴力、上瘾或其他有害行为的遗传倾向。目前,撇开性别选择不谈,当代优生学一般都使用基因筛查法以避免即将诞生的孩子可能遭受的疾病或残疾。在背后支撑它的是“基因神话”,露丝·哈伯德这么说,这也是她和她儿子伊利亚·沃尔德合著的名叫《破裂的基因神话》一书中使用的措辞。
哈伯德:如果你知道某些人的基因会表明他们将有或可能有的什么特点,那么,这并没有告诉你他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确实是这样的。事实是,基因检测到有蓝眼睛,这并没有告诉你会有这样的孩子,除非你碰巧成长在纳粹德国。我说的是真的。生命是很复杂的,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去弄明白:生命仍然是复杂的,我们不是去找简单的问题和简单的回答。
凯里:你和你儿子在《破裂的基因神话》一书中所写的基因神话……你当时是怎么理解基因神话的?
哈伯德:这种基因是预言性的。从个人的层面上讲,即通过在特定情况下了解你的基因你将能知道你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基因是预言性的。我们那时论证的是,就个体而言,即使在最可靠的情况下,你还是不了解其成长状况。在大多数情况下,你真正知道的仅仅是统计学意义上的东西。
凯里:哈伯德这里所说的可靠情况,是指家族黑蒙性白痴病(Tay-sachs disease)。这种病在东欧犹太人血统中大量发生,非常致命。他们患这种病的概率为1/3600,而在一般人口中患这种病的概率为1/100000。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现携带相关基因的精确检测一直有效。哈伯德说,这对于基因筛查是最好例子。
哈伯德:如果你的胎儿有双份涉及家族黑蒙性白痴病的基因,那么,其几率是相当好的或者是相当坏的,即孩子将患有在几年内死亡的一种疾病。所以,如果你想要查看是否有这一妖魔,那么,是的,你确实需要对父母双方进行检查。并且,如果父母双方都是阳性的,那么你就可以说——我的意思是它是隐性的——对于每个孩子来说,有四分之一的机会会得这种疾病。如果你感觉你不能忍受这个……
凯里:这是已知情况中最强的、即一个人在这一地区可能患该病的最肯定的情况吗?
哈伯德:四分之一的机会是你在该地区可能患该病的最肯定的情况,并且这是最强的情况之一,因为它是那些罕有的几乎不变的条件之一——或许你甚至可以把“几乎”去掉——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它是毁灭性的——你知道的,就是在2或3或4岁的时候。然而,我曾听说有这种经历的家庭提出异议,以及有其他孩子的家庭也提出过异议,这也是人类现实的一部分。并且,我确实会认为这对我们家庭来说是一个完全糟糕的经历吗?我不这么认为。但是,你知道,这依赖于你如何看待这个世界。让我们来谈论唐氏综合征(Downs syndrome),毕竟,可能大多数患者因此而堕胎。当今,你肯定用改进了的或不同的方式处理患唐氏综合征的孩子,许多家庭也会这么说,你知道,这是我们的孩子。你知道,也会有家庭说,这是我们的孩子,并且我会再生一个。我真的愿意要另一个没有患唐氏综合征的孩子,因为我也愿意有孩子的另一种经历。这确实非常依赖于你对生活、世界、健康和疾病、生与死的认识。
凯里:露丝·哈伯德通过回顾20世纪40和50年代她在实验室中研究眼睛的化学过程的时光开始今天的节目。那几乎就是为科学而科学的时代。她和她的同事仅仅就是试图理解一些事情是如何发生的罢了。在彩虹的尽头没有最终的宝藏,在观念上没有利润丰厚的技术衍生产品。在这期间,许多事情已经改变。生物学已变成了大企业。许多关于科学的纯洁和高尚的安慰想法也已经衰落。当然,也有例外。但是,露丝·哈伯德总结说,总体来说,科学简直就是个它隶属于其中的社会。
哈伯德:科学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又回到这个事实,科学是另外一种赚钱的事业,在其中有许多新的赚钱方式。此外,科学也是这样的一项事业,在其中,奖赏转到那些伴有最多金钱的事情上。它不再比别的东西更为纯洁。它或许比到外面买土豆纯洁。从某种程度上看,我们居住在想象的地方,因为只有对于像我一样的、把生物学看做在一种贫乏——经济上的贫乏——的科学中长大的人来说,事物才是变化的。化学家永远居住在这个世界中。永远。我的意思是,自哈勃(Haber)时代以来一直是这样,比如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因I.G.法尔本(I.G.Farben)这样的公司而获得巨大成功。而物理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所有他们生产的玩具包括炸弹而获得巨大的成功。生物学家有幸生活在一个更长时间段的纯真时代,以至于当我从那里起步时,那里已没有那么多钱可赚了。我不知道——我想象的——但我敢跟你打赌,乔治的首次拨款是500美元或1000美元。然后,它现在变成了10 000美元。哦,我的天[这与我们那个时代比也太多了]。我现在还记得,当我们发表一些东西或者做个报告、或者当我们用一种来自鱼肝油的维生素A来说明值得重视的事情时,我们获得了许多视网膜紫质的合成物;但是,当我们使用来自一些药房的结晶维生素A时,我们几乎没有获得什么。孩子,明天或者下周就会有人打电话来谈鱼肝油的事。为这事、那事和其他事,他们会邀请我们出去吃饭,诸如此类的;他们会为我们提供资金,让我们证明鱼肝油比结晶维生素A对眼睛更好。我们会心地笑了。我的意思是,你懂的,我们并不想进入这种状况。我的意思是,事实上,我们当时确实试图弄明白它们的不同点是什么,而这导致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原来维生素A有不同的形状,并且只有一种形状适合制造视觉色素。这是一项值得我们投入5年或10年的有趣工作。但是,我们不是处在像伴有DNA重组的生物学的大时代。你可能立即会说,它将会发生,因为所有的科学家突然间蜂拥排队等候获得资金。
凯里:在20世纪60年代,当露丝·哈伯德开始思考高科技战争中——之后在越南被发动——科学的作用时,她就首先想到并一直坚持这样的结论。她最后说,科学不可避免地必定是其社会的一个创造物。
哈伯德:很不幸,科学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系统有关。科学是政治。它与社会系统有关。作为一个科学家,你真的无法摆脱它。我猜想,你可以把自己卖了,但你必须非常有意识地作研究,并且你知道你为什么研究、如何研究。所以,只要当下的道德标准操纵局势——我不喜欢道德标准这个词,我实际的意思是指政治——政治一定首先出现。除非政治首先出现,否则,你就是待售的、就是要被购买的。
(淮阴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王荣江译校。标题、摘要和关键词为译者所加。)
责任编辑:王荣江
中图分类号:N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16)04-0446-07
收稿日期:2016-03-20
基金项目: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BZX023);2013年度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13ZXB003)。
作者简介:露丝·哈伯德(Ruth Hubbard),哈佛大学生物学教授,《女性生物学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Women’s Biology)一书的作者,并与她儿子伊利亚·沃尔德(Elijah Wald)合著《破裂的基因神话》(Exploding the Gene Myth)一书。
【科学哲学·如何认识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