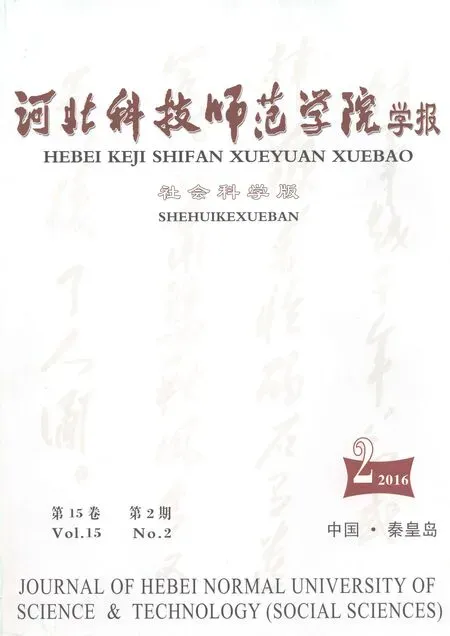论《牡丹亭》的叙事特色
任佳希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0)
论《牡丹亭》的叙事特色
任佳希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0)
汤显祖的《牡丹亭》是继《西厢记》后中国古代爱情戏剧的又一高峰。它的成就不仅在于思想上对“情”的高度赞扬,而且体现在高超的叙事技巧上。《牡丹亭》在叙事结构、叙事时空方面的设计独具匠心,创造性地设置了双线并行的叙事结构与交叉立体的叙事时空,体现了达情的叙事效果。
《牡丹亭》;叙事结构;叙事时空;叙事效果
《牡丹亭》是明代著名戏曲家汤显祖的代表作,沈德符在《顾曲杂言》中云:“《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1]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2]1汤显祖特别强调“情”的作用,认为创作都是“为情作使”,因而创造出双线的叙事结构与巧妙的叙事时空,来宣扬他“至情”的戏曲主张。
一、双线并行的叙事结构
汤显祖的《牡丹亭》讲述了一个奇幻的爱情故事:南安太守的女儿杜丽娘因情生梦,在后花园中感梦柳生,梦醒后因情不得抑郁而终,死后经历冥界的审判又回到人间,邂逅梦中人柳梦梅,二人经历一番波折后终成眷属。《牡丹亭》在叙事文本中所展现出来的这些内容,在叙事学中称为“故事”。
“‘故事’是指从叙事文本或者话语的特定排列中抽取出来的、由事件参与者所引起或经历的一系列合乎逻辑的、并按时间先后顺序重新构造的一系列被描述的事件。由此不难看出,故事属于蕴涵着一系列事件的一个更大的结构。”[3]
法国的叙事学家巴尔特把这些意义重大的并且处于事件转折处或关键点的事件称为“核心”事件;把意义小一些的事件称为“卫星”事件,它用以补充、丰富、联系、完成核心事件,使之丰满、具体、连贯。借此,《牡丹亭》可以分出三个“核心”事件,同时它们又具有叙事线索的功能。
第一个事件,因情而死。内容大致从第一出到第二十出,生长于官宦之家的杜丽娘在这一事件中作为行动主体频频活跃在事件中心。从小止于春闺的千金小姐杜丽娘,每日不过做些针织女工。父亲杜宝为了让她出嫁后能知书知礼、谈吐文雅,聘请腐儒陈最良讲授《诗经·关雎》,即陈最良口中的“后妃之德”。杜丽娘看似平静的面庞下却已萌动了情思。于是在得知府中竟然还有一个花园时,冒险让人肃苑游园。满园的春色让她感慨万千: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恁般景致,我老爷和奶奶再不提起。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窗——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2]45
园中繁花似锦的盛况更是冲击了杜丽娘的心房,看着满园的春色,只能任由它由盛转衰。由花度己,杜丽娘感慨自己年华正好,却不得婚配,只能虚度大好的春光。情思萌动展现了她心里最本质的欲求。柳生入梦,慰藉了她对情的渴望。梦醒时分,杜丽娘寻梦、写真、苦苦寻觅,于是相思成疾,直至缠绵病榻,香消玉殒。
杜丽娘作为此次“核心”事件的“核心人物”,主导着整个事件的发展和走向。而次要人物柳梦梅为配合核心事件的发展而出现。在剧情发展到杜丽娘“游园惊梦”时柳生上场,退场后作为另一支线中人物缓缓发展剧情——为谋求仕途“诀谒”上京赶考。
至于其他零星散落在事件中的“卫星”事件,大多只是过场戏,帮助完成剧中各式人物的上场定型。如第四出《腐叹》,将陈最良迂腐、庸俗的老学究形象生动地勾勒了出来;第八出《劝农》,对杜宝的功绩大加赞颂,着重刻画他勤政爱民、为国忘家的一面;第十七出《道觋》,虽开始对石道姑极尽刻薄的描述,但最后也让她逃离了世俗的桎梏,站在了情欲的肯定面;第十五出《虏谍》,完颜亮登场,因他觊觎西湖挑起战事。这里的“卫星”事件完成了剧中各式人物的登场,不但推动了情节的发展,还起到缓冲紧张的戏剧氛围、调节戏剧节奏的作用。
第二个事件,为情复活。从第二十一出到第三十五出,剧中的核心人物转换到了柳梦梅身上。在第二十出《闹殇》中杜丽娘逝去,她的身影便淡出人们的视线。柳梦梅作为行动主体,剧情重心就转移到了他的身上。柳梦梅为考取功名拜谒高官苗舜宾,从广州奔赴临安赶考,途径南安梅花观(杜府旧址),寥寥几出,便将故事的时间推到了三年之后。而杜丽娘在经过第二十三出《冥判》、第二十七出《魂游》后才与柳生重逢,在石道姑等人相助下成功复活。
此处的“卫星”事件不再散落在各处,而是成体系串联起来。如随着金兵南下,南安太守杜宝迁徙淮扬守城,剧中战事步步紧逼。战争支线发展的情节逐渐增多,戏剧的重心也在逐渐转移。
第三个事件,战争事件。从第三十六出到结尾第五十五出,戏剧的战争主线与杜柳的婚走取应支线情节并行发展,在戏剧结尾处剧中人物齐聚一堂。战争主线中,作为淮扬安抚使的杜宝设巧计击退金兵,高升至丞相;在支线故事的发展中,书生柳梦梅终于蟾宫折桂金榜题名。在戏剧结尾杜宝对他多加责难,柳梦梅凭借状元的身份,据以力争,不卑不亢,赢得了皇权的认可。杜宝无奈接受,最终获得一个相对圆满的结局。
三个事件各有侧重的“核心”事件与“卫星”事件,各个主线与支线也都是并行发展。就整个戏剧框架来说,可以将三个事件合并为两条故事线索——第一个事件与第二个事件相合并,第三个事件单独成线,即杜柳的爱情线索与战争线索,杜柳的爱情线索作为主线贯穿全剧,而战争路线则作为支线起以辅助作用,作为衬托,构建一个战争纷乱的时代背景。《牡丹亭》双线并行的戏剧模式,以爱情故事为主,辅以战事,将爱情的柔美绮丽与战争的刚强萧瑟相结合,使得戏剧层次更加丰厚。
二、交叉立体的叙事时空
故事是由两个及两个以上的事件组成,而联系这些事件的方式有:时间、空间、人物、因果联系。《牡丹亭》文本中的叙事时空别出心裁。戏剧叙事时空是指剧作家对戏剧的故事时空处理而表现出来的叙事文本中的时间与空间。汤显祖在时空运用方面可谓出神入化,写到所需之处,尽可信手拈来进行巧妙地安排,从而构造了一个充满梦幻色彩的戏剧世界。
(一)超前的叙事时间
在故事的叙事时间顺序上,一般以故事的顺序为主,采用的是体现时间一维性的直线式的叙事方法。法国叙事学家托多罗夫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叙事的时间是—种线性时间,而故事发生的时间是立体的。在故事中,几个事件可以同时发生,但是话语则必须把他们—件一件地叙述出来,一个复杂的形象就被投射到一条直线上。正因为如此,才有必要截断这些事件的‘自然’接续。但是作者往往不试图恢复这种‘自然’的接续,因为他用歪曲时间来达到某种美学的目的。”[4]汤显祖在遵循这种线性时间顺序的基础上,又采用了一些非顺序的叙事时序来达到更好的戏剧效果。其中,剧情内穿插了预序内容来打乱正常的叙事顺序。预序就是将还未发生的事情先于故事时间讲述出来,也就是叙事时间先于故事时间。
《牡丹亭》的故事时间以杜丽娘的描写为起端,杜丽娘为情而逝后三年,柳梦梅赴京赶考路过南安使其回生后定婚配,之后二人赶赴临安取士。后得知金寇入侵,柳生前往淮安相助反遭疑,一番波折后圆满结束。而戏剧的叙事时间却在其中插入了柳生忆梦、花神与胡判官话语等预序内容。
第二出《言怀》是柳梦梅的出场戏,讲述他半个月之前所做的一个美梦:在花园的梅树之下立着个亭亭玉立的美人,二人梦中相逢。而真正的故事时间本应在第十出《惊梦》中才出现柳梦梅此人:
“〔回看介〕呀,小姐,小姐!〔旦作惊起介〕〔相见介〕〔生〕小生那一处不寻访小姐来,却在这里!〔旦作斜视不语介〕〔生〕恰好花园内,折取垂柳半枝。姐姐,你既淹通书史,可作诗以赏此柳枝乎?〔旦作惊喜,欲言又止介〕〔背想〕这生素昧平生,何因到此?〔生笑介〕小姐,咱爱杀你哩!”[2]46-47
因此,第二出《言怀》里柳梦梅出现的时间是在第十出《惊梦》的故事时间的半个月之后。第十一出《慈戒》的时间是紧随第十出游园惊梦之后,因杜丽娘的母亲甄氏前去瞧看杜丽娘,而她却是在游园后困倦独眠。第十二《寻梦》的故事时间是游园后的第二日,因杜丽娘回忆梦境时“昨日偶尔春游,何人见梦”[2]57,因此,第二出《言怀》的情节大致在第十二出《寻梦》之后与第十三出《决谒》相接。也就是说,柳生出现的时间是在第十二出《寻梦》之后。而《言怀》之后柳梦梅在第六出《怅眺》的情节也应向后推移。因此,第二出《言怀》与第六出《怅眺》皆为预序内容。虽同为预序内容,但因所在的位置不同,而决定它们起到的作用不同。第二出《言怀》柳生登场,通过柳生之口讲述梦境,将他意识中模糊不清的梦境几笔带过;第六出《怅眺》讲述了柳生的志向抱负,同时也缓解了戏剧节奏来迎接戏剧的第一个小高潮第七出《闺塾》。但这两部分预序内容的插入,却共同展示了柳梦梅作为梦境另一主人公,奔走在仕途的路上,同沉迷于梦境的杜丽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文中除了情节布局上的预序之外,剧中人物的言语中也含有预序内容,如花神、胡判官。在第十出《惊梦》中花神上场:
“吾乃掌管南安府后花园花神是也。因杜知府小姐丽娘,与柳梦梅秀才,后日有姻缘之分。杜小姐游春感伤,致使柳秀才入梦。”[2]47
第二十三出《冥判》中胡判官判案:
“〔旦〕劳再查女犯的丈夫,还是姓柳姓梅?〔净〕取婚姻簿查来。〔作背查介〕是。有个柳梦梅,乃新科状元也。妻杜丽娘,前系幽欢,后成明配。相会在红梅观中,不可泄漏。”[2]122
通过花神、胡判官这些鬼神之口,将杜柳二人命中姻缘已定之事昭告世人,从命运上肯定二人的情感,解除人们心里对这种不符封建伦理道德行为的厌恶。
剧中预序内容的插入,将即将要发生的事情——杜柳梦中相会,且二人姻缘已定,告知人们。这样,人们只能朝着已定事实的结果去观察发展,等待着已经知道所要发生的事,这样会降低读者与观众的好奇心理,但同时也会产生另一种期待,即期待杜柳二人的爱情究竟要如何进展的,在人们已知的剧情下,剧作家能够创作出怎样的新意来吸引人们去关注故事的发展。这样,预序反而引起观众另一层的好奇心去继续期待剧情的进展。
(二)多维的叙事空间
空间是联系事件的又一因素,作家往往通过空间的转换来完成连接、组织、发展事件。在《牡丹亭》中涉及多维的叙事空间,主要是横向与纵向空间上的转化。
首先,《牡丹亭》中横向空间上的转换,体现在剧中地点的切换。在《牡丹亭》中涉及多个场景地点,明确提及的有广州、江西、江苏、浙江四个省份。柳梦梅出场自报家门时地点为广州府,随后拜访寄居在潮阳县的韩子才。后诀谒暂住在广州府香山的苗舜宾,得其资助,举身前往临安(南宋时的京都,今日的浙江省杭州市)考取功名。路过南安府(今江西省内),被陈最良所救,暂住梅花观(杜宝旧时府邸)。后复活杜丽娘,恐事迹败露,二人相伴奔往临安取应。正值金兵南下,高中状元的柳梦梅应杜丽娘的请求前往淮扬。到达扬州地界时,被金兵阻隔,后又被杜宝打入大牢押往临安。而杜宝出场自称南安太守,在女儿杜丽娘早逝后,奉旨晋升淮扬(今江苏省内)安抚使,前去镇守。杜宝在扬州镇守三年,淮安又起战事,杜宝奉旨前去挽救危机局面,最后战事得胜返回临安。
在柳梦梅和杜宝的奔波周转中,剧中的地点通过他们的行踪,由点到面,从南至北,从东至西,范围几乎涵盖了整个南宋时期的疆土领域,将当时南宋朝廷栖居江南的处境都展示了出来。剧中采用了一种戏谑的手法来描述当时的战争状况。南宋时期金兵南下,淮安首当其冲。剧中描绘得却不是萧条、血腥、残忍的战争场面,而是金兵的目光短浅、朝廷的用人不当、官员的庸碌无能。金兵南下,先锋却是南宋人李全;一纸降书只需“讨金娘娘”之称。甚至一场领土之战,只为争夺西湖的美景。这些可笑可悲的因素一扫因战事带来的悲凉之感,留下这些诙谐讽刺处供人思考。
其次,《牡丹亭》中纵向空间上的转换,体现在虚实阴阳场景的切换。从理论上来说,时间和空间作为物质的存在方式,二者不可分割,在一个情节中往往只对应一个固定的时间和空间。但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即同一时间对应不同的空间。
梦境与现实场景的切换。“梦并不是空穴来风”[5],弗罗伊德在《梦的解析》中肯定梦是通往人意识和潜意识的最佳途径。在睡梦中人的理智与道德束缚就会放松,心理最深层被隐藏起来的东西就会浮现出来,因而梦可以展示人类最原始最本质的情感。《牡丹亭》中的杜丽娘通过梦境展现了她对情感的欲求。杜丽娘从小长于深闺,严重的封闭性割裂了她与外界世界的联系。因而在她爱好天然与自由的天性被束缚后,她内心逐渐产生了反叛的心理。于是杜丽娘在看到满园的春色后,潜藏在她意识下对情爱的渴望就被激发了出来。在花神的相助下,在同一时间创造出了与现实空间相并行的梦境空间。柳生入梦,抚慰了她心理对情爱的诉求。梦本身具有虚幻性,梦境中的人事物皆为虚假,梦醒时分就烟消云散。而杜丽娘却对梦境流连不已,冒险两次寻梦,甚至郁郁寡欢缠绵病榻。她的梦境严重影响到了现实生活。剧中梦境参与了整个故事的发展,梦境与现实的界限不再清晰,二者相互影响,虚实相渗,虚实同一。
阴阳两界场景的切换。在杜丽娘去世之后,戏剧按照时间线继续向前进展,讲述柳梦梅进京赴试的过程。在此并行的时间内,汤显祖构造了另一个叙事空间,即冥界地府。杜丽娘死后归于地府,由胡判官进行判决。当年的柔弱小姐在地府为自己的感情据以力争,却被贬入莺莺燕燕之中。也就是说,在胡判官的律法和道德准则里,杜丽娘慕色而亡与之前“花间四友”一样都是有罪的。这样“情”的理念在现实生活中被活生生的扼杀,在冥界又被禁制,杜丽娘甚至还要因此剥夺为人的权利。阴阳两界将“情”的出路都给堵死了,来维持封建伦理道德所谓的纲常。然而,花神为杜丽娘求饶,“且他父亲为官清正,单生一女,可以单饶”[2]122,幸亏杜宝身为南安知府,又升迁为淮扬安抚使,于是胡判官看在他的份上准备奏过天庭再来判决。杜丽娘苦苦询问真相,只见婚姻簿上明文显示:“有个柳梦梅,乃新科状元也。妻杜丽娘,前系幽欢,后成明配。相会在红梅观中。不可泄漏”[2]122,胡判官大手一挥,释放了杜丽娘。杜丽娘的释放,不是胡判官为其情深动容而法外开恩,而是碍于“权”与“命”的制约,服从办事而已。终究“情”抵不过“权”,“权”抵不过“命”。
《牡丹亭》在多维的叙事空间上为我们呈现了一种世界观,即天地都由同一种秩序所制约:封建秩序。不论是世上的高官、市井流民,还是逃离凡尘的花神、判官,他们都被这种秩序所束缚,严格地秉持着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于是阴阳两界生生堵死了为爱执着的年轻男女们。因而汤显祖只能通过梦境这个虚幻不受拘束的空间去实现他对情爱的赞颂。
三、达情的叙事效果
汤显祖的《牡丹亭》是根据明代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改编而完成的。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讲述了南宋光宗时广东南雄太守杜宝之女杜丽娘,在游园之后感梦而亡,她生前自绘的小像死后为柳太守之子柳梦梅所得。柳梦梅日夜思慕,后与杜丽娘的鬼魂幽会。最后开冢还魂,二人结亲。
汤显祖在遵循话本故事情节的基础上,对戏剧的叙事结构与叙事时空进行了大胆的创新。戏剧的主题思想也不再单单是自娱与娱人,而是传达“情”的理念。美国的埃德加·爱伦·坡将打动读者的心灵效应作为创作的基础,“通过语言去引发读者的某种情绪,达到他所谓的‘预设效果’”[6]。因此,剧作家汤显祖通过娴熟的技巧,创造新的戏剧情境与新颖的戏剧结构,来取得 “达情”的叙事效果。
首先,双线并行的叙事结构。话本中,慕色而亡的杜丽娘顺利还魂,与柳梦梅结成夫妇,而且毫无阻碍地得到了父母的认可,以大团圆结局。而在 《牡丹亭》 当中,杜丽娘与柳梦梅历经周折,又遭受了战争的磨难,方才得到认可。汤显祖没有一味地描述男女缠绵悱恻的爱情,而是佐以战事,构建了一个战火纷飞的时代背景。战争支线的增加,使得杜柳二人遭受了更多磨难,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爱情的主题更加深入人心。
其次,超前的叙事时间。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遵循线性时间顺序,按照时间顺序将事件一个个镶嵌在时间格中一步步发展。而《牡丹亭》在线性时间的基础上,插入预序的内容,先于故事时间告知人们杜丽娘与柳梦梅的命定之情,夫妻之分。将二人之情以肯定的形式先得到人们的认可,然后再继续叙述二人之情走向夫妻之分的发展过程。超前的叙事时间为二人情感的完成和得到人们的“认可”打下了基础。
最后,多维的叙事空间。汤显祖更改了人物所处的地点,并加入了多个场景。通过人物的奔波来连接地点,勾勒出了当时金兵南下时,南宋栖居江南的疆域版图。地点的更改,为“情”营造了一个封建闭塞混乱的氛围,同时也加深了“情”的深刻性和社会性。戏剧就话本中的梦境也进行了一番改编。梦境在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中只是杜丽娘满足内心情欲的空间。而汤显祖在《牡丹亭》将梦中之情从虚幻中拉进现实,并赋予它战胜生死与冷漠世界的力量,同时又创造出冥界这一虚幻的空间。杜丽娘魂魄归于地府,由胡判官进行裁夺,这增加了她由死转生难度,也衬托了杜丽娘为情据以力争的气魄。此时剧中之情堪比金坚,而不再是话本中单纯的欲望。
除此之外,人物调整也是戏剧改编的一处亮点。《牡丹亭》中人物变动主要有:陈最良、石道姑、花神、胡判官、柳生父母等。其中最明显的是柳生父母的删除。失去父母的护佑,柳生便成了一个穷苦书生。而杜丽娘是杜宝唯一的子女,门不当户不对,且阶级地位悬殊,更是增加了二人情感路上的坎坷。而杜宝父女性情的差异,也带来了冲突。剧中杜宝冷漠权势,杜丽娘情比金坚,增加了以杜丽娘和杜宝为代表的矛盾双方的冲突。在冲破诸多阻碍之后,杜柳二人“有情人终成眷属”,使得“情”的主题更深入人心。
“为情作使”是汤显祖创作的原则。汤显祖运用娴熟的技巧对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进行创造性地改编,剧中所表现出来的独具特色的叙事技巧,是为了使“情”的戏剧主题得到更好的诠释,为了能让剧中的情感能得到更好的表达。
结 语
综上所述,《牡丹亭》作为汤显祖戏剧的代表作,展现了汤显祖卓越的叙事技能。这种叙事技能主要体现在他对文本叙事脉络的掌控能力以及对戏剧时空巧妙地安排上。而这些努力,是为了传达戏剧中的情感,完成“情”的戏剧主题思想。汤显祖对情感的追求,充满了蓬勃昂扬积极进取的精神,体现了他对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思考,同时也体现了汤显祖对人性的肯定和对人类主体人格的认可,这对当时沉闷的社会风气具有个性自由解放的影响。
[1]沈德符.顾曲杂言[M].北京:中华书局,1985:5.
[2]汤显祖.牡丹亭[M].徐朔方,杨笑梅,校注.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
[3]谭军强.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21.
[4]兹韦坦·托多罗夫.叙事作为话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506.
[5]弗洛伊德.梦的解析[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55-55.
[6]盛宁.人·文本·结构——不同层面的爱伦·坡[J].外国文学评论,1992:81.
(责任编辑:母华敏)
OnThePeonyPavilionNarrative Features
Ren Jiaxi
(College of Humanities,Wenzhou University,Wenzhou Zhejiang 325000,China)
ThePeonyPavilionwritten by Tang Xianzu is another peak of ancient Chinese love drama followed by theWestChamber. Its achievements not only lies in praising highly the ideology of affection, but also in its superb narrative skills.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narrative time and space ofThePeonyPavilionis quite unique, creating a double set of parallel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narrative cross-dimensional space-time arrangements, which reflected the effect of the narrative situation.
ThePeonyPavilion; narrative structure;narrative time and space;narrative effect
10.3969/j.issn.1672-7991.2016.02.010
2016-03-10;
2016-03-22
任佳希(1989-),女,河北省邢台市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戏曲。
I207.37
A
1672-7991(2016)02-005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