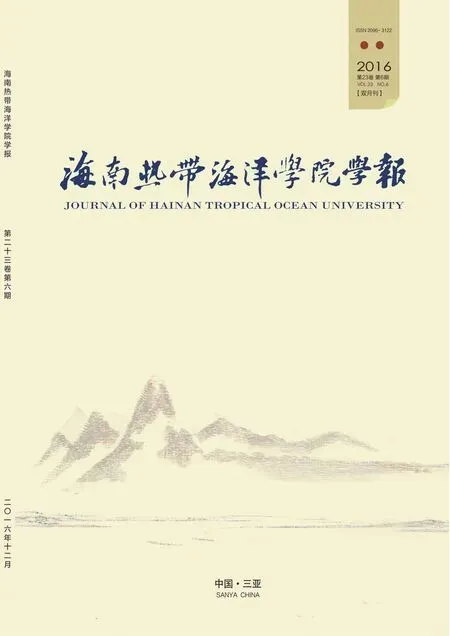论中国戏曲的通俗性品格
李宁宁
(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南宁 530006)
论中国戏曲的通俗性品格
李宁宁
(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南宁 530006)
戏曲可以说是一种通俗文学,而通俗性品格也是其最重要的审美特征之一,并且贯穿了整个戏曲发展的始终。可见,通俗性之于中国戏曲的重要性。对于中国戏曲来说,其通俗性品格主要体现在题材的日常化、结构和表现形式的单一化、语言的易懂化、音律的成规化这四个主要方面。从这四个方面来探究中国戏曲的通俗性,不仅能够深化研究者对戏曲通俗性品格的认识,最重要的是能促进中国戏曲朝着长远及健康的方向发展。
中国戏曲;通俗性;品格
引 言
中国戏曲作为一门集歌、舞、乐、念、白等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经久不衰。而其顽强生命力的源泉,究其本质,便是中国戏曲的通俗性品格。如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说:“像小说、戏曲,都要归到‘俗文学’的范围里去。”[1]由此可见,戏曲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通俗文学。对于何谓“通俗”?茅盾曾经这样解释:“‘通俗’云者,应当是形式则‘妇孺能释’,内容则为大众的情绪与思想。”[2]他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来说明通俗最主要的就是浅显易懂,贴近百姓生活,反映他们的内心诉求。但随后茅盾就又指出通俗和庸俗并不是同一个概念,而他的这一观念早在清代李渔的《闲情偶寄》中就有体现:“然一味浅显而不知分别,则将日流粗俗,求为文人之笔而不可得矣。”[3]21因此,通俗绝不等同于庸俗。虽说戏曲创作尚通俗,但也并非是一味求俗,而是要俗中见雅,这样才能将戏曲的通俗性品格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正如李渔所说:“能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3]23
中国戏曲之所以能长远发展主要在于其通俗性的提升与完善。戏曲的通俗性并不仅仅体现在某一方面,而是涵盖了题材、结构和表现形式、语言、人物以及音乐等多个方面。正是这多个方面通俗性的有机融合和透彻体现,才使得戏曲的通俗性品格更加完善。
一、题材的通俗性
题材的通俗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戏曲的通俗。戏曲是一种通俗艺术,其被郑振铎划归为俗文学的范畴,并认为戏曲是民间的、大众的文学。剧作家只有选取具有一定通俗性的题材才能适应观众的欣赏习惯,才能满足戏曲成为民间俗文学的要求。戏曲所表现的内容十分丰富,大都取材于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如家长里短、人情冷暖、婚姻爱情以及妇孺皆知的街尾巷谈等,这些都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这些普通的日常琐事经过剧作家的加工润色,便成为深受老百姓喜爱的通俗戏曲,正如陆学松所说:“底层人物的言行与文人们的精神追求相通,符合他们的内心动力因素,触发文人的大量创作就不足为奇了。”[4]针对戏曲的题材,明代王骥德在其《曲律》中提出了戏曲的虚实观。他认为戏曲在取材“尚实”的同时要进行一定的虚构,这样才能吸引观众。虽然他赞同戏曲的题材应取自民间,来源于真实的社会生活,但同时他也特别反对“捏造无影响之事”来欺瞒妇人和小儿。由此可知,王骥德也重视戏曲题材的真实性。但是真正做到戏曲题材尚通俗的是清代的李渔,他在《闲情偶寄·戒荒唐》中说道:“鬼魅无形,画之不似,难以稽考。狗马为人所习见,一笔稍乖,是人得以指摘。”[3]12之后又说:“凡说人情物理者,千古相传;凡涉荒唐怪异者,当日即朽。”[3]12由李渔的这番话可知,他极为重视戏曲题材的通俗性。他认为戏曲要反映现实社会中的人情物理,不能主观臆想,脱离实际。戏曲题材只有取源于真实的社会生活,才具有平易、通俗、为人所见习的特点,这样的戏曲才能取信于观众,赢得广大观众的喜爱与赞赏。例如河北梆子《蝴蝶杯》便是取材于民间的婚姻爱情故事,富家子弟田玉川因误杀总督卢林之子而出逃,在危难之际巧遇渔家女胡凤莲搭救,随即展开的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这个戏曲之所以广泛流传,正是因为其题材取自民间,具有很强的通俗性,因此为老百姓喜闻乐见。
二、结构和表现形式的通俗性
戏曲的通俗性包含有很多方面,除了戏曲题材的通俗性外,在戏曲的结构和表现形式上也呈现出通俗性特征。首先是戏曲的结构,戏曲大师汤显祖认为戏曲结构要“一线索到底”,主干清晰,不蔓不枝。到了王骥德,才有戏曲结构的系统论述。他十分重视戏曲结构的整体美,他在《曲律·杂论上》中就强调从全体力量来论曲。王骥德的戏曲结构论虽然重整体,没有过多涉及到结构的通俗性,但是他的观点对李渔“结构第一”论的提出有着至关重要影响。李渔虽有对王骥德戏曲结构论的继承,但更多的是创新,其“立主脑”“密针线”“减头绪”的戏曲结构理论便是重视结构通俗性的体现。李渔之所以强调戏曲结构的单一性,就是考虑到广大观众的理解能力。他认为戏曲的结构要围绕一人一事进行,避免过多头绪,如他在《闲情偶寄·词曲部》中评价《琵琶记》时曾说:“如一部《琵琶》止为蔡伯喈一人,而蔡伯喈一人又止为‘重婚牛府’一事,其余枝节皆从此一事而生。”[3]8李渔认为,普通观众的理解能力有限,而一人一事的结构安排简单明朗,便于观众了然于心,从而为普通民众了解剧情提供方便。例如李渔的戏曲作品《风筝误》便是以韩世勋和詹淑娟为全局主线,所有故事都是围绕二人展开,这样一条线索,减少头绪的结构就是易于广大观众理解。因此,李渔“结构第一”“一人一事”的戏曲结构理论正是戏曲通俗性的有力体现。
此外,在表现形式上体现戏曲通俗化的便是其形式的程式化。程式是在戏曲长期的表演实践中形成的,是经过戏曲艺术家高度概括的,被广大观众认同和接受的一种重要的形式。程式化的表演大都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符合人们的审美习惯,具有简单明了的特点。以鞭代马、以桨代船、以旗代军等这些程式化的表演方式具有通俗易懂的“无实物动作”特征,例如京剧《秦琼卖马》和越剧《孟丽君》等对“马”的刻画都离不开一条马鞭,仅仅用一条马鞭就能做出与马的各种互动,这就是程式化的表现。这样不仅能够调动观众的想象力,而且易于观众理解和接受,带有浓郁的通俗性色彩。
三、语言的通俗性
语言是架起戏曲与观众之间沟通的桥梁,语言的通俗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观众是否能够清楚明白的理解戏曲。因此,语言的通俗性在戏曲通俗性品格中也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语言的通俗性可以从曲文和宾白两方面分析。
首先是曲文的通俗性。曲文的通俗与否直接影响着观众对戏曲的接受效果。早在王骥德之前,就有徐渭、何良俊和吕天成等人推崇戏曲语言通俗易懂的本色论,他们反对刻意雕琢,主张清新自然,通俗易懂。沈璟更是直接将本色与俗字俚语等同起来,他们无不是真心地希望戏曲能被当时的观众广泛接受与理解。王骥德在吸取前人戏曲语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对戏曲曲文的理解,就是我们前文所提到的雅俗共赏。而李渔在继承王骥德戏曲语言理论的基础上更是提出了曲文要“贵浅显”“忌填塞”。如他在《闲情偶寄·贵浅显》中说:“话则本之街谈巷议,事则取其直说明言。”[3]18而后他在《闲情偶寄·忌填塞》中又说:“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3]23由此可见,李渔特别强调曲文的通俗性,重视观众的接受效果。但是李渔在重曲文浅显的同时也提出俗中见雅的审美标准,不能把俗与雅割裂开来,一味求俗而放弃雅的成分,会大大降低戏曲通俗性品格的艺术水准。
其次是宾白的通俗性。在古代的戏曲创作中,曲是戏曲艺术的核心 ,因此戏曲创作出现了重曲轻白的倾向。针对此种现象,很少有戏曲理论家对此进行探索。直到王骥德和李渔对宾白的作法研究,才弥补了中国戏曲史上宾白作法领域的空白。虽然鲜有戏曲理论家深入研究宾白的作法,但是对于宾白的通俗性,历代曲论家都十分重视。因为戏曲语言要具备通俗性,不仅曲文“贵浅显”,而且作为贯穿剧情,交代故事内容的宾白也要做到通俗易懂。针对宾白的通俗性,明代徐渭曾说:“唱为主,白为宾,故曰宾、白,言其明白易晓也。”[5]其意思就是说宾白要简洁明了,易于理解。与徐渭不同,王骥德推崇定场白要富有文采,但不晦涩难懂。而对于对口白来说,王骥德则要求明白简质,通俗易懂。总的来说,王骥德对宾白的态度是雅俗共赏的同时偏重于雅。之后凌蒙初在《谭曲杂札》中也要求宾白必须“直截道意”“不为深奥”。清代的李渔,在宾白作法和强调宾白的通俗性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指出宾白的创作需要从“词别繁减”“文贵洁净”和“少用方言”等几个方面入手,宾白的长短要视情况而定,用字要简洁明了,而且要避免使用方言入白,这样宾白才通俗易懂,为观众所理解。此外,清代的李调元、焦徇等人也强调宾白要通俗易懂。可见,宾白的通俗性与曲文的通俗性同等重要,都是戏曲通俗性品格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四、音律的通俗性
音律的通俗易懂对戏曲的通俗性品格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在戏曲的发展过程中,按谱填词逐渐成为约定成俗的音乐成规。而这种音乐体制以其通俗易懂的特点,受到观众的广泛欢迎。因此,剧作家在创作时不能随心所欲的破坏戏曲的音乐成规,因为这些成规已经深深地植入了广大观众的脑海里,破坏了这些音乐成规就等于破坏了观众日久形成的观赏习惯。明代的沈璟在戏曲音律体制方面就主张“合律依腔”,他严格音律,不仅强调音乐的形式,而且还考虑到观众的欣赏习惯,旨在以通俗易懂的形式提高戏曲的接受效果。而李渔在戏曲音律的创作上也特别重视其通俗特性。他要求剧作家“恪守词韵”和“凌遵曲谱”,反对那些不按音律填词而产生的一些聱牙和不顺口之语。他指出:“新造之句,一字聱牙,非止念不顺口,且令人不解其意。”[3]36这样的音律创作就很难达到通俗易懂的目的,而且也不符合观众的接受习惯,因此势必被人们所遗弃。但是按谱填词也给剧作家提出了更高要求,造成了他们创作上的难度。针对此种问题,李渔认为剧作家应该根据剧情的需要积极发挥曲谱音乐上的优势,这样所填的词就会灵动跳跃,就更能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从而为更多的观众所喜爱。此外,李渔在音律体制的创作中还注重“正五音”“清四呼”“明四声”和“辨阴阳”等,这些不得不说是他对沈璟的超越。
中国戏曲的通俗性除了体现在题材、结构和表现形式、语言以及音律这些方面外,还体现在人物、故事情节等其他方面。例如宋元以来戏曲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不再是清一色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逐渐代之以普通民众,作品描写的事件也多与百姓休戚相关,这些都是中国戏曲通俗性的体现。
结 语
通俗性品格之于中国戏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其不仅主导着中国戏曲的发展方向,更是中国戏曲经久不衰的动力源泉。通俗性艺术水平的提高,既丰富了当时的戏曲创作,而且也对日后戏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戏曲理论家徐大椿就深受李渔戏曲通俗理论的影响,认为戏曲是“愚夫”和“愚妇”共见共闻的娱乐化作品,他的戏曲理论显然是对李渔“俗中见雅”“言浅意深”的戏曲通俗论的继承和发展。此外,戏曲语言方面的宾白通俗论对后来的话剧演出也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例如经典话剧《茶馆》中的对白和独白就是贴近市民生活的通俗化的体现。但是随着对戏曲通俗性品格的重视,使得一些剧作家曲解了“通俗”的含义。而“文学审美品格的高下,归根结蒂是由作家的品格、气质和精神境界决定的。”[6]因此那些格调不高的剧作家为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市井常态,追求戏曲的通俗性而染上了市民思想的局限性,创作出了一大批流于肤浅的作品。可见,过度的理解甚至曲解戏曲的通俗性品格,不仅会拉低中国戏曲的艺术品位,还会导致中国戏曲陷入畸形发展的泥沼。而恰到好处的领悟和运用戏曲的通俗性品格,既可提升戏曲的通俗化审美水平,也会使中国戏曲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1]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1.
[2]茅盾.茅盾文艺杂论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729.
[3][清]李渔.闲情偶寄[M].沈新林,注评.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4]陆学松.清初传记文人物底层化倾向研究[J].琼州学院学报,2015(1):65-69.
[5][明]徐渭.南词叙录[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北京:中国戏曲出版社,1959:246.
[6]龚斌.论齐梁萧氏文艺的美学品格[J].琼州学院学报,2014(6):3-12.
(编校:李一鸣)
Popular Character of Chinese Opera
LI Ning-ning
(School of Arts,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530006, China)
Opera is a kind of popular literature, and its popular character is one of its most important aesthetic features and runs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pera. It is clear that the popularity is important to Chinese opera. For Chinese opera, its popular character is mainly embodied in the four aspects: the daily life of the subject, the simplification of the structure and the expression, the understandable characteristic of the language, and the regularization of the temperament. From these four aspects to explore the popularization of Chinese opera, researchers can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popular character of the opera, an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it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opera in the long and healthy direction.
Chinese opera; popularity; character
2016-06-15
李宁宁(1990-),女,河南洛阳人,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I207.3
A
2096-3122(2016)06-0112-04
10.13307/j.issn.2096-3122.2016.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