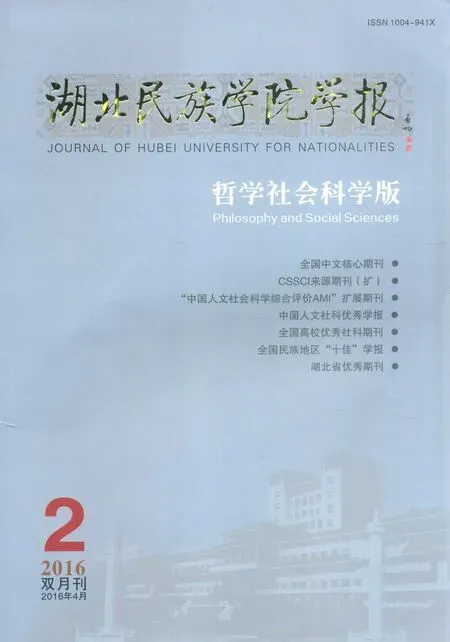拉康化的后马克思主义研究
——以阿兰·巴迪欧为例
彭均国
(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300387)
拉康化的后马克思主义研究
——以阿兰·巴迪欧为例
彭均国
(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300387)
当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盛行,以利奥塔、德里达等人为首的后现代主义氛围弥漫,社会主义理论面临着巨大挑战。于此时,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阿兰·巴迪欧,以拉康精神分析理论做方法、康托尔数学集合论为基础,对利奥塔和海德格尔等人发起的挑战进行批判;重塑由真理—事件—主体构成的三位一体的巴氏本体论;高举马克思、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大旗,批判资本主义;高举工人阶级旗帜,将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理论与实践的最终归宿,巴迪欧以一种胆量和气魄续写了共产主义。于巴迪欧之研究,探讨其如何以哲学为基,构建巴氏共产主义信念。然而,巴迪欧的共产主义思想依然存在很多缺憾,往往徘徊于现实与信念之间,可谓是存在于信念与现实之间的一位布道者。
巴迪欧;事件;行为;大写的一;共产主义
2009年专门针对巴迪欧《共产主义的假设》举办了“共产主义观念”的伦敦大会。在探讨国外社会主义思想时,阿兰·巴迪欧无疑会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于海外,巴迪欧之思想影响巨大,然而,国人知其人者寥寥,亦或对其理论了解不深。巴迪欧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点,在《概念的模式》、《存在与事件》等著作中,力图实现其理论的宏大哲学叙事与关怀;在《矛盾理性》、《主体理论》中又强调群众主体,以图实现政治关怀;在其关于电影的著作中,又力图实现美学关怀,并实现对现实的剖析。在其名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巴迪欧就试图关注于一个“无调”的世界,解构一个秩序性的世界,还原一个具有多元实践的复杂性世界。然而,巴迪欧之理论关怀远非限于此,其理论当为我们广泛研究。相反,在研究中,我们也应该看到巴氏理论不免带有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如同空想社会主义一般;对“事件”的极端崇拜不过是对历史偶然性的喜好,其理论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甚大,有时截然相反。但不容置疑的是,阿兰·巴迪欧在信念上坚信共产主义,在理论上部分承袭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现实上,忠实于客观事实,为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残喘的西方社会主义带来了新的“福音”,以精神的方式解救他们,将自己心中的信念带给芸芸众生,为他们点亮一盏去往共产主义的灯。
一、批判:对利奥塔和海德格尔所做的批判
这是一个话语时代。在哲学话语体系下,海德格尔和利奥塔同时对哲学做出了死刑判决。他们认为自然科学日新月异、人文科学突飞猛进,而作为形而上的哲学应该悄然离世。然而,阿兰·巴迪欧却借康托尔之集合论,对此种“谬论”进行严厉的批判,坚信哲学并未终结,共产主义必须存在。20世纪解构主义和语言分析的方法流行起来,作为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之基础概念被逐一“解构”。利奥塔就采取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规则”的一种相对主义的方式,宣告哲学终结。他认为根据规则之不同,世俗世界中的任何事物或话语之内涵就不同,任何一种叙事都将以规则为参照,规则成了“元叙事”。于是乎,世俗世界成了元叙事的世界,任何行为都变得毫无意义。从历史观上来考察,元叙事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肥皂泡式的幻想,幻想不值得认真,娱乐至死的生活态度被毫不遮掩地表露出来。与利奥塔不同,在海德格尔的眼里,“此在”被无情地抛入“此世”,并由于与自己的存在之根断裂,人只能在“此在”的有限性中不断寻找存在的无限性,于是乎一种惆怅便产生了,即海德格尔的所言“在世之愁”。“此在”与“存在”就成了无法接连的断桥,唯有通过诗性的语言(而不是单靠语言)两者才能有所联系。如其所言:“人之说话的结构可能是那样一种样式(Melos),语言之说,亦即区—分的寂静之音,通过区—分之指令而使终有一死者归本于这种样式。”[1]海德格尔依靠语言缝合哲学和诗,语言成了达至本体论之唯一途径,本体论被黯然埋藏于语言之中,使之作为形而上学之哲学被最终消解。于是乎,他也得出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哲学终结了!
在哲学被判死刑时,巴迪欧义无反顾地声称哲学并未终结,数学成为哲学之本体有其可能性和合法性。但传统之数学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原因在于传统之数学认为数与数之差异正是相互叠加或减除而来,而这种叠加或减除正是依靠数的规则进行。显然,这种阐释依然未能走出利奥塔的规则逻辑。巴迪欧借康托尔的集合论找到了一条去往无限的通道。康托尔认为任何一个集都由多元素构成,异质性的各集之间形成一个连续统,并达至一(具有统一性的整体)。然而康托尔未能交代一从何来。对此作出贡献的是科恩。科恩认为只有依靠主体的强制性赋予诸元素以不同概念或名称,而概念成了一种附加在诸元素之上的类性真理程序,此程序正是通过减除得来。这样一来,元素之间的差异性完全不能依据确定的规则表现出来,而依靠主体的积极行动获得类性真理程序,主体积极行动的介入打破了集合中元素的必然性,偶然性成了主导,无限便成为可能,并达至“一”。数学之一虽然解决了利奥塔的问题,但显然不能解决海德格尔的“断裂”,况且巴迪欧认为整体作为一的形式存在,其本身就是对本体论理解的障碍。巴迪欧以一种“回归柏拉图”的方式,认为“一”并非作为“整体”存在的图像,而是“一即为空”,唯有多元的内在性质才是本体论之真。作为本体论之数学的诸元素正是纯粹多元性的存在形式,这样巴迪欧采用颠倒被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即颠倒尼采对柏拉图的颠倒),使数学之间的关系变得息息相依。换句话说,构成系统之诸元素彼此异质最终导致了相互之间的“断裂”,然而各元素由于被力迫主体赋予强制性概念(或类性真理程序),诸元素又相互联系起来。
毫无疑问,在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发起挑战之际,巴迪欧以数学为基础捍卫了哲学。无论是对海德格尔的批判,还是对利奥塔的指责,巴迪欧最核心的一个元素就是“主体行为”。“主体行为”强调主体的积极实践才是改变世界的方式,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实践论的践行者毛泽东高度一致。人对现实世界的表象性图像是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然而,巴迪欧以数学做本体,虽然有主体的介入行为,但本体论终究表现出数的规则性,将哲学本体论又引入一个“规则”游戏圈。数学本体论只不过是一个更为抽象的本体。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关注社会现实已截然相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认为,世界的本原在于物质,而非物质性,物质范畴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唯物主义的基石,客观实在性才是物质必然的属性。物质本体论与数学本体论在此豁然地表现为唯物与唯心的对立。尽管如此,与宣扬本体论瓦解的思想相比,巴迪欧将本体论归属于抽象范畴的数学,但却捍卫了本体论存在。当然,这与巴迪欧受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密不可分,他正是采用拉康式的精神分析方式对本体论进行重塑。
二、重塑:三位一体的本体论构建[2]
巴迪欧认为,后现代主义在本体论的构建上完全陷入了一种本质主义的泥潭,而不可自拔。巴迪欧试图以一种以数学集合论为外形、以拉康式的三元结构为内核的模式,取而代之。这种模式就是真理—事件—主体的巴氏三元结构模式。
拉康认为真实域和象征域之间的断裂唯有依靠主体之想象才能同一。巴迪欧与齐泽克一样,采取借用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三大范畴,即象征域、想象域和真实域,完成了对本体论的重塑,提出了他的真理、事件和主体的三位一体的三元结构模式。关于真理,福柯、德勒兹、加塔利等后现代主义者如同遵守柏拉图“正义就是强者的逻辑”一般,认为真理源自于强权,正义是弱者的呼声,权力才是真理的构造者,否认真理的绝对存在。这种权力—真理的真理结构模式,必然造成社会高低等级之分,由此而来,整个社会将被侵略性所主导,部分群体被边缘化。巴迪欧反对这种以权力为主导的真理观,批判“真理是权力的附属品”的意识形态。但在真理观上,也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范式。他认为真理之存在必然是与主体和事件有关。其一,真理不外乎主体的积极行动。换句话说,真理本身匮乏至极,真理之所以存在,完全来自于主体的创造;在此,巴迪欧看到了主体的创造性行为,无主体行为就无真理可言,也就意味着认识到真理的相对性。但将真理完全归结于主体行为,也必然否定真理的绝对性,真理的客观性也将荡然无存。其二,主体的创造行为并非个体创造行为,而是一种被公认的共同创造行为,因此创造行为具有共同可能性;但是,在“共同可能性”的观念上与齐泽克所认识的不同。齐泽克认为“共同可能性”(巴迪欧语)不过是整个社会的共同“幻想”(齐泽克语)。其三,主体之创造行为必须以事件为依托,即忠实于事件。换句话说,真理不过是主体通过自己积极的行动,从事件中创造出来的“真实”。真实并非现实,“现实”属于拉康的象征域范畴,现实不过是真实的象征形式,“真实”才归属真实域范畴。可以看出,巴迪欧完全仿照了拉康。由此看来,在真理观上,巴迪欧力图摆脱唯心主义性质,并努力地向马克思唯物主义性质靠拢,并不想在理想的世界欢度,而是乐于在现实世界中耕耘,但始终不可抵达。关于事件,齐泽克与巴迪欧一致,都从更为抽象的层面来界定“物”的概念,将“物”界定为真实而非现实,共同认为物质性(而非物质)就是事件。巴迪欧认为,现实中的如昙花一现般出现的事件掩盖了真实,只有采取忠实于事件之方式(即主体表现出对事件的偏好),才能获得一条通往真实之路径。那么事件为何呈现,何时呈现?巴迪欧在此赋予事件以偶然性。他认为,事件具有不连续性,事件的突现纯属偶然。在先前的情景状态中也无迹可寻。这样一来,事件又成了“不可能”。这种不可能与齐泽克的“现实存在而不可能出现的不可能”不同,这种“不可能”既是不可能预测,又是不可能发生。正如《存在与事件》中所表达的那样:“一个事件就是一个纯粹偶然,它不可能从先前的情景中推导出来。”[3]又如《普遍主义的基础》所言:“事件的本质就是它不会有任何事先的征兆,以它独有的方式让我们震惊。”[4]不仅如此,巴迪欧认为事件也是一种存在着的非存在。虽然“事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无论事件消失得再迅速,它依然存在过,以至于存在的同时也消失了。或许这种情境就是巴迪欧希望达到的辩证唯物主义情境。关于主体,三元结构的最后一个元素就是主体,如同拉康的想象域一样,想象域接合了真实域和象征域;巴迪欧认为,在真理与事件之间唯有依赖主体的行动才能达至同一。主体的积极行动缝合了真理与事件之间的巨大鸿沟。然而对于主体之理解,他不像阿尔都塞那样将主体置于虚无境地。相反,他认为主体存在。但是这种“存在”与传统意义上的绝对存在又有所区别。他认为,主体之所以存在正是由于自己主动的积极的介入到事件中的行动才存在,即主体以自己的行为来证明自身的存在,主体之存在并非因其天然的生物属性,而是生活实践活动本身。毫无疑问,我们看到了事件与主体之间的互为条件性,主体以“非存在”的状态存在(即“非存在”也是一种存在方式),而“非存在”之状态正是一个事件。姑且不论这种认识是否恰当,但可以看到巴迪欧将主体放入一定的行为关系中来考察,而这种实践的观点源自于对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仰,又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主体之“存在”思想(即作为主体之人的“存在”是在劳动实践过程中结成的关系性的社会存在)相一致。简言之,马克思主义视域中作为主体之人的“存在”,其本质内核并非因其生物属性,而在于社会属性。主体参与到社会实践活动中,并能动性地存在于因劳动实践结成的社会关系之中,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主体存在”之概念。
不容置疑,巴迪欧高度强调主体的介入行为,即强调实践或革命行为,是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第11条“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虔诚信仰。值得一提的是,他对行为的共同性的认识,饱含着对人民大众的认可,是对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的关怀。然而,他对事件的“物质性”定义却否定了马克思对物的现实层面的第一关怀,将物又还原为抽象。不仅如此,事件的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因果关系,让历史变得无迹可寻,任何事物和话语都变得捉摸不定。巴迪欧从事件的生成时间上着手,偷换了马克思对物与存在的关系,认为随着时间推移,事件产生之后,存在者才存在,而不是现实的“绝对存在”或者“社会存在”。虽然我们能够在真理的逻辑中看到巴迪欧对事件的忠实,他的忠实只不过是对偶然性的忠实,而不是对历史和社会本身的忠实。在巴氏理论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真理本身也带着主体的行动的印记,真理是而且惟一是主体的创造,否认绝对真理。尽管巴迪欧之三元结构模式有许多差强人意之处,但无论如何,他都重塑了一个真理—事件—主体三元结构的本体论,为共产主义理论事业奋斗着。
三、布道:走向大写的一[5]
2009年于英国伦敦举办、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齐泽克主持的“共产主义观念”讨论大会,旨在探讨巴迪欧的共产主义观念。然而哲学上的系统论或集合论才是巴迪欧共产主义的根基。因此探讨巴迪欧的共产主义观念必然先从哲学开始,这又回到巴迪欧的数学本体论。虽然,真理—事件—主体的三位一体的本体论重塑,只能做到解释当下历史的问题,而不能解释现实历史的生成和趋向。那么巴迪欧是如何说明历史的走向问题呢,以至于走向共产主义?
让我们从巴迪欧的数学本体论开始。巴迪欧认为任何一个集合都是由诸元素构成,例如集合A由无限多个元素构成,集合A即为巴迪欧的“一”,A集合中各元素的呈现方式并非以单个的元素形式出现,而是首先以A即“一”的整体形式呈现,只是“一”中包含多个元素,即一之多,诸元素相互之间按照一定的规则形成具有一定结构的“一”。也就是说,“一”只不过是一种显在的结构,诸元素之间的纯粹多元(纯多)将被具有多元性(即一种再现结构)的“一”所代替,诸元素在再现结构中表现为集合A的子集,例如我们将A的一个小集合赋予a的概念,a就是A的子集,也是一种再现结构。以此推导,不同的元素相结合又可能以b的概念出现,同样b也是A的子集。然而问题不在于此。问题在于,各元素之间的呈现结构在逻辑上完全可能以一种异质性的形式出现,然而这种异质性的结构形式却无概念与之对应,如何解决?巴迪欧认为,当各元素以异质性的结构形式(其他不存在的概念形式)出现时,就是一个事件,这时候就要依靠主体的积极行动,在主体的行动之下获得一个概念c。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行动并非单个人的独立行为,而是一种公认的社会行为。通过主体行为的介入,异质性的结构形式就获得了子集c——一个被公认的共同可能性的概念。与此同时,主体也在行动之中证明自身的存在。集合各元素依赖主体在事件中的积极行动,使那些不具有概念或名的集合获得一个名,同时获得一个类性真理程序。换句话说,诸元素构成的“一”包含了许多A(显在结构)的子集(再现结构),例如a、b、c等,在主体的积极行动下,a、b、c等才构成了A的子集,最终诸元素才表现为A或一。如果到此为止,“一”在巴迪欧这里表现为完全的可预知性,即如果明了集合中的所有元素,那子集或再现结构完全可预知。在历史观上表现为,社会发展终究难逃历史决定论的宿命圈。显然,巴迪欧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说在A之外完全可能存在一个未知的B,巴迪欧称之为“溢出”,这时候却不存在一个概念或名能够容纳下A和B,这同样是一个事件,需要主体对该事件的再次介入,要求主体赋予能容纳A和B之名,从而获得共同可能性。这时候就需要主体赋予这个更大范畴的类性真理程序(即类性真理程序的再写),使其能容纳所有范畴。于是,整个逻辑就可理解为部分不同元素构成a;在a之外的部分不同元素构成b;a、b之外的不同元素构成c;{a,b,c}共同构成A;主体对类性真理程序的再写,使其出现一个能容纳A和B(溢出)的更大范畴,从而构成了大写的一。以此逻辑,巴迪欧最终将走向一个大写的一,使其能够真正容纳所有元素。
在历史观上,这个大写的一被巴迪欧看成是共产主义的化身,共产主义只不过是大写的历史范畴。巴迪欧以一种胆量续写了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的假设》一书中,将共产主义描述为三个步骤:假设的创立与落实、假设的胜利、无群众或政党的假设的再落实,而三个步骤都必须有主体的介入。也就是说,大写的一的实现或者说共产主义的实现必须依赖主体,在《主体理论》中,巴迪欧将其归属于人民群众,强调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力量。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共产主义主体的身影。但是,在共产主义的概念上,已经不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概念,而是被拉康化了的共产主义概念。巴迪欧对共产主义的解读,缘于对巴黎公社的赞扬。然而,这种赞扬最后却变成了一种极端的不切实际的信仰。从现实的角度来考察,巴迪欧认为,9.11或者2008年金融危机等的出现都是历史过程中的“事件”,认为这恰恰是我们去理解历史或共产主义的契机。换句话说,他心中的共产主义“大写的一”已不再是摆脱异化劳动的结果,而是完全脱离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因素的、完全偶然的事件,共产主义成了以偶然性事件为基础。更严重的是,将共产主义的产生归结到偶然性事件,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渐进模式完全不同。马克思主义相信,历史的生成、共产主义的产生,缘于社会内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矛盾的解决。由此来看,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只不过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现代表现形式。他认为,事件不外乎说明了由于主体介入特定的历史事件,依靠历史主体的积极行动,最终使得历史不断生成,最后走向共产主义,主体成了沟通事件与历史的桥梁。由此看来,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在现实中却又那么的空乏,以至于其信念只不过是对共产主义口号般的宣扬。
综上来看,巴迪欧作为后马克思主义者,其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本体论与共产主义理论的相关思想;又从必然与偶然的关系出发,批判了一种误认的言论:“我不想说历史主义必定总是导致这类事情。有些历史主义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想把人们从他们过重的责任中解脱出来”[6]。换而言之,在历史发展观上,巴迪欧赋予偶然性以首要地位(偶然性是第一性的),而必然性则是在偶然性的基础上形成并对历史发展稍起作用(必然性是第二性的),并对利奥塔和海德格尔等人发起的挑战进行批判;批判之批判的同时,采用拉康式的精神分析方式,重塑真理—事件—主体三位一体构成的巴氏本体论;在关涉现实的同时,对未来提供了希望之维,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高举社会主义之旗帜。基于此,巴迪欧以一种胆量续写了共产主义,将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理论与实践的最终归宿。因此,阿兰·巴迪欧是一个具有“后-”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具有拉康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即一个拉康化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其理论代表了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模式。
[1](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5.
[2]Alain Badiou.Theorie du sujet[M].Paris:Seuil,1982.
[3]Alain Badiou.l’etre et l’evenement[M].paris:seuil,1988:215.
[4]Alain Badiou.Saint paul et la fondation de l’universalisme[M]. paris:PUF.1997:119.
[5]Alain Badiou.L’Hypthese communiste[M].Paris:Lignes.2009.
[6]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M].陆衡,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9.
责任编辑:谭大友
B089.1
A
1004-941(2016)02-0139-04
2015-06-17
彭均国(1986-),男,四川简阳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西方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