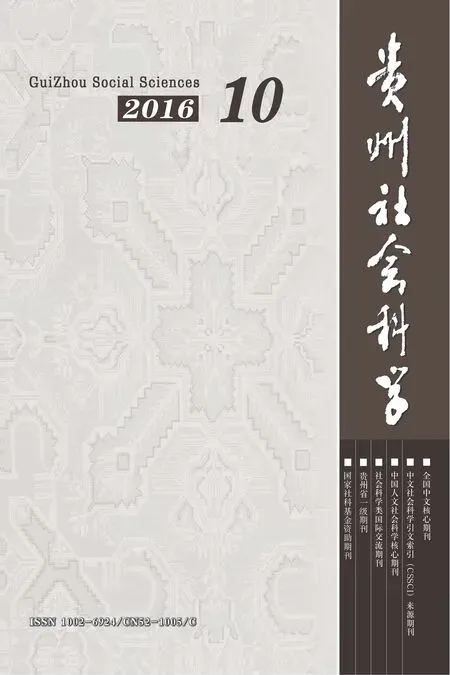主-Lord-Bhagavān:三大文化从神到帝演进的不同类型
张 法
(浙江师范大学,浙江 金华 321004)
主-Lord-Bhagavān:三大文化从神到帝演进的不同类型
张 法
(浙江师范大学,浙江 金华 321004)
“主”是早期文明由神到帝演进中的一个中间阶段,这一演进在中国、地中海、印度各有特色,主-Lord-Bhagavān分别为三大文化关于主的主要词汇。演进结果,地中海出现一神论的上帝,Lord也成为上帝的称谓,在印度,有的主完全上升到帝位,有的却没有。在中国,主未能上升到宗教的帝位,却转进到政治上的帝王。这一不同结果的原因在于,由神到帝演进的终段在轴心时代,三大文化都产生了哲学思想,宗教在与哲学的互动中受其影响。
神-主-帝演进;主-Lord-Bhagavān;中国-印度-地中海;宗教与哲学
在人类产生哲学思想的轴心时代(约公元前700-前200年)以前,宗教是文化的核心,这核心在各个时代又各不相同,原始时期是以虚体的灵(用美拉尼西亚原始时代的语言讲是mana,用西方语言讲是spirit)为主,早期文明时代是以实体的神(印欧语是deity,希伯来语是eloah)为主,神的进一步演进,在轴心时代地中海,最终定格在一神教的上帝上:犹太教的Yahweh(耶和华),基督教的God(上帝),伊斯兰教的Allah(安拉)。由神到帝的演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其中一个明显的环节,就是在由神到帝的中间,出现了“主”(地中海文化的 Lord,印度文化的Bhagavān,中国文化的“主”)。在地中海文化里,主的各种类型并没有完全进入到最后定格的上帝之中,但上升后的上帝也可以称为“主”,从而上帝=主。印度文化的主也有各种类型,主要有Bhagavān(世尊)和Īs'vara(自在天),前者完全进入到了方方面面的最高神中,后者却只在印度教里进入到了最高神中。因此,地中海主具有一种历史演进中的多样性,而印度的主却不但在演进中而且在结果上呈现出差异性。中国的主,在由神向帝的演进中,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当中国的演进最终定格在帝-天结构上时,主却离开了神系。因此,从地中海、印度、中国三大文化由神向帝演进中的主的不同地位的境遇,透出了三个文化的差异和特质。
一、地中海文化由神到Lord(主)的演进
早期文化的农业-城市-青铜-文字-国家,形成了地域联合体(崔格尔将之分为城邦国家和广幅国家两大类型[1]),出现联合的盟主或实际的盟王时,原来各城邑的众神也形形色色的组合形成了主神。地中海族群复杂多样,演进各有节奏,各族之主神在词义上有Lord之义的,有来自苏美尔神系的En-lil(恩利尔),希伯来神系的Tammuz(塔木兹),西北诸闪族神系的Baal(巴力),埃及神系的Osiris(奥西里斯),希腊神系中的 Adonis(阿多尼斯),伊朗神系中的 AhuraMazda(阿胡拉·玛兹达)……这些不同族群和文化中的神,内蕴着Lord(主)的内容。网上维基英语词典说,Lord从神的方面讲,是“在众神之上的具有权威性、控制力,神威力的神。”①网上维基英语辞典“Lord”辞条(https://en.wikipedia.org/wiki/Lord)然而,上面所列举的地中海文化中的主神,除了伊朗的阿胡拉之外,都没有达到后来God(上帝)的高度,虽然,地中海的Lord(主)都可以被用来指后来的最高神,但“主”在与最高神相关联的同时,又与之有区别,正是这一差别,呈出lord(主)作为由神向帝演进的中项的特征。
Lord(主)在地中海各族群中的多样性,透出了更为广阔的历史关联。人类的宗教演进是从虚体的灵到实体的神的演进。在进一步由神到Lord的演进中,也还可以看到与以前历史的多重关联。比如苏美尔楔型文字中的En(主),其词义最初既指祭司,又指祭司所祭之神主,在城邦兴起中,又指城邦的保护神,而苏美尔的神泛称Lil(利尔),与冥界、黑暗、混沌等特征相连,原始时代思想在天界与冥界,白昼与黑夜,明晰与混沌中,后者占了主导的地位,灵主要活动在冥界、黑暗、混沌之中,在由灵向神演进的早期文明之初,整个神系,仍带着较强的灵的性质。美苏尔是美索不达米亚最早进入早期文明的族群,其著名古都尼普不断发展壮大,其城邦之神成为了En -lil(恩-利尔),直译即众灵之主。苏美尔神话讲道,天神名安和地神名基,二者本来浑然一体,由于众神不断繁衍,天地难以容纳,天地二神所生之子恩利尔用刀从苍穹边缘割起,分离天地,天地之间被大气充满。于是宇宙分为天-地-空三界。恩利尔成为空界之王,最后成为宇宙大神。恩-利尔从混沌而来,透出了恩-利尔是在由灵到神,由混沌到秩序的转变过程中,不但成为神而且成为主神的,在这一过程的终点,恩利尔由众灵之主定型为众神之主。恩-利尔型众神之主的产生,透出的是在灵的背景中由神到主的历史线型演进特点,而地中海文化更多的“主”,则漏出了神何以为主的本质基础。在地中海各族群中,神之名同时具有“主”的词义的神,如埃及的奥西里斯,希伯来的塔木兹,希腊的阿多尼斯,而这些神之所以成为“神主”,在于他们都是植物神,具有每年生而死又在来年复生的生-死-复活的轮回特征,混沌之灵的规律最初从植物上体现出来,又由农业显示出其生死繁衍规律,当虚体之灵转为实体之神,植物神,成为最具这一规律的实体。因此,大凡属于具有死而复活性质的神,从其在由灵到神的被命名之初,就具有了“神主”的词义。萨伊斯说,美索不达米亚最初由苏美尔人主导时,虚体的Lilla(灵)占有主要地位,继而由闪米特人主导时,闪米特人的Zi(灵)具有了实体性,“从字义上看,Zi代表‘生命’,在古巴比伦原始的象征文字中,以一株开花的植物来表示。”[2],花朵具有的最高意义在整个地中海文化中特别突出,莲花在埃及具有在印度一样神圣象征意义,玖瑰与埃及的伊西斯,希腊的得墨忒尔,以及基督教的圣母玛利亚紧密相关,透出的都是植物在原始的虚体之灵的主导地位对后来神系的巨大影响。后来基督教中耶稣的死亡与复活也被与贯穿在原始时代的植物灵显和早期文明中植物主神的性质关联起来[3],耶稣被称为主也与阿多尼斯具有主的词义在深层上(死而复活)相通。植物灵具有圆转性,植物神又在其表示宇宙规律上有多重关联,如奥西里斯,既是植物生殖之神,又是水神,作为国王,还是太阳神。生命的生死与繁衍,既从大地植物上体现出来,又从空间风中体现出来,还从天上的太阳体现出来,风和太阳都是使植物得以生成的重要因素。苏美尔的恩-利尔从空界的风(气)之神上升为众神之主,来自迦南的Baal(巴力),既是植物神、丰收神,又是雨神、风暴神,也成为了众神之主,巴力后来又与闪族的Hadad和苏美尔Adad(二者皆可称哈大德)在词义上合一,有天主之意,可以说都是从风的层面进入神主的。伊利亚德专门指出了宙斯也有丰产之神和暴风之神的双重性质。[4]74从太阳进入神主之例在埃及体现鲜明,奥西里斯来自植物轮回但以冥界为主,太阳神拉的运转是白昼在天上而夜晚在冥界,但在主要以天界为主,在埃及,太阳神很早就同化了许多其他的神灵,比如阿图姆,荷鲁斯,圣甲虫何普里,并在第十八王朝的埃赫那吞法老时代,升格为唯一主神。美索不达米亚的太阳神夏西巴也有使死者复生的能力,因而被称为“公义之神”和“审判之主”。[4]134-135
总之,地中海各族的神主,可见出三种类型,一是地界的带有原始之灵痕迹的植物神,二是空中的具有力量的暴风神,三是天上的以太阳为核心的天神,这三类神本有关联,伊利亚德呈现了丰产女神与风暴神之间、风暴神与天神之间、天神与地神之间的丰富、复杂、多样的关系,而且三者都可以形象化为公牛。[4]73-83公牛在地中海各族群的图像中反复出现,体现的正是这一关联。但从灵-神-帝的演进角度,植物神如阿多尼斯,因过去历史的影响,而有神主的词义,但上升不到真正的主神,风暴神和太阳神,具有升上主神的基础,而且也确实占有了主神之位。但在更深的演进中从主神进入帝位的,则是波斯神系的阿胡拉·玛兹达,希伯来神系的耶和华,阿拉伯神系的安拉。还有结合了希伯来神系和希腊神系的基督。之所以把此四主神称为“帝”,在于地中海宗教思想的演进在这四位神上达到了最高峰。虽然升到帝位的只有四位,但各种神主虽面貌各异,却仍有共通之点,因此,四位大神入主帝之后,阿胡位词义本为“主”,而耶和华、基督、安位,仍可称主。可以说,在地中海文化中,由神到主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各种各样的主,经过各种竞争之后,只有一部分进入到God(帝)位。但进入到到帝位的,仍可称主,可谓是帝主一体之God(帝)。
二、印度文化由神到Bhagavān(主)的演进
印度文化在由神到帝的演进中,也产生了一系列“主”,如Bhagavān(汉译为“世尊”)、Īs'vraa (汉译为“自在天”)、Prabhu(主或主神)……而前两者具有由神到帝中间阶段的代表性。这两者中,Īs'vraa(自在天)在先,出现在后期吠陀经和中期奥义书里,Bhagavān(世尊)在后,吠吠陀经的奥义书皆不见其迹,直到《薄伽梵歌》和《往世书》才开始出现。不知道是否与出现先后有关,当印度神系最后定型在梵天、毗湿奴、湿婆这三位最高的三联神时,二者皆可用来称最高神,但佛教产生并进入印度神系时。Bhagavān(世尊)可以用来称谓佛陀,而Īs'vraa(自在天)却不能,只在佛陀之下的一个位置上。可以说,一个达到了God(帝位),一个没有达到帝位(God)。而这要由印度神的性质和这两个“主”的性质来说明。
先讲Īs'vraa(自在天)。此词分为两个部分,词根Ish的词义为拥有者、统治者、大能力……另一部分vara的词义依语境可分别为最优、吉祥、爱者……结合二者,Īs'vraa的字面义为:最好之拥有,精明之统治者,最宜之爱。①参维基英语辞条“Ishvara”(https://en.wikipedia.org/wiki/Ishvara),Jahn Grimes:A Concise Dictionary of Indian Philosophy:Sanskrit Terms Defined in English,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Albany,1996,p142-143印度文化的最高境界是解脱,所谓的最优最佳、最有能力,既在于体悟到生命轮回规律之后的自在,还在于达到了解脱境界后的自在。自在即我自为主,并以这一具有宇宙规律的主,去教导、统治众神,以进入梵我一如的境界。印度神系的演进是走向虚实一体。在印度教,一方面是无形无名的梵,另方面是有形有名的最高神,在如是的文化里,Īs'vraa (主)有着多方面的内容,就神系来讲,它包含了两个方面内容,从实的方面讲,是最高的存在(梵的形象体现),从虚的方面讲,是最高的灵魂(梵在内心的存在)。当印度教定型在梵天、毗湿奴、湿婆三位主神上时,Īs'vraa(自在天)可用来指毗湿奴和湿婆。这里,用来指湿婆具有更深的历史内容。考虑到湿婆由本土神演化而来,内蕴着从最初始之灵到后来之神再到最高主神的演进,因此,Īs'vraa与湿婆关联透出了由灵到神到帝演进中的历史内容。湿婆在三位主神中是与毁灭相关。毁灭,从积极的方面讲,意味新生,类同涅槃,又与自在有相同的意味。因此,Īs'vraa弥漫在由神到主的整个过程之中。然而,Īs'vraa一般不与梵天相称,大概一是因为梵天并没有形成教派,神庙和信众甚少,因此,Īs'vraa与梵天的关系没有受到关注。二是梵天是创造之神,创造的命定性与自大的自由性有一定的距离。但自在与梵的契合,因此在印度教中,基本上可以说Īs'vraa已经达到了最高的帝位,具有帝-主一体的性质。然而,在佛教上,自在天却未能达到神的帝位。佛教宇宙结构由欲界、色界、无色界依次向上的三界组成,欲界包括地上六类和天上六类,天的第四类化自在天和第五类他化自在天,方与Īs'vraa有所关联。地位不高。同样佛教的神系结构中,大自在天也不是佛陀,而是佛陀的护法神之一。因此,从佛教中看,Īs'vraa在主神中,有了一定的地位,但还没有上升到最高层。之所以如此,在于佛教的最高境界是空(S'ūnyatā)。空的重要本质,可以从无色界四天的命名上看出:空智天、识智天、无所有智天、有想无想智天。对佛教来讲,最高境界应是不觉自在而已经自在。因此自在天的以自在为名,应低了一等。自在为主,不是最高的主。这样,自在天作为主,在印度教达到了帝位,并透出丰富的历史关联,但在佛教里并未达到帝位。
再来看Bhagavān(世尊),解释甚多,小异大同。且举两例。《梵英简明哲学辞典》说:此词由词根bhag,意为善(good)的“运势”(fortune)、“力量”(Power)、“财富”(wealth)、“宏壮”(splendor),加上 van,意为“内有”(possessor)、“主宰”(master)、“拥有”(having)组成。意为内外各方面的最高者(主)。[5]《毗湿奴世书》说:“首字母Bh即为宇宙的珍贵者和支持者,ga意为创造者、推动者、领导者,二者合为Bhaga,意指六种品性:,统治(dominion)、威力(might)、荣耀(glory)、宏壮(splendour)、智慧(wisdom)、去情(dispassion)va意指 一切存在者的核心。①参维基英语辞典辞条“Bhagavan”(https://en.wikipedia.org/wiki/Bhagavan)中文将Bhagavān译为“世尊”,这世既是空间的世界之世,又是时间的世代之世,世尊者一切时空中的最尊者也。与自在天只是印度教中达到帝位不同,Bhagavān不仅在印度教中,同时也在佛教中达到了帝位,在佛经中,佛陀也被称为世尊( Bhagavān)。
Īs'vraa(自在天)和 Bhagavān(世尊)被称为“主”(lord),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受到印度由神到帝的演进特色影响,这就是神和帝都有虚实两性,因此,Īs'vraa(自在天)和Bhagavān(世尊)在这一演进中,也兼顾虚实两性,印度的神与帝,实的一面有多种关联,虚的一面则通向哲学的深邃,正在虚的幽玄上,先出现的Īs'vraa(自在天),在满足印度教的智慧上已经具足,在契合佛教的玄思上则有所不足,因此在佛教这里未能升到帝位。后来的Bhagavān(世尊)达到了印度教和佛教两方面的要求,从而全面的升上了地位。从Īs'vraa(自在天)和Bhagavān(世尊)在通向帝位上的不同遭遇,也反映出印度之神在从神到帝演进中的特点。
三、中国文化由神到主的演进和主从神系中的退出
中国文化由神到帝的演进,也包括了由神到主的演进,但主并没有演进为最高神的帝,而是转向了作为帝王的人主。主虽然并未通向帝,又是在由神向帝的演进中产生,因此中国早期文明的由神到主的演进,正好透出中国神灵演进的特殊性和中国文化本身的独特性。中国神的产生,是从灵到神时的实体化的鬼神一体开始的,鬼是神的外在之形,神是神的内在之魂。中国最初的宗教观念是从村落的立中(即立中杆以测天影,昼测太阳,夜测极星)开始的,立中在文字体现为“示”。丁山所讲:示是立杆以祭天[6]。叶玉森讲:示的写为“,乃最初之文。”[7]立杆观测日月星的运行,日月星后面之神是虚灵的。姜亮夫讲“示当即原始神字。”[8]可以说。示是从观察点也即神的降临点来说神,而(神)则是从神在观察点中的呈现来讲神。古人观星辰运行,是为地上的实践活动,天与地相关,由采集狩猎向农业生产的演进中,由村落向城邑的演进中,地的重要性大大增加,示又成为地神的标志,古人讲天地二神,有两种说法:天神地示和天神地祇。示即社坛中的中杆作为社神的符号,祇,由示和氏组成,氏是地域集团,这一地域集团所祭祀的此地的社神,即地祇。示强调地与天的关联,祇强调地本身。古文中的示,分为两类,(《甲古文合集》14841)、(14840)和(28273)、(《乙》7359),前二者主要是空地中观天的中杆,后二者虽然中杆在其中,但突出了社坛的形状,是天地合一但以地为主的杆柱。神灵的进一步演化,天神地祇与祖先神区分开来。鬼神也有了区分,天神地祇为神,祖神为鬼。随着天神地祇祖鬼的结构和历史演进,祖鬼的地位日益重要,祭祀中心由天坛社坛转向祖庙。原来在天社二坛上的中杆也缩小变成祖鬼的牌位,进入祖庙之中,祖庙即宗。宗即把祖鬼牌位的“示”放进祖庙建筑“宀”之内。中国早期的鬼神,都是用木杆石柱神树来象征,徐仲舒说:“、从象以木表或石柱为神主之形,之上或其左右之点划为增饰符号。卜辞祭祀占卜中,示为天神、地祇、先公、先王之通称……先公、先王、旧臣、及四方神主均称示。”[9]示体现了中国型神灵的特点。天地神灵以灵显方式出现,其虚实结合的本相是不易把握的,天坛社坛的中杆石柱中,就以“示”的符号方式将之把握住了。但祖鬼是实在的,在祖鬼的牌位中,其虚实结合更易进行实的把握。中国文化的演进是在血缘基础上的提升,王族祖鬼的核心地位由之形成,因此,在祖庙里,示就演成了主。姚孝遂、肖丁说:“卜辞的‘示’,指先王的庙主。”[10]杨升南说:卜辞的“示”即近代人们所称的“神主牌”。这还是从内容上讲,正是在现实内容变化的推动下,主字从示中产生了出来。唐兰、陈梦家,都讲示与主,本为一字①唐兰《怀铅随录(续),释示、宗及主》(《考古社刊》第六期,1937年):“示与主为一字,……卜辞中示、宗、主实为一字。示之与主、宗之与皆一声之转也。”陈梦家《神庙与神主之起源一一释且宜姐宗拓访示主等字》(《文学年报》第三期,1937年):“示、主本为一字”。。张亚初说“在商代甲骨卜辞中,示与主二字是经常通用。”[11]何琳仪先生在《战国文字通论》讲“示”与“主”乃一字之分化。[12]主,甲骨文有:(乙861)、(甲150),林义光说,“丶象火形。”商承祚说:“从木,象燔木为火。”[13]来源于中杆观天仪式中燔火以与天相通的常例。主来于观天仪式中的具体形状,示则从是对观天仪式中普遍性的概括。示与主,本就涵含着天之主的内容。在历史的演进中,由示到主的演进,体现了天为主的天地人一体演为祖为主的天地人一体的复杂过程,从世界宗教的普遍性,也就是示后面的从灵到神,示中本有主的内容。主后面从天神地祇到祖鬼的历史演进,主中仍有示的内容。如果说,示是神的泛称,那么,主则是众神的核心。主,正是夏商周王族与非王族在等级上的区分,从而王族之祖鬼与非王族之祖鬼在神鬼体系里的区分,在这一现实演进中,产生了出来。在中国神灵的演进中,一是产生了天神-地祇-人鬼之分,二是主从祖鬼中产生出来。主既与神灵体系中的天神地祇相连,又与现实中作为其子孙的人相连,鬼祖的主要目标是要对其子孙进行保护,后一部分比前一部分更为重要,因此,主由鬼主一方面扩展为神主,另方面扩展为人主,神主乃牌位为虚,人主是真人为实。更为重要的是,鬼主在宗教的天神地祇人鬼结构中不算最高,而人主在现实政治的结构中却为最高。这样,主转向了现实的人主,而未能上升到宗教的天帝。盖也因这一转向,主进入到现实社会结构之中,有各种各样的主,而在神灵方面,主却用得甚少。可以说,中国神史上由神到主的演进,产生了变异,转入非神领域。这样中国神史的演进,主要是由神到帝组成的。明确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文化的性质甚为重要。
在中国早期文明中,主神被称为帝。帝的原貌虽被以后的理性历史所遮蔽,但仍可在文献中看到主要痕迹,从空间上讲,各方自有其帝:东方太皋,南方炎帝,西方少皋,北方颛顼,中央黄帝。从时间上讲,历史上有前后相续的帝的更替:黄帝、太喾、颛顼、唐尧、虞舜。这里的帝,既是地上之王,又是天上之神,是二而一又一而二的。从文字上讲,帝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在甲骨文中,帝字形为:(明藏五0二)(甲七七九)(铁一五九·三)等,释义甚多,有释为花蒂,蒂为花本,引申为万物始祖神,这与地中海地区的植物神为主应有逻辑普遍上的关联。有人在性质上释为天上的神帝②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第一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6-56页释帝:有人因其象花蒂之形而释为花蒂(吴大澂、商承祚、戴家祥)或花本(高田忠周);也有人释为天帝(孙贻让)或君王死去称帝(裘锡圭),或宇宙万物的始祖(张桂光),神秘力量的总称(朱歧祥);还可释为祭祀方式,如迎气四方之祭曰帝(叶玉森),五方帝之祀(罗振玉,杨树达),以木加束薪燔以祭天(朱方圃,徐中舒)。,这与地中海地区的各种风暴神升为主神相关,但中国不强调武力的暴,而只彰显具有统一性的风,八方之风皆来自于北极-极星-北斗的运转。北斗运行,气注天下,形成八方之风,正是这一中国型的关联,有学人释帝的字形为天上的北斗③班大为:《中国上古史的揭秘——天文考古研究》,徐凤先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56页,释帝为天上的北斗。。这与北极圈及中亚各民族的天神在逻辑普遍性上关联了起来。中国的天帝的特殊性体现在,是把北极-极星-北斗作为一个整体,然后与八方之风关联起来,与春夏秋冬的运转关联起来,进而与地上人间关联起来。前面讲空间上的五方之帝和时间上的相续之帝,既是人间的人帝(王与祭司的一体)又是地上的神帝(各方的地祇之帝),还是天上的天帝,统领日月星辰之帝,在后来的天坛牌位上称为“昊天上帝”。这种一体化的“帝”,构成了中国神系从神到帝演进的特色。从商到周,帝又演变为天,因此,中国早期文明由神到帝的演进,是由神到帝-天的演进。
四、“主”在由神到帝演进中的不同境遇之文化关联
世界文化由神到帝的演进,在地中海、印度、中国三大文化中,都有“主”这一阶段,但主却有不同的内容和境遇,这与三大文化的在宗教演进的同时,产生了哲学突破有关。三大文化不同的哲学性质,在相当的意义上决定了“主”的境遇。地中海以希腊哲学为主,产生了以逻各斯(logos)和逻辑(logic)为主体的哲学,在印度产生了以梵(Brahman)和空(S'ūnyatā)为核心的哲学,在中国产生了以道和气为核心的哲学。当哲学产生之后,由神到帝的演进,是在与哲学的互动中产生的。理解了三大文化哲学的性质,就可以理解,三大文化的主在升向帝位中产生的不同结果。
地中海文化的神帝,从犹太教的Yahweh(耶和华),演进到基督教的God(上帝),伊斯兰教的Allah(安拉),否定了所有的异教,也否定了所有的神系,只有一个唯一的神:上帝,以及为之服务和受其旨令的天使。因为上帝之外的神都被否定了,其它作为主的神(如宙斯、奥西里斯、阿多尼斯等)都不存在了,主这一称谓被保留下来,指的是唯一的上帝。而《圣经》中讲上帝就是逻各斯(logos)。这是从整体上讲,从具体上讲,宗教的上帝与哲学的逻各斯展开了两个虽然关联(在文化总体上)而又相当独立的体系,形成了神学与哲学的本质分野。
印度文化的神帝,在印度教是三主神与梵的统一,在佛教是佛陀和空性的统一,在耆那教是大雄和解脱位的统一,把宗教与哲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时三种宗教把各种各样的神,按照自己的需要组织起来,构成各自的神系。正因为宗教与哲学被统合了起来,因此,属于主的神如Īs'vraa(自在天)和 Bhagavān(世尊)等都保留在神系之中,又因为哲学在其中的作用,各类主因其所达到的哲学深度不同,有的如Īs'vraa(自在天)不能完全进入帝位,有的如Bhagavān(世尊)则完全进入了帝位。
中国文化由神到帝的演进,最后完成在“帝”和“天”上,与印度一样是把宗教和哲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有了这一结合,天既是宗教上的作为最高神的天,又是哲学的自然运转之天。在前一意义上。天与上帝相同,在后一意义上,天与道相通。帝既可用来称天上的最高神,所谓上帝,又可用来称地上的最高位,帝王。在哲学与宗教的互动,主没有上升到神学的帝位,但却进入到理性政治的帝位,主相当于帝王。主与天的关系是天子与天帝的关系,主不是神的帝位,却与神的帝位有最亲的关系。主在中国进入不了神的帝位,却转进为人的帝位,透出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
主在三大文化中从神到帝演进中的不同,以及最后结果的差异,正可让我们由此去体悟三大文化各自的特色,以及在世界文化演进中的意义。
[1](加)布鲁斯·G.崔格尔.理解早期文明:比较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69-82.
[2](英)亚奇伯德·亨利·萨伊斯.古巴比伦宗教十讲[M].合肥:黄山出版社,2010:19.
[3](德)埃利希·诺伊曼.大母神——原型分析[M].李以洪,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270.
[4](美)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的存在:比较宗教范型[M].晏可佳,姚蓓琴,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5]Jahn Grimes.A Concise Dictionary of Indian Philosophy——Sanskrit Terms Defined in English[M].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6:81.
[6]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M].北京:中华书局,1988.3-4.
[7]叶玉森.说契[J].学衡,第三十期,1924:113.
[8]姜亮夫.姜亮夫全集(十七)[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77.
[9]徐仲舒.甲骨文字典[G].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11-12.
[10]姚孝遂,肖丁.小屯南地甲骨考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5:25.
[11]张亚初.古文字分类考释论稿[J].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辑,1989:254-255.
[12]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 [M].北京:中华书局,1989:291.
[13]李圃.古文字诂林(第五册)[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250.
[责任编辑:黄 昇]
B5
A
1002-6924(2016)10-054-059
张法,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美学、文化、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