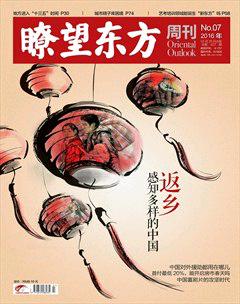新富乡村过年记
单素敏

鹤壁市街头群众摩肩接踵,欢度猴年春节
从北京西站坐上高铁,三个小时到达河南省鹤壁东站,坐大巴半小时到X县城,再乘小巴十几分钟回Z村,这是最近三年来我固定的春节返乡路线。
鹤壁东站所在的淇滨区也叫朝歌新区。3000多年前,这里就形成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早的繁华都市之一。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牧野大战后朝歌失守,殷纣王帝辛在朝歌鹿台自焚。后人就此演绎的电视剧《封神榜》,曾在上世纪90年代初创下过“家家追剧”的收视纪录。
当然,在现代,无论是鹤壁,还是河南,都远没有古时的辉煌。
但如今这座中原城市也发展迅速,即便在我的老家X县Z村,也出了不少“土豪”。其中我的街坊单九连做饲料加工和销售,供应附近的养猪场、养鸡场,还通过电子商务把货物卖到山东、河北、安徽等周边地区,年收入上千万元,是闻名乡里的青年才俊。
不过,在繁荣背后,X县和Z村的深处,却仍然和现代都市相去甚远。那里有崭新的高楼和宽阔的大道,但更引人注目的是几年来一直卖不动的住宅区和大道上飞扬的尘土;经济日渐繁荣的故乡有喧闹的人群,但置身其中,无法忽略的还有相似的欲望和深切的迷茫。
村里需装红绿灯
40多年前,我的姥爷拉一车烧火用的煤,煤下面埋上花生,从X县出发负重步行到70多公里外的新乡偷偷卖掉,一次卖十多元钱,打算贴补一家老小的春节花销。可是最后一趟在大赉店被人查了出来,手推车、煤和花生被悉数没收,辛苦了一个冬天的所得因“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罪名打了水漂。
30多年前的另一个冬天,我的爸爸为了给刚生下我姐姐的妈妈弄一个温暖的被窝,用玉米杆和麦秸在生着炉子的简易厨房里搭起来一张床铺,忙活了半天,再进屋发现家里的大白猪正躺在里面盖着被子享福,场面可笑、可气,又让人备感心酸。
爸妈对我讲起这些往事的时候,整个中国早已今非昔比。
朝歌及其所辖大赉店镇一直以来都是河南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贸易集散地。近年来,当地更是发展迅速。2014年,鹤壁的GDP增速是全省第一。如今,鹤壁这座中原北部的小城已是高楼林立、交通发达、贸易繁荣。
致富后的Z村有不少于上百台的小汽车,春节期间来来往往喇叭声不断,有村民开玩笑称有必要在十字路口架红绿灯了。
我从北京赶回,也有家人可以开车直接到鹤壁东——这座2012年底开通的新高铁站前来接应,走京港澳高速半小时就能到家门口。
KFS、麦肯基、康帅傅
X县有着日新月异的气象,也有着令人难以招架的慌乱。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全县最热闹的建业购物广场。比如,这里生意火爆到两公里外就开始堵车,但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车多,而是因为没有秩序。
但老家人对此景却有种自豪大过烦恼的感情——包括在一些公务员看来,交通拥堵是车多、人多、商业繁荣的表现,也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达与否的标准,秩序感反而会弱化这种繁荣的程度。
如今,乡村县城的商品是极大丰富了,可是质量不免让人担忧。建业购物中心入口处有一家装修风格极像肯德基的快餐店,名字叫KFS。我在KFS点过一杯果汁,颜色艳丽、甜到忧伤。而在另外一条商业街上,我曾经看到一家卖汉堡的店,名叫“麦肯基”。如果再往县城以下走,村里小超市还可以买到不加任何奶成分的奶糖、“康帅傅”方便面和“加乡宝”凉茶……
网购方便收货难
农村电商在近两年随着巨头的刷墙大战如火如荼,“生活要想好,赶紧上淘宝”、“发家致富靠劳动,勤俭持家靠京东”、“养猪种树铺马路,发财致富靠百度”等标语代替了前些年的“只生一个好”、“母猪配种找XX”,广告效果简单直接、一目了然。
但是,乡村物流的发展却有脱节的缺憾。2015年春节前我曾有过一次糟糕的网购经历,因为买的东西多而分散,快递只配送到县里,家人只能在置办年货的忙碌中一遍一遍地往县城跑,一次可能是买给爸妈的衣服,下一次也许只是两袋进口饼干,用我弟弟的话说“还不够搭功夫的”。
在大城市,如今物流体系已渐渐成为基础设施的一部分。但在中国的最基层,建立这一巨大的网络体系却并不容易。
事实上,因为基础设施的不足,类似购物容易收货难的尴尬在农村随处可见。
虽然村里用水越来越方便,但是污水排放量也在变大。以前,村里有蓄水的大坑,现在,因为人口增加,大坑被填埋做宅基地分配。所以,每条胡同、每个街道几乎每天都处在泥泞难走、无处下脚的窘境。

鹤壁市民间文艺团体表演高跷、秧歌等文艺节目,喜迎新春
这和日益丰富的物质产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春节期间我见到的是开着车子、衣着鲜亮的返乡人小心地踮着脚,试图找一片干净的地面,想要把吃剩的食物残渣、骨头和难降解的塑料垃圾,妥善处理而不得的情形。
负债的家庭们
以前看美籍华裔作家写《打工女孩》的张彤禾的一篇专访,她说“只有见过乡村,你才能看清城市”。
在冬天取暖的问题上,北方的农村跟同样没有集中供暖的南方城市没有可比性,除了自然气温条件不同,农房与楼房的建筑密闭性也差别甚大。这几年,农民在取暖问题上想了很多土办法,一个带烟囱的能生火做饭的炉子几乎成为街坊四邻家里的标配,但烧的多半是极其便宜的劣质煤。
但是,在基本的生存质量没有得到保障的时候,如何苛责农民们不懂雾霾、不顾环境?他们一样冷了要取暖、出门想坐车、也想勤洗衣、勤洗澡,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型城镇化似乎还没从我的家乡迈出最开始的那一步。
当城市的自由青年扛起“反催婚”的大旗时,很多农村的年轻男女20岁出头就已经生育了二胎、三胎或者更多胎。一些人甚至将“啃老”认为是天经地义。
我家有一个邻居单兰星,他的大儿媳妇因为两口子吵架,赌气住在娘家不归。单兰星没办法,只好凑齐儿媳娘家要的8000元钱保证金,把人“赎”了回来。二儿子与媳妇觉得这是个挣钱的好办法,两人合计也演了这么一出,把单兰星气得要命。
留守老人的情况更糟,他们一边要照看孙辈,一边还要负担同样繁重的农活,而种粮的收入几乎难以维持正常的开销。
在外打拼的农民子弟们,过了春节又一头扎进现代的城市文明,故乡起了几座高楼添了几条马路、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故事又会有什么结局,那些可怜的、可悲的东西都在登上现代化的高铁、飞机之后,被演绎成温情脉脉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