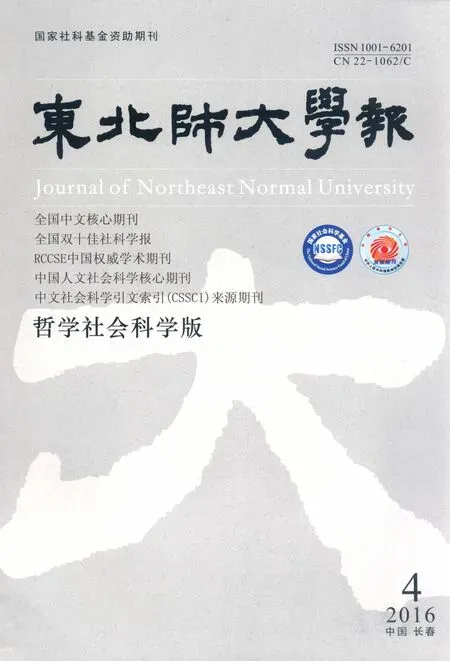构式语法理论有待深究的三个问题
陆 俭 明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中文系,北京 100871)
构式语法理论有待深究的三个问题
陆 俭 明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中文系,北京 100871)
构式语法理论有用,但有三个问题需要深究:(1)构式的本质特点是什么?作者认为构式的本质特点在于(a)构式本身能表示独特的语法意义,(b)其形式或意义都不能从其组成成分或其他构式完全推知,(c)他必须是一个结构。(2)构式是怎么产生的?对于这个问题,作者从外在语言作出了描写说明,又从内在语言作出了两个新的假设。(3)怎样提升构式理论的方法论价值?对于这个问题作者认为,构式理论真要发挥它在句法研究中的作用,要增强其方法论价值,它需要与语块理论(Chunk Theory)相结合。
构式理论;构式本质;构式产生;方法论价值
构式语法理论发端于上个世纪80年代Fillmore等人[1]对英语习语个案 “let alone”的研究。let alone是“更不必说/更不用说”的意思,例如:
We can’t even pay our bills,let alone make a profit.[我们连账都付不起,更不必/不用说赚钱了。]
可是“更不必说/更不用说”这意思,我们没法从let或alone预测或者说推知。因为let是动词,表示“允许”的意思,Alone是副词,表示“仅仅”的意思*Alone另作形容词,表示“孤独”的意思;let另作介词,表示“让”的意思;在let alone里,alone不可能是形容词,let不可能是介词。。Fillmore等就将let alone视为construction。后由Goldberg[2] [3]在Fillmore等人的观点的基础上论述成为系统的理论。构式语法理论一问世,立刻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与认可。在国际上,2001年4月在美国加州伯克莱举行了第一次构式语法理论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至今已先后举行了8次——美国加州伯克莱(2001.4.)、芬兰赫尔辛基(2002.9.)、法国马赛(2004.7.)、日本东京(2006.9.)、美国德州奥斯丁(2008.9.)、捷克布拉格(2010.10.)、韩国首尔(2012.8.)和德国奥斯纳布吕克(2014.9.),今年9月还将在巴西茹伊斯迪福拉大学举行第十次构式语法国际学术研讨会(2016.10.)。而在构式理论内部也已形成了不同的支派*进入21世纪初,在国际上构式语法出现了好多分支派别:以Fillmore和Kay et al.为代表的构式语法、以Lakoff 和Goldberg为代表的认知构式语法、以Langacker为代表的认知构式语法、以Croft为代表的激进构式语法(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后来又出现了体验构式语法(Embodied Construction Grammar)、流变构式语法(Fluid Construction Grammar)语篇构式语法(discourse construction grammar)以及跟以中心语驱动的短语结构文法(HPSG)相结合的基于符号的构式语法(Sign-based Construction Grammar,SBCG)和主张将自然语言理解和自然语言生成用同一套规则描述、在情境交互中学习的流变构式语法(Fluid Construction Grammar,FCG),等等。不过对我国语法学界影响比较大的还是Goldberg的认知构式语法。。在我国,自上个世纪末开始由张伯江[4] [5]、沈家煊[6] [7]、纪云霞、林书武[8]、董燕萍、梁君英[9]和徐盛桓[10] [11]等先后将构式语法理论引入以来,构式语法理论也已为汉语学界广为关注,一致认为有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至今已有200多篇论文,并已出版了专著和论文集,如朱军[12]、王寅[13]和刘正光[14]、段业辉、刘树晟[15]、牛宝义[16]等。但是,构式语法理论毕竟还是一个年轻的理论,尚有不少问题需进一步深入探究。
一、构式的本质特点是什么?
“构式”是汉语所取的名字,源自英语的construction。而construction,它作为语言学里的一个术语,早已有之。远的不说,索绪尔就用过这个术语,指的是词语间在句法上的“组合性联结”;美国结构主义用过这个术语,指的是句式,如“主谓宾句式”(SVO Construction)、“被动句式”(Passive Construction)、“分裂句式”(Cleft Construction),等等;乔姆斯基的TG理论用construction来指由原始单位生成出来的一种可被描写的结构,它可以从词汇与所依据的规则预测出来,所以只是一种“副现象”(epiphenomena);而在心理语言学中,用来指理解一个句子的心理过程。含义各不相同*用同一个术语指称不同的学术概念,这在各学科领域里是常见的。就拿大家熟知的case这一术语来说,在传统语言学中指主格、宾格、领格等形态格;在Fillmore的Case for Case(《“格”辨》)一书的“格”语法中,指的是与动词相关的施事、受事、与事、工具等语义格;而在Chomsky的生成语法学中,指的是名词进入句子必须取得的“格位”,为区别于先前的含义,Chomsky特别申明case头一个字母c要大写为C。。那么作为“构式”指的是什么呢?到目前为止,我们汉语学界对“构式”的认识与理解一般都源自Goldberg[2] [3]的两段话:
一段是Goldberg[3]:
这一段话告诉我们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构式是形式和意义的配对;第二层意思,构式能表示独立的语法意义;第三层意思,构式的形式或意义不能从其组成成分得到完全的预测,也不能从已有的构式得到完全的预测。这三层意思中,第一层意思是必须要说的,但并非构式理论的创见,也非构式的特点之所在,因为事实上任何事物都是形、义的结合体,这早已成为各学科之共识;第二、第三层意思,应该承认这是构式理论的创见*“构式能表示独立的语法意义”,前人也已有所知觉,譬如王力先生认为“把”字句表示“处置”义,因而称之为“处置式”;带结果补语的动补结构表示“使成”义,称之为“使成式”;朱德熙先生将“台上坐着主席团”、“墙上挂着画”跟“屋里开着会”、“外面下着雨”视为表示不同语法意义的不同的句式。在这些看法中就包含了Goldberg的第二层意思,但他们没有升华为理论,所以只能说有此意识。。由此可知,构式理论特别需要告知人们的是:(a)构式本身能表示独特的语法意义;(b)其形式或意义都不能从其组成成分或其他构式完全推知;(c)既然构式中含有组成成分,构式必然是个结构。此外,Goldberg[2] [3]和Croft[18]都确认语言中存在的就是一个个构式,构式是句法表征的“原素单位”(Primitive Unit)。这既是构式本质特点之所在,也是构式理论价值之所在。许多从事构式语法研究的学者,包括Goldberg本人在内,太看重第一层意思了,而使自己在认识中看淡了或者说模糊了第二、第三层意思,以致将构式的范围弄得很大,几乎从语素到语篇都视为构式了,以致造成了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举例来说,Goldberg把语素也看作是一种构式。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那么语素这种构式跟句法层面上的构式,显然会存在着在形式上无法统一的“不同质”问题。因为语素的形式只能是“语音形式”,句法层面的构式,其形式则显然不是指其语音形式,应该或者说可能是指形成构式的词类序列和形成构式的语义配置。可是这一来,对构式的“形式”的理解就会存在概念上的本质差异——不同质。再说,语素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结构体。。
另一段是Goldberg[3]:
Any linguistic pattern is recognized as a construction as long as some aspect of its form or function is not strictly predictable from its component parts or from other constructions recognized to exist.In addition,patterns are stored as constructions even if they are fully predictable as long as they occur with sufficient frequency.[任何语言格式,只要其形式或功能的某些方面不能从其组成部分或其他已经存在的构式中得到完全预测,就应该被看作是一个构式。此外,即使有些语言格式可以得到完全预测,只要它们的出现频率很高,这些格式仍然会被语言使用者作为构式存储。][19]
Goldberg[3]这一段意思怎么样?说实在话,这一段意思不怎么样。这段话实际将构式分成了两类,一类是不管出现频率高不高,形式或意义都不能从其组成成分或其他构式完全推知或预测,这也就是在Chomsky眼里视之为边缘的(peripheral)句法格式;另一类是形式和意义可以从其组成成分或其他构式得到完全推知或预测,也就是在Chomsky眼里视之为核心(core)的句法格式,但出现频率很高。显然,在Goldberg眼里那“另一类”构式不表示特殊的语法意义。Goldberg的这种看法并不符合语言事实。事实上,任何句法结构其格式本身都会赋予它一定的语法意义,即便是最一般的“主—动—宾”句法格式(如“约翰爱玛丽”、“我喝了一杯咖啡”)。关于这一点,配价语法的创始人特斯尼耶尔[20](Lucien Tesnière1959)有很好的说明。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Alfred parle.(阿尔弗雷德说话。)
特思尼耶尔认为,这个句子表面看只包含Alfred(阿尔弗雷德)和parle(说话)这两个词,实际上还有一个表面上看不到的但实际存在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成分,那就是Alfred和parle之间的句法关联(connexion)。“关联”对思想表达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它赋于句子以有机性和生命力。“关联”如同化学中的化合,氢和氧化合成一种化合物——水,水的性质既不同于氢,也不同于氧。为什么水会既不同于氢也不同于氧呢?这其中就是化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句法上的“关联”,建立起词与词之间的从属关系,也可以说是依存关系。特斯尼耶尔对“Alfred parle.(阿尔弗雷德说话。)”句子的阐释充分说明了句法格式会赋予句子某种特殊的意义。“约翰爱玛丽”、“我喝了一杯咖啡”跟“Alfred parle.(阿尔弗雷德说话。)”一样,这类以动词为谓语中心的主谓句子格式,表示的是“行为事件结构”,而这正是这类构式赋予句子的语法意义。人们之所以对这种语法意义不敏感,就因为这类句子是高频句,人们习以为常了,不像属于“边缘句法结构”那样会强烈感受到。
其实,对于构式可以作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而言,在句法层面上所有句子格式都可以视为构式,所有构式都能表示某种特殊的语法意义,至于有的构式我们感觉不到它表示什么特殊的意义,那是因为它的使用频率太高,已经让人不觉得有什么特殊意义罢了。狭义而言,构式就只指那些所表示的语法意义具有不可预测性或者说具有不可推导性的句子格式。广义而言的构式,是从理论上来说的;狭义而言的构式是就实际的句法分析研究来说的。对于构式理论,我们只用它来分析按狭义理解的、具有不可预测性或者说具有不可推导性的构式。
二、构式是怎么产生的?
构式是怎么产生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认可Chomsky[21] [22]关于“内在语言” (internal language,简称I-language)和“外在语言”(external language,简称E-language)之分的观点。“内在语言”是存在于人脑心智中的自然客体,是意象图式经过大脑处理后形成的表征系统(system of representations),它包括一个运算程序(computational procedure)和一个词库(lexicon)。“外在语言”,是内在语言的外部表现形式,这就是一般所说的“声音和意义相结合的符号系统”。对于构式的产生,我们就需要从外在语言和内在语言这两方面来加以观察和认识。
从外在语言来看构式的产生,我已经在今年《外国语》上发表的文章[23]中举例做了说明,这里不再赘述。
从内在语言看构式的产生,我在今年《外国语》上发表的文章[24]中也作了假设性的说明。只因为仅仅是假设,很需要大家一起来讨论,因此在这里不避重复,将我所作的假设再提供给诸位,请大家发表意见。
既然语言中存在的就是一个个构式,构式是句法表征的“原素单位”,而语言并不跟客观世界直接联系,都得经由认知域,因此“构式源于认知”这个论断应该没有问题。不过,“构式源于认知”毕竟还是个假设,有待于脑神经科学、心理学和神经语言学的学者们通过实验加以证实。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释解“构式基于认知”之说?
Goldberg[2]只是认为“构式义跟人类经验有关”,提出了“情景编码假设”,但她对这一假设只是作了这样的原则性表述:“与基本句子类型对应的构式把与人类经验有关的基本事件类型编码为这些构式的中心意义。”我国有学者进行过一些探讨(王黎[25],施春宏[26])。现在,我们试着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如下两种新的假设:
假设一*其中第ⅳ条设想是根据束定芳教授的意见设立的。束定芳一个很重要的意见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感知往往一开始就有语言(特定词语)的参与,如果是这样,语言往往就起到了引导和决定的作用,而不是到最后阶段再选择具体的词汇。”(2015-09-12给我的电邮)[“由内到外”运作假设]
“假设一”是就“说话人根据其自身的特殊感知或认识用某种言辞表达出来”这一过程,在说话人认知域中的运作。具体假设如下:
ⅰ.客观世界(客观事件或事物以及彼此之间客观存在的关系等);
→ⅱ.通过感觉器官感知并形成直感形象或直觉;
→ⅲ.在认知域内进一步抽象由直感形象或直觉形成意象图式;
→ⅳ.在认知域内借助内在语言进一步由意象图式形成具体的概念框架;
→ⅴ.该具体的概念框架投射到外在语言,寻找最能表示该概念框架的具体的表达构式——可能已有的构式能用来表达,也可能跟已有的构式发生碰撞,产生新的“修辞构式”,并呈现为具体的句子;
→ⅵ.按 “修辞构式”呈现的句子多次反复运用,并将进一步抽象概括,便分别在内在语言和外在语言形成相应的、稳定的语义框架和新的语法构式。
“假设一”是要告诉人们,当一个人有所感悟、有所认识,便要将此感悟或认识传递给他人,那么在人的认知系统中如何运作才足以把能用来传递此感悟或认识的某种新的构式“发明”出来,并由此为同一族群的人们所广泛使用并逐渐加以固化。
假设二*深圳大学的纪瑛琳教授为第二种假设提供了很好的意见,谨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由外到内”运作假设]
“假设二”是就听话人或阅读者对所听到、所看到的话进行接收并解读这一过程在听话人或阅读者认知域中的运作。具体如下:
当外在语言输入某个句子,譬如“他被杀害了”和“他被捐款了”这样的句子进入听话人的认知域就要接受核查。核查什么?我们知道,一个正常的人,一般两三岁之后就在认知域中不断积聚以母语为载体的内在语言结构和相应的概念结构所需遵循的规则或准则,所以外在语言输入的句子自然就会接受内在语言所形成的结构以及相应的概念结构所需遵循的规则或准则的核查。核查结果,无非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完全符合认知域中所存储的各种规则或准则,如“他被杀害了”,符合“被+及物动词+了”的规则,就完全通过并接受。
第二种情况是,并不完全符合认知域中所存储的各种规则或准则,如“他被捐款了”,是“被+不及物动词+了”,认知域中没有这一规则。没这规则怎么办呢?大脑就开始由数据驱动进行“自下而上”的搜索、处理,形成各种初步的意象图式,并做出由不同概念结构组成的不同理解,诸如(施春宏[26]):
(a)某人并不想捐款但被人劝说、引诱、要求或强迫而捐了款;
(b)某人并未捐款而由他人冒捐从而被认为自己捐款了;
(c)某人并未捐款而被他人传说捐了款;
(d)某人并未捐款而被他人在统计中写成捐了款;
(e)某人虽捐款但并不想让他人知道,却被人打听到后说出了捐款。
所理解到的各组概念结构,根据认知心理学的一些理论,其相应的各个意象图式间的关系,可设想为多种模块化模式:a.或是各意象图式之间互相联系,互为补充的联接模式;b.或是各意象图式之间相互作用,相互竞争的互动激活模式;c.或是各意象图式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意象域,由更高一级的更抽象的语言表征系统来统领各意象图式的重组模式。
无论是哪种模式,各个过程都是在“内在语言”中经由数据驱动进行“自下而上”(bottom-up)的搜索、处理和经由概念驱动的“自上而下” (top-down)的处理这二者互动而完成的。而在这加工、形成过程中还将会受到各种语境,包括社会性语境的影响,这种影响对形成更高级的抽象表征系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更高级的抽象表征系统就是有可能成为新构式的雏形“被捐款”。再通过泛化并接纳新的词汇进入该新构式(如“被就业”、“被苗条”、“被教授”、“被 82%”等),从而最终形成了稳定的不同于“被杀害”、“被批评”的带有讽刺和否定意义的“被X”这一新的语法构式。
“假设二”要告诉人们,听话者或阅读者是基于什么样的机制如何能接受他人“发明”出来的“修辞构式”并能从中领悟他人所要传递的感悟或认识?
以上都只是假设,希望能成为引玉之砖,但愿大家一起来进一步修正、完善这两种假设。当然也可以推翻这两种假设重新做出假设。我们认为,做好这项研究工作将有助于对构式理论的更有力的论证。
三、怎么提升构式理论的方法论价值
有学者已经注意到,“构式语法尚未表现出明显的方法论价值”[27]。施春宏[28]也早有此意思,认为“构式语法尚未清晰而系统地阐述其方法论主张”。我想原因就在于Goldberg等人目前主要着力于通过各种实验证明语言中存在的就是一个个构式,通过对双及物构式、“致使—移动”构式、英语动结构式、中动构式、英语way构式等个案研究,揭示语言概括(包括语言内概括和跨语言概括)这一语言的本质特点,并从语言习得等角度加以论述,同时分析构式的论元结构,这些研究无疑是有意义的,可取的,但是未注意研究、交代对一个构式本身的内部结构该作怎样的从大到小的分析。这就让读者感到,从语言观的角度来说,与以往的各种语法理论有很重要的区别,但从方法论的视角来看,未能让人体会到它的价值之所在。当然,对一个新兴的语法理论我们不能那样苛求,但我们需要去进一步探究这个问题,以便进一步完善这一理论。
我们认为,构式理论真要发挥它在句法研究中的作用,要增强其方法论价值,它需要与组块理论(Chunk Theory)相结合。(陆俭明[29] [30])
组块理论是由缪勒[31](Miller)的短时记忆理论演化而来的。我们所用的“组块”术语,其含义相当于英语的chunk或chunking*原先我们将chunk译成“语块”,这容易与国内的外语教学界和中文信息处理学界已经广泛使用的“语块”这一术语的含义想混。他们使用“语块”这一术语,更多的还是从词汇角度来考虑的,其含义大致相当于英语里的formulaic language。。组块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根据心理实验所提供的数据,大脑运用语言进行组码(即编码)也好,解码也好,能容纳的离散块的最大限度是七块左右(即 ± 7),关注范围是四块左右(即 ± 4);这样,一个语句表面看是由若干个语素或者说若干个词组合成的,实际的组成单位是组块(chunk)。正如陆丙甫[32]所指出的,组块是“人类信息处理能力的实际运用单位”。组块跟构式的关系是,无论从构式内部的语义配置来看,无论从构式的词类序列来说,也无论从构式的论元结构来说,组块是构成构式的组成单位。下面的例子很说明问题:
A BC
a桌子上放着玫瑰花。
b爸爸昨天从王府井放着一束妈妈刚从院子里
买来的红木桌子上摘下的玫瑰花。
[存在处所][存在方式][存在物]
上例a和b两句是现代汉语中存在构式的两个实例,不论长短,不管怎么分析,都得分析为A、B、C三部分——存在处所、存在方式、存在物。那三部分就是构成存在构式的三个组块——从构式的语义配置和论元结构来说,该构式是“存在处所—存在方式—存在物”;从词类序列来说,是“方位结构+V着+NP”。前面我们所举过的“V来V去+VP”构式,就可以认为由两个组块构成的:一个是“V来V去”,其形式特征是,前后两个动词相同,前一个动词后面带上趋向动词“来”,后一个动词后面带上趋向动词“去”。另一个组块就是那VP,会有两种形式,或是“还是/还数+形容词性谓语的主谓短语”,如前面所举的例(2)a—e各句;或是一个否定的周遍性结构,如例(2) f、g 两句。
从上也可以体会到,构式语法理论的层次观念跟美国结构主义的IC分析理论的层次观并不一致。美国结构主义的IC分析原则上是二分;而“构式—组块”分析法视构式的各个组成单位组块都在一个平面上,因此如果一个构式只包含一个组块,如追究不如意事件的原因的“VOV的”构式,实例如“看电视看的”(可以用来追究造成梗脖儿的原因)、“开夜车开的”(可以用来追究造成引发眼睛有点儿红的原因)等,就不切分;如果一个构式包含两个组块,如表示“活动凭借某工具而进行”的构式“V+NP[工具]”,实例如“吃大碗”(用大碗吃)、“捆尼龙绳”(用尼龙绳捆)、“(大门)锁铁锁”(用铁锁锁(大门))等,就二分;如果一个构式包含三个组块,如表示“存在”义的构式“NPL+V着+NP”,实例如“台上坐着主席团”、“墙上挂着一幅画”等,就三分;如果一个构式包含四个组块,如一般所说的双及物构式,那就四分。
我们认为,构式理论如果和组块理论相整合,就有可能提高构式语法理论的方法论价值。因为面对一个构式,不只告诉人们:“这是一个构式。”而需要进一步告诉、引导人们如何去分析这个构式,这就含有某种方法论意义了。按照“构式—组块”分析法的思路,对任何构式的分析手续或步骤应是:
a.分析各构式所表示的独特的语法意义,这种独特的语法意义需将该构式放在一定的篇章中才能分析获得。
b.依据该构式所表示的独特的语法意义,分析该构式内部的语义配置状况,亦即该构式内部的语义结构关系。
c.依据该构式所表示的独特的语法意义,分析该构式所包含的组块,以及各组块的特点。
d.分析该构式的词类序列,指出哪个是常项,哪个是变项。
e.分析该构式各组块具体选择什么样的词项,以及可进入该构式的词项的特点。
f.研究该从哪些方面考虑构式的语法分布状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各个构式的语法分布状况,进而给汉语中的构式进行语法分类。
ɡ.考察分析该构式的同形构式和同义构式、反义构式,如果有的话。
h.考察、分析该构式使用的语义背景。
我提出“构式—组块”分析法,不是要完全代替原有的句法分析思路。我一再申明[29][30],它只是对传统句法分析思路的一种补充。
[1] Fillmore,Charles J.Paul Kay and Mary Catherine O’Connor,‘Regularity and idiomaticity in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The case ofletalone’,Language,1988,64(3):501-538.
[2] Goldberg,Adele E..Construction:AConstructionGrammarApproachtoArgumentStructure[M].Chicago:The University Chicago Press,1995.
[3] Goldberg,A.E..ConstructionsatWork:TheNatureofGeneralizationinLanguage[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4] 张伯江.现代汉语的双及物结构式[J].中国语文,1999(3).
[5] 张伯江.论“把”字句的句式语义[J].语言研究,2000(1).
[6] 沈家煊.句式和配价[J].中国语文,2000(4).
[7] 沈家煊.说“偷”和“抢”[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0(1):19-24.
[8] 纪云霞,林书武.一种新的语言理论:构式语法[J].外国语,2002(5):16-22.
[9] 董燕萍,梁君英.走近构式语法[M].现代外语,2002(2):142-152.
[10] 徐盛桓.试论英语双及物构块式[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2):81-87.
[11] 徐盛桓.常规关系与句式结构研究[J].外国语,2003(2):8-16.
[12] 朱军.汉语构式语法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13] 王寅.构式语法研究:上、下卷[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14] 刘正光.构式语法研究[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15] 段业辉,刘树晟.现代汉语构式语法研究[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
[16] 牛保义.构式语法理论研究[J].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17] Adele E.Goldberg.构式:论元结构的构式语法研究[J].吴海波,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8] Croft,William A.RadicalConstructionGrammar.SyntacticTheoryinTypologicalPerspectiv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19] Adele E.Goldberg.运作中的构式:语言概括的本质[J].吴海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0] Tesnière,Lucien(1959)ElementsdeSyntaxeStructurale.中译本:吕西安泰尼埃尔《结构句法基础》(方德义选译),见胡明扬主编《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1] Chomsky,N..Languageandmind[M].New York:Harcourt,Brace & World,1968.
[22] Chomsky,N..KnowledgeofLanguage:ItsNature,OriginandUse[M].New York:Praeger,1986.
[23] 陆俭明.对构式理论的三点思考[J].外国语,2016(2).
[24] 陆俭明.句法语义接口问题[J].外国语,2006(3).
[25] 王黎.关于构式和词语的多功能性[J].外国语,2005(4).
[26] 施春宏.新“被”字式的生成机制、语义理解及语用效应[J].当代修辞学,2013(1).
[27] 陈满华.构式语法的方法论价值刍议[J].东北师大学报,2016(4).
[28] 施春宏.句式分析中的构式观及相关理论问题[J].汉语学报,2013(2).
[29] 陆俭明.从构式看语块[J].中国语言学:第四辑,2010.
[30] 陆俭明.再论构式语块分析法[J].语言研究:第31卷,2011(2).又见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2011(8).
[31] Miller,G..A..The Magical Number Seven[A].Pluse or Minus Two.ThePsycologicalReview,1956,63.
[32] 陆丙甫.直系成分分析法——论结构分析中确保成分完整性的问题[J].中国语文,2008(2).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6.04.001
2016-03-26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现代汉语构式知识库建设及其应用研究”(13JJD740001)。
陆俭明(1935-),男,江苏吴县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国家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国际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
H04
A
1001-6201(2016)04-000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