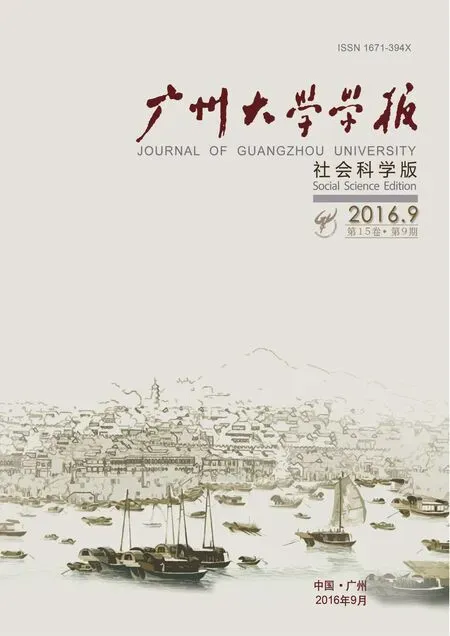唐代诗学“兴”范畴体系研究之一——关于“兴”范畴的溯源
王抒凡
(1.云南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云南 昆明 650091;2.昆明理工大学 国际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唐代诗学“兴”范畴体系研究之一
——关于“兴”范畴的溯源
王抒凡1,2
(1.云南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云南 昆明650091;2.昆明理工大学 国际学院,云南 昆明650091)
将唐代“兴”作为一个诗学范畴,对它的几个基本内涵即“讽喻美刺”的社会现实价值、“言有尽意无穷”的审美价值及“比兴”艺术等进行了溯源。弄清了“兴”的社会现实价值与儒家诗教理论的关系,“兴”与古代比兴艺术思维、比兴艺术手法的关系,以及“兴”的审美价值与儒、道、释三家美学的关系。
兴; 比兴; 兴寄; 兴象
唐代诗学体系形成以“兴”范畴为核心,经历了一个相当长内涵特征沉淀的历史过程。从最早的孔子以“兴”论诗,到汉代经学对“诗”“风、雅、颂、赋、比、兴”六义的阐释,再到魏晋刘勰、钟嵘的“比兴”论诗。“兴”范畴体系吸收了儒家诗教理论、汉代经学、魏晋南北诗学中的合理内涵,最终在初唐形成了重要诗学理论。
一、 “兴”范畴与儒家诗教
“兴”作为唐诗诗学范畴时,强调其社会现实功能,“美刺讽喻”内涵的说法影响特别大。诗歌“讽喻美刺”内涵是儒家诗教理论功利目的性的具体体现,缘自《诗经》的风雅比兴传统,经过历代文学批评家的阐释,成为“兴”范畴基本的特征之一。
(一) “兴观群怨”说
先秦两汉封建社会基本成型,需要有一种具有指导意义的价值思想体系,维持上层意识形态中各种社会关系,于是儒学出现了。孔子的哲学思想是以“仁”“善”为根本的道德伦理哲学,体现在其文学思想中,即强调文学对社会的指导、规范作用。从此,孔子具有政教色彩的诗学理论率先占领了古代文学思想领域。儒家以“诗教”为核心文学思想,诗歌成为了阶级统治实施政治教化的手段。《诗经》作为我国古代最早一部诗歌总集,孔子总结为“思无邪”,“思无邪”集中突出体现了孔子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和实用价值的诗学思想。在这种总体的实用主义诗学观的观照下,诗歌自然强调自上而下的教化和自下而上的美刺,即诗歌的“美刺讽喻”作用。根据朱东润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的统计,《诗》350篇,除《颂》诗不计外,《风》诗160篇中,美诗16篇,刺诗78篇。《小雅》74篇中,美诗4篇,刺诗45篇。《大雅》31篇中,美诗7篇,刺诗6篇。总计《风》《雅》265篇而刺诗得129篇。美刺诗在《风》《小雅》《大雅》中所占百分比分别是58.75%、66.22%、41.93%;在265篇《风》《雅》中所占比例是48.68%;综合《风》《雅》《颂》,美刺诗在《诗》三百中所占比例是54.67%,比重超过一半。
孔子《论语·阳货》篇云:“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 提出“兴观群怨”说是儒学诗教理论对《诗经》社会功用作出的全面价值判断。“兴”是感情起兴,可以托物、托景、托情;“观”可以知人识事;“群”在大众中产生普遍影响;“怨”可以进行文学批评,发不平之愤,发愤而作。西汉孔安国释义“诗可以兴”时说“兴,引譬连类”,由诗歌所描述的内容引申开来,联想到与此类似的事理。虽然他所说“引譬连类”并不是文学意义上的创作方法,而是特指儒家道德伦理哲学中君子的修身之道,即从纯粹经学意义上阐释“兴”义。但后世文学批评论述“比兴”时,完全将孔安国“兴,引譬连类”的经学意义移植到了文学土壤之中。“兴”义一方面指的是托物起情、托景起情,指的是文学创作阶段;另一方面,从文学接受层面来说,“兴”的含义已经具有了诗歌的审美价值功能。但从儒家诗教根本出发,“诗可以兴”的审美作用只是诗歌价值的最低级的层次,在此之上还有“诗可以观”的认识作用、“诗可以群”的教育实践作用和“诗可以怨”的批判现实作用,它们之间是层层递进的,最终落脚于诗歌的社会现实功能和政治教化目的。孟子的文学思想继承并且延伸了“诗教”观,提出了“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观点。“以意逆志”从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推知作者的思想感情;“知人论世”则是根据诗歌作者作品的内容推知时代的特征和风貌,同时说明了社会指导意义的重要作用。
孔孟“兴观群怨”“以意逆志”儒学诗论影响了整个汉代的文学批评理论。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对屈原作品进行批评,突出“怨刺”的观点,实际代表了司马迁的“以刺世事”的文艺思想。汉人的诗歌思想中依然坚持着孔子“兴观群怨”说重视文学的教化和美刺现实价值作用功能。这种价值评判也直接影响到了其他文体的创作观念并广泛辐射开来,从而成为汉代文学批评理论的主导思想。以汉赋为例,汉赋是汉代最主要的一种文体,批评家们以重视讽谏作用对当时流行的文体创作原则进行一系列规范。扬雄对赋前好后厌正是以讽喻的社会政治指导功能为标准的,少时认为赋好,即赋可以讽;后来认为赋不好,则是因为赋没有达到很好的讽的效果。所以,扬雄提倡的明显是文艺功利主义文学思想。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同样强调的是以赋为讽的文学观,强调赋的“劝百讽一”的功能作用。即便是以强调诗歌艺术性质为特征的魏晋时期的文学批评,也还是奉行着诗歌规讽功能一说。
从司马迁、王逸骚体怨刺创作论,到汉代扬雄、班固,晋代傅玄的赋体“劝百讽一”文学批判现实作用,“美刺讽喻”的社会现实功能性,占领整个汉代乃至魏晋的文学理论主流。从《诗经》的风雅比兴开始,文学的“美刺讽喻”功能已经从单一的诗歌体裁特征,横向辐射到了其他的文体中,形成整个古代文学现实主义诗论的主要内涵。“美刺讽喻”说之所以在汉代有如此的强大渗透性和穿透力,有赖于政治、哲学、社会学的基础。从西汉武帝构建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体系;到东汉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张衡,用社会进步的历史发展观看待文学,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王充提出文学有补于世的观点:“故夫贤圣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1]234-244(《论衡·对作篇》);“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2](《论衡·自纪篇》使得诗经风雅比兴的“美刺讽喻”传统的含义范畴扩大,文学理论由孔孟单一的美刺讽喻说,转变为了系统的社会功用说。所以在这样大的文学环境下,可见诗歌“比兴”是与社会现实密切相联系的。
(二) “六义”说
汉代《毛诗大序》的文学思想对“兴”范畴“讽喻美刺”内涵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就是在《毛诗序》正式提出了“六义”说,即以“风”、“雅”、“颂”,“赋”、“比”、“兴”论诗。此处关于《诗经》“兴”义的阐发,成为“兴”范畴诗学体系提出的基点。
一方面,《毛诗大序》“六义”诗论还是延续了儒家诗教思想,即“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另一方面,提出诗歌干预政治的思想原则——“美刺讽喻”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强调上层统治者对下层民众教化的同时,社会下层民众可以通过诗歌揭露讽刺统治阶级的政治弊端、道德缺失。这是孔子“兴观群怨”诗教理论的延伸,上对下实施教化,下对上进行讽谏,诗歌的根本作用在于对社会现实的指导意义。“美刺讽喻”说作为《诗经》风雅比兴传统的核心内涵,至此被固定了下来,诗歌也成为了诗人反映现实、批判现实的武器。历代诗论中都承袭了此观点,当然也包括陈子昂提出“兴寄”说所要恢复的《诗经》的风雅比兴传统,“美刺讽喻”就是其中内容之一。
从逻辑关系上来说,“比兴”说与“美刺讽喻”含义成为了一一对应的充分必要条件,诗歌凡运用“比兴”手法必须有“美刺”内容的现实所指,凡寄托“美刺讽喻”内容的诗歌能称为佳作的都是运用了“比兴”手法。可见,在唐代经学家眼中“美刺讽喻”功能被无限地扩大了,几乎成为了“比兴”唯一的本质特征。唐代的经学“比兴”观思想影响下,诗学理论也强调 “比兴”“美刺讽喻”传统。并以此作为改良齐梁浮华诗风,提倡复古革新的旗帜,陈子昂的“兴寄”理论也就由此而包含着讽喻现实的意义。中唐白居易等人更将“比兴”的美刺讽喻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关于白居易的现实主义以“比兴” 论诗在后面章节中还有详细论述,这里暂不展开。自陈子昂“兴寄”到白居易现实主义“比兴”论,再到晚唐各种诗论,唐代“比兴”“美刺讽喻”特征在各种诗论中未有断焉。如晚唐五代王梦简《诗要格律》的核心论点,“比兴”“不失正道”就是要合乎王道,有补于国事,也就是发挥诗歌“风雅比兴”传统,要求诗歌必须具有“美刺讽喻”深刻内涵。唐代的主张“美刺讽喻”的诗学理论,诗歌有无“比兴”,有无“美刺讽喻”内容成为了评判好坏的唯一标准,“比兴”论诗成为了古代诗歌批评的最重要的理论原则。
二、 “兴”范畴与“比兴”艺术
“比兴”体现在艺术思维和文学创作中,即成为联想、想象、意象象征。这种艺术思维由内心的感发而呈现出外在的艺术形象,就是诗歌创作基本形象思维和表现方式。具体而言,本段包含了“兴”范畴与比兴艺术思维和“兴”范畴与比兴艺术手法的两方面的研究。
(一) “兴”范畴与“比兴”艺术思维
我们可以借助古代美学思想中关于“比兴”艺术思维的理论,对“兴”范畴中包含的艺术思维方式一探究竟,有利于我们全面总结“兴”范畴的内涵特征。
1. 荀子《乐论》“物感”说
“比兴”艺术思维方式可以追溯到荀况的“物感”说。荀子的《乐论》从艺术思维角度阐释了音乐、诗歌的独立的审美价值,将儒家的诗教理论从政治功利“美刺讽喻”中解脱出来。张少康先生说“《乐论》最主要的贡献是提出了‘音乐——人心——道治’的模式”[2],借助此模式将荀子的“物感说”更完整地进行表达,即为“物感——人心——诗(乐)——道治”。由外物触发诗人的内心情感,产生诗歌艺术作品,这就是“比兴”艺术思维的直接来由。
“物感”说最终的目的还在于教化人心,所以它还属于儒学诗教范畴理论。但深究其哲学根源于“天人感应”的古老命题。古代哲学讲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自然外物与人在本质上有共同的契合点,人在自然中,自然在人中,有感外物激发诗人内心的情感,而成就诗乐。我们常说“兴寄”由物而兴、由景而兴、由情而兴、由感而兴,“物感”说本质就是关于诗歌“比兴”艺术思维的问题。黄霖先生认为“兴”是“心物交互作用的方式,也就是‘心化’过程中三种(赋比兴)不同的艺术思维……文学创作中的三种(赋比兴)最基本的形象思维和表现方式”[3]。“物感说”正体现了心物相互作用的艺术思维方式,成为“比兴”艺术思维的理论的直接来源。
2. 魏晋时期“缘情”说
先秦《诗经》“比兴”艺术思维还只是一种凭着感觉和经验的感性思维模式,魏晋时期,“比兴”成为了诗歌自觉理性的思维模式。“感物兴情”理论一经提出,在魏晋时期得到了更完全的文学层面的阐释。
魏晋时期的文学理论到创作实践,逐渐将“比兴”与“感慨”相联系起来,借以阐释“比兴”之“兴”的特殊含义,即作为文学创作中艺术思维方式存在的独立价值和意义。特别是陆机“缘情”说,借“感物兴哀”“寄其哀苦”的艺术思维方式的阐释,揭示了诗歌创作的整个过程。表面上看“缘情”说旨在强调感情色彩对诗歌创造的重要性,其实是对文学创作过程的第一次全面的规律性总结。“感物兴哀”即荀子“物感说”的继续,强调的是由物及心的艺术思维第一层次,“寄其哀苦”强调诗歌寄托思想情感,即艺术性创作思维的第二层次。单捻出“兴”“寄”二字,揭示了诗歌创作“感物及心”——“寄情成诗”的整个艺术思维及文学创作的过程。南北朝时期,由于诗人们的创作实践,“比兴”艺术思维方式方法的论述在各种诗论批评中逐渐多了起来。如,晋傅亮《感物赋序》:“怅然有怀,感物兴思,遂赋之云尔。”[4];梁徐勉《萱草花》:“览诗人之比兴,寄草木以命词。”[5];梁萧统《答晋安王书》:“炎凉始冒,触兴自高,睹物兴情,更向篇什。”[6];梁钟嵘《诗品·序》:“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7]北齐颜推之所言“标举兴会,发引性灵”[8]都是对“比兴”艺术思维的总结和肯定。
(二) “兴”范畴与“比兴”艺术手法
“兴”范畴的思想内容的社会功利性与表现手法的艺术性相互统一,具体体现为“比兴”与“寄托”的结合,称为“比兴寄托”说。“比兴寄托”说根源于“文质并重”的古老文学观,即在重视诗歌“寄托”的现实内容前提下,注重诗歌艺术技巧的运用,通过“比兴”艺术手法提高诗歌的审美价值。诗歌的文学自觉使得诗歌艺术手法的日益成熟,是诗歌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歌理论空前繁荣,在此种重视诗歌自身发展规律的文学思潮影响下,诗歌批评家们又赋予了“比兴”新的涵义和内容,为唐代“兴寄”说的提出,奠定了理论的基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学观点和著作有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
1. 东汉郑玄“比”“兴”阐释
其实在魏晋之前,就有学者提出了“比兴”作为艺术手法的观点,如东汉郑玄对诗“六义”的阐释明显承袭自儒学道德伦理哲学下的传统诗教观念,诗教的目的在于“政教善恶”,依然注重诗歌教化民众的功能作用。“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比”成为了教化人们察今之失的委婉表达方式;“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兴”成为了取善事教化劝诫的婉转表达。可见,“比”与“兴”的根本目的在于“美刺讽喻”,也就是“兴寄”说要求诗歌“寄托”要具有的社会现实内容。郑玄对“比”“兴”此层面的意义阐释显然是从《毛诗大序》的“美刺讽喻”诗经风雅比兴传统而来。但与《毛诗大序》中一味强调诗歌的社会现实意义不同的是,郑玄发现了“赋”“比”“兴”三种艺术手法的独立价值和意义。虽然这种艺术手法的发掘还是完全依附于政教内容,但这毕竟为后来诗“六义”从经学范畴中脱离出来,成为完全具有文学意义的诗学概念开启了先河。
关于如何进行诗歌“比”“兴”“美刺讽喻”的委婉表现,郑玄提出了“类比”和“喻劝”的说法,此种说法,来源于郑玄之先的另一位经学家郑众的“比兴”释义,“郑司农云:……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9]。“比”为比物,“兴”为托物,不能直言其事,托言彼事指代此事,取彼物而喻意他物,成为了“比兴”手法的艺术特征。“比兴”因此具有了最基本的艺术修辞手法比喻的功能和意义,并为同时代的其他文人广泛认同和接受。无论是作为哲学家的王符,还是文学家的王逸在对“兴”的认识上有着共识,认为“兴”是一种譬喻的诗歌艺术手法。就连东汉史学家班固在评价古人的文学创作动机时,也借用了“兴”的“引类譬喻”的类比作用。东汉时期哲学、史学及文学批评家关于“比兴”的观念形成了共识,即“比兴”作为具有比喻功能的艺术手法,其内涵在社会深层意识形态中达成了一致,并一直影响着后世的诗歌批评。
2. 刘勰《文心雕龙》“比兴”说
魏晋南北时期文学被称为文学自觉发展期,在这一时期作为一贯的政治附庸的文学终于从各种意识形态的复杂交汇中脱颖而出,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态呈现在世人面前,这出于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得益于当时发达的文学批评理论。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一时期为了突出文学的独立性,文学批评侧重强调文学的艺术形式,讨论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而对于文学的内容,文学的政治功利性的重视没有像前代那么重视,但是在当时的一些重要文论著作或是诗人评论中仍然不可避免地再次延续文学的社会意义。
魏晋时期由于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文学逐渐从经学的附庸中脱离出来,文学批评更关注诗歌自身艺术规律的探索。所以此时期的批评家侧重关注诗歌艺术性特征,对《诗经》中的“比兴”手法进行文学批评。“比兴”被冠以了“诗人之兴”的名称,说明晋代的文学批评已经完全明确地区分了《诗经》的经学意义和文学意义。这样当论及“比兴”时,社会现实作用的诗教层面的意义削弱,而作为一种诗歌艺术手法的功能作用逐渐在诗人和诗论家眼中得到关注。“比兴”“取义繁广,或举譬类,或称所见”强调的是“比兴”的比喻和联想、想象的艺术特性,“比兴”艺术手法的地位和作用在魏晋批评家这里得到了确认和提高。
“比兴”在他们的观念中还是偏重以“美刺讽喻”的风雅传统为主,而刘勰《文心雕龙》中有专门《比兴》一篇,提出“比”“兴”连用,在文学批评史上意义重大。“比兴”作为古代诗歌运用最广、最重要的艺术手法之一,从刘勰《比兴》篇开始它的文学价值正式确立。刘勰“比兴”说理论观点主要有二:第一,“比兴”手法运用的目的在“美刺讽喻”;第二,“比兴”是一种艺术手法。刘勰对“比兴”的认识明显受到郑玄“六义”释义的影响,维系着儒家诗教“美刺讽喻”的传统“比兴”观念,同时提高了“比兴”作为具有独立文学意义的艺术价值和地位。《文心雕龙·宗经》篇代表刘勰尊《诗经》为经典的儒家诗教观,所强调的仍然是诗歌的“美刺讽喻”功能和《诗经》的风雅比兴传统。但是另一方面刘勰指出“攡《风》裁兴”“藻辞谲喻”,运用“比兴”的艺术手法,对讽谏进行文学形式上的修辞修饰。
另外,刘勰注意到了“比兴”与物象的关系,扩大了“比兴”手法的意义和内涵,提出了“比兴”手法的另一种修辞功能意象象征。刘勰将意象细分为物象、事象和心象。“喻于声,或方于貌”视为物象,“或譬于事”视为事象,“或拟于心”视为心象。“比兴”不仅仅是诗歌最基本的比喻、比拟、类比修辞法,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艺术手法——联想、想象和意象象征。联想、想象集中反映诗歌创作艺术思维过程,从“触物圆览”到“合则肝胆”再到“拟容取心”,“触物圆览”观察生活,“合则肝胆”情感触发,“拟容取心”联想、想象,体现诗歌创作规律。另一方面,“比兴”的联想、想象功能使诗歌“兴之讬谕,婉而成章”,提升了诗歌本身的艺术性,增加了诗歌的审美意义。
从刘勰《比兴》论开始,“比兴”除了具有“美刺讽喻”的含义外,又多了比喻、比拟、联想、想象、意象象征等艺术手法的代称。以后批评家每论“比兴”指用“比兴”的艺术手法表达具有现实意义的思想内容。在强调“比兴”艺术手法的同时,也强调诗歌寄托思想内容的现实意义,也就是今人所称的“比兴寄托”说。
三、 “兴”范畴的美学渊源
任何一种诗学理论都可以追溯其美学根源,当然“兴寄”说也不例外。唐代是儒、释、道三教思想合流时期,“文有尽而意有余”作为古代美学最高层次意境的主要内涵,有着自身的美学基础,来自于佛、道、儒三家对美学的阐释。文艺美学集中阐释“兴寄”说的审美感受、审美趣味、审美观念、审美理想、审美心理等问题。
(一) 儒家“中和之美”的美学思想
儒家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中庸之道,即适中,不前不后、不上不下、不左不右,由此衍生出其美学思想的核心是“中和之美”,《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0]凡事有度,适度为“美”,超过了“度”即为“淫”,就没有了“美”可言,此所谓“中”;“和”,即平淡冲合,温柔敦厚,含蓄委婉。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11]《关雎》篇可以讲使人心灵激荡爱情,但是没有过度;恋爱中可以有的困惑哀叹,但是不能伤及身心,这才是夫子认为的美好的爱情。从侧面反映了孔子以和适为贵,以“中和”为美的美学思想。具体而言“中和之美”要求诗歌情感表达含蓄适度,委婉蕴藉。
以“美刺讽喻”为核心思想的《毛诗大序》“比兴”论诗,在关于如何运用诗歌进行讽谏是有特别要求的,那就是“主文而谲谏”。朱熹《诗集传》中对“谲谏”的解释是:“主于文辞而托之以谏”,也就是说,在进行讽谏的时候语言要有借托,不能直言其过,而需要用委婉含蓄的方式来劝诫,这与儒家“不偏不倚”的“中和”之美一脉相承。要求诗歌语言婉转地表达讽谏,在诗歌的措辞选择上要有所斟酌考虑,有所讲究,使之成为了一种语言的修辞艺术,一种修辞的婉曲格表达。也就是在诗歌语言措辞中的运用,“比兴”成为了一种语言修辞。这样的语言表达技巧在客观上就形成了诗歌“言有尽而意有余”的含蓄之美。清代诗论有温柔敦厚之说,本质内涵也是儒家“中和”之美。如清朱庭珍《筱园诗话》“诗有六义,赋仅一体;比兴二义,盖为一种难题立法。固有不可直言,不敢显言,不便明言,不忍斥言之情之境,或借譬喻,以比拟出之,或取义于物,以连类引起之。反复回环,以致唱叹,曲折摇曳,愈耐寻求。此诗品所以贵温柔敦厚、深婉和平也,诗情所以重缠绵徘侧、酝酿含蓄也,诗义所以尚文外曲致、思表纤旨也。”[12]从儒家诗教的温柔敦厚出发,深刻地揭示了诗歌“比兴”艺术与与“中和”“含蓄”之美的本质联系,是儒家诗教对“兴寄”审美价值的最完整地诠释。
(二) 老庄“得意忘言”的美学思想
“意境说”在中国古典美学理论体系中置于顶端,是我们追求的诗歌美学终极理想,是诗歌最高的审美追求。所以“兴寄”作为一种文学理论范畴,其发生、发展、演变与“意境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特别是唐代被美学界认为是“意境说”的产生期,唐代诗学理论中的种种概念都与“意境说”的发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我们考察“兴寄”说在唐代产生、形成、发展的同时,也要观照古典美学核心范畴“意境”,全方位地把握唐代文学理论。
意境说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美学结构中的最高层次,意境说的本质,简而言之,是情景交融,强调景中有我,我中有景,完全消解物我对立,以致自由无限制的审美境界。无限制的自由,即挣脱了语言文字的束缚,而在于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含蓄之美,与“兴寄”理论的美学内涵基本一致。道家主张用“心斋”“坐忘”——取消物我对立的方式到达“虚静”——绝对自由的美学审美境界,所谓绝对自由也就是庄子在《逍遥游》中无我两忘的超验审美体会。庄子对“道”的不懈追求,体“道”所达到的审美终极即为意境。《庄子》从“道不可言”“得意忘言”、“非言非默”中探究“道”的美学意义,从而可开启中国古代意境说之先河。
庄子认为“道不可言”,开启诗歌“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含蓄之美。《庄子·知北游》中说“道不可闻,闻者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13]301可见,“道”是不闻、不可见,亦不可名状。“道不可言”是庄子美学理论的哲学基础,也是古代诗学意境说的美学源头。庄子云“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田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田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说“道”为永恒,“道”有超越时空的无限性,因此“道”是无形无为的,是超物质无形精神世界,只能通过人的纯粹的理性智慧去体察。而语言则是有形的物质,可以通过语言文字对有形的物质世界进行认知。庄子的世界中有了“无形”与“有形”的对立,“道”与语言的对立,庄子认为不能从“有形”画出“无形”,不能从“物质”画出“精神”,不能从“有限”画出“无穷”。因此,也不能用语言来体会“道”。从美学的意义上来说,“道”就是庄子所要到达的终极审美目的,通过语言文字所不能表达,因为我们的理性思维也离不开语言,所以通过语言文字所不能体察的境界,用常人的一般思维认识中体会不出。“道不可言”,揭示了语言在传达审美信息方面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是符合语言规律的。
庄子认为“得意忘言”,是意境说的美学内涵。这里的“意”更接近于“道”的意思,即一种绝对的精神境界。这样的境界超出了人的语言和思维认知,因而得出了“得意”必须“忘言”的结论,“得意忘言”成为庄子意境说接受美学的核心理论,同时庄子提出能通过“见独”“坐忘”“心斋”等方法以达到“得意忘言”之境。所谓“见独”,即“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13]83分别讲了体“道”三日、七日、九日三个阶段的不同境界。经过九日的修炼,“我”即可以忘却外在的一切,如冲破黎明前黑暗的曙光一般,然后实现朝彻,最后便达到与道、与天地合一的境界。所谓“坐忘”,即“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与见独相似,坐忘也是一种忘却物我的方法。而“心斋”则更是如此,“如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13]44心斋即是虚怀万物、泯灭物我、齐一生死。这种见独、坐忘、心斋的基本精神便是取消物我的对立差别,做到物我两忘,以达逍遥游的境界,此为“得鱼而忘筌,得意而忘言”。
(三) 禅宗“六境”说美学思想
“意境”一词实际来源于佛教。“意境” 最早是佛家关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它的主要理论基础是“六根”说。所谓“六根”分别是耳、口、鼻、身五根和意根,每个感官都有特殊的功能和感官对象,因此称为“根”。耳得听觉知识、目得视觉知识、口得味觉知识、鼻得嗅觉知识、身得触觉知识,所以五根有不同对象感受,不同的对象即为“境”。五根结合为“意”,成为意根,五根加上意根就成了六根。“境”上升为六识,五根是感官的知识,意根是感官的能力,其获得的知识称为意识。因此有了六根、六境、六识之说,佛家正是通过六根、六境、六识来认识世界的。“根”是感官的功能、“境”是感官的对象,“意”的产生和形成是主客观的结合,所以强调主体主观能动性的强调。六根说,按唯识论整个客观世界都存在于主观认识,有了主观的识才有外在世界,没有识就没有外在客观世界。
“兴”范畴“言有尽而意无穷”审美价值内涵的形成除了受庄子“道不可言”“得意忘言”的审美思想影响之外,佛教哲学尤其是中国禅宗对其的影响也是颇大。庄子说“自不待言”“无无”“无有一无有”“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13]76都是类似于禅宗机圆活语。禅宗往往被解释为中国化的佛教,它是印度佛教与中国古典哲学,老庄道家和孔孟儒学的结合体。佛家讲求人生的彻底解脱,所以印度佛教一经传入就自然与同样讲求精神自由的老庄哲学找到了切合点。相传禅宗得于佛祖“拈花微笑”的传说:在灵山会上,大梵天王以金色菠萝花献佛,并请佛说法。可是,释迦牟尼如来佛祖一言不发,只是用拈菠萝花遍示大众,从容不迫,意态安详。当时,会中所有的人和神都不能领会佛祖的意思,唯有佛的大弟子——摩诃迦叶尊者妙悟其意,破言为笑。于是,释迦牟尼将花交给迦叶,嘱告他说:吾有正法眼藏,涅椠秒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转之旨,以心印心之法传给你。后来此修炼“法门”在南北朝的时候由达摩传到了中国,与中国其他哲学流派相互交融成为了中国禅宗。禅是梵文“禅那”的简称,汉译为静虑,是静中思虑的意思,一般叫做禅定,也就是庄子“心斋”“坐忘”以达“虚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禅与庄子之道都强调内心的自证,本心见性。
禅宗修炼法门讲求不立文字,只通过意会而不经言传的方式进行,与中国哲学思想中与老庄 “道不可言”“得意忘言”相契合,所以禅宗在中国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和广泛的发展。《楞枷经》(卷四)曰:“诸菩萨摩诃萨依于义,不依文字。若善男子、善女人,依文字者,自坏第一义。”[14]与此相类,在禅宗其他著述的语境中还有以“不假文字”“不用文字”“不着文字”“不拘文字”“不执文字”等说法。佛经《华严经·十通品》(第二十八)曰:“能于一切离文字法中生出文字来,与法与义,随顺无违,虽有言说,而无所著。”[15]特别禅宗六祖慧能之南宗,更认为舍离文字,直指本心,闻言当下之顿悟才是修禅正途。所谓“不立文字”是禅悟的独特修持觉悟方式,决定了它是超越思维逻辑推理的,是排斥语言文字的,即不立语言和不立逻辑,这又与庄子“道不可言”与“得意忘言”的审美境界不谋而合。
艺术意境必然是感性的直觉而非理性的认知。禅宗认为通过理性认知而得到的世界不是本原世界,所以“不立文字”正是要打破语言思维的束缚,不受既定逻辑、概念的影响。因为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在某种意义上讲,语言超越就是理性逻辑思维的超越。强调直观的知识而不是抽象的知识。所谓“道由心悟”,佛道完全是靠心领神会。于是禅宗往往运用棒喝、体势、默照、触境等非语言文字的体会方式,要求禅修主体直接从所接触的对象开悟得道的。在日常生活的自在中直观最高的真实,还原世界的本来面目,一个只能用心去感悟的世界。所以,只能这种“悟”直觉思维的方式本然状态下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审美知识。在艺术境界的表现,禅宗运用文字既用文字,又离文字,用其方便,离其名相,超其局限。禅宗以不离语言又破坏语言的方式,对语言的运用是超乎其上的诗意化运用。所谓“诗意化”,就是使语言从思维的顽固束缚中挣脱出来,赋予其深邃意境,超越语言,就必须从语言中进行超越,对语言的超越,就是借言显义,得义忘言。从而达到超理性、超逻辑性的无知之知、无修之修、无悟之悟,无得之得,使人们回到真正的禅悟之中。
佛教所讲的终极存在,是一个超越性的感悟境界,是最真实的彼岸。佛教哲学讲求的是生命的终极解脱,它的美学理想以超验解脱为目的。如何才能达到解脱,在于对道的体悟,这便是智能。智能在佛教来说就是般若与涅槃。般若既是一种工具,是洞悟道的工具,是对世俗知识的超越以后的所得,是一种小果。相对而言,涅槃则是一种大果,是洞悟之所得,即境界。般若与涅槃便是对道的体悟。“得意”和“忘言”在这里表现为语言与般若、涅槃的关系、可思议境与不可思议境的关系。
般若本义为“智慧”,指佛教的“妙智妙慧”,它是一切本心所具有的。《放光般若经》云:“般若无所有相,无生灭相。”[16]49般若智能并不关注具体的万物,而是关照万物的实相,体会事物的空性,又说“是以圣人以无知之般若,照彼无相之真谛;真谛无兔马之遗,般若无不穷之鉴。所以回而不差,当而不是,寂泊无知,而无不知矣。”[16]57般若不同于知识,而是用来关照无相的真谛,真谛并无具体的实体,般若也不是有形的存在。东晋僧肇《肇论》将佛教的“中观”哲学理论与中国老庄的道家哲学结合起来,为佛学的中国化开辟了全新的道路。《肇论》由“物不迁论”“不真空论”和“般若无知论”三个部分组成,在每个部分的论述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僧肇有意将“佛”与“道”相融合的迹象。如“物不迁论”与庄子“齐物论”“不真空论”与庄子自然辩证法、“般若无知论”与庄子“虚静”“心斋”“坐忘”等基本概念的哲学内涵,僧肇都找到了它们之间的相关相似性,在道家哲学阐释下的佛学“中观”论成为了中国禅宗的理论基础。
《宗镜录》曰:“圣智无知而无所不知,无为而无所不为。”[17]。智慧即般若,智慧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性智慧,僧肇解释圣智的本质是“无知而无所不知”;“妙智妙慧”即般若不同于知识,却又什么都知道,它超越于知识。“以圣心无知,故无所不知。不知之知,乃曰一切知。”[16]49相对于知识认识世界时的分析性、片面性、局限性,般若是从整体上把握世界的,因而克服了知识本身的缺陷,做到无知而无所不知,“智有穷幽之鉴,而无知焉;神有应会之用,而无虑焉。神虚而不无,存而不可论者,其唯圣智乎!”[16]51智虽无知,却能关于事外,从整体上了知世界之真谛、体悟万物之性空,获得智能,证得涅槃,这与庄子的进入体道的“虚静”状态极为相似。所谓涅槃或是“虚静”从美学意义上而言就是进入了审美的极致状态,即意境。
可以说,不可思议境指的是一种玄妙深绝的境界,它所揭示的内涵便是智能所关照的对象,或者说,自我一旦达到一念三千之境,便获得了智能,实现了肉体和精神的自由。佛教的美学思想正式建立的“可思议境”和“不可思议境”两级逐次递进,所以佛教审美讲求理性和超理性的结合,运用逻辑思维又超越思维,即利用语言文字又超越语言,而达成审美的最高意境。中国古代诗学理论在此美学思想的影响之下,更赋予了“言有尽而意不穷”审美价值更多地美学思考,无论是诗歌的具体创作者或是诗歌批评家都往往借用佛教美学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哲学中儒、释、道三家的美学思想都对“兴”范畴“言有尽而意无穷”审美价值和美学内涵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儒家的“中和”之美、道家的“得意忘言”美学思想、佛家的“六境”说共同指向了诗歌的最高审美层次意境说,是“兴”范畴“言有尽而意无穷”审美价值、内涵特征的直接来源。
[1]王充.论衡:下册[M].上海:大中书局,1933:234-244.
[2]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5.
[3]黄霖,等.原人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105.
[4]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文卷二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58:2574.
[5]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卷五十第九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8:3236.
[6]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卷二十第九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8:3064.
[7]钟嵘.诗品注[M].郭绍虞,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1.
[8]颜推之.颜氏家训[M]//诸子集成:第八册.北京:中华书局,1954:19.
[9]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十二·十三经注疏之四(黄侃经文句读,附校刊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335.
[10]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之六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892.
[11]郑玄,注.刘宝楠,注.论语正义[M].上海:上海书店,1986:41.
[12]郭绍虞.清诗话续编:下册[M].富寿荪,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2323.
[13]庄子.庄子注译[M].王世舜,注译.济南:齐鲁书社,1998:301.
[14]李英武,注.禅宗三经[M].成都:巴蜀出版社,2001:214.
[15]大方广佛华严经[M].实叉难陀,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232-233.
[16]僧肇.肇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1985:49.
[17]李理安.宗镜录[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6:1125.
[责任编辑尹朝晖]
Research Series No.1: On “Xing” Categorical System of Tang Dynasty Poetics——On the Origin of “Xing” Theory in Tang Dynasty
WANG Shufan1,2
(1. Postdoctoral Research Center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91, China;2.InternationalCollege,Kunming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Kunming,Yunnan650091,China)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esthetic value of “Xing” and the origin of “Bi-Xing” in the Tang Dynasty. As a poetic category of the Tang Dynasty, “Xing” basically meant the social value of “Metaphor and irony” and “finite words with infinite mean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cial value and the Confucian essence of “X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rtistic thinking of “Xing” and the ancient “Bi-Xing” aesthetic value and its artistic method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esthetic value of “Xing” and the aesthetics of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Xing”; “Bi-Xing”; “Xing-Ji”; “Xing-Xiang”
2015- 11- 12
王抒凡,云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昆明理工大学副教授,博士,从事中国诗学、唐代文学研究。
I206.2
A
1671-394X(2016)09- 0077- 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