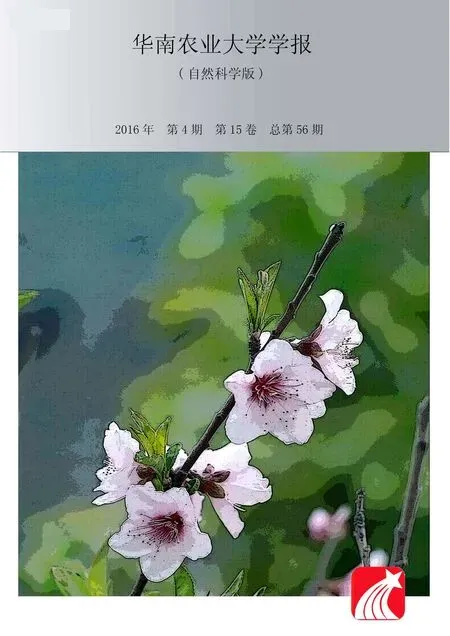社会治理精细化的框架及其实现
吴新叶
(华东政法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1620)
社会治理精细化的框架及其实现
吴新叶
(华东政法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1620)
摘要:社会治理精细化是一个实践命题,为一种增量治理方式,系针对以往粗放式治理的反思和矫正,它不是要实施颠覆性的改革,而是针对特定问题所展开的精准施策。从公共管理“过程论”的角度,精细化治理的框架可以围绕价值、主体和治理目标三个方面展开:以公民为价值归宿的精细化,目标是构建全民“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以多元主体能动性为导向的精细化,目标是激活“共建”诸主体的发展潜力;而以目标实现程度为参照的精细化,则是为社会治理提供管控的依据。
关键词:社会治理; 公共管理; 价值归宿; 多元主体; 精细化
作为一种实践理念,社会治理在我国推行多年,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部门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取得有目共睹成效的同时,也发现了许多具有共通性的问题。比如,出现重外延轻内涵、重结果轻过程、重多数轻少数等粗放式治理方式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尽管学术界和实践部门对社会治理的关怀不尽一致,前者倾向于实现社会自主,后者则致力于营造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但二者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难题:对于越来越微观的具体治理问题,如何使社会治理走向深入?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精细化”战略,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为社会治理实践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原则和路径。理论上,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有机构成,它从属于国家治理,因而治理体制与治理能力具有相对的同步性。就当前的情势而论,精细化是针对过去社会治理中存在问题的反思。在策略上,精细化治理并不追求颠覆性的改革,甚至也无需大刀阔斧地革新,而是一种增量式改革。本文试图以公共管理“过程论”的角度,将价值、主体和目标等治理过程中的三个核心因素结合起来,针对以往社会治理实践中出现的粗放式问题,研究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现途径,并探讨相应的学理依据。
一、文献回顾
在我国,社会治理及其精细化有两个源头:一是党和政府的战略导向,二是学术界的研究呼吁。
从文本上看,党的文献关于社会治理的表述经历了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及其精细化的发展过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概念,是作为“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战略部署[1]。党独立提出“社会管理”概念则始于2004年,在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被提升到执政党建设的一项时代任务而加以强调。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与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完善了社会管理的目标,号召“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这一定位在十八大报告中得到进一步深化,并增加了“法治保障”,演变成为二十字的“社会管理体制”。随后,随着国家治理理论的不断丰富和体系化,社会治理被纳入到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的框架之中。2015年召开的五中全会有所调整,提出了“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目标,而实现途径就是社会治理的精细化[2]。概括起来,这是党对社会治理再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也是对新时期社会治理战略的再部署。从党的文献中能够发现,这个“社会治理格局”的认识是螺旋上升的发展过程,最终突出的“全民共建与共享”目标指向,本质上是对治理主体作为价值归宿的一种体认,也是精细化治理的核心价值指向。
学术界关于社会治理的研究由来已久,而关于精细化的认知则系近年来的趋势。主要有两个依据:一是对社会治理主体及其价值定位的思辨激荡,二是对社会治理绩效的反思。对于前者,随着“以人为本”观念不断深入人心,社会治理“为了谁”、“走向何处”的共识基本达成,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主体价值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已经形成普遍共识[3];而后者关于治理绩效的争论则一直分歧不断,并可能在很长的时间内持续下去:是侧重于宏观层面的制度再建构,还是针对现有问题进行精细化“手术”?这两种立场都有充分的学理依据做支撑。不过,学术界所发现的有些问题则非常适用于精细化治理的操作,如基层治理的公共参与策略及其选择、网格化治理的信息管理与回应、社会安全的具体保障措施、公共服务的“最后一公里”[4],等等。
从现有文献判断,尽管存在共识,但也争论不断。客观分析,分歧产生的根源是对社会治理绩效的认知和判断不一致,因而立场难以统一。其中,不同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所引发的争议最大。在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社会治理涉及到政府放权、授权社会、社会自治等层面,并形成了诸如多主体、多中心、治理多元化等理念,因而绩效指标体系涵盖范围不断扩大,有越来越难以纳入统一体系的趋势。同时,随着学术交流和对话机制的不断开放,很多具有西方学术偏好的基本框架在事实上也影响着国内学术界的立场,扩大了争鸣的范围。在学术史的角度,我国的社会治理绩效研究源于政府绩效,而且系从国外引进。比如,美国政府责任办公室(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简称GAO)运用所掌握的数据,借助投入、能量、产出、结果、效率和收益以及生产力等六个指标,对联邦政府进行评估,以帮助联邦公共部门提高战略规划能力和应对挑战的管理能力[5]。该指标体系一度被我国公共管理学界广为引用。还有一套指标体系为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已故诺贝尔奖得主E.奥斯特罗姆及其团队所创设,他们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规划了一个五要素的指标体系:经济效率、财政公平、再分配公平、责任和适应性[6]。在我国,该体系也颇受学术界推崇,但并未有机会在实践中得以应用。主要原因是,国外研究成果有其理论范式的支撑,应用于我国的绩效评估实践难免遭遇本土化之困。比如,关于成本-收益标准,在公共管理实践中如何确定成本与投入的比率?这个问题放在社会治理上也是如此,以“政府负责”绩效评估为例,如何测算行政支出和业务支出的比率是否科学?其依据是什么?另外,社会治理的单位成本测定、资源占用率测定等,如何同治理目标结合起来?特别是在“共建共享”目标导向下,这些投入与产出的指标体系如何同“以人为本”的治理原则统一起来?事实上,学术与实践两张皮现象在西方也是存在的,比如帕特南对意大利南部的“制度绩效”研究就已经有所突破,没有唯成本等数字而下结论[7]。总之,社会治理的绩效衡量虽然不能局限于某一指标体系,但评估结果唯有可信,才可能是科学的。
在此方面,我国学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本土化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大学和中央编译局的学术团队,其使用的评估指标体系尽管也具有很强的西方学术素养,但在应用于对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实践评估中所取得的效果还是值得肯定的,赢得了理论界和实践部门的共同肯定*该团队使用的评估指标已经形成了系统化,具有很强的导向性。比如,指标体系中突出了“善治”的治理目标,在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有效性方面,进行指标建构。这一理论基础本身就是该团队一直为本土化所努力的成果。参见俞可平:《中国的善治之路:中美学者的视角》,《中国治理评论》2012年第1期。。值得注意的是,在已经实施的八届“地方政府创新奖”中,有三届特设了“社会治理”板块,旨在鼓励地方探索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子[8]。至于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践应用,学术界仍然分歧颇多,有研究主张从体制机制入手,从领导系统和主体间关系等宏观领域来推动精细化实践[9]。与此相反,有研究则主张从微观领域入手,以科学管理的角度推动社会治理精细化实践走向深入。比如,借助“标准化、流程化、信息化等手段,将全面质量管理等科学方法运用到社会治理实践中去”[10]。后者受到了更多的肯定和支持,并有来自于实践部门的经验验证。社会治理网格化就是一个典型,这也是中央所倡导的社会治理精细化方式方法。这种借助数字技术的治理将监督与处置进行了区分,使“复杂性问题不再由单一的个人或机构单独来解决,而是由整个网格提供的各种管理机制来辅助所有参与者共同完成”[11]。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信息技术平台体现了多元主体参与的民主与合作精神,特别是在政府主体的责任和回应方面,网格化的精准性还将随着技术更新而不断提高。但是,无论是宏观领域的治理精细化,还是微观领域的技术应用,对于公众参与鲜有涉及,人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并未触及,这同人是治理的价值归宿定位并不一致[12]。如果将这些思路应用于社会治理实践中,则可能会游离于“全民共建共享”的治理目标之外。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治理精细化需要规范和管控。
鉴于国外理论的本土适应能力与国内学术界的理论建构尝试,这些分歧和争论无疑还将持续下去。本文认为,认识差异源于不同学科的理论支撑和价值偏好的取舍,尽管对社会治理方向的影响不尽相同,但应用于社会治理实践则难免会造成部分领域存在偏差甚至盲区,而这恰恰是精细化治理倡导者对粗放式治理的反思之处,它不是要替代宏观的社会治理体制,也不是尝试制度创新,而是在特定时间、特定领域、使用特定方法,对具体特定问题进行精准施策,既解决现有问题,也预防类似问题的反复发生。
从比较研究的角度看,公共管理的“过程论”为社会治理精细化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其价值、主体、目标三要素可以被视为社会治理精细化的结构性要件,是实施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基本框架。
二、价值取向:构建全民“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在学理上,价值是一个哲学命题;在实证上,价值应用于社会治理所起到的作用是导向。在社会治理精细化的角度,公众是核心价值。这是由社会治理的属性决定的,其追求的目标涉及到“理性、自由、秩序、民主、公正、宽容、多元的社会‘公共生活理想’,向来被认为是人类共同追求和向往的最美好的生存状态和境界”[13],显然属于公共性范畴。马克思主义在批判康德的公共价值观时,跳出了公共意识、公共秩序与公共权利的小圈子,把价值提升到“人”的高度,认为人首先是社会人,作为人类与生俱来的根本属性,“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4]81从而迈向“意义世界”:其一,人作为价值核心是各种生产关系的体现,不仅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写照;其二,人作为价值核心是随历史发展的客观产物,对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形态具有决定性影响。国内学者关于社会治理价值的研究颇有启示,如将公共利益与公共制度做为治理的价值取向,这是间接反映人作为价值核心地位的立场:“一方面,公共利益存在于规范个体寻求其私人利益的努力之中;另一方面,公共利益又可被用来为私人利益的追求提供基本的公共设施和普遍分享的价值。”[15]总之,人作为社会治理的核心价值,也是治理价值的终极归宿,精细化治理应该围绕这个价值核心展开,而不是相反。综合考量,“人”作为社会治理的价值起点和归宿,其支撑性要素的功能指向应该明确如下:
其一,公共政策的价值偏好以公众为核心,须精准靶向。人作为社会治理的价值归宿,客观上要求政府“按照社会的共同利益和人民的意志,从保证公民利益的基本点出发,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16]。我国的改革持续了三十多年,尤其是在资源配置的市场导向下,公共政策一度出现过“效率导向”一边倒的现象,忽略甚至是无视公平。更严重的是,一些权贵阶层、市场单位甚至“绑架”政府和影响政府决策,最终导致“公民主体在公共生活中被边缘化。在规范的公共行政层面,克服政府被捕获的对策是回归公民主体,使公众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17]。另外,政府规制的价值偏好也须回归到这个价值核心来,让公众在共享社会治理成果的过程中,能够对政府主体的权力边界进行约束,使政府负责不至于偏航。总之,公共政策的价值实现是政府主导下的治理方式转变,要在坚持传统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的基础上,对偏离价值核心政策失灵领域进行精准施策和及时转型。
其二,公共财政的功能指向为公共领域,须精准到位。在实践中,国家的公共财政支出状况与财政能力,体现了公共利益与政治价值观的实现程度。当前,我国正在推行的“精准扶贫”就是精细化治理的有益尝试,这是借助公共财政的资源配置功能,通过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方式,引导社会资本流向社会而不是市场,对千差万别的贫困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扶贫,充分发掘有限扶贫资源的利用潜力[18]。在国外的社会治理经验中,动用财政资源也是一种最常见、最有效的行政工具,而且愈是发达国家对基本价值、社会环境和物质条件的要求愈高,财政功能的集中程度越是明显,如瑞典在公共文化领域的财政支持超过政府总支出的1%,日本则形成了由地方政府主导、中央和市级政府为配合的财政支持制度[19]。归纳起来,公共财政的价值指向应该是积极行政的公平观以及对公民的责任感。
其三,公共福利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有保障,须精准有效。众所周知,社会治理的价值实现程度同公共福利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尤其是那些具有“公共服务动因”(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的社会治理在“以脚投票”机制中往往能够得到及时回报[20]。当前,我国政府提出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目标,并对大众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制订了相应的发展指标。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国务院提出的均等化目标也存在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和群体差异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存在恰恰是社会治理精细化的作用空间。在宽泛的层面,不均衡的公共福利与公共服务水平需要政府的引导,政府作为责任主体,一方面要满足底层社会成员生活尊严的基本需要,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如基本的教育和文化服务、基本的健康保障服务等,另一方面还要致力于解决城乡差别、地区差异、群体差异等具体盲区问题,调整供给,务求精准有效,让公众有机会、公平地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最后,政府公共职能定位科学,须精准而规范。这涉及到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及其发挥情况,主要指政府在决策、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等过程中所体现出的职能及其履行状况。在我国,政府的公共职能配置一度存在规避责任的现象,如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农村社会发展上,过去应由政府承担的农村公共设施和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资金保障,而由农村集体和市场来承担。与此相反,在城市,政府则承担了更多不应当承担的责任。这些错位的政府职能需要调整,科学的政府职能体系包括“安全治理、市场治理、社会治理和事业治理”[21]。由此推论,未来的政府公共职能定位可以从社会治理精细化的角度,从公共需求、供给范围、公平配置和民主预算等层面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三、多元主体:参与“共建”的能动性源泉
社会治理是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过程,政党、政府、社会组织与公众,甚至是企业,都是这个多元结构的有机构成。“在治理过程中,政府的调控职能,企业的市场主体作用与社会组织的网络能力能够相互配合、彼此补充,协同推进社会发展。”[22]当前,社会治理的体制架构已经形成,无需再做根本性调整,因此精细治理的关键是如何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充分发挥不同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对此,学术界多论证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必要性,鲜有精细化运作的阐释,更乏有不同主体间协同治理的精细化路径研究。比如,经济学视角侧重于考量私人性产品存在的种种外部性缺陷,建议政府利用规制来控制外部性的发展与蔓延。当然,这里的政府是无可替代的主体,社会范畴的职能结构并不意味着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必须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公共管理视角的社会治理侧重于公共性范畴,强调不同主体的参与要兼顾社会治理的公共性功能领域,同时在管理客体、过程和目的等方面都尊重社会治理的规律。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公共性将呈现弥散状态,政府必然要同非政府主体进行合作,“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治理力量在获得公共性的同时也拥有了一定的社会治理责任,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建构起一种由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治理力量合作治理的局面。”[23]概括地说,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根本是调动参与协同治理诸多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以此推论,精细化治理对不同主体所提出的要求也不尽相同:
其一,政府主体方面,精细化的重点是转变治理方式,尽快走出“替民做主”的工作惯性。客观地说,以往政府工作方式中普遍存在的简单粗暴、官僚主义等现象已经得到根本性改观,但新形势下政府治理上仍然存在程序不合法、透明性不够、问责不落实等问题。其中,各级政府中普遍存在的“替民做主”治理方式需要改变,在没有获得公众认知的情况下就单方面采取措施,结果反倒招致群众的不满,“好心”办坏事。以基层治理为例,根据《村委会组织法》和《居委会组织法》规定,基层治理主体包括村(居)委员会党支部、村(居)委员会、群众性组织、社会组织、企业和村(居)民个体等。每一个主体参与治理的方式都存在差异,即便是同一类主体,其参与能力也不尽相同,政府自上而下的方式无法充分照顾到这种多样性,因而出现替民做主、假借民意或不符合民意的治理方式尽管情有可原,但并不符合治理规律。因此,治理的精细化就是要求有区别地针对不同治理主体特征,精准地祛除政府的不当治理方式。
其二,公民主体方面的精细化,重点是激活参与活力,尽快形成“共建”的治理格局。从学术界的研究发现,当前我国的公民参与普遍不足,且多集中于执行和监督环节,参与决策的机会很少,尚未达到“最低限度参与”的水平[24]。而从现有的制度设计判断,很多法律法规在实质性参与和程序性参与方面都有涉及,但操作性环节的规定不足则成为问题的关键。比如,听证会本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设计,许多听证会的程序设计也比较到位,但在参与人员的遴选与确定方面存在瑕疵,导致大多数听证会成为流于形式而饱受诟病。精细化治理对此提供了解决方案,能够在操作性环节等精准改进。当前,我国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呈现这样“三多三少”的态势:老年参与多而中年群体参与少;青少年学生参与多而职业群体参与少;女性公民参与多而男性群体参与少。这种参与现状无疑没有实现“共建”目标,如何通过治理的精细化,扭转不同群体参与热情不均衡问题,需要针对具体问题精准施策。
其三,在组织化主体方面,重点是提高协同治理的治理绩效。古语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结社水平能够反映出社会的整合程度和凝聚力程度[25]。在现有社会治理框架内,政府组织、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企业组织等形成了当今社会治理组织化主体的制度性结构,分别行使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治理职能,彼此之间既不能相互替代,又不能相互缺席。其中,社会组织是影响社会治理不可替代的组织主体[26]。但是,从我国社会治理实践来看,相比较于政府组织和基层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和企业组织的参与积极性和参与能力都普遍较低。其中,社会组织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依然没有根本性改观,尽管我国目前已经开放了“四类”社会组织的注册门槛,但社会治理的参与绩效并不显著。因此,当下的迫切任务是发现政社关系中的哪些因素制约了治理走向深入,精细化的任务是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需要说明的是,企业组织也是社会治理的主体,未来应该在企业社会责任(CSR)之外寻找更多的精细化空间和改进的可能。
四、目标实现程度:精细化管控的依据
公共管理的过程就是目标设定、组织实施、检验反馈的过程,而目标贯穿于管理过程的始终,既充当决策对象的角色,也是对治理结果进行管控的依据。在社会治理功能的角度看,目标达成是帕森斯所谓社会结构优化程度的评价标准,为社会稳定的终极性要素。那么,精细化管控如何围绕目标来展开呢?
其一,改变重结果、轻过程的目标分解方式,变粗放的指令下达方式为精准的权变配置方式,管控治理成本。传统的目标管理,尤为强调通过纵向或横向的途径来分解决策任务,并在时序上将目标体系统一起来,以完成决策目标。在科层制的强大吸附效应下,这种目标分解方式呈现两个特征:一方面,通过科层制组织进行目标分解,并落实到每一个人。显然,如此制度化的子目标设定并不是为了集中于完成目标任务,而是强调对人的责任,最终变成了个人负责制。如此一来,社会治理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效应就难以充分发挥出来;另一方面,科层制多采取指令式的目标分解方式,主要由高一层级的领导确定目标分解方案,无需同下级展开协商,因而既无法充分调动下级的积极性,也难能充分把握下级的具体情况,目标分解就成为“走流程”的程序性宣告。以此分析,精细化治理的空间很大,须避免这些粗放式目标分解方式,解决由指示、命令和计划等分解方法带来的消极后果,有效降低治理成本。
其二,对粗放式治理流程进行精准再造(reengineering),管控风险。在传统的粗放式治理流程中,通常是突出目标制定、分配任务、启动工作、跟踪控制等主要环节,但对关乎治理效果的微观流程则关注不够。在“细节决定成败”的背景下,精细化治理的作用能够完善这些微观流程,补足治理环节诸漏洞,管控治理风险:一方面,鼓励公众对治理流程进行定义和设计,改变“自上而下”的治理惯性,同时高层领导需要在流程完善中主动回应各种来自公众的诉求;另一方面,针对公众缺席参与决策的现实,再造规则流程,让公众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执行自定义的脚本,并“倒逼”上层对不适应治理需要的游戏规则做出应对;再一方面,资源配置流程精细化,如人力资源的分配、治理成本控制与质量监测等,从技术的层面提高社会治理的绩效。
其三,以标准化为突破口,提高治理工艺的精细化,管控治理效率。“治理工艺”是主体利用各种资源进行决策、执行和管控的方法与过程。理想的治理工艺原则是技术先进、目标达成有效率。当前,有些地方已经开展了标准化工程探索,力求从工艺上提高治理绩效。比如,大多数城市实行的“接警15分钟达到现场”制度、广东在政府部门引进“ISO9001标准”等[27],诸如此类的工艺创新实践举不胜举。遗憾的是,治理工艺尚未形成普遍的共识,有些地方开展的标准化试点甚至还未充分展开便不得不放弃。理论上,标准的制订对于治理对象而言是一种预期,对于治理主体而言是工作的具体化和明晰化,以避免出现推诿和搪塞现象。这些特征都符合精细化治理的要求,因此鼓励开展形式多样的标准化探索,并创造条件使标准化治理进入精细化的轨道,提升治理绩效。
其四,精准化地对目标群体进行衡量和判断,管控异议。在我国的社会治理实践中,有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令人忧虑:一旦有人组织抗议或表达不满,哪怕是公益性事业甚至是重大公共利益工程,通常的做法是暂停或取消。这种简单粗放的治理方式尽管兼顾了群众的诉求和表达,但显然缺乏科学的衡量与判断。尽管目标群体的满意度涉及到执政合法性,但需要区分这类人或这类群体是不是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立场和观点,不能放任民粹主义对社会治理的干扰[28]。为此,须对异议进行科学衡量,并作出精确判断。管控异议的对策有:一方面,要精准把握群众的主流立场和想法,衡量并判断这些积极表达诉求的人或群体能不能等同于公众;另一方面,要精准发掘“关键少数”的作用,使他们在引领社会舆论、表达公众诉求、示范行为方式中扮演主导性角色。
五、总结与展望
第一,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质是增量式治理,建立在对粗放式治理经验的反思基础之上,并非是颠覆性的体制革命,而是侧重于机制改进、策略方法等方面的创新与突破。同时,精细化治理更是一个实践命题,任何改进的思路和对策不能脱离实践舞台,所以精细化治理不是为了替代宏观制度框架,而只是完善治理的一个选项。
第二,不同视角下的社会治理精细化就有不同的治理思路,但殊途同归,都是为了提升社会治理的绩效水平。在“过程论”的角度,社会治理的精细化可以围绕价值取向、主体能动性和目标达成程度的框架而展开。其中,价值指向是精细化治理的核心,即精细化治理的价值取向要回归“人”的生活世界。
第三,精细化对技术的要求更为直接。在一些城市实行的“网格化管理”实践中,利用数理分析手段使网格规划更加科学;还有一些地方试图借用企业精细化管理的经验,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尤其是在大数据、互联网等数字技术日益普及的背景下,社会治理精细化的道路更为宽广,这是未来值得发掘的治理空间。
参考文献:
[1]胡锦涛.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N].人民日报,2004-09-27:1.
[2]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J].求是,2015,(21):3-7.
[3]吴新叶.农村社会管理何去何从:整体性治理视角的尝试性解读[J].理论探讨,2013,(2):145-149.
[4]蒋源.社会精细化治理新路径探索[J].人民论坛,2015,(2):47-49.
[5]Nancy Kingsbury,(2010). ‘The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and Congressional Uses of Federal Statistic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631, pp. 43-62.
[5]E.奥斯特罗姆,L.D.,施罗德,S.G.温.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政策透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7]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王列,赖海榕,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8]王俊,刘中兰.公民利益表达与地方政府管理创新——基于近三届“地方政府创新奖”相关案例的分析[J].理论导刊,2015,(2):20-23.
[9]赵孟营.社会治理精细化:从微观视野转向宏观视野[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1):78-83.
[10]陆志孟,于立平.提升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的目标导向与路径分析[J].领导科学,2014,(13):14-17.
[11]祝小宁,袁何俊.基于网格化管理的突发公共事件预警机制探析[J].中国行政管理,2006,(10):102-105.
[12]胡颖廉,罗俊锋.如何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N].学习时报,2015.12.17:5.
[13]袁祖社.“公共哲学”与当代中国的公共性社会实践[J].中国社会科学,2007,(3):153-160.
[1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5]詹世友.公共领域·公共利益·公共性[J].社会科学,2005,(7):64-73.
[16]周武星,田发.公共财政视角下的社会治理能力评估[J].重庆社会科学,2015,(4):18-23.
[17]吴新叶.如何防范地方政府被企业捕获[J].探索与争鸣,2009,(6):34-36.
[18]黄承伟,覃志敏.论精准扶贫与国家扶贫治理体系建构[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5,(1):131-136.
[19]张启春,李淑芳.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财政保障模式——来自国际的经验[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13-16,27.
[20]Wouter Vandenabeele,(2007). “Toward a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ory of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An institutional approach”.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Volume 9, Issue 4.pp.545-556.
[21]王浦劬.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含义及其相互关系辨析[J].社会学评论,2014,(3):12-20.
[22]郝郑飞,文宏.深化政府职能转变的理论探讨与实践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15,(3):152-155.
[23]张康之,张乾友.民主的没落与公共性的扩散——走向合作治理的社会治理变革逻辑[J].社会科学研究,2011,(2):55-61.
[24]张丽,周建国.社会管理中公民参与的困境与解决路径[J].岭南学刊,2015,(5):118-123.
[25]Ramzi El-Haddadeh, Vishanth Weerakkody,(2012).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alternative socially innovative public sector service initiatives on social cohesion (ALLIANCE): A research note”[J]. Transforming Government: People, Process and Policy,Vol.6,pp.283-299.
[26]A.K.M. Ahsan Ullah, Jayant K. Routray,(2007).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NGO interventions in Bangladesh: how far is the achievement?”[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Vol.34.Iss:4, pp.237-248.
[27]朱相达.“江门号”起航[N].人民日报,2008-11-22(8).
[28]陈龙,陈伟球.网络民粹主义传播的政治潜能[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297-301.
The Framework of Refining Social Governance and Its Practice
WU Xin-ye
(School of Politics & Law,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Social governance refining is a practice and an incrementally governance against extensive governance, and it is not aimed at a subversive reform but at dealing with specific problems. According to the process of public management, the framework of social governance refining should include value, subject and object. Civic values leads to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governance, therefore multiple subjective activities achieve their development potential. Meanwhile goal attainment is the basis for social governance.
Key Words:social governance; public management; value; multiple subjects; refining
收稿日期:2016-02-21
DOI:10.7671/j.issn.1672-0202.2016.04.0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4ZDC004);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4BZZ006);国家留学基金项目(201508310047)。
作者简介:吴新叶(1968—),男,安徽灵璧人,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基层治理、非政府组织。Email: wuxinye@ecupl.edu.cn
中图分类号:C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16)04-012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