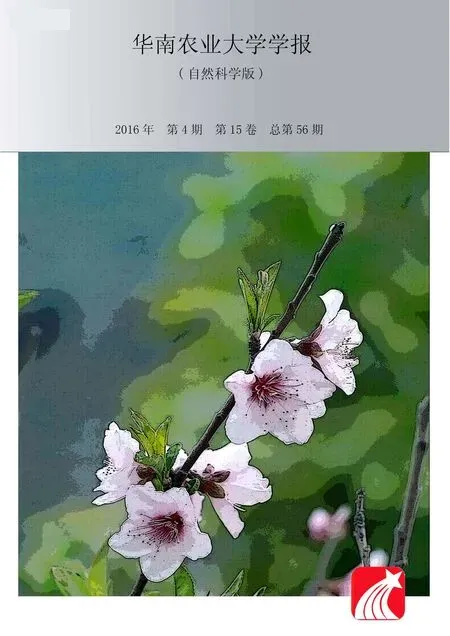地域社会学视角下的乡村都市化与村落转型
田 鹏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99)
地域社会学视角下的乡村都市化与村落转型
田鹏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99)
摘要:基于地域社会学视角审视中国乡村都市化进程,以地域社会分析框架从地域动力机制、社会样态及整合机制三个维度系统性考察超级村庄及城中村两种特殊地域社会类型。超级村庄是典型的市场导向内生模式,而城中村则属于行政驱动外生型模式;超级村庄地域社会样态呈现一种城乡衔接带特征,而实践中的城中村则是一种新型都市村社共同体样态;超级村庄通过一种后集体主义整合机制实现集体不散的神话,而城中村则通过复调型整合机制实现暂时性秩序,最终实现类贫民窟式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向现代城市社区转型。中国多元城镇化战略不仅要求学术界突破城乡二元对立的传统理论范式,也成为中国政府能否在城乡统筹意识话语中突破单向度发展主义模式和传统城乡二元体制的制度壁垒从而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之实践试金石。
关键词:乡村都市化; 超级村庄; 地域社会; 城中村
中国“乡村都市化”(Rural Urbanization)研究是人类学者回归本土田野的一次学科实践[1]。自20世纪80年代,人类学大师费孝通提出“小城镇 大问题”学术观点并陆续提出苏南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以及温州模式等一系列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学术议题后,志在富民就成为中国乡村都市化的内生使命。中国大陆关于城乡二元互动的相关研究大致集中在人类学(尤其是都市人类学)、社会学(尤其是农村社会学)、政治学(尤其是农村政治学),且分别冠之以“乡村都市化”、“农民市民化”或“农民工市民化”、“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同时,随着城乡二元实践的不同阶段,其研究重心和核心议题也经历了下述变化:第一,流动人口聚居区。以人类学者项飚关于北京浙江村[2]和王春光关于巴黎的温州人研究[3]为典型。第二,工业型村庄或内生的村庄。以折晓叶、陈婴婴关于超级村庄[4]和周怡关于华西村的研究[5]为典型。第三,城中村。以李培林、蓝宇蕴关于羊城村[6]、石牌村[7]和周大鸣关于南景村、凤凰村、大宁社区等的研究[8]为典型。第四,城郊农民市民化。以文军关于上海城郊地区农民市民化[9]和刘传江关于农民工、二代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10]的系列研究为典型。第五,“撤并村庄”和农民集中居住区研究。以王春光关于城市化进程中的行政社会实践逻辑[11]和叶继红等关于江苏农民集中居住区的相关研究为代表[12]。通过上述研究的爬梳发现,不同学科视角和理论框架下的研究成果难以进行理论对话并形成系统性学术话语;同时,即使同一学科内部也因单纯问题取向的研究路径导致“见树不见林”的碎片化、散点式知识格局,从而无法形成学科内部的研究体系和学术脉络。因此,中国乡村都市化与村落转型研究亟需一种超越问题取向和地理空间界限的研究进路,考察新型城镇化战略下中国城乡地域社会类型及其社会样态变迁。正如田毅鹏所言,中国城乡关系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必然要求相关学者超越既定学科界限将城乡关系置于一个更大的理论范式和分析框架中,而在日本逐渐兴起的地域社会学中的地域社会分析框架不失为一种可能和选择[13]。
一、地域社会:一个分析框架
20世纪60年代以降,以战后“都市过密化”和“乡村过疏化”为背景,日本兴起了以研究地域社会结构、集团构成以及人类行动为主要内容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学试图超越农村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的学科界限,以城市化背景下“生活社会化”为基本理论前提,以“乡村过疏化”为研究重点,围绕着“地域生活”、“地域组织团体”、“地域格差”、“地域政策”、“新公共性建构”等问题展开研究,建立起“结构分析”的学科范式。质言之,多元化的社会变迁要求一种超越城市社会学、乡村社会学学科界限以及传统城乡二元研究进路的新型理论体系,而以地域社会为核心范畴的地域社会学营运而生。目前,中国大陆关于地域社会学的系统性实证研究凤毛麟角,笔者以中国知网(CNKI)为检索平台,输入“地域社会学”主题词进行检索,仅有两篇文献,分别是上海师范大学蔡驎发表于《国外社会科学》杂志2010年第2期上的“地域社会研究的新范式——日本地域社会学述评”[14]以及吉林大学田毅鹏发表于《社会学研究》杂志2012年第5期上的“地域社会学:何以可能?何以可为?——以战后日本城乡‘过密—过疏’问题研究为中心”[15]。虽然大陆地区介绍地域社会学的学者凤毛麟角,但仅有的学术文献已大致勾勒出了地域社会学的理论范式:“现代地域社会何以可能”是地域社会学的元问题;尤其是现代地域社会的组织化问题,即现代地域社会形成的机制和过程,是地域社会学的基本课题;而地域生活论、地域集团论和地方政治论就从不同的角度展开对这一基本课题的研究,构成了地域社会学分析框架的主干部分。笔者综合目前大陆学术界仅有的两篇关于地域社会学的文献概括出地域社会分析框架,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下述学术命题及基本特征:
首先,地域社会的基本概念。作为地域社会学的基本范畴和核心概念,地域社会是指一种基于地缘关系而建立起来的社会集团的结构及关系性总体,在通常情况下学术界也将其称之为地域共同体[15]190。地域社会学意义上的地域社会或地域共同体具有如下基本特征:1. 地域社会的动态性,即地域社会学所关注的地域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地理学科中的静态物理空间,而是一种流动的、重叠的、甚至是充满利益博弈和价值冲突的动态地域空间;2.地域社会的统合性,即实践中地域空间的复杂性、多元化和流动性等特征是由城乡统合化变迁而引起的,且这种统合化变迁是建立在都市过密化和乡村疏离化基础上的,其统合动力则来自于地域经济结构转型;3.地域社会的关联性,地域社会的关联性是由动态性和统合性决定的,即地域社会是一个将都市和村落统合起来的统一体,是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
其次,整体性、系统性的研究视角及其关系主义的方法论取向。地域社会分析框架的整体性、系统性视角是由地域社会的实践属性决定的,即动态的、统合的、关联的地域空间必然要求突破静态的、城乡对立的、单纯问题取向的研究视角而采取一种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取向,换言之,地域社会学的特殊优势主要表现为在被限定的地域范围内,把握地域发生的诸现象、诸要素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对地域社会结构转型和关系变迁进行一种总体性把握[15]191。因此,地域社会分析框架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视角及其关系主义方法论取向提供了一种超越农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学科界限及传统城乡二元对立研究模式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可能。
最后,地域社会研究范式的基本议题。如果“社会秩序何以可能”是经典社会学的元问题,那么,现代地域社会的组织化问题,即现代地域社会形成的机制和过程则是地域社会学的基本议题[14]14。自日本地域社会学兴起以来,先后出现了包括地域生活论、地域集团论、地方政治论等相关论述在内的基本理论体系;同时,针对战后日本“城乡过密—过疏”的现实困境出现了包括地域结构分析与“城乡过密—过疏”对策研究,地域社会公共性转型与重构等政策性研究。当然,作为一门年轻的新兴学科,地域社会学仍处于发展阶段,在日本国内也出现了不同的发展方向,且因各种原因而面临困境。笔者无法详述地域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及困境,但此处借鉴该学科地域社会分析框架和理论视角,意在突破新型城镇化话语体系下中国城乡关系转型及一体化实践的相关研究局限性,如静态地域观、单纯问题取向、研究成果碎片化等,且因学科界限而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和对话平台。因此,笔者愿意将地域社会学视角进行一次本土化尝试,基于地域生活论、地域集团论和地方政治论等研究视角,并运用“地域格差”、“地域生成”、“现代地域生活”、“新公共性建构”等概念,系统性考察中国乡村都市化研究进程及其相关学术成果,以深化新型城镇化相关理论认识。
二、超级村庄与城中村:基于地域社会分析框架
按照Wirth—Redfield模型的理解,城乡关系的本质是城乡两种分化的互动,是都市性不断冲击乡土社会形成的一种乡土—都市连续统(Folk—urban Continuum)[2]8。从乡土—都市连续统模型而言,乡村都市化进程中的村庄面临的不仅仅是土地崇拜和工商精神导致的村庄工业化、村落无农化及社区边界多元化共存的特殊社会样态,即包括社会边界、文化边界、行政边界、自然边界和经济边界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现代性转型,且同时性存在于某一特定地域类型[6]38-39,更是一次乡土性与都市性的角力、一场总体性变迁[8]377。因此,笔者基于地域社会分析框架从地域生成机制、地域社会样态、地域秩序整合等维度系统性考察中国城乡互动历史沿革过程中两类特殊地域社会类型——超级村庄及城中村。
(一)“小村庄办大事业”:超级村庄
超级村庄是乡村工业化或村庄产业化的结果,是大市场中的小角落和市场网络所及、国家控制弱区的综合产物[16]。中国大陆地区曾出现过的超级村庄(当然也是政治明星村)主要包括人间天堂华西村、红旗不倒刘庄村、神秘的南街村、共有制的典型万丰村、“中国磁都”横店、天津大邱庄、“华夏第一钢村”永联村、北京房山韩村河等。
首先,就动力机制而言,超级村庄大致都属于先发内生型,往往肇始于农耕生计结构中的人地矛盾,农村工业是在农闲基础上用来解决困难的工业,起初仅仅是一种副业的经营状态;是一种发源于农、成就于工、借助于市的多维生成机制和动力类型;同时,这种超级村庄往往直接和某一个特定的克里斯马型人物(农民企业家,如华西村吴仁宝)有直接关系,甚至经济强人或村庄精英是此类经济强村发展的直接推动者和实践者[17]。当然,就先发内生型超级村庄的实践模式而言,学术界大致存在“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闽南模式”、“耿车模式”、“沪郊模式”和“民权模式”等七大类型[18]。也有学者从发展社会学视角将上述类型分为三种地域发展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以及三种村庄发展模式:“华西模式”、“南街模式”和“大邱庄模式”[19]。笔者此处无法详尽阐述每一类模式的实践操作机制,但就地域生成机制角度而言,是村庄(农民)对接市场并成为市场主体的结果,当然也离不开适度的体制松绑及国家控制程度减轻,无论是苏南模式下的依托集体主义遗产与市场进行主动对接抑或是温州模式、珠江模式下的农民生存理性产生的倒逼机制都表明,市场体系或市场机制成为超级村庄的原始驱动力。
其次,超级村庄的社会样态。作为一种中间形态的超级村庄是一个可具体明状的时空地域概念。折晓叶和陈婴婴将其社会特征概括为如下特征[20]:1.经济结构的非农化:工业化的成功使得非农产值,尤其是工业产值成为村庄经济的主要支撑。超级村庄已经形成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非农经济结构,工业产值和非农产值已占村庄全部产值的绝大多数,成为产值过亿乃至过十亿的发达村庄。2.社会人口结构多元化:发达的工业经济产生的劳动力集聚效应使得超级村庄逐渐成为农业劳动力转移人口的输入地,村社区内部已经形成以职业和身份多元化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分层结构。3.村庄经营公司化形成村落单位化:政经分离和企业办社区使得传统村庄整合机制松动,拟单位制和村落单位化现象日趋明显[21]。4.二元社区逐渐生成:社会福利的村庄内聚和基于村籍的均等分配原则,在强化村庄认同和利益整合之时也产生了一种二元社区[8]15-16。5.社会生活水平迅速提升:随着小村庄办大事业的逐渐发展,已经形成稳定的可用于村政和公益事业的村财收入,村庄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迅速发展,农民社会生活水平得到迅速提升。6.都市性嵌入:随着社会生活水平迅速提升和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加之流动性的进一步增强,传统乡土性发生嬗变,而都市性不断生长,新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和价值观念悄然崛起。
最后,从地域社会整合机制角度而言,超级村庄的社区整合机制面临一系列制度冲突和实践困境。1.作为企业组织的村庄与作为行政组织的村庄:村企分离和政经分离使得集体资产经营必然遵循效率优先的市场逻辑,其直接面对的是无形市场,而作为行政组织的村庄则需要发挥社区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利益分配和社会治理等功能,其直接面对的是有形村庄。2.作为政府的村组织与作为自治的组织:经济强大的超级村庄已超越自治功能并初具政府功能,尤其在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从摇篮到坟墓的“包”逻辑使得大部分超级村庄村民的社会福利已远远超过国家在“补”逻辑下为农民提供的福利水平,因此,超级村庄往往被视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前步入共产主义大门的样本和典型)两个维度已逐渐代替政府成为基层社区发展的直接推动者和社会福利的提供者。当然,“村庄能傍企业多久”仍然是目前超级村庄面临的实践困境[22]。且实践已表明,并非所有超级村庄都能在市场化大潮中顺利承担办社会的职责,也亦非所有超级村庄都能像华西村那样,顺利实现从集体主义到后集体主义的平稳过渡[5]32。3.作为拟城聚落的工业与作为城乡统一体的社区衔接带[23]:村落单位化使得超级村庄呈现一种拟城聚落的工业村地域样态,且导致社区整合仍然建立在村庄自治基础之上[24],难以履行作为城乡统一体的社区衔接带之职责并承担实现作为“村庄大转型”的弱质自治社区之使命。换言之,作为一种特殊地域类型,超级村庄社会整合机制内部存在结构性张力,如何突破传统村庄整合机制实现跨地域整合和新公共性体系建构,不仅是一个涉及政治生态环境、经济体制环境以及心理文化转型等多维度的巨变,正如折晓叶、陈婴婴所言,超级村庄的中间样态特征虽然是村庄在急剧变革时期集中形成的,但带有着深厚的乡土社会基础并不是一项行政政策和某些规章制度就可以改变的[20]48;且直接关系到超级村庄自身的前途和命运,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村办企业的社区化既不是现代企业的发展趋势,也不是农村社区城市化的趋势,村落社区面临着新的挑战[25]。
(二)“都市里的村庄”:城中村
城中村是继超级村庄后随着大城市优先战略和流动人口激增而在城乡连续统一体版图中出现的又一特殊地域类型,是既定制度体系和政策环境下传统与现代、城市与农村综合作用的产物。通过系统梳理学术界既有研究成果发现,目前关于城中村的研究大致集中在人类学,尤其是都市人类学和社会学两大学科门类中,其中,前者更多地关注城中村二元社区的社会样态及其社会影响[8]15~22;而后者则聚焦于城中村生成演化过程中的终结问题,如村落终结、无农化的村落、农民终结、户籍制度改革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一系列内生性制度冲突问题[26]。
首先,城中村生成与演化的动力机制。如果说超级村庄传统人地矛盾下农民式生存理性使然——主动对接市场,虽然往往遵循一种游走于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打擦边球逻辑;那么,城中村的生成则是伴随经济发展而展开的中国式圈地运动所致,是土地崇拜和工商精神的实践产物[6]16~17;当然,这一切的前提则是其特殊的地域空间——城乡结合部。城中村的另一重要生成机制则是国家人口迁徙体制松动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外来工的集聚式进入[27],而在安全第一的生存理性指引下为规避市场风险而形成的屋租市场则成为外来工落脚城市的一种特殊路径,换言之,作为一种农民理性的安全经济学与流动人口的落脚逻辑间是一种选择性亲和,但这也成为城中村演化过程中二元社区形成的主要逻辑,即是基于户籍制度的地方本文政策与作为生活方式的寄生性经济共时性作用的实践产物[8]21-22。一言以蔽之,城中村是由圈地运动导致的人地矛盾在生存理性、经济理性、社会理性三维一体的农民行动逻辑运作下(即从“种地”到“种房”)与国家体制松动产生的流动人口落脚城市在既定时空中综合作用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地域社会类型。
其次,多元地域属性下城中村的社会样态。作为地域社会学意义上的一种地域社会,城中村是一个多元地域属性集合体,不同地域集团视角下呈现出不同的社会样态:1.作为一种生存策略和生活方式的城中村。守护型经与弱性内部市场保护机制共时性生成城中村经济运作体制的两大特点,即安全第一的生存理性—保守经营的农民安全经济学为特征的守护型经济模式与村内的物业建筑不出村—物业经济为运作逻辑的弱性内部市场保护机制;也正是这两种不同模式和机制的亲和性运作才避免了无地农民生活的困境[7]10。质言之,作为首要地域集团,城中村首先是一种生存策略,无论是个体理性下的屋租市场抑或是作为一种集体行动的物业经济都是一种农民式理性的具体实践。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中村集中体现为非正式经济的繁荣与内外有别的经济利益内聚产生的都市性崛起,包括生计模式的非农化、经济结构(家户经济与集体经济)的三产化、社区阶层多元分化[6]117-128,如本地人贫富分化加速、外地人融入后形成的包括生产、生活、消费等在内的二元化。当然,不可回避的是,作为土地食利阶层或寄生性经济的“二世祖”及其社会教育问题则成为城中村生活方式中潜在风险。2.作为落脚城市的城中村。从流动人口角度而言,城中村仅仅是其进入城市的一种方式或路径,此时的城中村也被部分学者称之为流动人口聚居区或类贫民窟[28]148-150。一方面,作为一种自下而上城市化模式的“非预期性后果”,人口迁徙体制松动产生的大量流动人口面临寄居大都市的困境,且尤以住房问题最为典型,因此,低廉的房租和便捷的通勤使得城中村成为解决离土离乡外来人的首选;另一方面,准市民的身份定位及内外有别的村庄福利分配原则使得城中村非定居性移民的社区感与故乡情结共存。当然,走出城中村实现半主动性适应与建构型适应已成为部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普遍愿望。3.作为治理地域的城中村。高流动性与非正式经济的繁荣使得城中村被污名化为一个滋生越轨行为甚至犯罪的高危地带并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的重阵。城中村改造是一个涉及多元利益主体(包括市场、村庄、政府等)的整体性制度变迁,是一场里应外合的主动转型与自主变迁。就政府视角而言,一方面,加强政策供给和制度支持,尤其是在城中村完成文本意义上的村转居后的适度赋予其自治权并回归其自治理本质——公共性;同时,加强城乡一体化建设步伐,财政转移支付向城中村延伸并辅助其实现从类贫民窟式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向现代城市社区转型[29];另一方面,通过科学规划、合理引导并通过适度空间干预防止社会网络内聚导致的居住空间分异并构建政府—村民—开发商三位一体的利益均衡机制。
最后,地域社会何以可能?作为一种多元属性的特殊地域社会类型,城中村的终结之路必定无法一帆风顺,制度制约、利益冲突、村落权力复制循环与更新继替、村落文化与乡土性的苟延残喘等一系列现实问题表明,“一个具有上千年历史、经过历朝历代风风雨雨的古老村落,完成了它的终结过程,村落的终结和农民的终结不是完全同一的过程,不是非农化、工业化和户籍改革就能解决的,村落的终结更加艰难、更加漫长,一蹴而就的结果往往是造成社会的断裂”[6]415。一方面随着政经分离、村企分开,作为企业组织的城中村在市场中实现公司治理;同时,伴随着集体经济的不断壮大,社区福祉的进一步增加,都市性悄然崛起,让传统村落里的乡土性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黯然失色;另一方面跨越经济边界的城中村在集体利益内聚财富观念与村籍导向福利分配原则的共时性作用下,并未获得社会边界的实质性拓展,基于血缘、地缘的社会关系圈子仍然在转制后的公司经营、社区治理和居民生活世界中扮演者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不同程度地出现拟单位化趋势,即一种个体对组织的制度性依附,当然,并非城市社区单位制时代的总体性依附,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一荣俱荣的利益联合体逻辑。具体而言,作为一种多元属性的地域类型,城中村地域社会何以可能面临三个维度的内在张力:1.经济秩序重建中的边界张力与伦理冲突:一方面效率优先的市场本能必然要求作为市场主体的城中村遵循经济理性最大化的资本逻辑,能否突破村庄社会边界并重构一种全球一体化视野下的新型经济网络就成为城中村的本质使命;而作为滕尼斯意义上之村落共同体的城中村则是要求城中村同时必须扮演好人性养育所的基层性角色,共同体属性的城中村将会本能地阻止同为市场主体的城中村发生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意义上的“脱嵌”从而避免使其落入伦理困境之中。概言之,经济边界的本能拓展与社会边界地本能内聚共时性发生于某一特定的地域社会是城中村经济秩序内部张力的根源。2.政治秩序重建。转制后的城中村出现治理主体与权力来源双重多元化现象,被部分学者称之为双轨制权力模式,即街居体制下的社区治理模式与公司制结构中的法人治理模式二元并存的治理新格局。实践中不但面临治理原则、治理手段、治理内容、治理目标等一系列冲突,而且作为一种科层治理的社区治理模式还将面临转型困境,即村治模式的延续与社区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内在冲突[30]。因此,作为权力分配与再生产的重要载体,城中村政治秩序重构仍面临着多重困境。3.告别乡土与文化转型。城中村的文化转型面临的困境集中体现为作为共同体的角色延续与作为社会的功能再造。一方面集体经济利益内聚的福利分配体制主观上有效地防止了城中村的“脱嵌”式发展,但客观上也实现了作为村落共同体的城中村之社会边界固化,即血缘、地缘关系的不断再生产进一步固化了城中村的社会边界,内生其中的传统村落文化也得到了工具性传承;另一方面高流动性带来的现代性体验和高社会福利支撑的都市化生活方式使得都市性在城中村中悄然崛起,追赶时尚潮流、寻求心理刺激等都市化生活方式和生存体验逐渐为脱根的城中村主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所接受,而为满足流动人口而兴起的山寨文化也为其栖居之地——城中村增添了一份本不该属于它的文化色彩,而这一切似乎都与“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的田园式村落文化格格不入,也许正如社会学者李培林所言,“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但村落已不再是那个村落,羊城村从‘农村’变为‘工村’,又从‘工村’变成‘商村’,只是‘村’的帽子仍然难以摘下。”[6]34因此,如何告别乡土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
三、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批判性审视中国乡村都市化及传统城乡二元独立研究范式和分析框架基础上尝试性提出地域社会学视角下地域社会分析框架,并基于此框架爬梳中国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两种特殊地域社会类型——超级村庄及城中村,从地域动力机制、地域社会样态及地域整合机制三个维度系统性考察学术界关于超级村庄及城中村的既有研究。

表1-1 地域社会分析框架下的超级村庄与城中村
从上表中可以发现,地域社会分析框架下的超级村庄与城中村在地域动力机制、地域社会样态及地域整合机制三个维度均呈现不同特征。首先,地域动力机制。超级村庄是典型的市场导向内生模式,即通过体制松动、制度松绑在国家控制弱区实现村庄与市场的主动对接,换言之,“不找市长找市场”成为超级村庄地域社会原始驱动力的真实写照;而不同于市场导向内生发展模式的超级村庄,城中村则属于行政驱动外生型发展模式,即基于城乡结合部的特殊地域优势在中国式圈地运动和城市开发体制背景下实现被动对接市场,“从种地到种房”则是城中村地域社会原始驱动力的真实写照。其次,地域社会样态。作为一种市场导向内生型地域动力机制的实践产物,超级村庄成为乡村都市化及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衔接带,尤其表现为经济共同体转型,即基于农业和农民半市场化、半受非市场化保护的政策环境,以及双层经营而农户经营实际上更受政策支持的经营环境,村庄从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大队,转向具有不确定性的社区经济共同体[23]3;同于超级村庄的城乡衔接带地域社会样态,作为行政驱动外生型地域动力机制实践产物的城中村则表现出典型的都市村社共同体特征,包括守护型经济模式与弱性内部市场保护机制、经济关联型与拟家族化相结合的权力运作模式和权威再生产逻辑、乡土性与都市性共时性存在等基本地域样态和社会特征[7]10。最后,地域整合机制。虽然并非所有超级村庄都能在后集体主义时代延续集体不散的神话,但成功的超级村庄整合机制是典型的后集体主义,即一种自选性整合、利益整合、制度整合、权威产权整合有机协调和综合作用的新型整合机制,一方面延续了人们公社时期的传统集体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也是对传统集体主义整合机制的消解和再造[5]30。而实践中的城中村整合机制则呈现出一种多元化趋势和复调性特征,即基于某一特定价值观念和实践逻辑的国家、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和多重力量共时性作用于某一特定地域社会而形成的一种特殊整合机制,从而使得该地域类型呈现出一种未完成的社会样态。换言之,城中村在城市大开发体制和城乡一体化政治话语体系中,将从类贫民窟式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向现代城市社区转型。
当然,随着新一届政府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稳步推进,尤其是李克强总理提出的“三个1亿人”宏伟蓝图中的“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让中西部老百姓在家门口也能分享现代化成果”的设想,如何通过政府引导、市场推动、农民行动三者的有机结合实现“家门口的城镇化”,不仅是一个实践问题,也对传统城乡关系和地域类型的既有理论提出了挑战。笔者认为,中国学术界关于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不同地域类型研究虽已从不同学科视角、理论范式和分析框架下取得了丰富研究成果,但中国城镇化基本国情和多元城镇化战略不仅要求学术界突破城乡二元对立的传统理论范式和分析框架,也成为中国政府能否在城乡统筹意识话语中突破单向度发展主义模式和传统城乡二元体制的制度壁垒,从而通过城乡一体化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之实践试金石。
参考文献:
[1]周大鸣.“中国式”人类学与人类学的本土化[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3):30-35.
[2]项飚.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0:1-8.
[3]王春光.漂在欧洲[J].新闻周刊,2000,(24):10-11.
[4]折晓叶.村庄边界的多元化——经济边界开放与社会边界封闭的冲突与共生[J].中国社会科学,1996,(3):66-78.
[5]周怡.中国第一村:华西村转型经济中的后集体主义[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29-33.
[6]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17.
[7]蓝宇蕴.“都市里的村庄”:一个“新村社共同体”的实地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5:1-12.
[8]周大鸣.中国乡村都市化再研究——珠江三角洲的透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22.
[9]文军.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55-61.
[10]刘传江、程建林.双重“户籍墙”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J].经济学家,2009,(10):66-72.
[11]王春光.城市化中的“撤并村庄”与行政社会的实践逻辑[J].社会学研究,2013,(3):15-28.
[12]叶继红.农民集中居住与移民文化适应:基于江苏农民集中居住区的调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18.
[13]田毅鹏、徐春丽.新时期中国城乡“社会样态”的变迁与治理转型[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2):72-77.
[14]蔡驎.地域社会研究的新范式——日本地域社会学述评[J].国外社会科学,2010,(2):12-19.
[15]田毅鹏.地域社会学:何以可能?何以可为?——以战后日本城乡“过疏—过密”问题研究为中心[J].社会学研究,2012,(5):184-203.
[16]秦晖.传统中国社会的再认识[J].战略与管理,1999,(6):62-75.
[17]潘劲.经济强村研究:成因、问题与前景[J].中国农村观察,1999,(2):47-52.
[18]新望.村庄发育、村庄工业的发生与发展——苏南永联村记事(1970-2002)[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4:317-329.
[19]童星.发展社会学与中国现代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430-460.
[20]折晓叶、陈婴婴.超级村庄的基本特征及“中间”形态[J].社会学研究,1997,(6):35-43.
[21]毛丹.村落变迁中的单位化──尝试村落研究的一种范式[J].浙江社会科学,2000,(4):134-139.
[22]李强 等.多元城镇化与中国发展:战略及推进模式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85.
[23]毛丹.村庄大转型:浙江乡村社会的发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3-33.
[24]冯钢.整合与链合——法人团体在当代社区发展中的地位[J].社会学研究,2002,(4):7-14.
[25]张志敏.村落经济组织与社区整合[J].浙江社会科学,2003,(4):82-89.
[26]周大鸣.都市化中的文化转型[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97-102.
[27]蓝宇蕴.“村落终结”中的学术探寻——城中村研究随感[N].光明日报,2011-12-7(11).
[28]蓝宇蕴.我国“类贫民窟”的形成逻辑——关于城中村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5):147-153.
[29]闫小培、魏立华、周锐波.快速城市化地区城乡关系协调研究——以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为例[J].城市规划,2004,(3):30-36.
[30]田鹏、陈绍军.论“村改居”后村委会的功能嬗变[J].湖北社会科学,2015,(7):23-28.
Rural Urbanization and Village Transform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Sociology
TIAN Pe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99, China)
Abstract:Based on regional soci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rocess of rural urbanization in China and analyzes regional social framework from the regional dynamic mechanism, social state and integration mechanism system in three dimensions to study super village and urban village. First of all, on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regional perspective, the super village is a typical market-oriented endogenous mode, and the urban village belongs to the administrative exogenous mode; secondly, super regional village social state showing a convergence of urban and r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 the practice of urban village is a new urban village community like state; third, on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mechanism; the super dimension, through a village after the collective integration mechanism to realize the collectivism scattered the myth, the urban villages through the polyphonic integration mechanism of the temporary order, and ultimately the slum like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community transition to a modern city community; finally, Chinese urbanization strategy has become the touchstone of Chinese government, to breaks not only urban and rural split, but also one dimensional developmentalism and the traditional system of urban-rural dualism so as to realize urbanization.
Key Words:rural urbanization; super village; regional society; urban village
收稿日期:2016-04-14
DOI:10.7671/j.issn.1672-0202.2016.04.0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RK008)
作者简介:田鹏(1986—),男,江苏镇江人,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社会学。E-mail:tianpengdl@163.com
中图分类号:F3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16)04-01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