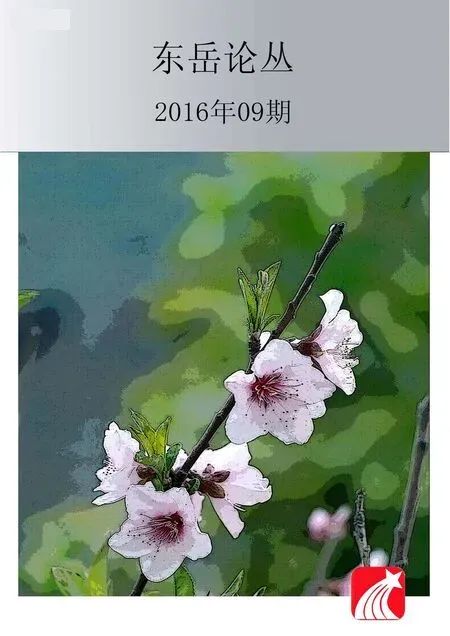老舍演讲佚文《灵的文学与佛教》续考与补正
徐慧文
(滨州学院 中文系,山东 滨州 256600)
文学研究
老舍演讲佚文《灵的文学与佛教》续考与补正
徐慧文
(滨州学院 中文系,山东 滨州 256600)
《灵的文学与佛教》是老舍在重庆汉藏教理院的演讲记录稿,最早于1940年12月刊载在佛教杂志《觉音》中,之后又历次刊载在《海潮音》、《正信》两种杂志中。但是,该文自上世纪80年代被发现后一直以《海潮音》的刊载文作为初刊文,并且在演讲时间的界定上,诸多说法不一。对《灵的文学与佛教》这则演讲佚文作续考与补正,一方面要更正其初刊信息,另一方面对演讲的具体时间作重新考察并予以新的材料补充。
老舍;《灵的文学与佛教》;汉藏教理院;演讲佚文
抗日战争期间,迁居重庆的老舍曾多次去往位于北碚的缙云寺,并且在寺中的汉藏教理院作过一次演讲,这次演讲由该院学僧达居记录整理后,以《灵的文学与佛教》为题发表在当时的佛教杂志《觉音》中,之后该文两次被其它佛教杂志转载,在民国佛教界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随着老舍研究资料汇编工作的逐步开展,《灵的文学与佛教》一文被重新发现,之后陆续收入老舍各类研究资料中,但是一直以《海潮音》1941年第22卷第2号的转载文作为初刊文,忽略了该文初刊于《觉音》的史实。在《灵的文学与佛教》这篇演佚文中,老舍主要从佛教对东西方文化艺术影响的角度出发,以意大利作家但丁《神曲》的创作为例,讲述了“灵的文学”与宗教的关系,进而强调了“灵的文学与生活”之于中国国民道德重建的重要性。因该文对老舍的文学思想与宗教思想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直以来学界予以关注颇多。
一
老舍的这一篇演讲佚文在上世纪80年代被安徽大学中文系吴怀斌先生首次发现,经由吴先生校对后陆续收入老舍各类研究资料中。目前,各类研究资料在介绍《灵的文学与佛教》原文出处时均以“《海潮音》1941年第22卷第2号”作为该文的初刊信息,并且关于这次演讲的时间,各类文献说法不一。今考该文最早刊载于《觉音》杂志1940年第19期中,而关于演讲的具体时间,并无确切记载。1940年12月18日出版的《觉音》杂志首次刊载了《灵的文学与佛教》*达居(记):《灵的文学与佛教——舒舍予(老舍)先生在汉藏教理院讲》,《觉音》,1940年第19期。一文,副标题为“舒舍予(老舍)先生在汉藏教理院讲”,作者栏署名“达居记”,这是目前能够找到的《灵的文学与佛教》这篇演讲稿的最早刊载记录。1941年2月1日,《海潮音》杂志第22卷第2号以同样的副标题,重刊了该文。之后的1946年5月15日《正信》杂志第12卷第3期转载了《海潮音》的刊载文,并直接以《灵的文学与佛教》为题,作者栏署名“老舍”。建国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该文长期湮没于历史的故纸堆中,直到1978年,张曼涛先生在台湾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时,才将该文收入丛书第19卷《佛教与中国文学》一书中*老舍:《灵的文学与佛教》,《佛教与中国文学》,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版,第317-323页。,该书收录时以《灵的文学与佛教》为文章名,作者为“老舍”,文中末尾未直接署名出处,却在《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目录索引》一书中标注“转引自《正信》杂志1946年第12卷第3期”。大陆方面,该文最早由吴怀斌先生在《海潮音》杂志中发现并予以校对,最早收入1984年8月由上海师院、安徽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四所院校合编的《老舍研究教学资料》一书上册中,收入时以“灵的文学与佛教”为文章名,文中末尾处标注“原载《海潮音》佛学月刊第22卷2号,1941年2月1日”*老舍:《灵的文学与佛教》,《老舍研究教学资料》,合肥:内部印刷版,1984年版,第288-293页。。1985年7月,该文以“舒舍予(老舍)先生在汉藏教理院讲”为副标题重刊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2期上,文后附加了朝戈金先生《老舍关于宗教的佚文》的按文。文云:“本期刊出的《灵的文学与佛教》原载《海潮音》佛学月刊第22卷第2号(1941年2月1日),加上原载《时事新报》(1944年10月10日)的《双十》一文,均由安徽大学中文系吴怀斌同志详加校对。”*朝戈金:《老舍关于宗教的佚文》,《中国现代文学丛刊》,1985年第2期。此后,由吴怀斌先生校对的《灵的文学与佛教》一文开始陆续被收入各类老舍研究资料中。1985年7月,收入曾广灿、吴怀斌主编《老舍研究资料》中;1990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老舍文集》第15卷中;1999年,收入舒济编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老舍讲演集》中,同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老舍全集》第16卷中。2001年,张桂兴先生在依照《海潮音》1941年的刊载文对全集的收录文作了23处补正*张桂兴:《〈老舍全集〉补正》,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193页。,2013年最新版《老舍全集》第17卷收录该文时,尽管编辑者已经强调“全集中所有作品在此次修订中,都参照最初版本、原发报刊及手稿进行校勘。”*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出版说明》,《老舍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但是,在参照张桂兴先生的补正文时,仍旧出现了一些错误,“影响到读者对文本的准确解读”*张炜炜:《内容的“残缺”与文学经典化生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目前,因张先生对该文的辑注已经非常详细,本文无须再作重复的全文转录工作,今依1940年《觉音》杂志的初刊文对《老舍全集》收录文作校对与补正,以期能为再次修订《老舍全集》提供一份必要的史实补充。(注:/号前为1940年12月《觉音》初刊文,后为2013年版《老舍全集》收录文,文中出现的标点均不添加。)
1、那时我在英国/那时候我在英国;2、那时我对他说/该时我对他说;3、结果他为我介绍了八十多部的佛书,据说那是最简要不过/结果他给我介绍了八十多部的佛书,据说这是最简要不过;4、它是任何研究文艺的人所必要念的一部作品/也是任何研究文艺的人所必要念的一部作品。5、单就他替西洋文艺苑中开辟一块灵的文学的新园地的这一点来说说/单就他替西洋文艺苑开辟一块灵的文学的新园地的这一点来说说;6、以为人死了就算了/以为人死了就完了;7、只是隐隐约约道出个地狱名罢了/只是隐隐约约的道出个地狱名罢了;8、第一部就是讲地狱/第一部就是讲的地狱;9、但天主教所奉的《圣经》并未说道地狱的情形怎样/但天主教所奉的《圣经》里并未说道地狱的情形怎样;10、谁也不能触犯他/谁也不敢触犯他;11、就生那一层天/就升那一层的天*“升”字在初刊文中全部为“生”。;12、实在是最大的贡献/实在是个最大的贡献;13、若不是古希腊雕刻传到印度/若不是古希腊的雕刻传到印度;14、西洋的近代雕刻画也许不会传到中国的/西洋的近代雕刻画也许不会输入中国的;15、故从这三方面说来/故从这三方说来;16、而且他与人世间打成一片了/而且他已与人世间打成一片了;17、还鼓打着乐器,敲打着乐器;18、没有一部写劝善改恶的东西/没有一部写劝善改恶的东西*原文中“部”后份有“份”字,疑为误排。;19、但都不是以灵生活骨干底灵的文字/但都不是以灵的生活做骨干底灵的文字;20、只不过一些劝世文罢了/只不过是一些劝世文罢了;21、也在说劝善的作品/也在说是劝善的作品;22、没有灵的文字出现/没有灵的文学出现;23、但收效毕竟很少的/但收效毕竟是很少的;24、尤其在中国这个非常的时期/尤其在中国这个抗战的时期;25、不做破坏抗建的工作/不做破坏抗战的工作;26、但未能把灵的生活推到社会去/但未能把灵的生活推动到社会去;27、灌输到人底的脑海去/送入到人民的脑海去;28、可以说我讲的一点小意义发生了作用/这样,可以说我讲的一点小意义发生了作用。
因为囿于文章篇幅,本文不再对《海潮音》刊载文与《觉音》初刊文作互校,从内容上看,两者所刊载的《灵的文学与佛教》除文字以外也并无较大差别。可以推测该文的刊载情况可能有如下两种:其一,1940年12月澳门的《觉音》杂志首次刊载了《灵的文学与佛教》一文后,《海潮音》杂志1941年转载了《觉音》的初刊文,并作了部分文字的修改,但并未署明“转载”字样;其二,汉藏教理院的学僧达居在记录完此讲稿后,同时投往法尊主编的《海潮音》杂志和竺摩主编的《觉音》杂志,但是因为海潮音在22卷第1期积压的稿件较多,无暇顾及这篇演讲稿,所以等到第2期才将其刊出。值得注意的是,《海潮音》1941年第22卷第2期除了刊登老舍的演讲文《灵的文学与佛教》之外,还刊登了作家王向辰的演讲文《从文学的观点上来谈谈佛教》。按王向辰的演讲发生时间为“1940年7月28日”,可知《海潮音》杂志当时确实存在稿件积压的情况。
二
老舍这篇演讲记录稿虽然在多种佛教期刊刊载,但是关于演讲的具体时间,在所有的刊载文中均未标注,加之老舍在重庆期间曾多次去往汉藏教理院,使得该演讲发生的具体时间考证复杂了许多。目前已出版面世的各类研究资料中,有关老舍在汉藏教理院演讲的时间说法不一,总计有如下种说法:“1939年暑假”说、“1940年8月”说、“1940年9月4日”说以及“1941年”说。其一,“1939年暑假”说,是杨化群先生在《我的老师——太虚》一文中提及的,文中写道:“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不堪日寇蹂躏的爱国人士,不愿当亡国奴,纷纷逃到后方,来到重庆。一些人来到缙云山,受到太虚老师的热情接待。1939年夏,老师利用暑假期间举办了一个训练班,邀请许多进步人士给师生们讲课。记得来讲课的爱国人士有:……老舍,以《神曲》为题,论述佛教神的思想,希望佛教徒把佛教消极的思想变为积极的思想,参加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中去。”*杨化群:《我的老师——太虚》,《名僧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210页。;其二,“1940年8月”说,据舒济主编的《老舍文学词典》(2002.2)中收录“太虚”一条记载:“老舍曾在1940年8月去缙云寺访问,并作《灵的文学与佛教》的演讲。次年又赠太虚一条幅。”*舒济编:《老舍文学词典》,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20页。另:该书第203页中“灵的佛教与文学”一条没有关于演讲时间的记载。;史承钧先生主编的《简明老舍词典》(2002.4)中“太虚”一条记载:“老舍1940年8月曾去缙云寺访问,并作《灵的文学与佛教》的讲,次年又赠条幅一帧。”*史承钧主编:《简明老舍词典》,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页。另:该书第167页中“灵的佛教与文学”一条却这样记载:“本文是1940年9月4日作者在汉藏教理院的演讲。”;其三,“1940年9月4日”说,据张桂兴先生《老舍资料考释(下册)》一书记载:“《灵的文学与佛教——舒舍予(老舍)先生在汉藏教理院讲》,讲于1940年9月4日,载1941年2月1日《海潮音》佛学月刊第22卷第2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2期重刊,初收《老舍文集》第15卷”*张桂兴编著:《老舍资料考释(下册)》,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版,第539、826页。另:在其著《老舍旧体诗辑注》(2000,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第75页《赠太虚法师》一诗的注释中云:“1940年9月4日,老舍曾应邀参观重庆汉藏教理学院,并向僧人们作了讲演。这次讲演由达居记录后,以《灵的文学与佛教》为题载太虚法师主编的《海潮音》佛学月刊第22卷第2号(1941年2月1日出版)。据老舍《致南泉诸友信》云:‘山上很美,庙里有许多花草,太虚大师住在一片竹林外的静室里。法尊法师请我们吃了素菜,还送了两包锅粑;我比僧人还穷,只好对学生们讲了几句话,否则真不好意思走出庙门。’”;其四,“1941年”说,据叶德先生在《老舍与佛教二三事》中记载:“抗战时期,老舍住在重庆,当时汉藏教理院设在重庆北碚缙云山,一些著名文化人士常到那里去,老舍也曾去那里造访佛教大德,与太虚法师、法舫法师等都有过交往。一九四一年四月,他集当时艺术家笔名成一小诗,写成条幅,赠与太虚法师,……当年老舍曾应邀在太虚法师主持的汉藏教理院作过一次讲演,题为《灵的文学与佛教》。”*叶德:《老舍与佛教二三事》,香港《明报》,1984年4月12日。
以上四种演讲时间说中,“1939年暑期说”和“1941年说”因为与老舍演讲稿刊出时间差别较大,在时序上是不能成立的。首先,老舍在汉藏教理院的演讲稿1940年12月就已经在《觉音》杂志上刊出,那么他的演讲无论如何也不会推迟在“1941年”发生,故“1941年说”为误判。其次,“1939年说”不成立是因为早在1939年6月,老舍就已经随“北路慰问团”离开重庆北上了,直至该年12月初才返回。据《绿旗》杂志1939年12月第1卷第3期“国内新闻”《北路慰劳团返渝覆命》一条记载:“北路慰劳代表团,自六月二十八日由渝出发后,南起襄樊,北迄五原,东达洛阳,西抵青海,旅行一万八千五百里,沿途宣慰军民,备极辛劳,兹该慰问副团长王石瑜,团员胡祥麟,陈希象,老舍,张西洛,徐剑模等一行九日(十二月)返渝市覆命,各界民众代表百余人郊迎……”*《国内新闻:北路慰劳团返渝覆命》,《绿旗》,1939年第3期。。可以得知1939年6月至12月老舍都不在重庆,故“1939年暑期说”可以排除;其次舒济先生编《老舍文学词典》和史承钧先生编《简明老舍词典》中收录的“1940年8月说”,未知时间参考来源。按老舍在《致南泉“文协”诸友》一信中所记载:“廿八日早半天,修改完事。吃过午饭,忽然想起,稿子是要交给华中图书公司的,何不到北碚去两天呢?交了稿,再开个会商议商议北碚‘文协’该办的事,岂不完了两桩心事?于是借了个小箱,就匆匆赶到车站。”*老舍:《老舍全集》(第15、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62页,第403-404页。可知老舍于该年8月28日才去往北碚。在到达北碚后一直在忙于“文协”分会的事,直到9月初会议结束之后才得以去缙云山,“1940年8月说”是否指的是1940年8月29日之前的某一天呢?目前尚无材料加以辅证。在四种时间说中,张桂兴先生“1940年9月4日说”似乎最接近史实,他所依据的材料是老舍1940年9月9日所写的《致南泉“文协”诸友》这封书信。在这封信中,老舍曾提及了“演讲”一事“决定次晨离碚,可是缙云寺僧人约去参观汉藏教理院,而且来碚数日还没见到赵太侔先生啊。又变了卦,决定上山。走到半路,遇到太侔先生,约他一同上山。……山上很美,庙里有许多花草,太虚大师住在一片竹林外的静室里。法尊法师请我们吃了素菜,还送了两包锅粑;我比僧人还穷,只好对学生们讲了几句话,否则真不好意思走出庙门。”“只好对学生们讲了几句话”当然是老舍对“演讲”的谦称,但演讲的题目是否就是《灵的文学与佛教》,尚不能确定。这封书信中,有许多关键的时间点,包含了老舍1940年8月底至9月初的全部时间行程。按照信中的时间点依次推理可以得知,老舍于8月28日晚到达北碚,“第二天(8月29日)遇到萧伯青兄。……伯青兄领我上了北温泉,……第二天(8月30日)一清早,他们走了,我就静候开会。两天两夜(8月30日—8月31日),雨没有住,……下了有两天的雨,看我不愿再继续听泉上雨声了,也就慢慢停了下来。把以群的存物交给旅舍,并留了条子,说明到碚去开会,我们就上了船(9月1日)……会是由下午二时开到五时(9月1日)。到五时,大家的话似乎还没有说完,可是复旦的友人们须赶快过江,故不能再谈下去。我本想次晨(9月2日)离碚,但胡风兄等都不许我走,愿拉我一同过江……过了江子展先生请吃饭,饭后到宗融兄处过宿(9月1日晚)。……第二天(9月2日),宗融兄领我到胡风兄处,子展先生也来了。……决定次晨(9月3日)离碚,可是缙云寺僧人约去参观汉藏教理院,而且来碚数日还没见到赵太侔先生啊。又变了卦,决定上山。……下午(9月3日)下山,绕几步道去看俞珊女士。”*《国内新闻:北路慰劳团返渝覆命》,《绿旗》,1939年第3期。如果按照老舍在信件中标注的时间来逐一推算,那么老舍在汉藏教理院作演讲的时间应为“1940年9月3日”,而张桂兴先生作“1940年9月4日”疑为少算一天所致。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得出的时间对于考证《灵的文学与佛教》的演讲时间来说,只具参考价值,还不能直接当“史实”用,因为信件中并没有记载确切的年月日,并且老舍在信中也没有提到关于演讲的任何细节,所以在没有确切的材料出现之前,是不能将这次演讲与《灵的文学与佛教》这一演讲等同的。
三
老舍曾经在回忆北碚生活时专门提及了汉藏教理院,他在散文《八方风雨》中这样写道:“北碚是嘉陵江上的一个小镇子,离重庆有五十多公里,这原是个很平常的小镇市;但经卢作孚与卢子英先生们的经营,它变成了一个‘试验区’。在抗战中,因有许多学校与机关迁到此处,它又成了文化区。……它已不是个小镇,而是个小城。它的市外还有北温泉公园,可供游览及游泳;有山,山上住着太虚大师与法尊法师,他们在缙云寺中设立了汉藏理学院,教育年青的和尚。”*老舍:《老舍全集》(第15、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62页,第403-404页。据《老舍年谱》以及相关史料的记载,老舍是1943年后才正式搬往北碚的,但是在此前的两三年他多次去往北碚*萧伯青在《老舍在北碚》一文中曾有记述:“一九三九年秋天,我到北碚工作。老舍每隔些时就来北碚一次,跟我商量设立一个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北碚分会。”说明在1939年秋之后,北碚成为了老舍的常去之地。,许多史料亦表明老舍在正式入住北碚之前,曾数次去过汉藏教理院。除了上文在信中记载的1940年9月参观汉藏教理院之外,1941年春夏之季,他还在汉藏教理院题赠太虚法师小诗一首,诗云:大雨冼星海,长虹万籁天,冰莹成舍我,碧野林风眠。并署题:“三十年四月,集当代艺术家笔名成小诗。大雨诗人孙大雨;洗君音乐家;长虹、冰莹、成舍我、碧野,均作家;万籁天剧导家;林风眠画家。写奉太虚法师教正。”2013年,北碚档案馆人员新发现的101页名家书册中,也有老舍在汉藏教理院题写的“佛光普照”一页(该页中只有老舍的朱文印章,未署名年月)。值得疑问的是,既然老舍曾多次去过汉藏教理院,那么他会不会在1940年9月之前就已经去过汉藏教理院并且在院中作过《灵的文学与佛教》的演讲?
1982年,作家赵清阁在回忆散文《嘉陵江畔》中写了一段关于四十多年前她和老舍等人一起游缙云寺的事,文中写道:“一九四二年仲夏,从美国回来的老作家林语堂住在缙云寺避暑,写小说。有一天他请我和几个文艺界朋友,记得有老舍、方令孺、梁实秋等上山素餐,还邀了法舫作陪。法舫和我们一起谈笑风生,林语堂带点讥笑地称他为现代新僧人,如果脱去袈裟,你不会相信他是和尚,因为他没有一般僧人的习气,开口‘弥陀’,举手‘合十’。”*赵清阁:《浮生若梦》,西安:华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474-476页。颇为遗憾的是,赵清阁这一则记述在时间上存在着明显的误记。因为林语堂住在北碚的时间是在1940年的夏季,他1940年五月下旬由美回国,经香港搭机直飞重庆,在重庆暂住了两个月后,于8月20日返回美国。另外,1942年仲夏法舫法师也不可能在汉藏教理院碚。法舫法师自1940年9月底就已经带着他的两个学生出国。他后来在印度学习了近9年的时间,直至1948年方才回国,在此期间没返回过重庆一次,很显然赵清阁误将“1940年”写成“1942年”了。如果赵清阁所记述的事件成立的话,那么它发生的时间一定在1940年5月下旬至1940年8月20日之间,由此也可以推断,1940年8月20日之前,老舍就可能去过汉藏教理院。这则回忆的材料虽不能为考证《灵的文学与佛教》的演讲时间提供确切的时间信息,但是其参考价值不容忽视。赵清阁在文中还谈及了名人在缙云寺作演讲的事,她这样写道:“缙云寺的庙宇很大,名僧太虚和尚在遨里办有佛学院;学生都是小和尚,除了讲授佛经以外,还教些一般课程,充实学生的文化知识。教师都是老和尚,具有一定文化水平;思想也相当文明开通,有点出家在家的精神风貌。他们常请游客中的名流给学生讲演,他们风趣地把这说成是‘化缘’;他们不要求布施金银钱财,只要求布施些文化知识。”*赵清阁:《浮生若梦》,西安:华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474-476页。文中还列举了郭沫若“布施”的几十分钟演讲,可以得知,当时文化名人在汉藏教理院的演讲可能是经常的事,并且一个人可能作多次演讲,老舍是否也在该院作过不止一次的演讲?这正是不能确定《灵的文学与佛教》演讲具体时间的最主要问题。
虽然目前没有更好的材料来确证这一演讲的具体时间,但是有不少的细节材料仍然值得重视。比如《觉音》1940年12月首次刊载这篇演讲记录稿,说明该演讲一定发生在刊载时间之前。另外《觉音》1941年2月出版的第20—21期合刊中,刊载的《弘一律师的修养与感化》一文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老舍演讲的记录者达居。在这篇文章中达居提及了老舍的这次演讲(标点依据原文,未作改动),文中写道:“一个人的言行,是否能够影响到大众——它的反应力底强弱,是因其感化力的大小而定的,而感化力的养成,要靠平常底道德修养。就以文学而言,没有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不是作者的心灵上修养得来的结晶,研究过西洋文学史的人,都承认但丁以后才有灵的文学,老舍——舒舍予先生在汉藏教理院演讲的时候,就特别指出中国的作家,缺乏真正的道德修养,所以很难产生伟大底‘灵的文学’。舒先生是新文学的老作家,他的话是笔者亲耳听到的,他吐出这个意思的时候,态度非常之认真,诚恳,面部的表情表现出无限痛心,他很希望我们佛教里产生出一个和但丁一般的人,救救中国的文章,使它更有灵魂。”*达居:《弘一律师的修养与感化》,《觉音》,1941年第20-21期。在《弘一律师的修养与感化》一文的结尾,达居还署名了写作时间地点“廿九、拾一、廿七、于仰光大金塔畔”,即写于“1940年11月27日”(民国纪年,不考虑新旧历转换)。又据《海潮音》1940年21卷11号《送法舫法师出国》一文中记载:“由世界佛学苑苑长太虚大师派遣到锡兰的传教师法舫法师,及留学僧白慧达居二师,已于九月廿九日由重庆出发了!”*石云:《送法舫法师出国》,《海潮音》,1940年第11期。可以得知,早在1940年9月底,达居就跟随法舫法师一道出国了,那么他所亲历的老舍演讲一定发生在此前。
此外,根据佛教杂志刊载汉藏教理院演讲稿的惯例,一般都会在演讲后的3-4个月内刊出演讲文。如郭沫若在1939年7月后在汉藏教理院作的《燃起佛教革命的烽火》演讲文,就在该年12月1日的《海潮音》杂志第20卷第12期中刊出;林语堂1940年7月28日在汉藏教理院作的《从现代欧美文化上来谈谈佛教》演讲文,在该年10月15日的《海潮音》第21卷第10期中刊出。如果按此推理,那么《灵的文学与佛教》这次演讲也一定发生在9月间了,但是史料讲求的是客观准确,在没有确切材料出现的情况下,任何的推理和判断只能作为“文献”式的参考,却不能当做“史实”用之。至于演讲具体发生于何时,依据目前所见的材料推断虽然无法得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要还原这则文献准确的历史信息以期对研究有所增益,除了持续的考证与追索之外,如何严谨地表述这则史料或许是我们考证工作中面临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
[责任编辑:王源]
徐慧文(1971-),女,滨州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I206.6
A
1003-8353(2016)07-016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