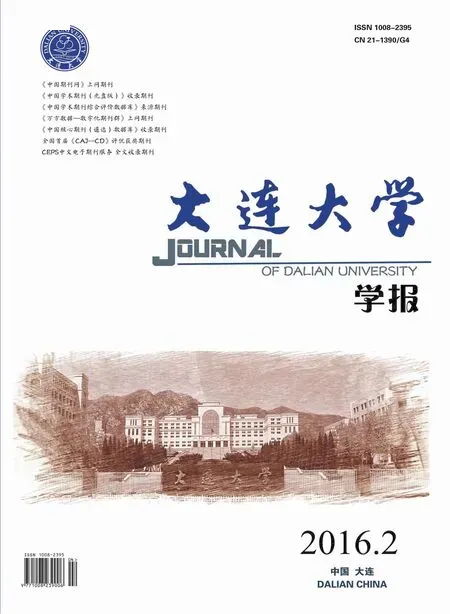格老秀斯及其自然法理论
——《战争与和平法》典读
肖灵姗(天津商业大学 法学院,天津 300134)
格老秀斯及其自然法理论
——《战争与和平法》典读
肖灵姗
(天津商业大学 法学院,天津 300134)
摘 要: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自然法的概念源远流长,其对西方民主、法治观念的发生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自然法观念的演化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批的大思想家,胡果·格老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就是其中之一。胡果·格老秀斯赋予传统自然法理论以新的思维视角、论证方法以及理论体系,发展了国际法理论,将神学教条和道德戒律从自然法中剥离开来,最终,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法学理论财富。他以一部超越了无理野蛮而极富智慧的巨作《战争与和平法》被誉为近代理性主义自然法学说的创始人,并被后世尊为近代国际法理论的鼻祖。
关键词:自然法;格老秀斯;《战争与和平法》
自然法(自然法学)既被称作一种学术的思潮又被称作一种学术研究方法,其根本宗旨就是强调公平正义和人的理性,认为现行的实在法要遵循自然理性,一切法律现象、法律规则的源头都归结于自然理性,它是永恒而普遍的。由此,实在法(制定法)一定要服从于自然法,并遵从这种公平、正义、理性等的根本理念。自然法学理论源远流长,在古希腊荷马时代就已经出现,它的发展历经古希腊罗马时期、中世纪神学主义时期、近代理性主义时期以及现代复兴时期。经过各个时期哲学家、思想家的阐释、发展、完善,到了17、18世纪时,自然法理论达到高峰并发展成完整的理性主义思想系统。
自然法是一面旗帜,它对西方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战争与和平法》这部著作体现了格老秀斯的自然法理论,不再是一种空洞枯燥的教条,而是一种解决问题的理论武器,他将自然法从神学中剥离出来,并以这种自然法理论为武器,详细论证了近代主权国家的产生以及近代国际法的一些基本原则。一切的学术,一切的学问必定是历史的,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与大师思想的对话上,而是要深思,在当代社会理论研究炙热的今天,格老秀斯的自然法理论是否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是否对我国法理学方法以及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价值呢,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一、格老秀斯的自然法理论
自然法(Law of Nature),就一般意义来说,它是指在人为制定的法之外永久存在、普遍适用的法,也即人类共同维护的一整套权利或正义。
(一)自然法是永恒不变的
格老秀斯认为“自然法是正当的理性准则,它指示任何与我们理性和社会性相一致的行为就是道义上公正的行为;反之,就是道义上罪恶的行为。由此可知,这种行为如果不是被作为造物主的上帝所命令的,就必然是被它所禁止的。根据所发布的这种命令作出的行为本身要么就是有合法拘束力的,要么就是不合法的,因而必须被看作要么是为上帝所命令的,要么是为上帝所禁止的。”[1]32这种区分标准显而易见的把自然法和人法相区别,而且也使得其与法区别开来。法不会命令本身就是不合法的事物,而是通过它的规定使某些事物具有约束力或者具有某些法律上的合法效力。格老秀斯认为自然法不仅与无人格无意志的事物有关而且还必然的与来源于人的意志的事物有关。比如,格老秀斯认为财产一旦被创造出来,就受自然法的约束与控制,一个人如果违背了他人的意志强占其财产就会被自然法所禁止。因此,法学家保罗(Paulus)说:“盗窃显然是为自然法所禁止的。”乌尔比安(Ulpian)把盗窃谴责为彻头彻尾的卑劣行为。为了增强论述的权威性,格老秀斯还补充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在《海伦娜》一诗(The Verses of Helena)中的语句:“因为上帝非常憎恨暴力,它不会让我们通过掠夺致富,只会让我们通过合法收益致富。如果富裕是通过不正当途径取得的,它只会是一种令人憎恨的东西。空气是人所共有的,土地也是。不过,每个人在充分享用其所有物时,一定不能对另一个人的所有物使用暴力或者做出损害。”[1]33
格老秀斯主张自然法是永恒不变的,上帝自己也不能将其改变。上帝的权力是无限宽广的,但是上帝不能改变一些本身外延就很清晰、很明了的一些事情,对于这些事情,理解途径是唯一的,不可能有其他的理解方式,否则就是悖论。比如,格老秀斯在本书中提到,二加二,必然等于四,而不能有其他任何可能。而且他还举例说任何内在是恶的事物,一定不是不恶的。亚里士多德说:“有些事情你可以很快地叫出它的名字来,但如果我们要发现其邪恶的本质,却要花上一段时间。这句话所表达的就是这种意思。”[1]34因为事物的性质和内容只由它自己来决定,所以事物的某些特性不是由上帝或者其他事物所支配的。有时候,上帝自己也要受到某些规则的制约和约束。格老秀斯在本书中还提到,自然法所支配的情形的变化并不是实质本身的变化,这种变化只是一种表象。一些永恒的自然法事实是不会发生任何变化的,变化的发生只是被支配事物的变化。比如,如果一个债主免除了我欠他的债务,我就不再有义务清偿该债务,这不是因为自然法已经不在命令清偿正当的债务,而是由于被免除,我的债务不再存在了[1]34。这个例子很好的支撑了格老秀斯主张的自然法是永恒不变的这一论点。在这一点上,阿里安在《艾比克泰德传》(Arrian in Epictetus)一书中正确的指出,借钱并不是产生债务的唯一要件,而是必须还有一个附加条件,即借钱未被偿还[1]34。因而,上帝特别命令去做的一些事情(根据法律是犯罪的一些事情)不能与犯罪联系起来。上帝所不能改变的自然法的一些规定是受某种情势所制约的。此外,格老秀斯认为,根据自然法,在财产权被引入之前,每个人都有权使用他所发现还没有被占有的任何东西(现在所谓的无主物);在法律被制定之前,每个人都有权通过武力报复其所受到的人身伤害。
格老秀斯主张自然法来源于理性,这种性质的自然法与蒙昧的神法不同,与现行中的制定法不同,因为后两种法依其性质本身不能强制人们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但是自然法可以,它可以支配人们的行为,自然法尊重自然存在的一些规律和事物,它也尊重从人类行为中产生的一些一般普遍性的事物。格老秀斯对自然法的这种解释也揭示了格老秀斯笔下自然法基本特征:
1.自然法与人法的关系。自然法高于人法,凌驾于人法之上;自然法是一种永恒法、绝对法,它是一种最一般、最基本、最普遍的法,起决定性作用;自然法永恒不变,普遍使用。
2.自然法是理性之法。虽然格老秀斯仍然主张上帝的意志是自然法的渊源,但是,他更加强调在上帝指导下的人的理性是自然法本身。格老秀斯突出人的理性对自然法的决定作用,他说“自然法是如此的不可变易,就连上帝也不能加以变更,上帝的权力虽然无限,但是有一些事情即使有无限的权力也是不能动摇的,例如上帝也不能颠倒是非,把本质是恶的说成是善的。”格老秀斯的自然法理论已经从神学中剥离出来,他从人的理性出发去观察事物、观察世界、解释世界中的一些现象。格老秀斯把自然法定义为一种正当理性的命令,它指示:任何与合乎理性的本性相一致的行为就有一种道德上的必要性;反之,就是道德上罪恶的行为。“即使我们应当承认我们并不承认的东西——因为这并非一种极恶,即上帝并不存在或者说上帝并不关注人类的事物”,这种自然法亦会普世于天下。据此,格老秀斯把自然法建立在一种遍及宇宙的永恒理性的基础上,尽管他承认一个有神论的基础也是有可能的。格老秀斯指出,有两种方法可以证明某事是否符合自然法。“演绎证明法在于表明某事物是否必然符合理性或是社会性;归纳证明法在于断定某事是否符合那种被认为是所有各国或所有文明发达之国所遵循的自然法——即使这种断定并不具有绝对的把握性,至少也具有极大的可能性。”
格老秀斯认为,与自然法相对的是“意定法”(volitional law)。意定法规则并不能根据明确的推理过程从那些永恒不变的规则中演绎获得,因为其唯一的渊源乃是人的意志[2]。
(二)自然法的原则及证明方法
格老秀斯认为,从人类理性出发,自然法至少要包括以下原则:1.不欲求属于他人的东西,即不得触犯他人财产;2.归还属于他人的东西并用我们自己的财物使他人的财产恢复原状,即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及由此获得的收益归还原主;3.遵守合约并践履诺言,即应当履行自己的诺言,执行和遵守契约;4.赔偿因自己的过错而给他人造成的任何损失,即应当赔偿因自己过错而造成的损失;5.给应受惩罚的人惩罚,即违法犯罪应受处罚。他还主张而其他一些具体的规则都是从这些规则中派生出来的。所有的这些原则和要求都是以人的理性为根源,所有人都要遵守这些基本原则。
格老秀斯把国家定义为“一群自由的人为享受权利和他们的共同利益而结合起来的完整的联合体”。因而,格老秀斯主张国家起源于契约。他认为,首先人类具有社会性,这种社会性就要求有一个机构来管理,这个机构就是国家。在他看来,自然法是永恒的、普遍的,但是它本身并不具有这种效力,只有与普遍的协议相适应才会有效力,人们会根据上文中所提到的自然法的一些基本原则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但是这完全靠人们的自觉和欲望行使,而人们的自觉和愿望都是主观上的情感,所以充满了不安性和不确定性,那么,这时就需要消除这种不安和不确定性,必须使人们的行为受到一定的约束,契约也就由此产生。契约由社会成员和国家签订,人民把他们的主权让渡给统治者,统治者操控着这一主权,同时,统治者有义务遵守自然法原则。
格老秀斯认为,自然法的证明有两种方法,即先验的证明方法(a priori)和经验的证明方法(a posteriori)。先验是相对抽象的证明方法,经验是相对通俗的证明方法。比如说,先验的证明方法就是指我们显示某种事物符不符合理性和社会性。而经验的证明方法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因而有一定的或然性,任何事物是被推断为与自然法相一致的。在一个国家或者是社会中,共同的基础决定了共同的认识,从而对待一些事物会达成共识。一般而言,普遍认为是正确的事情就一定会是正确的,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当所有人都同意我们的主张的时候,那就是支持我们观点的强有力的证据。”西塞罗也认为,“所有国家的同意无论如何都应当被认为是与自然法相一致的。”塞涅卡认为,“所有人看任何事物是完全一样的时候,那么,这些人的看法就是该事物真实性的一个证据。”昆提利安也认为,“只要所有人都认为某事物是真实可靠的,那么我们就认为这些事物是真实可靠的。”波斐里也指出,“一些国家如此的不开化,从而使他们做出的判决不符合人性。”罗得岛的安德罗尼库斯说过,“对于健全理智的人来说,自然正义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也是无法改变的,尽管神志不清或满脑子是邪恶想法的人会持相反的看法。”
格老秀斯的自然法思想主要就是集中于理性的自然法,其探讨了什么是自然法、自然法的特征、自然法的内容以及国家的产生与自然法的关系。他的自然法理论为以后自然法的发展提供了认识的基础,更为近代法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理性基础。
(三)自然法的多向度理性
其一,战争的合法性。格老秀斯通过探讨符合自然法原则的规则,并在分析这些规则的基础上得出了一些应用性的结论。西塞罗在《论善与恶的界限》中提到,每一个动物在其出生之日起就存在着自我照料、对其生存和健康的保护、对毁灭和引起死亡威胁的任何事物的憎恨,他把这些原初的自然状态称作“自然原则”。因而,在自然状态下保全自己,不与自然相违背成为首要的义务。那么,如果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保全我们的生命和身体的完整,或者为了获得一些生存和生活的必需品的话,那么这些都是与自然法原则相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使用武力,就绝不会与自然法原则相冲突,因为,所有的动物天生被赋予力量,是为了保全和保护他们自己,这是与自然法原则相一致的。所以,自然法原则中的任何内容都绝不会反对战争,在一定意义上,它们中的任何部分事实上都支持发动战争。
格老秀斯认为发动战争的理由是保护人身和财产,而这些理由根据自然法原则又是正当的,这类战争针对侵略者是合法的,当这种被侵略的危险客观存在而非主观想象时,那么杀死任何意欲残害某人性命的人都是合法的。
其二,惩罚的合法性。拉达曼修斯法则中有一项规定,“使任何犯下罪过的人承受同等程度的痛苦是正当的”。上帝是维护正义的,它报复所有触犯刑法的行为。希勒克勒斯曾指出正义的一个特性,“对所有恶行的治疗与补救”。所有惩罚都可以被认为是符合正义的,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一个惩罚意味着一项债务,这项债务就是因为自己的损害来赔偿受害人,作恶的罪犯必然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只是这种惩罚只能由有权之人做出。关于惩罚的目的,格老秀斯也谈到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一直以来宽恕他人是神和人性格中最优秀的品质之一。柏拉图说过,正义施加惩罚并不是为了已经实施且无法挽回的邪恶行为,相反,它是要阻止相似事情的再次发生。还有一些观点认为,惩罚的目的是复仇。自然法原则中规定,任何人不能作出伤害他人的任何行为,除非是出于某种明显和重要的利益。而复仇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利益,因而复仇是不人道的,它是主动伤害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因而,惩罚的目的是复仇的话是不正当的,也是不符合自然法的。
其三,获得领土、财产的合法性。自然法认可在正义战争中的捕获行为,这可以被视为债的履行,或者被称为对入侵者的一种惩罚。小涅尔瓦认为,财产可以经由占有而取得,比如从海陆获得的野生动物以及天空中的飞鸟,战争中的取得也是如此,一经捕获便立即成为最初捕获者的财产。只是,这种取得必须经过一定合理时间的占有之后才成立。不动产通常由一些公共行为取得,比如,将军队开进敌国,或者设置要塞。而任何动产都可以获取。
二、格老秀斯与中世纪自然法理论的异同
格老秀斯的自然法理论是建立在古代自然法学以及经院哲学基础之上的,因而,格老秀斯的自然法理论与中世纪思想家的自然法理论有共通之处。他们都承认人类理性的作用,认为理性因素是自然法的根源。其不同之处表现为:
其一,特性不同。中世纪自然法理论主要表现为一种“神性”的自然法,其本质上是一种神学的经院主义的自然法,其典型代表人是托马斯阿奎那,他的自然法理论同时具有奥古斯丁的神学法律思想理论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自然法理论的特性。而格老秀斯的自然法理论已然从神学中剥离出来,是自然法理论的一个分水岭,格老秀斯的自然法的最根本的特征,就在于它是理性主义的,他汲取了托马斯阿奎那和亚里士多德思想中的理性因素,排除了朴素的、先验的、直观的自然主义和蒙昧荒诞的神学主义,他主张自然法是在理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理性也就是自然法,即使上帝不存在,自然法依然存在。有关于此,凯利认为,16世纪,新教改革的影响力所及,“自然法”学说已经开始驱除经院神学的标签及与其之联系,并代之以“理性”话语。在17世纪,某种世俗化的自然法成为了法学理论赖以取得可观进展的基础。作为对自然法的释义,洛克说“理性就是自然法”[3]。
其二,内容不同。中世纪自然法理论主张法律是必要的,法律是理性的外在,是行为的尺度,法律创设的目的是为了全社会幸福的安排,他们认为这种理性是上帝的理性,人是通过参悟上帝的理性而制定了原则、规则,这些原则、规则就是自然法。他们的自然法是从神意出发并以神意为归宿;自然法不再是最高的法,法现象根植于自然和神,自然法服从于神法;人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格老秀斯的自然法理论内容体现为,主张法现象根植于人的理性,自然法来源于理性。马里旦认为:“每一类法律都是理性的作品,所以自然法的渊源也必然是理性:不是人类理性而是固有理性(Subsistent Reason),是与终极真理(First Truth)关联的理智(Intelligence),永恒法就是从它而来。”[4]
其三,程度不同。中世纪自然法理论也诉诸理性,其主张自然法来源于理性,而格老秀斯赋予理性含义的程度却比中世纪自然法理论深很多。理性在格老秀斯自然法理论中被赋予了新意。理性不再是存在于人之外,而是人的自然性中所固有的东西,格老秀斯自然法理论中的理性不再是古典时期的宇宙理性,不是神启示的理性,而是人所独立运用的理性,是典型的人学[5]。
其四,独特之处。格老秀斯所处的时代介于两个伟大时代的过渡时期,他依然与前一个时代保持着很多联系,但也致力于向近代的自然法理论传达其有别于前代的标志:唯理主义、社会性、具体的政治目标。这一切都类似于笛卡尔[6]68。格老秀斯第一个使自然法从中世纪的神学中剥离出来,从人的理性来论证自然法,认为理性就是自然法;格老秀斯的自然法理论涉及到了自然状态、自然权利等理论,建立了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他提出了契约理论,主张国家的起源是社会契约,主张人类具有社会性,这种社会性就要求有一个机构来管理,这个机构就是国家;格老秀斯坚持理性的看待基督教的基本原则,他通过一些方式强调了自然权利与基督教的信仰的分离。比如,在与苏亚莱的鲜明对比中,格老秀斯坚决否认了自然法能与旧约和新约等同,而苏亚莱则认为摩西十诫中包含了自然法[7]。
三、格老秀斯自然法理论的贡献及缺陷
格老秀斯的自然法理论基本上是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格老秀斯的自然法理论中总会看到前人的影子,他的自然法理论的主要贡献有:
其一,理论与现实的有机枢连。在《论捕获法》中“自然法”就是格老秀斯为荷兰东印度公司进行辩护的理论武器。他主张,根据自然法,浩瀚无垠的海洋由所有人共有,海洋资源是公有财产,任何个人、机构、国家都无权将海洋资源据为己有,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甚至教皇都不能剥夺荷兰在海上自由航行、捕鱼和贸易的自然权利。在《战争与和平法》中,格老秀斯要解决的是如何进行理性战争而不是如何避免战争。格老秀斯以自然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尊重和保护他人的基本权利”为理论依据,对战争的原因、目的、正义与非正义、合法与非法等战争中的一般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叙述,此外,他还将自然法理论扩展到国际法领域。施特劳斯教授还尊称他为“一个真正天资独厚的奇才和实干家”[8]。格老秀斯在法理学上的重要地位也是建立在他关于法律是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观念上的,他对国际法所做的贡献超出了政治理论史的范围。在17世纪,有一个定论认为,他应诉诸公认的根本法或自然法理念,而这种根本法或自然法乃是所有国家国内法的基础,并且因为其所固有的正义而对所有的民族以及对臣民和统治者都具有约束力[9]99。
其二,社会契约理论。主张国家的起源是社会契约,以自然法理论为基础,他创建了一套国家形成、职能、统治的政治理论。格老秀斯主张自然法是“沉默的法”,其本身不具有约束力和强制性,而为了解决人本身欲望性质与普遍遵守自然法之间的矛盾才产生了万国法(国家法),其实,国家法就是将自然法与人法揉和在一起,使自然法具有约束力。
其三,自然法的剥离。首先,格老秀斯将传统自然法中蒙昧的神性主义剥离出去,尽管格老秀斯承认自然法来源于上帝的意志,但是他更加强调在上帝指导下的人的理性是自然法本身,他承认的只是上帝创造了人类,使人类具有了理性这一事实,上帝改变不了人的理性。其次,格老秀斯将不具有实质约束性的道德戒律从自然法中剥离出去。自然法虽然不具有强制性但是它的内在约束力还是有的,而道德并不是法律,最终,只有体现财产权的一些基本原则被认为是自然法的一部分。
其四,格老秀斯的自然法理论之所以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还体现在方法论上,他为达致一整套构成政治安排和实在法条款之基础的命题提供了一种理性的方法,这种方法在17世纪则被认为是一种科学的方法[9]103。
纵观《战争与和平法》这部著作,其理论缺陷也较为明显:其一,他认为自然法是一种“沉默的法”它本身并不具有强制性,它的约束力仅表现在人们的自觉遵守上,而人类功利性、自私性的一种欲望与遵守自然法之间始终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矛盾会进一步体现出来;使自然法具有约束力那么自然又成了人法,由于人主观上的一些限制,矛盾也会增多。其二,自然法是一种先验之法,它具有不确定性,应该说现行法律的最终根源是一种假设、一种经验,谁也不能说尽自然法的所有原则,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永恒、普遍性质的自然法必然会受到冲击也许会被舆论的力量从自然法原则中剔除出去。其三,格老秀斯并没有承认人的理性的完整自主乃是自然法的唯一而不仅仅是最近的源头。他认为上帝是自然法的最高渊源,他同样认为《圣经》作为知识的一个原则与理性居于同一地位。格老秀斯在很大程度上仍生活于传统之中,从而能够以自然神论的方式解释自然法[6]65。
四、结 语
虽然格老秀斯的自然法理论存有缺陷,但是,无论如何,格老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中体现的自然法原则代表了他那个时代的进步要求,是一种理性探索,不仅为后世提供了一种理论,而且具有方法论意义,他的国际法理论也为后代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在中国法治发展的今天,如何走出一条更加稳固、完美的法治道路,需要法学者的研究探索,而格老秀斯的理论可以说是一种进行研究的基础,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也会成为巨人。
参考文献:
[1] [荷]格老秀斯.战争与和平法[M].何勤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 [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45.
[3] [爱尔兰]约翰×莫里斯×凯利.西方法律思想简史[M].王笑红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90.
[4] [法]雅克·马里旦.自然法——理论与实践的反思[M].鞠成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32.
[5] 申建林.自然法理论的演进[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29.
[6] [德]海因里希·罗门.自然法的观念史和哲学[M].姚中秋,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7] [丹]努德·哈孔森.自然法与道德哲学——从格老秀斯到苏格兰启蒙运动[M].马庆,刘科,译,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30.
[8] 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M].中文版.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455.
[9] [美]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M].邓正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Grotius and Natural Law Theory——Reading “the Law of War and Peace”
XIAO Ling-shan
(Department of Law,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Tianjin 300134, China)
Abstract:The concept of natural law has a long history in the West with influence on the western democracy, the rule of law. Dozens of great thinkers, Hugo Grotius ( 1583-1645) is one of them who give the traditional natural law theory with a new perspective of thinking, reasoning methods and theoretical system, thus developing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theological doctrine and moral precepts from the natural law leaving behind the wealth of law theory. He proposed the intelligence of the act of war and peace known as modern rationalism as the founder of the natural law and the moder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Key words:Natural law; Grotius; act of war and peace
中图分类号:D9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395(2016)04-0109-06
收稿日期:2015-12-08
作者简介:肖灵姗(1991—),女,南开大学法理学硕士,天津商业大学教师,主要从事法学理论、法史学研究。